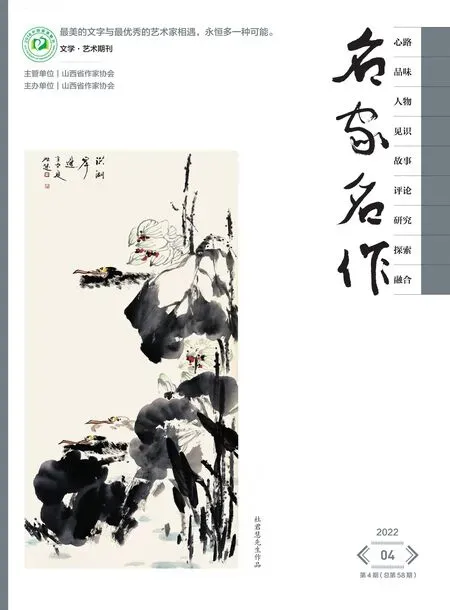书法接受美学研究现状及趋势考论
孙晨芙
近十年来,接受美学在有识学者的引领下受到越来越多书法研究者的重视,著作、期刊、硕博论文在接受层面日渐丰富。书法研究不应只聚焦于书家、书作、书论的分析,还应重视书家、作品、理论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接受者的审美经验。借鉴西方理论,用新视角看待中华传统艺术,以丰富书法研究之面貌。
一、接受美学的渊源
接受美学是颠覆传统美学形式的新型文化观,它强调接受者在整个艺术创作活动中的必然存在与重要作用。二战后,人们对现实生活发出质疑,一元观会激起社会动荡,多元思维方能长久,绝对和封闭不是解决之法,兼容与开放才能繁荣发展;理论家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思考,旧有的文化价值观已不足以解决人文社科的现状问题,文学史变成了纯粹记述作者、作品的学科,他们不希望史学研究仅仅是史料的堆砌或成为大事年表。科学主义已不能独占鳌头,需结合人文主义加以阐释。
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姚斯、伊瑟尔等学者受到哲学、现代释义学、现象学、形式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在新旧交替的大环境中率先阐发了接受美学理论,后经其学生及美国理论家深入演绎,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被广泛运用。
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学的理论被译者引入中国,早期是纯粹对接受美学相关文献进行翻译,如周宁、金元浦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后被借鉴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美学、艺术学等学科中。书法既有“史”的一面,“技”的一面,还有“论”的一面,它不是单一、片面的学科。书法史不应只是某书家或作品的分析,更需在同一时代中寻求共性,在不同时代中追溯经典。毛万宝先生在20年前就看到了书法接受的重要性,他说:“书法学体系陷入的第二个文化困境是缺乏应有的接受屏幕。没有观众的表演艺术是令人扫兴的。同样,没有读者的书法学体系也让人感到悲哀。”书法研究者日渐重视接受视角在书法领域中的推动作用,书法经典的发展历程中需要有书法接受这一支。单独存在的书法家是独立个体,因为有了接受者的推崇,这些书家没有被时代遗忘,历久弥新、万古流芳;单独存在的书法作品是一件物品,因为有了接受者的摹写探讨,这些作品因时相传,甚至传拓再版;单独存在的书法理论是文字堆积,因为有了接受者的学习研究,这些理论才能发挥更大价值。
二、书法接受美学研究现状析论
当代书法接受美学研究,主要分两个方向:一是用接受的视角去探讨书法作品、书论或书法家,此类研究现占据很大份额;二是围绕书法接受出现的问题与反思,因接受理论被引入书法学科时间不久,此类研究现在仍缺乏深刻见解。最早用“接受美学”来探讨书法的文章为郑军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中国书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此篇在1992年提出用接受美学的视角看待中国书法,用今天的视角看其中的观点无甚新意,在当时却具有很大前瞻性,毕竟其比《中国书法》杂志开办“书法研究方法论”的专栏探讨还早了3年。
接受美学在书法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21世纪后,此前也有著作、期刊、硕博论文提及接受,但体系还不完善。21世纪后,既有冠以“接受”之名的研究,亦有未名有实的接受研究,如刘恒《清代书家与〈兰亭序〉》、周睿《儒学与书道——清代碑学的发生与建构》、向彬《康有为眼中的〈爨龙颜碑〉》等。
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中统计,20世纪80年代提及书法接受的相关研究凤毛麟角,2000年之前,最多提及的一年是1997年,有20篇。在2000年至2010年,除2008年发文量有所下降外,整体相关发文量呈增长趋势,2010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有152篇。2011年后提及书法接受相关发文量一直呈上升趋势,在2013年至2015年,每年发文量在200篇左右。2018年、2019年是书法接受研究高产年,相关发文量为328篇,是2015年的1.547倍,是1983年的328倍。2020年发文量有所回落,但也有267篇,预测2021年与书法接受相关的研究可以达到300篇。此中统计为提及书法接受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专论书法接受的研究,此统计中,可以洞悉接受理论逐渐被书法研究者关注并运用。

图1 提及“书法接受”在中国知网的发文量趋势图

图2 中国知网中以“接受”冠名的发文量趋势图

图3 提及“书法接受”的学位授予单位分布图
笔者还在中国知网中整理了近年冠“接受”之名的书法研究共122篇,比对发现提及书法接受的研究与冠“接受”之名的书法研究虽然文章数量相差悬殊,但发表趋势非常类似。2015年以来,越来越多研究者投入接受领域,近年在北京、南京等地教授学者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学生也开始关注接受,研究接受史,这体现在各高校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及期刊文章发表上。
书法接受相关研究多集中于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其中高居榜首的是中国美术学院,这与范景中等先生积极引入西方美学关系密切。排行第二的学位授予单位是南京艺术学院,其中黄惇、徐利明、金丹、李彤、周睿等教授多有学生做书法接受相关的学位论文,如周睿教授的学生李霞2020年的学位论文为《〈曹全碑〉在清代的接受研究》,谭茹毓2021年的学位论文为《虞世南书法的接受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徐发《当代书法研究接受视角探论》一文,从理性视角出发,客观提出了现当代书法接受研究的问题,分析了书法接受的方法论。
三、书法接受美学研究价值探讨
接受美学启发我们看待书法史需结合作品创作的时代、创作的艺术家及作品本身进行梳理,如此研究书法的释义才能更全面。我们必须掌握众多一手资料,从原意中寻找书法的意义。现当代许多研究不能追本溯源,一家之言分析偏颇,会误导后世接受者,一人错,人人错。
这也提醒后世接受者要从客观视角做学问,有刨根问底的精神,抱着“问题”意识进行研究,切忌人云亦云,要保持本心。在自己的“视界”与前辈的“视界”之间找到平衡,此接受方向是从现代释义学中得到的启发。
艺术创作不是艺术家创作完成后就结束了,艺术创作的意义远超于此,它具有“空白”与“不确定性”,茵加尔登认为,对空白和未定性的填充越接近作者原意,也就意味着对作品质量与价值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入,这种审美理解就会更加正确一些。伽达默尔说:“艺术作品是包含其效果历史的作品。”“空白”和“不确定性”给了接受者无限遐想,艺术品的意义在历史中不断得到阐释和理解,艺术品的意义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例如东晋王羲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我们不能直击《兰亭序》的原貌,只有通过后代的勾摹或翻刻本才能体会其魏晋意趣。我们对《兰亭序》的理解并非来自一家之言,而是站在无数前辈的肩膀上体悟,尤其受《兰亭序》的“第一读者”唐太宗李世民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与高二适等学者的“兰亭论辩”再次将《兰亭序》带入大众视野。一幅书法作品之所以可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在每个时代中接受者对其都有新的解读。
造成郭沫若与高二适在《兰亭序》真伪上有分歧的原因是他们本身的政治观点、知识素养、认知方法、审美标准不一样,他们带着自己的认知和审美期待去评述作品时,就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样有争议、有故事的作品更有价值,正是这些接受者的贡献,才将其推向了高位。国外的评论环境相对有话语权,被“讨论”的作品会“一炮而红”,我国也需要这样有话语权的接受者,这就要求在接受时具有客观、全面的评价,这样大众才会信服,接受才有价值,被接受者的地位才能提升。
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是以文本为中心的,反对作者中心论。接受美学中文学的本体并未消失,读者的接受过程是读者对文学本体的接受过程,接受行为的研究离不开对作品的研究。创新的出现不仅仅是作者的功劳,同时也是接受者的贡献,由于接受者对旧有形式的审美疲劳和对新形式的渴望,推动着艺术家不断创新。反观当下书展,被选出的大多是中规中矩“不出错”的书法作品。接受者很难评述这样的作品,既无错又很难讲出其中意味。评审老师们时常也很惊诧自己选出的结果,因为每个评审老师有自己的“期待视野”,当一部书法作品完全与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吻合时,这部作品就索然无味,反之,如果一部作品超出了接受者的“期待视野”,这幅书法作品的艺术性便会显现出来。书法作品优秀与否取决于它是否具有革新“期待视野”的能力。一味囿于前人,只知模仿的作品是不具有艺术价值的,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写出真我,是每一位艺术家值得思考的问题。
接受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垂直接受,指不同时代接受者的接受情况,是从宏观角度看接受,我们称之为“历时性”;二是水平接受,指同一时代的接受者的接受情况,是从微观角度看接受,我们称之为“共时性”。在470年前,瓦萨里在《辉煌的复兴》中提出:“不仅要如实地记录一位君主或一个共和国所经历的枯燥乏味的事实,还要揭示那些导致人们成功或失败的意见、建议、决策和计划。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也就是说,历史的真正目的在于使人们变得审慎并懂得如何生活,另外,历史还可以通过重现过去发生的事情给人们带来快乐。”完整的书法史必须从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都深入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建立起新的书法史。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书法史并不是书法的本来面目,而是经过无数代接受者共同创造完成的。书法接受研究中,被探讨最多的当数王羲之,王羲之本人也很难想到,在后世书法中,他会有“书圣”的地位,他的作品会被追捧1600年之久。东晋后期,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的声誉高过其父,南北朝前期的宋、齐,直至梁武帝萧衍推出钟繇之前,一直是“小王”书风独领风骚,而梁武帝推出钟繇之后,王羲之介于两者之间的风格才昌明起来。隋朝短暂,处于南北书风渐融的态势,唐朝初期,李渊书学王褒,而王褒是“小王”书风的继承人,至李世民登基,在虞世南等人的影响下,李世民将王羲之推举到“书圣”的地位,自此在书法领域,甚至非专业的人民群众也对王羲之津津乐道。玄宗朝时,政通人和、百业俱兴,诗有李白、杜甫,文出韩愈、柳宗元,画是吴道子,雕塑为杨惠之,书法更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各体皆有新风入世,王献之在此时又一次被书家所重,虽然王羲之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王羲之一直在接受者的眼中和心中。
书法界可以被接受的人物、作品是有限的,现阶段的研究多焦在王羲之、颜真卿、米芾等经典书家,而作品多聚焦在《兰亭序》《寄侄稿》《张猛龙碑》《曹全碑》等耳熟能详、雅俗共赏的作品。造成这样的原因有三:一是作品本身具有潜能价值和传播意义,没有被时代淘汰,可以被不同时代的各种群体接受;二是因为有充足的资料留存,可供接受者研究,有些艺术并不是接受者不想研究,而是无从考据,难以研究;三是接受者需要经典来辅助现实,这些艺术可以满足他们的现实需求。
四、书法接受美学研究中现存的问题及启思
在现当代的书法接受美学中,笔者认为其存在着一些可修正之处。其一,大部分研究对欣赏者与批评者的称谓是“读者”,笔者认为改为“接受者”更妥当。“读者”的使用更适用于文学,尽管接受美学始于文学领域,但在书法领域中,欣赏者和批评者多通过看与评的形式,用“接受者”更为严谨。其二,现阶段的研究中,大多是探讨著名书家或书作在某一时期的接受问题,少有历时性的探讨,书法史需要从宏观角度来把握。当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相信,书法理论会愈发完善,会有越来越多学者投身其中,去建构更完善的书法理论。其三,因书法传播本身的困难而引发的书法接受的复杂性,拓本的版本、作品的真伪、翻刻的水平、保存的环境等因素都将影响、限制后世接受者的接受过程,这些困难需要接受者耐得住性情,用刨根问底的精神寻找真知。
现存的书法经典在刚现世的时候并不是“经典”,起初甚至是出于实用的目的,经典的价值是在接受、探讨中确立的,之所以流传,是因为融入了各个时代的思考构建。学术的发展正是在这条淘汰、争论、再淘汰、再争论的路上进步的,即使会有短期的鱼龙混杂,但真知的产生是值得的。学术的发展不需要一言堂,需要各抒己见,共同营造。接受者就是推动艺术进步的一大助力,艺术创作活动需要艺术家、艺术作品、接受者共同努力。真正的理论是大众的,陈振濂先生在1994年的文章中就提道:“没有大众接受屏幕的作品几乎不能算是作品,未被读者接受过的文本几乎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将接受美学引入书法领域的意义在于每个人是不同个体,每个个体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又有不一样的“期待视野”。每个接受者、每个时代的“期待视野”不同,书法史就会有更多层次。这会改变我们曾仅以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为中心的书法观,不同层面的不同观点有了合理的解释,我们会吸收各方观点,以营造一个客观、繁荣的书法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