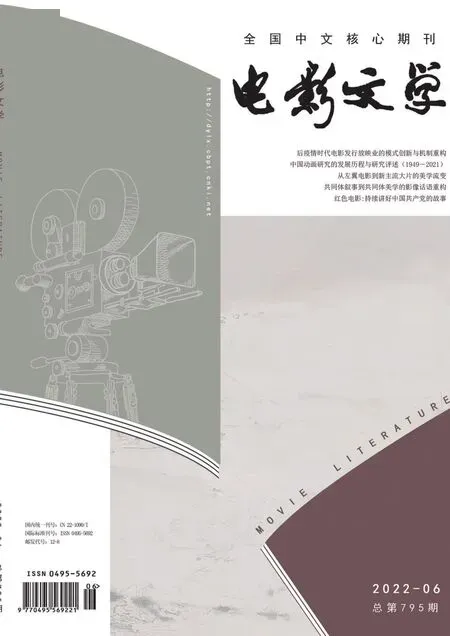从左翼电影到新主流大片的美学流变
陈丽君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 100024)
在100多年的中国电影史上,左翼电影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共产党首次参与中国电影工作,拍出了思想意识鲜明、题材内容丰实、时代色彩强烈的新电影,并从此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创作方向,使20世纪20年代受商业潮流左右的电影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进步之路,证明了通过电影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发言权是行之有效的,显示出进步力量的号召力,并影响了战后电影(1945—1949)和十七年电影(1949—1966)的创作。
改革开放之后,主旋律电影接续了左翼电影运动以来的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表达,但是由于说教意味较浓,并未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新世纪之后,伴随着电影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演变为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在最近几年以新主流大片的形式在中国银幕上大放异彩。新主流大片的特点在于影片中“国家的全球观念表达、国际空间呈现、一线明星出镜、紧张动作推进、起伏跌宕叙事、深层愿望满足等元素共同完成了新主流大片的整体结构。新主流大片也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产生了差异,成为一个新的创作现象”。
电影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左翼电影和新主流大片都以表达主流意识形态为主要任务和目标,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二者在表达方式、美学风格上也具有明显的不同。
一、社会揭露与国家建构
“社会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历史成果。社会本身,即处于生产关系中的人本身,即‘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本身,它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人与人的集合体、结合体、共同体。”“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和“国家”概念的解读可以看出,“社会”这一概念强调的是社会关系,而“国家”则是社会和民族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左翼电影运动更加侧重社会揭露,新主流大片则偏向于国家建构。
(一)左翼电影的社会揭露:对社会本质的暴露
之所以说左翼电影注重的是社会建构,一方面,是因为左翼电影以真实地揭示现实社会现实为主要目标和任务。20世纪30年代,社会矛盾突出,人与社会的关系异常紧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及社会观念,《啼笑因缘》这类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已经无法吸引当时的观众。观众向电影界发出“猛醒救国”的呼唤,要求在电影中看到反映现实真实状况的电影。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看到了电影阵地在宣传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性,积极参与电影创作。1931年,左翼剧联的《最近行动纲领》提出了左翼电影应当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描写无产阶级、农民群众的阶级斗争,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出路的主张。这一指导方针深刻地洞察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1932年7月左翼电影人创办的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在《代发刊词》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共产党的电影意识形态要求:‘中国的电影必定是被压迫民众的呼喊’”。
左翼电影最基本的特征是真实,其创作方法为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真实具体地反映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是其最基本的要求。在电影创作上,左翼电影人按照《最近行动纲领》的指导,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1932—1933年间,各电影公司纷纷转变作风,积极拍摄具有社会现实内容和爱国进步意义的影片。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工人、从底层阶级到小资产阶级到上层阶级、从男性到女性,左翼电影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深刻的揭露,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腐朽堕落的上层社会的讽刺和批判。
农民的生活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难以为继,《春蚕》展现了农村、农民“丰年成灾”的悲惨经历。城市工人不但要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还要面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香草美人》和《压迫》描写了工人的斗争;《上海二十四小时》表现都会生活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盐潮》表现了盐民的抗争;《渔光曲》表现了底层渔民家庭的破产和灭亡。知识分子站在社会的“十字街头”苦无出路,《时代的儿女》表现了在革命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和道路,《十字街头》批判了知识分子懦弱的性格,歌颂了积极的人生态度;《风云儿女》引导知识分子远离堕落享乐的生活,积极加入抗战的大潮。女性问题方面,《女性的呐喊》以包身工为题材表现女工受到的凌辱;《新女性》描写了女性知识分子在社会中面临的迫害,表达了女性的绝望;《神女》《马路天使》表现了妓女的血泪史;《脂粉市场》和《前程》则表现了女性的觉醒和独立。左翼电影呈现了全面的整体的社会,这个社会同时是一个悲剧性的社会,但是人物命运悲剧并非因为个人,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原因所导致的。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在阶层内部,当社会的悲剧加诸在底层人物身上的时候,底层之间通过相互扶持、抱团取暖来对抗上流阶级的迫害。底层民众的社会基础本就脆弱,日常生活勉强维持,所以根本经不起折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的磨难总是接踵而来。但是上层社会的压迫并没有淹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底层民众在共同的灾难面前,组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共渡难关。《马路天使》中底层人物的代表如吹喇叭的、卖唱的、卖报纸的、妓女等将彼此纳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人物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情感,生命的关联度更进一步。《风云儿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真正地体现了儒家倡导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十字街头》中的四个大学生,《上海二十四小时》中的老赵,《大路》中的修路工人,《小玩意》中围绕在华大嫂周围的村民等,都揭示了“只有穷人才能帮助穷人”的深刻道理。
总而言之,左翼电影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之下,塑造了各式人物,包括工人、农民、资本家、地主、市民等,底层民众受到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不同层面的压迫、剥削、迫害,而被迫走向悲惨的生活境地,揭露了悲剧性的、“吃人的社会”正是当时社会的本质。但是底层民众之间的互爱互助,又为愁云惨淡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亮色。
(二)新主流大片的国家建构:大国想象与国家话语建构
在新主流大片中,国家是一个整体,影片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更加着意塑造国家形象。和左翼电影不同,中国社会中人和社会的关系不再是新主流大片的主要内容,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的形象和价值观成为新主流电影主要的表达对象。通过对中国的重新言说和定义,不断强化对中国这一大国形象的确认。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的《东方学》揭示了西方人视角下的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新主流大片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东方的形象进行重新校正。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强盛、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世界格局重新调整的今天,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了更多话语权,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洗刷近代百年耻辱,刷新西方乃至国人对中华民族“东亚病夫”的认知,重新进行“大国”的自我定义。正如《战狼2》借冷锋之口,对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形象做出了回应,“老爹”轻蔑地讽刺中国“这种劣等民族永远是弱者”,但是冷锋以杀死老爹回应了老爹的妄言,非常解气而自豪地告知世界和观众:“那他妈是以前!”对中国的大国、强国身份进行了肯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主流大片在颠覆西方人认知中的落后、软弱、非理性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建构起强大、顽强、理性的大国形象。
首先,在新主流大片中,中国首要的责任是守护中国公民,尤其是当中国公民在海外遇险的时候,中国永远不会放弃她的任何一位公民。《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中人物行动的根本任务都是中国军人对于中国公民在海外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为了解救一个中国公民可以出动一支队伍,动用一艘军舰。为此,中国军人不得不应对极端艰难的作战环境,随时可能遭遇死亡。《战狼2》结尾传递给散落在世界各国的中国公民一个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也是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维护中国公民生命财产的决心。《红海行动》的片尾则再一次表态,强化了这一信息的真实度、可信度。
其次,中国是一个维护国际正义的国家。中国作为联全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立于世界之林,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与稳定,彰显了大国担当。《湄公河行动》中在泰国、缅甸、老挝对金三角放任自流,乃至同流合污的情况下,中国对金三角狠毒行为进行了彻底的打击。《红海行动》中的黄饼危机本与中国海军的营救任务无关,但是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全,中国海军小分队依然选择继续前进。此时的中国海军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保护伞,也是世界人民的保护伞。不仅如此,我国军人在维护国际正义的时候,并不会打着维护和平正义的旗号为所欲为,在他国战场上的进与退的前提都是遵循联合国的指示。
中国守护中国公民、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信心和基础来自不断增强的国家实力。我国具有先进的军事装备和一流的作战水平,我国的战舰始终是国民的后盾和堡垒,我国作战人员不畏艰险,团结协作,共同作战。在《战狼2》《红海行动》中我国军人在海外作战的时候,都有中国军舰在保驾护航。航母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航母几乎是对一个国家全部工业实力的总体考量。《红海行动》和《战狼2》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我国军舰进行了展示,在紧要关头也是中国航母及时出手才扭转了战局,拯救了绝大部分中国公民。这是中国力量显现的时刻,是国家信心的彰显。
新主流大片对我国大国形象的建构,建立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强盛的前提下,是对当代中国的真实呈现,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通过电影的表达,大国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二、戏剧冲突的不同法则
戏剧冲突是叙事类艺术的基本手段,早期中国影人就将电影称为“影戏”,认为电影是用影像的方式讲述戏剧故事,如中国电影的奠基人张石川、郑正秋就十分擅长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吸引观众。左翼电影和新主流电影同样继承了戏剧式的叙事法则,但是由于二者的社会基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戏剧冲突的运用法则也不同。
(一)左翼电影的累积式戏剧冲突
左翼电影以再现社会为主要目标,由于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斗争与矛盾,电影创作者将生活中的矛盾提炼为戏剧冲突,对生活给予了艺术化的处理。左翼电影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等为主要表现对象,其主要观众也是上海普通的工人、小市民等,这就要求左翼电影的表现手法必须是大众的。经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中国电影逐渐形成了一种大众化的审美标准:“它是娱乐的而又不仅是娱乐,它是教育的而又不仅是教育,它是审美的而又不仅是审美,它是营业的而又不仅是营业,它具有一种包容、兼顾、综合、均衡、全面、协调的素质。”早期的“影戏”观延续下来,以蔡楚生为代表,不仅在影片中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表达,而且“在注重市民观众的欣赏趣味和剧作叙事经验方面继承影戏传统的主要方面”,戏剧冲突就成了左翼电影叙事的基本法则,注重在叙事有头有尾的基础上,调动曲折的手段,强化情节的因果关系。
我们可以用“累积式戏剧冲突”来对左翼电影戏剧冲突的特点进行概括,它指的是人物在短时间内或者单位场景内同时面临诸多困境、打击、冲突等。人物首先面临一种困境,进而同时遭遇到其他困境,或者在处理这个困境时,生发出其他困境,使得困境往往接踵而至,且前一个困境尚未解决,后一个困境愈加严重,令人物招架不住,从而迎来被毁灭的命运。
这种累积式戏剧冲突,在左翼电影中表现充分。例如在《新女性》中,韦明因拒绝王博士的求爱,遭遇其报复,失去了音乐教员的职位。紧接着,韦明回家后就接到了银行催琴租的信件,韦明欠租三个月。小报记者也意图以金钱收买韦明,占有韦明。晚饭后,房东太太又来催收房租。三日后,银行按时来收琴,态度蛮横粗暴,韦明再一次受到了暴行。就在此时,韦明接到了姐姐关于自己女儿生病的电话,病情严重,须立马住院,而住院的费用如天文数字。无奈之下,韦明只能让女儿在家中苦熬。从韦明被学校辞退,到女儿病重危急,不过三日,而且在这种累积的暴行之中,韦明毫无喘息的余地和解决的能力,只能经受这一个又一个打击。
《新女性》通过音乐教员韦明的遭遇直观地体现了一个女性在万恶的社会中所经历的痛苦与绝望。累积式戏剧冲突在《新女性》中不仅是建构冲突的方式,也是影片的叙事结构,通过数个累积的戏剧冲突段落,一个女性在这个吃人的社会结束了她的一生。
在其他的左翼电影中,这种累积式戏剧冲突亦多处可见。《小玩意》中老华生病倒在路上,匆忙赶来的华大嫂着急忙慌只顾老华,却没有意识到才会走路的玉儿被人贩子抱走了,老华没有救活,儿子也不见了。再如《姊妹花》中,丈夫桃哥在工地遭遇意外,大宝预支工钱不得,偷金锁被发现后,慌乱中碰倒花瓶砸死了人,锒铛入狱,不仅桃哥的伤无法医治,由于失去了全部的劳动力,一家五口人的性命危在旦夕。
累积式戏剧冲突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由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底层民众的生活本就勉强维持,哪怕微妙的破坏都会给予其致命的打击。而底层民众解决问题的能力几乎为零,即使有邻居或者朋友的帮助,但是底层民众的社交圈同样是底层,并不能帮助其解决问题。因此,困难与危险接踵而至,最终酿成社会悲剧。左翼电影正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反映,影片让人物在单位场景或者事件内遭遇一个又一个障碍,因此,左翼电影的戏剧冲突以累积式戏剧冲突为主。累积式戏剧冲突揭露的是底层民众尤其是女性,在那个时代的绝望,从而更加深刻地表现出揭示万恶社会的主题。
(二)新主流大片的进阶式戏剧冲突
与左翼电影的累积式戏剧冲突相比,新主流大片更加善于运用进阶式戏剧冲突。所谓进阶式戏剧冲突,即在一个叙事段落里,人物只面对一个层面的冲突;解决完之后,再进入下一阶段;在下一阶段将会遭遇一个更大的冲突。这一冲突是对上一阶段冲突的升级或进化,直至主人公克服最后一个冲突,才实现终极目标。在每个叙事段落里,主要冲突也可能附加了一些次要冲突,但是次要冲突不属于第二种冲突,它与主要冲突属于一个层面,是主要冲突的附属物。
新主流大片的一个重要构成就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新世纪以来,在叙事层面,对我国电影商业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好莱坞电影。新主流大片吸收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以线性的戏剧结构层层推进,不断地深化矛盾。在影片的开头,一般会有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主人公生活的平衡或世界的秩序,麦基在《故事》中将这个“意外事件”称之为“激励事件”。激励事件必须彻底打破主人公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平衡,激发主人公深层次的心理欲望,因此,主人公唯一的目标就是恢复生活的平衡或者实现内心欲望,接下来故事的讲述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设置冲突。也就是说,这个终极目标是唯一的,而且“为了让故事产生纠葛,作者必须循序渐进地制造冲突,一直到线索的终点”,主人公面临的困境将越来越大,直至故事的高潮。
在新主流大片中,激励事件明确,主人公的目标明确,实现目标的过程冲突不断升级。《湄公河行动》的激励事件是中国船员无端被杀,主人公的目标是查明真相。查找真相的过程中,主人公的阶段性目标和面临的冲突非常清晰:抢救岩多帕,设局诱引皮尔、占蓬、依达、拿突等人上钩,活捉糯卡,杀死占蓬,13名船员沉冤昭雪。在战争题材中,冲突的升级主要表现为作战难度的加大,这又具体表现为对手方作战装备的增强、作战人员的增多和作战能力的提升,从而使得完成目标的难度不断加大。
这在《战狼2》和《红海行动》中也是如此。冷锋的主要任务是拯救陈博士及其余中国工人。第一场战斗的级别最低,冷锋只有三五个对手,武器是小型枪支,打斗过程虽然激烈,但是结果几乎没有悬念。第二场在华资工厂的战斗迅速升级,对方不仅发动突袭,还使用了大量先进武器及更多战斗人员。而冷锋由于在隔离区感染的病毒发作,实力衰减。两相对比,差距更大。第三场战斗,雇佣军不再受当地恐怖分子控制,冷锋及中国工人成了雇佣军的真正目标,矛盾加剧。战斗的级别也再次升级,作战人员不可数造成了数量极为庞大的认知,还动用了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我方具有作战能力的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而敌军还在不断涌来,生存的希望渺茫。
新主流大片的叙事和人物都要按照国际大片的模式操作……要有快速突进的矛盾冲突、跌宕起伏的故事节奏,还要有起承转合的故事发展。进阶式戏剧冲突对应的是线性的思维,即一对一地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它更能够适应影片的快节奏叙事,不断强化观众的观影情绪,并随着剧情高潮的到来,达到观众情绪的高潮,这也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主要手段。
三、影像表意与视觉奇观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画面是电影最为重要的表达手段。在无声电影时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画面的表达功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新的技术的发展,更加强化了电影画面表情达意的作用。在画面的表现上,左翼电影和新主流大片各有不同。
(一)左翼电影的影像表意
无声电影经过20世纪头十年至20年代的长足发展,曾产生过一批在视觉表现上较突出的作品,3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创作者经验的累积以及个人艺术化的表达,电影艺术也迎来了自己的高峰,在剧作、摄影、剪辑、表演方面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电影的影像表现能力大大增强,因此,很合理地产生了《神女》《小玩意》《上海二十四小时》《马路天使》《风云儿女》这类在视觉表现方面较为突出的影片。
同时,左翼电影更多地接受了苏联电影思想的影响,他们不仅从苏联电影学习表现革命思想的经验,而且学习了蒙太奇的电影思维方法和艺术表现技巧,在影片创作中自觉地对电影蒙太奇运用做了大量探索,通过对比、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再加上对镜头组接方式的探索,创造了大批独具深刻社会意义的画面,为影片的叙事和社会主题服务。
左翼电影擅长揭示阶层之间的对比,对比蒙太奇在左翼电影中运用自如。在《大路》中,影片将工人们简单的餐食与胡买办成堆的山珍海味相对比;在《小玩意》中,成堆出现的洋娃娃、乒乓球与华大嫂单个的手工玩具形成对比,这也是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和手工制作的对比。《风云儿女》的最后部分,战争再次发生,影片有两个对比镜头,前一个镜头是普通百姓逃跑时的混乱脚步,后一个镜头是中国军人整齐统一有力的步伐,在对比中强调了中国军人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希望。除了镜头的对比,对比蒙太奇还运用在影片的结构上,如《上海二十四小时》《新旧上海》《姊妹花》等影片中阶层的对比成为影片的主线,构成影片的结构。
左翼电影还擅长象征手法的运用。“桃花”在左翼电影中是重要的象征意象,在《桃花泣血记》中象征着淳朴的做人品质和纯洁的爱情,在《劫后桃花》中象征着“庭院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的繁华落幕。《马路天使》中的喇叭则象征着底层人民的凝聚力,尤其是当喇叭声响起的时候,散落在各处的底层人民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小喇叭身后,喇叭就是旗帜,喇叭就是号角。《小玩意》中的飞机坦克大炮本是玩具,但是当它叠印着真实的帝国主义的坦克和飞机大炮,并配合着字幕“起初,华大嫂和珠儿海以为外洋来的飞机兵船小玩具,至多不过使他们和许多靠手指吃饭的人少吃几口饭而已……直到某一天的晚上……”时,小玩具便象征着帝国主义从经济侵略到军事侵略的本质。
隐喻暗示手法的运用。《神女》通过流氓的胯下拍摄神女母子,隐喻着妓女的血泪史。阮玲玉饰演的妓女忍辱负重出卖自己的肉体,但是流氓强盗对她的欺辱不仅在肉体上,还要霸占她的整个人生,这样极具表现力的镜头进一步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小玩意》的结尾部分,新年的烟火和战争的炮火暗示着东西方国运和军事实力变化的原因。火药本是中国人发明,中国人将之用于生活娱乐,新年的烟火热闹非凡;西方人将之用于兵器,发动了残酷的战争,从此改变了东西方的命运。战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一个充满朝气的华大嫂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没有生机的人。
对比、象征、隐喻、暗示手法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在以内容为重的左翼电影中,这样的技术手法的运用都是为影片的社会主题所服务的,从而使得影片对社会本质的揭露更加具有说服力,更加深入人心。
(二)新主流大片的视觉奇观
20世纪30年代由于特定的时代诉求,意识形态表达是电影最为重要的任务,但是软性电影论者则提出了“形式美学论”和“娱乐本位电影观”。形式美学论认为“怎样描写比描写什么更重要”,娱乐本位电影观则提出“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激凌,是给心灵的沙发椅”,由于软性电影论对社会现实危机的无视,从而在客观上迎合了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引发了软性电影与左翼电影漫长而激烈的对战。
然而,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于当下再次审视软性电影论的时候,可以发现软性电影论对于形式和娱乐的追求还是有一定合理之处的,将意识形态通过一定的形式传达出来可以更好地吸引观众,这一过程正好可以体现在主旋律电影到新主流大片的转变中。变革后新主流大片的市场反应,证明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是合理而正确的。
新主流大片吸引观众的元素有很多,除了上文所述进阶式戏剧冲突的紧张刺激之外,视觉奇观也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快感。与左翼电影的影像表意作用于观众的意识形态不同,视觉奇观强化了视觉效果的冲击力,满足的是观众表层的直接的感官享受。学者列昂·葛瑞威奇将视觉奇观带给观众的吸引称之为数字吸引力,认为电脑成像效应和立体呈现激发了某种与火车效应相同的电影经验。
视觉奇观的营造以吸引观众的画面为主,创作者合理利用各项技术,打造出极具吸引力和刺激的电影影像。首先就是数字特效带来的超真实影像。以《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为代表的新主流大片正是在把握了数字技术之后,给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数字特效强化了视觉真实,它可以将现实生活中人眼不易抓取的细节放慢、放大,制造出罕见的真实感。例如《红海行动》中的“子弹时间”,影片以慢镜头细致地展现了一颗炮弹打出去后的运行轨迹,满足了观众的想象,打造了一动一静的节奏效果。
其次,视觉奇观还体现在新主流大片为了适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镜头节奏越来越快,而这种“快”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镜头时间越来越短,尤其是动作段落,以短镜头快速切换为主,展现了动作的复杂性。二是单个镜头内部的运动越来越复杂,包括摄影机运动和镜头内容的运动。单个镜头内的摄影机运动可以是推、拉、摇、移、跟、升、降的不同组合,实现了单个镜头的内部剪辑。镜头内容的运动主要表现为人物动作的瞬时变化。快节奏的镜头变化,挑战了观众的观看习惯,在吸引观众的审美注意方面确实颇有收获,观众为了抓住镜头中的每个细节,就无从分心,因为一旦分心,就会错失很多细节。
科技的进步带来了影像创造的更多可能,新主流大片在影像方面的自我追求也是对观众审美需求的更大满足。尽管视觉奇观作用的是观众表层的直接的感官享受,但是只有先吸引了观众,才能将影片的意识形态在更大范围内传播,收获更佳的传播效果。
结 语
比较左翼电影和新主流大片的美学风格的差异,犹如在不同年代之间穿梭,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人们对电影的不同诉求,也是人们对电影本质的不同把握。左翼电影和新主流大片都对电影意识形态功能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但是电影的时代使命依然赋予了两种电影不同的美学追求,无论是左翼电影的累积式戏剧冲突和更加突出的影像表意,还是新主流大片的进阶式戏剧冲突与视觉奇观,它们都服务于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达——左翼电影的社会建构和新主流大片的国家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