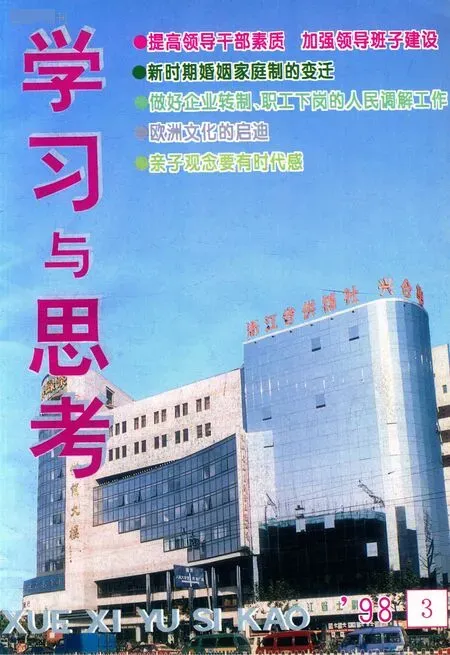再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
赵家祥
提 要:“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是正确理解马克思讲的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关键问题。从这个关键问题的普遍意义上说,即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上说,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否定的否定”过程,可以归结为: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更高级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这个关键问题的特殊意义上说,即从人类历史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说,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否定的否定”过程可以归结为: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个人所有制——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根据《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讲法,就是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对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歪曲,并且阐述了自己对“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理解,他的理解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本来意义。
我之所以把这篇文章的题目称为“再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在《理论视野》杂志2013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历史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短文。近些年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感到这篇文章没有把马克思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讲深讲透,所以有“再论”的必要。其二,最近看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十卷转载的几位学者论述“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文章,深感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争议颇多,分歧极大,学者们虽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理解,有些理解颇有见地,但总的看来,也还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深讲透,因此也有“再论”的必要。
一、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上考察“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结合与分离”的“否定的否定”过程
“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是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分为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方面。其一,从普遍意义上说,就是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上考察关于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二,从特殊意义上说,就是从人类历史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考察关于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就是经常把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论述的。正确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必须紧紧抓住“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关键问题,始终不能离开这个关键问题,从其他方面去理解和说明。如果离开这个关键问题从其他方面去理解和说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必定会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生出许多枝节问题,把问题搞得混乱不堪,歧义纷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章“货币资本的循环”中,就是从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相结合的角度考察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的。他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劳动者属于劳动的主观条件,生产资料属于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劳动者个人同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生产活动的,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活动,而二者结合的不同方式和方法,就形成各种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我们知道,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区分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标志。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它决定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产品的分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性质就是区分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不同的经济时期”,就是指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形态,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我们首先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角度考察“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资料是各个共同体(如氏族公社和部落等)成员的集体财产,各个共同体成员利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劳动,这种劳动者个人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就形成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不同地区的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也有所区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章中,曾经讲过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和日耳曼的三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的共同点和区别。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和奴隶是社会的两大阶级。奴隶主是剥削者,奴隶是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奴隶作为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甚至奴隶本人也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和役畜没有什么区别。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两个因素是分离的。奴隶在奴隶主的监督和皮鞭下,利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劳动产品全部归奴隶主所有,奴隶主只给予奴隶勉强维持其生命的生活资料,这种劳动者个人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就形成奴隶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在封建社会,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或农奴是劳动者,地主或农奴主是剥削者。地主或农奴主占有土地,农民或农奴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这两个因素是分离的。无地少地的农民或农奴,只有使用地主或农奴主的土地从事生产劳动,才能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过程。农民或农奴要向地主或农奴主缴纳地租,这种地租有三种形式,即劳动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种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就形成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则一无所有,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这两个因素是分离的,工人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劳动,才能在资本家那里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从而形成现实的生产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种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就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分工与协作,使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实现了劳动者个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劳动者个人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就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把上述五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即五种经济的社会形态分为三大阶段或称三大时期。第一阶段是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第二阶段是奴隶社会的、封建社会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恩格斯把这三大阶段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否定的否定”过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是对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的否定,这是第一个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是对上述三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是对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的重建,但这不是恢复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而是在更高级的形式上对劳动者个人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的重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了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说:“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越过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还是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决不会成为生产的束缚,恰恰相反,它会使生产摆脱束缚,并且会使现代的化学发现和机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个“否定的否定”过程,是原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被三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所否定、这三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又被未来社会的更高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所否定的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否定的否定”过程。这个“否定的否定”过程可以简要地归结为如下的公式:原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三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更高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
二、从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考察“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结合与分离”的“否定的否定”过程
现在我们从人类历史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考察“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需要考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的有关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说:“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者丧失生产资料,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让劳动者使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劳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只有在劳动能力本身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被它的所有者,即活的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出售时,货币才能购买劳动能力。条件是,劳动能力的所有者首先要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能够把它作为商品来支配。为此,他还必须是自由的劳动能力所有者。否则,他就不能把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这里说的“劳动能力”,就是《资本论》中所说的“劳动力”。如果货币所有者能够用货币交换活的劳动能力,或者说,向劳动能力所有者购买活的劳动能力,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那么,只有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商品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找到自由的工人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或者说,货币所有者才能转化为资本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在流通中、在市场上找到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自由的工人或卖者。因此,资本关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表示,资本关系只有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才能出现。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历史上一定的经济关系,表现为属于经济发展即社会生产的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系。”
第二,劳动者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成为除去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这是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的。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对小农的剥夺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当时,“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强行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个体农民或自耕农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个历史过程充分说明,对个体农民或自耕农的生产资料的剥夺使其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制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那时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和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使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种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在讲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被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公有制所否定以后,指出这个过程是一个“否定的否定”的过程。他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我在第一个问题中所讲的“否定的否定”过程,是从原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到三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再到未来社会的更高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这个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否定的否定”;马克思上述这段话所讲的“否定的否定”过程,则是人类历史一个特定发展阶段上的“否定的否定”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被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又被未来社会的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所否定的“否定的否定”过程。从“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结合与分离”的演变过程来看,可以把这个“否定的否定”过程简要地概括为如下的公式: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个人所有制”——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资本主义所有制——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个人所有制”。
在本文开头我就谈到,对马克思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在国内外理论界争议颇多,分歧极大。有学者在研究综述中把各种不同理解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重建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二是指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三是指重建人人有份的私有制;四是指重建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权;五是指重建人人有份的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我认为,这几种看法虽然各有某些合理之处,但都没有抓住“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正确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关键问题,因而都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把私有制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他指出:“私有制作为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中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两种不同的私有制相混同的错误观点时指出:“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私有制的。我认为,如果“从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分析“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断,就会相当容易地理解其含义。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论断,无非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结合“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即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这种“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所有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即相结合的“个人所有制”。因为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的所有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每一个劳动者个人都是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所有者,每一个劳动者个人都在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上重新实现了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所以马克思说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或“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十分清楚明白的道理,用不着转很多圈子去说明,或者说,用不着把本来简单明白的问题弄得复杂难懂,模糊不清。
如果根据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相关论述,就更容易准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现把法文版的中文译本的相关论述引证如下:“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占有,是这种仅仅作为独立的个体劳动的必然结果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法文版的这段论述与前面引述的德文版第四卷的相关论述相比,主要有两处改动:第一处是把“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改为“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这说明“私有制”与“劳动者的私有制”是不同的,“私有制”有多种形式,它包括奴隶制的私有制、封建制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以及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体私有制等等;“劳动者的私有制”是指“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已经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当然不能再去重新建立。第二处是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改为“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是不同的。“个人所有制”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奴隶主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封建主或地主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资本家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等等,都可以称为“个人所有制”;只有“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才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这种所有制与其他“个人所有制”的区别,而且体现了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它的重新建立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而不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本身的重建。之所以不能重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本身,是因为这种私有制虽然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但是它有非常大的局限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
三、全面评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所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讲的从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再到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否定的否定”过程,遭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攻击。杜林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深刻批判了杜林对马克思所讲的“否定的否定”过程的攻击。杜林在《哲学教程》中诬蔑马克思所讲的“否定的否定”过程,是靠“辩证法的拐杖”得出的,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辩证法的拐杖在这里起了“助产婆”的作用。他说:“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然而是在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更高形式上的重新建立。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这样,剥夺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杜林的这些论述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论断的恶意歪曲和诬蔑。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首先用“原始积累的秘密”、“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工业资本家的产生”等六节,详细论述了从劳动者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否定、再到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客观历史过程,最后才在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把这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归结为“否定的否定”的过程。这个“否定的否定”的过程的得出,根本没有借助所谓的“辩证法的拐杖”,更没有借助“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助产婆的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说:“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他说的就是这些。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恩格斯的论述说明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它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根本不同;说明了辩证法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证明的工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为什么要把“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使用“否定的否定”这种带有黑格尔辩证法色彩的“表达方式”呢?这与当时一些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不公正态度密切相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既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和唯心主义实质,又肯定了他的辩证法中包含着“合理内核”。恩格斯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写的“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有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既彻底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性质,又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利用了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的“表达方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含义的理解也不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本意。恩格斯在引证了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以后说:“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恩格斯认为,重新建立的“社会所有制”,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指的是消费品的所有制。恩格斯的这个理解显然存在不妥之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建立“社会所有制”与“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法文版中的提法)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的提法,或者说,“社会所有制”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而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建立“社会所有制”与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成了两件不同的事情,前者是关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属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是关于消费品的分配,属于产品的分配方式。众所周知,马克思历来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产品的分配方式看作是生产关系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对产品的分配方式起决定作用,从来没有把二者混淆起来,更没有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与消费品的分配方式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看作是等同的。而且在任何社会形态中,个人通过产品的分配分得的消费品,都属于个人所有,归个人消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莫不如此,没有例外。所以对于消费品归谁所有的问题,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消费品始终归消费者个人所有,不存在是否需要重新建立“消费品的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为了防止人们对他的论述产生误解,特意声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如果认为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重新建立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这显然不是马克思论断的原意,而且于理不通。马克思讲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否定的否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应该插入“消费品的分配”问题。这个道理恩格斯应该是十分清楚的。既然如此,恩格斯为什么还会违背他的一贯思想,对马克思的论断发生误解呢?我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恩格斯没有从“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个关键问题上去理解马克思的论断。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从“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历史演变过程方面理解马克思的那个论断,才能正确理解其含义。
另外,恩格斯之所以对马克思的那个论断发生误解,很可能还与他把那个论断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的一段论述相联系有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的那段论述是这样的: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就是指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劳动的总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部分。生产资料仍然归社会全体成员所有,用于扩大的再生产;生活资料作为消费品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社会成员分到的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这里讲的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讲的“劳动者个人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结合与分离”的“否定的否定”过程不是一回事,不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这段论述去理解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有关论断,可能也是造成他对第二十四章的那个论断发生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