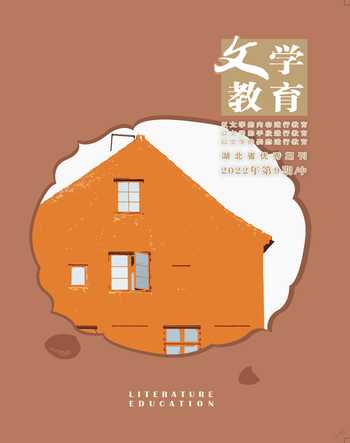《哈扎尔辞典》中的共同体意识
梅雪 李水霞
内容摘要:米洛拉德·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中依托哈扎尔民族面临的宗教论辩、历史与民族的流散失落,给出特有的共同体实践。从“绿书”中知识巨人阿丹·鲁阿尼的重构,到以梦境为基础实现经验交互的捕梦教派、现代社会中流散的犹太家族,这些探索虽然各有优缺,但作为共性强调的“沟通”“共同”,无不体现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关切。本文拟结合共同体理论,分析帕维奇在《哈扎尔辞典》中进行的共同体实践,总结其中问题并寻找解决之道。
关键词:米洛拉德·帕维奇 《哈扎尔辞典》 共同体
米洛拉德·帕维奇是塞尔维亚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美国、欧洲、巴西学者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于1984年发表的小说《哈扎尔辞典》以帕维奇追求的叙事迷宫为基础,通过阿勃拉姆·勃朗科维奇-(撒母耳·合罕/库洛斯)-苏克博士的轮回重复,将散于过去与未来的记述以暗线串连,于文本中呈现了“百科全书式的神通和困局”,开创“辞典小说”之先河。
在中国,《哈扎尔辞典》有关的学术研究整体较少:截至2021年9月,以“《哈扎尔辞典》”及“哈扎尔辞典”为关键词在知网检索,共有期刊及硕博士论文54篇;相关的西方文学介绍书籍,如《20世纪西方文学明珠》等,对《哈扎尔辞典》的介绍也多流于只言片语、不够深入。除作家陈丹燕的散文集《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在作家生活、行动、思想转变等方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地资料外,大部分的资料与论文集中于《哈扎尔辞典》的形式、人物形象、创作与技巧分析等领域,类型较为单一、亟待拓展。有关《哈扎尔辞典》与共同体、针对《哈扎尔辞典》中的共同体形式展开探索的学术研究,目前暂未收录。
米洛拉德·帕维奇以他精妙的想象与笔触,将他对时局变化中有关国家政治变迁、巴尔干长期宗教政治思想杂糅、多民族共处等问题隐于此书,通过散见于红、绿、黄三本书却一以贯之、以哈扎尔捕梦教派为核心的精神共同体,以阿丹·鲁阿尼为核心意象的在建宗教共同体,以及流散覆灭中艰难过渡的哈扎尔民族共同体三者组建成多类型的共同体形式,表达帕维奇对共同体建构中多方问题的关切与预演。
本文拟结合共同体理论,分析《哈扎尔辞典》中帕维奇设计的共同体实践,探讨这些构成相异、结果不同的共同体中存在的问题,尝试寻求民族、宗教共同体在背负自身沉重传统之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
一.知识巨人的传承与重构:宗教共同体的形塑
《哈扎尔辞典》分为红、绿、黄三本书与补编部分。相对“红书”的晦涩难懂、神秘气氛浓郁,“绿书”中伊斯兰教主体的记述为“红书”语焉不详、碎片式的散乱表述揭开了第一层面纱。
帕维奇在该部分构建了“阿丹·鲁阿尼-捕梦教派”这一神与使徒的程式:阿丹·鲁阿尼是知识巨人,它承载的知识意象散轶世间;捕梦教派基于重现阿丹·鲁阿尼、传承哈扎尔知识,寻求构建新的共同体的目的,为“在世间重新创造阿丹·鲁阿尼的巨大肉身①”而存在。“神”作为一个宗教意象,它最初指代的是哈扎尔论辩前的、哈扎尔人的原本信仰。三教论辩后,这一信仰的载体破碎,实质上也就是原有的哈扎尔精神共同体的破碎,这个民族原有的一切知识体系、知识传承走向崩毁。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宗教凝聚力的关键所在。②宗教共同体的式微,一方面是因为语言本身地位的式微,另一方面则是接触到的地域的扩大以及和不同民族、国家的交流增多,对这一语言形成冲击。哈扎尔民族的语言在《哈扎尔辞典》的表述中只存在于三教论辩之前。在哈扎尔王朝覆灭后,神随着哈扎尔语言的消失、三教的文化冲击而破碎,精神共同体也随之瓦解。
神为了保存“知识”而破碎身躯,捕梦者们为了拼合神而寻找、传承知识,使得神能够再现、知识能够真正得到传承。
帕维奇的叙述虽然没有直接给出捕梦者们寻求共同体弥合的行动,却通过描写“陶罐的故事”③表达出作家对“《哈扎尔辞典》”这一具有整一名称、碎片式分散却又具有内在统一的共同体的探索。“《哈扎尔辞典》”本身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哈扎尔辞典》不是仅由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单独创作出的书籍,而是具备集体创作基础、达成了“沟通”的历史记述。另一方面,《哈扎尔辞典》的记述极有可能散轶、重述多次。如今分为红、绿、黄三本记述的,是与书中陶罐承载的隐喻相合的“共同体”。“陶罐”的“拼合”指向了“神”的“拼合”与“再现”,而“神”所具有的“拼合”与“再现”,指向的不仅是知识巨人走向同一,更蕴含了从分散走向拼合、重构的共同体形式的探索。
南希在《解構的共通体》中阐述了对宗教时代“神”与“共同体”关联的思考,认为“上帝之死”实质上也正是宗教社会破碎的标志。④在“被打断的神话”一节中,南希也提出了“沟通”对于共同体(《解构的共同体》一书中,“共同体”与“共通体”并无明显意义差分)的极大影响:“……事实上,神话绝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个孤立的英雄。这个英雄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共通体共通起来——而且他一直产生沟通,在定义上,在交往中,他操作自身,操作起生存与意义,个体与民族:‘英雄的生活方式正是神话虚构生活的经典形式。在神话虚构中,事情也同时是象征的。”⑤
《哈扎尔辞典》中,身负使命、成为沟通桥梁的捕梦者们以梦为载体,突破地域与时间的限制,长期维持着共同体的共通。绿书中捕梦者被神话化了的叙述、秘不外传的任职方式、入梦时认知他者与传递经验的特殊能力,在串连起捕梦教派的精神共同体基础同时,也让这些捕梦者成为流散在历史中的、具有神话象征能力的“英雄”,赋予阿丹·鲁阿尼为首的宗教共同体以个体化、可触摸的切实“锚点”。捕梦者们往往独身一人奋斗于重建知识巨人的事业中,他们最终的目的也正是通过知识巨人的重构,最终使共同体重现人间。
帕维奇在“绿书”中,以虚构的知识巨人阿丹·鲁阿尼为核心意象,建构起了信仰维系下的知识-宗教共同体形式,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对共同体发展与实践的探索。语言传承式微与三教文化冲击背景下共同体的崩溃,其成员选择以捕梦教派为基础,寻求共同体的再次建构。
二.精神底层的捕梦教派:精神共同体的建构与解构
在《哈扎尔辞典》中,捕梦教派作为贯穿全书、串联三教记述的重要存在,在哈扎尔民族的精神变迁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也正是由于历史“阴面”地位形成的暗线记述形式,让捕梦教派的一切无不充满迷雾,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究。
滕尼斯在界定共同体时指出,精神共同体是“心灵性生命之间的关联”,是“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⑥。捕梦教派虽然托生于宗教,它的根本性质却与典型宗教共同体不同,其承载多元文化、成员之间以经验交换寻求共同体维系的形式缺乏以神为中心的活动,使它更应被归类为精神共同体形式。其教义中少世俗规约、强调梦境沟通作用的特质使它得以跨越地域分隔、减少表层文化对意识的规约,达成精神上的沟通,具有承载多元文化的可能性。捕梦教派基于梦境展开的成员间经验交换,也能够让他们在参与到他人的梦境的同时加深自身对这一精神共通基础的认同,从而达成捕梦教派内精神共同体的建构。
看似具有多样优越性的捕梦教派作为帕维奇在全书中设伏最多、最具有神秘色彩的共同体实践单元,却未能在历史中长期留存,反而走向消亡。笔者认为,目标的缺乏、语言文化的消亡,构成了这一共同体实践走向失败的核心原因。
捕梦教派之所以走向消亡,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缺乏统一整合的目标。捕梦者们传达彼此经验带来的能力增长未能服务于共同体的发展;相反,过度的神秘性质、强烈的轮回倾向和宿命论使得沟通中的捕梦者易于陷入历史反复的泥淖。他们构建精神网络、记录民族历史这一所谓目标,在神秘、宿命、轮回的影响里变质为哈扎尔人于不同时代反复循环、本质相同的历史。无从进步的精神共同体无法与不断发展的时代相匹配,无疑只能淡出历史。
与此同时,捕梦教派是基于哈扎尔民族与哈扎尔语发展的精神共同体形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了宗教与王权共同体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捕梦教派在强调捕梦者的神秘性、跨越地域限制与表层文化影响的能力时,它扎根的土壤却并非能与它能够接受的个体多样性对等。依靠单一的哈扎尔文化、依托单一的哈扎尔语作为一切教义传达的基础,捕梦教派自身的存在必然极不稳固。松散而缺乏核心目标的精神共同体形式使得捕梦教派在面对发展节点时不堪一击:哈扎尔民族仅仅在哈扎尔人成年以前使用哈扎尔语,成年以后个体放弃哈扎尔语而皈依三教之一、仅运用对应宗教语言的做法不仅使得哈扎尔语的传承面临巨大危机,更让捕梦教派走向中空。精神共同体仅仅做到了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却未能实现更重要的兼容并包。
文化的多元与向心力、凝聚力的缺失,让精神共同体的维持仅仅浮于表面,最终导致哈扎尔大论辩后哈扎尔王国走向分裂、民族走向流散的结局。
三.复归前的迷雾:共同体的愿景
在《哈扎尔辞典》的记叙中,补编部分作为对哈扎尔人循环历史与轮回中近现代部分补足篇幅虽短,却更鲜明地体现了帕维奇对共同体的探索与态度。补编中他借女招待“阿捷赫”之口,叙说范登·斯巴克家族的分崩离析与哈扎尔人对共同体的质疑。
走到现代边缘的哈扎尔人,在自身的哈扎尔精神共同体崩溃、语言文化传承几乎不存的同时,还面临着融入非哈扎尔社会的困难。如果将生活在哈扎尔王国、接受多元宗教文化影响的哈扎尔人所处的共同体譬为“宗教世界”,那么在补编部分中,哈扎尔人所需要做的便是从“宗教世界”向“世俗世界”的过渡。
范热内普在《过渡礼仪》中关注仪式的重要性,强调借助“产生于特别感情与心智之特殊行为”的仪式,能够帮助每一未进入共同体的成员达成从隔离、“停止、等待、通过、进入,最后被聚合”⑦与接纳的过程。哈扎尔人在融入新的共同体的同时也面临难以寻找到自身传统应在的位置的问题。哈扎尔人的轮回观、梦境独特的作用能够形成广泛意义上的“沟通”,但也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沟通本质是缺乏导向的、无目的的游离。无法形成集聚的共同体流于形式,文化的消亡让哈扎尔人难以借助某种中介作用的“仪式”,在“指引者”的教育与带领下逐步融入新的社会。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同样存在着与南希的“共通体”相区分、类似“过渡礼仪”作为新旧世界中介、帮助社会思想过渡的“共通体”作为媒介。其中,安德森强调文化与集体想象编织出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对共同体的维系作用。哈扎尔民族在论辩后走向崩溃,哈扎尔人面对的除“仪式”的缺乏与过渡的失败,更多是他们对“哈扎尔人”这一身份必要性的认同问题:文本中呈现出的哈扎尔民族的生存状态极为异常。他们既不被生活在王国内的其他民族认同、占据人口大多数却因哈扎尔身份而低人一等,哈扎尔语也在改信宗教时弃之不用,王国对哈扎尔民族的苛待、不平衡,以及捕梦教派中消弭自我意识的“沟通”,在让哈扎尔民族的生活状态陷于迷雾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反映出哈扎尔人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难以维系对共同体的认同。女招待对哈扎尔人身份存在意义的讽刺也便不无道理。
四.“再造亚当”与共同体的未来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识是指由思想见解根本不同的人们达成的一致,是艰难谈判和妥协的产物,是经历过多次争吵、许多次反对和偶尔对抗后的结果,而共同理解则先于所有的一致和分歧,它是一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一旦这种共同理解变得不自然,需要大声叫嚷、声嘶力竭时,它就不会再存在下去,此时,共同理解也就变成了深思熟虑和详细审查的对象。⑧
帕維奇在《哈扎尔辞典》中给出的共同体实践虽然多以失败告终,除去作家个人由于所处时代对共同体的消极态度外,他在探索中给出的多样共同体形式,呈现出了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与维系之难:无论是捕梦教派,还是存在于精神中代拼合的知识巨人,亦或是勃朗科维奇所追求的“将凡人变成亚当”,它们无不呈现出了共同体缔结应有之义,也即服务于共同体内的根本需求,与成员之间达成沟通。沟通仅仅是第一步,在沟通之上更重要的,是能维系共同体不断发展、服务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目标。
与此同时,“传统既可以达成交流,也可能系统地排斥真正的交流。⑨”哈扎尔大论辩作为哈扎尔民族的发展拐点,它带来哈扎尔人的流散、捕梦教派的彻底失根、共同体的崩溃,种种问题瞬间暴露的同时,也表明了沟通基础上,只有努力挣脱自身传统下的精神障壁与枷锁,真正尊重成员意愿,求同存异、消解自身的视域局限,才能迎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融合。
参考文献
[1]郭台辉.共同体:一种想象出来的安全感——鲍曼对共同体主义的批评[J].现代哲学,2007(05):105-110.
[2]马衍阳.《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J].世界民族,2005(03):70-76.
[3]高小岩.“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困境与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30(01):73-77.
注 释
①(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著;南山,戴骢,石枕川译.哈扎尔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43.
②(美)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
③(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著;南山,戴骢,石枕川译.哈扎尔辞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288.
④(法)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著;郭建玲等译.解构的共通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24.
⑤(法)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著;郭建玲等译.解构的共通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84.
⑥(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7.
⑦(法)范热内普著;张举文译.过渡礼仪[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
⑧张志旻,赵世奎,任之光,杜全生,韩智勇,周延泽,高瑞平.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31(10):14-20.
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81.
基金項目:2021年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国家级(A级)项目:碎罐的拼合:《哈扎尔辞典》命运共同体研究。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