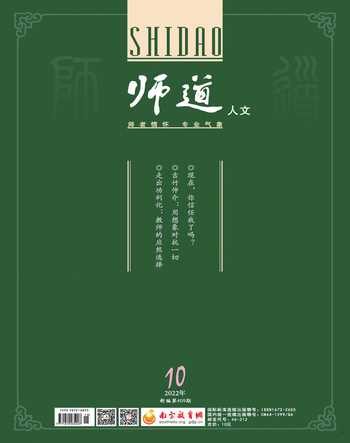夏天,与梭罗相遇
马惠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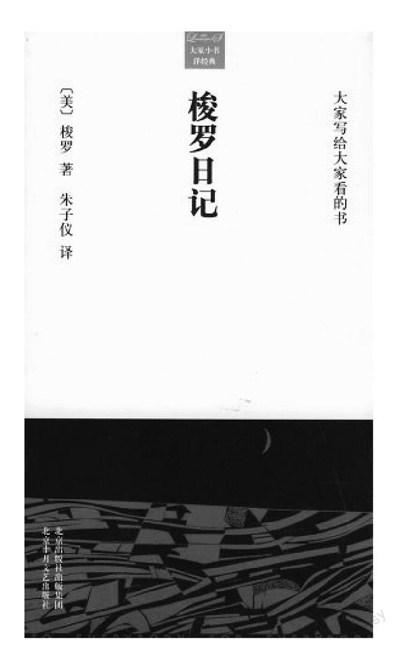
最热的日子里,我终于迎来了暑假,对于每天工作长达十四个小时的寄宿制学校老师来说,现在一天的时间都属于自己,近乎奢侈。日子竟然显得漫长,每个躲避酷烈炎阳不外出的下午都仿佛长得没有了尽头。这从三月就开始遥望等待的盛大节日终于来临,我在这时,开始一年一度最安静的阅读。
这座南方小城,夏日温度普遍在35℃以上,那扇西向窗户的玻璃被晒得烫人手,空气温热如同粤人喜好的热汤,人泡在其中,汗出如浆昏然欲睡。我常常坐在餐桌前,一边大杯大杯喝白开水,一边划拉下一张书页。
虽然性情不算浮躁,然而宁静是久违了的,有些陌生,楼道里传来阵阵笑语,手机时时振动的提示,仍把我裹挟在洪潮般的信息流中,放下书要走出去的冲动三番四次追索着,逼迫着,将我从文字中一次次剥离出来,一个炽热如这盛夏气温的问题悬在心头:是该这样安然地读梭罗?还是该用这些时间去加班去挣钱去创造更加现实的利益,在更宁静美好的环境里再来读这本书,而不是现在!
可是,此时我手里抓着这本《梭罗日记》,仿佛安迪紧紧握着那把鹤嘴锄,这是惶然无措屡屡向灼热坚硬的现实投降的我拥有的一剂清凉散,是治疗浮躁的唯一解药,只有在这文字中,我才找到慰藉,能在快快快中喘息片刻。
于是强迫自己坐下来,坐在椅子上,努力压下再次站起来的冲动,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停,请试着不停地读下去读下去,读梭罗的书,他的日记、还有那本《瓦尔登湖》,还有《野果》。
这是让人宁静的文字,出自一个自由、独立、睿智的美国男人之手,他的风采穿越近两百年时光的幽暗隧道,在他处处珠玑的宝藏文字里光华照眼。
总是遥想1845年。32岁的梭罗将背影留给拥挤的文明社会,只身一人,带着一把斧头走向大自然,住进了瓦尔登湖畔的小屋。
这一住就是两年,直到1847年返回康德科。从1845年7月起,梭罗日记里就有了大自然的无限魅力。只活了44岁的他此时正处于生命的顶峰状态,日记里处处能读到热情饱满、元气充沛的文字,他对大自然充满的勃勃生机做了详尽描述。
7月5日:关于林中小屋的描写。这是上午的书写,对林中小屋中的晨晖尤为赞赏:“它们的周围在拂晓时分似乎拥有更为鲜艳的曙光氛围”。心境平和,身体健康的人对自然光线的变化非常敏感。
7月7日:仍然无限留恋小屋的晨昏时光,包括晚上坐在门边上的自由想象。
就在这个月里,一个苹果以它纯真无邪的扑鼻香味陪伴着梭罗在田野上漫游,他想到诸神的赐予,倍感万物的美好,满怀感恩之心,“以另一种方式摄取营养”。这种谦和感恩对于物质需求极其贪婪的现代人来说简直就不可思议――谁会去感恩一个苹果?即使对一辆豪华汽车感兴趣也不过是三五个月而已啊!所以我们的天空只会越来越低,滋养灵魂的时光越来越少,心灵世界越来越芜杂。人群被挟持在潮流中汹涌向前,顾不上审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顾不上思考匆忙脚步走向何方,体重不断超标,营养却在流失。我们很忙,从早到晚,连每顿饭吃东西都会计算时间。“有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吃饭的时候匆匆忙忙,简直莫名其妙”,梭罗用“粗鲁”责备人们吃饭时的仓促和匆忙,这个词多好,把心灵越匮乏,越需要大量物质填补的掠夺者的样子描画在眼前。我不正是“粗鲁”者中的一个吗?吃下顿饭时根本想不起来上一顿吃过什么,因为热衷于扮演世俗安排确定的角色,心的自由一别经年,独特奇异的经历失之交臂,只一味地觉得还需要去赚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东西。这颗心纷杂凌乱,像旅游区的山间小溪,粼粼清波上漂洒着许多刺眼的白色垃圾。从来不敢仔细去想将来有一天,生命暮年的自己,坐在屋檐下,回想这匆忙一生,除了努力工作认真赚钱之外,还对生存过的空间了解过些什么,热爱过什么!
南风从阳台进来,时不时掀动放在餐桌上的书页,仿佛在一行行的文字中找寻着什么,这襟怀潇洒的朋友,是在书页中找寻梭罗传递的精神密码吗?突然发现,我那道自以为构筑得高大坚固的心灵防御墙根本就不堪一击,一念之间就会崩溃坍塌,随波逐流的泡沫浮泛地向前漂着,轻而易举就淹没了精神世界的深流,这深流的力量日渐枯寂难以为继,软弱暴露无遗。而梭罗正好和崇尚物质追求速度的现代相背而行,城墙可以崩塌,钟楼已成废墟,深邃美丽的灵魂却如夜晚缀满星辰的高远天空,优雅,从容,高贵;他的精神质地如同汉白玉一样,底纹清晰而晶莹,格外引人遐思。
8月,他继续沉浸在大自然堪称经典的杰作中,“尽管遂心如意却哑口无言”。在23日的记叙中,他又一次反复告诫自己:“为什么不过一种艰苦的和特殊的生活呢?”生命,古代艺术,人的进程,活的目的这些探索人生的问题被他敏感的大脑反复思索,“高尚的生活是持续和不间断的,至少要以更长的半径活着”“让白天照亮你吧,让黑夜为你秉烛”。这样的句子到处是,钻石一样在文中闪烁光芒。
时间延伸到1851年7月19日,梭罗34岁。
这一天,他独享静穆,审视自己的生命历程,“生命几乎完全没有伸展开”。这本来是一棵擎天苍松,必是森林里风姿特秀的那一棵,可惜风霜的摧折太过频繁,他来不及伸展开枝叶就被疾病夺去生命。我只能通过历经遥远年代的文字回响来推测这棵大树曾经覆盖过大地的幽幽绿荫,华盖如云。他说他的生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还是萌芽状态!”他多么珍惜这顽强而鲜活的生命,“生命的长度连让人取得一项成就都不够,”可是他又是知足的,因为他“让一个人按他所听到的音乐节拍行走,无论怎么样都是适度的。”因为爱,因为珍惜,即使不完美,也是最好的。
生命足迹延伸到了最后阶段,剩下的十年,梭罗继续在故乡的土地上漫游。早年对自然物候的浓厚兴趣已经初见端倪,此时更在行动中加以实践。他总是在午后出门散步,不管是烈日當空还是细雨霏霏;他甚至在帽子上做了一个小盛物架,用来盛放野外收集的植物标本。这个不怎么为美国人所理解的孤独的梭罗,如果是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肯定也是个怪人,未必能让我引之为知音。远离人群的他把自己交给了大自然,洞晓自然密径的人也接受了自然的慷慨馈赠。他笔下的野草莓香气馥郁——“也许,那来自泥土里的芬芳,是千百年圣贤的哲理名言在那里酝酿而成。虽是花开后便结的果,但我没有观察到草莓开的花。不过,可以肯定,由于这是造化神功奉献的一年中,最早的美果,所以,一定将春天里所有的芬芳馥郁都赋予它。草莓来自天赐,岁月悠悠,其芬芳也悠悠。难不成每一颗果实的汁水里都浓缩了大气中的精华?”这般滋味渐成绝响——如今,草莓已被喜好快餐的人们种植在停车便利的路边,用化学制剂培育,想什么时候成熟就什么时候红艳艳的逗人喜爱,以“草莓园”之名,满足那些追求速度的现代人偶尔怀旧的“田园梦”。当你清洗后品尝,那汁水却充斥难以形容的味道——从此,我们再也品尝不到“浓缩了大气精华”的草莓,我们只能在梭罗的文字中去寻找大自然曾经存在过的无上美妙。
正值盛年的梭罗,未来得及娶妻生子就被结核病挡住了脚步,尽管拥有过爱情,却极其短暂,至死仍孑然一身。如果他活着,应该一切都来得及,这颗睿智心灵对未来生活的预见和忠告也许能引起世人深思,能推动社会文明更为合理地发展。然而,现实却是他在病前把手稿用厚厚的纸包起来,仔细捆好,近千页的文字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小柜子,开始了漫长岁月的等待。
也许梭罗已经料到这些文稿要经历漫长等待,所以他说“假如生命就是等待,那就由着它吧”,等待什么呢?生命的自然成熟,生命的丰硕回报,还是生命的光彩过程?他再也没有回答,这是永恒的谜。可是和他一样被奉为自然文学先驱的约翰巴勒斯仿佛是在远处回应:“上帝眷顾的是那些所求甚少却不惜余力工作的人,我双手合十,平静地等待。”这世上多的是所求过多之人,往往被欲望带向耍弄机巧贪得无厌的不归之途;而那些看似愚笨,所求甚少的劳作者省下许多精明算计,往往获得最大的心灵自由,无所求却终有所得。
答案如沉重的雨滴穿过轻盈的云层向地面坠落,而“蓝眼睛的苍穹”永远无语,但它明了一颗火热的心,那内里的岩浆曾经怎样奔突横流?那颗心“活过每一个季节;呼吸空气,喝水,品尝水果,让自己感受它们对你的影响。”那颗心灵放射的光辉在归于平静的文字中照彻平庸的我,让一个中年女人在狼烟四起的现实中仍没有间断阅读和书写,哪怕每天只是读几页书写几百个字,即使对着厚的障壁,坚硬的岩层,深藏于心的泉源也未枯竭干涸,沁化为水滴,盈盈的,一滴一滴又一滴,汇聚,然后坠落,迸射,化为无数沫点,终汇成汩汩细流。如果奔涌,急湍,滔滔,澎湃是水流变化无限的风景,那我现在的模样,就该是原野上那个双手合十,平静地等待水滴装满陶器的劳作者,这样的模样,才算没有辜负这个炎夏的午后与梭罗相遇,邂逅清凉。
(作者单位:广东东莞市东华小学)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