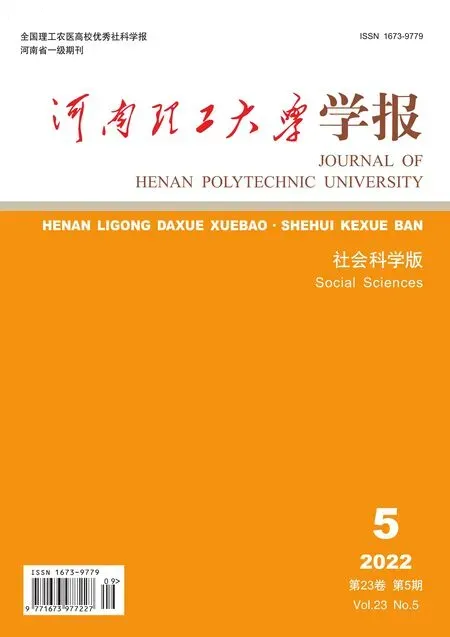从《中国女子教育》透视中国晚清女子教育状况
柴 橚,赵燕凤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相关史料浩如烟海却未成体系。直到1911年,Fleming H. Revell公司出版了女传教士M.E.伯顿撰写的《中国女子教育》(TheEducationofWomeninChina)[1]一书,情况才有所改观。《中国女子教育》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介绍晚清中国女性教育发展历程的著作。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史学家熊明安曾在《中国女子教育通史》[2]一书的序言中提及此书,南治国[3]也在探讨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时引用该书。除此之外,国内外鲜有学者关注此作。基于此,本文试图系统探究《中国女子教育》这一力作,把握西方视域下中国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脉络、特质与进步意义,在梳理晚清教会女学与中国自办女学差异的同时,探索当时推动女子教育发展的诸多因素,发覆中国晚清女子教育。
一、玛格丽特·伯顿与《中国女子教育》
玛格丽特·伯顿生于一个信仰基督浸信会的美国家庭。1908年,她陪伴身为教授、牧师的父亲出访中国、日本等地。沿途所见所闻令她对中、日女子教育好奇不已。在中国长达半年的游历成为伯顿学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她自此投身于女子教育与宣教活动,坚信二者存在紧密关联。她曾出版《中国女子教育》《中国近代知名女性》[4]《日本女子教育》[5]《东方女工》[6]等反映当时中、日女子生存境遇的著作。在这一系列专著中,伯顿多次阐释了一种价值观,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日女子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宣教活动。同时,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基本思考与详细阐述主要源于《中国女子教育》。正如朱爱莲指出,作为一种主观与客观、真情实感与客观陈述的混合物,“异国形象”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固有的宏观性文化阐释[7]98,《中国女子教育》也因此成为西方视角下晚清女子教育发展史的发轫之作。
《中国女子教育》以历史为轴线,从中国传统女子家庭教育现状出发,穿插对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这一阶段女子教育发展情况的评论,将女子教育分为教会女学和中国自办女学两大阵营,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汕头、广州、福建、宁波、天津等沿海富庶之地。全书共11章,配有16张伯顿本人拍摄的照片,细致、全面、直观地展现了中国清末女学风貌。她对东汉曹大家(班昭)的《女诫》、清代蓝鼎元的《女学》的释读,以及对九江儒励女中、南昌鲍德温女校、上海中西女中、北京贝满女塾等女校的详细走访调查,使得《中国女子教育》成为一部并非单纯记录作者主观感受的游记,而是一部由大量史料整理与实地考察熔铸而成的学术著作,蕴含了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等多个层面的西方理解与评判。
二、从《中国女子教育》看教会女学与自办女学的异同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了中国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医院、学校等特权。同时,清政府还须保证教堂和传教士的安全。这为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创造了有利条件。教会女学初见端倪,但其萌蘖却历经艰难。
在伯顿看来,早期教会女学遭遇排斥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人鄙视女子教育,其深层内涵在于中国社会长久以来将“女子无才便是德”奉为圭臬。大多数被支配、被奴役的女性失去自我存在感,缺乏自我教育意识,社会地位远低于男性。这让女性不自觉地接受“我是女子”“不要指望女子能读书”[1]27等社会规约。大多数女子在十几岁时就已嫁为人妇,相夫教子,丧失教育机会。次要原因是,晚清国人对西方传教士心怀戒备、疑虑、偏见。当时,传教士积极倡导女子接受教育,收获的却是诽谤与被妖魔化:“有人鼓唇弄舌,散播骇人听闻的消息,煞有介事地告诉周围人外国人如何挖掉小孩子的眼睛入药……将女孩们带到遥远的西方,将她们杀死、煮烂,炼制长生不老药。”[1]45-47
经过传教士的不懈努力,国人在19世纪末对教会女学的疑虑、偏见逐渐淡化,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女儿送往学校读书,教会学校不再因招生问题烦恼。福州卫理公会女子学校办学之初只有1名女学生,1872年已有30名学生,而1897年,却出现50多位女子因师资有限而被拒之门外的事件。同一时期,北京贝满女塾不再提供各类补助与津贴,父母能否为女儿提供衣食成为入学的首要条件。
“反对和嘲笑的日子一去不返,我们为这来之不易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教会女学逐渐赢得社会认可。新一轮的太阳冉冉向东,我们的女校不再囿于一隅,而是遍布全国,中国人对女子教育的热情日益高涨。”[1]165自1844年第一所教会女校成立之初步履维艰至20世纪初的盛极一时,教会女学收效甚佳,“女性走出校门后取得的成就,为女子教育事业带来无限荣光,影响宏大”[1]77。
不过,随着中国自办女学的涌现与繁盛,教会女学的发展受到限制。《中国女子教育》在比对、分析教会女学与中国自办女学后,总结出前者式微的缘由:首要原因在于资金不足。无论是慈禧太后牵头的官办女校还是民办女校,中国自办女学均拥有雄厚的投资资金支持[1]130。相比之下,教会女学早期承诺提供免费食宿以及每日十文钱的补贴,以此招揽学生,这耗费了大量财力,加之本身资金匮乏,办学环境较为艰苦,老旧的实验仪器使理科课程难以开展[1]218,供体育锻炼的场所也只是带有简易体育器械的庭院[1]219。原因之二在于师资力量薄弱。伯顿指出,微薄的工资难以聘请到优秀的教师,当时教会女校教师的薪资仅为自办女学堂的五分之一,且授课强度过大[1]133。她希冀“教会学校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否则有一天会失去中国女子教育的引领地位,帮助中国人建设强大国家的有力手段将会失效”[1]231。
事实上,伯顿将教会女学的日暮途穷归因于资金紧张,未免流于表面。正如马克思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8]57119世纪末,晚清教会女学的兴盛极大地激励了国人,本土改革派和进步人士强烈地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1898年,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1902年,吴馨和蔡元培又在上海各自创办务本女塾和爱国女学。随后,全国陆续开办广东移风学校、常州争存女子学堂、南京旅宁第一女学、浙江爱华女校、上海城东女学校、湖南第一女学堂等女子学校[9]。这一热潮的原因如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指出:“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10]“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欲强国,必由妇学。”[11]同一时间,慈禧太后的态度亦有所改变,在她的授意下,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从而在政治层面振兴了本土女学。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1906年中国自办女学堂仅有学生306名,1907年达1 853名,1908年增至2 679名,到1909年已经多达12 164名[12],发展迅猛之势远超教会女学。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自办女学由教会女学催生而来,但依然具有本土“特质”。
首先,教会女学最初针对的对象是穷人,走的是“通过大众化教会教育、自下而上引发文化环境变革的路径”[13]201。而自办女学却是彻头彻尾的富人教育,官僚士绅们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女校[1]130,政府建立土地税收制度供以充足的资金支持[1]123。这让自办女学与富人之间达成共识,前者为后者提供教育,后者则为前者投入大量资金以满足其发展。从此,自办女学便拥有了舒适的教育环境、充足的教辅设备以及为教师提供优越薪酬的资本[1]132。

图1 广州官办女校[1]116
其次,正如德国教士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所指出:“上不以为教,故下不以为学。”[14]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培养的是记忆力而非推理能力”[1]136,自办女学尽管购置了大批先进设备仪器[1]136,但“重德育、轻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薄弱的自然学科师资力量都让当时的中国“未有一所自办女学堂能够让学生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好准备。女学生不大理解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即便明白,自办女学堂依然无法给予她们教导”[1]145。
最后,教会女学资金匮乏,而中国自办女学教师自身能力有限。受“男女授受不亲”封建礼教的约束,教育女子的重担自然落在女性教师身上,对于未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来说,教授女红一类传统女性技艺轻而易举,但让她们教授数学、地理等科目则实属难题[1]141。
三、《中国女子教育》的拓新价值
比起中国知识分子,外籍人员拥有更加广阔、自由的言论空间,能够大胆表达真实想法,并以他者视角评判国人习焉不察之处。在《中国女子教育》的每一章节中,伯顿都记录并评论中国女子教育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与发展。她认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晚清女子教育从根本上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尤其在启迪社会、深化认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由此引发了激烈与深刻的社会变革。
(1)子女教育逐渐平等。晚清女子教育逐渐解构封建社会的种种沉疴痼疾,社会风气日开,培养出的“贤妻良母”有着更加开明的子女教育观,“她们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智慧和仁慈……孩子们顽皮淘气时,她们不会像泼辣无理的母亲那样采用惯有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大吼大叫,吓唬着要把他们扔进黄土坑”[1]93。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他们对子女教育观念的转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新一代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可从后代女子名字的变化窥知一二。过去女孩常常取名为“召娣”“来娣”“婷妹”等,暗含“重男轻女”思想。女子教育兴起之后,女性多以“宝妹”“晓爱”“晓暖”为名[1]158,这一现象昭示的是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2)更加自由的婚姻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娃娃亲”是封建社会不可逾越的箴规。但在晚清,受过教育、深受国外“新自由精神”影响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反抗包办式婚姻,主张婚姻自由,革除婚姻中的不平等。不仅如此,20世纪初女子教育骎骎日上之际,男性的择偶标准亦有所调整。著名女传教士茱莉亚·博纳菲尔德曾经提到,面对长辈包办婚姻,福州一名年轻男子始终抵抗娶文盲女子[1]153。
(3)废止缠足与强身健体。妇女缠足始于北宋后期,兴于南宋,盛于清朝。清朝女子大多将脚缠得瘦窄、平直,社会各阶层均以娶小脚女子为荣。倡导男女平等和天赋人权的传教士自然鄙夷这一陋习。由此,1872年北京卫理公会女子学校将女子天足列为入学条件之一[1]172。此外,《中国女子教育》还翻译了1897年梁启超筹备经正女学时手订的《女学堂试办略章》(后又名为《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其中规定“缠足为中国妇女陋习,既已讲求学问,即宜互相劝改,惟创办之始,风气未开,兹暂拟有志来学者,无论已缠足未缠足,一律俱收,待数年以后,始尽定界限,凡缠足者皆不收入学”[15]。而在解放妇女双脚的同时,女学也侧面推动国人对女子体育锻炼的重视。在当时,体育课是教会学校的必修课。上海圣玛丽亚女中(St. Mary’s Hall)的校长与北京贝满女中的教师认为,长期裹脚、持续做女红导致中国女子圆肩驼背、身体羸弱、频染肺病。体育锻炼改善了女性健康,曾经身材臃肿的女性如今变得体态轻盈,充满活力[1]74。见证教会女学倡导体育锻炼带来的积极改变,中国自办女学大为触动,将健美操列为主课之一[1]127。
(4)晚清新式女子教育的广泛推行为女性就业架起了桥梁,社会上逐渐出现职业女性,她们颠覆了传统的女性生存观,加速社会结构转型。在《中国女子教育》中,伯顿认为,女子教育主要培养出两类职业女性:教师和医生。很多女性毕业后选择从事教师职业,这恰恰是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办女学共同的需求与愿望[1]202。伯顿也对从医的中国女性颇为赞赏,书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第一代女西医护石美玉和一批女医生的卓越事迹[1]97。伯顿甚至另外出版《中国近代知名女性》一书,对中国近代杰出女性的事迹详加叙述。

图2 正在做操的南昌鲍德温女校学生[1]152

图3 毕业于教会学校的中国女医生[1]81
(5)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往往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这种境况直至晚清女子教育的推广才得以改善,女性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献计,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可。1888年,在伦敦举行的传教士大会上,斯旺森首先谈及中国女性在过去遭受的屈辱,随后指出“今天的中国女性却拥有非凡的地位,她们逐渐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1]169。
不久前,福州召开了一次妇女大会……会议议题是抗议浙江省为修建铁路而向英国贷款。所有人都希望建成铁路,但也期盼这条铁路属于国人……
近期,我遇到一位中国女子,她告诉我每个月她们都会在妇女大会上讨论国家要事……最近,她们十分关切反鸦片运动,因此不停地集会,发放请愿书……她们甚至给英国反鸦片协会写了一封联名请愿书。此事意义重大,因为此前中国女性从未签署过任何公共文件[1]177。
在伯顿看来,女子教育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推动社会进步有赖于传教士的努力。这种想法贯穿于整部著作。中国自办女学堂尚未创办之前,伯顿就已认为,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女性是“对女性是否有能力、是否值得接受教育等质疑的有力回答”[1]99,教会女学是中国自办女学的表率,贯穿中国女子教育改革发展始终[1]212。
四、探索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客观因素
《中国女子教育》不乏客观陈述与真情实感,但是“这些文字不可避免地带有居高临下的战胜者的姿态,带有西方文化优越的民族歧视和阴暗心理”[16]。伯顿等传教士声称开展教会女学为中国带来福祉,是一场“为争取中国妇女‘平等权利’的十字军运动”[17]566。可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女校的大部分学生家境贫寒,传教士教育女性自力更生并非为了获取收益,而是为了培养她们的自尊心,唤醒女性对基督教的感恩之心”[1]59。“我们来到中国,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带到上帝面前。”[1]222“我认为向中国女孩传授基督教教义是传播基督教最高效的方法。”[1]202此外,1877年,在全国开设的347所教会学校中,女校仅有120所,男校数量则约占教会学校总量的2/3。这暴露出传教士发展中国教育的初衷:尽可能地扩大传播西方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范围与受众群体。诚然,如伯顿所言,晚清女子教育在解放国人思想、移风易俗、培养职业女性、推进女子参政议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教士也为此沾沾自喜,认为这些归功于教会女学,但他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女子教育得以发展的根源在于中国人的自主选择,而这也正是教会女学随后逐渐走向没落的根源。
(1)女子教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于国内政治革命运动。陶行知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时势之产物,学校制度,亦不违反这一原则。”[18]194中国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紧随国家政治运动的脚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都曾致力于提升女性地位,加强女性自我认同感。如1903年,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在与张百熙、荣庆等共同拟定《奏定学堂章程》时,主张女子学习科学知识,“使全国女子无学,则母教必不能善,幼儿身体断不能强,气质习染断不能美”[19]573。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20]43
(2)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鸦片战争后,江河日下的中国引入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民族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工厂的大规模建立对女子职业教育提出要求。除开展基础教育的“综合性”女子学校外,各地纷纷创办桑蚕女学堂和女工传习所,如上海创设的女子蚕业学堂、福建蚕桑女学堂、杭州蚕桑女学堂、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杭州工艺女学堂等等[21]。新兴工业对女工需求剧增,女性纷纷走出家门,务工养家,工厂女工的数量远超《中国女子教育》关注的女教师与女医生,这一现象不应忽视。
(3)文化民族性稳固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蕴含人文关怀的儒家思想历久弥新,牢牢占据华夏文明的主流位置。不同时期的文化民族性虽然存在差异,譬如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但正如汤谦繁指出,晚清高等教育简单因袭西方教育发展,看似是被动选择的结果,可实际上并未脱离中国文化自身演进理路的制约[22]。晚清教会女学为尽快得到国人的接纳并在中国发展,不得不在课程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自办女学堂也始终讲授《四书》《五经》等传世典籍。这些都表明晚清女子基础教育的萌发、创立、发展,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性在不同时期主动选择的结果。优秀的儒家思想在晚清女子教育中得以传承,并在无形中融入其中,构成本土化特色。这也是中国女子教育并未自始至终沿着西方理想道路前进的内在动力。
(4)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女性自身的觉醒。19世纪下半叶,随着百日维新等政治改革运动深入开展,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过去长期被“压制”的女性开始拥有自我意识,追求自由,如康广仁之妻黄谨娱、梁启超之妻李蕙仙等受教会女学的激励,先后主张国人自办女学堂。女权运动家秋瑾在《勉女权歌》中疾呼:“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23]121何香凝、张竹君等女权先驱在积极参与民主革命的同时,反对桎梏女性的遗俗,主张新式婚姻与平等的夫妻关系。《中国新女界杂志》主编燕斌所著的《中国婚俗五大弊说》[24],痛斥旧式婚姻的弊病。类似的文章还有汪毓真的《论婚姻自由的关系》、杜清持的《男女都是一样》等。由此看来,女性的自我努力是晚清女子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在推动力之一。总之,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发展,足以让风雨飘摇的晚清对女子教育的态度呈现“过山车”式转变。在此意义上,中国的求变内因与西方外来因素的联合作用使得晚清成为中国女子教育及女性解放的发轫期。
伯顿的《中国女子教育》为我们揭示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晚清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种种细节,并在西方视域下,归纳出社会风俗变迁、职业女性造就和女子参政议政等方面的进步意义。但同时,我们应该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互鉴态度,拨开历史迷雾,通过更加真实、客观的视角,还原晚清中国女子教育崛起的复杂过程,厘清其发展壮大的多重缘由,为中国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化历程提供一管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