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及其前景
——基于部落政治文化视角的解读
刘 伟
【内容提要】部落是塔利班发展壮大的基本社会基础。作为阿富汗部落社会的主体,普什图部落以普什图瓦里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荣誉文化、自治传统、庇护文化与势头文化等部落政治文化,并深刻影响着阿富汗国家的兴衰更迭。2001年后,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阿富汗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结构,但与该国原生的部落政治文化极不适应,国家重建失败。相反,塔利班通过迎合部落政治文化,获得源源不断的部落支持,重新崛起并最终夺取政权。事实上,特定的政治结构需要匹配相应的政治文化才能有效运作,特有的政治文化也是与之契合的政治结构长期培育的结果。虽然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阿富汗局势充满不确定性,但部落政治文化始终是阿富汗恒定不变的“文化底色”。塔利班新政权利用部落政治文化稳步推进阿富汗重建,不仅考验塔利班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倾力帮助。
2001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已在阿富汗进行了长达二十余载的重建工作,然而阿富汗仍然动荡不安,对地区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2021年8月美国撤军,塔利班随即攻占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并最终进驻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逃往阿联酋,塔利班在阿富汗全面掌权。阿富汗再次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考验,前景愈加扑朔迷离。塔利班成为影响阿富汗当前局势的核心变量。塔利班再次掌权证明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在阿富汗遭遇重大失败。人们不禁发问,塔利班为何能够在美国的威压下不断壮大,再次问鼎阿富汗。事实上,特定的政治结构需要与之匹配的政治文化才能维持和运转,而特定的政治文化(1)“政治文化”一词最早可见于18世纪德意志启蒙学者赫尔德的著述中,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和研究工具则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愈益流行。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并未达成共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也最具经典性和影响力。参见:李剑鸣:《美国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7-178页。亦是与之协调的政治结构培育和维持的结果。部落政治文化与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冲突,正是美国主导下的阿富汗重建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塔利班迎合阿富汗独特的部落政治文化,依靠部落社会深厚的群众基础,最终再度崛起并上台掌权。
阿富汗问题在国内外学界一直备受关注,相关研究侧重于部落社会的起源谱系、政治结构和基本特征,历史上部落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问题。(2)Olaf Caroe,The Pathans:550 B.C.-A.D.1957,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58.Christine Noelle,State and Tribe in Nineteenth-Century Afghanistan:The Reign of Amir Dost Muhammad Khan 1826-1863,Richmond Surrey:Curzon Press,1997.Ahkar S.Ahmed,Pukhtun Economy and Society:Tradition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Tribal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13.Jennifer Murtazashvili,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Shahmahmood Miakhel,“Understanding Afghanistan:The Importance of Trib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in Security and Governance,”Asian Survey,Vol.35,No.7,1995,pp.1-22.Nivi Manchanda,“The Imperial Sociology of the‘Tribe’in Afghanistan,”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46,No.2,2018,pp.165-189.S.Yaqub Ibrahimi,“Afghanist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Dilemma:The Centralist State Versus a Centrifugal Society,”Journal of South Asian Development,Vol.14,No.1,2019,pp.40-61.国内学界聚焦于阿富汗的现状分析,从多个视角探讨阿富汗的重建前景和发展方向,同时关注阿富汗变局产生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3)闫伟:《身份政治与阿富汗国家建构的难题》,《当代世界》2021年第10期,第31-36页;闫伟:《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国际论坛》2021年第4期,第118-135页,第159-160页;闫伟、刘伟:《部落问题: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南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2-134页,第158-159页;车轲、邢瑞磊:《外部干预、精英惯习与阿富汗国家建构困局的根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4期,第139-156页,第160页;何可人:《阿富汗部族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 2期,第97-104页;冯绍雷、张昕、崔珩:《阿富汗问题与欧亚秩序构建——关于世界大变局的对话》,《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4期,第3-21页。对于部落组织与阿富汗问题的多维互动,特别是部落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国家兴衰更迭却乏善可陈。实际上,纵观阿富汗历史,部落组织一直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也是研判阿富汗当前局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透过纷乱复杂的现实可以发现影响阿富汗政治稳定的结构性问题,即在部落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如何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从而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本文分析了阿富汗部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表征,由此深入剖析部落政治文化对阿富汗重建失败的深刻影响,并从部落政治文化的视角阐释塔利班掌权的深层原因,以及探讨部落政治文化与塔利班政权的前景,为客观认识当前的阿富汗变局提供些许参考。
一、阿富汗部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表征

第一,荣誉文化。荣誉(Izzat)的概念源于普什图人的部落精神:“荣誉意味着光荣地捍卫自己与部落的权利。”它不仅基于捍卫个人尊严的内心号召,也源于对所属部落世系的坚定忠诚,是个人身份与价值的必要基础。(9)Frederick Barth,“Cultural Wellspring of Resistance in Afghanistan,” in Rosanne Klass eds.,Afghanistan:the Great Game Revisited,New York:Freedom House,1987,p.187.对普什图人而言,捍卫荣誉是至关重要的行为准绳。人们认为捍卫荣誉的普什图人是“楠格拉伊”(Nangyalai),意为“光荣者”。(10)Fida Mohammad,Alexander R.Thomas and Iffat Tabassum,“Honor,Revenge in Socio-Geographic Space of Pashtuns,”Pakist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Vol.8,No.3,2016,p.76.他不仅能获得部落民的尊重,并能在部落世系中找到盟友,在必要时得到部落支持。反之,由于个人荣誉与所属世系的荣誉相互依存,丧失荣誉意味着失去部落身份,无法在部落社会中立足。(11)Bruce L.Benson and Zafar R.Siddiqui,“Pashtunwali—Law for the Lawless,Defense for the Stateless,”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7,2014,p.112.千百年来,部落民因捍卫荣誉展开激烈争斗的案例比比皆是。正如阿富汗诗人哈塔克(Khushal Khan Khattak)所言:“对我来说,死亡比没有荣誉的生命更加甜蜜。”(12)Niloufer Q.Mahdi,“Pukhtunwali:Ostracism and Honor among the Pathan Hill Tribes,”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Vol.7,No.3-4,1986,p.297.这种荣誉文化延伸至国家层面,国家权威向部落逐渐渗透会被解读为破坏部落自治,有辱部落荣誉,遭到部落民众的强烈抵制。无论是阿富汗历届政府扩展国家权威的尝试,还是美国主导下阿富汗重建的努力,都被部落视为有损部落荣誉的行为,无法得到部落社会的有效配合。塔利班则充分利用这种荣誉文化,将自己塑造成抵御外侮、捍卫荣誉的正面形象,获得部落源源不断的支持。(13)Yoshinobu Nagamine,The Legitimization Strategy of the Taliban’s Code of Conduct:Through the One-way Mirro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96.
第二,自治传统。阿富汗地处亚洲腹地,境内遍布高山峡谷。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独特的社会单元——部落,并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部落社会缺少向外部世界交往的动力,实际上成为独立自治的“微型国家”。人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却无等级隶属关系,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14)Louis Dupree,Afghanist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p.248-251.从国家内部来看,历代统治者都赋予部落高度自治,国家无法向部落征兵、征税,强化国家机器,只是形式统一的“部落邦联”。在某种程度上,阿富汗国家只能与部落达成微妙妥协,以收买首领的方式治理部落社会。(15)穆沙希班王朝时期开创了“双轨统治”模式,就是这种统治方式的代表。详见闫伟:《阿富汗穆沙希班王朝的部落社会治理及启示》,《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第106-129页。即使是美国支持下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也无法真正控制部落社会,只能让部落首领在政府任职以获取支持。塔利班根植于部落社会,也需要与当地部落精英进行谈判,并接受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16)Faiz Ahmed,“Shari’a,Custom,and Statutory Law:Comparing State Approaches to Islamic Jurisprudence,Tribal Autonomy,and Legal Development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Global Jurist,Vol.7,No.1,2007,p.5.从对外关系来看,阿富汗历来被称为“帝国坟场”就可窥见一斑。2021年5月,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就是对此最好的当代注脚。事实上,这都源于部落笃信独立自治,反对外部控制的政治传统。正如一位普什图部落首领所言:“我们宁流血牺牲,也不愿接受卑躬屈膝地臣服。”(17)Haroon Rashid,History of the Pathans(Vol.1,The Sarabani Pathans),Islamabad:Printo Graphic,2002,p.6.
第三,庇护文化。礼遇来宾是部落民最珍视的品质之一。其中,除了全力给宾客提供最好食宿,部落还要为客人进行安全庇护(Panah)。无论来客是谁,也不论其与主人有何关系,一旦他获准进入主人家中,主客之间便订立了某种“安全契约”。任何人都不能伤害来客,否则等同于对主人荣誉的侮辱。当客人受到攻击时,主人将尽最大努力保护他,并充当客人与仇敌之间的调解人。保护客人意味着捍卫自己及其部落的荣誉。(18)Shahmahmood Miakhel,“The Importance of Tribal Structures and Pakhtunwali in Afghanistan:Their Role in Security and Governance,”in Arpita B.Roy ed.,Challenges and Dilemmas of State Building in Afghanistan:Report of a Study Trip to Kabul,New Delhi:Shipra Publications,2008,pp.102-103.被保护人可以长期在部落中居住生活,但并非部落的正式成员,无法享有土地分配与参与部落事务等方面的权利。寻求庇护是普什图地区的重要安全机制,提供庇护之人会享有至高荣誉,但因此也可能付出巨大代价。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庇护文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巴边境的部落地区就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反苏武装分子。塔利班的崛起也得益于这种庇护文化。2001年政权垮台后,塔利班成员迅速向部落地区转移,不断化整为零,迅速完成重组。(19)Habib Ullah and Muhammad H.Khalil,“The Impact of US Invasion in Afghanistan on the Tribal Culture of Waziristan,”Pakist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Vol.40,No.1,2019,p.125.此外,这种庇护还有金钱与部落谱系的加持,形成了塔利班强大的地方支持网络。(20)Muhammad A.Rana,“The Taliban Consolidate Control in Pakistan’s Tribal Regions,”CTC Sentinel,Vol.1,No.7,2008,p.8.
第四,势头文化。阿富汗部落社会有着追随强者的生存哲学,即民众的支持与服从随实力强弱而变化。(21)Ali A.Jalali,“Afghanistan:Regaining Momentum,”The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Parameters,Vol.37,No.4,2007,p.6.由于阿富汗权力结构松散,部落民通常会支持实力强大的一方,跟随强者才能生存。相机行事和见风使舵是普什图人的传统,部落民会根据“得势”与“失势”的力量对比在适当时机转变立场。(22)Zachary Laub,“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Vol.4,No.7,2014,p.3.同时,人们也会同时“下注”,表现得更加灵活务实,增加获益的可能性。势头文化是影响部落支持的重要变量,意味着西方国家将塔利班视为叛乱组织与“恐怖之源”,但对部落民众而言,塔利班只是在国家权力变幻中的政治选择之一。(23)Jagmohan Meher,“America’s Coming War in Afghanistan:The ‘Bloody’ Iraq Model,” in Arpita B.Roy and Binoda K.Mishra eds.,Reconstructing Afghanistan: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New Delhi:Shipra Publications,2011,p.106.尽管塔利班发动袭击也会使平民遭受巨大伤害,但许多部落民众仍支持塔利班。究其原因,在部落民看来,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根本无法提供公共产品与保障安全,属于“失势”一方。(24)Kaushik Roy,“Introduction:Warfare and the States in Afghanistan,”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Vol.15,No.3,2012,p.197.塔利班也注意到势头变化能影响民心向背,频繁发动袭击,杀害政府官员,以营造“得势”的政治印象。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给部落社会留下了“势头”属于塔利班的景象,出现支持塔利班的“雪球效应”。(25)Shehzad H.Qazi,“The ‘Neo-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1,No.3,2010,p.491.
在部落体系中,部落民众孕育出独特的部落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阿富汗国家政权的兴衰变迁。特定的政治文化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治结构,才能构建稳定的政治秩序。如何适应阿富汗独特的部落政治文化,在此基础上构筑相应的政治结构,成为阿富汗重建中不可逾越的难题。然而,美国主导下的阿富汗重建以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结构为样板,导致与阿富汗原生的部落政治文化严重不匹配,正是阿富汗重建失败的根源所在。
二、部落政治文化与阿富汗重建的失败
2001年后,阿富汗进入国家重建的新时期。在国家政治风云变幻中,虽然普什图部落社会不断遭受冲击,但它并未完全消亡,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深刻影响着阿富汗重建进程。2021年8月,塔利班在阿富汗再度执政,美国主导下的阿富汗重建最终失败。究其原因,部落社会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则希望在阿富汗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结构。这种外来“移植”的政治结构并不适应阿富汗原生的部落政治文化,因此自然无法在部落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文明之花”。
第一,分权自治传统对现代政治发展形成巨大阻碍。政治发展(26)对于政治发展的学理概念,学界并没有统一界定。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将政治发展解释为政治制度化。他认为政治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政治遗产,政治稳定与否取决于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政治发展预示着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政治制度化以适应社会主体政治参与的要求。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则揭示了政治发展的三种趋势:即个体平等观念的生成、国家能力的增强、政治制度分化与专门化,具体表现为政治结构多元化、政治角色专业化、政治体系制度化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达到高度一体化。参见 [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 67页;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 and Toronto: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6,pp.45-48.是政治生活与政治社会形态由简到繁,由原始到现代的演变过程。它反映了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文明的发展嬗变,揭示了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威的演化变迁。就阿富汗而言,部落社会在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领域对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首先,政治一体化就是以单一的、合法的国家政治权威超越传统的、多元的社会政治权威。(2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27页。阿富汗部落享受高度自治权,国家无法有效整合控制部落。中央政府式微,传统部落对现代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其次,政治制度化主要表现为政治体系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28)Selznick Philip,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New Orleans:Quid Pro Books,2011,p.5.阿富汗政治重建照搬了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架构,忽视了本土原生的部落政治文化的影响。因此,制度化低下的中央政府无法对抗强大的部落社会。最后,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普通部落民众的政治参与仅局限于部落事务,对国家大事并不会投入更多的政治热情。
第二,部落荣誉文化对现代选举政治产生消极影响。阿富汗人具有多重身份,从属于族裔、宗派、语言群体和部落组织等多个群体。他们专门有一套个人身份来定义自己,以反映其社会关系、部落归属及族裔划分等。身份就代表了一种明确区分“我者”与“他者”的身份标识,核心是优先考虑亲属忠诚和部落成员共同行动,捍卫本部落的集体荣誉。(29)法国社会学家吉尔斯·多伦索罗(Gilles Dorronsoro)专门讨论了阿富汗人的这一特征。他指出,“在阿富汗,每个人的认同都由一系列从属关系加以明确定义”,例如,家族成员、部落成员以及伊斯兰社区成员。参见 Gilles Dorronsoro,Revolution Unending:Afghanistan 1979 to the Present,No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10.这种由身份衍生出来的荣誉文化主导着政治竞争,服从或忠诚于部落首领是部落荣誉的召唤,比法律与中央政府的命令更为重要。(30)Akbar S.Ahmed,“Honour and Power in Afghanistan: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Models in Society,”Strategic Studies,Vol.4,No.4,1981,pp.44-47.这种荣誉文化映射于选举政治中,部落民众的政治偏好并不以候选人的个人品德、政治主张、执政能力为主要依据,而是以部落身份附属的荣誉感为重要参照。候选人也会将自己当选宣扬为本部落的集体荣誉,将部落选民的投票支持神圣化为捍卫荣誉的本能。(31)Ken Whalen,“Defacing Kabul:An Iconography of Political Campaign Posters,”Cultural Geographies,Vol.20,No.4,2013,p.544.在某种程度上,统治精英对荣誉文化的操纵和工具化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大大限制了阿富汗重建的努力。
以2009年的大选为例,前任总统卡尔扎伊的亲信竟帮其选举舞弊,一方面对部落首领许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则利用部落身份凝聚荣誉文化,号召同一部落的首领给予投票支持以捍卫部落荣誉。(32)See Timor Sharan and John Heathershaw,“Identity Politics and Statebuilding in Post-Bonn Afghanistan:The 2009 Presidential Election,”Ethnopolitics,Vol.10,No.3-4,2011,pp.297-319.在某种程度上,卡尔扎伊胜选就是部落偏好的结果。在普什图部落之外,他就无法获得重要支持,甚至被戏称为“喀布尔市长”。(33)Shehzad H.Qazi,“The‘Neo-Taliban’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1,No.3,2010.p.497.2014年总统大选,部落仍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加尼在参加阿富汗总统竞选过程中,特地在自己姓名后面加上了部落名称“阿赫马德扎”,以示代表部落竞选,召唤部落选民的荣誉感。(34)Timor Sharan and Srinjoy Bose,“Political Networks and the 2014 Afghan Presidential Election:Power Restructuring,Ethnicity and State Stability,”Conflict,Security & Development,Vol.16,No.6,2016,p.628.在部落荣誉文化的背景下,不考虑阿富汗国情,照搬西方模式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将会出现诸多问题。一方面,候选人在某种程度上基于部落民捍卫荣誉的朴素情感当选,个人品质与执政能力无从谈起,导致政府低效腐败;(35)Michael Callen and James D.Long,“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and Election Fraud: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Afghanista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5,No.1,2015,p.356.另一方面,部落选民的“荣誉投资”要求获得回报,促使人们只想通过部落裙带关系与公共部门“打交道”,政府威信受到严重损害。
第三,政权合法化脱离部落政治文化语境。政权合法化是以自愿而非强制的方式实现合法权利的过程。国家维持非法统治的成本巨大,故而其合法性必须为所在社会认可。(36)[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郭华译,学林出版社,2017年,第37页。政权合法化对国家统治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以来,阿富汗民主政权遭遇的诸多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合法性危机。阿富汗政权合法化需要置于部落政治文化语境中,处理好与部落的互动关系。杜兰尼王朝的建立就源于部落社会的共同推举。历代国王也都与部落建立密切的互利关系,并被人们视为国家层面的“部落首领”。捍卫荣誉的部落忠诚延伸为支持国王统治的信念,加上现实利益的巨大诱惑,国家在部落政治文化语境中实现了政权合法化。一旦国王不考虑部落利益,破坏部落的自治传统,部落随即反抗国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便不复存在。
2001年后,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成为阿富汗中央政府形式上的政权合法化来源。选举被视为战后政治重建的必由之路,象征着从暴力冲突向和平稳定的过渡。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机制来改变以前的恶性政治竞争,并使新的政治秩序合法化。然而,选举产生的阿富汗民主政府无法被所有国民认同,政权合法性难以维系。实际上,阿富汗重建以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作为合法性来源,试图用“法理型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取代阿富汗根深蒂固的“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37)马克思·韦伯将统治合法性归纳为三种权威类型,即传统型、法理型和个人魅力型。“传统型权威”基于对行之多时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权力的遵守与接收,人们不再深究其合理与否;“法理型权威”基于对以理性方式建立的法律制度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个人魅力型”也即“奇里斯玛式型”,所谓“奇里斯玛”(Charisma),本意为神圣的天赋,源于对领袖人物非凡魅力的崇拜与信赖。参见:燕继荣:《发展政治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不过政权合法性始终遭到质疑。阿富汗民主政府也曾意识到这一问题,尝试从部落传统政治文化中探索政权合法化的路径。
最典型的就是通过传统的部落大会制度(支尔格大会)来实现政权合法化。阿富汗先后于2002年和2004年召开紧急支尔格大会和制宪支尔格大会,试图在全体国民中寻求最大共识,从而实现政权合法性。带有浓厚部落色彩的“平民支尔格”(Wolesi Jirga)和“长老支尔格”(Meshrano Jirga)也分别成为国民议会上下两院的新称号,尝试以此凸显部落政治文化,强化政权合法性。然而,这也仅是“新瓶装老酒”。传统部落是高度动态的,遵循其自身的规则,具有独特的政治文化,并在许多情况下与现代国家和民主政体相矛盾。阿富汗在传统部落政治文化的外壳下是一系列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38)以2002年紧急支尔格大会为例,近三分之二的会议代表签署请愿书,要求流亡国王查希尔参与阿富汗新政权的总统竞选。但美国的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勒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却迫使查希尔沙让位给卡尔扎伊,将卡尔扎伊内定为新政府的领导人。美国以贿赂、秘密交易等形式在幕后大规模干预阿富汗大选,使卡尔扎伊最终胜选。参见Thomas J.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309-310.此外,北约驻军的大量存在更与部落的自治传统相悖,使阿富汗民主政权遭到来自国内部落群体的广泛仇视,始终无法摆脱西方傀儡的“污名”。(39)Thomas J.Barfield,“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fghanistan,”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 political-legitimacy-afghanistan,访问时间:2022年2月11日。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政权,美国主导下的阿富汗重建最终失败。
三、部落政治文化与塔利班重掌政权
相比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塔利班扎根于阿富汗原生的部落社会。(40)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AAN Thematic Report,No.4,June,2010,p.3.塔利班以家庭、家族和部落的关系网络整合动员民众,将个人行为转变为集体行动。(41)Ishrat A.Abbasi,et al,“An Overview of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Tribal Areas of Pakistan,”Journal of Academic and Social Research,Vol.1,No.1,2018,p.11.部落作为极具弹性的社会单元,使塔利班拥有了“死灰复燃”的内生能力。自2005年起,塔利班就依靠部落社会重新崛起。可以说,塔利班的再度掌权离不开部落群体的巨大支持。从纵向看,塔利班利用共同的家族、部落关系使其与地方社会网络融为一体;从横向审视,组织成员由共同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身份凝聚团结。(42)Theo Farrell,“Unbeatable:Social Resources,Military Adaptation,and the Afghan Taliban,”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Vol.1,No.3,2018,p.62.由此,部落构成塔利班强大而稳定的社会基础。塔利班正是利用阿富汗独特的部落政治文化,不断弱化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平叛能力,才最终重掌政权。
第一,塔利班利用部落的荣誉文化实现整合动员,壮大自身力量。部落社会中的所有行为无不受到普什图人荣誉观的影响。荣誉可以被看做是阿富汗生活的核心特征。荣誉可以转化为权力,而权力没有荣誉则无法维持。(43)Akbar S.Ahmed,“Honour and Power in Afghanistan: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Models in Society,”Strategic Studies,Vol.4,No.4,1981,p.44.在阿富汗人眼中,荣誉是最高的个人价值,任何侵犯或失去一个人“荣誉”的行为都会促使人们立即采取报复行动。阿富汗人认为,不正当地闯入一个村庄或家庭,杀害自己的家庭成员,触摸自己家庭以外的妇女,以及在家人和邻居面前给阿富汗男性戴上头罩和手铐,都是对个人荣誉的极大侵犯。寻求报复的人通常会将当地反政府的塔利班相结合,以“纠正他们的错误。”(44)Shehzad H.Qazi,“The ‘Neo-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1,No.3,2010,pp.492-495.人们可以为捍卫荣誉而战死,但不能忍受丧失荣誉却苟且偷生。辱没荣誉会是某个家族、部落几代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正如普什图谚语所言,“我为头颅舍弃珍宝,我为荣誉牺牲生命。”(45)Shahmahmood Miakhel,“Understanding Afghanistan:The Importance of Trib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in Security and Governance,”Asian Survey,Vol.35,No.7,1995,p.3.
自治是普什图部落在阿富汗国家体系中获得的传统特权之一。(46)Afghanistan Analyst Network,“Doing Pashto:Pashtunwali as the Ideal of Honourable Behavior and Tribal Life among Pashtuns,” AAN Thematic Report,No.1,March,2011,p.2.而这也与荣誉文化息息相关,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干预会被视为有损部落荣誉。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在部落荣誉文化的刺激下,普什图部落也迅速投入到抗苏运动中,大多以亲族、村庄或部落为纽带形成独立地方武装进行抗争。苏联撤军后,普什图部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社会和政治权威日益弱化和瓦解。相反,以北方联盟为首的少数族群却不断崛起。作为阿富汗历史上的统治精英,普什图人将之视为集体荣誉的巨大耻辱,必须加以改变以捍卫荣誉。在这种背景下,由于部落的社会权威呈现“碎片化”,普通部落民无法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塔利班便成为部落社会的最佳选择,以恢复普什图人的统治地位。(47)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How Tribal Are the Taleban?”AAN Thematic Report,No.4,June,2010,p.3.因此,部落构成塔利班强大的社会基础,塔利班的政治实践也充分迎合了普什图人的部落文化与集体诉求。从塔利班领导层就可管窥独有的“部落印记”,大多数高级领导人都具有部落身份。(48)See Ahmed Rashid,Taliban:Militant Islam 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252-255.
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尝试在部落社会实行直接统治,填补农村部落地区的权力真空。但是,部落社会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治传统。在荣誉文化的影响下,这种自治传统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无法自治意味着辱没荣誉,部落社会坚决反对政府的集权化努力。在这种情况下,荣誉文化被塔利班用来转移公众对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忠诚。塔利班有关荣誉的叙事模式明确使用阿富汗历史上的例子,通过唤起普什图人抵御外侮的集体记忆,试图与所有普什图人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系。它不断鼓吹北约驻军的存在是外国势力对阿富汗的第四次入侵,宣称世代战斗是一种荣誉,是真主的奖赏,从而在阿巴边境的部落地区迅速重组。(49)Hiranmay Karlekar,Endgame in Afghanistan:For Whom the Dice Roll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12,p.23.同时,塔利班还对当局的政策失误进行猛烈攻击,将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污名化为美国支持的“傀儡”政权,提出“今天,一些受美国训练的仆人……破坏了阿富汗的荣誉历史,这是巨大的遗憾。”(50)Thomas H.Johnson,et al,Taliban Narratives:The Use and Power of Stories in the Afghanistan Confli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64.由此,塔利班刻意将自身塑造为部落荣誉的“捍卫者”,获得了部落社会的广泛支持。根据民调显示,2019年,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扎布尔和乌鲁兹甘省,超过半数的民众同情塔利班。(51)Tabasum Akseer and John Rieger eds.,A Survey of the Afghan People:Afghanistan in 2019,The Asia Foundation,2019,p.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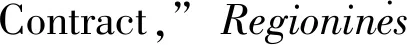
事实上,塔利班一直有意识地努力创造和维持这种“文化弹药库”。这在战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组织成员的战斗士气、团队精神和荣誉认知。他们利用自豪与荣誉的部落元素,动员部落支持以维护正义,抵抗外国入侵者。借此,塔利班拥有源源不断的后备战斗人员,其支持者不一定是宗教狂热分子,而是普通的阿富汗人。这些战士是“被迫”加入塔利班的,目的就是捍卫荣誉,或“纠正”地方腐败政府的错误。塔利班很容易唤起人们的愤怒,利用支持者的情绪冲动进行暴力活动,并宣称其为报复不荣誉和纠正对个人自尊侮辱的工具。一方面,塔利班会发放外国军队对妇女不当触摸的传单,(53)有关传单的详细内容,参见Fida Mohammad,et al,“Honor,Revenge in Socio-Geographic Space of Pashtuns,”Pakist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Vol.8,No.3,2016,pp.74-90.以此向“潜在的支持者传递公开信息,是呼吁阿富汗人寻求报复与捍卫荣誉的集结号。”(54)Ayaz A.Shah,et al,“Jihad or Revenge:Theorizing Radicalization in Pashtun Tribal Belt along the Border of Afghanistan,”Global Political Review,Vol.4,No.2,2019,p.67.另一方面,外国驻军在阿富汗村庄进行例行扫荡,搜寻塔利班成员时,对村民进行人身虐待,损坏个人财产,并对妇女进行搜身,这是对一个家庭荣誉的重大侮辱。塔利班会对这些行为进行大肆宣传,进一步抹杀国际军事力量的信誉。如果出现了平民死亡,将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普什图人和阿富汗社会普遍重视荣誉和报复(Badal)。正如普什图谚语所云:“除非一个人向敌人报仇,否则真正的人不会休息、吃饭。”(55)Fida Mohammad,et al,“Honor,Revenge in Socio-Geographic Space of Pashtuns,” Pakist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Vol.8,No.3,2016,p.81.人们常说,一个无辜者的死亡会造就十个未来的敌人。正是这种荣誉文化的加持,塔利班的所有行为都带上了神圣的“荣誉光环”。对塔利班来说,维护荣誉和展示男子气概的重要表现是愿意与其合作,寻求对外国驻军的报复,拒绝任何塔利班认为非伊斯兰的影响。
除此之外,塔利班还有多种形式利用荣誉文化进行宣传动员,其中创造诗歌也是另一种重要的方式。2009年11月,塔利班已故领导人毛拉·奥马尔发表开斋节声明,呼吁阿富汗诗人帮助支持塔利班。他敦促“坚定而明智的诗人在诗歌与文学作品中保留圣战史诗与圣战者的英雄行为,并为独立、荣誉与伊斯兰的复兴激发情感。”(56)Thomas H.Johnson,et al,Taliban Narratives:The Use and Power of Stories in the Afghanistan Conflict,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109.塔利班诗歌的主题就是保卫祖国,伊斯兰教及阿富汗人的荣誉。诗中反复提到个人荣誉、男子气概、寻求复仇等词汇,以最大限度地引起普什图人的荣誉共鸣。这些诗歌不仅是为他们的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方式进行辩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更大的伊斯兰社会使战争神圣化。塔利班试图将正在进行的斗争描述为一场荣誉之战。另外,夜间信件(Shabnamah)也是塔利班传播荣誉观念的重要载体。这种信件往往会威胁使用暴力或死亡,但其内容也包括颂扬“殉道”的力量,要求勇敢的阿富汗人必须牺牲自己来拯救阿富汗,宣称对抗敌人的斗争涉及到拯救荣誉。
现今,塔利班不仅东山再起,演变成所谓的“新塔利班”,再度夺取阿富汗政权。究其原因,部落始终是塔利班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它通过不断复制“宗教+部落”抵抗模式,充分利用部落政治文化,更好地整合动员了异质的部落群体。(57)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8期,第5页。一方面,荣誉和耻感文化是普什图人的独特情感。塔利班将之与强烈的宗教情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转化成最为有效的动员工具。(58)Michael Semple,Rhetoric,Ideology,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aliban Movemen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14,p.13.塔利班将自己所有的行为都带上了“荣誉光环”,深度嵌合了部落社会根深蒂固的荣誉文化,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部落支持,以很小的代价获取更大的胜利。(59)Shehzad H.Qazi,“The ‘Neo-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1,No.3,2010,p.488.另一方面,外国军事力量并不了解这种荣誉文化。在平叛过程中,他们的不当行为屡屡触犯部落的“荣誉禁区”,不断挑衅部落荣誉的神圣性。加上塔利班的大力宣传,他们在阿富汗的行动被异化为辱没荣誉的“入侵”,无法取得合法性,部落支持的天平逐渐倾向塔利班。
第二,部落的庇护和礼遇文化使塔利班能“化整为零”,实现重组。普什图部落具有慷慨待客的悠久传统,也是普什图人最为自豪的荣誉之一,表达了部落民不求回报的给予习惯。对普什图人来说,送出财物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礼遇(Melmastyā)与庇护是表现慷慨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是否来自同一部落抑或是陌生人,甚至是仇敌,只要他获准进入普什图人的领地,都会被热情招待与获得保护。普什图人认为,客人是安拉派来的礼物,好客是一种信仰虔诚的行为。任何在部落中停留的路人都会被视为整个部落的贵客,将被邀请至“胡吉拉”(Hujra)(60)即公共招待所,除了清真寺,“胡吉拉”也是普什图人的公共活动与社交场所,普什图青年正是在这里通晓了普什图瓦里。参见Shahmahmood Miakhel,“Understanding Afghanistan:The Importance of Trib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in Security and Governance,”Asian Survey,Vol.35,No.7,1995,p.8.居住。普什图人会提供最好的食物,赐予宾客最好座位。茶余饭后,部落中的所有男性成员都聚集在“胡吉拉”陪侍访客,聆听客人的经历故事,也为他们提供娱乐活动。对普什图人而言,热情待客的人会受到极大尊敬,属于部落社会中的至高荣誉。而拒绝礼遇与庇护宾客的人将不被视为普什图人,带走客人更是对普什图人最大的侮辱。(61)Shahmahmood Miakhel,“Understanding Afghanistan:The Importance of Tribal Culture and Structure in Security and Governance,”Asian Survey,Vol.35,No.7,1995,pp.7-8.
事实上,庇护和礼遇是普什图人展示财富和获得声誉的一种方式。该传统由保护旅行者的安全演变而来,实际上是一种传播信息的机制。在普什图部落,要想让荣誉足够有价值,关于荣誉的信息就必须广泛传播。荣誉在部落社会就是“虚拟财富”,如果一个普什图人付出沉重代价捍卫了荣誉,那么他的个人事迹和美好品格必须为人所知。(62)Bruce L.Benson and Zafar R.Siddiqui,“Pashtunwali——Law for the Lawless,Defense for the Stateles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7,2014,pp.115-116.因此,普什图人会以最高的礼遇招待和庇护过路宾客。他们会成为最好的传播媒介,将普什图人的荣誉最大范围地传播开来。然而,2001年以来,庇护和礼遇的概念已逐渐改变,部落社会将外国势力视为阿富汗动荡的根源,反而会违背礼遇庇护的传统,允许塔利班驱逐外国势力。(63)Muhammad Tariq,et al,“The Pashtun Tribal System and Issues of Security,”Global Social Sciences Review,Vol.3,No.1,2018,pp.106-107.相反,塔利班成为部落社会礼遇庇护的重点对象。
正是由于这种庇护和礼遇文化的加持,即使政权瓦解,塔利班也能在阿富汗南部的部落地区迅速“化整为零”,实现重组,演变成所谓的“新塔利班”。(64)Zahoor A.Wani,“Afghanistan’s Neo-Taliban Puzzle,”South Asia Research,Vol.41,No.2,2021,p.14.在美国和北方联盟联合打击下,虽然塔利班伤亡了约20%的成员,但残余势力却逃到部落地区得到了安全庇护。(65)Antonio Giustozzi,The Taliban at War:2001-2018,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17-18.塔利班进入部落地区会被当作尊贵的“客人”,部落民会不惜一切代价提供庇护。(66)Shahmahmood Miakhel,“The Importance of Tribal Structures and Pakhtunwali in Afghanistan:Their Role in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in Arpita B.Roy ed.,Challenges and Dilemmas of State Building in Afghanistan:Report of a Study Trip to Kabul,New Delhi:Shipra Publications,2008,pp.102-103.这种庇护文化为塔利班“编织”起庞大的部落庇护网络,使其不断获得强大的部落支持。比如,部落民成为塔利班招募的主要对象。有些部落甚至协助塔利班从事袭击和破坏活动。据一项调查显示,2006年后,普什图部落的青年成为塔利班的重要招募来源。他们缺少工作机会,生活异常困顿,对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极为不满,在塔利班的动员下便加入了该组织。(67)Antonio Giustozzi,“Negotiating with the Taliban Issues and Prospects,”A Century Foundation Report,June, 2010,p.11.在部落地区,庇护和礼遇文化使塔利班拥有强大的安全屏障,抵消了外国驻军的技术力量与优势。
除了安全庇护,部落社会还为塔利班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构筑了庇护文化与部落亲缘相结合的地方后勤系统。(68)Muhammad A.Rana,“The Taliban Consolidate Control in Pakistan’s Tribal Regions,”CTC Sentinel,Vol.1,No.7,2008,p.8.部落民为其秘密提供基础设施,充当上传下达的联系枢纽,协调塔利班具体的叛乱行动。由于每个地区的乡村部落情况各异,这种支持网络的组织结构也大相径庭。一般而言,它通常由一名部落长老策划,同部落的青年负责具体实施,而这些人的亲属很可能就是塔利班成员。他们行动隐秘,负责充当向导,运送弹药与汇报当局动向等工作,有时甚至行使“影子政府”的职能。(69)[澳]戴维·基尔卡伦:《意外的游击战: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修光敏、王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6-99页。正如一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官员所言,“部落力量在阿富汗非常强大,如果整个部落能够形成共识,禁止塔利班进入,塔利班在部落将难有容身之地。相反,现在部落民普遍认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是外国势力支持的‘坏政府’,他们故而对其全无好感,转而支持塔利班。”(70)UBC Liu Institute for Global Issues,“The Challenge of Constructing Legitimacy in Peacebuilding:Case of Afghanistan,” CIR Working Paper,No.47,October,2008,p.13.
塔利班一直就刻意利用这种庇护文化,将自身塑造成部落底层的政治代表。许多部落民开始坚信塔利班就是他们的“救星”,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庇护。(71)Muhammad A.Rana,“Taliban Insurgency in Pakistan:A Counterinsurgency Perspective,”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Vol.2,No.2,2009,p.8.第一次执政期间,塔利班忽视民众诉求与切身利益,政策极为僵化保守。然而,2002年后,塔利班逃往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部落地区,不仅利用传统庇护文化获得安全庇护,而且给予当地贫困的部落成员大量金钱,以获得部落社会的全面支持。(72)事实上,收取客人钱财违背了庇护的传统,也公然违反了普什图瓦里的所有规范,参见Abdul Shakoor,“Pakhtun Cultural Values,Terrorism and the Contextual Meaning of Violence,”Pakist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Vol.5,No.2,2013,p.78.大多数部落民都选择为塔利班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丰厚的金钱。人们甚至将这种庇护当成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在自己的房屋中为塔利班建造了秘密营地。塔利班为日常开支向所在部落家庭支付了大笔费用,不仅为武装分子向部落地区渗透铺平了道路,还导致部落成员中寻租文化的勃兴,从而进一步深深扎根于部落社会。
此外,塔利班还关注到部落地区的社会治理,为当地的部落民提供公共服务。以司法审判为例,由于当局的司法体系腐败低效,塔利班设立宗教法庭,以公正高效地为部落民解决司法纠纷。与此同时,塔利班也充分尊重部落首领与长老,迎合部落地区的风俗传统,不断宣传在保卫伊斯兰信仰与部落文化。(73)Michael Semple,Rhetoric,Ideology,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Taliban Movemen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14,pp.72-76.当地的部落民始终相信,他们为塔利班圣战者提供庇护,实际上就是在为伟大的伊斯兰事业服务。(74)Habib Ullah and Muhammad H.Khalil,“The Impact of US Invasion in Afghanistan on the Tribal Culture of Waziristan,”Pakistan Journal of History and Culture,Vol.40,No.1,2019,p.126.当外国驻军在部落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时,部落民会加以抵制。他们认为,这些外国势力是在与自己的塔利班客人作战,无法庇护塔利班会辱没荣誉。(75)Surat Khan,et al,“The Effects of Militancy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on Pashtu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in FATA,”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3,No.1,2019,p.77.尽管许多普什图人愿意支持西方军队确保和平与稳定,但大多数人由于必须在当地部落庇护塔利班而受到限制。庇护文化成为维持塔利班的文化黏合剂,在部落地区为塔利班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76)Jonathan Hawkins,“The Pashtun Cultural Code:Pashtunwali,”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Journal,Vol.180,2009,pp.16-19.加上通过提供金钱来收买当地部落民,塔利班拥有了部落的“庇护堡垒”,最终重新崛起并再次掌权。
第三,塔利班努力迎合部落势头文化以换取支持。通权达变是部落民的传统特征。阿富汗人有在适当时机“叛变”的传统,投机性背叛的艺术与阿富汗本身一样古老。他们历来勇武并崇尚强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最终目的就是在动荡冲突的社会环境生存下来。因此,“势头”成为部落民众选择支持对象的重要参照。虽然血缘谱系对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至关重要,但它无法左右部落民的联盟取向。在部落地区,政治联盟的内在动因完全以现实利益为基础。人们经常变换阵营,昨天的仇敌很可能成为今天的盟友。经过一系列利弊权衡,部落民总是愿意追随那些能给其带来巨大利益的“胜利者”。部落地区自古就有不与“失败者”为伍的政治传统,并逐渐衍生出“权力先行,支持随后”的势头文化,即人们的政治从属紧跟权力变化,权力体系有一系列个人选择来构建,只要强者才能获得广泛支持。(77)[挪威]弗雷德里克·巴特:《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一个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范例》,黄建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页。实际上,在权力分散的政治环境中,这种“识时务”是部落社会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
对部落民来说,塔利班并非实施暴力袭击的恐怖组织,而是在混乱动荡社会环境中的一种政治联盟选择。(78)Jagmohan Meher,“America’s Coming War in Afghanistan:The ‘Bloody’ Iraq Model,” in Arpita B.Roy and Binoda K.Mishra eds.,Reconstructing Afghanistan:Prospects and Limitations,New Delhi:Shipra Publications,2011,p.106.抗苏运动时期,普什图人就表现得非常务实。一个家庭中的不同成员会选择加入不同的政治阵营,既有人支持人民民主党政权,也有人加入穆斯林游击队。人们会根据局势变化适机转变自己的立场,政治联盟的关系往往是短暂且松散的。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一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分别加入了塔利班、地方军阀、北方联盟等政治阵营。(79)Vern Liebl,“Pushtuns,Tribalism,Leadership,Islam and Taliban:A Short View,”Small Wars & Insurgencies,Vol.18,No.3,2007,p.497.塔利班也注意到了这种势头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它利用多种方式动员普什图人支持塔利班,其中就包括通过营造“得势”的社会印象,增加对部落首领与追随者的吸引力。(80)Shehzad H.Qazi,“The ‘Neo-Taliban’ and Counter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1,No.3,2010,p.488.大多数阿富汗人支持塔利班并非只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他们对冲突双方的势头都保持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最终目的都是能够加入胜利的一方生存下来。
2001年以来,虽然塔利班在实施暴力活动的过程中常使平民也遭受巨大伤亡,但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孱弱无力,无法为部落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失势的“失败者”印象。不与“失败者”同行的政治传统导致部落民众纷纷支持塔利班,以获得最大的现实利益。(81)Kaushik Roy,“Introduction:Warfare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Vol.15,No.3,2012,p.197.一名塔利班高层透露,塔利班在国家部门、军队与西方援助机构中拥有数千名“线人”。另据报道,在塔利班重掌政权之前,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官员与安全部队就已出现与塔利班接触的现象。(82)Hiranmay Karlekar,Endgame in Afghanistan:For Whom the Dice Rolls,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2012,pp.35-36.许多阿富汗人提前为塔利班回归做好准备,将之视为一项长远的政治投资。他们希望将来塔利班重掌政权后能够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可以说,普什图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政治联盟的选择中,只有现实利益才是普什图人主要考虑的优先事项。
鉴于这种独特的势头文化会影响政治联盟,在某种意义上,塔利班在阿富汗国内频繁发动叛乱活动就是为了塑造“得势”的形象,从而积极争取部落社会的拥护。例如,塔利班在阿富汗东部和东南部等地区充分迎合这种势头文化,通过杀害政府官员,支持政府的毛拉和占领卫戍哨所等行动。同时,他们的行动往往伴随着强大的宣传攻势,给人们留下一种得势的“胜利者”印象。(83)Brian G.Williams,Afghanistan Declassified:A Guide to American’s Longest War,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2,pp.171-172.而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表现出了更强的撤军决心,并与塔利班在多哈密切接触与谈判,塔利班制造的袭击活动急剧上升。(84)从袭击对象来看,相比于“伊斯兰国”无差别地发动袭击,塔利班攻击的对象主要集中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官员和军警等目标。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部落势头文化的影响。这一方面有争取谈判资本的政治考量,更多的是营造塔利班“得势”的政治形象。正是在这种势头文化的影响下,随着美军的撤离,部落民众根据局势发展不约而同地选择支持塔利班,导致社会支持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反观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则如“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政权垮台一发不可收拾。
总体来看,塔利班在阿富汗再度掌权并非偶然。一方面,塔利班通过不断改组整合,组织结构日益完善成熟,并通过各种渠道募捐活动资金,向全球招募人员,使其获得不断再生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塔利班深深扎根于部落社会,深度嵌合部落传统政治文化,凭借各种宣传渠道不断动员部落民,以获得部落地区坚实的社会基础。当前,塔利班再度执政已有数月,仍然充分发挥部落政治文化的实际效用,以伊斯兰传统与部落政治文化重塑阿富汗社会。
四、部落政治文化与塔利班政权的前景
2021年8月,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掌政权,并开始了重建国家的政治实践。政权更替是阿富汗历史发展的变量,而恒量则是根深蒂固的部落政治文化。部落社会是阿富汗历史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形式,孕育出了独特的部落政治文化,深刻影响着阿富汗国家的历史演进。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浪潮波及阿富汗,部落社会与现代国家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成为阿富汗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事实上,这一特征本质上体现了传统部落社会如何与现代国家深度嵌合。其中,现代政治结构如何适应的传统部落政治文化,是阿富汗政治精英必须要解决的深层症结。虽然国家具有二元性,即国家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也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但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建设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
阿富汗社会文化的核心不是西方式的公民,而是部落成员。部落归属使人们充满自豪感和自尊心,激励家庭相互保护和彼此关心,并遵守严格的仪式,确认他们作为部落成员与祖先、土地和神灵的联系。这种亲属关系创造了信任和忠诚,人们知道并且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维持部落秩序的不是等级制度和法律,而是强调相互尊重、荣誉尊严的普什图瓦里。普什图瓦里凝结了部落民的集体智慧,也衍生出部落别具一格的政治文化,稳定地维持了地方秩序。部落本质上是保守的,人们讨厌改变,亦不会改变。(85)David Ronfeldt,“Tribes——The First and Forever Form,” The RAND Pardee Center Working Paper,December,2006,p.73.几个世纪以来,部落制度一直是中亚的治理手段。自居鲁士大帝以来,外部力量越是试图改变部落的生活方式,部落就越反抗。(86)Jim Gant,One Tribe at a Time,Los Angeles:Nine Sisters Imports,2009,p.14.部落民众不太关国家事务,而更关心保护他的家庭领地、部落习俗、部落首领及战士荣誉。部落群体为阿富汗国家提供了独特的部落政治文化,反映在政治上便是充斥着前现代治理模式的文化元素。
2001年后,新的政治秩序和民主政权建立起来,阿富汗重建也随之开启。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中央集权形式的政治结构最适合阿富汗,强大的总统权力一直与法律、秩序和稳定联系在一起,并被认为符合该国数百年的文化传统。(87)Inomzhon Bobokulov,“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Decentralization vs.Centralization,”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Vol.16,No.2,2015,p.107.2004年,根据阿富汗宪法规定,阿富汗是一个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意味着部落没有自治权,只能进行政治参与。(88)“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 The_Constitution_of_the_Islamic_Republic_of_Afghanistan.pdf,访问时间:2022年3月12日。然而,阿富汗的权力传统上是在部落一级执行的。部落权威充当政府与乡村之间的权力中介,中央政府从未成功地推翻或改造这种根深蒂固的部落组织形式。(89)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Afghanistan’s Alternatives for Peace,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Transforming Subjects to Citizens and Rulers to Civil Servants,”The Afghanistan Papers,No.2,August,2009,p.6.在多年的内部冲突中,部落的自主性和社会政治意义得到加强,并拥有大量资源来对抗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喀布尔当局表现无能,几乎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政治稳定,维护社会治安和促进经济繁荣。事实上,阿富汗是世界上权力最分散的国家之一,但在法律意义上却拥有集中化的宪政体系,这是自相矛盾的。(90)Robert D.Lamb and Brooke Shawn,“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Strategy in Afghanistan:A Report of the 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pril,2012,p.15.
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宪法第137条规定:“在维护集中制原则的情况下,政府应依法将必要的权力移交给地方行政部门,以加快改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并促进人们参与和发展国家生活。”(91)“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IMG/pdf/ The_Constitution_of_the_Islamic_Republic_of_Afghanistan.pdf,访问时间:2022年3月12日。然而,地方自治的原则从未付诸实施,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国家总统权力。在卡尔扎伊时期,总统制成为国家政治体系的核心环节。国家元首掌握了所有权力,关键的政治决策则由他所主导的中央政府做出,甚至关于各省学校校长和教师的任命也完全由喀布尔决定。(92)William Maley,“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Challenges and Pathologies,”Central Asian Survey,Vol.32,No.3,2013,p.259.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争取政府集权与部落要求独立自治的冲突便随之爆发。随着政府日益集权化,部落支持也随之减少。正如阿富汗谚语所言:“每个阿富汗人都梦想有一天能占领喀布尔。但一旦他这样做,他将失去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93)Bobokulov Inomzhon,“State-building in Afghanistan:Decentralization vs.Centralization,”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Vol.16,No.2,2015,p.112.即使在现代军队的帮助下,以西方国家观念为基础的中央国家集权模式也无法摧毁阿富汗社会组织的部落基础。美国学者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就曾指出,“阿富汗政治生态的特点是一个中心(无论它在哪里)主导着不同地区,而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政治精英。”(94)Thomas J.Barfield,Afghanistan:A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62.这从官方当局只能控制喀布尔,无法影响广大的乡村部落地区就可窥见一斑。
不难发现,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的新秩序是为了回应国际期望,不仅挑战了阿富汗原生的部落政治文化,还对该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原始忠诚形成威胁。(95)Anwar Ouassini,“Afghanistan:The Shifting Religio-Order and Islamic Democracy,” Политикологиjа религиjе,Vol.12,No.2,2018,p.313.以集权为特征的民主政治结构与阿富汗原生的部落政治文化并不相适应。部落群体的分权自治与荣誉相联系,国家向部落社会的渗透都会被视为有损荣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阿富汗内部“马赛克式”的分裂。加上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腐败无能,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务实灵活的势头文化促使人们全力支持塔利班。对部落民来说,如果政府不能保护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站在塔利班一边。塔利班多年来一直在部落地区运作,建立伊斯兰法院和“影子政府”以深度嵌合传统的部落政治文化,向部落民提供无法从偏远和腐败的政府那里获得的公平和正义。塔利班还利用捍卫荣誉的文化武器宣传动员,在心怀不满的部落成员中寻找“新鲜血液”,许多部落成员将塔利班视为生存的唯一途径:像塔利班一样杀戮或被塔利班杀死。(96)Jim Gant,One Tribe at a Time,Los Angeles:Nine Sisters Imports,2009,pp.26-29.实际上,正是塔利班利用传统的部落政治文化来建构合法性,才能够获得稳定的部落支持。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严重依赖外援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自然无法抵御塔利班的猛烈攻势。
普什图部落构成塔利班强大的社会基础,但部落本身并不是敌人。部落是文明演进过程中衍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自己的运行逻辑,与阿富汗国内独特的自然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原始、落后与野蛮。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部落与国家是属于“针尖对麦芒”,现代国家的集权性必然会破坏传统部落社会的自治权,并和与之相关的部落政治文化背道而驰。然而,国家政权的稳定构建无法脱离传统的社会文化土壤,政权更迭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的“长时段”部落政治文化恒量。(9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集权特征的政府体系与阿富汗原生的部落政治文化相悖,这导致美国支持下的阿富汗政权走向垮台成为必然。
事实上,政府是政治体系的核心要素,被称为“国家”的架构的稳定性本质上取决于它。政府作为在宪法框架内运作的政治机构应符合社会的基本原则,并结合共存于其中的民众的价值观和传统规范,这被认为是极其合理的。在此过程中,将地方自治机制充分融入国家权力体系,赋予地方机构实权是极其重要的。聚焦于阿富汗,部落社会往往高度自治,没有专门的政治角色,对专门政治对象的认知接近于零。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国家重建的政治实践中面临着部落狭隘的政治文化。由于部落政治文化未能与中央政治体系朝着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阿富汗最终形成了一种多元混合的政治文化,与其新兴的国家政治结构之间存在深刻的不一致。(98)Jim Gant,One Tribe at a Time,Los Angeles:Nine Sisters Imports,2009,p.14.
虽然部落社会在多年冲突中遭到残酷打击(99)部落地区的大量汗和马利克被秘密处决或驱逐,参见Jennifer Murtazashvili,Informal Order and the State in Afghanist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pp.54-55,58-59.,但通过支持部落地区独立自治,充分迎合部落政治文化,塔利班可以在阿富汗取得积极进展。塔利班明白部落是阿富汗社会唯一不变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也是所有阿富汗人都理解的社会传统。他们要做的就是为普什图部落保留数百年的生活方式,并将普什图霸权在阿富汗加以制度化。(100)Anwar Ouassini,“Afghanistan:The Shifting Religio-Order and Islamic Democracy,”Политикологиjа религиjе,Vol.12,No.2,2018,p.320.毫无疑问,现今塔利班新政权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塔利班希望采用“真正的伊斯兰制度”来建立政府架构;另一方面,他们对国家的制度设想又要向国际社会妥协,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援助。从部落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无论该政权建立何种政治结构,它都需要适应以普什图瓦里为核心的部落政治文化。在此基础上,阿富汗才能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推动国家重建进程。这不仅考验塔利班领导层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帮助。
当前,塔利班领导人还没有阐明他们如何构建国家的清晰愿景。塔利班声称,政策承诺需要安全、资源和时间。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依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程,其细节在很大程度上仍很神秘。相对而言,塔利班内部对统治模式也有多种看法,仍在努力构建和正式确定其治理结构。(101)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Afghan Taliban Views on Legitimate Islamic Governance:Certainties,Ambiguities,and Areas for Compromise,” Peaceworks,No.183,February,2022,p.4.由于伊斯兰教法没有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提供现成的制度设计,也没有规定塔利班应该如何管理国家,塔利班第二次执政的政治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塔利班还无法改变阿富汗根深蒂固的部落社会结构,政策实施会迎合传统的部落政治文化。比如,塔利班通过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对政敌实行特赦,来展示塔利班的仁慈。(102)Mahfuh B.H.Halimi,et al,“Radical Ideological Narratives Following the Taliban’s Takeover of Afghanistan,”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Vol.14,No.1,2022,p.123.在某种程度上,部落社会拥有宽恕(Nanawati)的传统政治文化,宽恕自己的敌人会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誉。塔利班的做法无疑会在部落社会获得极大的称赞,从而进一步争取部落群体的支持。塔利班如今已变得更加务实灵活,它将如何进行政治制度设计,以深度嵌合部落传统的政治文化,值得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