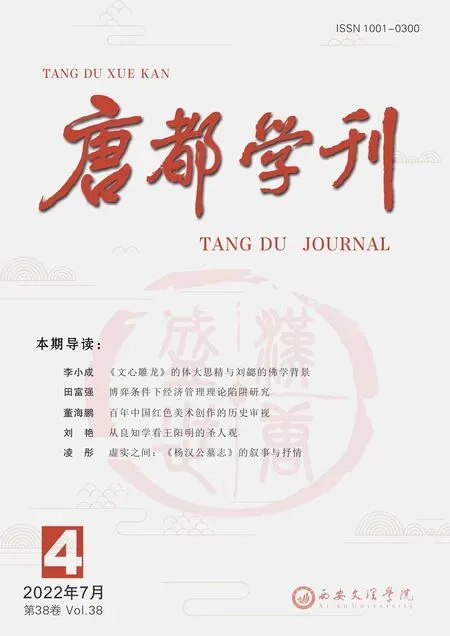明中叶内阁首辅之争与阁臣失意文学
张 英
(江苏理工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天顺年间,明代内阁开始出现首、次辅之分。内阁票拟权渐归首辅,阁权向首辅集中。阁臣们为首辅之位展开了或明或暗的激烈争夺,而其成败直接关涉阁臣的处境和人生感受,并影响到阁臣文学创作的风貌。一般而言,馆阁文学多呈现“雍容典雅”之态,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应制和应酬之作为多。而斗争中失利的阁臣却往往能超脱于馆阁文学的一般特点,打破自己以往诗歌创作的套路和模式,呈现出另一番风貌。本文中,我们把阁臣在内阁斗争失利后的文学创作,称之为“失意文学”。“失意”文学与“贬谪”文学以及“隐士”文学具有相似之处,其作者都不是或不再是身居高位之人,但与“贬谪”相比,“失意”者涵盖范围更广,可以“泛贬谪”视之,凡贬谪、罢官、致仕、下狱等状况下所写的作品,都可包含在内;与“隐士”相比,“失意”者更加被动,“隐”的状况并非他们的主动选择,因此失意文学中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更为明显,很难达到一种旷达平和的状态。这些“失意文学”往往质量较高,甚至可能成为一个人创作的巅峰,值得我们关注。
一、内阁首辅之得意与失意
内阁权力的加强与集中,使嘉靖至隆庆年间的内阁首辅之争异常激烈,而在首辅之争中,阁权对皇权之依附愈加明显,皇帝的信任与偏爱成为得到重用的关键。阁臣对首辅的争夺中结合了对皇帝的谄媚与对政敌的构陷,助长了专制与腐败,实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嘉靖中后期夏言、严嵩、徐阶相继为首辅,其间的斗争可作为内阁首辅之争的典型。首辅们无论在得意抑或失意之际,均为皇权之棋子,内阁在表面上权力膨胀,实际上进入了最无建树的时期。
(一)夏言、严嵩之争
夏言前期仕途较顺利,以请“分祀天地”而“大蒙帝眷”,升为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入阁,十七年(1538)底即成为首辅,严嵩则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始入阁。严与夏皆江西人,严嵩入阁较晚,对夏言甚为恭谨,而夏言则只将严嵩当门客看待。严嵩曾云:“吾平生为贵溪所狼藉,不可胜数。”[1]在此屈抑之下,严嵩韬光养晦,对夏言柔媚敷衍。《明史·严嵩传》中记载:“(嵩)始倚言,事之谨,尝置酒邀言,躬诣其第,言辞不见。嵩布席,展所具启,跻读。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2]7915
严嵩与夏言在争首辅之位的过程中,谄媚嘉靖是其主要手段,他对嘉靖帝之性情有细致体察,“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3]与之相比,成为首辅之后的夏言常有恃才傲物之举,未妥善顾及皇帝的感受。嘉靖帝因崇信道教,在宫中常做斋醮之事,斋醮所用之“青词”,常由内阁文臣来完成。夏言与严嵩都擅长青词撰写,但自夏言成为首辅之后,渐对青词漫不经心,每不能令嘉靖满意,而严嵩则对此格外用心。嘉靖帝曾赏赐五位近臣“香叶冠”,夏言不肯佩戴,而严嵩不仅佩戴“香叶冠”,且为示恭敬而“笼以轻纱”。此外,夏言还有违制乘轿入苑的情况,凡此种种,令嘉靖帝越发疏远夏言,遂借天象之由令夏言革职闲住:“当是时,帝虽优礼言,然恩眷不及初矣……,帝积数憾欲去言,而严嵩因得而间之。”[2]7916
夏言被革职后,严嵩独掌内阁大权,日益骄横。嘉靖察觉后曾再度召回夏言,夏言对严嵩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言至,直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顾嵩,嵩噤不敢吐一语。所引用私人,言斥逐之,亦不敢救,衔次骨。”[2]7916打压之外,夏言本欲揭发严嵩之子严世蕃贪腐,严嵩得知消息后与严世蕃跪求于夏言榻前而得解。这一事件之后,严嵩对夏言越发欲除之而后快。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总督曾铣上《请复河套疏》,请朝廷派兵收复河套地区,夏言表示支持,而嘉靖帝先赞同而后又动摇。严嵩察觉其真实想法后,上言力陈河套不可复,称曾铣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并暗指夏言专权独断,阻断言路,还授意言官弹劾夏言收受曾铣贿赂。结果曾铣以“隐匿边情,交结近侍官员”[2]5197的罪名被斩首,夏言被捕入狱,几个月后遭弃市之刑,成为明代首辅遭极刑的第一人。
(二)严嵩、徐阶之争
徐阶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内阁,十年之后扳倒严嵩而成为首辅。在政治上,与恃才傲物的夏言不同,徐阶既欲在事功上有所作为,同时在政治手段上相当老到,机警而隐忍。在其入阁之时,严嵩已把持朝政十余年,大权独揽,“大臣希得谒见,惟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2]7917徐阶因曾受夏言提拔,遭严嵩的种种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徐阶一方面曲事严嵩,不惜将孙女嫁给严世蕃之子为妾,“分宜(严嵩)在位,权宠震世,华亭(徐阶)屈己事之,凡可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附籍、结姻以固其好。”[4]另一方面,“益精治斋词迎帝意”[2]5633,渐渐取得嘉靖帝的信任,“(帝)有所密询,皆舍嵩而之阶。”[5]215
嘉靖四十年(1561),徐阶抓住修缮宫殿一事,使嘉靖帝对严嵩更加疏远嫌恶。此前,在“壬寅宫变”后,嘉靖帝从大内搬入永寿宫,后来宫殿失火,暂时搬入玉熙殿。因殿内狭窄,嘉靖欲重修永寿宫,而严嵩主张让嘉靖帝暂住南宫,令嘉靖帝大为不悦。时为次辅的徐阶揣摩圣意,极尽献媚之能事,许以最快的速度重修永寿宫,完工后进为少师,与严嵩的官阶相同。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又收买了皇帝身边得宠的道士蓝道行,设计了一场扶乩活动,令蓝道行在扶乩时借神仙之口攻击严嵩。“上由此渐疏嵩,凡军国大计悉诏之大学士徐阶,嵩不得一与闻。”[5]215之后,御史邹应龙在徐阶的授意下上《贪横荫臣欺君蠢国疏》,弹劾严氏父子,严嵩被令致仕回籍休养,而严世蕃则被判充军。
严嵩回籍后,徐阶成为新的首辅,对严家实行了铲草除根不遗后患的打击。嘉靖四十三年(1564),在徐阶的授意之下,御史林润再次上书弹劾严世蕃,令其下狱。而在审讯严世蕃的过程中,徐阶缜密罗织了严世蕃“谋反”“通倭”等罪状,最终嘉靖帝以“交通倭寇、潜谋叛逆”的罪名将严世蕃斩首,严家被抄,严嵩郁郁而终。
(三)徐阶与高拱之争
高拱与徐阶之间,并无对首辅之位的直接争夺,但同样矛盾重重。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由徐阶推荐入阁,与李春芳、郭朴共同辅政。因引荐高拱入阁,徐阶视高拱为同党,而高拱本为太子裕王之师,早已属意于首辅之位,并不感恩徐阶的提携,反而对徐阶独揽大权深为不满,“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2]5634最令高拱愤恨的是,在起草《嘉靖遗诏》时,徐阶未通知高拱而仅带张居正入内合谋完成。“阶草遗诏独与居正计,拱心弥不平。”[2]5634
徐阶与高拱之间,发生过数次摩擦,终以两人同时离开内阁而暂告一段落。如嘉靖四十五年,给事中胡应嘉曾上书弹劾高拱,言 “拱入直以未有子,每寅夜潜归,上一日病颇甚,拱尽敛其直舍器服书籍岀。”[6]因胡应嘉为徐阶同乡,“拱疑应嘉受阶指,大憾之。”[2]5634此事虽因嘉靖帝病重并很快去世而未对高拱有实质性影响,但之后胡应嘉在京察结束后上疏弹劾杨博时,则被高拱抓住把柄,与郭朴一同力主斥去,胡应嘉被削籍后,高拱因得罪言官被交章弹劾,其中欧阳一敬的措辞尤其严厉。高拱的门生御史齐康则与之论辩并弹劾徐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2]5639。结果引发了又一轮更激烈的对高拱的弹劾,高拱招架不住,只得乞归,“拱不自安,乞归,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养病去。”[2]5639而在高拱辞官不久以后,给事中张齐弹劾徐阶“为人臣不忠,与人交不信,大节已亏久矣”[2]5640,徐阶也就此辞官归里。
隆庆三年(1569)高拱还朝,在穆宗青睐之下,不仅入阁,且兼吏部尚书。高拱对徐阶进行了报复打击,史书称“扼阶不遗余力”“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2]5641。此时徐阶老病衰朽,先有海瑞勒令苏、松豪门退还所占田产事,又有苏松兵备副使蔡国熙借孙克弘案重治徐府诸弟子不法事。徐阶长子、次子皆被充军戍边,小儿子被削籍为民,直到一年后张居正成为首辅,高拱去位,方遣还。
二、阁臣失意文学的基本风貌
夏言、严嵩、徐阶三人,其“失意”状况与结局各不相同,涵盖了明代内阁斗争失利者所遭遇的三种可能:夏言先入狱后遭弃市之刑,结局最为悲惨;严嵩罢相后复被抄家,子孙离散,郁郁而终;徐阶迫于压力而辞官归乡,受到昔日政敌报复但侥幸化解,得享天年。与他们的不同遭遇及不同性情相对应,其文学风貌也各不相同:夏言革职期由山水之乐转向前途之忧,入狱期从一线生还之望到彻底绝望,其情感之波动起伏最为激烈;严嵩从离都时的隐忍不平,到归家后的感皇恩与对家居日常的从容描写,符合他一贯的谨慎圆滑;徐阶年复一年追思先帝,同时又反复言说自己的衰病之体,在政治失意之外有一种更加普泛化的悲哀况味。
(一)夏言革职及入狱期间作品
夏言入阁为首辅之后,曾于嘉靖十八年(1539)、嘉靖二十年(1541)分别有两次短暂的被迫致仕,但旋即起复,因时间较短,故此期间的作品不在我们考察范围之内。而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七月罢官闲住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八月重新入阁,这三年罢职闲居期的作品,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夏言还朝后仅三年,便因河套之议被严嵩构陷入狱,从入狱到最后行刑弃市,在狱中留下了八十多首诗歌,也是其“失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罢职期间夏言有大量游赏山林之诗,在其《赐闲堂稿》中占据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彼时虽失意,但对入阁已六年的夏言来说,也不失为一次难得的休息。他时而独游,时而与三两好友相约,在山水之间吟咏消忧。如《登三台楼》:“夜登三台楼,望见溪南山。楼台入烟际,灯火出林间。伏枕苦阴雨,闭门阻跻攀。 倚槛消百虑,旋悟此身间。”再如《白鸥园泛舟》:“三翁齐鹤发,一醉共鸥塘。地讶神仙境,人夸宰相乡。楼台回倒景,舟楫溯流光。未远登高节,篱边菊正黄。”田汝成《赐闲堂稿序》中云:“盖公玄襟冲澹,念泯热中,机事都忘,物我无竞,故受命无饮冰之感,为园有狎鸥之娱,不借声色以怡情,而骋玩翰墨之间,自有天然之预暇矣。”(1)参见田汝成《赐闲堂稿序》,嘉靖二十五年杨九泽刻本,上海图书馆馆藏。不过,这种山水之乐并不纯粹,夏言不甘心就此终老,一直希望有起复之机。他将庄园命名为“宫恩庄”,楼为“望宸楼”,堂为“赐闲堂”,亭为“晚节亭”,表明了自己对皇帝恩宠的感怀与对被起用的渴望。随着居乡日久,乡间宁静生活带来的喜悦与游赏山水的新奇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郁郁寡欢的落寞。而以往身居高位时的荣宠与恩赐皆随着罢官而消失,精神与物质上的巨大落差使其内心抑郁。《明史》记载:“久之不召,监司府县吏亦稍慢易之,悒悒不乐。”[2]5197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后,其笔下便很少有纯粹的山水之乐,取而代之的是忠君恋主的表达。如“独有江湖忧尚在,每依南斗望台垣”“麟阁琐闱成旧梦,葛巾藜杖是新恩”“烟霞自是堪人赏,鱼鸟犹能恋主恩”“梦中长侍君王侧,不省还乡已二春”等等。
嘉靖二十四年夏言终于起复,但短短三年后便在严嵩构陷下入狱。在狱中,夏言与聂豹相遇,与之频繁唱和,留下了24首诗歌,这些诗中往往有关于“道”的思考,他也就开始了佛教的相关研究,写下了四首偈子,分别是《说佛》《说法》《说僧》《说禅》,而在此之前,夏言的诗集中还从未出现有关佛禅思想的表达。入狱之初,夏言心中还存有出狱后归老田园的念头。在对家乡强烈的思念中,他写下了八首以家乡风物命名的诗歌,分别为《怀白鸥园》《怀龙岗别业》《怀象麓草堂》《怀桂洲先庐》《怀南皋野堂》《怀后乐园》《怀闻讲书院》《怀凤池新卜》。而随着“与曾铣交通”罪名的确立,夏言已绝出狱之念。在秋天到来临近刑期之时,对故土的强烈怀恋终究成为了“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的悲叹,其《次双江韵七首》每首诗歌尾句皆以“愁”为韵,凄凉悲怆。其《三五七言二首》以“秋天凉,秋夜长”为首句,语言通俗浅白,而其内在情感却令人不忍卒读。而在最后的绝笔诗当中,夏言也终于放下了一切牵绊与不舍,获得了内心的平静:“劳形生何为?忘情死亦好。游神入太虚,相伴天地老。”
(二)严嵩罢相致仕后的创作
严嵩罢相后作品并不多,从嘉靖四十一年(1562)回乡到嘉靖四十六年(1567)病死,他仅留下了一卷《南还稿》(2)参见严嵩《南还稿》,明嘉靖刻本,国家图书馆馆藏。,诗歌总计40首,并未收入《钤山堂集》中。尽管数量不多,但《南还稿》却一反严嵩鼎仕时期的“篇章庸猥”[7]535,回归到自然质朴与悲凉真切的风格,文学价值颇高。从内容来看,《南还稿》应写于罢相伊始到被抄家期间,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初罢相时的心情,并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回顾总结;第二部分写南还途中所见所感;第三部分写归家之后的生活与感慨。
严嵩初罢相时的心情集中表现在《六月二日出都作》八首中,诗中情绪复杂,总体上弥漫着一种并不激烈的委屈与不平。其中第三、六首最值得注意。第三首写临行时同僚相送的场面,诗中“群公劳相送”的“劳”字、“执别或叹吁”的“或”字,似乎表明这些同僚的勉强与观望之态度;后四句 “别言不及私,努力在公车。才杰侍天阶,贱子山泽居”则更明显地带有一种讥讽与自嘲。第六首隐喻了自己与皇帝的关系:“马牛服耕乘,积岁已云疲。主人未忍弃,顾已良自知。勉欲效驰驱,筋力弗可支。言念刍秣恩,永负天地私。”严嵩把自己比作辛勤耕耘一辈子的牛马,虽然主人不忍抛弃它,但自己已知道筋力衰朽,不堪重用。此诗颇微妙,在感恩之下暗含牢骚。
南还途中,严嵩有许多对沿途风景的描写、对所经过的城市或古迹的咏怀,也有一些与当地朋友会面、送别类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南还路线——《至徐州》《初入淮口》《宝应县》《扬州》《望金山》《嘉兴与太宰默翁话别》《经严陵祠》《鄱阳湖阻风》。其写景之作如《舟行即事》:“长堤绿树浓于幄,细草繁花秀若茵。日晚沿洄那得住,不知何处是通津”,笔触细腻清新,秀丽雅致。在对风景的描绘中,诗人也时或融入自己的人生感慨,如《初入淮口》:“积水浮天气混濛,淮山遥在有无中。行云忽散千江雨,拍浪频吹万里风。听入沧浪歌渐近,望随芳草思何穷。尘劳愧我年堪叹,欲买纶竿学钓翁。”这首诗气象开阔,尤其是“行云”两句,对仗工稳而流畅自然,在“千江雨”与“万里风”所烘托的气势之下,诗人心中的郁结不平也似消散了许多。
严嵩还家之后的诗歌开始于三首感皇恩之作,分别为《罢政归里入居,御赐耆德堂有赋》《百禄堂》《府城忠弼堂作已二十余年始获入居》。耆德堂与百禄堂之名均为嘉靖皇帝所赐,《百禄堂》一诗可见严嵩罢相后在物质方面不减从前的待遇:“既老仍其禄,视与居职一。至于数盈百,今昔鲜其匹。”严嵩在诗中反复强调自己被赐还归乡乃皇恩浩荡,“兹宸荷皇泽,宿愿始由申”“出处总由天意在,生成深荷圣恩余”。这三首诗之后的十余首,或写游赏山水之乐或写家居日常饮食坐卧等,均平实亲切。
《南还稿》中并没有严嵩被抄家之后的作品。这或许是因为其时严嵩面对的是真切而痛楚的生存考验,已无暇写诗,也或许是因为《南还稿》结集刊刻是在严嵩境况较好的时候所进行的,之后的作品未及刊入,已散佚不知去向。
(三)徐阶辞官后居家之作
徐阶辞官归乡后的作品收于《世经堂续集》中,是他去世之后,其孙徐肇惠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编次刊行,共14卷,包含各种文体,内容十分庞杂丰富。我们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卷13、卷14中的三百余首诗歌,其中有与亲友的交往赠答,有山水记游,有日常生活的感喟,有关于时事的评说等等。在这些繁杂的内容中,有两个方面颇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对嘉靖帝的怀念追思;其二是对“衰病”的反复言说。

徐阶辞官归家时65岁,至万历十一年(1583)去世,享年80岁,是阁臣中少有的善终且高寿者。其辞官居家的十五年的确是徐阶的晚年,也即按常理而言身体逐渐衰朽多病的人生阶段。但尽管如此,“衰病”之言仍然昭示了一些疾病之外的意味。以隆庆四年(庚午年)所作的18首诗为例,其中提及“衰病”的有九首,占一半:“独挥衰泪向残边”“老去久拼人共弃”“抱病经冬卧一丘”“春来抱病废琴书”“访戴身衰体尚疏”“欲叫帝阍身老病”“遁世自缘衰腐甚”“白发朝来亦罢梳”“交游白首嗟能几”。而隆庆五年(1571)所写的21首诗中,提及“衰病”的有14首之多,占2/3。其他年份的诗歌中“衰病”之言所占比例大约一半。在生理性衰病之外,诗歌一方面表现出辞官后从对外界的关注转向对自身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退出官场后的落寞感与挫败感所形成的对身体衰病的一种强化性认知。如作于庚午年的《感赋》:“潦倒无心问酒垆,闭门频阅岁年徂。天空苑树秋声急,霜落庭花画影孤。老去久拼人共弃,愁来仍苦吏常呼。风波林壑同湖海,信是人间总畏途。”其中“老去”两句较明确地表现出徐阶居乡后内心的落差感甚至窘境——随着人的衰病老去,以往的权势风光都将不复存在,成为“人共弃”“吏常呼”的对象。另一首《谢浔阳董宗伯过访》同样作于庚午年,这首诗是在答谢旧友董宗伯的拜访,而拜访的可贵正在于诗人归乡之后因权势不再而满树猢狲皆散之的现实。诗歌起首便言病:“春来抱病废琴书,枕簟萧然对敝庐。”在门可罗雀的孤寂之中,“抱病”在生理性的不适之外实际上亦是心理性失意的隐喻。
三、阁臣失意文学的典型特征
夏言、严嵩、徐阶三位阁臣虽然在失意时期所写的作品各有特点,但总的来看,与他们在内阁时期的创作相比,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写作空间发生了从“台阁”到“山林”的转换,文学创作则表现出“台阁”与“山林”之间的融合与摇摆。其二,“公身份”向“私身份”的转变,使得失意阁臣文学创作的目的由“为人”转向“为己”。这两个方面其实又有一个核心的连结,那就是“真实性”的突出。
(一)“台阁”与“山林”的摇摆
“台阁”与“山林”之间出现融合与交集,始于明代茶陵派领袖李东阳。他曾在《麓堂诗话》中说:“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须有其一,却不可少。”[9]他提倡台阁与山林并重,对于纠正此前台阁体之弊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茶陵诗派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明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李东阳所倡导的茶陵派,融合台阁气和山林气,本身是成化至正德时期阁臣失意心态的一种反映。当然,李东阳并没有贬谪的经历,这种失意仅属于心理层面。作为四十年左右不离都城之台辅重臣,他从未有过真正的山林生活,其诗歌中的“山林”多在京郊,其“山林气”更多的是在审美品味、心理倾向上对山林诗人的追慕,与真正在野的诗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古澹犹相类,悠远则不及。这是因为他的山林毕竟过于局促,他的处境毕竟没有陶、韦式的超然。”[10]
如果说李东阳代表着身在台阁而倾慕“山林”的趋向,那么夏言、严嵩、徐阶在实际的“失意”之后,对“山林”的感受则更为自然而真切。“台阁”“山林”之别首先来自“写作空间”之别。所谓 “写作空间”,既是物理意义上的所居之处,也包括在此基础上的身份意识、人生态度、心境胸襟等等。宋代吴处厚就曾说过:“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11]他明确指出“道不得行”与“得位于时”,这种沉浮荣辱之别,引发两等之文。明初宋濂则称: “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12]宋濂所说的“所居之地”便是“写作空间”之意,是最为直接最为自然的“台阁”“山林”之别的因由。因此“台阁”与“山林”,并不昭示一成不变的身份,更多的情况下,它只代表着彼时彼刻的人生际遇。当际遇变换,心境顿改之时,文风很难不发生改变。
不过,如夏言、严嵩、徐阶诸人,作为与皇帝关系极为密切且有“权倾朝野”之影响力的重臣,一朝失意退野,与真正的山林隐逸者在心境上仍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说李东阳诗歌是以“台阁”为本向“山林”的倾斜和侵入,那么夏言、严嵩、徐阶三人在失意时期的诗歌则是以“山林”为本而表现出对“台阁”的向往和不甘。李东阳是身在魏阙而有江湖之想,而夏、严、徐三人则是身在江湖而有魏阙之思。夏言罢职回乡后那种悠然闲适的山林心境只持续了一年左右,继之而起的是对重新起复的焦虑;严嵩罢职之初即有一种婉转的委屈不平,其归乡之后的诗歌在山水之赏的同时不断叨念主恩;徐阶则年复一年追思先帝,反复叹息自己的衰病之体,流露出对以往君臣相得的事业黄金期的留恋。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台阁”与“山林”之间的融合与摇摆,这种融合与摇摆,是在其处境与心境的转变之下自然而然地发生,其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或许有限,但却是情感的真实表达。纯粹的山林诗固然有高洁出尘之美,而士大夫之怀禄固宠、忧谗畏讥乃至于进退失据,其实表现了更加普泛的人性欲望与窘困。夏、严、徐三人在失意期间的创作虽既无纯粹台阁之“温润丰缛”,亦非纯粹山野之“枯槁憔悴”,但自有其意义和价值。
(二)“为人”与“为己”的转换
孔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3]这种“为人”与“为己”之别,不仅存在于“学者”,也存在于“诗人”。笔者在《论中国古代诗歌功用的作者之维》一文中曾将诗歌对于作者的功用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登第科举、晋身仕途之用。其二,汇入群体、融洽关系之用。其三,留名后世、精神不朽之用。其四,倾诉情感、慰藉心灵之用(3)参见张英《论中国古代诗歌功用的作者之维》,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这四个方面如果要用“为人”“为己”的标准来划分,那么第一种与第二种功用具有鲜明的“为人”的特征;第三种与第四种功用,尤其是第四种,则更多地体现了“为己”的特征。明代诗歌并不直接为科举服务,因此第一种功用体现得并不明显,但第二种功用即社交功用仍旧十分突出,在入仕时期内阁大臣所写的诗大多都可归于第二种功用,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如此,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诗歌基本上也是如此,而嘉靖时期三位重要的内阁首辅夏言、严嵩、徐阶在他们未曾“失意”之时所写就的诗歌也不例外。而在失意前后,“为人”与“为己”之间有着明显的转换。
从应制诗歌来看,嘉靖朝本来就是一个高峰。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中曾经对此有过详细论述,他认为,明代的应制诗歌在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间均是兴盛期,但正统之后渐至消无,直至嘉靖朝复炽,“消沉百年之后,至嘉靖年间,此风复盛”[14]。夏、严、徐三人身为阁臣时都有大量的应制创作。夏言诗歌题目中多有“奉旨”“恭和御制”字样,数量达三百多首,这些诗在当时受到了高度评价,如曹忭在《桂洲诗集序》认为夏言所作雅颂诸诗“典则以毖体,正大以孚极,铺张以载实,详密以著事,俊朗以昭式,婉曲以输尽。”“上溯有汉,及于唐宋,宰相中以才名称后世者,未有若是其兼美者也。”[15]174。杨九泽在序中也盛赞夏言此类诗歌:“崇国体于西周,律格虽唐,义犹雅颂。概以表功昭德,垂示无疆,非以剪雪镂冰,流连光景也。”“玩其词旨,凝重而森严,盖深于礼者也;和平而温润,盖深于乐者也。所谓兼资具美,亶乎难能者,仅见于公。”[15]174这种赞颂有明显的因夏言的政治地位而对之进行的有意拔高。如果用纯粹的文学标准来看,这些诗歌的价值无疑要大打折扣。夏言如此,严嵩、徐阶也有着同样的情况。王世贞《艺苑卮言》卷8中评价严嵩之诗:“强仕之始,诗颇清淡。既涉显贵,虽篇什日繁,而恶道岔出。”[16]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评价严嵩晚年诗歌时说其“直庐应制之作,篇章庸猬,都无可称”[7]535。王士禛评论严嵩的诗,说他“早年诗有王、韦之风,贵后皆应制腐恶之作耳”[17]。在这些歌功颂德的应制诗之外,他们还为皇帝写了大量的“青词”。很明显,这些青词更加具有“以为禽犊”的“为人”之用。除了与皇帝密切相关的应制诗之外,馆阁应酬诗是另一类用于社交的诗作。以夏言为例,其一千六百多首诗歌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酬酢应答之作,其中涉及的文人有四百多人。在夏言位高权重的时期,以他为中心形成了馆阁诗人群体,经常举行诗歌唱和活动,如嘉靖十一年(1532)在翰林院以“赏莲”“直庐”“阅卷试士”为主题的唱和;嘉靖十二年(1533)以“贺新堂落成”“贺新居落成”“游天坛”“游邵园”为主题的唱和;嘉靖十六年(1537)的“为海天春晓图赋诗”活动;嘉靖二十年(1541)的“贺寿”以及嘉靖十八年(1539)的“送别崔铣”的唱和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均为朝臣,以内阁、翰林任职者居多。
这些应制诗与酬和诗,在夏言、严嵩、徐阶三人失意时期的创作中几乎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遣兴之作,体现了第四种功用:倾诉情感、慰藉心灵。应制诗已失去了写作的资格,酬和诗虽仍有创作,但数量锐减,且酬和的对象不再是“同僚”而是“朋友”,不再是带有功利意味的奉承敷衍,而是朋友之间的真诚交流,起到的其实已是遣兴、遣怀之用。他们用文字的方式陈说自己的感受,尤其是内心中的郁结情绪,通过这种表达化解烦恼,得到心灵的平和与自由,其主要的读者是作者自己。诗人们抛开重重身份的束缚,揭去层层面纱,露出赤子之心;不必考虑自己的诗作是否能得到皇帝的青睐以及随之而来的祸福,不必考虑在与别人的互动之中他人的品头论足以及对社交关系的改变或推动,一切回归到最为纯粹的心灵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失意”所失去的是荣宠与地位,但与此同时,通过文学的表达,真正的“意”却从内心深处被召唤出来,呈现在自己面前。明初高启在其《缶鸣集》自序称:“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为之也,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岂以为务哉!”[18]“以为务”与“发于性情之不能已”正是“为人”与“为己”的区别,而以夏言、严嵩、徐阶为代表的阁臣在失意期间的作品,正是不再期于用世,“发于性情之不能已”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皇权高度集中的专制环境下,阁臣们的内心往往处于扭曲的状态,在“媚上”与“谏上”之间,在“权势富贵”与“士人风骨”之间辗转腾挪,耗尽心力。而阁臣斗争中的失意者则在很大程度上从这种扭曲状态之中解脱出来。尽管非己所愿,但“失意”的处境确实给诗歌写作开启了一扇窗子,打破了“应制”“酬和”之工具性虚与委蛇的沉闷,带来了清新的空气。这其中有对山林的赏爱,有对故乡的眷恋,有对内心痛苦的敏锐感受和审思,有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思考和追问。他们从台阁走向山林,又从山林遥望台阁;他们收敛起写诗“为人”的虚荣与疲惫,开启了以诗“为己”、表达自我、慰藉心灵的新篇。文学史上无数名篇佳作,大多是文人们在“失意”状态下写就的,而明代阁臣的“失意文学”,是古代文学史“失意文学”链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