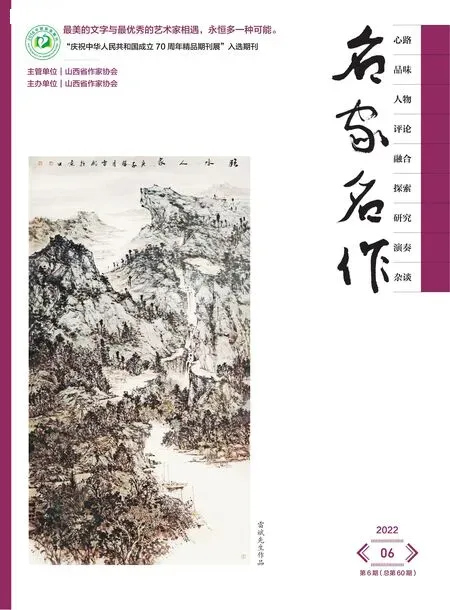时代群像与家国情怀
——从《茶馆》到话剧《花桥荣记》
席冠南
一、引言
胡筱坪执导的话剧《花桥荣记》由张仁胜编剧,改编自作家白先勇的小说集《台北人》中的《花桥荣记》,于2016年10月26日在桂林大剧院首演。话剧《花桥荣记》主要讲述了因为世道纷乱从桂林流落到台北长春路的春梦婆在离乱的艰辛中苦苦支撑着自己的桂林米粉店花桥荣记的故事。她看着身边的桂林老乡颠沛流离的命运,真切怀念着她的桂林老家。话剧在她不停的回望中表现了当时纷乱的时代落在每个小人物身上的悲剧。
《茶馆》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戏剧的巅峰之作,以裕泰茶馆为缩影讲述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这两部作品都是以动乱年代一家小店的浮沉为视角,塑造涵盖各个阶层的时代群像,折射小人物的家国情怀。话剧《花桥荣记》的改编以米粉店花桥荣记为基点,用人物群像素描展现了山河破碎下的浓烈乡愁,其深层与“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花桥荣记》是对《茶馆》内容和形式上的回望与继承,从戏剧美学上看,是一脉相承的。
二、时代群像的展现
《花桥荣记》中的人物都是1949年以后生活在台湾长春路上的人,这些经历迥异的人相聚在一条街上,看似热闹的交往中潜藏着各自过往的伤痕。有开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春梦婆,也有家境优渥的小少爷,有容县的县太爷,也有手握着柳州半座城的李半城。除了流落台湾的广西人,《花桥荣记》还塑造了好色的擦鞋匠、泼辣的洗衣婆阿春和阿春妈、尖酸的包租婆顾太太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包含各行各业,通过群像速写展现着人性的不同方面。
老板娘春梦婆展现的是中年女性的情感悲剧。春梦婆一直在为自己的米粉店张罗奔忙,是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形象,但展现精明的同时并没有遮蔽她个人柔软的情感世界。在剧中,春梦婆常是在关注身边广西同乡们离散的情感遭遇时,回想起自己的感情故事,在理智的现实和感性的回忆中游走。春梦婆回忆自己还是桂林水东门外花桥桥头荣记米粉店的米粉丫头时,和桂林行营的营长恋爱结婚,跟着他去了不少大地方。春梦婆的丈夫是军人,在“苏北那一仗”中下落不明,毫无音讯。与丈夫失散的春梦婆,只能独自狼狈地逃往台北,不知何时可以再与丈夫团圆。她在许多夜晚里梦见丈夫一身血淋淋的,梦境暗示着她身为营长的丈夫可能已经在战争中丧命的悲惨结局。春梦婆之所以被叫春梦婆,也是因为她心中始终都怀着与丈夫团聚的执念,“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归梦里人”。战乱给人带来的生活的倾覆、家庭悲剧给女性所带来的悲苦可见一斑。
卢先生展现的是希望的破灭和精神的迷惘。在桂林家庭优越、无忧无虑的小少爷,到了台北变成了长春国校教国文的卢先生。一边教书一边养鸡,把自己搞得臭烘烘的,就为了存一点钱,可以托香港表哥把自己的爱人罗小姐从大陆带到台湾来。但他辛苦积攒十几年的十根金条被表哥生生骗了过去,和未婚妻罗小姐相见,也没有了希望。他顿时精神崩溃,一改过往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形象,和放荡泼辣的洗衣婆阿春搞在了一起。因为精神支柱的倒塌,沉迷性爱、人性堕落的卢先生最终郁郁而终。验尸官在死亡单上填了“心脏麻痹”,这其实是卢先生真正死因“精神麻痹”的另一个说法。卢先生当年与罗小姐矢志不渝的忠贞终究因社会的冲击和战乱的折磨、自我的堕落而告终,酿成了悲剧。
秦癫子展现的是过往辉煌被战乱打破之后的沉沦颓废。广西容县县太爷在台湾成了台北市政小公务员,游荡在街头巷尾,大家总觉得他疯疯癫癫的,喊他“秦癫子”。从前心爱的几房小老婆在战争中走散,再加上身份地位的落差,秦癫子精神开始扭曲变形。他不但在工作上漫不经心,在情爱上也变态,“在市政府做得好好儿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被开除了”。秦癫子丢了工作,毛手毛脚的毛病更是愈演愈烈。剧中秦癫子有两次挨打,都是因为调戏女性。一次是在菜市场侵犯卖菜婆,被追着打几条街。后来更加过分,变成了在板缝里偷看阿春洗澡。他侵犯女性的地点从办公厅、米粉店到了菜市场,再到了浴室板子缝后面。空间流于低俗,手段从公开调戏变成了猥琐下手。在疯疯癫癫中,秦癫子在暴雨后的一条臭水沟里淹死,好几日才被打捞上来。
李半城身上呈现的是财产价值的灰飞烟灭和父子伦常的崩溃。李半城出场在花桥荣记热闹开张时,大家传说他“做木材生意,赚了大钱,买房收租,整个柳州城的房子都是他的”。但在他与秦癫子发生口舌后,却连一碗粉钱都掏不出来。从广西跑到台湾,只要出门他都提着箱子,守着箱子里的179张房契,可战乱频频,房契早就失效了,只有他还当宝贝一样守着。他盼着儿子寄钱过来,儿子却一直没有消息,仿佛把他这个父亲忘掉了。没几年光景,他没等来儿子的支票,手也扯起了鸡爪疯,生日那天也只能求老板娘赊账再吃一餐,最终在穷困潦倒中绝望吊死。
1949年,从桂林流落到台北的这一群人,曾经各自有各自的坚持和辉煌,后来却流落于一条小小的长春路,不得善终,满是现实的苦涩心酸和无可奈何。他们时常会想起自己的故乡,会想起过去的生活,感叹命运的不公与当下的窘迫。这些小人物只是千千万万裹挟在战争时代洪流里鲜活生命的缩影。
《花桥荣记》借鉴的是《茶馆》对群像人物的速写手法。老舍在写《茶馆》时并没有按照戏剧创作中人物少而集中的传统,而是延续自己写小说的习惯,将小说人物塑造方法引入了剧本的创作。《茶馆》一共写了70多个人物,进行了跨时代的群像速写,且70多个人物个个特色鲜明。有清宫的太监,吃皇粮的旗人,吃洋教的教士,主张实业救国的资本家,借“改良”而谋生存的商人,贫苦到卖儿卖女的农民,军阀的军官、大兵、警察,还有一大批依附于清朝、军阀、国民党的社会渣滓——特务、流氓、打手、相面的、拉纤的、女招待等。人物众多但不杂乱,各有其代表的社会阶层。作者以茶馆为舞台,把人物的不同经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形成时代的剪影,通过复杂的人物关系反映时代背景。
茶馆掌柜王利发苦心经营裕泰茶馆,在三个时代更迭中不断地苦心“改良”,支撑茶馆,谋求生存,但战乱不断的社会环境带来了经营的大萧条。特务官吏对茶馆的抢占剥削终于把王利发逼得上吊自杀。
搞实业救国的民族资本家秦仲义躬行实践,但到头来他的工厂被国民党当作“逆产”没收了,他只从工厂的废墟中捡回几个机器零件和一支写过宏伟蓝图的破旧钢笔,体现了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民族资本家的悲剧。
常四爷在第一幕中是个有“铁杆庄稼”特权的满族旗人,因为说了一句“大清国要亡了”,便被吴祥子、宋恩子二人抓走坐牢了。出狱后,他便参加了义和团,进行抗日,具有刚正不阿的爱国精神。在义和团失败后,他便归隐于北平城内,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商贩,卖蔬菜、卖花生米。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从原来的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贫苦的自食其力者,但还是逃不脱毁灭的命运。《茶馆》中的人物群像与《花桥荣记》一样,人物悲苦的命运之下折射着时代悲剧。
《茶馆》中还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父子相承,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像小二德子、小刘麻子、小唐铁嘴各自继承了父亲流氓打手、买卖人口、江湖骗子的职业。此类负面人物也“子承父业”“代代相传”,在《花桥荣记》中这种手法也有展现,爱勾引男人的阿春曾在街坊四邻面前对阿春妈说:“反正你要嫁去花莲,莫要在长春路给我立什么烈女牌坊!”洗衣婆阿春妈和阿春都生性泼辣开放,人物父子、母女之间的继承性具有极强的讽刺性,艺术构思巧妙。
三、店面兴衰中的家国情怀
在《花桥荣记》中,春梦婆在台北长春路重开花桥荣记,开业街坊四邻都在捧场,恭贺开业,好不热闹。但好景不长,米粉店好死不活地运转八年之后,生意靠几个广西老乡帮衬支撑不下去了,只得迫于生计放弃了只卖米粉的原则,也在牌匾边上写上了“炒菜米饭”,违背了祖传米粉店的传统,是对生计的妥协。连吃不腻桂林米粉的卢先生也向老板娘提出要换成米饭炒菜。到十五幕,从前帮衬店面的广西老乡死的死、疯的疯,从前和祖宗牌位一起供奉起来的米粉秘方也被白蚁蛀了。
春梦婆回忆年轻时奶奶给她讲秘方,说桂林米粉的精髓在配伍,做一碗小小的粉,就如同布下千军万马一般。做粉就是摆阵带兵,将主题指向了处在战时的时代背景。而被白蚁蛀了的秘方,更加深了老板娘对无法回故乡的绝望。剧中春梦婆有一句台词:“我面对一个‘花桥荣记’找准帅不难,菩萨面对这片海。会以什么为帅?”这里从秘方暗喻着本剧深刻的主题:乡愁背后对和平和祖国统一的渴望。
《花桥荣记》的作者白先勇先生,祖籍是广西桂林。他的童年便是在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苦难深重的时代大背景下度过的。1944年长沙大火之后湘桂大撤退,白先勇便跟随家人离开桂林,辗转到了重庆。在此之后,他在南京、上海等地生活了几年,1949年以后迁居台湾,一去便是半个世纪。白先勇的生活背景从战争年代跨越到了和平年代,生活空间也经历了从大陆到台湾以及海外等诸多转换。这些生活经历使他对战争与和平、家与国的感悟愈加深刻,也给了作品深刻的历史底蕴。
白先勇表示,在创作“台北人”系列小说时是以刘禹锡的《乌衣巷》作为基调:“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戏剧改编中,《花桥荣记》的作品意义也在不断生长。
《花桥荣记》处处在说乡愁,在乡愁背后是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战乱不断的世道对百姓生活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是战乱造成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的百姓在正当壮年或是已经可以颐养天年的年纪里仍然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怀着对过往美好生活的追忆,在异乡台北生活,甚至是在一地鸡毛中苟且生活。在《花桥荣记》中,处处在怀乡,其实也是处处在呼唤着生活的和平安定,反对令百姓流离失所的战争。“乡愁”是编剧拖到观众眼前的主题,而呼唤和平和反对战争的家国情怀才是深层的内蕴。
可以说战乱对当时百姓的生活是毁灭性的,它作为一个根本的原发导火索,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引爆。具体说来,战乱之下亲情、爱情的离散以及事业的重创和精神的迷茫,是《花桥荣记》中几乎每个人物都要面临的人生的痛楚。
结合《花桥荣记》作品的故事背景,我们会体会到一些具体的时代困局。但事实上,一部作品的指称可以从更为宏大的人类学视角来看。《花桥荣记》呼吁的是人类文明的和平,期待的是双方止戈获得统一后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不单单只指向一个孤立的战争或者是只指向一个区域的人。
《茶馆》也是在用小店的经营悲剧来折射整个时代的悲剧。《茶馆》的故事集中发生在老北京的裕泰茶馆中。茶馆是三教九流的会面之处,容纳了各色人物。全戏只有三幕,却用茶馆这样一个方寸之地承载了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5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全剧并未正面描写社会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将小人物揉进大历史,用小茶馆表现大社会,将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割据时期、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三个时代的横断面与历史纵线交错结合。
对社会背景的反映直接体现在了茶馆的布景变化中,从第一幕到第三幕中茶馆陈设的变化便可以看出社会环境的活跃程度在日渐下降。第一幕中,茶馆的“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后院还有高搭着的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这表明,茶馆的经营状况非常好,不但上座率高,还承担着百姓茶余饭后遛鸟的休闲功能。
然而时隔十余年,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内战时时爆发,茶馆作为市民的活动领域已然遭到破坏。茶馆看似经过改良后获得了新的发展,实则已经逐渐走向没落的边缘,悲剧氛围已经显现。
而到了第三幕,抗战胜利后,日本人被驱除出了中国的土地,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幸福的生活,而是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境况。茶馆此时早已不复从前的热闹沸腾,而是萧索冷清,“藤椅已不见,代以小凳与条凳。自房屋至家具都显着暗淡无光”。
茶馆包罗着人世百态,对茶馆经营由盛转衰的描述使人深感民族前途命运堪忧。《茶馆》是从历史文化的深层对国民自身的劣根性进行现代性的审视与面对中华民族所处困境的反思。有多少类似唐铁嘴这类的中国人民麻木愚昧、毫无目标地活着。在时代冲击下,他们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只是随波逐流。当悲剧的时代推动百姓往前走时,面对的必然也是悲剧。老舍面对如此社会群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从麻木的百姓身上看到了麻木的旧社会,老舍对民众麻木心智的唤醒是家国情怀的升腾。
四、结语
一间小店,来往路人皆汇聚于此。在时光的流逝中,从客人身上看到了岁月的变迁、时代的更迭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从王谢厅堂到了寻常百姓,一家小店就是历史见证者。来往的人命运沧桑巨变,这背后便是时局混乱带给每个人的悲剧,悲剧之下展现的是作者深重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