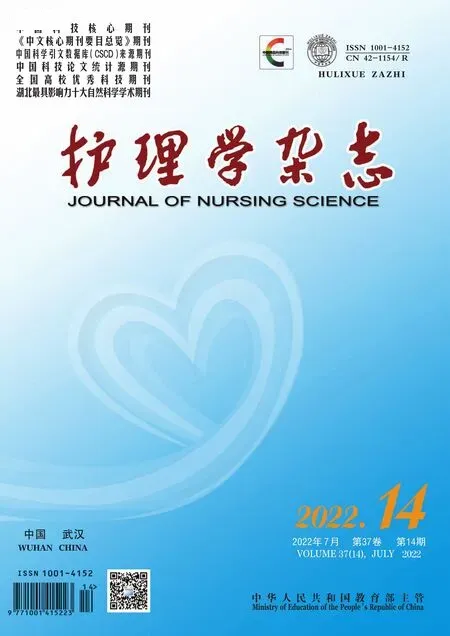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纵向研究
张婷,张莉,周家梅
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CHD,下称先心病)是指胎儿时期心血管系统发育障碍或异常所致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是目前最常见的儿童出生缺陷之一。其发病机制复杂,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等特点,已对儿童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1-2]。目前,生存质量成为一种新的健康指标,能全面评价疾病发展及诊疗过程中患者身心和生活等方面的变化[3-5]。随着诊疗技术、手术水平以及护理技术的进步,约90%以上的先心病患儿可存活至成年[6]。虽然手术治疗可以矫正患儿心脏缺陷,但先心病儿童的发展和心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在运动认知、社交和情绪功能、学业成就、就业及整体生存质量等方面均会受到不利影响,而且这些问题可能会持续到青春期,并随着学习需求的增加,甚至可能会出现新的缺陷[7-8],严重影响患儿生存质量。对于许多慢病患者而言,儿童时期的生存质量水平对其远期生活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于先心病患儿而言,生存质量可以纵向追踪其健康水平,是患儿健康的重要检测指标[9],值得深入研究。鉴此,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纵向研究,了解患儿术后不同时期的生存质量水平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提高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在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内科确诊为先心病并行手术治疗的患儿及其主要照护者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已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标准:①诊断为先心病;②择期行体外循环下心内直视术、开胸封堵术或经皮介入封堵术;③年龄2~18岁[10];④纳入研究患儿主要照护者为照护患儿时间最长,且与患儿为亲属关系的照护者1名;⑤患儿和(或)家属无认知及表达障碍,能正确理解本研究目的;⑥自愿参与此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患儿年龄<5岁者仅由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余由患儿和家属共同签署)。排除标准:①先心病并存其他复杂性疾病,如21-三体综合征、脑瘫等;②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如低心排综合征等;③二次手术或在院期间死亡。剔除标准:①随访期间主动退出;②各种原因失访(家属失访等同于患儿失访);③随访过程中患儿死亡。本研究在患儿出院时收集患儿及照护者资料各106份。在1年的随访期内,7名主要照护者更换联系方式无法取得联系;4名主要照护者拒绝随访,最终获得患儿及照护者有效资料各95份。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
1.2.1.1一般资料调查表 根据本研究内容并结合既往文献资料[11-13]由研究者自行设计,由患儿社会人口学资料及临床资料两部分组成。前者包括患儿性别、年龄、家庭子女数量、家庭居住情况、主要照护者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主要照护者对疾病认知程度、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等,后者包括就医延迟时间(若患儿首次出现症状时间与首次至医疗机构就诊时间≥30 d则视为就医延迟[14])、术后并发症、再入院情况等。
1.2.1.2儿童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系列心脏病模块(Pediat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 3.0,PedsQLTM3.0)中文版 该量表经黄卓燕[10]翻译汉化,包括儿童自评和家长报告,分别从家长和患儿自身的角度测量2~18岁心脏病患儿的生存质量,其中家长报告比患儿报告多了2~4岁患儿的测量量表。除2~4岁患儿家长报告由6个维度23个条目组成外,其余均由心脏症状及其相关症状(7个条目)、治疗Ⅱ相关问题(该条目由术后服用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患儿填写,3个条目)、感知身体外貌相关问题(3个条目)、治疗焦虑相关问题(4个条目)、认知心理问题(5个条目)、沟通相关问题(3个条目),共6个维度25个条目组成。儿童自评问卷总表可由5~18岁儿童自行填写,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0.68~0.87;家长问卷总表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0.91;儿童和家长两次重测问卷报告各维度和总分的组内相关系数值均达到0.7以上,证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15-16]。
1.2.2调查方法 于患儿出院前1 d征得患儿和(或)家属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当面对患儿及家属进行社会人口学资料收集并当场记录;临床资料收集由研究者在患儿出院当天在医院住院医生工作站提取并记录,其中患儿术后病情变化资料与生存质量数据采集时一并获取。于患儿手术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时通过电话随访收集患儿生存质量数据,每次调查约30 min,调查者据患儿和(或)家属的回答如实记录。

2 结果
2.1患儿及其主要照护者一般资料 患儿95例,男48例,女47例;年龄2~17岁,其中2~岁55例,5~17岁40例;75例患儿发生就医延迟,延迟时间平均为31.31个月。家庭居住地:农村56例,城市/镇39例。医保类型:新农合89例,居民医保6例。术后25例发生并发症。主要照护者:母亲61人,父亲21人,祖父母(包括外祖父母)13人。照护者学历:初中及以下72人,高中/中专14人,大专及以上9人。照护者职业:家庭主妇28人,务农26人,务工20人,其他21人。照护者对疾病的认知:不了解56人,了解一些39人。家庭人均月收入:<1 000元11人,1 000~3 000元30人,>3 000元54人。子女数量:独生子女21人,2孩47人,≥3孩27人。
2.2患儿术后不同时间点生存质量得分
2.2.140例5~17岁患儿与家长报告生存质量得分比较 见表1。

表1 40例5~17岁患儿与家长报告生存质量得分比较 分,
2.2.255例低龄患儿父母报告生存质量得分比较 见表2。

表2 55例低龄患儿父母报告生存质量得分比较 分,
2.3不同时间点家长报告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得分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见表3。

表3 不同时间点家长报告先心病患儿生存质量得分的单因素分析 分,
3 讨论
3.1先心病患儿术后不同时间生存质量水平及动态变化 本研究采用的测评量表由家长报告和患儿自评报告组成。家长报告和患儿报告结果均显示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3个时间点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分析原因可能为:对出院后3个月对患儿来说,正处在恢复期,而且患儿术后需在心脏重症监护室进行监护,由于重症监护室的特殊性、患儿抵抗力较差、探视时间短暂、家长无法24 h陪护,加上病情危重,需要进行密切的观察和治疗[17],导致其出院后3个月,生存质量整体水平及各维度得分都相对较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患儿身体逐渐恢复,生存质量水平也逐渐提高。此外,40例5~17岁患儿报告与家长报告配对比较结果显示,患儿自评与父母评价生存质量得分虽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仅心脏症状及其治疗相关问题、治疗相关焦虑问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说明家长报告虽不能完全替代患儿自评报告,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患儿年龄小、病情重、沟通能力不足等不能对其自身生存质量进行自评时作为临床的参考,反映患儿生存质量水平,但在评估时应注意患儿症状、治疗和焦虑相关问题。其差异可能与父母与患儿对某一事件的理解水平和解释可能不一致以及对同一事件做出的反应存在差异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家长对患儿病情的过分关注,如心脏相关症状等,导致家长报告得分低于儿童自评报告得分,使得两者的报告结果出现差异。家长报告结果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临床的参考,指导临床的治疗工作;但在患儿有足够的认知能力对自身生存质量水平进行自评时,家长报告则可作为补充,以便更加全面、充分地评估患儿的生存质量水平。因此,鉴于儿童的特殊性,在生存质量测评时最好二者平行测量,从而使测评结果更接近真实情况。
3.2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影响因素
3.2.1照护者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照护者角色、文化水平、职业对疾病的认知程度的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主要照护者为母亲的患儿生存质量高于其他(父亲或祖父母),这可能与我国照顾责任具有鲜明的女性化倾向以及女性性格中的特点,比如温柔、耐心,会承担更多的照顾孩子的责任有关[18-19]。其次,照护者职业类型也会对患儿生存质量产生影响,主要照护者职业为务农的患儿生存质量低于其他职业,如务工等,究其原因可能与不同职业收入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其家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不同有关。务工及其他职业如教师、经商等收入均高于务农,此类照护者在满足患儿基本医疗需求方面优于照护者职业为务农的患儿;照护者为家庭主妇的患儿,家长虽然有更多空闲时间关注疾病对患儿身心的影响,但由于长期待业在家、无收入来源,容易产生自责、担忧等不良情绪,父母的不良情绪状态可能会影响患儿对疾病的应对方式,从而影响患儿生活质量。最后先心病患儿照护者的文化水平和对疾病的认知也是患儿术后生存质量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显示,患儿家长文化程度与其生存质量呈正相关,随着患儿家长文化程度的提高,其患儿的生存质量也上升[13,20-21]。可能是由于患儿照护者文化水平高者,对知识的获
取和接受能力更高,获取问题解决方法的渠道更多,对疾病的认知也更加全面,且照护者文化水平高者较低者而言,对儿童的早期教育、特殊教育、心理发展等方面关注度更高,一定程度上可促使先心病患儿得到早期治疗。因此,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患儿主要照护者的护理指导,在其住院期间加强疾病知识指导,出院时传授必要的护理知识与方法,提高术后患儿的护理质量和康复效果,在进行健康教育时应除了充分考虑患儿及其照护者文化水平、背景的差异,尽可能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外,对文化水平低者还可提供具体的健康指导手册,以便在患儿出院后随时随地学习和查阅。
3.2.2家庭因素 家庭是儿童接触社会的第一场所,是影响患儿外环境中最基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提高患儿的家庭支持力度,从而改善其生存质量[13]。Kolt等[22]也认为,家庭的支撑和情感功能影响着先心病青少年的健康相关生存质量。可见,家庭对患儿术后康复的重要性。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家庭居住地、经济水平、子女数量的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得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家庭经济水平低、子女数量多、居住在偏远农村者,患儿生存质量更低。患儿父母经济水平高,不仅能够满足其基本医疗需求,还可为其提供额外的早期的医疗保健服务有关。此外,患儿父母经济水平越高,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陪伴患儿,满足其生活需求,进而提高其生存质量。有研究指出,先心病患儿使用处方药的频率是健康儿童的3倍,家庭保健服务是5倍,专用医疗设备是8倍,加之手术产生的费用,其家庭则可能承受更高的经济负担[23]。对于家庭子女较多的患儿而言,患儿手术本就是一笔巨额支出,甚至有部分家庭因为手术而负债,加上家庭子女数量多,经济压力也更大,患儿家长就可能会忽略对患儿的关心,从而影响其生存质量。这提示医护人员应充分考虑到先心病患儿及其家庭所面临的疾病与经济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为其提供相应支持,如为符合条件的患儿申请大病专项救治服务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社会补助等,以减轻经济负担并促进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还可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或延续性护理服务,为患儿及其照护者提供院外照护支持。
3.2.3就医延迟 本研究结果显示,发生就医延迟的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评分较低。有研究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就医延迟,不仅使先心病患儿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即便后期积极治疗预后也会较差,严重影响患儿生存质量[7],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而早发现、早诊断、及时治疗是降低先心病儿童病死率,减少并发症,提高其健康生存水平的关键。因此,降低先心病患儿就医延迟的发生率也是提高其生存质量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
3.2.4术后并发症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发生并发症的患儿生存质量水平较未发生并发症的患儿更低(P<0.05)。目前,儿童先心病治疗主要为手术治疗,但手术时间长,创面大,术后恢复时间长,易发生并发症,大大降低患者后期恢复情况及生活质量[24]。同样,一项关于先心病手术后住院儿童的运动表现、感觉和运动状态评估的研究发现,约有64%儿童术后运动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且下降程度与机械通气、重症监护时间延长呈正比[25],而术后发生并发症则会使患儿重症监护时间延长。因此,医护人员应关注患儿围手术期恢复情况,注重并发症的预防和护理,改善患儿预后,促进其恢复,进而提高其术后生存质量水平。
4 小结
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是动态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患儿术后3个月生存质量处于较低水平,之后生存质量水平相对提高。此外,先心病患儿术后生存质量得分影响因素较多,各个时间点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提示医护工作者应注意早期识别不同阶段影响患儿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及时就影响因素的差异性采取个体化的护理干预措施。家长报告可大部分代表患儿的生存质量状态,但应注意症状、治疗和焦虑相关问题。本研究的局限性:仅调查了1所医院就诊的先心病患儿,代表性有限,未能将可能影响患者生存质量水平的因素全部纳入。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挖掘影响因素,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探讨不同因素之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