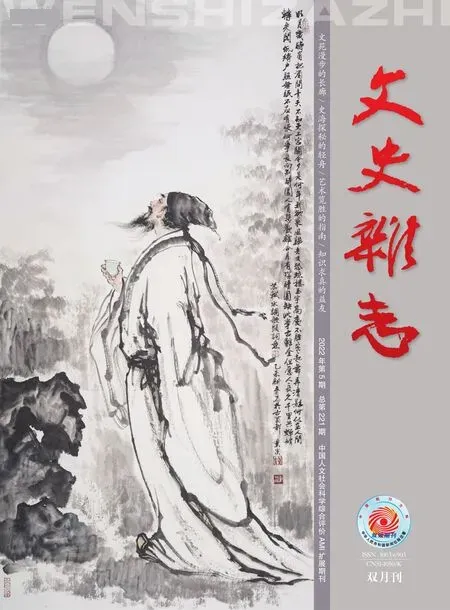家国、巴蜀与东坡
——因缘际会,造就奇才
舒大刚
苏轼无疑是从巴蜀走出去的最伟大的奇才!他的成就和为人,用任何一个“家”来概括都是徒劳的。说他是文学家只得其文,说他是书法家只得其艺,说他是政治家仅得其用,说他是思想家虽得其魂而未得其全,说他是保守党只得其形……他其实就是苏东坡,不可复制,不可方物!
《宋史·苏轼列传》评论说:“(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器识”“议论”“文章”“政事”四者俱佳,古今能有几人?这“四要素”还只是显性的,其隐性的还有“特立之志”与“迈往之气”,“志”与“气”是成就其“四要素”的支撑,而且是更根本、更深沉,也更重要的。因为“特立之志”决定他志存高远,不落流俗,不随大流,甚至还不畏权势,不谮君主;“迈往之气”决定他充沛的精气神,自有圣贤气象、仙风道骨、浩然之气、远见卓识、豁达乐观。故史臣又说:“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如果说东坡“文章”似花朵,“议论”似枝叶,“器识”如果实,“政事”如树干的话,那么东坡的“节义”“志气”则是使东坡精神文化之树常青的根柢触须。这决定了他不仅有思想、有学问、有才气、有谋略、有文采,还决定他有气节、有操守、有精气神,得志不骄,失意不馁,在朝不傲,在俗不俗;“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就是苏东坡!是何种力量成就了东坡精神呢?
一、读书造就丰富学识
作为普通农民、市民出身的三苏父子,要成就自己首先当然是读书。与东坡相倚相知的弟弟苏子由所作《东坡先生墓志铭》已为我们揭秘: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东坡的“议论”“文章”皆得益于贾谊、陆贽等汉唐政论;而其“迈往之气”则得益于《庄子》等道家风骨。
至于其“器识”“政事”“节义”与乎“特立之志”,亦必有其来路。苏辙又说:“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云云。可知东坡在人们熟知的文学作品外,还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而这些著作,都是在他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后完成的!可见其积极入世、敢讲真话、屡战屡败、虽败犹荣的性格,也就是“器识”“政事”“节义”与“特立之志”,多半得力于对儒家经典的寝馈、浸润和阐释。
以上还只是个人的因素。如果缺乏良好的环境配合和成全,虽有其才却无以发挥,也是成就不了苏东坡的。
二、环境成就英迈胆识
好在当时苏轼所处大时代和小环境,都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帮助。中国是“家、国、天下”的社会结构,任何人才的成就都离不开家国天下的怀抱。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治平之业的第一个驿站,同时也是人生旅程的最终归宿。家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国是地方环境,直接影响社会风气、道德好坏和成长利屯。天下则是更大的时代背景,是成长人才更广阔的陶冶空间。一个人才的成长,都离不开家国天下这三大因素的影响。有幸的是,苏东坡成长过程中,在这三个方面都打了正分。

眉山三苏祠
宋代崇尚文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君民关系比较和谐,不杀士大夫言事者,重文偃武,文教昌明。
《宋史·艺文志序》写整个宋代的文化政策曰:“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
“道艺”即《周礼》之“德行道艺”,即重视道德品行和学术修养,这属于政治学亦即“治术”。“经术”即重视中华根魂儒家经典研究,从历史典籍中汲取经验教训,这属“经学”。“道德性命之学”即重视个人心性、道德、修养的研究,这属哲学、伦理学,亦即“道学”。三者分属于“治统”“学统”“道统”三大领域,但都是重视文治教化的儒化之治。
清儒全祖望也说:“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同文)在宋,泰山孙氏(复)在齐,安定胡氏(瑗)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琦)、高平范文正公(仲淹)、乐安欧阳文忠公(修),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其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
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当时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角色。他们有的是政治改革的鼓吹者与推行者,有的则以讲学为主、倡导儒学革新,以新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作育人材。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诸人相继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改革时弊,整顿政治,将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他们本人也是当时名儒。他们的儒学观点、经学取向对于普通士子无疑具有表率作用,其中范仲淹是这批人物中的核心。
全祖望又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宋代士大夫究心理论研究,精神不受桎梏,自立学派,创见极多。此后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程颢程颐兄弟继起,蔚为大儒,成为宋学的代表。三苏父子也是其中重要领袖!
以上是就全国而言。就三苏父子成长的小环境而言,巴蜀大地不仅物华天宝,而且人文蔚然,贤孝辈出。《华阳国志·蜀志》赞语:“蜀之为邦,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显族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蜀地从天文、地理,到人文、风俗等方面,都非常优秀,这里岷山、嶓冢耸立,岷江纵贯,上应井宿络野,有文明秩序的气象;自古是圣贤(如大禹、嫘祖)和神仙(彭祖、王乔)诞生的地方。下文又说:“开辟及汉,国富民殷,府腐谷帛,家蕴畜积。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穆(和)之咏(按即王褒《中和颂》),侔乎二南。”物华天宝,国富民殷,文明和乐的歌乐,上达天庭,与《诗经》“二南”齐名。又载巴地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故于《春秋》,班侔秦楚,示甸卫也。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俗惇厚,世挺名将。”可见,巴地的历史也十分悠久,而且世挺名将。蜀国多圣贤神仙,巴地多忠烈名将,“巴将蜀相”,渊源有自,这与两地的地理特征、气候环境是有关联的。
进入汉代以后,武帝之时已是“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五教”即《尚书·舜典》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之所指,也就是夫、妇、父、子、兄弟等五伦教化。这里人伦关系雍雍和和,秀才茂士联袂而出;人物既多,故文学发达,风谣大行。“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在朝之臣,能尽忠为公;在乡之士,能崇尚文教,尽情歌咏。《华阳国志》于巴蜀二志展示的都是优美向上、重节尚忠、能文有武、移风易俗、砥励德行的风俗。
迄至宋代,苏东坡还在《眉山远景楼记》里盛情赞美:“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今吾州近古之俗,独能累世而不迁,盖耆老昔人岂弟之泽,而贤守令抚循教诲不倦之力也!”
苏轼说故乡风俗在三个方面与三代、汉唐相近:一是士大夫有推崇儒学和重视世家的传统;二是老百姓则尊敬官吏,遵守法纪;三是农夫们共同劳动,团结协作。这是一个有文化(贵经学)、有历史(重氏族)、讲团结(合耦相助)、敬官家(尊吏)、讲法治(畏法)的区域。这种风俗“累世而不迁”,其动力源泉盖得益于“耆老昔人岂弟(恺悌)之泽”(悠久的文化传统)和“贤守令”(地方官)“抚循教诲”(明良的地方治理)。正是这一上下的互动、一古一今的传承,才使孝悌传统得到提倡,民风民俗实现清明,于是便造就了一方家族文化胜景。

清·刘墉书苏轼《眉山远景楼记》(节书,立轴)
苏洵《苏氏族谱亭记》也说:“匹夫而化乡人者,吾闻其语矣。国有君,邑有大夫,而争讼者诉于其门;乡有庠,里有学,而学道者赴于其家。乡人有为不善于室者,父兄辄相与恐曰:‘吾夫子无乃闻之!’”意思是说,有作奸犯科的刑事案件,要到官府去处理;学习道理和文化知识,则到乡校向先生求知;而有关道德善恶方面的事情,则由乡贤绅士来评判。这里讲“匹夫而化乡人者”,是一种自信:即使没有官禄爵位,也可以教化乡里。是即孔子所说:“孝夫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为政!”这就是乡贤的力量!
眉州如此,同处井络一域的巴蜀各州县也有相似的风俗,因此自来巴蜀世家大族层出不穷,家族文化十分发达。巴蜀家族不仅人丁兴旺,而且人才辈出,文化鼎盛,成果丰富,高潮迭起,嘉话不绝。这一现象从汉代就开始了,经南北朝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达到顶峰,延续至明清,皆世有望族,族有达人。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巴蜀地区就涌现出了大批书香门第和文化世家,如成都二张(霸、楷),成都四赵(定、戒、典、谦),蜀汉诸谯(玄、纵、周等);至宋代巴蜀的家族成就更为突出,眉山三苏(洵、轼、辙)、铜山三苏(苏易简、舜钦、舜元)、华阳诸范(镇、百禄、祖禹、冲)、阆中四陈(省华、尧叟、尧佐、尧咨)、丹棱三李(焘、埴、璧)、陵阳二虞(允文、集)、绵竹二张(浚、栻)、井研四李(舜臣、心传、性传、道传);等等。
这些家族无不以出人才,出文章,出思想著称。三苏父子就是这众多巴蜀文化世家中的一家,当然是最为闪亮的一家!
三、家教成就高尚人品
巴蜀自古重视家教。东汉有犍为太守夫人杜泰姬;三国有刘备、诸葛亮和向朗。宋代更突出,世家多,家训亦富。

程夫人(左)与苏八娘(雕塑,在眉山三苏祠。选自“眉山东坡文化”公众号)
阆中陈氏注重家教和母教都是远近知名的,《宋史·陈尧佐列传》载:“父(省华)授诸子经。”说明在学问上,尧佐、尧咨得力于父亲陈省华。《南部县志》说:“宋陈省华对客,子尧叟、尧佐、尧咨列侍,客不安。省华曰:学生列侍,常也。”说明二陈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是受父亲的严格训导的。《宋史·陈尧叟列传》:“母冯氏,性严,尧叟事亲孝谨,怡声侍侧,不敢以贵自处。家本富,禄赐且厚,冯氏不许诸子事豪侈。”《保宁府志》又载:“陈冯氏,南部人,陈省华妻,多智术,有贤行,教子以礼法,以尧叟贵,封鄢国夫人。”说明二陈的成长还得力于母亲。冯老太君最善治家,以严厉著称。据说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他中状元,守荆南,回家省亲,母亲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答:“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官员所佩象征品位的金鱼)。现在阆中犹有“落金坡”,就是纪念冯氏教子故事的。陈氏诸女也将冯氏教子之法带到夫家,创造了良好的治家业绩。
铜山三苏之所以成就辉煌,也是得力于母亲薛氏的教育。《宋史·苏易简列传》载,宋太宗曾经“召薛氏入禁中,赐冠帔,命坐”,并问:“何以教子,成此令器?”薛氏答曰:“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太宗赞:“真孟母也!”苏舜卿的母亲王氏亦善教子,苏舜钦回忆,兄弟仨“得以俱登进士,得以艺升,不为家羞者,盖积是训厉,使去怠傲而自进立。”(苏舜钦《先公墓志铭并序》)苏舜元亦“课子舍治经史,率有准程,所以诸子皆积学有立”(蔡襄《苏才翁墓志铭);其夫人刘氏“薄于奉身而厚于施人,严于教子而宽于御下”“子男七人皆以才显”(苏轼《刘夫人墓志铭》)。
眉山三苏的成就,也与一位伟大的女性分不开,那就是苏轼、苏辙的母亲,老苏的妻子程氏。程氏出自名门,自幼熟读诗书,颇具远见卓识。苏洵早年累试不第,持家教子的任务全由程氏担当。苏家贫穷,程氏相夫教子,从无怨言;家里虽穷,从不向富裕的娘家求助,以免让倔强的夫君感到委屈;而是自己纺纱织布,贴补家用。特别是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成长,程氏倾注更多心血。据苏轼回忆,他曾夜读《后汉书·范滂列传》,忽有所感,问母亲:“儿若为(范)滂,母亲许我乎?”母大喜曰:“汝能为滂,吾不能为滂母乎?”程氏信佛,不许杀生,禁止小孩攀树掏鸟窝;有人在宅内发现前人所藏金银,程氏重新埋好,不许挖取,曰:“非分之财,分文不能妄取!”从而培养出轼辙兄弟勤奋读书,正直处事,忠贞不屈,廉洁居官的性格。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赞曰:“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不愧为古代一贤母!”

眉山三苏祠披风榭
此外,苏洵也有《名二子说》,结合两个儿子的禀性和世道规范,语重心长地对苏轼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洵其实在担心苏轼不能掩饰自己,招人忌妒。他又对苏辙说:“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这里预言苏辙善于自处,将免于大的灾祸。是文准确地预言了两兄弟后来的命运和处境。
在三苏父子正直品德、绝世文章的传统影响下,三苏家族也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和家训:“凡吾子孙,必讲文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正妇顺,内外有别;老小有序,礼义廉耻;为人豪杰,处事必公;费用必俭,为官必廉;非义不取,救死扶贫;敦亲睦族,敬老尊贤。”还对后世苏氏族人之为“士农工商”者制订了行为标准:“士不必名世,要之贤良;农不必千钟,要之力本;商不必巨万,要之廉贾。”以上条教至今还刻于湖北松慈武穴的苏氏祠堂中。可见苏氏家风家教之隽永!
中国是一个缺乏全民宗教的国度,没有教会,也没有忏悔,也没有牧师,没有人来给你布道。我们崇拜的是“天地君亲师”!崇拜天地,因为天地是万物之源;崇拜祖宗,怀念家庭,因为亲人是个体生命之源;崇拜君师,因为君师是启智益智、发挥想象、奔向远方的向导。家国天下——这个结构中的三大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君明臣良,国富民殷,政通人和,家安子才,这数者,苏东坡都打了正分。其成就了奇才,成就了东坡。东坡何幸!斯民何幸!
[1]全祖望:《庆历五先生书院记》,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四部丛刊》本。
[2]《宋元学案》卷首《宋元儒学案序录》。
[3]参见胡昭曦、蔡东洲:《阆州陈氏研究》,载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