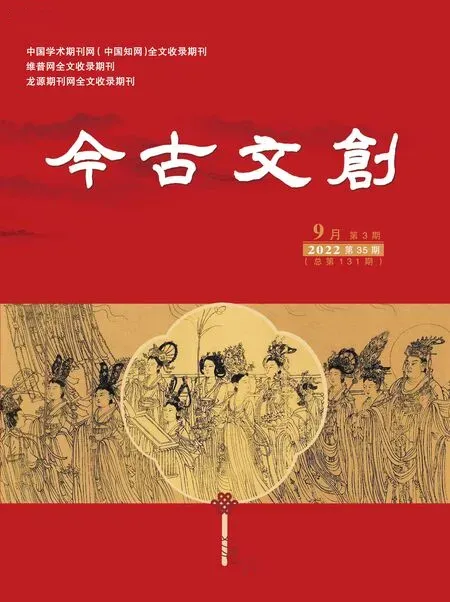论《护送》中小人物的身份焦虑
◎周智莹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护送》是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于1996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小说以“我”在去往桑给巴尔途中,意外结识了出租车司机萨利姆为端,继而展开了“我”与萨利姆之间的交往和种种故事…… “身份焦虑”视角或为人们解读萨利姆的形象提供了启示。阿兰·德波顿指出,“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意思是站立,即地位。广义的身份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身份焦虑则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罗洛·梅则认为,“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他存在的根本。威胁可能是针对肉体的生命(死亡的危险)或心理的存在(失去自由、无意义感)而来,也可能是针对个人认定的其他存在价值(爱国主义、对他人的爱、以及“成功”等)而来。”
桑给巴尔的种族歧视和殖民压迫,都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一种身份的焦虑。在这种大环境中,出租车司机萨利姆身上呈现出强烈的身份焦虑。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客观环境本身;二则是涉及的个体心理本身。正是外在的客观环境和个体精神焦虑的双重折磨,推动萨利姆自觉走向了麻木和沉沦。“我”,既是故事中的归乡人,又是故事的隐含作者,并没有进行简单的善恶价值判断,而是以一个外来者的目光审视着出生地桑给巴尔的一切,意在展现出被殖民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真实人生状态,并给予理解和同情。不难发现,萨利姆的焦虑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
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个人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小说中萨利姆有三种社会身份,分别是出租车司机、“非洲公鸡”和被抛弃的男人。
(一)出租车司机——小人物底层身份的展示
萨利姆的职业是一名出租车司机,驾驶的是一辆破旧的车,小说对此有详细描述:“汽车座椅笨重坚硬(而且是绿色的),塑料内饰已有些年头,裂痕斑斑……仪表盘上尽是窟窿,露着几截破电线,里面原先可能随手丢着打火机、收音机或手套。”这暗示了萨利姆经济状况的不佳,可见他在物质层面正遭受着贫困的痛苦。
职业、经济地位的地下加剧了社会地位的不佳。罗洛·梅指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工资代替生产活动本身成为工作的价值标准,社会尊严和自我尊严的基础,也由创造性的活动本身,转变为财富的攫取。”由此,当财富成为公认的成功标准,经济地位的低下自然变成了一种痛苦。显然出租车司机这个身份无法为萨利姆赢得尊严和尊重,他在精神层面遭受着受人忽视、冷落甚至遭人白眼的痛苦,连“我”也不例外。小说有较多篇幅描写了初见时“我”对萨利姆的不理解和厌恶:“我”初次坐上萨利姆的车,却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甚至后悔自己应该看到他的苦瓜脸就立马走开;“我”有一搭没一搭地低声嘟哝,表明自己懒得跟他说话。“我”用眼里充满憎恶、满脸不屑、冷酷而痛苦、满脸坏笑、轻蔑地哼了一声、野蛮地按着喇叭、脾气这么坏来形容“我”对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和情感甚至贯穿了“我”和萨利姆的整个交往过程。由此可见,物质上的贫苦和精神上的备受忽视、冷落造成了萨利姆深刻的经济身份焦虑。
(二)“非洲公鸡”——殖民视野下种族身份的展示
桑给巴尔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萨利姆以戏谑口气调侃道:“你们见过他们怎么打扮这些狒狒吗?他们把她们从山上带下去,给她们套上黄围裙,扎上黑领结,然后管她们要服装费用。”桑给巴尔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于此可见一斑。非人化的待遇、被剥削的艰难处境,是整体桑给巴尔人民的共同遭遇。总体来看,小说并无刻意强调萨利姆的非洲身份,但由身份带来的偏见和歧视间接性暴露这一事实。酒吧里,萨利姆对三个欧洲人的话作出回应,但人家“似乎并不在意他”。他们对萨利姆的搭话视而不见,甚至没有瞥上一眼;我质疑马来亚女人之所以能看上萨利姆,是因为他“在海滩上十分了得”,此时萨利姆显得“似乎有点小受伤”。“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正是这些偏见和歧视让萨利姆在心底产生了自我怀疑。威廉·詹姆斯说:“对一个人最残忍的惩罚莫过如此:给他自由,让他在社会上逍遥,却又视之如无物,完全不给他丝毫的关注。”在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建构下,对黑人的忽视、排斥和歧视,是引发萨利姆种族身份焦虑的根源。
(三)被抛弃的男人——情爱关系的失意
萨利姆总是孜孜不倦地向“我”讲述他的“马来亚女人”故事。他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有人讲这些故事,你认为他们在说谎——他们在梦中与有钱的欧洲妓女约会——这些都是一派胡言。在我遇到我的马来亚女人之前,我也这样想”。这种欲扬先抑的故事开端,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为了增加故事可信度而使用的拙劣技巧。他一边走一边说,“脸上洋溢着微笑,沉浸在回忆之中”。
“马来亚女人”故事的真实性不置可否。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萨利姆是在幻想中,为他自己编造了一场类似艳遇的情爱故事。萨利姆编造了种种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前后矛盾而显得不真实:萨利姆带“我”去参加婚礼,他说新娘是他老婆的亲戚,自己已经结婚了,“我”继续追问,他却罕见地只字不提;萨利姆说马来亚女人很有钱,“要是用外币来算,那也没多少钱。你知道的。不管怎样,她很有钱”。作为隐含作者的“我”,也已在内心认定这是一个老套的疯狂欧洲人追求非洲公鸡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技巧拙劣,漏洞百出,但萨利姆却深深沉醉其中。他为自己安排了一个“被抛弃的男人”的角色:马来亚女人带着他去乌拉亚、去利物浦、去法国,又去澳大利亚。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他还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女人寻欢作乐……因为他流血了,最终被抛弃,回到了桑给巴尔。这似乎为他孤身一人作出了合理解释。笔者认为,萨利姆意图掩盖的是,他在追求性与情爱中的挫折和不如意。连“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女人会随随便便看上萨利姆,更何况是一个有钱的欧洲女人。事实上,可能根本没有一个女人会看上萨利姆这样没有钱的非洲黑人,或许他还有着“会流血”的生理缺陷。“性的权利通常被认同是个人权利、尊严、威望的表征。”出于现实情爱的焦虑,抑或是美化自己的生理缺陷,萨利姆选择为自己安排了如此的男性角色,这一角色似乎更能博得理解和同情。
二、个体的焦虑
(一)生的苦闷
萨利姆接连两个夜晚的主动拜访,这让“我”吃惊非小。因为旅馆远离尘世,“我”并不期待,也未曾料到会有人来找“我”。萨利姆上身穿着白色花朵和蓝色独木舟图案的绿色丝质短袖衬衫,下身裹着宽松的灯芯绒牛仔裤,胸前口袋里还露出太阳镜的一条腿,俨然是非同于平时的精心打扮。他执意要请“我”和酒吧招待喝一杯,意欲继续讲他的马来亚故事。强烈的倾诉欲或许正是萨利姆不顾偏远二次登门拜访的原因。他实在是一个孤独、苦闷的出租车司机,过着逃不掉的单调生活。而“我”恰好又是一个忠实的听众。或许“我”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搭理他、倾听他的痛苦与不幸的乘客之一。“最能让不幸的人感到宽慰的事情莫过于找到一个愿意倾听他们不幸的对象。”正是“我”表现出的些许理解和同情,极大安慰到了萨利姆,使他的痛苦和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并让他执着于把故事讲下去。
(二)性的苦闷
德波顿认为,“每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包含两个关于爱的故事,第一个是追求性爱的故事,第二个是追求世界之爱的故事。”萨利姆在追求世界之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及其存在的关注)的道路上并不顺利,在追求情爱关系的道路上也失败了。萨利姆和马来亚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流血了。她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不碍事,但他依然不能留下来。他最终还是被那个马来亚女人抛弃了,这给萨利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使他患上了“一和女人啪啪,就会流血”的病。“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我一和女人啪啪,就会流血。”“会流血”是萨利姆的性的焦虑在生理层面的具体化。“个人有意识地忍受焦虑的能力与身心症状的出现大体成反比关系。”换言之,萨利姆愈是有意识地感到焦虑,压抑得越深,他出现流血等焦虑症状的可能性就愈小。而他本身并无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焦虑。“流血”症状在后来的每一次重演,都是萨利姆自身对性的焦虑的一种无意识抵抗。
(三)获得认同的迫切需要
临走当天,萨利姆特意来送“我”去机场。他开口请“我”下次给他带一个同样的公文包来,保证少不了“我”的钱。显然公文包与萨利姆的身份并不相配,那为什么他还要请求“我”为他带一个呢?在萨利姆眼里,公文包是一种身份标志,象征着体面的工作和生活:“我”从遥远的奢华之地“尤因格雷扎”来,是来自英国的贵客;“我”的职业是一名老师,有社会地位,受人尊敬;“我”带着一个公文包……初次见面时,他就三番五次地瞥看“我”的公文包,认定了它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受人尊敬的、奢华之地的重要身份标志,而这样的身份正是萨利姆所缺少和需要的。萨利姆迫切地需要拥有一只这样的“有身份”的公文包来改善他现在的境况。
马来亚故事或许能够真正或再次发生,像萨利姆盼望的那样,而“我”就是那根摆脱现实生活的救命稻草。萨利姆恳求“我”带他一起走。只要能带他一起走,让他干什么都行。此时的萨利姆一改以往脸上的憎恶与傲慢,带着温柔、羞怯的微笑,甚至慢慢变成恳求。
三、小人物的挣扎和沉沦
(一)萨利姆的“憎恶”
小说开头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初见时萨利姆的“憎恶”:“他折好报纸,溜出门,瞥了我一下,眼里充满憎恶。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惊讶得浑身直抖,整个身体都被掏空。也许这并不是憎恶,而仅仅是对躲不开的挫折和逃不掉的单调生活的恼怒和不满。可这表情让人觉得更像是憎恶。”隐含作者用了憎恶、恼怒和不满、愤怒、咆哮、满脸不屑、冷酷而痛苦、故意残忍、骂骂咧咧、野蛮、大喊大叫、脾气坏、毛骨悚然、怨恨和愤怒、恶意和傲慢、嗤之以鼻等等字眼来描写萨利姆,给读者留下了“恶”的形象。反之,“我”在与萨利姆的接触中,也渐渐发现了他柔软、胆怯的一面。小说中有10次写到了他的“笑”,有“微笑”“坏笑”“不情愿的笑”和“咧嘴笑”。临别时,“我”把身上所有的当地货币都给了他,他“咧开嘴大笑”。总体上,萨利姆性格中“憎恶”的一面占据了上风。初见时,“我”的外表似乎就已经惹怒了萨利姆,使他的眼里充满了憎恶和愤怒的神色。“个人理所当然地会对具有威胁性的、又带来无助与焦虑痛苦的人事产生敌意。”萨利姆的“憎恶”,是一种敌意,以对抗“我”的突然出现给他带来的焦虑与痛苦。在路上,萨利姆总是抱着傲慢、轻蔑的态度跟“我”说话。也许正是他感觉到了自己与“我”在身份上的差距,所以才想方设法地耻笑“我”,“他哼了一声,‘学生?’”贬低“我”的身份是他的目的,以此缓解发现自己不如别人的恐惧和焦虑。理论指出,“焦虑会带来敌意,敌意会给焦虑者带来更强烈的焦虑”。如此,萨利姆的“憎恶”演变为一种恶性循环。
(二)诉诸酗酒和嫖娼
酗酒和嫖娼是萨利姆缓解焦虑的两种手段,与之对应的则是“酒吧”和“夜店”这两个叙事空间。萨利姆接连两晚来拜访“我”,小说都围绕着“酒吧”展开。他显然嗜酒成性,他边讲故事边喝酒,喝完了便“轻轻把杯子朝我推过来”,抑或是抓住“我”的手腕不放,直到又点了一轮。而“我”则仿佛是一个愿意为他支付酒钱的“冤大头”。萨利姆也热情邀请“我”去夜店,而这个“夜店”竟是“一帮男人聚在树林中黑暗的房子里偷偷喝酒”,与“我”想象的大不相同。“阿齐扎”则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形象,是萨利姆和他的朋友们的嫖娼对象,身体年轻丰满,眼里却空无一物。萨利姆称之为“肮脏的游戏”。
显然,萨利姆的内心是有明确的善恶道德价值判断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小镇上,是什么让他放下一切去饮酒作乐呢?《焦虑的意义》指出,“酗酒和强制‘性’行为都是这类例子。动机不再是活动本身,而是活动的外在成效。”换言之,萨利姆追求的并不是酒和性本身,而是它们所带来的效果:暂时忘却或舒缓他心头的焦虑。
临行前,“我”将一大捆当地钞票都留给了萨利姆,真诚地希望他能够好起来。他咧开嘴大笑,并没有注意“我”说了什么。他走开了,“挥挥手,没有回头”。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不得而知,萨利姆为何没有回头,也许是他正在奋力抑制想要离开的冲动,也许是深感无望,而就此向命运低头了。
四、“护送”的三重隐喻
“护送”一词是小说的标题,仅在全文中出现了一次:萨利姆带着我去参加婚礼,“正赶上新郎家人和朋友的队伍护送他到新娘家门口”。“护送”在小说中有以下三重隐喻意义。
(一)婚姻关系的渴求和化解困惑的想象
小说中“护送”的婚礼片段设置意在展现萨利姆对于美好婚姻等社会关系的渴望与焦虑。家人和朋友们簇拥着、护送着新郎到新娘家门口,这也许是萨利姆幻想中的自己的美好婚礼的场景。他之所以称嫖娼为“肮脏的游戏”,正出于他内心存有对建立美好爱情婚姻关系的渴求。这种渴求,是他性的苦闷与焦虑的延伸。想象是萨利姆化解这种身份焦虑的惯常方式。小说未点明萨利姆和新郎新娘是什么关系,但萨利姆“嘲笑地哼了一声”,说“新娘是他老婆的亲戚”。这句话的真实性是存疑的。或出于嫉妒,萨利姆为自己编排了一个新身份:这时他已俨然变成了一位有妻子的丈夫,“我和她结婚好长时间了”。“我”的继续追问,则让他意识到了这个故事的纰漏,显得前后矛盾,因而他“微微一笑”,便再也不提起了。事实上,萨利姆可能根本没有妻子,为人夫也可能仅仅是他的幻想。人总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得以确认自己。婚礼上萨利姆幻想了自己的丈夫身份,在这种想象中,萨利姆短暂地确认了他自己。
(二)萨利姆对“我”的“护送”
“护送”也指出租车司机萨利姆对“我”的一路护送。在桑给巴尔的日子里,“我”和萨利姆之间似乎突然建立起了某种类似友谊的特殊情感:他只是“我”无意中搭到的一辆出租车的司机,但他接连两晚来拜访“我”;“我们”在酒吧喝酒,给“我”讲故事;邀请“我”去他和朋友们的“夜店”;带着“我”去参加婚礼……显然萨利姆是喜欢“我”这个外来者的。
究其原因,其一,萨利姆和“我”算得是同乡。“我”出生于桑给巴尔,意味着“我”和桑给巴尔及它的人民同时存在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正是这一点上的共通,使得“我”和萨利姆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尽管“我”认为他总是憎恶的、愤怒的,“不想走进他的朋友圈”,但是他的故事往往使“我”不得不承认对其更容易产生天然的理解和同情。其二,“我”和萨利姆正经历着相似人生,只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而已。“我们”同样都是桑给巴尔人,而后又离开了故乡去往异国。不同的是,几经兜转,萨利姆最终还是回到了故乡。而“我”仍漂泊在异国与故土的边缘,不知道该去往何方,暗含了“我”无根的身份焦虑现状。临行前,萨利姆不顾我的推辞,主动来送“我”去机场,他说:“下次你可得留下来呀!”这个小人物不仅在一路上默默护送着“我”,还为处于身份困惑中的“我”指明了方向。
(三)桑给巴尔对“我”的“护送”
对于英国来说,“我”来自桑给巴尔,始终是非裔移民,是外来者。“我”与真正的英国社会永远有着距离和隔阂。对于桑给巴尔来说,又似乎仅仅是“我”护照上的出生地。殖民统治下,“我”被迫离开桑给巴尔,割断了与故土的精神联系。再次回到桑给巴尔的“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很陌生。小说时刻都在提醒着读者们,“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更多是以一个外来者事不关己的目光和心态,审视着这片土地上的贫困落后的一切人与物。“我”的叙述语气冷漠平静,甚至时时显露出自以为是的强烈优越感,显然“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这也是隐含作者古尔纳对于自身移民身份的一种焦虑:既不能彻底融于英国社会,也已无法真正归于故土。对他而言,这两种环境都是陌生的、异己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排斥着他。他是一个游荡在异国与故土间的“边缘人”,始终怀抱着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焦虑和追问。小说接近尾声时,古尔纳借萨利姆之口给出了这样的回答:“萨利姆说:‘很快你就玩够了,要回到故乡。每个人都得这样,要不然,他们就会在异国他乡沦为笑话。’”因此,“护送”也暗喻着故土桑给巴尔对“我”的护送:“我”和桑给巴尔之间拥有着永恒的血脉联系。“我”无所可去之时,最终理应回到桑给巴尔去。这也是古尔纳为千千万万像他这般深受殖民迫害、背井离乡而又挣扎徘徊于异国与故土间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启示:回到故乡去。
五、结语
《护送》中,古尔纳客观呈现了桑给巴尔底层小人物萨利姆的生存困境和身份焦虑,并给予其深刻理解与同情。萨利姆的身份焦虑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也有独特的个体性因素。萨利姆个人的强烈身份焦虑,正是当时桑给巴尔社会关于身份认同的一种社会性困惑与焦虑。对此,古尔纳在小说中给出了他的答案:回到故乡去,回到桑给巴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