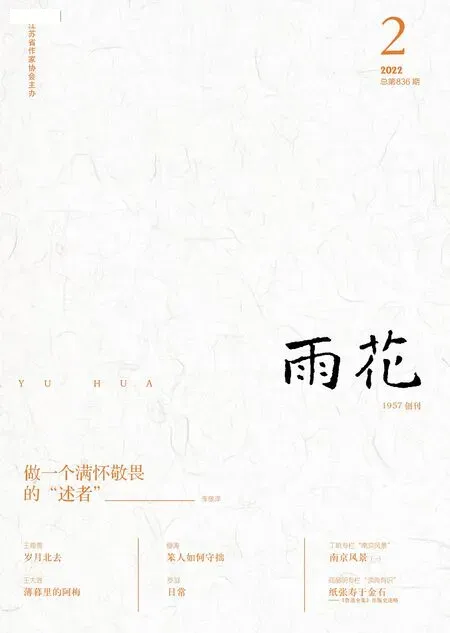金鱼
王宁婧
我跌跌撞撞地闯进花鸟市场。一片热烈的狼藉。热带鱼晃动在大大小小的玻璃箱里,被猛然惊起,像炸开的黄色瀑布。水草好像漫过了我的鼻尖,我感觉到痒。柔软的绿萝、吊兰、发财树,它们嫩绿的枝条旁逸斜出,从道路两边纠缠在一起,慢慢绕成繁杂的结。我沿路拨开叶子走着,眼睛不断和那些中年妇女探询的眼睛不小心碰上,可是就好像被淹没在绿色植物的喧嚣之中,我发现自己实在是口不能言。其实我只是想要一条鱼,一条血红色的金鱼,就像我们那里的博物馆中那块对半剖开的玛瑙一样。春游的时候我们总是去那家博物馆,玻璃展柜里的几件藏品同学们都要看厌了。可是那里的彩色石头多么好看。几次走过这个花鸟市场,我都满心憧憬地假装不经意瞥一眼那些巨大的透明水箱,想用那个挂在水箱上的绿勺子舀点水,捞一条和玛瑙一样红的鱼装进塑料袋里,这样我就能拎着袋子走在路上,水和鱼就会在烈日下粼粼闪光,那是一个只有我理解的倒悬的世界。
左手边,一个穿粉红色上衣的中年女人叉腰立在店门口,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扇。一束盛放着的茉莉从她耳边伸过去,一片烂漫,花香馥郁。她双颊耷拉,脖子上已经有很多圈细小的褶皱,腰上系着一个暗蓝的挎包,缀满廉价的假珍珠。包的拉链敞开,纸钞向外花花绿绿地翻涌出彩色的边角,五块钱、十块钱、一百块钱,蓝的、绿的、红的。就在我默数的时候她已经张口叫住我:“哎!你要什么?”我于是赶紧往她的店里探过头去。满屋的繁花和鱼缸,但是晦暗不明的枝条和花盆间可以辨认出受潮剥落的灰墙,盖布的麻将机和神龛上油亮的寿桃,半张已经卷曲的红奖状,一个边削铅笔边抬头看电视看得呆住了的男孩的后脑勺。
我知道这些精明的妇女会看出我是一个闯进来的外行人,一个笨口拙舌的小女孩,所以我暂且不声张。天气闷热,几团云低压在天际,太阳高远而眩目。我脚下的石子路滚烫,楼上一扇旧窗户“吱呀”一声被推开,一个穿睡衣的女人在对面打哈欠,挽过她柔软的头发—我总是在这样的时刻突然走神,第六感漂游在一片浮躁之中,时间拨慢它的指针,然后突然静止。回忆起整个童年,我只能捞捕出许多满溢着的无意义片段,使我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一条全是斑斓碎片的河流中—然后我回过神来,猛然回到平衡的时间里,壮起胆子,就像怕她听不见似的大声问:
“你们卖不卖鱼?就买一条。”
“你要就拿两条。一条不好卖,这鱼太小了呀。”
“但是我只要一条。”
“十五块再买个鱼缸吧。我给你装上。”
“我也不要鱼缸,我就要一条鱼。”
“鱼食呢?五块一袋,八块我给你两袋。”
“不要了。我只要鱼。”
她给我把鱼捞上来装进袋子,鱼在阳光下跳动,明亮亮的水珠四溅开来,有一滴落在我鼻尖。果然是用那个绿塑料勺,水浇进透明的袋子,鱼飞快抖动几下,又恢复了它的流利自如。多漂亮的鱼啊。我转过身把钱搁在麻将桌上。那男孩睡着了,呼吸均匀起伏,枕着因为用橡皮使劲擦而起皱的作业纸。阳光穿过横斜的枝叶落在他杂乱的黑头发上,晶莹的汗滴从额角滑过。桌边陈旧松软的木质楼梯拐进昏暗的楼道里消失不见,一扇半掩的铁门里露出半个空旷的后堂和缺半角的天空。好新鲜的一天,天蓝得像要融化塌陷下来。湛蓝而永恒的天空总是引起我们的许多感触,因为在这样一座巴掌大的小城里,随便拣一片空地,你都可以轻易毫无遮拦地望见整个延伸到无尽远方的苍穹。
无尽,一个触动人心的词,就仰卧在头顶上,和我们蜗居穿行的窄小人间如此背道而驰。我们的世界平静、热闹、精致、灿烂、无忧无虑,它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微缩造物,喧哗得让人感觉心里踏实。但是我们依然会不时把目光投向高远的天空,被那种失衡的无边广阔所俘获。有谁说过:“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我想起来是庄子说的。老师讲那篇课文的时候正好也是清新而空阔的秋天。在要开运动会的时节里,学校的树上每天落下丰腴肥大的花瓣,枯枝慢慢淹没了操场的边沿。有一群值日生在阳光下扫地,挥舞着扫帚打架,落叶变成很多金色的蝴蝶。跑完八百米我们躺在操场上,假装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整个身心掉落在一片热烈和昏倦里。蚂蚁在玉兰树落下的巨大花瓣里小心地蜿蜒爬行,钻进我灼热的手心。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伏在地上看天,才知道织就我们生活的歪歪扭扭的建筑们究竟有多矮小。基督教堂以往高耸的红十字和旧蓝玻璃窗掩映在缠绕交叠的电线里,而钟楼和医院隐没在杂乱的建筑群里,它们都蛰伏在广袤的天空下,只有修理电器的喇叭声回荡在寂静的午后。我心里猛然产生一种落空的茫然感。我其实每天都在做题。我快毕业了。毕业以后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我想象不出我自己坐上火车去读大学的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到底应该干什么呢?到底做什么才会一点时间都不浪费?什么样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老师也不知道。要做的事太多了。我周末坐在新华书店的地上读到一首诗:“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蛊惑着的/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被点燃,卷曲又卷曲,却无处归依。”我们的天空是多么冷静而复杂、引人遐想的东西啊。
星期天周云和我在食堂里擦桌子。一整排铁水龙头正在“哗啦啦”地放水,几千只碗筷盘子碰撞发出的闷响回荡在寂静的大厅里,让我们知道楼上肯定忙得不可开交。食堂的地永远油腻得黏脚,我们小心地在其中移动,从一张桌子转到另一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铺有花色不同的廉价桌布,同一种甜美的欧式花纹无限地重复下去,从桌上垂到桌下。菱形的石砖从脚下向前延伸,延伸到远处刷成墨绿的墙根。擦桌子的时候我们忘掉了一切。简单的劳动让我们变成两条绳索,反复拧紧又反复松开。在无意识的茫然里好像是我告诉她,她真应该看看我新买的金鱼。
这时候她爸爸从楼上摇摇晃晃走过来,他是个食堂师傅,光洁锃亮的脑袋,白色的臃肿工作服,就像一只羽翼丰满的白鹅。周云哼起歌,抹布上的水一滴一滴落到地上,灼热的阳光映在我眼皮上,我眨了两下眼睛,泪水流出来。近日来大人们发明了消磨时间的新办法,我们周末就在这里打工,中午五块钱两小时,擦完一层楼所有的桌子。现在周云爸爸端着盛有两个油光闪亮的鸡腿的盘子,让我们快去洗手,劳动时间终于结束了。很久很久以来,白塔小学里只有我们两个在此上学的职工子女是住在大院的。象牙白的破旧宿舍楼掩映在高大的苍翠杉树间,荒草萋萋,篱墙外就是广阔的池沼洼地,这就是我们长大的地方。周云大我七个月,和我一样上五年级,在她班里当班长。每周一升旗,我一抬头就能看到她站在隔壁班队首,意气风发,和周末我们一起爬树捡垃圾时判若两人,那是一种让我无比仰羡的威严。我们跑出食堂卷帘门,天光大好。周云轻巧地吹了一声口哨,美好的周末还有半天可以消磨。
那一年夏天我妈妈在宿舍门前的绿化带里放了一只芦花鸡。鸡在萋萋荒草里四处啄食,扑棱着它被剪掉一半的翅膀,周云拽住它一边的翅膀,强迫它坐下去,捋它头上的羽毛。它卧在棕榈树发黄的烂叶中一动不动,浓烈的阳光涂在金黄的绒羽上,熠熠生辉。我蹲在旁边,观察这个孱弱温热的生命。在它诚惶诚恐的眼神中,我突然产生某种疑惑。鸡也有它自己的想法吗?永远徘徊在大地上的蚂蚁在想什么?甚至,我都不能确定周云、我的爸爸妈妈、老师同学是不是真的有他们自己的意识,他们为什么会活着?芦花鸡抖动它蓬松的新羽,粉尘飞扑,趁周云愣神的工夫从她手里滑脱出去,钻进草丛里。周云拍拍手站起身来,我们要玩捉迷藏的游戏了。她总共数二十声,我跌跌撞撞钻进宿舍里我家的门,缩在柜子里,把柜门扣紧。涂料的刺鼻气味和霉味,多么熟悉。只不过这次我学会了新的伎俩,把鞋子藏在窗帘后面,让她第一次扑个空。我闭上眼睛,脚步声在屋子里转圈,窗帘被一把掀开又拉上,脚步声又在屋子里转了个圈。然后柜子猛然被拉开,眼前乍然一片光明,我们都吓得大笑大叫起来,我几乎是摔出木柜,叠好的衣服全都落在地上。
我屋里空间很小,只有一张旧办公桌,权当书桌,外加一张床、一个衣柜。书桌上有一个旧相框,一个笔筒,抽屉里还藏着我和周云设计的一张泡沫船图纸。我们做过很多次实验,想用学校空调机的泡沫包装、破烂堆里的木板,造出一艘可以在学校的池子里航行的船。一个月以来,从幼稚的图纸到材料、工具,本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居然慢慢成形。有很多次,我梦见一艘巨大的航船,扬着白帆,从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随风而来,太阳在它身后升起,成团的白云在大海上塌陷,伴随巨大的轰鸣声。大海寓意无尽的未知、无法企及的远处与另一个世界,而我想要航行,往无尽处去,往未知去,往死亡去。当我醒来,发现一个守序的物理的世界正在运转,钟敲响七下,芦花鸡在门外边踱步边“咕噜噜”地叫,突然发现这种愿望在现实中显得分外失真。浮现在脑中的只剩下今天要交什么作业,晚上几点可以开始玩游戏。那个老师套着一件紧巴巴的衬衫走进教室,在哄笑声中摘下头上的叶子;学校楼道角的一面墙上写满了小学生幼稚的表白,有人在上面写下校长的名字,打了个叉。笑成一团的学校生活。可我也没有忘记我的船,放假后周云和我一起画图纸,她和我一样无聊。但她是多么受欢迎,我羡慕她和谁都能做朋友。她帮我画图的时候一心一意,她爸爸在食堂的手艺也很好。周云转头看了看桌子,这时候我跑去把抽屉拉开,我说好耶,我们继续造船吧!
我十二岁,对许多事情有了自己的朦胧判断,譬如说有时候我会在镜子前端详自己的脸,不相信这张真切存在的脸可以代表我,代表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我发现自己没有周云好看,这是一张扁平、粗糙的脸,一具略显干瘦的身体,一条过分鲜艳的蹩脚裙子。我凝视我自己,像在凝视一个陌生人,凝视一种枯燥而无法得偿所愿的现实。现实中什么都需要规则,聚沙成塔,汇流成海,榫卯结合,一个一个螺丝拧好才行。品学兼优的人如周云,精打细算地计划生活。而我散漫、快乐,暑假最后一天才开始写作业,像动物一样短视地活着。贫瘠的生活经历,窄小破败的房间,还有我,飞在房顶上的我,有那么多的狂想,那么多的渴望,它们远远地越过了规则,凌驾在缺失之上,让我感受不到不幸和失衡。我的红色金鱼,此刻在桌上一个透明饼干盒里游动,让我感到我们也是宇宙这座大花园里的金鱼,是博物馆里某个有象征意义的陶土盘子,是顺着纹路生长的螺旋,按照一定的生命密码转化为实形,轻飘飘而来,轻飘飘而去,然后陷入无梦的睡眠。我们带不走任何东西,出色的人生,悔恨与遗憾,那只是短暂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被缝在更宏大的永恒之中。我们确实应该开心一点。
周云在桌上把图纸摊开,习惯性地咬铅笔笔头。尺子铺成一摊,散落在日光下,我翻出最大的一块泡沫、八个螺丝、九个螺帽、一箱针线、三块小木板、剪刀、螺丝刀,一一排好。门“吱呀”一声响了,阳光下拉开一个影子—小叶子探进头来,她又来了。小叶子刚念大班,才开始学拼音,周末她爸妈就在学校英语组办公,而她常在学校里晃荡,喜欢摸进宿舍找我和周云玩。我感到极为扫兴,可是周云满不在乎,她把小叶子抱在腿上,像模像样地手把手教她剪下白纸上画的一面小旗。小叶子扭来扭去,极不适意,偏要桌上那把螺丝刀。芦花鸡踱到门口探看,又若无其事地踱走。我想到我爸妈今天要阅卷,我们还能玩很久,就期待小叶子快点走。她却像是要赖在这里,对我们的工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每样材料挨个问一遍。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螺丝。”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螺帽,不要动。”
“这个怎么用?”
“这个是当旗杆的,我来切一下,尺寸更合适一点。”
我在中间凿空的塑料板上铺上木板,转头看见小叶子正把头贴在装金鱼的饼干盒上,伸出手去碰触盒壁。我赶紧把她的手扯开,让她别碰。谁知道她却蹦出一句:
“你们说,让金鱼在船上游是不是很好玩?”
少年时代我们对所有活物都怀着浓烈的好奇。落在地上的半个柚子散发着馥郁的香气,我们剥开每一瓣扔进水塘,池里溯洄游动的蝌蚪被装进塑料瓶里,以至于白粉蝶收敛双翅将歇在花上时,所有孩子都跟着我们学会了悄无声息地捏住它单薄漂亮的翅膀。我们会咀嚼松针,从酸辛里尝出一点橙子的味道,我们会把青草连同细白的根拔起,编成草环,扎上草结。现在我和周云如小叶子所言,为一个新鲜而略有些残忍的游戏跃跃欲试。于是我们推开半掩的木门,在繁花下前行,跳过每一级石阶,我手里端着塑料盒,小心翼翼不让水溅出来,金鱼在水光中晃荡,漂亮的鳞片泛出金色。学校有一个莲花池,我们常爬过假山去摘莲蓬。拨开桂花树丛,潮湿的苔草沿池缘生长,我们三个人鱼贯而入,张望着池上垂下的葱茏绿荫,暮色正在降临。
小叶子自告奋勇要给金鱼舀水,因为将鱼倒进甲板上后水浅得只够扑腾。
“不行!水边危险!”
“就一下下,不要紧的。”
小叶子说着已经跨出去,用塑料罐在池水里舀了一罐水,倒进船里,正回头向着我们:
“你看—”
下一秒她忽然毫无征兆地脚下一滑,随着砾石落进池水里。船被打翻,泡沫和木板散落一池,金鱼鲜艳的一抹红在混乱中消匿。小叶子甚至来不及伸开双手,就以一种即将伸展的姿态像雏鸟一样歪进水中。池水短暂地震荡,然后依旧沉入冰冷的平静中。我们看见一双手没下去,最后只剩下一串升起的气泡。我保持着一个徒然抓握的姿势,冰凉生涩的池水好像也倒灌进了我的鼻腔,乃至朦胧无序的意识。周云立刻转头飞快地跑走了。我留在原地,不知道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该想什么,小叶子栽倒的场面如在眼前,而冗长的等待还在继续,无尽的绝望还在拉长。黄昏时节天边浮动着寒鸦,我多么希望我也变成其中之一,可以轻捷地掠过这漫长无望的等待。可是命运迫使我注视那一串浮动的气泡,在池水中一定正有一场殊死挣扎。半缕晶莹的蛛网挂在池面上,被撞落的桂树叶渡向池中央,一切是那么安闲自适。但我的心剧烈地起伏着,死亡的阴影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抚掠过我们。
隐隐有一阵嘈杂呼喊声,渐渐地近了,近了,他们来了。周云弯下腰来大口喘气,额上挂着晶莹的汗滴。她爸爸已经跳进池水中,不一会儿拽着小叶子的胳膊慢慢浮出水面。小叶子闭着眼被平摊在池边,围聚的大人们中有人挤按她的肚子让她吐出水来。在那一片喧哗忙碌中,我看见周云远远地蹲了下来。我走近她,而她低垂着眼帘,拨弄着地上的石子。
我问她:“怎么了吗?”而在她张口回答之前,只听她爸爸一声断喝:
“跪下!”
周云跪了下来。她的膝盖重重地落在石砾路上,我忽地惊觉一种后怕。在迟滞的惊疑中我的目光落在远处我父母的身影上,他们正凝望着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呆呆地僵站在那里没有跪,而周云的爸爸开始厉声训话,这漫长的时间里,我的思绪却在向黄昏中晦暗不明的远方飘去。小叶子嘹亮的哭声,也终于响起来了。
我顺着竹梯爬上宿舍顶上旧仓库的阁楼。踩上单层陈旧的木板时它们一下一下颤动,飘起的灰尘弥漫在夕阳的余晖中,呛得我噙起眼泪。在蒙眬泪光里我四处张望,看见周云伏在堆积的条凳和簸箕中间,趴在仓库狭小的窗边向外远眺。铝窗条的半截封膜纸在晚风里歪斜晃动,窗栏里满是死去苍蝇的残骸和蜷曲腹部的甲虫。我也踩过去伏在她身边,顺着她的视线向外张望。多美啊,我们小小的学校,蛰伏在成团的柔软绿荫之中,如同不经意缀在草茵中的白绒花。而绵延不尽的平原沼地里荒草无声无息地日夜生长,潮湿的绿色淹没并缠缚我们,包裹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生长着的这片土地,这里的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砖瓦,每一个意识每一次细微的呼吸,都浸润在绿色的血液里,生来就彼此声气相通,互为表里。白塔小学那座象牙色的白塔在落日里就要融化,塌陷进粉蓝的晚云中。我忘了说话,忘了和周云说对不起—对不起,船明明是我要造的。可是我全然忘记了,脑子里却浮现出一个相似的黄昏,有一天放学后我们游荡在一个楼道的拐角,楼梯下一面隐蔽的墙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表白。在其中我找到了周云的名字,指给她看,我们因之笑成一团。那个下午我发现一个严肃的事实,我们正在一天天成长,一天天没入一个新鲜而陌生的世界。可是我们真的长大了吗?或者我们真的还是孩子吗?
我的金鱼落入池水中再也不见,它就像所有发生在这个荒芜世界里的谜团一样蓦然隐匿,或许我们的童年有太多这样蛰伏而被遗忘的线索。在无止无尽的思索和迷惘中,我们就在奔流的生命之河里生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