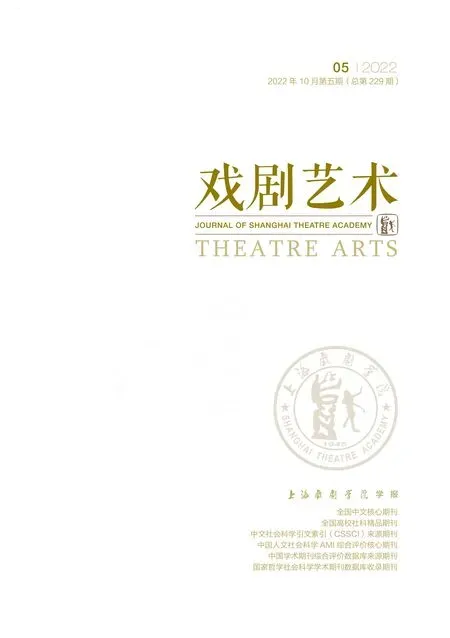是“文”不是“戏”: 从金圣叹评《西厢记》看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
汪晓云
《西厢记》为戏曲之祖,自问世以来,评本无数。在众多评本中,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独占鳌头。李渔言:“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他又称:“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在李渔看来,只有金圣叹评《西厢记》,才能阐发《西厢记》的幽微之义。其言下之意,只有看懂金圣叹评《西厢记》,才能看懂《西厢记》;看不懂金圣叹评《西厢记》,即看不懂《西厢记》。金评《西厢记》是《西厢记》评点史上的高峰,然在当时亦不乏批评者,如梁廷枬《曲话》即反对金圣叹割裂更改《西厢记》。但总的看来,清代学者对金圣叹的推崇远远多于批评。
金评《西厢记》诸多惊人之说,如《西厢记》是“文”而不是“戏”、搬演《西厢记》为大过、《西厢记》笔法全同《国风》、《西厢记》只写了三人或一人、《西厢记》其实只是一个“无”字等,亦为现代学界所关注。不过,今人对金评多茫然不解,更有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公然声称金圣叹于戏曲是门外汉。《西厢记》为戏曲之祖,理解《西厢记》即理解中国古代戏曲,金评《西厢记》是研究《西厢记》乃至中国古代戏曲难以回避的问题,破解今人对金评《西厢记》的诸多疑点,或可开掘解读《西厢记》乃至中国古代戏曲的重要路径。
一、 《西厢记》之“事”为国事
《西厢记》为戏曲之祖,当为“戏”无疑。更何况,在金圣叹生活的时代,《西厢记》早已被搬上戏曲舞台。可是,金圣叹却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再强调《西厢记》是“文”不是“戏”,并斥责搬演《西厢记》者为“忤奴”。《西厢记》是“文”不是“戏”,正是金圣叹评《西厢记》最核心的论断,金圣叹对《西厢记》的所有论述皆围绕这一中心论点展开,如其言《西厢记》是“才子书”,是“妙文”不是“淫书”,论《西厢记》“立言之体”“笔法”“写法”“手法”乃至“读法”等,都是在强调其为“文”。金圣叹言《西厢记》不仅不是“戏”,甚至不能当作“剧本”。金圣叹论《西厢记》,根本是在阐明作为“文”的《西厢记》与作为“戏”的《西厢记》意义不同。
金圣叹首先指出,世人说《西厢记》是“淫书”,“只为中间有此一事”。接着,金圣叹即将“事”转向“文”,言:“须看其如许洒洒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束高阁起不复道。”“此一事”是什么事,金圣叹并未明言,而是虚晃一枪,说《西厢记》之事与《国风》相同。
《国风》之事是什么事?《毛诗序》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后妃之德”实与“先王之教”相对,暗示“风天下而正夫妇”为王政教化。“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亦表明,“此一事”为“国事”。由此,“国风”即国家之风俗教化,《毛诗序》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一国之事”表明“此一事”为“国事”,“系一人之本”则暗示“此一人”为帝王,故《毛诗》先言“后妃”再言“先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风天下而正夫妇”“先王以是经夫妇”表明夫妇为上下。夫妇为男女,夫妇为上下即意味男女为上下,“正夫妇”“经夫妇”即“正男女”“正上下”,故金圣叹言《西厢记》写男女为“立言之志”,其本在于《诗经》男为君王、女为后妃。
金圣叹说世人以《西厢记》为“淫书”“只因为中间有此一事”,“此一事”即“男女之事”。金圣叹言《西厢记》之事与《国风》相同,则表明“此一事”为“一国之事”。显然,《西厢记》与《国风》一样,实以“男女之事”言“一国之事”。《西厢记》为“文”,即以“男女之事”为表,以“一国之事”为里;《西厢记》为“戏”,只看到表面的“男女之事”,而没有看到内在的“一国之事”,从而遮蔽了《西厢记》的原义。
因此,金圣叹评语皆是揭示《西厢记》何以以“男女之事”言“一国之事”。《西厢记》开头,张生瞥见莺莺,莺莺翩然而去,“风魔了张解元”。金圣叹评点:“男先乎女,固亦世之恒礼也。人但知此节为行文妙笔,又岂知其为立言大体哉!”此实言“男先乎女”为“立言大体”。金圣叹又言《西厢》为“立言之体”,并言:“才子之停于西厢也,艳停于西厢之西故也……而令万万世人传道无穷。”为何“男先乎女”与“西厢”为“立言之体”?“令万万世人传道无穷”暗示,“男先乎女”与“西厢”皆关于“道”。
何为“道”?中国古代“道”本为帝王之道,然帝王无道自称有道,使“道”有真假之分,天人、内外、圣王、王霸、大小、无为与自然、天理与人欲等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皆言“道”有真假之分,故中国古代学问为“道问学”,亦为“天人之学”。“道”有天人之分,故“难道”,“道”“难道”而以“气”寓,故为“以气寓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即以“阴阳”之“气”寓“天人”之“道”、以“争气”寓“争道”、以“正气”寓“正道”、以“阴阳”变为“阳阴”寓“天道”变为“人道”。“阳阴”即“扶阳抑阴”,寓“尊君抑臣”,“阳阴”之“气”不明言,而以“乾坤”“男女”“东西”等言,《周易系辞》所谓:“乾道为男,坤道为女。”古代文字中的“男女之人”本为“阳阴之气”,寓“乾坤之道”,“乾坤”变“阴阳”为“阳阴”,通过“扶阳抑阴”寓“尊君抑臣”。
金圣叹之所以言《西厢记》“男先乎女”为“立言大体”,即因“男女”为“阳阴”,“男先乎女”即“扶阳抑阴”,寓“尊君抑臣”,故《国风》言“男”为“先王”、“女”为“后妃”,即暗示“男先乎女”为“正夫妇”“正男女”,也就是变“阴阳”为“阳阴”,寓“尊君抑臣”。“西厢”之所以亦为“立言大体”,则以“东西”言“阳阴”,“西”为“阴”,“东”为“阳”,“西厢”为“才子”与“艳”停,实隐言“阴阳”取代“阳阴”、寓“天道”取代“人道”,从而“令万万世人传道无穷”,此“道”即“阴阳”,为“扶阴抑阳”寓“尊臣抑君”“天道”。由此,金圣叹所谓“立言之体”,实言中国古代文字通过“以气寓道”实现“文以载道”。
弄清楚《西厢记》之“事”为“一国之事”,《西厢记》“立言之体”为“以气寓道”因而“文以载道”,即可理解金圣叹说普救寺为武周金轮皇帝所造之大功德林,月下西厢之事为相国为因,老夫人为一品国太君,双文为千金国艳,阿红为上流姿首。“金轮皇帝”“月下西厢”即以“金”“月”“西”言“阴”所寓“天道”,“皇帝”“相国”“一品国太君”“千金国体”“上流姿首”则言其关于国事,从而表明“道”为帝王之道。金圣叹言《西厢》十六篇都写儿女情事,偏觉官样,亦隐言儿女情事为官样文章。故在评张生病重、莺莺写一简为药方时,金圣叹言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大抵十分之七皆儿女之事,其实质是“借家家家中之事,写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秽;意在于文,故吾真曾不见其鄙秽”。《文史通义》亦言《国风》男女之辞,皆属诗人所拟,风、雅“起于宫闱,事关国故,史策载之”;六朝杂拟“情虽托于儿女,义实本于风人”。皆表明男女之情、儿女之事关于国事。
二、 《西厢记》之“人”“物”为王道
金圣叹言《西厢记》只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双文”。金圣叹言“双文”为国艳、天人,张生是相府子弟、孔门子弟,写张生全是写“双文”,将写“双文”而写之不得,因置其不写而先写张生,为烘云托月之秘法;红娘峻拒张生、过尊双文、切责夫人,似周公制礼,也全是写“双文”,并言“锦绣才子必知其故”。金圣叹之所以不称“莺莺”而称“双文”,是因为古代文字以音表义,“莺莺”谐音“阴阴”,文中的“莺莺”并非作为“人”的名字,而是作为“文”的“阴阴”,暗示“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以气寓道”,“双文”则隐言“莺莺”为双“阴”,以双“阴”寓“天道”反复,“莺莺”因此为“文以载道”,故金圣叹言“锦绣才子必知其故”。“锦绣才子”即通过“文”以载“道”之文人。
在金圣叹笔墨下,莺莺为“国艳”“天人”“双文”,“国艳”暗言“一国之事”,“天人”暗示“天人之道”,“双文”则隐言“文以载道”,“莺莺”并非真实之“人”,而是以“女”言“阴气”,寓“天道”。故金圣叹言“莺莺”为“古今以来人人心头之无价宝器”,而郑恒为“人人厌之恶之之一恶物”。金圣叹实以将人物化的方式揭示《西厢记》中人为“道寓于器”。
张生是“相府子弟”“孔门子弟”,实以“相府”“孔门”隐言与“天道”相对之“人道”,也就是帝王无道自称有道,“张君瑞”即帝王无道自称有道以希望自身统治长治久安。故金圣叹评张生出场所唱,言:“看他一部书,无限偷香傍玉,其起手乃作如是笔法。”并言其为“奇文大文”“奇笔”,暗示张生非等闲之辈。《词谑》言《西厢记》为《春秋》,并以“春王正月”释“游艺中原”。“春王正月”即以“春”言“阳气”,寓“人道”,“王”即王权;“月”为阴气,寓“天道”、民权,“正月”即官方话语权“扶阳抑阴”,通过“正气”以“正道”;“春王正月”即王权政治通过改变“气”之顺序改变“道”之法则,变“阴阳”为“阳阴”,通过“扶阳抑阴”寓“尊君抑臣”。“红娘”也完全不是戏曲中活灵活现的人物,而是以“红”言“火”,以“火”隐言暴政,故金圣叹言红娘“贼”“怨毒”“满身烟熏火辣气”。因此,其言红娘“峻拒张生、过尊双文、切责夫人”亦非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而是以“周公制礼”言帝王无道自称有道。
与金圣叹相比,潘廷彰更直白地揭示男女之情为阴阳之体,说《西厢》只有三人,其实只为两人而设,此两人即崔张,崔张之事不过男女之事,崔张之情不过男女之情。“譬如天地之理,不外阴阳,阴阳之体,成于对待。期间或盈或虚,或消或息者,则成于参互错综之用。是故崔张,对待之体也;红娘,参互错综之用也……恶知男女情中,有如许消息盈虚之致,足以成变化而行鬼神哉!”“天地之理,不外阴阳”即“阴阳之气”寓“天人之道”,“理”即“道”。“阴阳之体,成于对待。期间或盈或虚,或消或息者,则成于参互错综之用。是故崔张,对待之体也;红娘,参互错综之用也”则以“成于对待”与“参互错综之用”言“扶阳抑阴”,“阳阴之气”不明言,而以“男女之情”“鬼神之变”隐言,从而暗示“男女”并非真实的人,而是“阳阴”变为“男女”“鬼神”。
“道”以“气”寓,“乾坤之道”即“阴阳之气”转变为“阳阴之气”,“气”不仅以“男女”之“人”言,还以“熊蛇”之“物”言,如金圣叹言《西厢记》写男女为“立言之志”,其本在于《诗经》男为君王、女为后妃,而其最初不过梦中飘然忽然一熊一蛇,从而揭示熊与蛇和张生与莺莺一样,皆为“以气寓道”。因此,金圣叹言《西厢记》只写了三个人时说除双文、张生、红娘外,其他人都是“所忽然应用之家伙”。如红娘为二人之针线关锁,“若夫人、法本、白马等人,则皆偶然借作家伙”。显然,《西厢记》中的“人”皆非真实的人,而是“诸变相”,故金圣叹言:“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炮制时所用之姜、醋、酒、蜜等物。”“题目”“文字”与“文字之起承转合”揭示文字表述之人物并非真实生活中的人,而是文字表述的逻辑关系;“病”“药”与“制药治病”亦言其并非真实的人,而是“病”与“药”的因果关系,此“病”即帝王政治之“病”,为男、阳所寓“人道”,“药”则为治帝王政治之“药”,为女、阴所寓“天道”;“其他人算只是制药使所用之物”更将“人”化为“物”,揭示“人”为虚拟,而非实写。
由此,作为“文”的《西厢记》并非描写人物故事,而是“载道”“传道”。因此,金圣叹言《西厢》,《西厢记》“眼法、手法、笔法、墨法,固不单会写佳人才子也”,也可以写诸葛亮出师、昭君出塞、伯牙入海等,“任凭换却题教他写,他俱会写”。在金圣叹看来,诸葛亮出师、昭君出塞、伯牙入海与《西厢记》异曲同工,皆为虚拟之相。
李渔言:“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古代文字表述之“人”,其实并非真实的人,而是虚拟的“鬼神”,是“神气活现”。故李渔言:“凡阅传奇而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梦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传奇无实,大半寓言,不仅事迹可以幻生,人名亦可以捏造。”“虚则虚到底。”与李渔言传奇“虚则虚到底”相同,徐渭亦称:“大抵本来戏剧,总系情魔,种种色相寓言,亦亡是公、乌有之例,而必援文切理,按疵索瘢,反失之矣。”“色”为“气色”,“色相”亦“以气寓道”。因此,《西厢记》有诸多版本,其中本事与文字多有差异,金圣叹更以改窜《西厢记》原文揭示传奇为虚拟,非实事。
不仅《西厢记》中人为虚拟,是“以气寓道”,《西厢记》中物亦为“以气寓道”。金圣叹言佛殿、僧院、厨房、法堂、钟楼、洞房、宝塔、回廊乃至罗汉、菩萨、圣贤等“都是虚字”,皆为言在此而意在彼。其评“扑剌剌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络丝娘】 碧澄澄苍苔露清,明皎皎花筛月影”,言:“宿鸟、花梢、落红、苍苔、花影无数字,却是妙手空空。”“妙手空空”即非实写,而是虚写。因此,金圣叹说《西厢记》其实只是一个字,这个字就是“无”字。
三、 《西厢记》以“以气寓道”为“立言之体”
金圣叹自言其评《西厢记》乃至“六才子书”,是为了“教天下以立言之体”。何为“立言之体”?《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立言之体”即以外在“声”“文”抒发内在的“心”“志”“情”,所谓“言为心声”“文以载道”。
“道”以“气”寓,“气”诉诸文字即为“器”。古代文字以声明义,“气”为阴阳,“器”则由阴阳之气变幻出世间万象,所谓“气化流行”“气象万千”即由阴阳之气变化出世间诸器。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引朱子言:“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阴阳,气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气”即“器”,“理”即“道”,宋儒“理气说”实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及“一阴一阳谓之道”,揭示“道寓于器”源于“以气寓道”,古代文字通过“器”实现“文以载道”的目的,这就是古代“立言之体”“文体”。中国古代文字为隐微之言,少直白明晰的理论,多隐喻联想式阐释,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即以训诂学为桥梁与纽带,通过训诂阐明古代文字通过“道寓于器”表达“以气寓道”的隐微之义,金圣叹评《西厢记》亦不例外。
金圣叹在重点揭示《西厢记》“人”“事”“物”皆“以气寓道”的基础上,言《西厢记》所有文字皆为“以气寓道”转化为“道寓于器”,所谓“作《西厢记》者,其人真以鸿钧为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万象为墨者也”。“鸿钧为心”即“道心”,“造化为手,阴阳为笔”即以“阴阳五行”之“气”为“立意之本”,“万象为墨”即以“器”为“文”。因此,解读《西厢记》,须将“文”所表述的人、事、物之“器”还原为“气”,再由“气”推原“道”,而不能以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事、物论,故李渔言金圣叹论《西厢记》“无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逆溯其源”即通过“文以载道”溯源至“器以寓道”,再溯源至“以气寓道”,将“文”所表述的“器”还原为“气”,再由“气”推原“道”。“命意”即金圣叹所说的“立言之体”,也就是金评中多次出现的“写法”“笔法”“手法”。
金圣叹常以“古人寄托笔墨之法”“烘云托月之秘法”“鬼斧神工之笔”“奇文”“妙文”“绝妙好辞”“奇笔”“虚笔”“神化”“神理”等言《西厢记》之“写法”“笔法”“手法”,其实皆言《西厢记》以“以气寓道”为“立言之体”,使“道寓于器”,从而实现“文以载道”的目的。金圣叹所有评点都是教人领悟《西厢记》文字如何以“以气寓道”为“立言之体”,也就是“文”为何、如何载“道”,故其言:“古人寄托笔墨之法”为“夫天下后世之读我书者,彼岂不悟此一书中,所撰为古人名色,如君瑞、莺莺、红娘、白马,皆是我一人心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无极,醉梦恐漏,而至是终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之人之事以自传,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乎?”金圣叹明确指出,书中人物并非真实之人,而为“古人名色”,“色”为“气色”,“名”为“名气”,“名色”即以“以气寓道”为基础,滋生诸器之名,使“道寓于器”。金圣叹评《西厢记》文字,即揭示“名色”皆为“气”,为“以气寓道”。如莺莺出场,“宜嗔宜喜春风面”,在今人看来是莺莺的外貌描写,而金圣叹却言:“后之忤奴必谓双文于尔顷已作目挑心招种种丑态。”“春风面”之“春”为“阳”、“春风”为“扶阳抑阴”,寓“尊君抑臣”,但经优人搬演,载“道”之“文”即变为无道之“戏”,“道”之本义被遮蔽,故为“丑态”。又如“临去秋波那一转”,金圣叹言“尽人调戏”为“天仙化人”,从而揭示“临去秋波”与“天仙化人”同义,也就是以“气”之变言“道”之变。金圣叹言千载徒传“临去秋波”,不知已是第二句,即以“第二句”言“变”。金圣叹注言:“妙!眼如转,实未转也。在张生必争云转,在我必为双文争曰不曾转也。忤奴乃欲教双文转。”“秋波”并非眼睛,而是与“春风”相对,“临去秋波那一转”即以“气化流转”寓道之变,张生与双文为男女、阳阴、人道与天道之异,“在张生必争云转”“在我必为双文争曰不曾转”“忤奴乃欲教双文转”即揭示“转”与“不转”意味着“道”不同。周旁、蓝眉皆言:“男窥女则目逆而送,妙在‘送’字。女窥男则临去秋波,妙在乎‘转’。”邓眉云:“一转者,情转也。”“男窥女”与“女窥男”,实为“阳窥阴”与“阴窥阳”,揭示阴阳“争气”寓天人“争道”;“情”即“道”,“情转”即“道变”。再如“宫样眉儿新月偃,侵入鬓云边”,在金圣叹看来并非描写人物外貌,而是以“宫样眉儿”“月偃”“侵入鬓云”隐言阳侵阴、“人道”取代“天道”,因而是“活双文”而不是“死双文”。
同样,今人以为是景色描写,亦皆为“以气寓道”,如“梵王宫殿月轮高”为“真大力也,真大慧也,真大游戏也,真大学问也”。“月”以阴气寓“天道”,“梵王宫”则与“帝王宫”相应,故为“大力”“大慧”“大游戏”“大学问”。金圣叹言:“普天下锦绣才子,二十八宿在其胸中,试掩卷思此七字是何神理!”“二十八宿”实言“阴阳”之“气”,“二十八宿在其胸中”即“以气寓道”,故为“神理”,“神”为“神气”,“理”为“道理”。其后用大段篇幅写月之行,揭示“月”寓“天道”,言张生意欲看莺莺,托之看道场,又托之看月与琉璃瓦。“莺莺”“道场”“月”与“琉璃瓦”皆为“器”,其着眼点在于以文字之“器”载“道”,因此,金圣叹说“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并非写道场,而是“写道场之震动如此”。“道场之震动”即“天道”取代“人道”、造成政治震动,与文中所写“月轮”“瑞烟”“云盖”“海潮”“春雷”“风雨”隐言“阴”所寓“天道”相应,也与后文“只愿红娘休劣,夫人休觉,犬儿休恶,佛啰成就了幽期密约”相应,揭示“张生”“红娘”“夫人”“犬儿”实为偷香窃玉、无道自称有道之“人道”,“莺莺”为“天道”、辅助并救治“人道”。因此,“红娘”让“莺莺”看在自己份上饶过“张生”,金圣叹言其“似玄宗皇帝与太真事”,“玄宗皇帝与太真”隐言君王与后妃、“人道”与“天道”。
不难看出,凡金圣叹赞为“奇文”“妙文”“奇笔”“妙句”“绝妙好辞”“鬼斧神工之笔”处,皆以“以气寓道”为“立言之体”,故为“古人寄托笔墨之法”“烘云托月之秘法”“虚笔”“神化”“神理”。相反,《西厢记》中说得非常直白的文字,则被金圣叹称为“腐句”,如第五卷张生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即直言其为帝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五卷莺莺唱“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别一个怎退干戈”,金圣叹言其为“妙句”“出神入化之文”,只因此处将“张生”称为“张解元”,又以“别一个”隐言“别一个帝王”。因此,金圣叹亦以隐言隐,不直言“帝王”而言“宰相”,言“便以吾张解元为宰相不愧耳”。
四、 中国古代文字皆以“以气寓道”为“立言之体”
今人看金批《西厢记》,认为其中观点多是金圣叹“一家之言”,实际上,金圣叹在批评中处处揭示传统、强调普适性,如“立言之体”强调其为体统,“笔法”“写法”“手法”“读法”“古人寄托笔墨之法”暗言其为普遍遵循的法则,“普天下锦绣才子”“万万世人”“天下万世人”则强调普适性,“立言之体”“文章之事”“古今来绝大文章”“自古至今无限妙文”“世间妙文”更是针对所有文字而言。因此,金圣叹评《西厢记》,实揭示中国古代文字皆为“文以载道”且如何、为何“载”“道”,从而引领读者发现“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文以载道”的内在逻辑。从这一角度看,金圣叹论《西厢记》对解读中国古代文字书写传统意义深远。
金圣叹言《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即言古代戏曲小说(《西厢记》《水浒传》)与诗词歌赋(《杜诗》《离骚》)、经传子史(《诗经》《左传》《庄子》《史记》)一脉相承,皆为古代文人“载”“道”之“文”。故李渔言:“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小说戏曲与诗词歌赋、经传子史皆为“古今来绝大文章”,为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之一脉,因此,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写法时常常说到“锦绣才子必知其故”,实即揭示古代文字书写传统皆以“以气寓道”为一以贯之的“立言之法”,以实现“文以载道”的目的。
在评点《西厢记》写法时,金圣叹不仅常以“锦绣才子”暗示古代文人一以贯之之笔法,更常常有意论及中国古代文字传统,如其言“谛信自古至今无限妙文,必无一字是实写”。金圣叹不仅言《西厢记》为“妙文”“奇书”,亦提醒天下人不要轻视古人之书,表明其所评并非《西厢记》,而是古代所有文字与书籍。金圣叹更以“圣叹外书”揭示整个古代书写传统为“文章之事,通于造化”,也就是以“以气寓道”为基础滋生的“道寓于器”。
实际上,金圣叹之说并非空谷足音,章学诚即言六经为载道之书,六经亦皆器。“六经皆器”“六经载道”即表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文以载道”的具体化,“文”为“虚器”,“道”为“实指”,故须“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也就是由形而下之器追溯形而上之道,“逆溯其源”。
“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以气寓道”的隐微表述,中国古代文字以“以气寓道”为“立意之体”,使“道寓于器”,“文”得以“载道”,故中国古代文字皆有表里之义,“经传制事,皆有微显、表里二意”。表为“文”(言、声、音、诗)为显,“里”为“道”(理、情、志、心)为微,解读古代文字,需由表及里,通过“文”之“器”逆溯“气”,再由“气”抵达“道”。因此,李渔感慨:“甚矣,此道之难言也。”
由于“道”难言、“阴阳五行”“以气寓道”不能明言,“道”与“器”亦难解,《文史通义》即以“道寓于器”“即器存道”“即器而示之以道”言古之学,以“溺于器而不知道”“舍器而言道”“离器言道”言后儒之学,揭示由于帝王无道自称有道“离经叛道”,使古代文字意义发生改变,“道”与“器”分离,进而导致“道”与“文”分离。因此,今人看古代文字,只看到“器”而看不到“道”,从而导致对古代文字的误读。这一误读因“文”变为“戏”而更加严重,当载“道”之“文”通过搬演变为“戏”,作为“虚器”的“文”就变成真实的人、事、物,“文”所载之“道”即与“器”分离,本为“妙文”之《西厢记》即变为“淫书”乃至“淫戏”。
五、 通过《西厢记》理解中国古代“文以载道”传统
古代文字虽以“文以载道”为传统,但不同的文人所载之“道”亦有所不同。《文史通义》即明确指出:“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因此,《西厢记》自产生以来即多次被篡改。《曲律》言:“《西厢》《琵琶》二记,一为优人、俗子妄加窜易,又一为村学究谬施句解,遂成千古烦冤。”李渔则认为有“完全不破之《西厢》”与“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
《西厢记》屡经改编,其“善”与否,并非因于文之工否,而是“道”之不同导致“文”之不同。《剧说》言“所谓《南西厢》,今梨园演唱者是也”,即因梨园为官方掌控,《南西厢》所表达的是将“北”“阴”所寓“尊臣抑君”改为“南”“阳”所寓“尊君抑臣”,故《剧说》引《南音三籁》言“陆天池作《南西厢》,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志可谓悍矣”。《南西厢》之“悍志”,即为官方意识形态。李渔痛诋力斥《南西厢》,言其玷污《西厢》名目、坏词场矩度、误天下后世苍生,是因为“放郑声者非仇郑声,存雅乐也;辟异端者非仇异端,存正道也”,从而暗示《南西厢》与《北西厢》之异在道之异,故其言阅《西厢》南本,“未有不废卷掩鼻而怪秽气熏人者也”。“气”以寓“道”,《南西厢》之“秽气”即为“南”所对应之“火”,寓霸道,李渔力斥《南西厢》,即“存正道”。
对《西厢记》改编之“续”“竟”“翻”“后”等具有明显指向性与针对性的动词表明,《西厢记》是“天道”与“人道”“争道”的重要场域,解释与改编《西厢记》是古代文人表达自身政治立场、进行权力斗争的方式,对《西厢记》进行改编、解释、搬演并非纯粹的学术行为,而是政治行为。由于《西厢记》一再被改编,成为权力斗争的场域,更由“文”变为“戏”,由虚拟的人、事、物变为真实的人、事、物,对《西厢记》本义的理解就变得更艰难。
今古悬绝,在古代文人笔下,《西厢记》以深奥难解著称。《南村辍耕录》言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曲律》言《西厢记》“千古绝技,微词奥旨,未易窥测”。李渔言金圣叹评《西厢记》为“穷幽极微”。《西厢记》之所以难解,即因其为“文以载道”,为微言大义。时至今日,不仅“文”与“道”、“道”与“器”分离,“气”与“道”以及“以气寓道”成为秘密,古代“文以载道”传统也已被现代知识体系与现代话语意义改变,古代学者通过训诂学解释经典“逆溯”文字之源也多被现代训诂学取而代之,遂使金圣叹之论茫然不解。
实际上,说《西厢记》是“文”而不是“戏”并不始于金圣叹。胡应麟即言《西厢记》“字字本色,言言古意,当是古今传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献尽此矣。然其曲乃优人弦索弹唱者,非搬演杂剧也”。在今人看来,“优人弦索弹唱”与“搬演杂剧”似乎并无二致,然此处却处处强调其为“字”为“言”为“文”的“本色”与“古意”,可见其为“曲”亦强调“文”之本义,而为“戏”即“扮演杂剧”,却改变了“文”之本义。
致和堂本《六幻西厢记》有意将《西厢记》定为“戏”,实际上却以“六幻”明确《西厢记》为“幻”。“会真六幻”开首言:“云何是一切世出世法?曰真曰幻。云何是一切非法非非法?曰即真即幻,非真非幻。元才子记得千真万真,可可会在幻境。董、王、关、李、陆穷描极写,撷翻簸弄,洵幻矣,那知个中倒有真在耶。”“穷描极写”亦表明《西厢记》为“文”而非“戏”。
《红楼梦》亦暗示《西厢记》是“文”而不是“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黛玉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想到“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表明《西厢记》是“文”而不是“戏”,戏中情景并非文中意义。
李渔更是金圣叹的知音,言金圣叹所评《西厢记》“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然而,与金圣叹言《西厢记》不可搬演相反,李渔与《六幻西厢记》校者“三山謏客闵寓五”则强调《西厢记》不仅可为戏,亦可由“戏”探究其为“文”之本义。李渔表示:“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文”可变为“戏”,“戏”亦可逆溯“文”,金圣叹只看到了“戏”对“文”的改变与遮蔽,却没有看到“戏”亦可逆溯“文”,进而通过“文以载道”发现“戏以传道”。《六幻西厢记》“会真六幻”即说到昔日有老禅笃爱斯剧,有人问佳境安在,老禅说是“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作者因此说“此老可谓善入戏场者矣。第犹是句中玄,尚隔玄中玄也”。显然,由“文”变为“戏”,使“戏”成为“玄中玄”,故作者表示:“会得此意,逢场作戏可也,袖手旁观可也,黄童白叟朝夕把玩都无不可也。不然,莺莺老去矣,诗人安在哉?”戏中的莺莺,传达的却是“诗人”之意,是《西厢记》为“文”所载之“道”,故“六幻西厢记”第一幻为“幻因元才子会真记”,下注“诗赋说梦”,直言其为“诗赋”而非“戏剧”,说的是梦之幻境而非真人真事,“会真”即由幻境而表达真义,此为所有《西厢记》之源头;其后诸“幻”则揭示《西厢记》诸本皆以“幻”为根本,从而使《西厢记》本事、结构、作者等诸多聚讼涣然而解。
金圣叹乐观地相信,《西厢记》乃至中国古代之书在后世必有可知之日。李渔亦相信“焉知数百年后,不复有金圣叹其人哉”!金圣叹与李渔等古代学者试图通过文字跨越历史的时空,与后人对话。从这一角度看,今日解读《西厢记》乃至中国古代戏曲与文字传统,是我们对古人不得不做出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