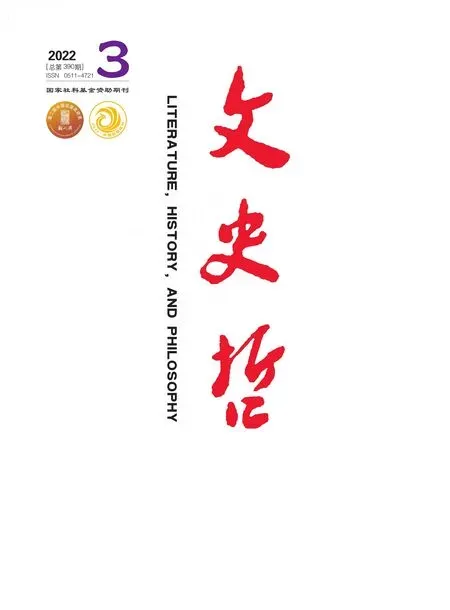惠特曼的城市想象与生态整体观
——兼议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的契合
马 特
1856年,梭罗在布朗逊·奥尔科特的带领下拜访了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惠特曼。在这次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面中,梭罗提到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与“东方主义思想非常契合”。当他询问惠特曼是否阅读过东方主义著作时,后者却回应称自己并未接触过,并请梭罗予以讲解。尽管后世对惠特曼回答的真实性众说纷纭,但他作品中的东方色彩是不可否认的。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没有一位美国作家像惠特曼一样领悟到了东方主义的精神内涵。”目前,学界在印度教教义、印度早期吠陀文明、古波斯诗歌、苏菲主义、佛教经典、古埃及神秘主义等诸多方面论述了惠特曼的创作及其理念与东方主义思想的平行关系和关联性质。与之相比,对惠特曼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关系的研究在深度及广度上都显得欠缺,其研究关注点不仅主要局限在惠特曼作品中神秘主义、泛神论和决定论等思想与古典道家哲学的对比研究,在文本上也主要集中于对《我自己的歌》一诗的探讨。或者说,正是研究文本的单一性导致了目前这类研究在论点上的局限性,有时甚至会导致一些误读。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惠特曼的作品体现了与老庄哲学一脉相承的“自然神秘主义”思想,是一种置于城市框架内凸显荒谬的思想,进而推论惠特曼崇尚自然状态,注重自然与非自然的二元划分,反对一切形式的“人造物”,将之看作是现代文明对人的禁锢;还有学者认为惠特曼与老子具有类似禀性,推论称惠特曼具有古典道家的“出世”思想,认为现代建筑物是对个人自由的束缚,并且将世界划分为“阴”与“阳”的二元对立等。这些看法不仅将惠特曼的思想与老庄哲学简单对等、全盘照搬,而且忽视了惠特曼作为“美国第一城市诗人”在其作品中展现出的对现代都市文明的积极接纳。惠特曼创作视野广阔,作品内容包罗万象,他称自己“既是歌颂城市的诗人,也是赞美自然的诗人”。惠特曼并未追随美国19世纪时期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反城市思潮,而是在看似繁复的城市文本中演绎出清晰而独特的城市生态思想。目前学界对惠特曼思想中生态意识的研究多局限于对其自然书写的研究,将其生态意识归类于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歌颂自然美景、向往田园牧歌的传统,对惠特曼城市书写中体现的生态意识以及隐藏在城市文本深层的生态思想却鲜有涉及。实际上,惠特曼城市生态思想不仅对应当代环境研究的“城市转向”,填补了城市生态研究的文学文本空缺,也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古典道家思想不仅为我们解读惠特曼的城市生态思想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生态批评第三次浪潮后,学界不同批评流派之间的争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庄子“三籁”与城市生态复调
在美国19世纪作家的城市书写传统中,城市是与自然相对的存在,具有神秘、黑暗、压抑、冷漠、异化与孤立等反生态特征。城市是爱伦·坡笔下“无法解读”的迷宫深渊,是霍桑描绘的由“原子化的城市居民”构成的非人世界,是梅尔维尔叙述中横亘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异化障碍。在超验主义作家如梭罗和爱默生的城市书写中,城市更是被比喻为“巨大的阴谋”“废墟”和“坟墓”。与这些非生态的城市意象相对,惠特曼的创作虽然也受到了超验主义思想影响,其城市文本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生态视域。惠特曼的城市想象解构了城市作为“自然对立面”的扁平化形象,指出城市文本并非以人类为中心而展开,不是以人类声音作为单一主调(homophony)而构成的平面图景,而是由多种不同的独立声音交织相连而构成的更复杂的生态复调(polyphony),从而将城市中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由线性的转化为立体的,由孤立的转化为整体的。
“主调”与“复调”相对,指的是多声部音乐中存在的两种主要织体形式。主调音乐强调多声部内的一个主要旋律,并以之作为主导韵律,其他声部则作为和声起到陪衬与烘托的效果;而复调音乐则同时调动两条或以上的独立旋律线,这些旋律同时演奏,按照对位法的规则结合,彼此不分主次,通过形成对比或者相互补充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乐章。1929年,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首次将“复调”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引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中,并指出复调理论的基础是“声音多重性”,是“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而“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庄子在《齐物论》中论述“三籁”时,曾以自然界中的穴窍之声为例,形象地阐释了这种在对立中保持协调、在多样中蕴含和谐的“复调”现象: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
自然界中万物各有不同,穴窍因形态差异而在有风吹过时发出不同的声音,譬如水流声、射箭声、斥骂声、吸气声、喊叫声等。众窍之声先唱后和,小风则小和,大风则大和,至无风则万物归于静籁。在整个过程中,无论是万声齐发还是一片静寂,都保持着整体性与和谐性。这段文字不仅勾勒了一幕和谐的众声交响曲,也代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艺术境界。如果我们将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与惠特曼的城市文本相结合,将庄子所言的“众窍之声”延伸至城市中的各色存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惠特曼在他的城市书写中叙述了多组交错相叠、彼此独立的声音:他打破“自然的沉默”,与自然环境中的绿色声音“交谈”,指出看似无言的自然实际上是“雄辩的”;他所建构的城市空间还包括了以高楼、工厂、烟囱等为代表的来自人造世界的声音,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个体的声音等。这些来自不同空间维度的声音在城市空间中同时共存,相互影响,是一种符合生态和谐整体原则的城市生态复调。
这种城市生态复调在惠特曼的作品中有许多文本例证,如诗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我自己的歌》《曼纳哈塔》《想一想时间》等。其中,在散文《民主展望》中,惠特曼这样记录了1870年秋季的纽约和布鲁克林:
大都市繁华而美丽,拥有大海般的广博和汹涌的动感。这里有前所未有的情景:河流与海湾,闪耀的海浪,昂贵的新建筑及其大理石与钢铁构成的外观拥有原本的光泽与优雅的设计……那些无数的船舶,人潮涌动的街道……还有批发市场,高级商店,船坞,纽约中央公园以及布鲁克林公园的群山……聚集成群的城市居民,他们之间的交谈、贸易以及晚间的娱乐活动……——可以说,像这样的各种存在让我深深感受到力量、丰富与动感。
在这幅万花筒式的城市图景中,惠特曼将自然存在(河流、港湾、山峦等)、人造产物(高楼、店铺、街道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人群、对话、贸易、娱乐等)杂糅在一起,展现出这三类存在之间紧密的关联:海洋催生了码头,码头带来了船舶和人群,人群建造了街道和商店,而熙攘的人群与建筑的设计又回应了涌动的潮水和广博的大海。在这个复杂的城市空间内,人类不是独霸言说权的主导式存在,而是与各种去符号化的声音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在动态中保持平衡,形成一个“有机的过程”。这样的城市图景不是线性思维下由单一的主调旋律(人类)构成的平面文本,而是保持城市内各种存在的多样性与关联性,在现代化视域内建构的立体而动态的城市文本,是一种生态意义上的多维的城市复调。在这种生态复调中,“每种生物都自己定义自我,并通过与其他事物的相互作用而在心理、精神或客观层面上达到了真正的‘自我’”。后现代城市生态学研究指出,现代城市研究常常将人类简单地抽象为生态环境的消耗者,“遗忘”了人类、动植物以及大地等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范畴,城市是人类与其他动植物共同栖居、互相影响的生物群落或生物共同体(biotic community)。惠特曼的城市想象中富含这种生物共同体意识,其中的各种生态元素彼此交织,相克相生,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城市生态网络。
在《齐物论》中,庄子借南郭子綦与子游的对话,将世间的声音分为三类:人呼出的气体经由乐器发出的箫管声为“人籁”,长风吹动山林地洞所造成的“万窍怒呺”为“地籁”,悟道之人方能听到的自然状态下的无声之声则为“天籁”: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庄子提出三籁之声并非为强调三者之间的不同,而是为了引出子綦“怒者其谁”的提问。怒者,发动者、产生者也。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中注解曰:“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也就是说,“道”是天地万物自然运行的准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准则既是可以言说的,又是玄妙幽深的,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怒者”作为三籁之声的源动力,必然也依“道”而行。庄子在《齐物论》中并未直接说明“怒者”究竟为何,后世也对此有多种观点。笔者综合各种观点认为,“怒者”如“道”一样,本质是玄妙幽深的,在现实中则化为不同的具体表征。在“人籁”中,怒者是人类腔体呼出的气体;在“地籁”中,怒者又是大地酝酿而生的“大块噫气”,在“天籁”中,怒者存在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怒者既能让“万窍怒号”,也可使“万籁俱寂”,是各种“声音”的发起者和调节者。
在惠特曼的城市生态复调中,也存在这样的“怒者”——它既激起不同维度的各种“声音”,又将所有声音统一于一个具体空间内,这个怒者就是城市。惠特曼笔下的城市不仅仅是容纳各种复调声音的物理容器,还是整个生态复调运作的动态过程中的枢纽与媒介。城市生态学研究指出,城市化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传统生态系统格局,城市的空间扩张或内部变化都会造成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的诞生或终结。生态位指有机体在生态群落中占据的时空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之间的功能关系,生态位的变化意味着生态系统中某些生物群(biota)在数量和分布等方面的动态变化。成熟的城市环境不是由单一种群构成的生态范畴,而是一种不断变动的“生态马赛克”(ecological mosaic),甚至拥有比乡村或荒野更加多样的植被、动物栖息地与生态循环。其中,城市公园或家庭花园就是这种马赛克式的生态镶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惠特曼笔下的城市生态复调中,公园也是城市发挥枢纽作用的主要媒介之一。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曾认为,惠特曼并不像纽约中央公园的主要设计者奥姆斯特德那样重视作为公共绿色空间的城市公园,“比起在林中散步,他(惠特曼)更重视(建造价格合理的)浴室”。但是,经过对惠特曼城市文本的细读我们会发现,其中不仅经常出现华盛顿公园、布鲁克林公园等城市公园的身影,惠特曼还提到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去中央公园散步、兜风或静坐”,欣赏公园的“美丽与纯净”,认为在公园散步或与他人交谈是人类活力的重要来源。如果说公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与生态环境中其他种群接触的一种稳定途径的话,那么城市现代交通网络则是惠特曼生态叙述中的另一种动态平台——包括渡船、铁路与公路。无论是青年时期的纽约富尔顿渡口,还是老年时期的新泽西坎姆顿渡口,都是惠特曼“与河水、空气以及星空中的明暗交谈互动”的媒介;他认为,哈德逊河沿岸的铁路是与自然的完美契合,拥有“由自然构成的路基”,在惠特曼晚年行动不便时,铁路也成为增加其个人移动性、“在户外生活”的主要方式。这样,静态的公园与动态的交通作为惠特曼城市调节生态复调运作的具体媒介,构成了复杂而完整的生态联系网,为生态环境中不同生物群之间的接触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道通为一:从椭圆到同心圆
相比于城市规划、城市生态学与城市史研究等学科对城市空间中“自然叙述”(natural story)的认可与重视,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哲学研究更关注以“荒野”为代表的原始状态的自然环境,在理论建构与文本解读中,城市长期处于“缺席”或“盲点”状态。城市环境作为承载人类文化的实体,被看作是与自然环境相对立的人造空间,是“‘商业环境’或‘政治环境’,而非城市生态系统”。环境伦理学代表人物罗尔斯顿甚至直言,自己不太清楚“城市生态系统”为何意。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与城市的二元划分,倡导一种“椭圆”的世界布局:在平面几何学中,圆形只具有一个圆心,椭圆则有两个圆心/焦点;映射在环境伦理学传统视域内,前者代表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后者则以自然/人文为双圆心,构成二重视野。然而,这种双圆心的二元划分范式虽然具有分析的明晰性,却也容易陷入简单化的线性思维。椭圆范式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个圆心之间的比较与平衡问题,甚至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会有偏重某一圆心,或催生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倾向或嫌疑。
与双圆心的椭圆范式相比,惠特曼解构了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二元划分,转“一分为二”为“合二为一”,使椭圆范式中的双圆心彼此重合,建构出一种杂糅了自然环境与人造空间的同心圆结构的世界,契合了中国古典道家哲学的深刻智慧。“一分为二”的椭圆范式强调个体的殊异性,是一种“以物观之”的世界观。庄子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事物的称谓是由人确定的,不同存在之间的界限也是由人划定的。由于世间的存在物在时间与空间范畴内是无限的,而个体的认知是有限的,这便决定了二元划分认知中的分裂世界是非真实的,并且会因个体的不同立场或标准而产生不同的评价与判定。与之相比,惠特曼生态视域中“合二为一”的同心圆结构超越了事物外在形态的差异性,注重基于世界本原的整体性与共通性,是一种“以道观之”的世界观。《老子》第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不仅是万物运行的玄妙准则,也是世间所有存在物的共同本原,是“所有事物共有的共相”。通过设想“道”,古典道家哲学思想深入世界的本然状态,揭示出繁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内在统一性。可以说,“合二为一”的“一”是对“一分为二”的“一”的升华与整合,是解构了二元对立的真正同一的“一”,也是庄子所言的“道通为一”的“一”。
《庄子·齐物论》曰:“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憰诡怪,道通为一。”郭象注曰:“则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也。”从道的层面看,世间万物只是存在形态殊异,内在本质是共通统一的。在《庄子·齐物论》中,变化万千的“人籁”与“地籁”之声其实始于同一源头,即人类呼出或大地形成的“气”。“气”经过与“比竹”或“众窍”的接触后,转化为表象多样的竹箫声或呼啸声等。也就是说,在形态万千的经验世界中,看似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具体存在物只是在现象层面存在差异,其本质源于同一。在惠特曼的城市生态复调中,“气”在“怒者”即城市的调节下,经由不同媒介的具化,体现为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中的各类存在,投射为无数个不同直径/表征的同心圆结构。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惠特曼所建构的就是这样一种大圆套小圆的多圈层的世界形态。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单纯、紧凑、衔接得很好的结构”,包括“最细微的事物”在内的世间万物都如“珠子”一样串在一起,展现出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重要的普遍联系性特征。
在美国19世纪城市中,河流、潮水、天空等自然景观与繁华城市存在图景之间的联系常被忽略。惠特曼打破“人造城市与乡野田园之间的浪漫主义划分”,将人造/棕色空间(brown spaces)与自然/绿色空间(green spaces)连为一体。在惠特曼复刻的19世纪纽约城景中,他以并置的手法展示了自然景物与人类产物共同构成的一种混杂的和谐:“放眼望去,树木的绿色与建筑物的白、棕、灰三色很好地混合在一起,在奇迹般清澈的天空下,上有苍穹之光,下有六月迷雾。”绿色与白棕灰三色的混合既象征了自然空间与人造环境之间隔阂的瓦解,也是对自然环境与人造空间二元对立的解构。此外,惠特曼经常在并置两类空间的同时在其间自由切换。在《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一诗中,描绘夏日长空、流水与微风的诗行之后常常紧接着对铸造厂、烟囱与仓库的叙述。这种频繁的空间切换,拉近了两类空间的距离,使二者交织成章,不分彼此。
惠特曼对自然环境与人造空间二元划分的解构不止局限于艺术技巧和行文安排,他更注重对两类空间固有属性的探讨和比较,着力展现二者的共通性与融合性。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庄子也有“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和“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之语。换言之,万物之间并无彼此是非之分,价值是相对的,属性也是相对的。美与恶、善与不善、是与非、彼与此、可与不可、然与不然、分与成、成与毁等看似相异对立的概念,实际上也有深层的共同之处和相互转变的可能。因此,所谓的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在本质上只是人为建构的二元对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正如有学者指出,惠特曼的城市书写是将城市“自然化”并转化为“自然的延续体”的过程。他将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如“镜像般连结起来”,展现出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似性与对偶性。与其说惠特曼作品中建构的是一个“半城市半田园的世界”,不如说更多的是一个有意不区分人造空间与自然环境的杂糅的世界。在散文《民主展望》中,惠特曼在称赞“熙攘的人群”和自然一样伟大之后,紧接着补充说自己并非要将两者予以区分比较,表示自己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偏见主义”。正如米勒所指出的,“惠特曼展现出(二者的)不同只是为了对其(不同)进行消解”。惠特曼认为,自然环境和人造空间中的各类存在都是“为灵魂作出了贡献”的“沉默的、美丽的使者”,自然界的丰收和城市街道中无尽的人群带给他同样的“持续欣喜感与纯粹满足感”,因为二者都是“多种多样的”。他不愿意区分城市空间的动态丰富性与自然环境的丰盛性,比起从中作出选择,他更强调对二者相通之处的融合与统一。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指出,“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区分为两种环境是错误的……只有一个世界”。惠特曼笔下的生态环境超越了孰优孰劣的机械划界,透过多样性与相对性揭示出宇宙的共通性,使分化的世界成为“一个世界”,实现了从椭圆范式至同心圆结构的转变。
惠特曼的城市生态书写建构了一个由各种元素彼此交织构成的多圈层的城市生态系统。这个城市生态系统以生态复调为核心,主张调节人类能动性与自然环境演变之间的平衡,拒绝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蕴含了深刻的生态整体思想。惠特曼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和谐感的推崇与古典道家重视系统性、强调圆满的传统是一致的。老子曰:“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也就是说,人们应当从变化出发,进而着眼于整体的稳定和完善。对立的元素在相生相克中虽有损益,但不会导致总体的破坏或失衡。古典道家思想强调注重对立面之间相承相应、相比相得、相和相通、相济相成的互补关系,而不主张对立面的排斥与斗争或二者之间的妥协,原因在于,事物只有在往来屈伸的运动中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张岱年先生提出,在道家思想中,“道”是统领一切规律的“普遍的规律”。他解释说:“凡物有所动,皆系遵循一规律而不得不动;凡物之生,亦系遵循一规律而不得不生。然各物的规律并不是相离立而不相干的。此等规律实有其统一,为更根本的规律所统一。或者说,一切规律都根据于一个大规律。”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通过减少自然中多余部分补给自然中不足部分,使阴阳两极相济为用,相辅相成,以此调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整体性。惠特曼笔下的城市生态系统的各个圈层便是在这种同一、互补、竞争、对抗的关系中演变与生存的。
三、结语:古典道家的生态智慧
在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后,学界在人类与自然、城市与荒野等议题上也开始出现新的声音。生态学第一定律指出,万物是相互联系的,而城市生态系统与非城市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可以说,忽视城市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就是在研究一个残缺而不完整的生态网络。在此背景下,“环境”一词的内涵也被重新定义,以荒野为代表的“纯粹的”自然环境不再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环境类型,城市环境等人文景观的价值也逐步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大地伦理”不再被视作是仅限于“荒野”区域的概念,而是也同样“适用于人口密集的城市空间”。可以说,在文学批评的想象视域内,人造空间与自然空间共同构成了城市生态环境。生态系统如重力一般广泛地存在,超越了城市与荒野之间的界限,促使人们开始聆听“隐藏在街道下的土地的歌声”。惠特曼在城市书写中所记录的城市生态复调便是对这些隐匿于城市街道之下的土地的歌声的忠实复刻。
生态批评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其内在的精神实质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美国人文物理学家卡普拉指出,“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慧”。惠特曼虽然与中国古典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时空远隔,但他的城市生态思想与古典道家思想在结构与内容上都有所契合。揭示这一点不仅为惠特曼的城市书写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城市生态学研究增补了文学文本论据。诚然,受当时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惠特曼的城市生态思想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亦有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在于,惠特曼的生态思想以城市生态系统为出发点,他对自然环境的歌颂与热爱并未导致对城市空间的抵触,在不损害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前提下,他对人类能动性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古典道家思想则更推崇“为而不恃”“为而不争”的“无为”思想,这是一种希冀在社会纷争中保持素朴自由的政治愿景。如果纵向而立体地看待人类精神世界的演化历程,惠特曼独具特色的城市生态思想也可以看作是对古典道家思想的螺旋式发展与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