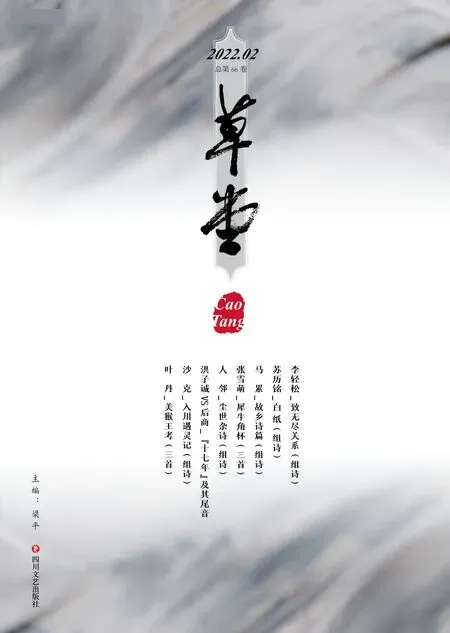万物与以前一样
◎ 李轻松
我想从卡佛说起,因为我先是喜欢他的小说。当时是一位女作家向我推荐他的,当然是他的小说。当我开始读他的作品时才惊讶地发现,他还写诗、写散文。我很兴奋,我喜欢一个作家不同的样式,我相信它们是互相映照的。当人们大谈他的小说时,我反而静下心来读他的诗,这个诗人的身份,卡佛本人也是在意的,强调的。这个生前的失业者、酒鬼、妻离子散者、英年早逝者,死后在墓上把诗人刻在了第一位,然后才是短篇小说家、散文家,说明卡佛很钟爱他的诗。卡佛的诗与他的小说一样,都带有一种灰暗,但我把它看成是他独有的色彩,你不能说灰色就不是颜色吧!他在小说中奉行的是“极简主义”,我的理解就是大片的留白,尽可能地省略形容词,甚至是介词。这种克制尤其对我有用,使我对自己的铺张浪费感到羞愧。正因为他的简约,我在他的诗中也看到了一种空旷感。他最高超的手法是,他从不写满,所以他预留的空间极大。我最会意的地方是,他发现了这个世界的隐秘部分,“隐秘的心”“万物与以前一样”,他细微的观察和撕裂现实的冷酷感,呈现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张力。他的克制与深邃常把我带入广阔的遐想,当然还有他适度的抒情,几乎就是一个样本,使情感在诗歌中的运用变得如此美妙。
由此,我需要改变一下我的写作习惯,我尝试最大限度地克制我的泛滥。多年来,我写得太满、太溢,没有留白,不懂极简,恣意汪洋几乎成为我的惯性。但从哪里开始呢?其实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命运。
2021年,疫情继续,每天诸事缠身,尤其是近九十岁母亲,不能去另一座城市去看她,只能每天通话。话题除了病毒、传染、消毒,便是她的兄弟姐妹,为芝麻粒大的事情伤心难过,一粒尘埃都会把她压垮,然后便是听力下降,有时我大声喊话,可她依然是自说自话,无法再形成交流。我不得不想,母亲离开家乡也已二十年,但她的魂依然还生活在那里,她对城市没有一点概念,故乡山水人情便是她的全部。但也因此,我沿着母系的河流,可以真实地触摸到血脉的延续,它是那样的有力,无法中断。
我离开家乡正好四十年,有一天梦见小时候生活的街道、房屋、左邻右舍,哪里都不再认识,四面竖起一道黑幕,把我紧紧地包围在其中,让我无法突围,我急得大哭起来……醒来时已是大汗淋漓。那些与我相关的街与道、山与水、亲戚同学,众多我熟悉的面孔全都鲜活起来。这一年,我写了一部反映农村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长篇小说,让我将那些交织在一起的关系又重新梳理起来。
虽然1990年我的家彻底搬离故乡,但我每年都要回乡探望,从未间断过。那些我熟悉的亲人们,有时变得十分陌生,有时又能从他们的相貌与声音中找到血缘的联系。这秘而不宣的感觉是那么神秘莫测,似乎与我疏离已久,却又不可分割。这不仅是街与道的改变、山与河的退场、老人故去与新人出生,还有一些固有的观念更新、一些风俗消失、一些时光流逝……
我曾刻意回避的部分也会进入我的梦境,或不自主地来到我的文字里。因为,我依然与她血脉相连。我九十岁的奶奶和近一百岁的姥姥埋在那里,现在还住着我的两个舅舅及脑血栓后遗症的堂兄。而我对它的书写,剪不断理还乱,总是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其中,无力自拔……
我想,这种关系实在是太强大了!仿佛我的伯父姑妈、舅舅姨母,还有他们的下一代,都是难以割裂的所在;那些山川河流、一草一木、家禽野兽,我与它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些时光过往、乡亲故旧、乡路老屋,也一直在我的梦里存活着。四十年来,我似乎一直想要摆脱那种亲情的困扰,但我发现这是生命的根须,已深深地扎进命运,那隐藏在深处的爱与痛、得与失、悲与欢时刻牵扯着我、触动着我,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真正触摸到心跳。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在大地上的挣扎、挫折、失败与屈辱,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动人的梦想与英雄传奇。这些错落纷繁的关系无穷无尽,是写不尽的资源。有时以为它们都已退场,但各种的交织令人困惑与欲罢不能。有时,我被网罗其中,挣不脱逃不掉,被折磨又被滋养。
在这样的书写过程中,诗意伴随着小说应运而生。 我一直尝试以不同的形式来写作,比如,同一块布料,我希望做成裙子再做成衣衫,同一个题材,我愿意写成戏剧、小说和诗歌,我在这种穿梭变换中感受到无限的乐趣。诗写到现在,似乎享尽了那词语的繁华,但繁花的中央必是凋零。我曾经执迷于在空中飞翔,现在我更喜欢踏踏实实地落在地上。包括去掉一些形容词,更包括更简洁一些。当然,小说让我学会了叙事,当它重新回到我的诗歌中时,正好中和掉我的泛抒情,让我在虚与实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我愿意继续尝试下去,我愿意,在无尽的关系中,找到极简、朴素的那一种。我认命,被束缚、被围困,甚至被伤害,但也被滋养、被感动,甚至被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