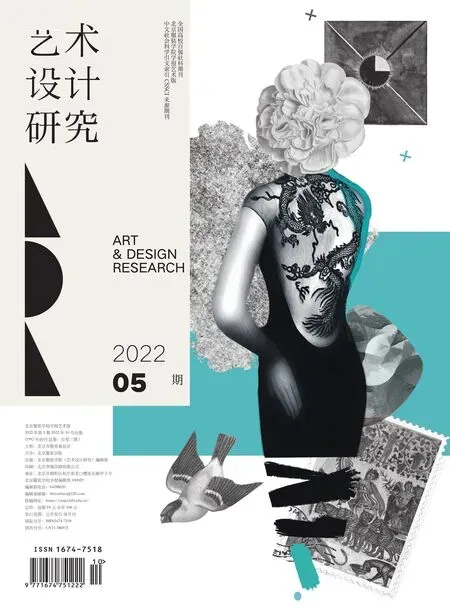“深衣”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陈 晨
一、中日往来交流中“深衣”的东渐
虽然至迟在东汉后期中国与日本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贸易与文化往来,但关于“深衣”东渐的具体记载,却是在唐宋以后随着儒学的东传才逐渐出现。中国儒学东渡日本兴起于隋唐,流行于宋元,盛行于明清。明清时期,中日两国学者接触频繁,大批汉文书籍东传,儒学各派学说流传并深入到日本社会,对于日本思想界乃至整个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①但日本不同于朝鲜,尽管儒学对其知识精英及官员影响很大,但这都根植于日本人对于中国儒学的吸收和改造,显现出其独到的本土文化特色。
资料显示,“深衣”在日本的传播,在宋元明时期几乎很少涉及,从明末开始逐渐出现在儒学圈,一直发展至清代。“深衣”这一名词不仅局限于儒家学术群体,还出现于漂流民这种商人群体的交谈中。《巡海录》记载了一则江户时代(清代)日本儒士和清国漂流民关于“深衣”的交谈:
余携深衣幅巾及东坡巾,示曰:此是深衣,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㴀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儒者有异同之论,贵朝必有此物,今日赞之诸子。高程董仔细看过曰: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已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藏留,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历朝服式耳。其东坡巾亦有正是。②
由此可见,在江户时代“深衣”不仅活跃于日本儒学圈,并且还被儒士知识阶层以外的人群所议论。这一现象说明“深衣”在日本的穿着使用虽然没有涉及社会大众,但它在江户时代被认知的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儒者,而是逐渐扩大至社会层面。尽管如此,大多数文献也仅是为了考证“深衣”有利的一面,并不能证明它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普及,而仅仅是受到了一部分人士的重视。
在中国,直到宋代,“深衣”才被逐渐复兴,后世仅有部分人群试图根据《礼记》中记载的情况去复原“深衣”的形制。受朱熹、朱舜水等一辈儒学家对礼制提倡与推崇的影响,促使“深衣”作为一种次等礼服慢慢被儒家所重视,这也是宋代以后它传播至日本等域外国家并被重视的原因。明清之际,各国纷纷将儒学文化进行转化与改造,遂形成了本国特有的儒学面貌,但在本源上都离不开中国儒学的影响。“深衣”在日本后世的发展虽然可能注入了日本对其独有的理解,但却不可能脱离中国“深衣”的本质和特征。“深衣”在日本的传播,除了朱舜水的影响,日本儒者的制作实践与大力推广也功不可没。
二、 日本儒学代表人物对“深衣”传播的推动
在日本儒学发展史中,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在江户时代,随着儒学在日本的进一步推进,“深衣”也随之得到了发展。在林罗山第一次拜见藤原惺窝时,从惺窝的言语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惺窝问答》记载:
先生谓余曰:呜呼!不生于中国,又不生于此邦上世,而生于当世,可谓不遇时也。虽然,孔子不生于唐虞之际,而生于春秋侵伐之间;孟子不生于文武之时,而生于列国战乱之伐。由此观之,志道者不可论时。然则不生于上世,而生于当世,亦奚嗟焉!③
藤原惺窝(1561~1619)在近世日本儒学界可称为始祖,是日本江户时代儒学思想的引领者,林罗山称他为“中兴之明儒”。他对“深衣”的穿着使用,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儒学的接受,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深衣”在日本传播的事实。《惺窝先生行状》记载:“秋九月,幕下入洛,先生深衣道服谒,幕下欲听其言。”④可知,藤原惺窝平日有穿着“深衣”“道服”的习惯,以儒者自居。其中又云:
九年甲辰,贺古宗隆偶居洛。道春初见先生于宗隆宅,论道学,评文章。床上有论语大全,开之叩以数条。先生为之辨拆,且告曰,今所问我亦十余年前尝有此疑也。又曰,我非翅嘉其利智,只嘉其智而已。伶俐者世多有,而立志者寡矣。又揭陆舟二字,令道春作说。不觉日之晚也,辞去。翌日寄手简曰,深衣一领,道服一领,以备制法,深衣兼依国服之式。春遂至缝掖以著之,且作陆舟说以呈之。先生语宗隆曰,近时皆驴鸣犬吠也,故久废笔研,今夫道春起予者,韩山片石可供语者。⑤
上述所言“深衣”“道服”“缝掖”三者,皆是儒家较为常用的服饰名物。可见,藤原惺窝在宣扬中国儒学的同时,并制备了传统服饰以应中国传统礼制,其对“深衣”的制作与穿着则为日常之举。这种行为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更表现了日本儒学圈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罗山林先生年谱》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先生二十二岁,二月与吉田玄之谈朋友交际之事,论朱陆异同,并大学三纲领。……三月朔日,先生作书寄玄之,玄之请惺窝作答书。既而,先生揭经说数条,就玄之问惺窝。今秋,先生初谒惺窝,论道学,评文章,应其求作陆舟说。惺窝寄深衣道服,先生自是著深衣讲书,而录疑问条件呈之,惺窝为之批答……⑥
藤原惺窝将“深衣”“道服”寄予林罗山,可见他十分重视此服饰所蕴含的意义与价值。而林罗山自是较为钦佩惺窝先生的学识,向其请教论学,进而师承于藤原惺窝,为日本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林罗山(1583~1657)是日本江户时代早期的著名思想家,一生用力于朱子哲学的学习,同时也在若干方面受到明代中国理学发展如王阳明哲学思维的影响;他既是一个博学的学者,也对儒学伦理有相当深入的思考。⑦如同其他朝鲜时代的韩国朱子学和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学一样,林罗山的论述和思想表明,这一时期东亚儒学使用的是共同的学术概念,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认同共同的学术渊源,共同构建了这一时代的理学思考、讨论和话语。林罗山的出现,标志着17世纪以后朱子学中心开始向日本转移。
然而林罗山最初与藤原惺窝的接触几经周折,正如林罗山所言“余因贺古宗隆而见惺窝先生”,即通过贺古宗隆才与惺窝相遇于宗隆府邸,两人之间才有了往来问答。《惺窝问答》记载:“时余请贺氏,借深衣欲制之。先生听之,翌日深衣道服到。余乃令针工以法裁素布而制深衣。”⑧看来,当时贺古宗隆已有“深衣”,当初林罗山就想借用他的深衣来自己制作。然而由于惺窝先生的关切,“深衣”“道服”于第二天就被送到林罗山那里。⑨由此可见,在日本江户时代对“深衣”的制作已经逐渐在儒学圈形成一种趋势。这说明藤原惺窝等人已经对“深衣”进行了复原和制作,并热衷于对它的弘扬与推广。在林罗山与藤原惺窝的往来交谈中,曾多次提及“深衣”问题。例如藤原惺窝在给林罗山付寄书简中说到:“前回不虞之会,明快不可言。假言于贺氏,晓此意以达否。所诺之深衣一领,道服一领,备制法。深衣者,少杂国服之样,盖取一时之便也。若从皇明之制,则短其袖,长其裳可也。”⑩据此可知,藤原惺窝对于“深衣”的形制似乎做了相应的改变,而并非完全是中国式“深衣”。目前日本保留着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的深衣像(图1、图2),二者表现出大致相同的造型特征,衣长过膝与踝齐,衣襟交掩右衽,黑缘,头戴幅巾,腰系大带,并附以彩绦,脚穿黑履,具有一套完备的搭配形式。但从整体上看,日本“深衣”与中国宋以后的“深衣”在形制上并无较大的区别,只是形成了统一的风格,从制作方面来讲应该是受到《家礼》所记“深衣制度”的影响(关于日本“深衣”将在本文第三节进行具体分析)。

图1:藤原惺窝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狩野永纳原画,渡边华山模写

图2:林罗山像,林智雄氏藏,狩野探庵手笔
在日本江户时代,对于儒学以及“深衣”的推动,除了正统力量的作用外⑪,作为大儒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毕生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发展儒家文化,倡导礼制,试图在日本建立一种儒家礼制的理想社会。但对于“深衣”的推动并非一帆风顺,前期制作“深衣”的过程也较为曲折。
藤原惺窝辞世后,林罗山为追悼先师,遂作《无言排律一首奉追悼焉》:
先生忽弃群,归去帝乡云。净几五更烛,深衣十幅裙。
异端能早辨,吾道既朝闻。和靖无封禅,陶潛有祭文。
悠闲知独乐,清浊发微醺。疾首人同兽,诛心臣弑君。
雅风排郑卫,后代接关闽。学术渊源远,论谈泾渭分。
……⑫
林罗山用以上诗句以表追悼,也用特别的方式追溯了藤原惺窝的思想生涯。在此,“深衣”与“异端”划出了界限,则其所象征的必是儒学。⑬由此可知,“深衣”对于藤原惺窝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深衣”是儒服,穿着“深衣”即是对儒礼的体现。正如他在给林罗山的答复信函中所言:
来书所谓儒服之制,非不为荣足下之许称。虽然,他人见之,则彼指议曰,足下悦人以溢美之言,余受人以不虞之誉,然则彼此无益而却有害。且夫儒服之制,以余为滥觞者亦奚为?本邦居东海之表,太阳之地,朝暾晨霞之所辉焕,洪涛层澜之荡潏,其清明纯粹之气,钟以成人才。故昔气运隆盛之日,文物伟器,与中华抗衡;诸儒居大学寮者,砥节砺行,孜孜不倦,屹屹不怠;释奠之礼,试科之制;昭昭乎菅右相遗录。当此时,若诸儒不服儒服,不行儒行,不讲儒礼者,何以妄称儒哉?抑亦儒名而墨行乎?墨名而儒行乎?呜乎!猿而服周公之服,鹤而乘大夫之轩,余第恐其服不称其身,何暇论他衣服哉?若又礼义不误,何优人言?⑭
看来林罗山应该也较为关注“儒服”问题,曾专门向惺窝请教。而从藤原惺窝的答疑中可以得知,他对“深衣”的重视,也是源于他对儒学的重视。值得关注的是,藤原惺窝想要表达的是,儒服、儒行、儒礼三者之间有着递进且缺一不可的联系,是儒者需要兼备的重要因素。服“儒服”才得以行“儒行”,才可以称之为讲“儒礼”,这在无形中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礼制文化。朱子学对江户儒学的影响较为深远,藤原惺窝以及林罗山等日本江户儒者更是较为认可朱熹等宋儒的立场,进而由于朱舜水在日本的讲学,更是将中国礼学传统根植于日本儒学圈。所以说,“深衣”在日本的制作、使用与发展并不为奇,这正是随着日本儒学的兴盛发展而必然会产生的现象。后来在日本形成了一种以穿着“深衣”来进行形象塑造的风气,进而使得“深衣”在某些方面或某些群体中成为了一种媒介。
此外,还有诸多日本儒臣,如小宅生顺、人见竹洞、人见懋斋等人对于日本“儒服”及“深衣”问题也极为关心。其中,水户藩儒臣小宅生顺就曾向朱舜水问学,并得到回应。朱舜水向小宅生顺介绍了多种文物制度,对于“深衣”,他说:“服深衣必冠缁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带;系带有绦,垂与裳齐,履顺裳色,絇繶纯纂。”阐明了其整套穿戴方式,以提供儒者服饰之参考。⑮江户幕府儒臣人见竹洞出身儒学世家,自幼即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朱舜水也向他介绍了许多文物制度,例如科举与服饰、道服和野服之制等。水户藩儒臣人见懋斋也曾拜在朱舜水门下,以笔谈、书信的方式询问经义,他也曾向朱舜水请教与“简牍牋素之式,深衣幅巾之制及丧祭之略”相关的问题。
总体来说,“深衣”在日本的发展,主要是受到了诸多儒者的推动。同时,正是由于东亚国家之间学者的往来交流,才促进了“深衣”的传播及影响力的加深。而日本江户时代儒者的习遵古礼,则将“深衣”制作与穿着推向了高峰。
三、 “深衣”在日本的制作与穿着使用
从上文论述可知,日本对于“深衣”的制作基本发生在儒学圈范围内,其制作法度也多是以《家礼》中的记载为参考。目前,日本保留下一部分有关“深衣”的珍贵资料,但一直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因此,通过这类资料来研究日本“深衣”,可以更好地拓宽“深衣”研究的国际视角,也可以进一步反映中国“深衣”在日本的影响及其传播发展情况。
1、形制特征
据研究得知,除了朱舜水寄居日本时与相关人士有较多关于“深衣”问题的交流之外,其实对日本“深衣”制作影响最深的还是朱熹的《家礼》,日本多有根据《家礼》中“深衣制度”制作“深衣”的记载。例如:日本松冈辰方旧藏《朱文公深衣制》,成书于享保十九年(1734),现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服部文库;此外,服部文库还藏有大量有关“深衣”的重要资料。笔者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考察,搜集整理了大量与“深衣”相关的材料。《朱文公深衣制》是根据朱子《家礼》“深衣制度”所制的写本,其中包含上衣、下裳、幅巾、大带以及纸质深衣的样本,它是日本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套有关“深衣”的样本材料。此材料直观地反映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对“深衣”的解读和制作,是当今研究日本“深衣”形制的重要一手资料。其所有图示详见表1。
松冈辰方旧藏《朱文公深衣制》中关于“深衣”的各类纸样图示,不管是衣服的形制,还是大带、幅巾等搭配形式,都表现出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对朱熹《家礼》的解读以及对“深衣”形制的复原。

表1:《朱文公深衣制》样本示意表,松冈辰方旧藏,现藏于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服部文库

图片来源:(日)吾妻重二编著:《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7》,《朱文公深衣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8年,第291-295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续衽钩边”问题,这在中国以及域外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日本中井履轩在《深衣图解》中对此有如下论述:“衽,襟也,缀身旁,而上接袷末,故曰续任也。续者谓缀足之也。衽,下广上狭,狭头亦稍斜,紧接袷末,其外边斜割,更留广二寸。钩屈之如袷,故曰钩边也。夫身单而袷表里者,盖欲其硬起不挠废也。钩边之义,正与此同。成衣之绞,袷与衽边,一直如一物,观图可知矣。按家礼仪节载白云朱氏曰:衽,说文曰:今注,交衽为襟。尔雅:衣皆为襟,通作衿。正义云:深衣外衿之边有缘,则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阔,内连衣为六幅,下属于裳。玉藻曰:深衣衽当旁,王氏为袷下为衿,赵氏谓上六幅,皆是也。玄说正与余意合,然其解钩边,则曰别裁直布而勾之,续之衽下,若今之贴边,其谬如此。故并前说,不为人所取,岂不可惜哉。”⑯关于“续衽钩边”,中井履轩并不认同郑玄的观点,认为对此的解释应该是“衽,襟也,缀身旁,而上接袷末,故曰续任也。钩屈之如袷,故曰钩边也。”因此,其根据自身的研究和推论,进一步绘制了示意图(图3),并结合文献和图片进行了综合解读。如果将示意图碎片进行组合,他所认为的续衽钩边则是笔者在图4中所标示出的红色区域中的位置,这似乎可以合理地解决“续衽钩边”的疑问。

图3:中井履轩《深衣图解》之“裁缝之图”

图4:中井履轩《深衣图解》之“深衣前图”
综上可知,日本对“深衣”的制作,一方面来源于言传,另一方面主要是参考礼经以及朱子《家礼》中的制度。但不同人士的解读或有差异,因此导致所制“深衣”在形制结构上存在不同。但从整体上看,基本没有脱离宋代以后中国“深衣”的形制特征。
2、搭配方式
据考证,日本“深衣”在穿着搭配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特征。目前,日本还保留着诸多儒者有关深衣姿态的肖像,从图像看,皆是着“深衣”“幅巾”的形象,如表2所示。

表2:藤原惺窝、林罗山、读耕斋肖像
表中所示人物皆为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儒者,对比以上三位的着装姿态,则是统一使用“深衣”与“幅巾”来进行搭配,穿着方式皆为交领右衽,领、袖皆为黑缘,其造型特点表现为典型的中国式“深衣”。还可以得知,此群体穿着“深衣”的搭配方式已经有了固定模式,显然是受到了《家礼》中“深衣制度”的影响。虽然图像并不能完全证实其是否与现实生活相符,但日本有关这种服饰形象的人物肖像画实在较为多见,而且也有相关文献记载表中所示人物使用“深衣”的事例为证。
《日本美术馆》一书载有一幅《渡唐天神像》(图5),人物着装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服饰特征。此书对这幅天神像的描述为:“这是天神在圆尔辨圆的推劝下,参谒中国的无准法师,接受法师传法授衣与他,根据这个典故创作的画像。从现存大量画像的构图来看,大多为天神正面拱手而立,头披中国的头巾,身穿道服,左肩配衣囊,手把梅枝的形象。中国的宁波也有制作天神画像的,并被前去明朝的贡使商人贩卖。此幅画像上还有方梅崖⑰的题赞。”⑱其中将天神所着服饰描述为“中国的头巾”和“道服”,但从其整体装束搭配可以判断,这显然是“深衣”的一套固定穿着方式。其中“深衣”“幅巾”“大带”“黑履”一目了然,衣襟交领右衽,都体现了“深衣”的着装特征。此幅《渡唐天神像》成于15世纪,正值中国明代中叶,在这一时期,宁波佛教在对外交流中得到大力发展。笔者认为,画中人物的服饰是典型的明代“深衣”式样,此时正是“深衣”复兴后不断发展并在日本传播的阶段。综合相关资料可知,其搭配形式基本上是按照《家礼》“深衣制度”而定,几乎没有做任何改变。

图5:渡唐天神像(局部),15世纪
综观大量日本有关肖像画,其中对人物整体服饰形象的塑造皆为“深衣、幅巾、大带、黑履”的搭配。在日本这类图像资料较为多见,可以推论,日本的“深衣”在穿着搭配形式上应该是与《家礼》所载“深衣制度”相一致的,它继承了宋以后“朱子深衣”的遗制。正如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服部文库藏《家礼改图》所示“深衣”的搭配部件,其以立体透视的形式绘制出了基本式样(图6)。

图6:《家礼改图》中所示深衣搭配部件
从日本保存下来的与“深衣”相关的资料来看,日本学者对朱子《家礼》“深衣制度”有过深入的研究,“深衣”在日本的搭配情况也基本上是按照《家礼》中的标准来实行的。可见,虽然日本学者对“深衣”的解读和制作或许有所改良,但在搭配形式上,还是遵循了中国传统古礼。
3、穿着使用
关于“深衣”在日本的穿着使用,我们主要从穿着者身份和穿着场合来分析。第一,从穿着者身份来讲,日本对于“深衣”的关注与使用主要来源于中国儒学的传入,并引起了一批日本儒学人士的注意。因此,对于“深衣”的穿着使用,日本儒学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更离不开朱舜水的贡献。明朝灭亡后,有一批包括朱舜水在内的明代遗民曾试图反清复明,并多次往来日本。但后来以失败而告终并长期流亡日本,开始在日本讲学宣扬中国儒学。朝鲜通信使文献中使臣所记笔谈资料,可以证实朱舜水在江户的影响和成就。《随槎日录》记载:
越缉又来,余问曰:“日本与中原通海船,中国人亦多往来云,足下见之否?”答曰:“吾正德出,明之宗室贵族数人来,今皆死矣。”余曰:“明宗室死于贵境耶?其子孙尚在贵国耶?”答曰:“吾水户候甚敬之,其子有二人,今为吾国人,水户光国公喜文辞,故收置明人逃来者凡十三人矣。”问曰:“十三人皆有子孙矣?”答曰:“二人则明之宗室一人名谕,号舜水,水户侯敬之,遇甚厚,设馆食邑,劝置妻,有子,其妾吾国人也。其他在海西诸侯之国,各有子孙两三人。”余曰:“明之宗室衣冠如何?”答曰:“终身着明朝衣冠矣。”又曰:“水户侯为忠臣楠河州建庙,使明宗室朱谕名之山崎,即曰朱氏不能死节,远托吾国,其言与楠公何重。”⑲
朝鲜使臣关心明朝宗室或遗民在日本的情况。而从上述笔谈资料可以看出,在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通往来中,确实存在中国明人流亡日本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为中国儒学传播以及日本儒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朱舜水。据越缉所言,朱舜水终身穿着明朝衣冠,这说明他虽然身在日本讲学,但依然铭记自己是明朝人,一直以明朝的礼仪习俗行事。他在日本受到德川幕府的重要礼遇,在日本江户极受重视,他对“深衣”的制作和穿着应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舜水作为明朝儒学家,在日本期间经常被问学,其中多有关于“深衣”制作与穿着使用的问题。前来交流这类问题的基本还是日本儒士、文人等群体,所以说,当“深衣”在日本还没有得到稳固发展的情况下,主要还是被儒士、文人等阶层所使用。诸如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学群体十分关心“深衣”的情况,已经在尝试制作并穿着使用。
第二,从穿着场合来看,因其用途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一,在藤原惺窝的倡导下,其弟子将“深衣”的穿着使用进行了传承。宽永十年(1633),在上野忍冈的家塾中建成了先圣殿(孔子庙),林罗山在此首次举行了释菜仪式,全体参与人员身穿的都是深衣、幅巾。此事见于犬塚逊《昌平志》卷二《事宝志》:“十年癸酉二月十日,始释菜孔庙,林信胜(罗山)献官。逊按,献官以下诸执事,皆服深衣幅巾,释菜孔庙昉于此。”⑳释菜礼是在初始立学时祭奠先圣的一种仪式,而林罗山带领门人在新建立的孔庙中举行仪式,并穿着“深衣”“幅巾”,则表达了对先圣孔子的敬重,同时也说明“深衣”在释菜礼仪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孔庙也是学堂,可见在学堂这种传授知识文化的环境中应该也有穿“深衣”的情况。目前日本东京都文京区汤岛一丁目还坐落着由德川五代将军纲吉建立的“汤岛圣堂”遗迹,被称为“日本的孔庙”,作为祭祀孔子以及讲授儒学的圣地。因此可以得知,“深衣”在日本使用于释菜礼仪以及学堂等场合中。其二,史料记载,林罗山平日以“深衣”燕居。在朝鲜与日本往来之际,林罗山家族世袭皆主文之人,曾“累接前后信使,癸未使臣赵龙洲、申竹堂,乙未使臣南壶谷,皆与之酬酢,诸诗俱在文集。”㉑与此同时,多有请谒见之,遂有“家君以深衣幅巾接于燕寝,副从亦来会。”㉒由此可知,“深衣”在日本亦有“燕居服”的作用,以便于日常生活穿着使用。其三,由于朱子学传入以及朱子《家礼》的影响,在日本也有结合《家礼》规范社会礼仪制度的情况。如《丧礼略私注》云:“西山大君(即第二代德川光圀)好礼之余,当命儒臣据文公《家礼》等籍,译之俗语,令众庶以便采用,且夫敛葬之具,商其有无降杀,得宜而易从,特置葬地于水城之南北,以为仕臣者之墓……”㉓另有《泣血馀滴》,林罗山就此有言:“本朝释教流布阖国,为彼徒所惑,无知儒礼者。……近世有志之人虽偶注心于《家礼》,然拘于俗习,虽欲为之而不能行者亦有之。今余丁母之优,丧葬悉从儒礼,因叙其次序,滴泪以记之如左,取高柴亲丧之言,而号曰泣血馀滴。”㉔以上两部著作皆是根据《家礼》来制定丧礼制度,与《家礼》中的制度如出一辙,“深衣”的使用也被纳入其中。在日本确实有按照以上丧礼来实行的,例如读耕斋的葬礼就根据《泣血馀滴》的记载穿着“深衣幅巾”以敛。所以说,“深衣”在日本也使用于丧礼场合,对于丧祭礼仪而言,儒家一般会依照朱子《家礼》行事。
结语
总体而言,从“深衣”在日本的制作来看,由于受朱子《家礼》影响,日本的“深衣”在整体形制和搭配方面与中国“深衣”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一般都是参照礼经以及《家礼》制度进行,只是在部分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深衣”在日本的穿着使用主要以儒者、文人阶层为主;其穿着场合主要包括释奠礼仪场合、丧礼场合、燕居场合等。其实,日本的“深衣”,在以礼经为经典的基础上,主要还是参照《家礼》制度,并继承了中国传统。这也从文化角度反映出中国“深衣”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注释:
① 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第175页。
② 关修龄辑:《巡海录》 一册,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参见《宝历三年八丈导漂着南京船资料——江户时代漂着唐船资料集 一》,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昭和六十年(1985),第69页。
基于ALARP准则的某土石坝运行期风险评价………………………………………………阿依古丽·沙吾提(2.40)
③ (日)《惺窝问答》,参见《藤原惺窝集》,京都:思文阁,1978年,第391页。
④ (日)林罗山:《惺窝先生行状》,参见《藤原惺窝集》,京都:思文阁,1978年,第8页。
⑤ 同上,第9页。
⑥ 《罗山林先生年谱》,参见《本朝通鉴》首卷,国书刊行会,1920年,第75页。
⑦ 陈来:《近世东亚儒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5页。
⑧ (日)《藤原惺窝问答》,《藤原惺窝集》下,转引自(日)吾妻重二著,吴震、郭海良等译:《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2页。
⑨ 转引自(日)铃木章伯:《藤原惺窝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78页。
⑪ 这里所指的正统力量,即日本德川幕府的作用,德川光圀较为重视朱舜水的学识,积极与其互动,并为其在日本的讲学提供便利的条件。
⑫ (日)林罗山:《无言排律一首奉追悼焉》,参见《藤原惺窝集》卷上,京都:思文阁,1978年,第301页。
⑬ 转引自(日)铃木章伯:《藤原惺窝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234页。
⑭ (日)《答林秀才》,参见《藤原惺窝集》卷上,京都:思文阁,1978年,第138、139页。
⑮ 林俊宏:《朱舜水在日本的活动及其贡献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4年,第76页。
⑯ 按丧服之衽,旧解:缀衣下,相掩如燕尾,亦谬宜因深衣之例而推焉。仪礼文义自明,又丧大记。徒跣极衽。注曰:披深衣前襟于带也,可并考。(日)中井履轩撰:《深衣图解》,参见(日)吾妻重二编著:《家礼文献集成 日本篇7》,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2018年,第82、83页。
⑰ 方梅崖为明代文人,在明代中日文化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⑱ 此段文字为笔者根据日文翻译,原文参见(日)折桥俊英:《日本美术馆》,株式会社 小学馆,1997年。
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员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四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0页。
⑳《昌平志》卷二《事实志》,《日本教育史资料》第7册,第14页。转引自(日)吾妻重二著,吴震、郭海良等译:《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㉑(朝鲜)洪景海《随槎日录》,参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员编:《朝鲜通信使文献选编(第四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
㉒ 同上。
㉓《丧礼略私注》序,参见(日)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Ⅰ,朱舜水文献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㉔《泣血馀滴》,林罗山“砚与泪同滴以书”序言,参见(日)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Ⅰ,朱舜水文献释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