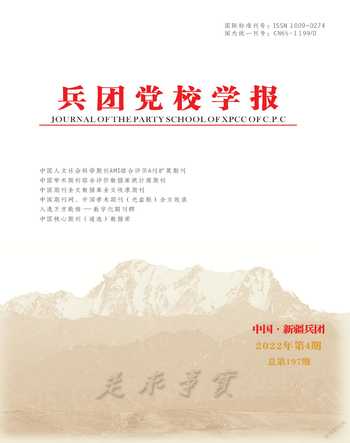毛泽东关于疫情防控思想:内容、特点与经验
史春林 付媛丽
[摘要]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一是全面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防控;二是积极进行预防,加强应急防控;三是发挥科学作用,实行全民防控;四是努力争取外援,开展合作防控。毛泽东有关疫情防控思想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具有人民性、协调性与均衡性等鲜明特点。在毛泽东有关疫情防控思想的指導下,新中国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就遏制了各种疫情的爆发与蔓延,而且对于今天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等疫情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疫情防控;生命健康;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F124;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2)04—0081—10
[作者简介]史春林,男,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付媛丽,女,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历来高度重视各种传染病、寄生虫病与地方流行病等疫情的防控工作,经常亲自过问与调查,听取汇报,开会进行研究与部署,发布一系列批示、通知与决定,对疫情防控的重要地位、宗旨、原则、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科学阐述,形成了丰富、系统的思想,有力指导了疫情防控的实践,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疫情防控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今天国内外各种疫情流行,全面回顾毛泽东疫情防控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疫情防控思想主要内容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疫情的流行都会危害民众与士兵的生命健康,造成财产损失与社会恐慌,对战争胜利与经济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毛泽东对疫情防控十分关心,倾注了大量精力,提出了一系列有效防控思想。
第一,全面统筹规划,突出重点防控。旧中国由于受统治者横征暴敛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造成各种疫情肆意横行与蔓延,严重危害广大民众与士兵的身心健康,同时也给革命战争以及根据地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并给新中国疫情防控留下了沉重负担。对此,毛泽东强调应根据疫情流行的危害程度,有针对性、按计划、分步骤进行全面统筹,做到综合防治、突出重点。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就把当时根据地流行的、对红军战士与群众身体健康影响较大的疟疾、痢疾等疫情作为重点防控对象。而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则把伤寒、回归热、痢疾等疫情作为主要防控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有关指示,卫生部首先把天花、鼠疫、霍乱与疟疾等高传染率、高发病率、高死亡率的疫情作为重点防控对象,到1951年底这些疫情就得到基本控制。对此,1952年8月毛泽东指示中央防疫委员会准备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予以检查,并规定1953年的防疫计划”[1]509。
在此基础上,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各地党委7年内基本消灭鼠疫、脑炎等“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2]509-510。1956年1月毛泽东在审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时,对此再次做了全面规划与具体部署,即从1956年开始在7年或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的最严重的疾病”[3]19。为此,1956年3月毛泽东两次批示,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参会讨论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其他严重疾病也“宜加以讨论”[3]47-48。1960年3月毛泽东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其他严重疫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4]150。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当时严重影响民众生命健康的各种疫情进行了明确分类,并结合各地条件与实际情况提出了长期规划、因地制宜、分期治理的思想,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迅速遏制了历史上长期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的疫情,其他一般性的疫情防控也取得显著成效。
在全面防控的基础上,毛泽东高度重视血吸虫病的疫情防控,对此给予了长期持续的关注与指导,这是因为该病是当年流行疫情中危害最为严重的一种:一是传染性强,“我们现在10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会受到威胁”[5]。二是流行地区广,患病人数多,全国有“一千万人受害,一亿人民受威胁”[6]54-55。三是对群众生命健康危害大,死亡人数高,“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7]234。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反复提到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妨害生产,威胁健康,是有关整个民族的问题”[8]。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血吸虫病疫情防控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1953年9月毛泽东在给政协副主席沈钧儒的信中强调“必须着重防治”[9]。195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对身边人员表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疫情”[10],同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相关汇报后正式向全国发出了这一伟大号召。1956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号召全党与全民动员起来,“消灭血吸虫病疫情”[6]54-55。1956年3月毛泽东连续三次做出批示,对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筹备、议题以及参会人员情况等进行具体部署。该会召开后卫生部将有关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3月20日毛泽东将有关汇报加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标题,并“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3]77-78,要求认真落实。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有关汇报时再次强调:“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5]。
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与部署下,再加上有关部门及疫区广大群众的不懈努力,很快就有效控制了血吸虫病疫情。1958年7月毛泽东在得知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虫病以及全国灭疫大有希望的消息后,兴奋地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的诗篇来表达其喜悦之情[7]234,热情讴歌了党和政府领导广大人民与该疫情进行英勇斗争的精神及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此,当时访问过中国的一个英国医生代表团曾赞叹道,这是中国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10]。
第二,积极进行预防,加强应急防控。在革命战争年代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疫情防控资源极其有限,因此始终存在着预防与救治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强调应以积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体现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理念。
一方面中国作为十分落后的国家,采取措施积极预防疫情暴发与蔓延是一种非常经济与高效的方式。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强调:“对疾病的治疗要和预防结合起来,要做好预防工作”[11]111-113。1932年初针对江西富田疫情流行问题,毛泽东强调根除疫情在主动防止[12]67。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预防胜于治疗”的口号,特别是1944年7月毛泽东针对延安郊区出现的疫情明确提出,减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13]1083。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提出防疫“要以预防为主”,据此新中国正式将其定为卫生防疫方针之一。
其一,加强疫苗预防注射。对于一些严重的疫病而又没有特效药能治愈的情况下,最简单与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疫苗预防接种来有效提高身体免疫力。如1929年3月红四军解放了福建汀州城,而当时此地正流行天花疫情,毛泽东接受了福音医院傅连暲院长的建议,及时为战士接种了牛痘,从而阻止了天花向部队蔓延。1952年初美军发动细菌战后,2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要在东北开展疫苗预防注射获得批准。3月毛泽东又批示“京津一带速办防疫”[14],从而有效阻止了疫情扩散。
其二,建立专门隔离病房。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北京没有防疫隔离病院的实际状况,1952年4月毛泽东批示“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并请周恩来具体部署[15]。
其三,切断疫情传播途径。毛泽东深知环境卫生与疫情防控的内在关系,因此他对消灭疫情传染源以达到预防的目的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把消灭苍蝇、蚊子、老鼠与麻雀(后以臭虫替代)“四害”作为疫情预防的一个主要任务。如1955年12月毛泽东就要求在7年内基本上消灭“四害”以及其他害兽与害鸟[2]510。1956年1月毛泽东更是明确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5年、7年或12年内分阶段“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四害”[3]19。1957年10月毛泽东再次强调:“两年试点,五年突击,三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四无国”[3]593-594。1958年1月毛泽东又进一步要求各地可根据本地实际,“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16]361。2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时强调:“向群众提出的具体口号各地可以因地制宜”[17]75,根据各疫区不同状况有针对性地增加消灭钉螺、白蛉子、臭虫、跳蚤等疫情主要媒介。由此可见,毛泽东除“四害”及其他害虫与害兽的主要目的是将其同疫情产生与传播的自然条件、卫生环境以及病源、病媒等联系起来,如1958年4月毛泽东在与医学专家朱琏谈话时指出,你们治疟疾的道理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道理都是一样。因此,毛泽东主张通过积极主动改造疫情孳生的自然环境消除病源,以達到根治的目标。对此,当时英国有医疗专家认为毛泽东所倡导的除“四害”“对肠胃传染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影响”[10]。
另一方面当突发疫情出现后,毛泽东则会有针对性地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部门要及时、迅速、准确公开信息,开展疫情监视与报告,做好疫区封锁与隔离,调集防疫人员与医疗物资积极救治患者,降低死亡率。如1944年5月,毛泽东针对延安郊区发生的疫情强调应“想办法加以解决”[18]154。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区多次派遣医疗队下乡控制疫情,没有造成大范围蔓延。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鼠疫发生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治,疫情不到1个月就得到控制。1950年冬毛泽东得知上海郊区爆发急性血吸虫病后即派出医疗队前往防控。1952年3月毛泽东针对华北疫情,要求“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341。1952年春美军发起了无耻的细菌战,用飞机连续在朝鲜、中国东北和青岛等地投放带有细菌的昆虫,在辽宁等地引起疫情流行。对此,2月1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注意此事,并予处理”[1]239。20日毛泽东再次批示:“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1]318。这样,到1952年冬就基本粉碎了美军细菌战,保卫了军民健康。
第三,发挥科学作用,实行全民防控。毛泽东强调疫情防控一定要尊重科学,实行群防群治,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一方面,疫情的预防与扑灭、患者的救助与治疗等都需要在专家学者、专业医生与防疫人员指导下运用科学方法与手段来解决。
其一,开展疫情实地调查。为掌握疫区实际,总结防控经验与教训,需要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如1951年3月毛泽东就派专业人员到江西余江开展血吸虫病疫情调查。1955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开会期间还专门安排身边人员去郊区了解血吸虫病疫情,同年11月又指派卫生部领导到浙江血吸虫病严重的疫区开展调研。1956年毛泽东指示中央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与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组到江西余江考察血吸虫病疫情防控情况。而且毛泽东本人也常到疫区视察,如1958年9月毛泽东亲自到安徽省博物馆了解血吸虫病疫情防控规划,为科学防控奠定了基础。
其二,听取专家防控意见。1956年2月生物学家秉志给毛泽东写信建议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须用火烧才能永绝后患,毛泽东立即指示卫生部照办,并请其参加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3]47-48。1956—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广东等地视察期间,又特地接见了苏德隆、吴光、陈心陶等血吸虫病防控专家并认真听取他们有关意见,体现了毛泽东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
其三,加强防控科技研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疫情防控的科技研发,要求组织有关专家开展集体攻关,探讨有效的防控措施。如1953年4月毛泽东就指派有关医生进驻江西余江,开展血吸虫病疫情防控科学实验。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有关汇报时,强调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研制血吸虫病有效防治药物与方法。1956年3月全国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召开后,卫生部建议要“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毛泽东表示赞同[3]77。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与防治血吸虫病专家苏德隆座谈,鼓励科技人员好好研究[10]。这样,有关部门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组织广大科技与医疗专家协作攻关,很快就发明许多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的办法,同时还研制出300余种血吸虫病防治药物,从而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疟疾肆虐,当时越共领导向毛泽东请求支援。曾在中央苏区染过疟疾、深知其害的毛泽东回复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据此,1967年5月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国力量研发抗疟新药。1972年3月药学家屠呦呦在南京有关会议上做了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的报告,后来据此研发的青蒿素成为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2015年10月屠呦呦因此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对此,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文章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指示,那个时代的中国不可能发明青蒿素[19]。
其四,重视中西医相结合防控。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医,努力发展西医,并强调中西医要紧密结合、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与促进、共同提高疫情防控的效果,从而建立了中国现代新医学与中国式疫情防控体系。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针对当时敌军进攻与封锁导致根据地缺医少药与疫情流行的状况,强调要“用中西两法治疗”[20]65,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要中西医都用”[11]111-113。针对1944年初延安郊区疫情防控问题,毛泽东更是明确强调中西医“这两种医生要合作”[18]154。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再次强调新医一定要联合边区现有的旧医一起进步[13]1012,共同抗疫。经过中西医共同努力,延安郊区疫情没有大范围扩散。1950年8月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时号召要“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21]493,因此该会议把“团结中西医”定为新中国疫情防控一个基本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主张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努力发展新医学。一是毛泽东号召“西医要向中医学习”,并在1958年10月提议开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以尽快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16]423。如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当年就参加了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这对于她后来发明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起了重要作用。二是毛泽东也号召中医要向西医学习,即“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16]78-81。总之,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国新医学,有效弥补了當时疫情防控资源匮乏问题,最大程度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这是新中国疫情防控的一个特色与创举。
其五,培养防控专业人员。为了战胜各种疫情,还要拥有一支规模宏大的疫情防控专业队伍作为骨干力量来有效开展工作。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要把培养与培训防疫专业人员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一是毛泽东认为防疫人员教育与培养首先要从学校抓起,为此1951年4月卫生部等部门做出了《关于发展卫生教育和培养各级卫生工作人员的决定》,其中就包括防疫专业人员教育与培养问题。二是毛泽东主张要对有关人员开展防疫专门培训,如1952年4月卫生部在向毛泽东汇报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情况时提出要对卫生人员开展防疫专门训练[15],毛泽东对此要求应认真贯彻落实。特别是在1952年反对美军细菌战斗争中,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要大力加强专业防疫人员的培训,以便更好地应对疫情扩散。
另一方面,疫情防控还必须开展全民防控、联防联控。疫情防控是一项涉及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不仅要求每个人要做好自身防疫工作,而且还要大力加强公共防疫工作,因此单靠政府、科研工作者、专业防疫力量与医护人员的努力并不够,如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有关防控血吸虫病疫情汇报时就强调做好粪便与水源管理以及消灭中间宿主钉螺等工作都需要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10]。由此可见,疫情防控必须依靠专业技术人员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才能收到良好防控效果。为此就要大力宣传、动员、组织广大民众这个主力军参与进来,才能更好地把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健康地开展下去。于是毛泽东将党的群众路线成功运用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让群众自己起来自觉同疫情做斗争,树立正确的防疫观念,养成良好的防疫习惯,积极整治产生疫情的卫生环境,从而使疫情防控工作成为人民自己的事业。
毛泽东组织开展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最能体现其全民防控思想。1932年初,毛泽东针对江西富田出现的疫情,就强调要“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12]67。1933年12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强调要“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22]310。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3月针对美军发动的细菌战,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爱国卫生防疫运动。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614。对此,当时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称赞该运动“使得由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23]。美军细菌战被粉碎后,毛泽东认为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不能就此结束。这样,从1953年底开始,根据毛泽东有关指示精神,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向讲究卫生、除害灭病、环境整治等方向深入发展,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并将疫情防控与兴修农田、发展水利等生产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了千军万马齐上阵、六亿神州送瘟神的壮观局面。
第四,努力争取外援,开展合作防控。毛泽东历来强调疫情防控工作首先要立足自身,但同时也要积极争取外援,开展国际合作,学习国外疫情防控经验,特别是要力争苏联支持与帮助。一方面在华北,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鼠疫发生后毛泽东向斯大林致电,请求苏联空运生菌疫苗等防疫物资,并请苏联派遣防疫队帮助开展防控,斯大林接到电报后立即派出专门医生、防疫队并支援了药品。另一方面在东北,新中国成立初期鼠疫频发,苏联多次派出防疫队到东北疫区设立防治所、举办训练班、制订防控方案、救治患者。对此,毛泽东表示感谢并称赞苏联防疫队在中国东北鼠疫防控工作“成绩甚大”[21]98-99。
1952年初美军针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对此在搞好国内疫情防控的同时,2月18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呈报毛泽东建议请求苏联予以援助,对此19日毛泽东批示请周恩来处理[1] 239。周恩来立即拟出了具体防控报告并获得毛泽东批准实施,其中争取国际援助包括:中朝发表声明开展舆论配合,并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建议向全世界控诉及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罪行,同时向苏联通报并请求其帮助。21日毛泽东又致电朝鲜领导人,建议“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23日毛泽东批准了苏联顾问协助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制订的防疫计划大纲[24]217-219。这样在苏联、朝鲜以及世界上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大力支持下,美军细菌战到1952年冬基本被粉碎。
二、毛泽东关于疫情防控思想鲜明特点
毛泽东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根据革命与建设实际,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并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一,疫情防控的初心坚持人民性。毛泽东有关疫情防控的核心思想是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生动体现了其为民情怀。众所周知,疫情防控关系百姓的身心健康与幸福生活,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因此疫情防控首先要以群众健康为中心,这是毛泽东疫情防控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一方面人民大众既是疫情防控宣传的主要对象,又是疫情防控工作的主要参加者,更是疫情防控运动的具体行为者,因此需要广泛发动、教育、组织与依靠群众。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又是疫情防控的主要对象与直接受益者,开展疫情防控有助于鼓舞与调动民心,从而得到其拥护,并发挥其积极参与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
因此,毛泽东怀着对人民负责的初心与依靠人民的胸襟,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愿望与利益放在第一位。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防疫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宗旨[10]。1932年初针对江西富田疫情,毛泽东强调防疫工作“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发展革命战争的胜利极其重要”[12]67。1月12日毛泽东还专门主持了防疫会议,并决定“保障工农群众的健康、防止疫病在各地传染起来”[25]。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要注意解决群众卫生疾病等具体实际问题[26]136-138。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举办了一次卫生展览会,其中一个专题就是疫情防控问题,毛泽东亲自给展览会题词:“为全体军民服务”。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要求“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13]1083。
新中国成立后,毛澤东指示卫生部要把5亿人口的生老病死这件大事管好[27]。据此,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把“面向工农兵”作为防疫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得知卫生部原定想用15年时间初步消灭血吸虫病疫情,毛泽东认为应考虑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前消灭。后经认真、充分讨论,改为7年基本消灭疫情。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生动体现了其始终以人民安危为根本、以为百姓生命和健康服务为宗旨的历史自觉。
第二,疫情防控的机制注重协调性。疫情防控是一项纷繁复杂、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管理、法律等诸多问题,需要综合治理。因此疫情防控不仅仅是医疗、卫生、防疫等专业部门的事情,而应将其置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考虑。1960年3月毛泽东在有关指示中强调:“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而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革命,相互结合起来”[4]150,为此就要加强各部门与各领域相互协调与配合。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与机制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以下两方面的协调:
其一,正确处理疫情防控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十分注意把疫情防控与生产建设结合起来,强调两者不能偏离,在保护群众生命健康的同时,要注意促进生产同步发展。如1952年在反对美军细菌战的斗争中,4月周恩来在给毛泽东提交的《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强调了防疫与生产相结合问题:“不照顾生产,不照顾物资交流,从单纯防疫观点出发,是不对的”,“当然也不应由于照顾过多而失掉防疫原则”[15],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方面,不能因为只抓生产建设而忽视疫情防控。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落后,因此某些地方党委与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抓生产建设,而忽视疫情防控工作,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疫情,进而影响生产建设。如1958年11月河北邯郸出现伤寒、痢疾等疫病,造成这一状况的主因是当地只抓生产而忽视民众生活,身体抵抗力下降,致使疫情蔓延。对此毛泽东批评指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并明确要求“工作生活同时并重”[17]530-531。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河北及邯郸各级党委马上行动,很快就解决了疫情蔓延问题。1958年11月云南省委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由于有关领导不注意关心群众基本生活,致使云南春夏之间发生了痢疾等疫情。对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一个教训》一文,要求各地不要再犯类似错误,强调“生产、生活同时抓”[16]451-452。
另一方面,搞好疫情防控有助于生产建设。疫情防控工作的目的是要保护大众生命健康、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疫情防控工作与生产建设的目的是一致的,应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即疫情防控应配合、促进、服务生产。如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有关汇报时,强调要把防治血吸虫病疫情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10]。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大疫区把消灭血吸虫病中间宿主钉螺、铲除蚊蝇孳生地、开展饮水及粪便等卫生环境整治与积肥、造田、兴修水利等生产活动相结合,有力促进了疫区农业生产发展,真正做到了除害灭病与生产建设一举两得。
其二,注重将疫情防控与社会建设相结合。毛泽东并不是孤立地看待疫情防控工作,而是将其与文化建设、思想改造、移风易俗以及提升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相联系。一方面,把疫情防控看作是一种文化。毛泽东认为一些老百姓不讲卫生的陈规陋习如同文盲与迷信一样是文化落后的产物,应在改善不良卫生习惯过程中创建一种卫生防疫新文化,因此搞好疫情防控工作必须同人们长期形成的旧俗恶习做斗争。如1944年10月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强调我们必须让广大人民自己起来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13]1011。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次强调要使群众逐渐离开“不卫生的状态”[18]241。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要求把除“四害”、讲卫生“这个文化大为提高”[16]308。由此可见,疫情防控既是满足人民大众生命健康的需要,又是文化发展的要求;既是人们自身修养的内化,又是社会文明的表征,有助于提高群众卫生与文化素质。另一方面,疫情防控还体现了一种荣辱观。1960年3月毛泽东在有关指示中强调要使广大人民“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4]150。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卫生防疫工作当成了改造思想、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途径,并把它提升到改造国家与世界的高度。如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审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强调,除“四害”与除疾病的根本精神都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3]606。195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强调,号召人民讲卫生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真能搞出一点成绩,“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28]1657。1960年3月毛泽东在《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指示中更进一步强调,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具有“改造世界的意义”[4]150。
由此可见,毛泽东有关疫情防控的思想及其实践,不仅有效遏制了疫情的发生与蔓延,而且还极大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面貌,同时广大民众也从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卫生防疫与环保意识,开始向落后的生活方式以及不良的卫生旧习惯与旧思想宣战,从而促进了全民健康事业的发展。
第三,疫情防控的布局体现均衡性。毛泽东基于国情,非常关注农村与农民的疫情防控工作,注重均衡性发展。由于中国农民占绝大多数,且广大农村相对落后,卫生条件较差,再加上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存在封建迷信思想,以至于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整体开展。疫情一般首先在农村发生,但由于缺医少药,防控困难较大,导致蔓延很快,因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村疫情防控问题。如1944年5月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延安郊区疫情防控问题,要求“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18]154。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防疫工作离不开3亿6千万农民[13]1078。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针对当时城乡医疗与卫生防疫资源分配不均衡导致农村防疫落后问题,强调要探索与推广适合农村的检查与治疗方法,同时应把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放到农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上,并为此发出了“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29]505-506,从而明确了新中国疫情防控的重点向农村发展的方向,这对于改善农村防疫状况具有极大帮助,使有限的防疫资源能够惠及更多的村民。
其一,组织下乡巡回医疗队开展防疫工作。1965年1月毛泽东批转了卫生部提出的《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30]318,开始组织城市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分期、分批轮流下派到农村开展流行病调查,进行免疫接种,并对乡村医生进行防疫培训以及向村民开展防疫知识宣传。
其二,普及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医疗制度。在此基础上,1968年11月毛泽东批转了湖北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典型经验[31]604,推动了全国农村兴办合作医疗的热潮。这种合作医疗除了为村民提供一般疾病诊治及转诊服务外,还承担着计划免疫、疫情监测、组织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动等任务,因此这种低成本、广覆盖的疫情防控保障机制在农村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三,大力培养半农半医乡村卫生员。1965年6月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就明确提出要放低门槛要求,以便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培训一批能在农村治疗最基本疾病的卫生防疫人员。1968年9月毛泽东批转了《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31]557,赤脚医生队伍从此迅速壮大。这些赤脚医生除了能治疗农民常见病外,各卫生防疫机构还经常组织赤脚医生开展集中培训,使其能够承担农村防疫的基本职能,如当年全民防疫任务在农村落实基本上都由赤脚医生来完成。
三、毛泽东关于疫情防控思想基本经验
在毛泽东疫情防控思想的指导下,使人民的疫情防控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可资借鉴,这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疫情防控事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第一,政治保障:加强与改进党的领导。疫情流行会危及民众生命健康,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疫情防控本身的这种重要性与特殊性就决定了其既是公共卫生问题,又是民生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对疫情防控工作给予明确定位:“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2]176。此后,毛泽东在指导具体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也多次强调要当作政治任务来抓,如1955年11月毛泽东指示卫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6]54-55。
疫情防控既然是政治任务就决定了此项工作党性很强,必须高度负责,不能出任何差错,为此就要加强和改进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与领导,以便协调各方、整合资源开展有效防控。1954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的批示》中强调防疫工作“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32]。毛泽东还具体指出:“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基本保证。[6]70毛泽东不但强调要加强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而且还要不断改进党的领导。如195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必须改正各级党委对于防疫工作“缺乏注意”这一严重问题[2]176。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坚决克服防疫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问题,绝不允许对疫情视而不见、闻而不报、玩忽职守等行为。如1953年3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上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到了该部某些领导在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对业务缺乏指导以及对工作人员缺乏政治思想领导;领导水平不高,推卸责任等。对此,毛泽东在批示中对这种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并由此想到政务院卫生部是否也像军委卫生部那样“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因此毛泽东责成有关领导与部门要严肃检查与认真解决,以“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33]176-177。总之,加强与改进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是关键,正如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中所说,血吸虫病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取得成效“主要是党抓起来了”[7]234。
第二,组织保障:建立与健全管理机制。中国由于地广人多,需要各方面合作才能很好达到疫情防控的目的。为此,就要建立与健全疫情防控的组织体系,完善相应管理机制,为疫情防控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强调:“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22]11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强调要加强组建专门防疫机构。
其一,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鼠疫爆发后,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成立专门的防疫机构来组织领导灭疫工作。据此,周恩来首先成立了中央防治鼠疫领导小组并开始组建中央防疫总队。在此基础上,各省、市、县也都相继成立了鼠疫领导小组与防疫队。
其二,1952年春为应对美军细菌战,毛泽东明确要求国内各大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1]339。据此,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各地防疫工作。在此基础上,各大行政区及沿海各省、市等也都先后成立了防疫委员会。
其三,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有关汇报时,认为血吸虫病疫情防控不能光靠卫生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防治领导小组统抓全国工作。根据毛泽东提议,立即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全国防控工作,随后在流行疫区的省、市、县也都相应成立了领导小组。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上述这些具有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疫情防控机构的建立实现了分散力量高度组织化,基本上形成了覆盖全国的自上而下的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机构,初步建立了有效管理的组织体系与运作机制,这对于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进行疫情防控的应急集中处置与全面综合治理具有重要作用,开创了中国独特的疫情防控的组织模式。
第三,制度保障:制订与完善法律规章。制订与完善相关法规,可为疫情防控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促进有关工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直接过问下,1932 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就发布了《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和《实行防疫卫生运动训令》。1933年5月中央苏区总卫生部部长贺诚为苏区卫生管理局草拟了《卫生管理条例》,后经毛泽东审阅并根据其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卫生运动纲要》与《卫生防疫条例》两个规章。1933年10月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央苏区《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国外特别是苏联的有关经验,亲自起草了《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等10余个专门指示、通知、决定等,同时还指示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令等,通过制度性的规范对疫情预防、应急处置以及防控部门的目标定位、组织架构、人员职责、行动措施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如1957年12月毛泽东签署主席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这些规章制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从此新中国疫情防控工作走上了规范化轨道,基本上能够做到有章可循、依法防控。
第四,资金保障:筹集与增加相应经费。疫情防控属于公共事业,因此毛泽东主张有些项目可免费,“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34]。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要想办法多方筹集与不断增加疫情防控的资金,尽量保证政府的财政投入。如1951年9月毛泽东批示防疫经费,“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2]176。当时华北乙型脑炎疫情较为严重,对此毛泽东指示防疫部门要专门拨款用于防控工作。后来,毛泽东还多次指示要追加血吸虫病疫情防控经费,使得药品供应与患者救治等能够及时有效。如1956年3月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召开后,卫生部建议应“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3]77-78。
第五,宣传保障:动员与鼓励大众参与。加强疫情防控的广泛宣传、教育、培训,普及疫情防控的科学知识、方针政策、法规制度,传播正确、健康的防疫观念,形成积极、向上的舆论导向,有助于提高大众自身防疫意识与素养,改变传统旧习,增强自我保健能力,自觉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去,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有关疫情防控的宣传、动员、教育与培训等工作。如1932年初江西富田疫情发生后,毛泽东强调“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防病知识”[12]67。1944年初延安郊区疫情发生后,3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18]119。1944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号召教育、报纸和文艺等都要及时反映和指导“群众卫生运动”[35]30。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4月卫生部在向毛泽东提交的有关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情况汇报中提出要深入宣传防疫知识,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15]。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有关血吸虫病疫情防控汇报时,指示要编辑通俗小册子加强宣传。1957年12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对他起草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中的有关宣传问题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要把“有关道理讲清楚”,同时在办法上“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16]336。另外,毛泽东还主张通过竞赛等方式,抓评比、树典型进行宣传与奖惩,及时总结与推广经验。如1952年 8月毛泽东就中央防疫委员会有关防疫部署进行批示,要求“在北京开一次全国卫生防疫展览会……并对优胜者给奖”[1]509。这样,不但可广泛发动群众学习防疫知识,提高自身对防疫工作的认识,而且还极大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疫情防控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总之,毛泽东有关疫情防控思想内容丰富、特点鲜明、针对性强、影响力大,在实践上使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便遏制了各种疫情的爆发与蔓延,甚至是消灭了历史上长期危害人们健康的疫病。对此,毛泽东无比自豪地表示,许多疫情“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36]486。而且毛泽东疫情防控思想还为人民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有力推动了防疫事业的进步和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今天新冠肺炎等各种新型疫情仍严重威胁着百姓健康,因此回顾与总结毛泽东疫情防控的宝贵思想,这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防疫水平和促进现代防疫体系建设、实现健康中国梦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王龙友.卫生防疫,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J]. 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1996(S1).
[6] 编写组.当代中国卫生事业大事记(1949年—1990年[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
[7]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施亚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血防工作的重视与领导[J].党史文苑,2011(4).
[9]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胡新民.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J].党史博采,2018(10).
[11]穆静.傅连暲传略[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
[12]冯彩章.贺诚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李洪河.反细菌战调查与建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肇始[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5]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J].党的文献,2003(5).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9]刘炳峰.毛泽东与中国医药界的“两弹一星”[J]. 钟山风雨,2017(3).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2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J].科学通报,1952(S1).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5]朱红英.试论中央苏区的卫生防疫管理[J].农业考古,2010(3).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7]曹普.论毛泽东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大贡献[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1).
[28]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9]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2]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3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34]刘雪松.毛泽东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J]. 党史博览,2016(5).
[35]教育科学研究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