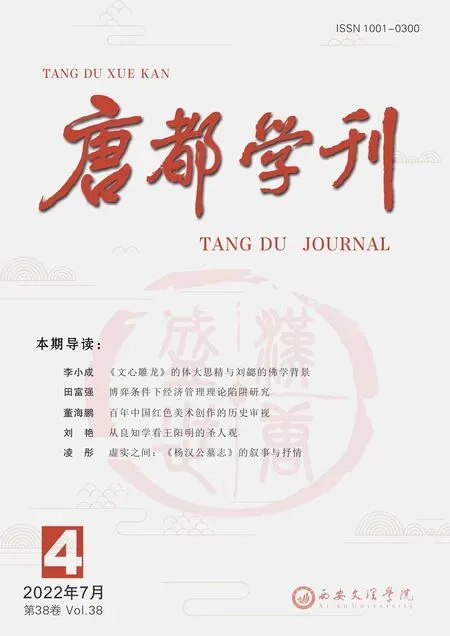百年中国红色美术创作的历史审视
董海鹏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宝鸡文理学院 美术学院 ,陕西 宝鸡 721013)
红色记忆是当代中国历史记忆的重要特征。从五四运动到建党百年,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美术创作,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建构中国美术精神图景的历史使命。红色美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记忆,是对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历史形象的还原,是延续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其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是对历史真实问题的视觉叙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所呈现的一部审美史。鉴于此,回顾一百年来中国红色美术的发展历程,研究红色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红色美术”创作的维度与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因此树立文化自信首先要树立对红色文化的自信。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美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产物,是现当代美术创作的主旋律。
红色美术是“红色”与“美术”两个词汇结合而形成的概念。广义的“红色美术”是指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的红色美术作品;狭义的“红色美术”主要是指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题材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美术创作。基于狭义的红色美术创作范畴,以艺术本体论的研究视角,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红色美术创作进行深度思考,从文化内涵和特征上解读中国革命史,概述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不屈抗争→图强崛起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从整体上把握红色美术创作所表达的思想内涵。这种创作形式既具有独特的美学形态,又贯穿于时代命脉的价值追求,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在革命和建设中迸发出的文化使命和独特的精神品质。
“红色文化作为反映中国共产党探究救国、兴国和强国历程中的产物,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时代情势相结合的必然结果。”[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红色”的起点,此后“红色”一词逐渐成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象征符号,承载着推动革命、呈现时代发展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抗战形势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思想,他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的表现出来。”[3]866红色美术创作的政治形态在以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下逐步确立了“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艺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成为塑造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教科书”。然而,从革命文艺发展的客观意义上来讲,“红色美术”的政治内涵是中国革命文化衍生出的一种美术类型,革命美术家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再现了为民族解放与国家振兴而艰苦奋斗的英雄人物,还原革命情境的真实性,从而建构了留存在人民记忆中的红色美术经典图像。
红色美术创作是红色文化历史、红色文化符号和红色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从创作主体上可划分为两条脉络:其一是以亲历者为创作主体的红色美术创作,其二是以非亲历者为创作主体的红色美术创作。无论从哪一方面来探究作品的审美性,都是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各时期美术自身艺术观念与审美观点的演变。从“审美意识形态论”上来看,红色美术的审美形式自抗战以来,因特定历史环境下折射出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使得美术创作的政治生态和大众的审美心理重新整合,直指人心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艺术家们的审美追求,并由此确立了中国当代美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可以说,红色美术创作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发展的精神与审美诉求。
二、红色美术创作的重要成果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领下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思潮的转型,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红色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诠释与再创,为中国红色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而中国几代美术工作者以“笔墨丹青”延承历史记忆,记录百年巨变,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美术成果(1)本文列举的重要成果均出自国家官方展览的获奖作品及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作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美术创作的视角主要聚焦于反动统治阶级对工农的压榨、剥削尤其鼓励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等方面。这一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有胡一川的《到前线去》、杨涵的《人民的军队回来了》、江丰的《平型关连续画》、古元的《抗战胜利》等经典作品。如江丰的《平型关连续画》,作品以“连续纪实”的叙事手法再现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战前、战时和战后的三个场景,即作战会议、战斗之中、战斗胜利。画家在形式上以阴刻线条为主,以黑白色为主调,将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生动准确地刻画了“八路军指挥员坚定必胜形象”“八路军战士英勇冲锋形象”“八路军与人民群众军民合作形象”,这三种真实的人物形象在唤醒民众持续抗战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画家有意识地将‘抗战宣传’与‘木刻版画’的本体语言有机融合,将木刻版画‘大众化’‘民族化’的深度思考与民间年画的‘旧形式’进行‘新理念’的实践探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美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5]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美术的发展形态,形成了现实主义美术创作的范式。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政策的确立,红色美术逐渐繁荣。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主要聚焦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和“文革”等社会变革场景的具象化表现,画家们力图从不同的视角片段式记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面貌,创作出了如周令钊的《五四运动》、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程十发的《歌唱祖国的春天》、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石鲁的《转战陕北》、沈尧伊的《唤起工农千百万》等优秀作品。以程十发的《歌唱祖国的春天》为例,该作品描绘了上海郊区的工农兵大家庭欢聚在桃林中,画面中的人物群体正在听一位老妈妈放声歌唱的欢乐景象。作品创作于1956年,此时中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年轻的新中国日新月异,整个民族精神气象焕然一新。画家将工业文明的场景融入自然风景中,暗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对新生活的向往。20世纪60年代初期,“文艺界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创作思路,尝试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实现对历史的真实重塑。”[6]如石鲁的中国画《转战陕北》,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后开启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画面以“高山仰止”的纪念碑式构图,将毛泽东背侧面眺望远方的形象与黄土高原雄浑博大的“精神基质”融为一体,着重突出“革命领袖‘运筹帷幄、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的坚定信念,而转战陕北的千军万马,仿佛隐藏于山壑之间”[7]。毛泽东雄才远略、气吞山河的气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工作者始终将对社会的关切与人民的关怀融入自身的绘画创作中,形成了鲜明的绘画语言和艺术风格。美术创作主要集中于再现“革命历史记忆”与阐释“时代精神风貌”。代表性作品有吴云华的《跨过鸭绿江》、孙浩的《平型关大捷》、林永康的《1992·邓小平在广东》、华其敏的《铿锵玫瑰——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何红舟、黄发祥创作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许江等人创作的《红潮——五四运动》、张静的《中国速度》等作品。从“革命历史记忆”这一主题作品来看,其创作虽源于革命战争年代,但又不止于革命美术,它是新时代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是激发中国人民内在反省的思想源泉。以何红舟、黄发祥创作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为例,作品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登船“启航”的历史瞬间,再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和英雄气概。许江等人创作的《红潮——五四运动》,以张弛有力的视觉感受塑造了宏阔的历史意象,以写实风格再现了“有血有肉”的革命形象,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发出时代最强音,凸显了中国青年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近四十年来,红色美术创作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开始注重思考“人”本身的话语空间,蕴含了浓郁的家国情怀。无论是从领袖与人民视角创作的诸如孙黎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彭湃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彭华竞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从军民团结角度塑造的如晏阳等人创作的《淮海战役》、李卓等人创作的《为了和平》;抑或是从基层领导干部服务人民群众视点刻画的如宋克的《焦裕禄》、赵振华的《进军小汤山》、张峻明的《三线建设》等人物形象,都是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和自强精神的视觉再现。
三、红色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
百年红色美术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独具审美意蕴的人文思想和文化特征,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独特气象。革命、建设年代的红色美术创作,作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美术立场的双重存在,影响着人民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一)红色美术创作的历史价值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3]857习近平总书记延续并进一步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8]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革命文艺的实践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主流美术创作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对于“人性”的思考。抗战时期唐一禾创作的《全面打击侵略者》、周多的《妇女手中线,战士身上衣》、丁正献的《一个出征军人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孔德创作的《二级战斗英雄杨国良》、列阳的《行军途中》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刘大为创作的《人民公仆》、秦文清的《士兵们》、孔平的《追星》等作品,都蕴含了艺术家对人性的思考,对他人命运的关怀。所以,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本质,也必定成为红色题材美术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红色美术当代价值的实现,既需要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也需要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发了有关红色文化的重要论述,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0],并充分肯定了中国红色文化的历史价值。于是,红色文化的书写从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叙事转化成新时代“民族精神”的阐释,何加林创作的《老寨新韵》描绘了傈僳族——一个摆脱贫困、焕发新生的古老村寨。作品背后蕴藏了扶贫干部扎根一线开展脱贫攻坚的真实过程,书写了新时代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郭健濂、褚朱炯、井士剑的《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描绘了“农民”教授李保国向人民大众传授剪枝技术的场景,展现了李保国教授“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的精神信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的讲话时所言:“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在观念和手段结合上、内容和形式融合上进行深度创新,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11]只有以此为创作导向,才能凸显中国红色美术创作的时代思想和艺术特色。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美术创作不再过于强调外在的形式构成,更加注重“拥抱时代、关注现实、扎根人民”的内涵性表达,拉近了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使扶贫、脱贫事迹引发共鸣,为时代留下了丰厚的视觉形象和精神印记。
百年中国红色美术创作始终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为主导,坚持形象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进行史实记录。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强调绘画情节与历史情境的再现,无疑都是为了真实有效地叙述历史与事件,而历史与事件的主体则是人物。杨之光的国画《红日照征途》中对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场景表现,陈承齐的油画《迎着曙光》中的群像塑造,都着重展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刻画,深刻揭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伟大真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艺术家创作的《王进喜》《雷锋》等共产党员形象,着重体现了“一心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战洪魔》《抗击非典》等作品均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主导,使画面既有真实存在的现场感,又有超越时空的崇高感。可见,现实主义是艺术表现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真实性、典型性、客观性和人文主义精神,使塑造的红色题材绘画有了独特的审美思想。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现实主义美术在中国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构成了红色美术创作的主体面貌,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百年社会的现实景观。
(二)红色美术创作的艺术价值
红色美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美术,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无论从红色美术的题材、形式还是创作内容上看,百年中国红色美术的发展在艺术内涵、风格形式和语汇图式等方面求变革新,形成了属于新时代审美理念的语言样式。
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美术创作的核心,尽管各种美术思潮间的矛盾和争论并没有完全被“救亡”的呼声所掩盖,但因社会的现实需求,全民抗战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下艺术创作的主要趋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如力群的《饮》、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莫朴的《百团大战》、张仃的《日寇空袭平民区域的赐予》、李可染的《侵略者的炸弹》、唐一禾的《七七的号角》、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吴作人的《重庆大轰炸》等作品,以鲜明的革命主题,在还原战争场景的同时不忘立足于生活实际,形成了中国美术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潮,并由此展开了“中国本土文化”“民族本质”的大讨论,而创作者正是从这种“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中逐步思考本民族美术创作的文化内涵和特质。所以,抗战美术是基于中国革命历史实践的新事物,完成了民族形象的时代构建。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红色美术创作的政治功能看,最能代表当时社会“政治状态”和“民族化”探索的绘画应属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作为“新中国”的政治象征,《开国大典》形象地揭示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派。从画面的构成要素看,毛泽东主席处于领导者的核心位置,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领略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面容,画家有意识地将领导人画得略侧一点,通过红柱子、红灯笼和黄色菊花这些富有民族特色事物的巧妙点缀,与天安门下声势浩大的场面遥相呼应,体现了中国崛起的时代历程。“《开国大典》完成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领导人在中南海集体观赏此画并接见了董希文。”[12]毛泽东看过画后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13]所以,作为新中国形象的象征性表达,它激活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将“油画民族化”的矢志探索与政治思想、历史传承、民族身份和文化诉求融为一体,揭开了新中国美术史册的崭新篇章。
改革开放之初,在红色美术创作上,艺术家重新恢复了对于革命战争题材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受“八五思潮”美术思想运动的影响,反映主流意识的主题性红色美术在整体性绘画创作中的比重相对较少,这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以来,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艺方针主导下,“主旋律”的绘画创作得以凸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七届美展金奖作品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九届美展金奖作品韩硕的《热血》、九届美展金奖作品冷军的《五角星》等等,在创作形式上可以看出艺术家开始回避平铺直叙的描绘或赞扬,他们不再囿于崇高主题的弘扬,而是突破了以往的“纪实性”描绘,强调人文关怀与生命体验,并将个体审美融入对革命历史的叙述中,从而建构出了新型美术形态的内在结构与价值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
从艺术审美属性上看,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人民性”思想的不断增强,新时期的红色美术创作也随之突破了宏大叙事的桎梏,逐步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融合,拓展了红色美术创作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探索。如六届全国美展中的金奖作品——汪建伟的《亲爱的妈妈》,画面中描绘了一位士兵在战壕中给妈妈写信的场景,标题中的“妈妈”既是对家乡母亲的思念,也是对祖国母亲的守护。从艺术形式上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美术创作”中展出的作品,如黄洪涛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构图上以前排一老一少两个战士作为低点,围绕画面两边高点的“小区域”构筑以杨靖宇将军为中心的大的聚焦区域。画家通过光影、时间和人物的内心塑造,衬托出恶劣环境下革命英雄视死如归的信念,是诗性历史的真实捕捉。王君瑞的《红旗渠》对人民群体与环境关系进行多维度延伸,画家有意将两个山体表现成一个“窗口”,从视觉上将蜿蜒山势延伸到远方,为观者营造出丰富的想象空间。而作为媒介的笔墨,吴宪生的《耕者有其田》从艺术语言、形式法则、视觉审美等方面突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羁绊,将现代水墨的构成意识与传统造型相兼容,人物与背景打破共通,创造性地突破了水墨画难以承担大型“主题性”创作的困境,为现代水墨人物画的创作图式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总之,通过以上作品可将艺术家的个体审美融入对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的叙述之中,“以小见大”地刻画出新时代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主题,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红色题材美术创作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实践,其核心思想贯穿了中国现代美术的话语建构,是助推中国主流美术良性发展、传递中国精神的重要载体。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使得红色题材美术创作必须遵循某种方式和准则,那么如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开放,新时期的美术工作者就必须继续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新时期美术创作的逻辑起点与根本价值取向。所以,通过对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和典型场景的艺术再现,进一步挖掘红色美术所彰显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中国人民的高尚品质,从而更好地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形象,这仍是中国美术工作者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