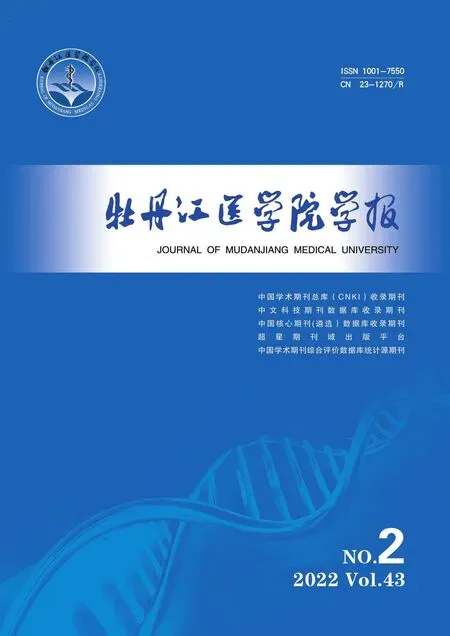超声评估膈肌功能障碍研究进展
陈玉秀,邱思遥,吴 柳,温建立
(遵义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贵州 遵义 563000)
膈肌功能障碍(Diaphragm Dysfunction,DD)是指多种病因导致的单侧或双侧膈肌暂时或永久性的膈肌无力及膈肌瘫痪。临床上DD发病率很高。脓毒症患者DD发生率高达64%,病死率达37%[1]。同时,研究表明机械通气患者通气18~69 h即可导致约50%患者出现膈肌萎缩,需长期通气的患者约80%会发生DD,约20%的机械通气患者存在撤机困难或延迟,患者上机后40%的时间用于撤机[2]。DD会导致患者运动耐力下降、呼吸功能降低、呼吸衰竭,也会致呼吸机依赖、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撤机拔管失败等呼吸机相关并发症发生率升高,增加治疗费用,甚至增加患者病死率。因此,早期识别、诊断DD并及早干预治疗,对于降低相关并发症的发病率及患者死亡率,促进患者康复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评估膈肌功能的传统方法,超声具有无创、无辐射、低风险、操作简易、可重复操作等优点,且进行膈肌检查的超声设备在现有医疗设施中极易获取。对于危重症患者,在床边即可进行检查评估,也不依赖于患者的配合,检查者可快速完成检查。本文就超声在评估膈肌功能障碍中的应用展开综述,以期为临床医生更好进行疾病管理、治疗及随访提供一定思路。
1 膈肌功能障碍的机制及临床现状
DD临床常见病因包括心肺及腹腔脏器损伤、颈椎损伤、神经肌肉病变、感染、机械通气、药物、手术及放射治疗等,肥胖、腹内压增加、年龄、休克、电解质代谢紊乱、代谢性碱中毒、低氧血症等因素则可加重DD[3]。其发病机制涉及众多,且各种机制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对于呼吸机诱导的DD,其主要的发病机制为机械通气会损伤膈肌线粒体损伤致过氧化物、乳酸等有害物质蓄积影响膈肌正常的收缩功能,同时使内质网/肌浆网上的钙通道受体结构发生重塑及功能障碍致膈肌肌浆网Ca2+漏出至胞质,并激活多个信号通路,一方面使膈肌蛋白水解增加,另一方面增加膈肌自噬,从而引起DD的发生[4]。感染如脓毒症导致DD,其发病则与促炎基因上调紧密相关,致使多种促炎细胞因子表达增多,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将会损伤膈肌线粒体,使钙离子利用障碍,最终导致促使膈肌收缩功能发生障碍[5]。X线检查是临床常用评估膈肌功能的检查方法之一,其敏感性高,但特异性只有44%。胸部透视则存在6%假阳性率,且无法检查双侧DD。胸部CT及核磁共振检查虽然可清晰反映膈肌占位性质,但存在辐射大、费用高、场地限制、仪器操作复杂及转运风险等缺点。肌电图具有并发气胸风险。肺功能、呼吸力学指标等检查则十分依赖患者的配合。对于危重症患者,特别是需行机械通气、血流动力学不稳及药物镇静患者,上述检查手段均不适用。
2 超声评估膈肌方法及指标
2.1 超声检查膈肌概述超声能直接对膈肌进行观察及测量,可动态实时反映膈肌运动情况及功能状态。超声评估膈肌是以脾脏作为声学窗,对于双侧DD患者,左右两侧膈肌的厚度及厚度变化无明显差异,且右侧膈肌测量可重复性更高,所以超声评估膈肌运动时以右侧膈肌测量为主。针对单侧DD的患者,则应同时对双侧膈肌功能进行评估。目前,B型及M型超声应用较为广泛。B型超声可较为清晰且真实显示某一时刻膈肌情况,而M型超声可连续且动态反映一定时间内膈肌随时间运动情况。ABCDE法不需依赖肝脾声学窗,具体操作方法是将超声探头放置于腋前线(Anterior axillary line)水平,观察患者呼吸(Breathe)运动时肺滑动情况,而后探头沿尾部(Caudally)滑动,识别胸廓下缘与横膈膜贴合部位,即膈肌ZOA区,从肋间隙中快速寻找膈肌(Diaphragm)进行测量检查(Examination),有助于提高检查成功率[6]。
2.2 超声监测评估膈肌功能常用指标超声监测评估膈肌功能常用指标包括膈肌厚度、膈肌增厚率、膈肌移动度、膈肌动度浅快呼吸指数、膈肌收缩速度等。膈肌厚度可反应膈肌萎缩情况及收缩能力,测量方法为B型超声模式下,选择右侧腋前线或腋中线8~10肋间,当超声束与膈肌测量部位垂直,选取图像清晰部位进行测量即可,在此基础上选定测量线改为M型超声模式下,即可动态观测膈肌厚度随呼吸变化情况。膈肌增厚率被认为是一项比膈肌厚度更敏感的指标,是在M型超声模式下,对一个呼吸周期内平静呼气末与最大吸气末膈肌厚度进行测量,通过计算公式[(最大吸气末厚度-平静呼气末厚度)/平静呼气末厚度×100%]得出。膈肌厚度及增厚率是诊断DD的两项重要超声测量指标。临床上通过对健康受试者进行超声测量膈肌厚度及增厚率,目前认为,静息状态下,正常人群的膈肌厚度为0.22 cm~0.28 cm,女性下限值为0.12 cm,男性下限值为0.13 cm[7],膈肌增厚率为28%~96%,当膈肌呼气末厚度小于0.2 cm或膈肌增厚率小于20%即可诊断DD[8]。膈肌移动度可反应吸气时膈肌力量,测量方法为在B型超声模式下,选择腋前线和锁骨中线间低位肋骨下缘部位,当超声束垂直于膈肌时,见一条高回声膈肌亮线,改为M型超声模式,选取测量线,记录膈肌运动轨迹,测量基线至曲线最高点的垂直距离。平静呼吸下,正常成年女性膈肌移动值约1.6 cm,男性约1.8 cm,深呼吸情况下,女性膈肌移动度约为5.7 cm,男性约为7.0 cm[9]。膈肌浅快呼吸指数是2016年由Savino Spadaro等人将膈肌移动度联合浅快呼吸指数建立的新指标,其计算公式为自主呼吸试验期间患者的呼吸频率/膈肌移动度[10]。膈肌收缩速度也是反应膈肌肌力的一项重要指标,计算方式为膈肌移动度/吸气时间。Soilemezi E等人分别在安静状态下、佩戴鼻夹及口罩、给与呼吸阻力负荷三种情况下,应用超声测量正常人膈肌收缩速度,结果分别为(1.3±0.4)cm/s、(1.2±0.3)cm/s、(0.8±0.3)cm/s[11]。
3 超声评估膈肌功能障碍的临床应用
3.1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致DD中的应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不可逆的气流受限且呈进行性发展的常见慢性肺部疾病。长期气流受限、全身炎症引起的肌病以及过度充气均可导致DD。同时氧化应激、肌肉萎缩、蛋白质合成减少和膈肌细胞凋亡增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2]。Kazuki Okura等人应用超声分别对38例男性COPD患者、15例健康青年及15例健康老年男性志愿者肺总量、功能余气量和余气量时的膈肌厚度,并计算肺总量及余气量时的膈肌增厚率。结果发现测定COPD患者肺总量时的膈肌厚度及膈肌增厚率明显低于健康成人,且测值与年龄的增长无关[13]。在对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研究中,应用超声分别测量病情加重和症状改善后72 h内的膈肌移动度及膈肌增厚率作为膈肌功能指标。结果发现膈肌增厚率由(80.1±104.9)mm增加到(159.5±224.6)mm。膈肌移动度无明显变化,这可能是由于膈肌移动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患者的自主呼吸,如呼吸频率和气道阻塞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膈肌移动度。但膈肌移动度的变化与患者恢复时间呈负相关,与患者下一次再发加重间隔时间则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膈肌移动度改善较多的患者病情恢复所需时间较短,且下一次再发加重之前有较长的稳定期,因此,COPD患者恢复期膈肌移动度改善情况差可能是患者病情频繁恶化的重要标志。也说明了膈肌变化情况与COPD病情是否加重紧密相关[14]。对于COPD稳定期患者,Evrin发现膈肌移动度与FEV1呈高度正相关,认为膈肌超声可能有助于临床评估COPD稳定期患者病情严重程度[12]。
3.2 在神经肌肉疾病致DD中的应用神经肌肉疾病(Neuromuscular Disorders,NMD)如糖原贮积病Ⅱ型、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等常累及膈肌,对膈肌功能进行评估与监测是十分必要的。Boon等人应用超声对66名患者,共131个半侧膈肌,进行膈肌功能评估,发现在82个异常的半侧膈肌中,76个出现异常的超声表现,如膈肌萎缩或收缩能力降低,49个正常膈肌中则未发现假阳性结果,膈肌超声诊断膈神经病变的敏感性为93%,特异性为100%[15]。Abdallah等人将89例NMD患者和27名健康受试者进行对比发现用力吸气时超声时的膈肌活动度与鼻内压显著相关,并能准确预测FVC<60%,ROC曲线下面积为0.93[16]。此外,NMD患者的平静吸气和深呼吸时的膈肌活动度也低于健康对照组。研究发现,NMD患者的膈肌厚度及膈肌增厚率也低于正常人[17]。在高度脊髓损伤和神经病变的患者中,超声可能也是诊断DD的有用工具。呼吸肌无力引起呼吸衰竭是ALS患者常见死亡原因之一。研究发现许多ALS患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膈肌组织学改变,如肌肉萎缩和重塑,但相关呼吸损害指标改变则较为轻微,表明ALS患者肺活量、最大吸气压、跨膈压等数值大小与膈肌萎缩程度无关,常规呼吸指标并不能很好地预测膈肌功能的变化[18]。目前,众多对比ALS患者和正常受试者膈肌厚度、膈肌增厚率的实验中均发现,ALS患者的膈肌厚度及膈肌增厚率低于正常人,说明ALS患者膈肌明显萎缩,膈肌收缩力明显减弱。且膈肌厚度与ALS患者肺活量呈正相关,当患者深吸气时,膈肌厚度与最大呼气压、用力肺活量相关。膈肌厚度、膈肌增厚率则与二氧化碳分压呈负相关,特别是当膈肌增厚率≤1.39可被预示着ALS患者存在严重高碳酸血症情况。此外,膈肌移动度可用来预测ALS患者肺功能受损严重情况,其敏感性为100%,特异性为69%[19]。同时超声对膈肌的动态观察还可能有助于早期识别需要进行无创机械通气的ALS患者,从而提高患者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3.3 在危重症中的应用脑卒中作为当下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危重疾病之一,具有极高的发病率、致残率和致死率。卒中患者偏瘫侧膈肌常伴有DD,膈肌移动度及膈肌增厚率较对侧显著减少,右侧偏瘫患者甚至可能出现两侧的膈肌移动度减少。相关实验表明,膈肌移动度及膈肌增厚率与用力肺活量呈显著正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卒中患者呼吸功能[20]。因此,超声评估卒中患者膈肌情况,对指导制定卒中患者呼吸功能康复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ICU机械通气患者,目前超声用于评估膈肌功能,帮助预测机械通气患者撤机情况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早期临床上用于预测撤机的最常用的指标是浅快呼吸指数(RSBI),有研究表明,膈肌增厚率对于撤机时机和撤机结果的预测具有指导作用,而且较传统的预测指标(RSBI)诊断价值更高。同时,膈肌移动度对预判患者撤机成功与否,也具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当机械通气患者膈肌移动度>25 mm时或膈肌增厚率>30%~36%,自主呼吸试验(SBT)成功的可能性更大[21]。此外,超声还可通过监测膈肌厚度及膈肌增厚率变化情况判定机械通气患者人机是否同步,从而指导呼吸机参数调整。
3.4 在创伤致DD中的应用对于创伤患者,DD、膈神经损伤、膈肌破裂很难早期识别,常延误诊治。闭合性腹部外伤和合并膈肌破裂患者,床旁行膈肌超声检查,可见膈肌异常运动及膈肌不随呼吸运动表现。对于胸腹穿透伤患者,常用创伤重点超声评估法检测膈肌情况与腹腔镜结果相比,并不十分有效,而超声诊断的特异性可达100%,但敏感性较低,仅为50%[22]。
4 超声追踪斑点成像技术与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
超声追踪斑点成像技术(Speckle Tracking Imaging, STI)通过利用高分辨率二维图像连续追踪斑点标记,重建运动轨迹,定量定性反映组织运动速度、应变、应变速率等,多应用于评估心脏功能情况,同时也可以用于评估膈肌功能。在不同强度的吸气肌阈值负荷下,通过STI测量受试者膈肌的应变和应变速率,发现两者与跨膈压和膈肌电活动高度相关,且对于膈肌收缩力评估更为优越[23]。同时,相较于普通M型超声,STI能可靠地显示和测量左侧膈肌,还能全面准确的反映在膈肌的移动轨迹,而不仅局限于单一方向,由此推测,STI或可成为一种更有用、可靠的超声评估膈肌运动的方法。
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Shear Wave Elastography, SWE)是通过探头使声束连续聚焦于组织,同时产生横向剪切波,剪切波的速度可反映组织的弹性和肌力情况。通过对比正常受试者与COPD患者SWE测定和肺功能检查结果,发现SWE可作为定量评价COPD患者膈肌功能的有效检查手段,有助于随访监测COPD患者膈肌功能变化情况,指导患者个性化管理[24]。Fosse等人则应用SWE测定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剪切模量发现其与跨膈压的变化显著相关,SWE或许可替代跨膈压测定用于评估机械通气患者膈肌功能情况[25]。
5 不足与小结
相较于目前临床常用评估DD的检查方法,超声具有便捷、快速、有效、费用低廉等显著优势,但仍具有一定局限性。对左侧膈肌进行评估时,由于吸气时肺肠下移影响,检查则较为困难。此外,超声评估DD的准确程度,一方面依赖于检查者的操作水平高低,尽管重复训练可以提高准确性,但国内尚缺乏此方向培训课程及方法的研究;另一方面在临床实际操作中,常受限于患者体位、探头分辨率等因素影响,且临床对膈肌重视不足,膈肌损伤相关研究较为欠缺,缺乏较为统一的标准。未来关于超声技术有待进一步研究,超声追踪斑点成像技术及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或许能更好的协助评估膈肌功能,令超声在诊断膈肌疾病、监测膈肌功能以及促进膈肌康复等方面的应用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