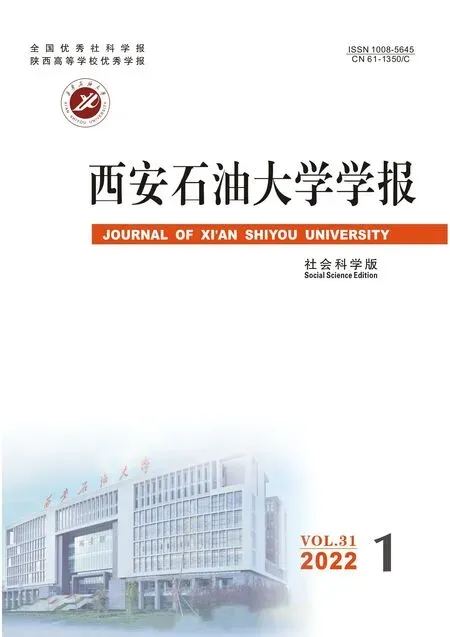“太和所谓道”:论张载理学中太和、太虚与气之关系
李东升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0 引 言
张载作为北宋五子之一,是宋代理学“濂关洛闽”中关学的创始人,其理学思想规模宏大、极富原创性,为宋明理学之规模奠定了基础,也对洛学与闽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因而张载又是宋明理学实际上的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学科和中国哲学史的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受此影响,中国哲学史家开始以西方哲学体系来为中国哲学撰写哲学史,宋明理学自然是中国哲学史撰写当中的重中之重。张载作为最为重要的理学家之一,必然会进入哲学史家的视野,这也正式拉开了张载理学哲学化的序幕。所谓的理学哲学化,实质上是宋明理学被研究者西方哲学化,即以西方哲学的体系和思维方法对理学进行重新梳理和研究。这样虽有利于中国哲学学科和中国哲学史的建立,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打开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促进了中西方哲学的积极互动,但是,将理学西方哲学化却存在无法规避的缺陷。宋明理学本是儒家在三教合流思潮下诞生出来的新儒学,宋明理学体现着传统儒家士大夫对宇宙、社会、人生、政治、道德等领域特殊的时代认知,理学的构建过程也内蕴着理学家独特的思维范式,将理学哲学化则必然有着解构理学的理论危机。对张载理学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就成果颇丰,但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走上了将张载理学西方哲学化的道路,这就使西化的研究模式对张载理学研究形成一定程度的遮蔽,尤其是在张载理学体用论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不自觉地将西方本体论思想代入张载理学研究中,造成了对张载理学定位的认知分歧。张载建构其学尤为强调“体用不二”,辨析张载理学的本体,就必须回归中国哲学体用论的研究范式。
1 “体用不二”意义上的张载理学研究范式
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又可称作存在论,其代表着对事物本身的根本性存在进行哲学思辨,本源性的存在是现象世界存在的根本依据,与人伦道德并无关涉,人只能通过理性对本体进行对象化的直观与把握。宋明理学,尤其是张载关学中的“体”,并非脱离现实世界而独自存在,且讲“体”的最终目的也并非为世界存在寻找本源性根据,而是时刻以“体”关照人世,因而“体”实际上是指本质性的理与道。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家都承认本根不离事物。西洋哲学中常认为本根在现象背后,现象现而不实,本根实而不现,现象与本体是相对立的两世界……在中国哲学,本根与事物的关系,不是背后的实在与表面的假象之关系,而是源流根枝之关系。”[1]48-49熊十力也指出:“从来谈本体真常者,好似本体自身就是一个恒常的物事。此种想法,即以为宇宙有不变者为万变不居者之所依。如此,则体用自成二片,佛家显有此失……非离变动不居之现象而别有真常之境可名本体。”[2]12在宋明理学当中,凡讲体用,最终必然要落脚于人之主体,不存在与主体并无关涉的“体”,也不存在脱离主体的“用”。“体”贯通于“用”之中,“用”是“体”由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外在化彰显,无“体”自然不必言“用”,“体”是最本质的理或道,为形而上者,位居与人相对的天道层面,“用”是经验性的人的活动,“用”亦是对人而言,是具体的、实在的、经验的。
张载作为宋明理学的造道者,其关注的重心在于建立儒家天道性命体系,以回应佛老对儒家的批判,因而张载的体用论必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路进行理解分析,其哲学中的“体”并非宇宙或客观事物存在的本体,而是时刻与人的道德性命息息相关的本质之理,唯有以天人相贯通的理,才能建立起儒家道德性命之学,才能将天与人、体与用、本与末、有与无真正统合起来。张载造道的目的并非是要为11世纪的儒学建立新的世界观,而是要以宇宙生成之本根为人之道德性命建立形而上依据。在张载理学中,天道论在体系层次高于道德性命之学,天道是性之本,性为天道所赋而人所秉受,这是继承《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思想,天道论由上而下贯通道德性命之学,为道德性命之学建立形而上的天道根据;但就张载造道的精神和整个宋明理学价值而言,道德性命之学为本,而天道论为末,天道论只是构建道德性命之学的手段,建立天道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为道德性命之学建立形而上的依据,使得儒家道德性命之学能贯彻天人,彻上彻下。张载及其他理学家的目的并非要探索宇宙的生成方式,也并非要构建某种唯物或唯心的世界观,理学家创建理学就是要重新挺立儒家道学,在内圣之学的基础上建立外王的事业,为人何以为人、人何以成圣确定指向,在这个意义上来讲,道德性命之学是本,天道论才是末。明白了这一理学建构的大前提,才能真正进入张载理学“体用不二”的思维范式,才能对张载天道论和道德性命之学有一个真正清晰的把握。
20世纪以来,对张载哲学本体论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以张岱年为代表的“气本”论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虚本”论。张岱年在其1937年完成的著作《中国哲学大纲》中提出:“张子认为气是最根本的,气即是道,非别有道。宇宙一切皆是气,更没有外在于气的;气自本自根,更没有为气之本的。”[1]76在张岱年看来,“太虚无形,气之本体”[3]7并非指太虚为气之本体,此处的“本体”是指“本者本来,体者恒常”[1]77,这就将太虚理解为气的本然状态,太虚实质仍是气。因而张岱年认为,张载所谓的“太虚即气”就是指“万物只是气,气只是太虚。太虚乃气之本然,并非由太虚而生出气”[1]78,但将太虚作为气的本然状态,则太虚就成了气,其实质是彻底否定“虚”的存在。张载在《正蒙》中讲:“太虚不能无气”[3]7,“合虚与气,有性之名”[3]9,明显是将太虚与气作为两个不同质的存在而言,若太虚就是气、虚气同质,自然就不会出现二者离与不离、合与不合的思考。“太虚即气”关键在于对“即”的理解,此处“即”并非“是”的意思,而是相即相生之意,因而“虚气相即”实质就是虚气相即不离,在此意义上才可言“体用不二”。张岱年将张载理学定位为“气本”论,而太虚、太极、太和均不过是气的不同状态,如此则只能说明宇宙之生成,而张载苦心要构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宇宙论,他所追求的是要在辟佛老的过程中构建起儒家的天道性命体系,如只是将张载理学本体定位为“气”,即使是就理学体用论来讲“气本”,则气既要为体,又要为用,既要生化宇宙万物,又要主宰人的道德性命,天道不过是气化自然流行,并无一点道德价值,如此则人性并无向上提振之形而上根据,变化气质也不过是在气之清浊间用功。《张载传》也认为张载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3]386,“气本”论与《中庸》《孟子》所讲的“天命之谓性”与“尽心、知性、知天”均格格不入,将张载理学定位为“气本”论,不符合张载本人的造道精神。
牟宗三强烈反对将张载理学定位为“气本”论,他提出:“横渠以天道性命相贯通为其思参造化之重点,此实正宗之儒家思想,绝不可视为唯气论者。”[4]375牟宗三清晰地把握住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大前提,而强烈反对“气本”论,因为气无法承担理学家构建天道性命体系的重任,因而才坚持“太虚神体”。但牟宗三又认为:“‘太和’固是总持地说,亦是现象学地描述地说。而其所以然之超越之体,由之可以说太和,由太和而可以说道者,则在太虚之神也”[4]376,“太虚是由分解而立者,一方既是与气为对立,一方又定住太和之所以为和,道之所以为创生之真几”[4]380。诚然,太虚可以将人世道德向上提振,太虚当为气之本体,但这只是在天道下贯至道德性命之中时,才可有此价值判断。直接以太虚为太和之所以为太和之本,以“太虚神体”为宇宙生成之动机,则又落入在宇宙论层面强分虚气之高下的西方本体论思维之中,使其所诠释的张载理学陷入体用殊绝的境地。
张载“太虚即气”是虚气相即不离,以工夫修养层面言之,人应变化气质,摆脱气质之性的遮蔽而迈向天地之性,此时太虚与气在心性论层面的价值判断下才有体用之别,精神境界与道德价值也有高下之分,而并非太虚与气在宇宙生成领域就有高下之判,正如粮食与营养的关系,人不可能只要营养(理)而不要作为营养载体的粮食(气)。从“体用不二”的思维范式来看张载理学,“虚”能赋予人天地之性,具备将人世道德向上提振的作用,气流行到人性之中造就了气质之性,“太虚即气”既是说明宇宙生成领域必然是太虚与气相即不离、互化互资才能生化流行,又为道德性命之学提供天道论的形而上支撑,“太虚即气”彻上彻下、贯通天道性命,才会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因而张载能提出“太虚即气”本身就是“体用不二”思维下的理论成果。
2 从《语录》到《正蒙》的虚气关系转变
张载理学规模宏大、自成一家,但张载本人为学之经历却有一个日益久、学益明的过程。依弟子吕大临所作《横渠先生行状》记载:范仲淹劝张载读《中庸》,“虽爱之,犹未以为足也,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求之六经。”[3]381由此可见,张载早年就已有出入佛老、返诸六经的为学经历。张载三十七岁左右时,在京城与二程兄弟共论道学之要后,才涣然自信,坚定了为理学造道的志向,尽弃佛老之异学(1)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记载:嘉佑初,张载在京师见二程,共语道学之要,其后二程门人就此认为张载是受二程指点才明道学,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也认为张载之学虽自成一家,其源实由二程所发。然《行状》所载,张载见二程是作为道学同道共论“道学之要”,张载此后坚定了吾道自足的认识,尽弃佛老。程颢曾评价此次讲论:“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可见程颢也并不认为此次讲论只是自己启发张载,否则便不可能有此叹。因而两方是互启互发、引为同道的。。程颐评价张载道:“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而时有之。”[5]596张载是否“无宽裕温厚之气”与“意屡偏而言多窒”尚有可争议之处,但程颐对张载“苦心极力”和“考索之此”的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张载本人自道其为学经历:“某学来三十年,自来作文字说义理无限,其有是者皆只是亿则屡中”[3]288,“某向时谩说以为已成,今观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门庭,知圣人可以学而至”[3]289,“某观《中庸》义二十年,每观每有义,已长得一格。六经循环,年欲一观”[3]277,可见张载也自认其学问长进有次序,而并非生而知之者。综上,张载之为学明显有一个循序渐进、由博返约的过程,因而对张载理学的分析,应首先厘清张载现存文本中的思想承继关系,若不认清张载的为学次第,则必然导致对张载理学思想的认知错位。
林乐昌教授就认为张载为学大致可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前期阶段以张载二十一岁读《中庸》为起点,此阶段张载进行了思想探索,奠定了理学基础;中期为张载思想的形成期,大约从张载四十岁到五十岁的十年间;后期为张载思想的成熟期,大约从五十岁到去世前的七八年间。[6]525-528以张载思想三个阶段的划分,考察今存的张载主要文本,《横渠易说》当为张载早期的经说,体现着张载对《周易》思想的汲取,为日后构建理学体系奠定了学术基础;《张子语录》和《经学理窟》是张载思想中期以及开始转向晚期时的作品,记录了张载从虚气关系、变化气质、知礼成性等方面对儒家道德性命之学的探索;《正蒙》是张载晚年俯读仰思、苦心编撰以传其学的作品,当为张载理学思想之定论无疑。张载作为理学的造道者,必然要经历一个思愈精、理愈明的过程,虽然张载思想有着早期、中期和晚期的界限,但并不意味着三个阶段的思想之间并无承继关系,更不意味着张载思想的转向就是对之前思想的全部扬弃,因而张载理学思想有得于早而历久不变者、有理渐明者、有晚年而新出者。
分析《横渠易说》思想,张载凡于《易说》中讲宇宙论都是以“太极”为宇宙生成之本根,基本是对《周易》文本思想的阐释和发展。所论“太和”,也只是对《周易·乾·彖》中“保合太和,乃利贞”一句的解释,与《正蒙·太和》篇所讲“太和”相去甚远。关于《横渠易说》中的“太虚”,据刘泉博士考证,“在《横渠易说》中,张载对‘太虚’的表述很少,且多在‘时空义’的层面来使用,并未有更多诠释。”[7]101《横渠易说》不从虚气角度言宇宙之生成,讲“太和”也只就《易传》本义说“太和”,并未从“太虚即气”的角度说“太和”。张载三十七岁入京,坐虎皮椅讲《周易》,《横渠易说》大致应当是这一时期的著作,可视为张载早期的思想成果。明人汪伟曾为《经学理窟》作序,汪伟认为:“所谓文集语录及诸经说等,皆出于门人之所纂集。若理窟者,亦分类语录之类耳,言有详略,记者非一手也”[3]247,观《经学理窟》虽有篇名,实是门人弟子将张载平日散论分门别类,编辑而成,因而也可视为按照主题分类整理的语录。《张子语录》和《经学理窟》都是门人弟子整理张载讲学论道的话语编辑而成的,古人记载语录并不在每条之后记录时间,因而无法对语录逐条区分具体时间和思想阶段,但可以根据文本所录事件追本溯源,以及对文本所表述的思想进行分析,由此可基本确定文本所体现的思想阶段。《经学理窟·自道》篇有“某学来三十年”[3]289与“某既闻居横渠说此理”[3]290两句,表明大致是张载在50岁后归郿讲学时的语录,《经学理窟·义理》又说:“某观《中庸》义二十年”[3]277,此句当为张载四十出头时的语录。《经学理窟》的内容主要可总结为:诸经注说、井田制、变化气质、道学义理、为学之要、自道为学和礼制历法等,《经学理窟》仅有几处言及太虚与气,也只是在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层面说起,全篇未曾提及“太虚即气”。综合文本中出现的时间点和对思想内容的考察,可知《经学理窟》基本是在张载思想中期及向晚期转变时的作品。今存《张子语录》共有五卷,其中只有三卷记载张载本人的语录,后两卷为二程、朱熹评点张载其人其学的语录集。张载本人的三卷语录并无明确指明其大致时间的证据,但为何又将其归为中期或转向晚期的文本呢?这就在于从《语录》到《正蒙》之间,张载有一个对虚气关系认知的巨大转变,这个转变就成为定位、诠释张载理学的关键。
值得关注的是,《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皆未提及“太虚即气”这一《正蒙》中极为重要的观点。“太虚即气”究竟为张载何时提出,就成了分界张载思想真正迈入成熟的标志性时间点。程颐的《答横渠先生书》提到:“观吾叔之见,至正而谨严。如‘虚无即气则虚无’之语,深探远赜,岂后世学者所尝虑及也”[5]596,此处“虚无即气则虚无”当为张载后在《太和》中所讲的“知太虚即气则无无”[3]8。张载认识到“太虚即气”正可根治佛老“恍惚梦幻”“有生于无”之病,才写信给二程兄弟论学,因而程颐回复此信当是张载提出“太虚即气”不久,张载、程颐这次论学的时间则是张载思想走向成熟期的标志性节点。程颐《再答》中说:“况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师,相见且请熟议,异日当请闻之”[5]596,据张波所著《张载年谱》考证:“熙宁二年,张载在被外支治明州狱案之前与程颢均在京城,符合程颐再答所说‘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师’的情况”[8]62,因而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当在熙宁二年(1069年),此时张载正好五十岁。《张子语录》集中在第二卷语及虚气,却未说“太虚即气”,《张子语录》中记载,“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3]324,“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3]325,“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3]326,此处所呈现的太虚与气是一种生成和被生成的关系,天地、万物与人皆出自太虚,太虚才为永恒不灭之至实,明确指出太虚生气,气复归于太虚,从宇宙生成的层面而言,太虚就是宇宙生成的本根。《语录》中明显以“虚”为宇宙之起源和本根,张载正是认识到“太虚”贯通天道性命以及向上提振人伦道德的特殊作用,才以太虚为天之实,并将太虚作为宇宙生成之本根,对宇宙生成模式的构建,其实质目的还是为了完善儒家道德性命体系。张载晚年著《正蒙》,有感于若言“天地从虚中来”则会有“有生于无”之弊病,故转向“太虚即气”,太虚与气不离不分,言太虚则气必随之,无离气之太虚,亦无离太虚之气。在《太和》篇,张载坚定地反对以虚气相分的方式理解宇宙生成,“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3]8张载认为,若言太虚能生气,且太虚无穷、气有限,则必然会陷入道家“有生于无”和释家“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体用殊绝境地;而气与虚相即不离,虚气相为依凭,正为对治释老体用殊绝之病而发。“知太虚即气,则无无”[3]8,“太虚即气”才是有无混一、体用不二之至理。在《正蒙》中,太虚与气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而是太虚为散殊而可象之气提供聚散之场域,二者为相即不离的关系。太虚与气皆是无限,宇宙生成过程当中虚气不可分离,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依旧坚持了太虚至实不亡的观点,这是因为太虚本身寂静不动,而气有聚有散,循环往复未曾止息,因而从二者的表相来看,太虚至实而不亡,太虚下贯的道德性命领域所体现的天地之性也自然是“死之不亡者”,而作为万物生成质料的气却不能没有聚散的特征,由其所生之气质之性才有了变化气质的可能。
张载晚年认识到,若言太虚生天地,则不免有“有生于无”之病,因而才在《正蒙》专讲一个“太虚即气”,太虚与气相即不离,虚不能凭空生气,气亦是自在存在者,若强行区分高下,则陷入了体用殊绝之弊病。张载出于对佛老弊病的深刻认识,而从“虚生天地”转向了“太虚即气”,但张载并非为了与佛老相区别而进行了天道观的转向,而是为从根本上打通天道性心之间的关系,建立体用不二的圆融理学体系。
3 “一两”之道——太和、太虚与气之关系
《正蒙》开篇即言:“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3]7“太和”本出自《周易·乾·彖》:“保合大和,乃利贞”,此处张载在《周易》的原义上赋予太和“道”的地位,丁为祥教授就认为“‘太和’即是张载借取《易传》的概念,通过另赋新义的方式,为其体系所设定的逻辑起点”[9]48。
“太和”究竟是何含义,张载并未对其做出直接的解释。《说文解字注》载:“后世凡言大而形容未尽,则作太”[10]565,“太”本身就有极致、至大、始源的意思,“和”是相对于“同”或“一”而言的,唯有“不同”、有“多”,才可言“和”,若是“同”和“一”则自然不必言“和”。“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浮沉、升降、动静、相感,皆是气化过程中的状态,絪缊、相荡、胜负、屈伸,则是气化过程表现出的性质,因而太和之道就是气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道。但不可认为太和之道就只是针对气而言,气不可能离太虚而有气化,气化之道也不可认为气能独自生化流行而成道,张载所讲之太和就是太虚与气相合,太和之道也就是“太虚即气”之道。“太虚即气”是张载为防止体用殊绝的理论弊病而提出,为何又要在太虚与气之前再另置太和这一概念?而且将《太和》作为《正蒙》之首篇,开篇即言“太和所谓道”,“太和”究竟在张载晚年思想中占据何种地位?
张载早年就在《横渠易说》当中提出了“一两”之道,“若一则有两,有两亦一在,无两亦一在,然无两则安用一地。”[3]233“一”只要存在就必然会有“两”,若无“两”,“一”的实体虽然也存在,却不可能出现“一”的概念,“一”必然是相对于“两”或“多”时才能出现的概念。而“两”在或不在,“一”都必然存在,但若无“两”,“一”就无法彰显出它的作用来,因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3]9。若无“两”,则“一”就是没有对立,无法分化,没有运动的僵死的“一”;若只有“两”而没有“一”,则会出现张载所批判的“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3]8的境地,世界分裂破碎没有统一性可言。《横渠易说》中的“一两”之道最初是针对太极而言,太极为“一”,阴阳二气为“两”,“一无两体者,气也”[3]233,“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3]233,“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3]233,在《横渠易说》中,太极与阴阳二气体现着“一两”之道,太极是阴阳的总体性概念,但只有太极则无法诠释宇宙生化流行,一阴一阳方谓道,阴阳交际才可化生万物,这种思维模式被张载同样运用到了《正蒙》当中以阐释太和、太虚与气。
“一”为太和,“两”为虚气,言虚气则有分、有两,虚气相即则宇宙才有生机,可生化流行成就天地万物。无论“两”在不在,“一”都必然存在,但独自存在的“一”只是僵死的本根,并不能生化流行、孕育万物,当“一”分解为“两”时,宇宙生化才有了最初的动机,才能够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太和虽然在张载晚年思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张载在《正蒙》当中却极少言太和,往往是从太虚与气的角度说宇宙生成与道德性命,这是因为太和作为“一”并不具有直接演化世界和赋予人道德性命根据的能力,当太和分解为相即不离的太虚与气时,既时时内蕴太和本根的实然存在,又能构建宇宙生成和天道性命的体系。
在宇宙生成领域只能说“太虚即气”,也就是“太和”,虚不能独立于气而存在,实因虚、气皆是“太和”一物之两体,太和生发出太虚与气来,虚气相即又演化万物,既展现了宇宙生成的过程,又下贯到道德性命之中。
《太和》篇讲“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3]9,太虚乃天之实,由气化而彰显天之道,气化并非只有气,是虚气相即相资的结果。“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实质上就是“由太和,有性之名”,张载以《中庸》为体,《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张载对“性”的认识相较《中庸》有所不同。因为“太虚即气”不仅是宇宙论的概念,还与道德性命相贯通,太虚与气下贯到道德性命之中,为人所秉受,人所秉之性必有清浊,太虚下贯至性则为天地之性,气流行于性则为气质之性。天所命之性,必为善性,故孟子道性善,然虚与气杂糅不离,合二者而成太和。太虚与气合,方有性,性就是太和在人身上的彰显,因而“合虚与气,有性之名”之“性”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合。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并非水火不容,常人之性中皆内涵两种性,只是二者或多或少之别,变化气质就是要将气质之性从人身上格去,转化为天地之性,这就是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工夫。太虚具有湛一清通之特征,且太虚就是天之实,因而太虚代表着天地之性的最高来源,且太虚具有将人伦道德向上提振的作用。太虚下贯至性则为天地之性,天地之性为天人相通提供理论基础,天人合一实质上也是天人合德。气流行于性则为气质之性,而气虽也有清浊之分,但气基本上只能对人的德性起到阻碍,虚与气合而有“性”,因而此“性”是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合一之性,这就决定了人一出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气质之性的影响,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共同扎根于人性之中,成圣的工夫就是要变化气质,在日常工夫当中扬弃气质之性,以达到天地之性的境界。此时虚为体,气为用,这是中国哲学体用论意义上的主从关系、本末关系,而非西方本体论哲学现象与存在的关系,宋明理学讲的体用一定不脱离作为主体的人,虚体气用也专指道德性命领域,而非宇宙生成领域。
太和为太虚与气和合而成,“太和所谓道”即是天道。太虚与气并不能独自存在,“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3]7,虚气相即共同作用而生化流行,张载以虚气相即、体用不二的天道性命体系,消解了佛老体用殊绝之弊病。张载所言“太虚即气”,太虚与气不可分离,二者是合而一的关系,若从本体论意义上强调虚本或气本,则都有弊病,且此种强分本体的思维方式,实非中国传统思维范式,宋明理学所讲之“体”不可离“用”,为形而上之理,而非西方本体论所谓的事物本身存在之根源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