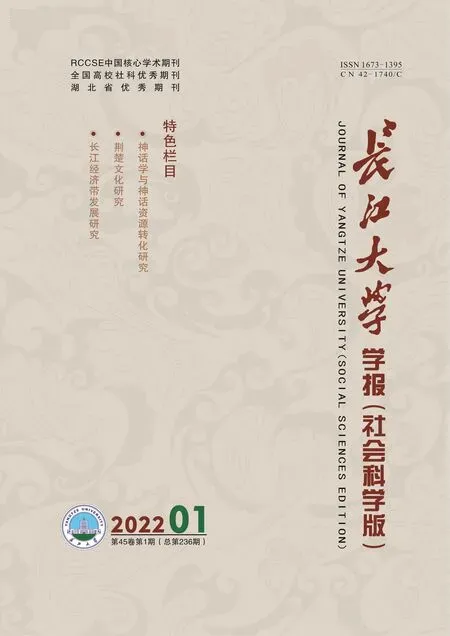多维视域下的诗歌“抒情言志”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诗言志”与“诗缘情”,本为一体,孔颖达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以制六志”即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诗歌的本质特征为抒情言志。作为诗歌初心的抒情言志,不同视阈下有着不同的意味。本文拟就此做一点探讨,以见其有着怎样的演化与发展。
一、口头表达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原始
诗歌抒情言志的表达,经历了从声音到语辞,从笼统到明确的过程。语言产生之前,人类以声音抒情言志,《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感于物而动”的是“声”而不是“言”。《吕氏春秋·音初》:“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于心则荡乎音,音成于外而化乎内。”[1](P49)“感于心”而出者为“音”。《吕氏春秋·淫辞》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1](P159)《淮南子·道应训》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些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2](P279)“舆謣”“些许”就是如此的“音”或“声”。这些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杭育杭育”。其《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3](P513)
因“感于物而动”发出的“声”“音”,是诗歌的前身,《毛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它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即“感于物而动”发声即“发言为诗”,这是语言产生以后的情况;但《毛诗序》随后又补充说“情发于声”,这是说“发言为诗”的“声”,“言”也是一种“声”。
诗歌的初始状态是从声音到语辞,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论《离骚》:“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4](P2482)情志抒发之至,就是呼天喊地,呼唤父母,这也是最早的诗。从呼天喊地,呼唤父母,也就可以判断出某人情感抒发的强烈。《庄子·大宗师》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5](P285~286)从子桑的鼓琴而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得出其霖雨饿病之中的悲痛之情志。
诗歌的初始状态,声音与语辞相互配合而成,《吕氏春秋·音初》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1](P48)“候人兮猗”作为南音之始,语气声音词与语辞俱存。于是,“发言为诗”还须有单纯的“音”或“声”介入,“候人”的抒情言志还须“兮猗”之类的语气词介入。早期的诗歌大都是如此,如《五子歌》的“呜呼曷归”,《战国策·楚策》载书后“赋”曰有“呜呼上天,曷惟其同”的“呜呼”,以及诗歌常规运用的“兮”等“音”或“声”。而后世的诗歌发生,或亦先为发声发音,《汉书·杨恽传》载其自叙诗歌创作:“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6](P2896)他是“而呼‘乌乌’”才创作“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的诗歌。到唐代,李白《蜀道难》起首就以“噫吁嚱”与“发言为诗”相互配合来抒情言志。
语气声音词与语辞相互配合的诗歌的抒情言志,充分说明诗歌原始是一种口头表达的影响力;那么,怎样令口头表达更精彩一些?《毛诗序》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诗歌表达主动地寻求歌舞相配。古代文论史上最经典的一段话,是《尚书·尧典》所记载的:“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就是讲诗的抒情言志应该是合乐合舞的,从诗的原始以来就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1](P43)诗的抒情言志应该是合乐合舞的,可以是合乐合舞的,如汉代刘邦过沛,“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4](P389)。汉代楚歌的演唱多有舞蹈伴随。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有乐府一类,就是重在合乐的。唐宋起有词,元代起曲的盛行,亦是如此。至今的诗歌,也有合乐合舞者,目的就是当“言之不足”时令抒情言志更精彩一些,更强烈一点。
钟嵘《诗品序》说:“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这是说诗歌有着口头表达的渊源而重歌唱,“重音韵”。虽然钟嵘质问曰:“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尽管有些诗是不合乐的,但他还是要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7](P332,340)他强调的是“自然英旨”的“口吻调利”。而更有强调人为音律的,这就是沈约的“四声八病”,“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8](P1779)。就是因为诗歌原始就是口头表达,古代诗歌一直是要求合乎声律,强调“讽读”而追尚“口吻调利”。但是,强调“讽读”而追尚“口吻调利”,并不见得就是诗歌作为诗歌亘古不变的本质,诗歌亦如印刷物上的、网络上的产品,除了音律上“口吻调利”的美感,亦或有视觉上的节奏、美感,那又该有怎样的追求呢?
二、创作方法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强化
诗歌要抒情言志,俗称七情六欲,直抒的也就那么几种,那么,诗歌的抒情言志如何强化?诗歌的抒情言志还需要哪些手段,哪些创作方法?从抒情言志本身来说,最先的抒情言志强化,就是反复抒发,反复吟咏,简单的如《韩诗外传》载《夏人歌》的“乐兮乐兮”,《左传》载《南蒯歌》的“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左传》载《宋城者讴》的“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进而演化为叠句、叠章,如《南风诗》:“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9](P772)《诗经·鹊巢》:“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维鹊有巢,维鸠方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维鹊有巢,维鸠盈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叠章的反复吟咏,是《诗经》作品重要的表现方法,甚或一首诗中又两个叠章组成,如《郑风·丰》。诗歌用多种创作方法以强化抒情言志,此处讲较为原始的几种。
其一,以行为动作强化抒情。《诗经》中,《周南·卷耳》以“采采卷耳,不盈颐筐”以及“置彼周行”的身体动作来表达“嗟我怀人”的思虑之情,《邶风·击鼓》以“执子之手”的身体动作表达“与子偕老”的情感。繁钦《定情诗》把以身体动作表达情感说得很明白,也运用得很充分:“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用什么来表达“拳拳”之情?用身体动作“绾臂双金环”来表达。以下是一连串的如此叙写:“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跳脱;何以结恩情,珮玉缀罗缨;何以结中心,素缕连双针;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何以答欢悦,纨素三条裾;何以结愁悲,白绢双中衣。”《乐府解题》曰:“《定情诗》,汉繁钦所作也。言妇人不能以礼从人,而自相悦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以结绸缪之志,若臂环致拳拳,指环致殷勤,耳珠致区区,香囊致扣扣,跳脱致契阔,佩玉结恩情。”[10](P1076)又称诗中“自以为志而期于山隅、山阳、山西、山北,终而不答”,以情人不至而只有清风吹衣,表达自己的失望。
其二,“赋比兴”的提出。《毛诗序》提出“六义”说,《周礼》提出“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赋、比、兴”是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与诗歌之体的“风、雅、颂”,统称为“义”,可见古代对诗歌创作方法的重视。比、兴手法是借助对他物的吟咏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1](P1,4)郑玄注《周礼·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则是说直接的抒情言志,此所谓“诗之用”。《周南·关雎》首章,郑玄称之为“兴”,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吟咏,以河洲上和鸣的鸟兴起淑女是君子的好配偶,二者相融构成情景画面,既激发读者的联想,又增添了作品的意蕴。《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熹称之为“兴而比”,情思如“江之永矣”,令作品多出一道风景线,令抒情言志的特征更加鲜明突出,令抒情言志更为动人,更为完美。
其三,诗歌创作抒情言志的来龙去脉及其过程。《鄘风·柏舟》首章,先述“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先直抒场景与情人容貌,以下“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的抒情,就是依此而产生的。又如《氓》,第一二节就叙写抒情的由来:“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主人公“泣涕涟涟”与“载笑载言”的情感变化,是由于“氓”的行为而产生的。以下四节“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也罔极,二三其德”,“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都是有事件作为依据与支撑的。作为对比,我们来看《汉书·外戚传上》所载汉武帝的一首诗:“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6](P3952)此处“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为诗,其他为散文所叙,为抒情言志的某些过程尤其是发生原因的叙写。既然散文所叙令诗歌的抒情更为完整,那么为什么不把抒情言志的某些过程或来龙去脉,全在诗歌中表达出来?让诗歌抒情的演进,令抒情的依据、支撑、铺垫、背景都成为诗歌的组成部分,诗歌的抒情则更为完整有力且丰富多彩。《文选》所选诗的“公宴”“祖饯”“游览”“行旅”“军戎”之类,以及《玉台新咏》所录宫体诗,大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就其普遍性而言,抒情言志与事、景、物、史联系起来,诗歌抒情言志通过对事、景、物、史的审美改造,以达到抒情言志的心灵自由与广阔视野,创作方法令诗歌抒情言志的发展有着更广大的前景。
三、人际交流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对象化
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为什么?不仅仅只是因为万事万物“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只是个人化的,内向化的,对自己而言的。诗歌的抒情言志还有外向化的目的,如公共化的“美刺”。“美刺”是要有外向化的对象的,如《诗经》中,《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前者是说抒情言志是面向什么事的,后者是说抒情言志是面向什么人的。这是在追求人际交流。此处专说抒情言志外向化的对象问题。
屈原有首著名的诗作《天问》,“天问”就是“问天”,为什么要“问天”?屈原多自称“世既莫吾知”,《渔父》中屈原自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人世间无人可问,只好“问天”。王逸说,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12](P179,85)。于是可见诗歌对人际交流的渴望。
其实,诗歌本是人际交流的工具,或诗歌本有对话式的,《尚书·益稷》载:
庶尹允谐,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这是虞舜与皋陶君臣会话式的对歌。《左传》宣公二年载以诗歌的对话: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这是城者与在上位者华元的对歌、对话。
诗歌抒情言志,有时要选取特定对象,《诗经》有“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又如曹植《责躬》《献诗》,就是因为“(曹)植尝与杨修、应玚等饮酒,醉走马于司禁门。文帝即位,念其旧事,徙封鄄城侯。后求见帝,帝责之,置西馆,未许朝,故子建献此诗也”[13](P363)。古时所谓“无言不雠”,献给最高统治者的诗可以不用诗作来回复,其他作品一般是有回复的,赠答类诗作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从魏晋赠答诗中可以看到诗人自述以诗对话的情怀。王粲《赠士孙文始》称“无密尔音”,要对方多来信来诗。刘桢《赠五官中郎将》称“望慕结不解,贻尔新诗文”,以赠诗表白自己对友人的爱慕。曹植《赠徐干》称“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指友谊之责任在于真诚勉励,除赠诗之外不再说什么。张华《答何劭》称“是用感嘉贶”而作诗。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中称“形影旷不接,所托声与音;音声日夜阔,何用慰吾心”,把诗歌对话当作抚慰心灵的最好之物。其《赠冯文罴》称“愧无杂佩赠,良讯代兼金。夫子茂远猷,款诚寄惠音”,述说自己赠诗的愿望,并盼对方回赠。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称“发言为诗,俟望好音”,把一赠一答的对话说得很明白。潘尼《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称“昔子忝私,贻我慧兰。今子徂东,何以赠旃”,叙说诗作来往;又称“寸晷惟宝,岂无玙璠。彼美陆生,可与晤言”,认为如此的诗作对话是最为美好的。卢谌《答魏子悌》称“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恨无随侯珠,以酬荆文璧”,对来往赠答对话充满渴望。谢瞻《答灵运》称“忽获《秋霖》唱,怀劳奏所诚。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伊余虽寡慰,殷忧暂为轻。牵率酬嘉藻,长揖愧吾生”,称赏来往诗作的对话抚慰着心灵。谢灵运《酬从弟惠连》称“倾想迟嘉音,果枉济江篇”,又称“犹复惠来章,祗足搅余思”,都是说来往赠答。颜延之《赠王太常》称“属美谢繁辞,遥怀具短札”,寄怀抱于赠诗之中。其《直东宫答郑尚书》说“君子吐芳讯,感物恻余衷”,称自己被赠诗所感动。王僧达《答颜延年》称“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谣吟。栖凤难为条,淑贶非所临。诵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表现了对赠诗的珍重。谢朓《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称“惠而能好我,问以瑶华音”,深深感谢对方赠诗。
当称诗歌“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这是指诗歌创作的公共性;当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是指诗歌创作的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公共性须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歌创作的个人化,则要“写心出中诚”(张华《答何劭》)。当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实现对象化时,则诗歌创作也各有标准。
赠答诗如此抒情言志,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周易·乾》讲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是对知音的寻求。《列子·汤问》载伯牙、钟子期为知音,是以音乐为中介的:“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14](P178)傅玄《何当行》曰:“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诗歌作品把人心联系在一起,人们用诗歌创作来实现人际交流,追求知音。诗歌本来就是人际交流的工具,是面向公共空间的交流,还是针对私密化的交流,不同的面向与针对有着不同的传播方式、表达意味与表达标准,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古代诗歌应该注意的。
四、阐释视阈下的“抒情言志”读者化
诗歌一旦生成,虽然抒情言志之“文”已经定型,但抒情言志之“义”则因读者接受而异,西语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古代则称“断章取义”,称“诗无达诂”。
宋代人朱熹在《诗集传序》里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11](P2)但读者对其却各有阐释,如《诗经》首篇《周南·关雎》,《毛诗》称:“《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鲁诗》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关雎》之人见机而作。”[15](P4)即便是赠答诗,也有对所赠之诗另有理解的情况,如刘琨《重赠卢谌(五言)》,臧荣绪《晋书》曰:“(刘)琨诗托意非常,想张、陈以激(卢)谌;(卢谌)素无奇略,以常词酬琨。”[13](P468)
阐释视阈下的抒情言志,因读者的不同而不同的情况,以《玉台新咏》所录诗最为集中。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对《玉台新咏》与宫体诗之间有这样的评价:“本书中有不少并非宫体诗,只因‘篇中字句有涉闺帏’,虽内容全不相干,也被收录。”[16](P2)如卷一张衡《同声歌》,《玉台新咏》录入,此即为艳诗;但《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称之为君臣之诗:“言妇人自谓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思为莞簟,在下以蔽匡床;衾裯,在上以护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10](P1075)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张衡“仙诗缓歌,雅有新声”,萧涤非认为就是指此诗,“以篇中有天老素女之言也”[17](P107)。或称之为男女交往诗,或视其为“臣子之事君也”,或视其为“仙诗”。又如卷九张衡《四愁诗》,《文选》所录有序,称之为:“时天下渐弊,(张衡)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氛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18](P1356~1357)而《玉台新咏》所录,删去这些文字,《玉台新咏考异》这样解释:“若存本序,则与艳题为不伦,故删去以就此书之例,非遗漏也。”就是因为诗中“皆裾裙脂粉之词,可备艳体之用”[19](124),把它阐释为男女交往之诗。卷九又有《晋惠帝时童谣歌一首》:“邺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乐府诗集》录此童谣,其解题引《晋书》称,此童谣“明年而胡贼石勒、刘羽反”[10](P1243)。那么,此童谣就是“谶语”,读此童谣所谓“观风”,是了解施政得失,预示社会将大乱;而从童谣“篇中字句有涉闺帏”,读出其意义所指在于“闺帏”,则是艳诗集编纂者的阐释。
诗人也知道诗歌之“义”可以由读者来决定,其创作有时就故意为之,以隐蔽的话语不把自己的真实意思明白地表达出来,令作品多义化,一来诗人可以避免表达意见之祸,二来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阐释,或许也会得到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这就是阮籍《咏怀诗》。李善就解释其创作时的想法:“(阮)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13](P419)历代注阮籍《咏怀》者颇多,但对诗中之“象”究竟是哪一个社会历史史实,各自“情测”,争议颇大,各人都引史证之,似各成理。如《咏怀·湛湛长江水》:“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13](P424)刘履《选诗补注》认为,此是魏齐王曹芳因荒淫无度被司马师所废之事;何焯、蒋师煜认为,此是魏明帝与曹爽之事,后来陈沆等从这种说法。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各位阐释者都自有判断的依据。由此也可以推测“苏李诗”的成因,或以为是汉末文人代“苏李”作诗,或以为先有这些汉末古诗,读者阐释为“苏李”所作而题名为“苏李诗”。
诗歌一经创作出来,对其阐释就交到了读者手中。读者对诗歌的阐释,或依据诗人的创作思路开展,或按照读者的意愿来进行,或有着社会的导向,都要求读者在特定审美经验基础上发挥积极能动性。诗人在创作诗歌之时,一旦主动注意读者会有怎么样的接受的话,诗歌将会更向有利于抒情言志的方向发展。
诗歌的抒情言志,是一个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涉及到诗歌文体、诗人、文本、读者、社会、文学史等方面的因素,简单片面地探讨与研究其某一方面的价值属性,有可能得到对此一方面深入的认识,但如此的探讨与研究,只是信息的主动选择、接纳或抛弃而已,决不能替代全面的多维视阈的对诗歌抒情言志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