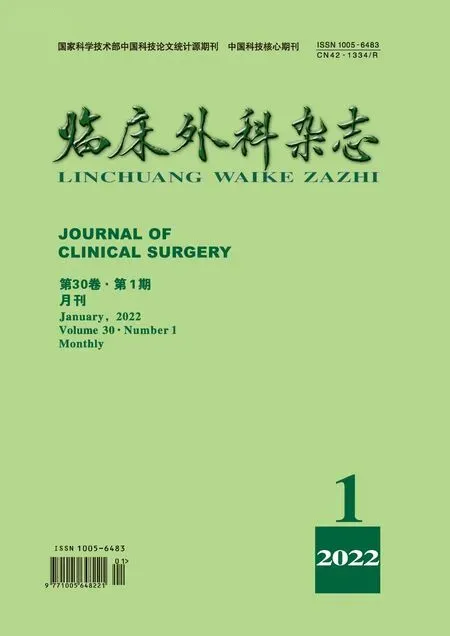2021英国麻醉医师协会《麻醉和恢复期间监测标准推荐意见》解读
李世勇 罗爱林
提高病人围术期安全、降低麻醉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率是围术期麻醉管理的基本要求。哈佛医学院4所附属医院于1986年发布了第一部《麻醉病人监测标准》[1],随后有多部围术期监测相关的指南或专家共识发布[2]。这些指南的实施和推广促进了围术期病人监测趋向标准化、同质化,在降低围术期麻醉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最新一版相关指南是英国麻醉医师协会于2021年5月发布的《麻醉和恢复期间监测标准指南》[3]。该指南在第四版指南基础上进行了细化和拓展[4],共提供了11条核心推荐意见,其中专门讨论了呼气末二氧化碳(end tidal carbon dioxide,ETCO2)监测在镇静和区域麻醉中的监测标准,新增了镇静和转运期间病人的监测标准,同时更新了处理后脑电图(processed electroencephalogram,pEEG)和神经肌肉功能监测的适应证。本文将围绕新版指南以上关键内容逐一解读。
一、麻醉医师是否在岗
该指南强调在麻醉期间具备资质(经过培训且有临床经验)的麻醉医师全程在岗是保证病人安全的基石。该要求适用于深度镇静(病人反应明显迟钝或失去语言交流能力)及体外循环期间的工作场景。若是接受外周区域阻滞的病人,在病人清醒且可沟通的状况下,麻醉医生可以把病人移交给其他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要求能识别并处理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管理,而麻醉医生本人可对另一例待手术病人行区域阻滞,但在外周区域阻滞完成后的前15分钟内,要求麻醉医师必须在场。若需要辅助静脉镇静或镇痛用药,则麻醉医师必须返回岗位且必须在场,直到病人再次清醒并可保持有效沟通。
科室应有一名备班麻醉医师,机动参与某些特殊临床情况,如病人抢救或麻醉医师为协助抢救而长时间离开原岗位(在麻醉医师参与其他病人抢救时,麻醉助理应保持在岗)。此外,备班麻醉医师应轮换长时间单独工作的同事进行必要的休息,避免工作疲劳而导致工作警惕性下降。
二、麻醉记录
所有监测设备产生的数据、信息均应准确地记录并保存。推荐应用自动化电子麻醉记录系统,并将其集成到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当人工记录麻醉单时,心率(HR)、血压(BP)、SpO2、ETCO2和pEEG等指标应至少每5分钟记录1次,其他监测指标至少每15分钟记录1次。若在记录时间间隔内生命体征有剧烈波动,则应详实记录。在紧急情况下电子记录可能难以适时同步记录,临床情况允许时应使用存储在监测设备中的趋势数据填补电子记录中空缺的数据。
麻醉医师交接班时,在麻醉记录单中需详细记录交接情况。该指南建议采用WHO交接清单中的“ABCDE麻醉要素”核查方式交接班[5]。在接班前,接班麻醉医师要核对所有监测设备处于工作状态且报警阈值设置恰当。
三、麻醉设备与报警设置
麻醉医师应提前检查并熟悉所有麻醉设备。使用前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所有麻醉设备的报警阈值并确保处于可用状态。所有实施麻醉的场所应有毛细血管血糖(capillary blood glucose)、酮体监测设备并确保随时可用,而对于接受治疗的糖尿病病人应至少每小时测量1次血糖。此外,该指南还提出以下建议:(1)科室内部标准化监测设备报警的阈值;(2)科室及医院层面要关注设备的维护、校准和更新;(3)淘汰需要使用混合气体而无缺氧保护设置的麻醉机;(4)在合并心血管疾病、衰弱、急诊及特殊类型手术中可考虑应用高级心血管监测,如心输出量监测设备,以指导围术期血管活性药物使用;(5)推荐在小儿和产妇等特殊人群应用超声心动图作为休克的初筛工具。
四、病人监测
麻醉医师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维持合适的麻醉深度、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在麻醉过程中,麻醉医师通过临床观察和监测生命体征指标动态评估病人的生理状态和麻醉深度。听诊器是必备的临床工具。观察内容包括病人黏膜颜色、瞳孔大小、眼泪、胸壁运动和(或)呼吸囊变化及对手术刺激的反应,必要时进行触诊和听诊,并适时关注尿量和失血量。
关于监测项目,新指南要求的基本监测是带描计图的SpO2、NIBP、ECG,麻醉前到手术结束每30分钟测量体温1次。基本监测是最低标准,所有麻醉病人均应建立基本监测;监测应持续至病人离开PACU,包括转运至PACU期间。麻醉诱导期间无法配合建立监测的儿童和不合作的成人,诱导开始后应尽快建立监测并记录延误原因。
若是全身麻醉,还要求监测吸入气和呼出气的氧浓度及ETCO2描记图、机械通气期间的气道压力、潮气量和呼吸频率;以下监测技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采用:若使用了N2O,应监测其浓度和气管装置套囊压力;若使用了吸入麻醉药,则需常规监测呼气末吸入麻醉药浓度(ETAC);若使用了肌松药,则需行量化的神经肌肉功能监测;接受全凭静脉麻醉(TIVA)或吸入麻醉的病人, 不论是否使用肌松剂,都应进行pEEG监测,维持合适的麻醉深度。
在转运麻醉或镇静病人期间监测标准应与麻醉期间标准相同,转运人员必须是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要求能识别并处理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便携式氧气瓶需具备压力和流量监测装置,使用前麻醉医师应确认氧气量。
接受程序化镇静病人、区域麻醉的基本监测包括NIBP、SpO2及ECG;当病人不可唤醒时,应监测ETCO2;麻醉医师应全程在场。 区域麻醉时,最少持续监测30分钟局麻药相关的不良反应。若病人接受手术室外全麻或区域麻醉和/或镇静时,应采用与前述相同的基本监测。该指南特别指出,接受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病人的麻醉最低监测标准应与手术室内接受镇静病人的监测标准相同。磁共振成像室需使用专用的监测设备,麻醉医师应在使用前接受相关培训。MRI扫描时,麻醉医师可在控制室进行远程监测。
五、气道相关监测
气道管理是术中麻醉管理的核心工作, 麻醉医师可通过视、触、听等基本技能发现气道相关不良事件,虽然这些基本临床技能重要,但监测设备帮助我们快速寻找导致这些不良事件的原因。该指南建议监测气道装置的套囊压力、气道压力、分钟通气量及ETCO2。
1.气道装置的套囊压力:合适套囊压力是确保不漏气同时避免损伤气道黏膜。该指南建议使用合适的压力计监测气管导管或声门上气道装置的套囊充气压力,并且套囊压力不能超过生产商设定的最大值;如果厂商未指定或未推荐最大套囊压力,声门上气道装置套囊压力避免超过60 cmH2O[6],气管导管套囊充气量为可预防漏气的最少量(因为气管黏膜毛细血管平均动脉压为32 mmHg, 一般建议套囊内压力不超过30 mmHg,以免导致黏膜缺血坏死)。由于气管导管套囊材料特性不同、外科手术时间长短不一及缺乏高质量临床证据,故目前尚无气管导管套囊最大压力推荐值。
2.通气压力和容量监测:呼吸功能与麻醉密不可分,麻醉中必要的呼吸功能监测便于观察呼吸系统动态变化,有助于发现呼吸相关不量事件。该指南建议在控制通气和自主呼吸期间均应监测气道压力。在控制通气期间,除监测潮气量、呼吸频率和分钟通气量等基本参数外,还建议监测气道峰压、平台压、平均压及呼气末气道压力(最好是波形图)等参数。若病人保留自主呼吸,气道压力监测有助于发现气道阻塞、潮气量过大和限压阀意外关闭等情况。
六、ETCO2监测
ETCO2是无创、便捷、实时、连续的监测指标,可监测和反应病人的通气、换气功能及循环功能[7]。临床广泛用于评估人工气道定位,监测呼吸和循环生理改变,可辅助肺栓塞、恶性高热、心脏骤停等紧急情况的病情判断。ETCO2波形图是气管内插管成功的金标准,可排除气管导管误入食管;麻醉中ETCO2波形图是监测气道是否通畅和肺泡通气的重要指标。国内有专家共识建议使用ETCO2监测仪协助多种管路定位[8]。
鉴于ETCO2在临床应用中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该指南单独讨论了ETCO2在镇静和区域麻醉中的监测标准,并建议各年龄段和各场所的所有接受麻醉病人均应监测ETCO2。对全麻病人,从诱导、建立气道、麻醉维持、转运病人和苏醒期间都应全程不间断监测ETCO2;程序化镇静病人亦建议监测ETCO2。
麻醉医师应熟练识别并解读正常和异常ETCO2描计图,以尽早发现某些紧急情况。参与苏醒或镇静期间监测的医务人员应接受培训以识别安全和不安全的ETCO2波形。在体重极小的患儿(<1 kg)中,ETCO2波形图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解读[9]。
ETCO2只是一项临床监测指标,并不可完全依赖它做出临床决策。众所周知,ETCO2是气管插管定位的金标准,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严重的支气管痉挛病人,ETCO2可能无法判断气管插管位置,熟练使用支气管镜就显得尤为重要。
七、神经肌肉功能监测
神经肌肉松弛药物(简称肌松药)的临床应用是现代麻醉技术的重大变革,但随之而来的肌松残留风险不利于病人的康复[10]。2015年我国多中心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全麻手术拔管时肌松残留发生率为36%,而全麻腹部手术拔管时肌松残留发生率高达57.8%[11]。全球范围报道的肌松残留发生率为4%~64%[12-13]。肌松残留导致苏醒延迟,并增加误吸风险、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和全麻期间术中知晓等严重并发症。因此,临床实践中量化的神经肌肉功能监测非常重要。
临床判断肌力恢复的体征,如持续抬头、握手及伸舌准确度低。病人临床表现,如恢复自主呼吸、达预期值的潮气量、呛咳及指令性肢体活动,也不能排除肌松残留。目前倾向于认为四个成串刺激(TOF)监测中T4/T1比值(TOFr)<0.9提示存在肌松残留效应。该指南建议,任何使用神经肌肉阻滞药物(包括超短效的琥珀胆碱和米库溴铵)的场景都应配备量化神经肌肉功能监测设备,监测从诱导启动与神经肌肉阻滞药物起效之前开始,并持续整个麻醉过程。病人苏醒和拔管前需确认TOFr>0.9。尺神经是神经肌肉监测最常用的部位。然而,如果术中不便于监测拇指运动时,替代方案包括使用压电神经肌肉监测设备或监测其他部位如面神经或胫神经的肌电图。若监测面神经肌电图,肌松残留的风险增加5倍[14]。因此,最好在手术结束时重新监测尺神经肌电图。
八、pEEG监测
传统判断麻醉深度是依据病人生命体征和临床表现,如心率增快和血压升高、出现体动和流泪等均提示麻醉深度不够,可能发生术中知晓,但此方法不客观也不可靠[15]。EEG反映的脑皮质神经细胞电活动,已被证实与睡眠或麻醉深度直接相关。由于原始EEG的解析非常复杂,因此,临床用于监测麻醉深度EEG是处理后EEG(pEEG)。pEEG帮助麻醉医师调整麻醉药物剂量而维持合适的麻醉深度,精准把控苏醒时间并减少术后谵妄和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发生。pEEG监测是该指南单独讨论的另一部分。
当使用TIVA维持全身麻醉时,监护仪并不能确认麻醉药物是否按设定目标输入病人体内。ETAC监测仅关注术中知晓,未涵盖诱导后至手术开始前和手术结束后至苏醒前这两个阶段。而有报道显示,近2/3术中知晓病例可能发生在上述的两个阶段,并且大多数病例无法通过监测ETAC预防[16]。因此该指南建议,接受TIVA或吸入麻醉的病人, 不论是否使用肌松剂,都应进行pEEG监测;pEEG监测应在诱导前开始并持续到神经肌肉功能完全恢复;建议麻醉医师对pEEG波形、频谱、信号密度分析有基本地了解以更好的解读pEEG监测参数。
该指南也存在以下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分娩镇痛是手术室外麻醉的一个特殊场景,ECG监测是否是分娩镇痛的基础监测存在争议。一方面这些监测限制了产妇活动,另一方面产妇的活动也影响这些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在肌松监测中也存在争议,第一问题是TOFr基线值的获取时间是诱导启动后,影响基线值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后续肌松效应的判断;第二争议是以TOFr>0.9作为神经肌肉功能恢复的指标是否恰当,有研究发现,TOFr为0.9时,支持上呼吸道肌肉的张力并未完全恢复;而已更高的阈值作为肌肉张力恢复的指标,有利于减少术后肺部并发症[17]。因此新版指南部分内容有待完善。
总之,麻醉和恢复期间基本监测是最低监测标准,可根据病人病情适当增加某些监测项目,但也无需任一病人均采用当前医疗机构可提供的所有监测项目而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正如该指南开篇所提到的有资质的、保持高度警惕状态的麻醉医师全程在岗是保障围术期安全的基石。就监测工具而言,虽然智能化、小型化、可视化的监测工具越来越普及,但仅有传统的工具-听诊器被认为是不可少的。当前超声在围术期应用广泛,被称为麻醉医师的“第三只眼”,有人认为它将取代听诊器,但熟练使用超声需要专业培训;从成本上来说,超声很难做到像听诊器一样做到随手可及。最新回顾性分析发现,在欧美国家2010~2020年发表的围术期医学相关专家共识或临床指南中,不到20%的推荐建议来源于高质量的临床证据[18],因此不能迷信于当前专家共识或临床指南。综合来看,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围术期医生,不仅需要加强自身知识体系建设,还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习惯、以解决临床问题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临床应急反应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