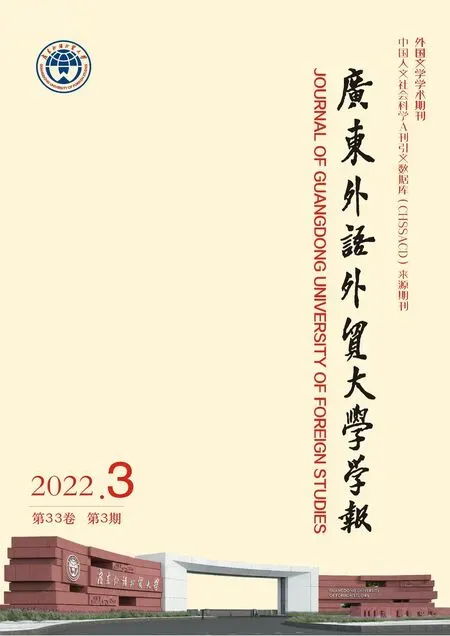语言·身份:论《中间的孩子们》中在日华人的伦理选择
姜奥育 杨晓辉
引 言
温又柔(Wen Yuju,1980-)生于中国台湾地区,3岁随双亲移居日本。在日本法政大学求学期间,从师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凑(Minato Kawamura,1951-)以及使用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美籍作家李维英雄(Ian Hideo Levy,1950-),随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身份是流散文学(也被称为‘移民文学’等)的核心主题”(钱超英,2006:80)。从在《昂星》杂志发表的处女作《好去好来歌》(2009)到小说《鲁肉饭的唠叨》(2020),关于在日华人这一越境群体的身份认同的探讨是贯穿温又柔小说创作的主题。对于身份的追问也是温又柔进行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此外,温又柔还出版有随笔集《我住在日语》(2016)以及与作家木村友祐(Yusuke Kimura,1970-)的书信集《我与你之间——现在居于这个国家》(2020)等,其主要内容均为温又柔对于语言与身份之关联的思考。
温又柔的小说《中间的孩子们》(2017)入选第157届芥川奖候补作品后,其越境创作受到诸多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关注。芥川奖评审宫本辉(Teru Miyamoto,2017:383)认为,“对日本的读者来说,该小说描述的是无关痛痒的事,难以产生同感”。这一评价蕴含的是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即认为身份是一种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杨柳,2018:38)。而温又柔通过越境文学创作想要传递的正是对于本质主义身份观的反思。与本质主义的身份观相对,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具有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身份是一种建构,而非一成不变。在谈论在日华人作家的越境书写时,跨越国族的流散身份研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话题。研究温又柔的创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对理解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温又柔基于自身生活体验进行创作,并借由书写“越境文学”来表达对身份认同的追问和挣扎。由于这种越境文学尚在发展进程中,同时代的研究者或许无法对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作出系统的评价(王宁,2012:5)。但通过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厘清作品中的伦理线以及伦理结,或有助于读者明晰文本的伦理结构,进一步把握越境文学创作中“越境者”之语言观与身份观,这对理解越境文学以及在日华人的身份认同大有裨益。
目前有研究者将温又柔归类为“在日中国台湾作家”(蔡佩茹,2019),但若将温又柔置于在日华人作家的大框架下进行讨论,或能梳理出更全面的日华文学谱系。战后活跃于日本文坛的陈舜臣、东山彰良、温又柔等在日中国台湾作家屡屡在日获得文学奖或文学奖提名,可谓已成为日华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王宁(2012:8)提出“用西方的语言表达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可以更有效地影响西方人”。同理,在日华人作家使用日语进行的越境创作直接面向日本读者,其在传播中华文化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中国是日华作家的文化母国,研究日华作家的日语文学创作中的中国形象书写对于打造中国对外形象也有借鉴意义。
作为伦理环境的“越境”
《中间的孩子们》讲述自幼居住于日本的中日混血儿天原琴子在上海留学期间经历的伦理身份困境,属于越境文学的范畴。“越境”原意是指越过省界或国界。李维英雄提出,外国人用日语写作可以看作一种“越境行为”(蔡茂丰, 2008:4-5)。《中间的孩子们》交织着温又柔对越境身份的思考,是作家对当今移民现象引起的伦理身份问题思考的艺术表达。岛村辉(Teru Shimamura,2014:28-29) 在《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现状及方法论的变迁》中曾提到受后殖民主义发展的影响,日本文学中‘日本’的构成要素遭到了质疑。跨越国界、语际的越境文学实践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并引发了评论界对“日本文学”定义之讨论。从这一层面说,越境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中国作家阎连科也曾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只有混血写作才能取得进步”(唐卉,2010)。可见越境文学的影响已超越国界,引起了中日两国文学创作者及评论家的重视。当今华文文学研究已成风气,而日华文学作为华人流散写作以及世界移民文学的组成部分,其研究文献数量及研究深度尚不及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华人文学研究。通过对在日华人越境文学的研究,既有助于认识当今日本文学的多元性,也有助于完善全球华人流散写作的研究。
“越境”是《中间的孩子们》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环境。“伦理环境是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即使描写的是现实社会中正在发生而没有结束的事,但文学一旦形成,也就变成了历史,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去加以分析” (聂珍钊,2014:256)。读者之所以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难以共情”之感,实际上正是因为未能了解作品的“越境”环境。《中间的孩子们》中伦理矛盾冲突最激烈的一段是琴子在课上演讲时说“对我来说,日语并不是‘妈妈’的语言,宁可说那是‘爸爸’的语言。所以我想把日语叫作‘父语’”(温又柔,2019:103)。这原本是琴子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后对自身语言与身份的错位做出的和解,而陈老师却以为琴子是在开玩笑。毋宁说陈老师始终未能理解琴子成长于复数语言环境的这一“越境”背景。
《中间的孩子们》共分为《出发前夜》《在上海》以及《再次,出发前夜》三部分。小说的第二部分《在上海》叙述了自幼生活于日本的中日混血儿琴子在上海学习中文时的见闻,其中既描绘了在豫园、老城隍庙体验到的传统中国风情,也描写了在外滩、南京路感受到的上海作为现代化“魔都”的繁华,涉及百年间上海从租界到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变迁,体现出上海这座城市对中外文化的包容与开放的态度。“异域环境有助于转变和重建旅行者的身份认同”(骆谋贝,2021:119)。对琴子来说,纵然在上海能找到熟悉的文化因素,但上海无疑是一个越境的“异域环境”。“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是身份问题的两个方面。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最初表征:它要么触发身份危机与毁灭, 要么推动身份建构与重构”(杨柳,2018:38)。虽然在上海只度过了短暂的一个月,但这一个月中琴子第一次感受到身份焦虑,并开始深入思考身份认同这一严肃问题。在上海的经历也影响了琴子的职业选择,可见越境环境对于琴子的影响。此外,在上海这样一座兼容并包的都市中,与中文老师、身边同学以及诸多上海市民的交流后,琴子感受到的却是对身份认同的困惑。这种对比也体现了越境者的他者性,以及越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作为越境者发声渠道而存在的必要性。
伦理线与伦理结之解
作品的伦理线是凝结作者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用文学伦理学批评阐释作品的关键。“在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伦理线的表现形式就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 (聂珍钊,2014:265)。贯穿于《中间的孩子们》的伦理主线毋庸置疑是琴子对于伦理身份的探寻。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出发前夜”以及最后一部分“再次,出发前夜”中,都提到中国台湾地区出身的母亲特地包了水饺为即将前往异国的女儿送行。“在中国,人们为亲友送行时,行前的最后一顿会吃饺子,以期盼亲友早日平安归来、重逢团聚”(周星,2007: 92)。在琴子到上海后,来自日本的留学生们也曾在中国同学的家中举办“包饺子大会”,一起做水饺。“食物作为文化隐喻符号在族裔文学中广泛存在”(黄新辉, 2020: 52)。饺子在中国多指水饺,而在日文中通常指煎饺。在《中间的孩子们》中,“水饺”也有隐喻中国文化之意。由此可见琴子虽自幼居住于日本,但在家庭生活中仍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该细节也为琴子在沪面临的伦理困境埋下伏笔。身为成长于日本的移民第二代,琴子对中国的情感是一种对文化故土的眷恋。因此琴子内心渴望学习汉语,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但同时因为琴子从小接受的是日语教育,所以琴子极少使用汉语。而同为中日混血儿的好友陈嘉玲在家庭教育中接受的是汉语教育,所以汉语要比琴子流利很多。琴子也因此感到自卑,这也在无形中加深了琴子对伦理身份的困惑。
“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问题”(聂珍钊,2014:258)。《中间的孩子们》中最重要的伦理结是语言与身份的错位。琴子生于中国台湾地区,母亲也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父亲是日本人,三岁时随父母移居日本后,琴子便只学习日语。由于琴子母亲的日语不够流利,因此在讲日语时会夹杂中国台湾地区的闽南语。琴子将母亲使用的这种混杂着日语和汉语方言的语言称为“妈妈语”。语言上的越境同样影响了琴子的伦理身份认同。涉及日语、用简体字表记的汉语普通话、用繁体字标记的中国台湾地区“国语”以及用日语片假名表音的中国台湾地区闽南语等“复数语言”的写作方式是温又柔小说创作的一大显著特征,也体现了琴子生活中语言之复杂。
《中间的孩子们》中许多矛盾和冲突亦是围绕着对语言与身份之关联的讨论向外辐射,构成了小说的伦理结构。“华人在海外为了生存,必然需要首先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其次才会考虑民族文化继承的问题”(费勇,1997:28)。因此在给琴子起名字时,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外祖父说“还是取个像日本人的名字吧”;琴子母亲提议在家中使用日语,希望琴子可以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但由于琴子缺乏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深入学习,因而在中日两种文化间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这是移民后代普遍遇到的困境。
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6-18个月的孩子处于“镜子阶段”,即“孩童通过将镜中自己的形象作为他者的方式来认识自我”(拉康,2001:89-96)。琴子离开久居的日本来到上海后,通过上海市民以及周围老师同学对自己的评价,琴子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自己并进一步思考自己的身份。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中该阶段被称为“伦理启蒙”。“一个人只要缺乏伦理选择所需要的任何知识,他都需要伦理启蒙”(聂珍钊,2014:258)。长期使用日语、生活在日本的琴子来到上海后不得不直面语言与身份的错位,这也迫使琴子开始思考语言与身份的关联。而陈老师对琴子“南方口音”的指责进一步催化琴子产生对语言及伦理身份的困惑,并使得琴子在伦理选择过程中逐步陷入伦理困境。琴子曾倾诉“以前自己常被夸赞汉语好,但到上海后,如果别人知道了自己母亲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反而会觉得我的汉语没有那么好”(温又柔,2019:61)。由于琴子母亲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加之琴子幼年时曾在中国台湾地区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琴子自幼习得的汉语便是带有“南方口音”的汉语。琴子在上海时的中文教师陈老师认为,中文教师的使命在于教给学生“正确的中文”,因此她试图纠正琴子讲汉语时的“南方口音”。由于自幼琴子的中文就常受到身边人夸赞,陈老师对纠正“南方口音”的执着让琴子开始思考何为“标准语”。他人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评价是琴子确立身份意识的催化剂,这种差异促使琴子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出身,进而思考自己的定位。
“获得主体性依赖于社会文化因素”(胡宝平,等,2021:28)。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谢惠贞(2017:36-38)提出“天原琴子在到了上海后才感受到了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的碰撞,由此产生对于身份认同的思考。而幼时的琴子只认为世界上语言分为家里用的语言和家外用的日语,并没有将语言和身份相关联”。中日混血的琴子离开日本后,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首先要回答的便是“你是哪里人”这一提问。他人会先入为主认为讲日语的就是日本人,从而把琴子看作是日本人。而在得知琴子母亲是中国台湾人后,他人则会提出“那你不该说自己是日本人吧”这一疑问,而这对于琴子来说同样也是难以解答的困惑。一方面虽然自己持有日本国籍,并居于日本,但由于自己有一半中国血统,琴子无法完全将自己划为日本人;另一方面,虽然自己自幼习得一些简单的汉语,且在家庭生活中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但由于久居日本,接受日语教育,学习日本文化,长期生活于日本社会中的琴子也无法完全将自己归为中国人。由此琴子陷入伦理困境,斯芬克斯因子中的兽性因子占据主导地位。失去理性的琴子无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甚至一时冲动下提出要放弃学习汉语。
语言与身份的错位问题是温又柔的越境创作中矛盾的焦点。在与李维英雄的谈话录中,温又柔曾提到,“在李维英雄的课堂上接触到李良枝的作品让我大受震撼。《由熙》(1989)一书促使我开始思考对于个人来说母语究竟是什么”(リービ英雄、温又柔,2017:28)。《由熙》一书讲述的是在日朝鲜人由熙为寻根而前往韩国留学的故事。由于成长于日本,由熙无法驾驭韩语,也难以融入韩国的社会文化,最后选择回到日本。拥有韩国人血统,但却只对日语有归属感,这种语言与身份的错位同样也是小说《由熙》中最为关键的伦理结。温又若本人也曾提过“处女作《好去好来歌》是‘温又柔版’的《由熙》” (リービ英雄、温又柔,2017:36)。温又柔毕业于法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大学期间曾赴上海学习汉语,这一点与《中间的孩子们》中的琴子极为相似。可以说《中间的孩子们》同样有《由熙》的影子。
主人公的道德榜样与伦理选择
“道德榜样一般都是理性人物……道德榜样能够通过人性因子控制兽性因子,通过理性意志控制自由意志”(聂珍钊,2014:248)。龙舜哉早于琴子认识到自己的伦理身份,因此龙舜哉在琴子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中是道德榜样一般的存在。龙舜哉长期生活于日本,但却有着中国人一样的名字。与他人在名字上的差异既暗示了他的越境身份,也让他比同龄的琴子更早产生身份意识。“龙”在中国文化中常为天子的象征,而“舜”则是中国古代帝王的名字,作者在此暗示龙舜哉本人的领导力及其在寻找伦理身份这条主伦理线中对琴子的引导作用。龙舜哉帮助琴子厘清了汉语之于身为混血儿的琴子的意义,并确立了“中间的孩子”这一伦理身份,使琴子的人性因子重新控制和约束兽性因子,理性重新发挥作用,找到了越境者的价值与意义。“名字不仅仅是代表自己的符号,为了理解自己的名字代表自己这件事,一个人需要培养区别自己和他者以及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小林由紀,2012:113)。
龙舜哉将自己所说的日本关西地区方言称为“西日语”,这为苦恼于“何为正确的汉语”的琴子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史书美的“华语语系”,谢惠贞(2017: 45)提出“《中间的孩子们》中提到的普通话、‘中国台湾地区国语’等都属于‘华语’的范畴”。据此,龙舜哉所谓的“西日语”或许也同样可以归为“日语语系”。而琴子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打破了原有的关于“汉语”标准化的定义。琴子也观察到上海的学生在一起时比起说普通话,会更习惯于说上海话。在琴子确立开放的语言观的过程中,龙舜哉无疑起到榜样作用。琴子也能从此不再执着于改正自己的“南方口音”,正视自己具有“越境”色彩的口音和身份。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脑文本是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既定程序”(聂珍钊,2017:33)。面对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受挫的琴子,龙舜哉提出“语言与身份的关系应该是更自由的”的观点。“去标准化”的语言观在琴子大脑中形成脑文本,之后也指导了琴子“中间的孩子”的伦理选择。确立开放的语言观后,琴子终于从语言与身份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以乐观轻松的心态学习汉语,这也为琴子确立更开放的身份观奠定了基础。龙舜哉提出“既是日本人,也是中国台湾人”(温又柔,2019:39)即“中间的孩子”的概念。有别于琴子此前二元对立的身份观,“中间的孩子们”的观点模糊了界限,将越境者置身于两者中间。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罗钢、刘象愚,2000: 211)。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移民热潮不减,“越境”者的身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不同的文化框架间行走给予旅行者个人成长的机会,旅行者借此可以过上比旅行之前更令他满意的生活”(骆谋贝,2021:119)。离开上海回到日本后,琴子成为一名汉语教师。面对同样具有越境背景的学生,琴子也将这种开放的语言观传递给学生。琴子在帮助越境者成长的事业中实现了人生价值,最终琴子的人性因子战胜了兽性因子,完成了伦理选择。
在进行伦理选择时,琴子没有把自己置于中日任何一边,而是通过“告白”的方式,承认了“我不是完全的日本人”,确立了“中间的孩子”的伦理身份。所谓“告白”即诚实地、毫无隐藏地说出心中所想(生田長江,1913:64)。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自由竞争让人们首次有了“自我”的意识,产生“近代的自我”。而在此之前的“自我”都被隐于封建制度中。知识分子产生了自我意识,渴望个性解放,却仍被占据主流的传统思想束缚,由此孕育出告白制度。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2003:69)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2003)中提出,日本的现代文学是与告白制度一起产生的。狭义的告白是指日本近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自我意识与封建思想相矛盾的伦理困境时所作出的选择。而在日作家将自己的感受投射到作品中,通过写作表达在异乡的所思所感便形成了越境文学这一带有告白性质的文学。温又柔在写作中表达自己对于身份的思考,逐步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越境文学。小说中的琴子通过宣告“我是中间的孩子”完成了自己的告白。作者温又柔本人也曾透露“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能够安居的地方,感觉得到了拯救”(リービ英雄、温又柔,2017:28)。对于温又柔来说,写作越境文学也是自己的“告白”。因此越境文学可谓是告白文学在当代的一种全新形式。
结 语
越境作家温又柔结合自身经历的越境小说创作拓宽了日本文学的边界,也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解读越境者的伦理身份及伦理选择过程,可以抽丝剥茧般对伦理环境、伦理线、伦理结等各要素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把握在日华人面临的身份困境及其作出选择的缘由。这或许能为我们探讨中日之间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带来一些启迪。日华作家的越境书写是全球移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以温又柔为代表的越境作家的创作也有助于梳理移民文学的谱系,推动移民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期待当代日华作家能突破狭隘的自身局限,正视历史,审视现实,以更多元的视角进行创作,发挥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