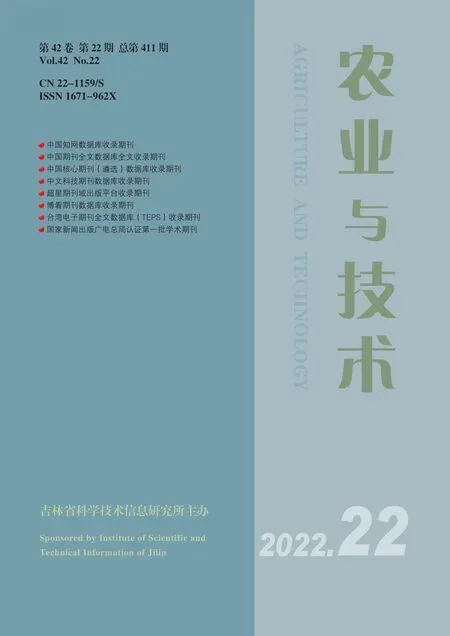昆明市彝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分形哲学研究
---以昆明晋宁打黑村为例
王静 刘扬
(西南林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引言
泱泱中华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在华夏大地上孕育出形态各异、极具民族特色的村落空间。传统村落是在自然条件下,受社会和文化影响而人为形成的人类聚居地,其历史源远流长,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农耕文化的传承,传统村落不仅是当地居民的集体回忆,而且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彝族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是一个拥有神秘起源、古老文字、独特信仰的少数民族,受到不同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宗族习俗等社会人文环境及其他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极具独特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形态[1]。打黑村,昆明市晋宁区的彝族特色村寨示范点,一个鲜为人知的世外桃源,一个古朴而色彩浓厚的村庄,一个传统的彝族聚居村落,至今仍然保留着传统彝族生产、生活方式及本民族的语言。彝族人遵循崇尚自然、珍惜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法则,择宜居之地。彝族村落是受彝族文化熏陶、为适应自然与周边环境相融合而形成的聚落,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可作为分形理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因此利用分形理论研究彝族村落的空间形态有理可循。
分形理论相关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首次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张济忠在1995年发表的《分形》一书初步对分形学做出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此后,分形学开始在国内发展,并逐步运用于城市空间形态[2]、城市规划设计[3]、城市土地利用[4]等方面的研究。随着分形理论在城市规划和设计方面的研究逐渐深入,少数学者发现,传统村落呈现出的遵循自身规律发展的分形特征更为明显,因此,逐渐有学者开始从分形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传统村落,尝试用科学客观的理论来支撑传统村落的保护更新。王辰晨发表的《基于分形理论的徽州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研究》一文中,利用分形理论中的计盒维数法,计算并分析徽州传统民居的聚落整体、建筑平面和外墙等空间形态的分形维数值,将新的方法和理论延伸到传统民居的研究中[5];刘泽等于《基于分形理论的北京传统村落空间复杂性定量化研究》中,采用分形理论中的计盒维数法对京西的传统村落进行研究,计算村落中不同类型的外空间的分形维数值,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空地和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形态是影响村落复杂性的重要因素[6];李彦潼等于《基于分形理论下村落空间形态特征量化研究——以南宁市村落为例》中,基于分形理论,提取相关村落的平面图斑,定量分析其空间形态,探究村落形态的量化特征,并深入分析空间形态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7];杨汝婷等于《杨梅村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分形与句法研究》基于空间句法和分形理论,定量分析杨梅村的空间形态,获取村落整体空间形态特征,对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保护与更新上的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验证[8];马莉等于《基于分形理论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分析》中借助分形理论模型量化研究城镇边缘区传统村落的空间转型形态,通过对比分析转型前后分形维数值,从科学客观的角度解释村落空间形态转型特征与城镇发展形态的关系[9]。
分形理论的相关应用遍及几大学科:哲学、数学、物理学、艺术学等,而当前社会重大科研成果越来越依赖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因此笔者试从哲学的角度去解析分形理论作用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机制,丰富传统村落的研究成果;另外,学术界目前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方法大多停留在现象性描述与经验性归纳,缺乏定量分析与实证分析,对村落空间形态的内在规律研究不足,遂本文以昆明市彝族村寨示范点打黑村为例,解析打黑村空间形态的生成规律,总结彝族村落空间形态的分形哲学规律,可为彝族村落甚至是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与优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1 分形理论概述
1.1 分形理论思想
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教书曼德尔布罗特出版的《分形对象——形、机遇和维数》一书,首次提出了分形几何学。其在著作中解释了“分形”的基本内容:形,即对象的外观形态;机遇,是随机性或者说偶然性;维数,则是用来描述对象不平整度、复杂度和卷积度的特征量,直接反映了对象的产生肌理和构造方式[10]。所谓“分形”,就是研究对象某一部分与其整体在一定的标度区间内存在相似性。分形从特征上讲分为规则分形和随机分形,规则分形的任意局部与整体完全相似,多存在于数学模型中,见图1;随机分形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相似性,多存在于自然界中,见图2。本文所研究的传统村落即为随机分形。分形理论的根本特征是从量化的角度来探索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最原始的自然属性,这种方法更贴近于对复杂体系的本质和状态的描述,与客观世界的变化和复杂程度更加吻合。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1.2 分形哲学观
分形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将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其虽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但本质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形哲学观将相似性、破碎不规则性、标度不变性以及迭代生成性等分形理论的核心理念同局部与整体、无序与有序、偶然与必然以及量变引起质变等哲学观念联系起来,拓展了分形理论的应用广度。
分形理论的自相似性揭示了自然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即存在分形特征的物体,可以通过其局部感知整体,在不同的尺度上揭示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从另外的层面丰富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破碎不规则性为自然界中的无序与有序提供了依据,自然界中任何看似不规则复杂的物体都有自己内在的简单规律,其发展遵循于这种规律,最终形成一个复杂而稳定的整体;标度不变性完善了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事物的发展是必然的,但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是偶然的,许多偶然的因素以稍有偏颇的方式影响其必然的结果,但必然的结果无法忽视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本质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迭代生成性阐释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内在规律,当形体经过反复的变化复制增加,就会从有限到无限,从简单到复杂,如一个单体建筑经过多次的迭代生成之后就会发展为一个聚落。
2 研究地概况及研究方法
2.1 打黑村概况
打黑村始建于元代,依山而建,半月古村,彝族传统民居遗存集中,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被列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乡村示范点。村落历史文化保存完好,生活环境舒适宜人,农耕种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村庄用地以农田、山林为主,村落格局清晰完整,自然环境优美和谐,见图3。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由于彝族独有的部族、支系社会结构因素,以及内争外患的山地自然环境因素等影响,彝族聚落形成了聚族而居、据险而居、靠山而居3大特点。打黑村的建筑依山而建,形成了1个半月形的格局。在村落内部,以一条古街为主轴,连接各条大小街巷,形成“大街—小巷”的两级交通体系,街巷的布置呈现出“鱼骨状”的格局,村内道路四通八达,村中的古民居布局,是夕阳彝族乡彝族建筑的典型代表。整体来说,打黑村村落空间结构清晰完整,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比较高。
2.2 研究方法
2.2.1 计盒维数法
分形几何中,计盒维数法是测量距离空间中分形维数的一种计算方法,实质是改变图形粗视化程度,对其进行测量,从大尺度依次到小尺度,通过计算非空格盒子数获得图形的分形维数值[11]。按照分形的大小,选取边长为S的网格,将分形放在矩形网格阵列上,并计算出覆盖分形所需的网格数量,所得网格数即非空盒子数记为N(s)。如果缩小网格的尺寸,则N(s)增大,计算公式:
其中,Db代表分形维数值;N(s)为非空盒子数;S为单位网格的尺寸。从分形维数值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分形维数值D的理论值一般在1.0~2.0,1.0表示1个最简单的矩形斑块,而2.0表示最为复杂的图形斑块。1.3794以下为低分维区,1.5046以上属于高分维区,处于二者之间的属于中分维区[12]。
2.2.2 分形维数
分形维数英文为“Dimension”,是分形的定量表征和基本参数[13]。从图形学上看,分形维数是一个统计值,描述其研究对象填充整个空间的程度,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图形固有的不规则性和复杂性的定量特征[5],以分形维数来描述其分形特性,从侧面也可以反映某一空间形态的丰富程度,总结空间形态特征。
大尺度的分形维数值反映了聚落整体平面与周边环境的紧密性;中尺度层级的分维值反映了聚落原始形态基因的继承程度以及原有生长是否遭到破坏;小尺度的分维值反映了建筑单体与聚落组团之间的紧密程度。若某一尺度的分维值越大,则图形越丰富,包含的要素越多;比较不同尺度层级之间的分形维数值大小变化,若在小范围内呈稳定增长或降低,则说明该图形符合自然界广泛存在的自然特征,连续性较好,自相似程度高;若不同尺度层级间,其分维值突然急剧增加或减少,说明图形不具连贯性,相似程度低,且该图形在发展中被外部因素所扰乱[14]。
3 基于分形理论的打黑村空间形态解析
3.1 打黑村空间形态的现状分形特征
打黑村整体析出的边界错综复杂,看似杂乱无章,缺乏规则,实际其村庄的空间形态具有高度的层次感和不规则性,内部的建筑物存在规律感和相似性。打黑村大多为围合院落,以“一颗印”建筑形式为主,中间是院子,民居由土掌房围合封闭的形式与坡顶建筑结合,见图4,因彝族先祖冬居营窟,夏居桧巢,所以彝族传统民居多呈封闭围合的特点。建筑空间的规则性与周围普通住宅相似,即都以矩形围合院落为核心复制迭代组织成的空间群。结合分形理论,可以得出,村落的平面,立面街巷等空间形态均可作为分形的要素,是村落运用分形理论进行研究的主要特征。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改绘。
3.2 打黑村空间形态分形解析
通常来讲,对视觉信息识别的距离进行分析总结,可知想要清晰的辨认出建筑物的细节,需在20~30m范围内;想要清晰地辨认出物体的门窗、形体的变化,需要在100m之内;而大于500m时,人眼对于景物只存在模糊的形象。因此,结合打黑村的规模,本文选取尺度层级70~35~17.5~8.75m进行分形维数值的计算研究,见表1。

表1 打黑村分形维数计算
数据表明,3个尺度层级的分形维数值较为接近且均处于高分维的阶段,说明空间结构的连续性较好、稳定性强、自相似程度也较高,且空间形态复杂。据打黑村原住民回忆,目前村落内多数人群的祖先是由靠近中央王朝的内地迁来,在此定居,繁衍生息,到19世纪50年代,当地进行民族识别时,村民已经学会了彝语,并称自己为“聂苏泼”,因而被识别为彝族。彝族信仰毕摩,毕摩文化是维系和凝聚非亲属关系民族成员之间的核心力量,是打黑村村民至今保持独特的生产生活习惯的根源所在。因此,打黑村以毕摩文化来管理规范村民,维护群体的稳定发展。
在中尺度层级35~17.5m,分形维数值最低,为1.6586,与最大的尺度层级70~35m的分形维数值最为接近,相差0.0113,说明其原有的自生长特性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即村落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村落的空间结构遭受到轻微的破坏,使得村落出现逆生长。结合相关资料得知,矣姓是打黑村的开村之祖,矣姓祖先在此地发现古井,认为这是一处福祉,便在此地定居。后全村闹霍乱,矣姓家族成员死伤殆尽,现如今打黑村的矣氏一族仅剩3户人家,而村子里大部分人的祖先都是从中原附近的内陆地区迁移过来。
在最小的尺度层级17.5~8.75m,分形维数值最大,为1.6959,处于最佳分维值1.701±0.025之间,在这一层级,建筑单体和村落组团之间存在较高的紧密性,说明其组团空间结构稳定,村落整体空间布局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状态。此外,小尺度与大尺度分维值相差极小,仅为0.026,说明打黑村空间形态经历了自生长的过程,空间形态具有随机分形的特征,村落发展按其自身规律演变。
基于上述不同尺度层级的分形维数值对比,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证明打黑村经历了由简单的单体建筑迭代生成复杂稳定的聚落这一过程,即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生活生产需要、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建筑由间到宅到院,再形成街道组团,最后生成聚落。在打黑村的逐步发展中,人口规模的增加促进了空间形态趋于丰富,促使打黑村内外的空间结构趋于成熟和稳定,而由于毕摩文化的约束,致使其空间形态呈现标度不变的特性,因此村落无论在何种尺度之下,其内涵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使得聚落空间结构形态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稳定性。
4 昆明市彝族村落空间形态特征的分形哲学
据彝族经典古籍《西南彝志》以及相关彝经记载,彝族发源于如今的云南境内,彝族死后送魂也是送入昆明滇池、云南昭通、大理点仓一带,说明彝族是从南方迁来。另外,著名学者张增祺在其所著《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一书中曾提到过“古代‘昆明’是近代彝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蒙默则认为“彝族是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从旄牛檄外南迁至云南的‘昆明夷’”;在其他彝族传说中,“昆明为彝族之先祖”也有相关记载。由此,昆明彝族极有可能为现大多彝族的起源点,昆明彝族传统村落象征了我国彝族村落的基本情况,而打黑村作为昆明市彝族村寨的示范点,其空间形态可以代表多数彝族村落原始的空间形态,因此,以打黑村的空间形态特点为基础,结合分形理论,可推导出彝族村落空间形态的分形哲学规律。
4.1 以局部见整体——村落形态自相似性
分形理论中的自相似原则表明具有分形特征的物体,其任意局部与整体都存在一定的相似关系,因此,事物整体可通过部分来识别。一般来讲,传统村落的发展是由村民自发组织、自下而上的发展,没有明确的规划意图,受地理位置以及民族文化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村落,即从空间构成来讲,住宅组成院落,院落形成街道,街道构成村落。简言之,打黑村某一院落组团的空间肌理结构与村落整体形态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见图5,这些小空间与整个村庄是局部和整体的联系,不论是文化亦或是空间形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整个聚落的缩影。

图5 打黑村村落肌理图
4.2 无序与有序——空间布局不规则性
彝族遵循珍惜土地,重视山水,保护森林,合理利用自然能源的原则建设村落,房屋建造多选择在山谷内相对开阔的阳面或山侧南向缓坡上,依山傍水,依据地形和等高线的走向有顺序地排列。昆明彝族民居普遍采用的建筑形式为一颗印式,部分民居为顺应坡地地形,分化出半颗印建筑,有的建筑围绕古井、古树和农田有序建设,致使某些局部建筑之间的密度和空间秩序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这些因素导致若干小空间的边界变得不规则,进而使村落整体空间形态呈现无序化。各种有序的局部空间共同构成了复杂无序的村落整体空间形态,见图6,而这种复杂、连续的分形特性,恰恰是传统村庄比现代建筑更加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根本原因[15]。

图6 规则的组团不规则的聚落
4.3 偶然与必然——文化内涵标度不变性
标度不变性是指在一定的标度区间中,对具有分形特征的对象进行任意一部分的放大或缩小,其性质和内在结构均不发生改变。这个标度区间,不仅指空间尺度,也指时间维度。每一个聚落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而时间维度则是贯穿这一过程的始终,不论是建筑单体,还是聚落整体,从形成到稳定,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信息。对于彝族村落来讲,这个历史信息则是维系民族凝聚力、贯穿民族发展始终的毕摩信仰,这个信仰使得其村落朝着一个必然的方向发展,即以毕摩信仰为支柱的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如科技文明、数字化时代等使得毕摩社会朝适应时代的方向发展,但不会改变其内在本质。而空间维度的标度不变性,体现在村落上便是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小到一户,大到一村,都有着相同的文化习俗,相似的建筑风貌,这正是传统村落的灵魂所在,也是打黑村标度不变性的体现。
4.4 量变引质变——空间形态迭代生成性
所谓迭代生成性,即基础单元按照某种规律反复迭代生成复杂物体,上一变化的结果即为下一变化的开端,如果将输入称为因,输出称为果,那迭代的运作机制就是: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循环往复,直至无穷[16]。
一个村庄的诞生,最初都是少数人因某种缘由选择一处福祉定居,建造屋舍,后由于生活需要和功能需求,不断扩大住所的规模,进而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村落,即一个单体建筑经过多次的迭代复制后,最终生成聚落。以间作为基本分形空间单元,根据功能进行适当的放大或缩小,再进行并列或垂直排列组合,形成三间两耳一颗印式云南彝族民居空间形式;以宅作为分形单元,通过复制排列组成同一家族聚居的院落形式;以院作为分形单元,顺应交通分布和地形变化,通过缩放旋转,排列组合逐渐迭代生成不同尺度的街道;为满足人口的需求以及经济的发展,街道通过进一步复刻相似的经济模式从而迭代为具有区域特色的村落,进而形成了间-宅-院-街道-村落迭代规律的彝族村落,见图7。

图7 村落空间迭代机制
5 结语
中国文化起源于传统村落,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这种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尤其珍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源泉,而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诠释着乡情、宗情、落叶归根等民族情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人们多重视文化内涵的传承及体现,缺乏对村落发展所蕴含的自身规律的研究,使得村落的保护优化只有形,没有魂。分形理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可用来研究自然界中的复杂现象,挖掘自身的发展规律,为探索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观。传统村落是在自然环境下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而人工形成的一个聚落,村落内部空间形态复杂并丰富,外部边界破碎且不规则,利用分形理论定量研究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特点,既有科学意义,又有实际意义。
打黑村空间形态受自然地形地貌的影响,在社会人文因素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一个靠民族精神纽带维系的稳定聚落,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通过量化研究不同尺度下空间形态的分形维数值,对比分析得出,打黑村的不同尺度层级空间形态的相似性较高,空间结构的连续性好,稳定性强,空间形态复杂。本文试图在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中引入分形理论,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得出了彝族村落具有村落形态自相似性、文化内涵标度不变性及空间形态迭代生成性的分形哲学规律,为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探索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