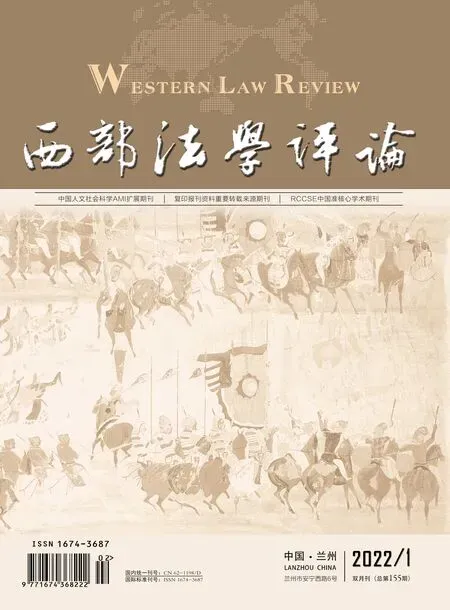论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
——兼评RCEP投资待遇规则
闫 旭
由于公平公正待遇本身的抽象性与模糊性,再加上其多元化的规定模式,导致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成为最具争议性的条款之一。实践中,对于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往往涉及到最低待遇标准,然而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处于模糊状态,是否应当参照最低待遇标准来解释公平公正待遇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理论界与实务界。有观点认为,引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于限制仲裁庭的扩张解释没有发挥预期作用。(1)参见陈正健:《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新发展:表现、效果及应对》,载《法学论坛》2015年第6期。但也有观点指出,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使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义务要素的认定更加严格和狭窄。(2)参见王彦志:《国际投资法上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改革的列举式清单进路》,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
当前,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仍然是公平公正待遇的主流规定方式,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多,包括我国近期签订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采用了此种规定方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之间的关系,明晰在何种情况下应当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解释公平公正待遇,以及参照最低待遇标准对于解释公平公正待遇的实际效果,并根据得出的基本结论对RCEP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进行具体评析。
一、关系问题之缘起
在国际交往初期,外国投资者通常享有投资东道国的国民待遇。随着国际投资的不断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法治状况良莠不齐,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待遇已不能满足投资者需求,缺乏最基本的保护外国人及其财产的措施。在此情形下,发达国家提出确立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以应对东道国保护程度过低的情况,通过国际法为外国人提供一些基本权利,规定国家不论其国内立法和实践如何,在对待外国国民及财产时都必须尊重的一套最低原则,违反该最低待遇标准即可能导致国家承担国际责任。(3)Alexandra Diehl. The Core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145.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就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存在分歧。发达国家支持使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国民待遇进行限定,而发展中国家则对此极力反对。在国际投资法律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如果明确强调内容抽象、带有歧视意蕴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而不赋予其具体内容,显然很难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于是,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开始在“公平公正”这一看似中立,更易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包装下被逐步引入国际经济条约。(4)参见刘笋:《论投资条约中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6期。
国际法律体系逐渐丰富了最低待遇标准这一概念,1926年的Neer案是有关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里程碑案例,对最低待遇标准的概念产生重要影响。该案确立了国家违反最低待遇标准的严格责任门槛,即行为只有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才构成对最低待遇标准的违反。(5)L.F.H. Neer & Pauline Neer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1926) IV RIAA 60.该案主要涉及一位美国国民认为墨西哥当局没有对其丈夫的谋杀案进行适当的调查,这种失误构成“拒绝司法”,从而违反了国际法。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对于是否应当参照Neer案确立的严格责任标准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当下所适用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依然应当采用Neer案所确定的严格责任标准。但也有观点指出,当下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对于Neer案标准已经向前演进,即违反标准的责任门槛已经明显降低。
虽然公平公正待遇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之间的关系争论不断,但这并未妨碍仲裁庭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来解释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热情。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对于公平公正待遇解释所发挥的作用产生新的变化,由限制低水平的国民待遇,逐渐转变为限制高水平投资保护的角色。实际上,对于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所发挥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二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规定方式。在条约中明确规定与最低待遇标准相关联的情况下,仲裁庭应当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来解释公平公正待遇,但实际限制效果在仲裁实践中存在争议。在条约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公平公正待遇往往被理解为独立的待遇标准。此种情况下,是否应当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在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对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分情况进行分析探讨。
二、条约中明示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
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最初主要得到美国、加拿大的条约实践、NAFTA有关案例的支持。长期以来,理论界和仲裁实践对此褒贬不一,但选择这种方式来规定公平公正待遇的投资条约仍然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可归于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使判断东道国违法行为的责任门槛达到一个较高的标准。然而,研究表明,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没有形成对待遇义务内容的有效限制,仲裁庭往往基于最低待遇标准“演进性”的观点对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内容做扩张解释。此外,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的证明方式在实践中往往被模糊处理。上述两点原因导致公平公正待遇涵盖内容的不确定性,将二者相联系的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一)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确定的责任门槛较高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1105条是将公平公正待遇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典型规定。该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当给予他国投资者依据国际法的待遇,包括公平公正待遇以及全面的保护与安全。”由于国际法渊源的多样性,NAFTA仲裁庭在适用该条款时做出了极宽泛的解释。为了扭转此局面,2001年北美自由贸易委员会(FTC)颁布关于NAFTA第1105条的解释,指出“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是提供给其他缔约方投资者的最低待遇标准。”该解释将NAFTA中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渊源限定为国际习惯法,排除了国际法一般原则等其他国际法渊源。(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FTC解释的目的是为了限制NAFTA相关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扩大解释,然而实践中仍然有部分仲裁庭忽略FTC解释对其设定的限制。例如,Mondev诉美国案中仲裁庭指出应当参考“世界主要法律体系所认可的正义原则”。ADF诉美国案仲裁庭明确参照了“文明国家所认可的一般法律原则”。同样的,在United Parcel Service of America诉加拿大案中,仲裁庭没有单纯依据习惯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而是参考了一般国际法律体系(the general body of international law)。
自FTC解释出台后,NAFTA仲裁庭在解释最低待遇标准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参考Neer案确立的判断标准。但该案主要涉及对外国人实体安全(physical security)的保护,而非针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保护。因此,实践中一些仲裁庭认为Neer案、Roberts案和Hopkins案等关于最低待遇标准的裁决不能够直接适用于现在的外国投资领域。例如,ADF诉美国案的仲裁庭认为:“没有任何逻辑必然性以及任何一致的国家实践,支持将Neer案的结论自动适用于现今东道国对投资者以及投资的待遇问题上”。(7)ADF Group Inc. v. United States, ICSID No. ARB(AF)/00/1, Award, 9 January 2003, Para. 181.应当认识到,Neer案所确定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涉及政府行为的国际合法性问题,并不是有关于投资者的相关待遇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直接适用Neer案解释公平公正待遇,仅仅是将抽象的、不确定的“公平”和“公正”的概念与Neer案中“惊人的”“震惊的”相交换。(8)Roland Kläg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88.因此,在实践中直接将Neer案中的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适用在外国投资这一专业领域,其正当性不免受到质疑。
但实践显示,绝大多数仲裁庭将Neer案所确定的标准直接适用于判断行为是否违反公平公正待遇,即当缔约国的行为达到极端恶劣或极不公正的程度,才有可能导致违反公平公正待遇义务。例如,S.D. Myers诉加拿大案仲裁庭要求,当投资者所遭受的专断行为“从国际视角看是不可接受的”才满足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标准。(9)S.D. Myers Inc. v. Canada, UNCITRAL, First Partial Award, 13 November 2000, Para. 263.Waste Management诉墨西哥案仲裁庭强调需要是“完全武断的行为”。(10)Waste Management, Inc. v. Mexico, ICSID No. ARB(AF)/00/3, Award, 30 April 2004, Para. 115.Thunderbird诉墨西哥案仲裁庭要求行为达到 “低于国际标准的明显的任意性”的程度。(11)International Thunderbird Gaming Corporation v. Mexico, UNCITRAL, Award, 26 January 2006, Para. 163.可以明确的是,与最低待遇标准相联系的公平公正待遇,使判断东道国违法行为的责任门槛达到较高的标准。
(二)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演进性”特征导致待遇内容扩张
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始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争议的焦点问题。尽管晚近投资条约中频繁使用“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这一措辞,但没有协定就该标准的含义给出定义,直到今天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仍然未形成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尤其应当注意到,实践中仲裁庭往往强调最低待遇标准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仲裁庭的扩大解释,导致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不确定性。例如,在Pope & Talbot诉加拿大一案中仲裁庭特别指出:“国际习惯法原则并没有冻结在Neer案时期,国际习惯法通过国家行为而演进变化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方面”。(12)Pope & Talbot, Inc. v. Canada, UNCITRAL Arbitration, Award in Report of Damages, 31 May 2002, Paras. 57-66.在ADF诉美国案中仲裁庭同样指出最低待遇标准是不断演进的。仲裁庭以国际习惯法的演进性特征作为扩张解释的借口,绕过FTC解释渊源的限制,对与最低待遇标准相关联的公平公正待遇给予宽泛的解释,导致这种解释下的待遇标准往往高于最低待遇标准。(13)Patrick Dumberry,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A Guide to NAFTA Case Law on Article 1105.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3, P. 109.甚至在Merrill & Ring诉加拿大一案中,仲裁庭认为国际习惯法近年来演进变化迅速,导致国际习惯法下的最低待遇标准与不受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趋于等同。
如果以静止或退化的观点来解释公平公正待遇,会打消未来投资者在特定国家进行投资的积极性。(14)Barnali Choudhury, Evolution or Devolution: Defining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05, 6 (2), P. 320.然而,那些基于最低待遇标准“演进性”进行解释的仲裁庭,几乎很少试图去解释最低待遇标准的演进程度,以及时至今日该标准应有的含义是什么。实际上,即便有少数仲裁庭尝试解释其演进后的具体内容,但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作为通适于外国人的待遇标准,其演进后所形成的内容除了应满足国际习惯法的构成要件之外,还需由国际法院这样的权威性机构作出认定,而不能听凭形形色色的临时国际投资仲裁庭群起妄断。(15)参见徐崇利:《公平与公正待遇: 真义之解读》,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所以演进后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此可见,参照这样一个内容不确定的待遇标准来解释公平公正待遇对于厘清待遇内容所提供的帮助有限。
(三)国际习惯法证明方式模糊处理导致解释内容缺乏正当性
习惯国际法的证明方式在实践中往往被模糊处理。具体而言,仲裁庭对于公平公正待遇具体义务内容的认定倾向于单纯依靠仲裁裁决等辅助性渊源,而非逐案分析满足国际习惯法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尽管NAFTA在第14章附件中明确规定,“最低待遇标准”条款中所提及的国际习惯法需要经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个要件验证后得出,但根据NAFTA相关仲裁实践显示,仲裁庭依然倾向参照之前的仲裁裁决和学术著作来进行判决,并未提供充足的关于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方面的证据。(16)Matthew C. Porterfield, A Distinction Without a Differe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Under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by Investment Tribunals, Investment Treaty News, 2013, 3(3), P. 4.而且,由于其依赖的仲裁裁决也并非基于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这两个构成要件得出,所以,在此情形下得出的解释内容缺乏正当性。此外,国际习惯法证明责任的归属问题在实践中同样存在诸多争议。例如,在Glaims诉美国一案中,仲裁庭明确公平公正待遇义务需要经国际习惯法构成要件的检验。但又指出,投资者应当承担证明东道国违反国际习惯法的义务,证明该项义务内容是基于确实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形成的国际习惯法。(17)Glamis Gold, Ltd. v.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ward, 8 June 2009, Paras. 600-605.然而,让投资者承担公平公正待遇的义务内容形成国际习惯法的证明责任,显然负担过重,在实践中也较难实现。
三、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
未附加限制条件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往往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外资待遇标准。(18)Christoph H. Schreu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Arbitral Practice, 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 2005, 6(3), P. 364.一般情况下,这类条款都宽泛地规定给予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不附加其他条件和限制。相关约文多表述为“给予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依据国际法的公平公正待遇”或“依据国际法原则的公平公正待遇”。实践中,仲裁庭对于是否需要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来解释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存在诸多争议,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观点。其中,不需要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为当前仲裁实践中的主流观点。
(一) 不需要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
仲裁实践中,大部分仲裁庭认为,不需要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解释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因为如果条约缔约方想要提及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应当在条约中指明,而不是使用这种不附加条件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19)Dolzer Rudolf, Stevens Margret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Martinus Nijuhoff Publishers, 1995, P.11.该类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从条约文本解释的角度出发,如果缔约国想表达的真实意思是想参照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条约会使用“公平公正待遇”这一表达方式去代指这一众所周知的概念。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最低待遇标准与公平公正待遇标准一样,都是内涵不确定的概念,因此不能够用以解释公平公正待遇。(20)Christoph H. Schreu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FET):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standards,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2007(4), P.2.该观点同样被一些权威机构所认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研究报告曾指出,尽管公平公正待遇和最低待遇标准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互重合的内容,例如专断行为,歧视和非理性对待等情形,但并不意味着投资条款中的公平公正待遇自动包含国际最低待遇标准。(21)UNCTA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1999, P.40.
仲裁庭在不考虑最低待遇标准的情形下,根据平义解释的公平公正待遇的含义往往更加宽泛。例如,Enron诉阿根廷案仲裁庭指出,公平公正待遇可能包含那些不属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具体义务,某种程度上比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更宽泛。同样的,在Cargill 诉墨西哥一案中,仲裁庭认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义务范围比自治的公平公正待遇要窄很多,因为存在违反行为严重性的要求。有仲裁庭总结,自治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包含保护投资者合理期待、诚实善意、透明度、一致性以及正当程序,然而以上的这些内容并未完全反映在最低待遇标准的义务内容中。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包含透明度义务,但透明度义务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通常不被视为是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22)OEC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Working Papers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o.2004/3, September 2004, P. 37.Glamis Gold诉美国一案中,美国明确表示 “NAFTA的三个缔约方都认同第1105条不包含透明度义务并且明确否认透明度的概念存在于国际习惯法”。(23)Glamis Gold, Ltd. v.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NCITRAL, Award, 8 June 2009. Para. 580.同样的,有仲裁庭认为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包含法律体制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24)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and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a, ICSID No. 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 3 October 2006, Para. 131.然而NAFTA下的Mobil诉加拿大案的仲裁庭认为,“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国际习惯法包含保证稳定的法律和商业环境的义务”。(25)Mobil Investment Canada Inc. and Murphy Oil Corporation v. Canada, ICSID No. ARB(AF)/07/4, Decision on Liability and on Principles of Quantum, 22 May 2012, Para. 153.由此可见,在不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的情况下,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包含更宽泛的义务内容。
(二) 是否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不存在区别
有观点认为是否参照最低待遇标准对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不会造成实质影响。换言之,无论是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还是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等同的公平公正待遇,二者的解释结果不存在实质不同。(26)Deutsche Bank AG v.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ICSID Case No. ARB/09/2, Award, 31 October 2012. Para. 419; Saluka v.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17 March 2006, Para. 291; Azurix Cor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12, Award, 12 July 2006, Para. 361;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Award, 12 May 2005, Paras. 282-284; Occidental Exploration & Prod. Co. v. Republic of Ecuador, UNCITRAL, London Cour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ase No. UN3467, Award, 1 July 2004, Para. 190.这一观点也被称为是“融合性(Convergence)”学说,该观点尤其为那些提倡国际习惯法演进性特征的学者和仲裁庭所支持。他们认为,演进后的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与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相等同。例如,Merrill & Ring诉加拿大案仲裁庭指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没有被冻结在过去,而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在向前演进,演进后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和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提供给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是相同的。(27)Merrill & Ring Forestry L.P. v. Canada, UNCITRAL, Award, 31 March 2010, Para. 210.但实际上,上述说法并没有解释最低待遇标准是如何演进的,也没有论证演进后最低待遇标准的具体内容是否满足国家行为一致与法律确信的构成要件,仅强调演进后的结果相同,不免让外界怀疑他们只是用演进性特征作为扩张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借口。并且,强行将最低待遇标准与公平公正待遇相等同,外表看似二者关系被“和谐”处理,但实则是对是否参照问题的回避。
(三)应当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
实践中,部分仲裁庭认为应当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解释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这尤其体现在仲裁庭对那些约文表述为“符合国际法要求的公平公正待遇”或“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中。任何缔约国都不可能脱离一般国际法的背景规则去订立条约,就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而言,缔约国在签订条约的过程中不会讨论或谈判“公平”和“公正”这二者的具体概念,而是决定是否在条约中嵌入公平公正待遇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含义模块(module of meaning)。公平公正待遇这个模块已经被重复运用在大约2500个条约中,它的内涵并不取决于任何文字表述的细微变化,而是基于一般国际法。(28)Santiago Montt, State Liability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Global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in the BIT, Hart Publishing, 2009, P. 305.这意味着对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将不可避免地参考到国际法中的最低待遇标准或是国家所认可的一般国际法原则。例如,Siemens诉阿根廷案的仲裁庭指出:“尽管条约中没有规定要参照最低待遇标准,但在考虑‘公平与公正’本义的同时,也必须在国际法中寻找这些条款的含义”。(29)Siemens AG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No. ARB/02/8, Award, 17 January 2007, Para. 291.据此,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理所当然成为解释的参照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类仲裁庭持有的观点是“应当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但并不意味着其解释结果受最低待遇标准的限制。换言之,作为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只是其解释过程中的参照对象,并不能起到限制解释内容的效果。
但与上述仲裁庭不同,一些仲裁庭认为不但要参照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同时最低待遇标准能够起到限制解释的作用。在Saluka 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作为国际习惯法的最低待遇标准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一国具有约束力。(30)Saluka v.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17 March 2006, Para. 292.同样的,Alex Genin诉爱沙尼亚案的仲裁庭认为,国际法下的公平公正待遇要求东道国提供独立于东道国国内法的一般待遇标准。考虑到该标准的内容尚未确定,因此应将其理解为不同于国内法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31)Alex Genin, Eastern Credit Limited, Inc v. Republic of Estonia, ICSID Case No. ARB/99/2, Award, 25 June 2001, Para. 367.这种理解事实上是将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等同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使解释内容受到最低待遇标准的限制。(32)参见刘笋:《论投资条约中的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6期。
实际上,受“国际法”或者“国际法原则”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与未附加限制条件的公平公正待遇之间不应当存在区别理解。条约是以国际法为准的协议,它的订立、效力、解释和适用等问题是由国际法来规范的,投资条约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作为国际法的产物自然不能脱离国际法的约束而自成一体。因此,条约文本中不受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和依据“国际法”或“国际法原则”的公平公正待遇等类似的表述在本质上不存在实质区别,后者并没有增添任何实质义务内容。实践中仲裁庭倾向于对有“国际法”或“国际法原则”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参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进行解释,可能是因为条文中存在“国际法”或“国际法原则”的具体表述,能够使其依照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解释内容更易取得正当性。
(四)关系讨论没必要,应当关注内容要素
除了上述三种观点外,还有部分观点认为,无论是作为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还是参照最低待遇标准的公平公正待遇,二者在解释方法上不存在不同,都是关注公平公正待遇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包含的子要素。换言之,很多仲裁庭认为这样的讨论不存在实际意义,对于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关系问题的讨论已慢慢转向公平公正待遇所包含的内容要素的讨论。例如,Azurix诉阿根廷案的仲裁庭表示,公平公正待遇是否是比国际法规定的最低待遇标准更高的待遇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关于该待遇的实质内容。(33)Azurix Corp. v. Republic of Argentina, ICSID Case No. ARB/01/12, Award, 14 July 2006, Paras. 368-370.同样的,在2016年Allard诉巴巴多斯共和国案中,仲裁庭认为无需判断公平公正待遇是等同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还是一项独立的待遇标准,关键问题在于判断公平公正待遇是否包含投资者合理期待的义务内容。(34)Peter A. Allard v. The Government of Barbados, PCA Case No. 2012-06, Award, 27 June 2016, Para. 192-194.仲裁庭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公平公正待遇应当包含的内容要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欧盟等投资条约缔约国选择通过列明内容要素的方式规定公平公正待遇条款。
四、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与最低待遇标准的比较分析
仲裁实践显示,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解释渊源并未指向既定的法律体系或已有的法律先例,大部分仲裁庭倾向于在个案中具体考虑外国投资者是否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根据仲裁员主观认为的什么是“公平的”和“合理的”来进行解释。(35)F. A. Mann, British Treatie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2, 52(1), PP. 251-254.在此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矛盾情形。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政府的行为有可能是符合公平公正待遇的。但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政府行为有可能被认为没有提供公平公正待遇。换言之,国家发展水平不同,对何为公平公正待遇的理解会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不确定性。(36)Stephen Vasciannie, The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and Practice, The British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9, 70(1), P. 161.其次,什么是“公平的”或者“合理的”是非常概括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任由仲裁员主观定夺,缺乏明确性,容易导致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独立自主的外资待遇标准在其适用上“法官造法”的特点明显。(37)参见徐崇利:《公平与公正待遇标准:国际投资法中的“帝王条款”?》,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据统计,仲裁庭认定东道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行为已多达11种,而随着新的国际仲裁裁决判例的发展,公平公正待遇可能还会增添新的内容,导致公平公正待遇成为一个内容不断膨胀的外资待遇标准。(38)参见徐崇利:《公平与公正待遇: 真义之解读》,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在此情形下,公平公正待遇内容宽泛,东道国任何有“瑕疵”的行为都有可能面临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风险。
据统计显示,NAFTA项下的公平公正待遇和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相连,原告的成功率要远低于依据独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提出主张的成功率,这主要是由于最低待遇标准所适用的高责任门槛。(39)UNCTAD.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UNCTAD Series on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I, 2012. P. 110.Saluka 诉捷克共和国案中仲裁庭指出,作为国际习惯法的最低待遇标准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一国具有约束力,即使国家遵循的政策是反对外商投资,仍然需要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最低限度的保证。在此情形下,与最低待遇标准相连的公平公正待遇提供给投资者不超过最低限度的待遇。因此,政府的行为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不合理的程度才导致政府行为违反该待遇标准。但考虑到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结目的往往是为了促进缔约国之间的直接投资和经济交往,在此背景下的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旨在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个积极的鼓励。因此,政府行为达到较低程度的不合理就有可能违反该待遇标准。(40)Saluka v. Czech Republic, UNCITRAL, Partial Award, 17 March 2006, Paras. 292, 293. (“in order to violate the unqualified FET standard, it may be sufficient that States’ conduct displays a relatively lower degree of inappropriateness”).可见,将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将投资者的保护限制在“极端的情况下”,提高了东道国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责任门槛。与之相反,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能够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加包容的保护,是一种保护程度更高的独立待遇标准。
对此,有观点认为,这样的解释结果符合缔约国设置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初衷,因为投资条约缔约国签署条约是为了给予投资者最好的保护,所以降低投资者的保护标准可能并不是缔约国的真实意图。(41)Marcela Klein Bronfman,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 Evolving Standard, Max Planck Yearbook of United Nations Law, 2006(10), P.666.但应当注意到,许多曾经反对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签署的投资条约中同意嵌入公平公正待遇,这些国家是基于期望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门槛会高于国际最低待遇标准。(42)Hussein Haeri, A Tale of Two Standards: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 and the Minimum Standard in International Law,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011, 27(1), P.32.在最低待遇标准盛行时,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推行卡尔沃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主张对外国人适用国民待遇,即外国人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享有与本国国民所享有的待遇相等同的权利。所以很难理解那些发展中国家设立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的意图是为了提高对投资者的待遇。因此,扩大待遇内容,降低责任门槛,让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提供给投资者高于最低待遇标准的保护程度并不是缔约国最初缔约时的本意,而是仲裁庭肆意解释的结果。
然而,仲裁庭的肆意解释并非“空口无凭”,独立的、未做任何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给仲裁庭的扩张解释提供了充分“借口”。不同的规定方式显示了缔约国对于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所要实现的不同目的,最低待遇标准是为了防止针对外国人的行为低于某一特定的国际法责任门槛,是消极义务。Glamis Gold案中仲裁庭认为:“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是一个最低标准,它的意义是作为一个基底(as a floor),一个绝对的底层,在此之下的行为都是不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43)Glamis Gold Ltd v. United States, UNCITRAL, Award, 8 June 2009, Para. 615.而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标准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能够“促进”“创造”“激励”权利,是积极义务,可以理解为为投资者提供任何能够保证其享有公平的和公正的待遇环境的义务。(44)MTD Equity Sdn Bhd and MTD Chile SA v. Chile, ICSID Case No. ARB/01/7, Decision on Annulment, 21 March 2007, Para. 71.换言之,任何有可能被解释为“公平的”“公正的”义务内容都会被涵盖在公平公正待遇中。如此理解下,仲裁庭对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内容扩张解释的现象不足为奇。不过,如上文第二章中分析,仲裁庭扩张解释的现象并不限于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最低待遇标准“演进性”特征为仲裁庭的扩张解释提供了说辞。可见,最低待遇标准也不是对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内容进行有效限制的“灵丹妙药”。
五、RCEP中的公平公正待遇评析
近年来,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数量还在不断增多,RCEP的投资待遇条款也同样采取了此种规定方式。该条款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当依照国际习惯法外国人最低待遇标准给予涵盖投资公平公正待遇”,并在此基础上规定,“公平公正待遇要求每一缔约方不得在任何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中拒绝司法”。可见,RCEP在条款中明确列举了“不得拒绝司法”的单项义务。同时,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平公正待遇不要求给予投资在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之外或超出该标准的待遇”。这意味着东道国依据公平公正待遇所承担的保护义务受到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的限制。相对来讲,这样的表述方式比约文中使用“参照”或“依据”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表述方式更有助于限制仲裁庭扩张解释。
还应当注意到,RCEP在附件中特别指出,投资待遇条款所提及的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是源于各国对法律义务的遵循而产生的普遍和一致的实践。实际上,诸多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规定方式的缔约国都选择在附件中进一步明确国际习惯法的证明方式,试图以此限制仲裁庭依据仲裁先例对公平公正待遇进行的扩张解释,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一)条款可能存在的风险及漏洞
1.内容不确定造成仲裁庭扩张解释的风险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使用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限定公平与公正待遇的方式能够在责任门槛上达成较为一致的高标准,即当东道国明显的(obviously)、严重的(grossly)、故意的(deliberately)情形才能构成对公平与公正待遇的违反。然而,最低待遇标准本身内容模糊,用来解释公平公正待遇同样会造成义务内容不确定。尤其在仲裁实践中,大部分仲裁庭都是依靠先前的仲裁裁决来确定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而非基于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这两个构成要件来判断。同时,随着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发展,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演进性”特征也使其内容范围变得愈发宽泛。在此情况下,仲裁庭在确定何为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问题上依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公平公正待遇存在被扩张解释的风险。
RCEP对于公平公正待遇的情形仅明确列出“不得拒绝司法”这一项义务作为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内容。有观点认为表述方式采用的术语是“要求(requires)”而非“包括”,是一种封闭式列举,应当理解为将公平公正待遇完全限定在了“不得拒绝司法”的义务范围之内。(45)参见王彦志:《国际投资法上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改革的列举式清单进路》,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6期。但这种理解并不适用于RCEP,因为条文第3款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平公正待遇不要求给予投资在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之外或超出该标准的待遇”。如果缔约国的原意是公平公正待遇仅指不得拒绝司法这一项义务内容,则没有必要在后文中规定义务内容不可超出最低待遇标准这一限制条件。因此,单纯的列明和纳入这项义务的意义是使其可以直接适用于争端解决,并不意味着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限于不得拒绝司法这项义务。换言之,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仍然取决于仲裁庭在实践中的具体解释与适用。因此,不排除被扩张解释的可能。例如,美国与中美洲五国多米尼加2004自由贸易协定(CAFTA-DR)对于公平公正待遇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但在实践中仲裁庭仍然对该条款作出宽泛的解释。基于该条约,在Railroad诉危地马拉一案中,仲裁庭认为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下的公平公正待遇应当包括尊重投资者合理期待,透明度、非歧视、不得专断、非恶意和遵守正当程序。(46)参见Railroa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v. Republic of Guatemala, ICSID Case NO. ARB/07/23, Award, 29 June 2012.可见,即使基于最低待遇标准和不得拒绝司法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进行限定,公平公正待遇所包含的内容范围仍然可能比较宽泛。
尤其应当注意到,近年来仲裁庭往往基于国际习惯法最低待遇标准向前演进的观点,将投资者合理期待要素包含在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范围内。RCEP在投资待遇条款中并没有对该要素作出特别规定。考虑到投资章节第一条对投资的定义包括“收益或利润的期待”,这意味着投资者合理期待符合投资的定义。可以推测,这样的规定很容易让仲裁庭作出扩大解释,将投资者合理期待要素包含在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中。换言之,此种规定方式扩大了投资者基于违反投资者合理期待要素对东道国提起仲裁的风险,也相应地增加了东道国的败诉风险。
2.忽略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
尽管公平公正待遇的模糊性特征使其可以灵活解释,达到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目的,但如果国际投资条约中缺乏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安全港”方面的规定,这种“敞口”状态不排除会为投资者恶意利用,进而对缔约东道国造成不利影响(47)参见余劲松、梁丹妮:《公平公正待遇的最新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对策》,载《法学家》2007年第6期。。尤其应当注意到,晚近一些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采用扩张解释的态度,要求东道国负有保证法律框架稳定性的义务。在此情况下,缔约国基于保护公共利益而更改法律的行为,也会面临被投资者诉至仲裁庭主张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条约规定的“先天不足”容易造成仲裁庭片面强调投资者利益,忽略东道国的正当规制权,造成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利益失衡。RCEP中既没有对公平公正待遇本身设置相应的例外条款,一般例外条款中也并未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管制措施进行排除。同时,争端解决条款也没有将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规制措施排除在外。在此情况下,缔约国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正当行使规制权的行为也极有可能被投资者以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理由诉至争端解决机构,容易造成规制权空间受到不当挤压,公共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二)条款优化路径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RCEP的投资待遇条款主要存在义务内容不明确以及对公共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实际上,任何缔约国所承诺的投资保护都不会以牺牲本国主权为代价。之所以在实践中出现仲裁庭的扩张解释,缔约国规制权受挤压的状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缔约国在授权之初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对主权的风险及影响没有作出充分的预期。(48)参见李庆灵:《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缔约国解释:式微与回归》,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当前,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资本输入国以及第二大资本输出国,在国际投资中身份混同的特点更加要求中国在签订国际投资协定时应当审慎考虑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设置。既要保护“走出去”的中国投资者的利益,同时又不能将标准放的过宽,为我国正当行使规制权留有空间。
尽管RCEP已经生成正式的条约文本,但可以尝试通过附件、法律解释文件等方式对RCEP的投资待遇条款进行完善。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中国主要采用嗣后协定的方式,例如,与德国、瑞典、荷兰等不少国家就投资条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达成相关议定书(49)LG&E Energy Corp., LG&E Capital Corp., and LG&E International, Inc. v. Argentina, ICSID No. ARB/02/1, Decision on Liability, 3 October 2006, Para. 131.。本文认为,应当进一步明确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内容,同时设置相应的例外条款以保护东道国的施政空间,从而有助于实现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内容的明确性,对仲裁庭自由裁量空间的限定性以及对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均衡保护。
1.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具体义务内容
随着仲裁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演进,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核心义务内容已经渐趋明确和稳定。可以说,演进的判例法已经识别出诸多成熟且稳定的公平公正待遇的具体义务内容(50)Rudolf Dolzer, Fair and Equitable Treatment:Today’s Contours, Santa Cla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4,12(1), PP.10-11.。但相较于仲裁庭在具体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在条约中明确公平公正待遇的具体内容更有助于还原缔约国本意。同时,仲裁庭在解释和适用公平公正待遇时,对于条文中明确标出的义务内容可以直接适用。这样的方式使得仲裁庭在解释的过程中有确定的标准可循,解释结果更具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应当注意到,即便是一直以来推崇与最低待遇标准结合规定方式的美国,也开始在近期的条约实践中采用明确义务内容的方式对公平公正待遇条款进行具体化。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第9.6条采用的是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并且在条款中明确列举了“正当程序原则”“不得拒绝司法”这两项义务内容。实际上,纵观仲裁实践,经国际习惯法构成要件检验,真正构成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应当包括不违反正当程序、不得采取专断措施以及不得拒绝司法。由此可见,RCEP中所列举的义务内容除了“不得拒绝司法”以外,至少还应当包含正当程序原则和不得采取专断措施。
此外,还应当注意对投资者合理期待这项义务内容进行明确。例如,2020年7月1日生效的《美墨加协定》尽管大体上保留了NAFTA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规定模式,但仍然辅之以清单模式对义务内容进行明确。在原NAFTA公平公正待遇内容的基础上又新增一条规定,“当一方采取或未采取的措施与投资者期待不相符时,无论涵盖投资是否因此受到损失或损害,不构成违背最低待遇标准。”2018年签订的CPTPP第9.6条最低待遇标准也采用了同样的规定方式,对投资者合理期待义务进行排除。除此之外,一些投资条约对投资者合理期待义务内容进行细化区分。例如,《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仅承认缔约国对投资者作出特别陈述而产生的合理期待,但明确否认投资者基于缔约国法律稳定性而产生的合理期待。第8.9条规定,缔约方修改法律的管制行为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或者挫败了投资者的期望(包括其对利润的预期),不构成违反本节下投资保护的义务。对此,RCEP可以参考上述规定内容,将投资者合理期待义务进行具体细化处理,保留缔约国对投资者作出具体承诺的保护义务,排除投资者基于法律稳定性产生的投资者合理期待义务。换言之,保留缔约国在必要情况下,基于正当目的修改法律的权利。
2.设置例外条款
实践中,仲裁庭在解释例外条款时,往往受限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而作出狭义解释。例如,在Enron诉阿根廷一案中,仲裁庭认为条约的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因此对条约所作出的任何解释都不应当轻易地免除缔约国的义务,例外条款也不例外,必须对其做狭义解释(51)Enron Corp. v. Argentina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Award, 22 May 2007, Para. 325.。值得肯定的是,RCEP在序言条款中强调缔约方为实现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而进行监管的权利。但是,单纯的序言条款只是原则性规定,仲裁庭在对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过程中不能够直接适用。在此情况下,如果公平公正待遇配套以相应的例外条款,能够更好地保证东道国行使正当规制权的空间。应当注意到,基于公共利益原因设置间接征收例外的国际条约实践相对较成熟,通常规定缔约一方采取的旨在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等合法公共福利的非歧视的法律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投资条约可以参照设置公平公正待遇的例外。当然,如果上述例外能够适用于整个条约的话,则不必对公平公正待遇单独设立例外条款(52)参见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此外,还可以考虑将基于公共利益采取的措施排除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范围之外。例如,中澳FTA投资章节下第11条第4款规定,“一方采取的非歧视的和出于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等合法公共利益目标的措施,不应作为本节项下诉请的对象。”这一规定意味着,投资者不能将东道国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以违反公平公正待遇的理由诉至仲裁机构。由此,既保护了公共利益,又同时维护了东道国正当行使规制权的空间。
结 语
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协定中公平公正待遇标准的规定方式。其一,条约中明确与最低待遇标准相联的情况下,仲裁庭对公平公正待遇的解释受国际最低待遇标准的限制。NAFTA相关仲裁实践显示,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使得判断东道国违反待遇标准的责任门槛较高,但仲裁庭往往基于国际习惯法“演进性”特征进行扩张解释,导致待遇内容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二,在条约未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公平公正待遇往往被理解为独立待遇标准。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与最低待遇标准的关系在实践中主要存在四种不同情形。主流观点认为,其不受最低待遇标准的限制——这导致实践中独立的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宽泛,且责任门槛较低。可见,条约可采用明确内容要素和责任门槛的方式,以避免仲裁庭的扩张解释。RCEP采用与最低待遇标准相结合的公平公正待遇,这一规定存在待遇内容被扩张解释的风险。因此,有必要明确待遇的具体义务内容,同时考虑设置相应的例外条款,维护东道国正当规制权空间。
——来自广西金秀的田野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