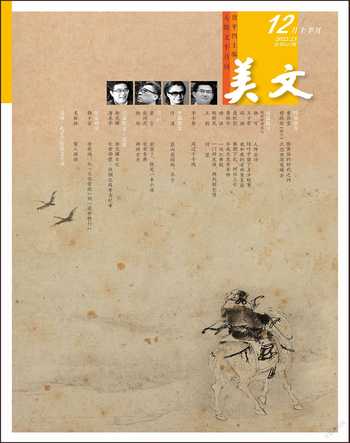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泥步修行”
韩少玄
似乎一段时间以来,余秋雨先生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以至于,我们只能谈论他的过去,比如他的《文化苦旅》,比如他在“青歌赛”的精彩点评等,除此之外,对于余秋雨先生近些年的工作与生活,确实知之不多。 实际上,余秋雨先生从来未曾刻意离去,只是他越来越倾心一种“大隐”的生活方式,他说“这种生活方式有一个最简单的标志,那就是谁也找不到我”。“大隐”的生活,给予他安静、给予他自由,安静的生活、自由的行走。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行走的意象,贯穿于余秋雨先生文化思考和写作的始终,并且成为“当代走得最远的人文学者”。《文化苦旅》《行者无疆》是“行走”,当然《泥步修行》也是“行走”。只不过,他的脚步越发轻快、思绪越发虚灵,远超我们的脚力、心力,这才造成了误会。所幸的是,在“行走”的间隙,余秋雨先生也会稍事停留,告诉我们一路走来的见闻、心得。
敞开书法的生命空间
2017年5月25日,“余秋雨翰墨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为期15天的展出,每一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大多是余秋雨先生各界友朋和读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或许他们互不相识,但是他们面对满壁翰墨几乎同时惊叹,原来余秋雨先生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
于是,观展之余,他们也留下了各自的赞叹——
“在余先生笔下,书法既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也是文化的一种载体,字里行间还原了书法艺术的文化面貌与文人的生活气息。五四运动把书法艺术与文学创作分开了,绕了一大圈,秋雨先生又把它们合到了一起。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冯骥才)
“余秋雨先生的书法,从远处看,有气象,在近处看,有气质,构成了一种能够把人深深吸附住的气场。”(吴为山)
“余秋雨老师的翰墨大展,真名士,大氣概,所有行文内容与笔墨韵致互为注脚,一句“我擎孤笔在汉唐”,万千气象,傲岸孤岑。”(于丹)
……
没有必要再一一引述,激赏之情,已跃然纸上。
毫无疑问,“余秋雨翰墨展”的展陈主体、也可以说是此次展览的最大亮点,是余秋雨先生应各地所请自撰、自书的碑文,如《炎帝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钟山之碑》《大圣塔碑》《金钟楼碑》等,他称之为“重大碑书”。这些作品之所以重要,或如冯骥才先生所言,因其重新实现了书法艺术和文学创作的结合,因此称得上是“历史性大事”。冯先生所言固然不差,但并不尽然。书法与文学的结合,终究不过是在书言书、在艺言艺。依我看来,余秋雨先生的“重大碑书”之所以堪称“重大”,乃是因为他让书法实现了宏大生命空间的回归和重塑。众所周知,秦汉盛唐的书法之所以气象雄浑,乃是因为这一时期书法的存在空间是自然天地、四海天下,一点一画、一碑一石无不与万物共呼吸与日月相辉映。而明清书斋里的书法、当下展厅里的书法,日渐陶醉于小情趣、小格调,如何能够与之相比?当下书法论者往往悲叹今不如昔,徒叹奈何。实际上,当代书法的困境、窘境并不难打破,只要转换书法的存在空间,让书法走出书斋、走出展厅,在自然天地中书写、为万千民众书写,师造化法自然、叩天地问苍生,书法艺术的浑沦磅礴元气自然也就恢复了,困境也就不存在了。更重要的,书法的元气复归了,中国文化的元气也就复归了。元气饱满,一切病灶自然消退。所以说,余秋雨先生之所以不辞劳苦撰、书那么多的大碑,其意不在书,而是为了完成他的文化使命。而且也不难看出来,正是通过“重大碑书”,余秋雨先生审视文化的视角开始转变了,写作“文化大散文”的时候他用的是“人”的视角、“史”的视角,而现在,则更多“自天地而观之”。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余秋雨先生虽然不是以书法作生计的人,相对于书法,他的着眼点始终是宏观意义、终极意义上的文化,书法于他,却也不可等闲视之。他可以由书法思及文化,但是,他却不曾将书法作为思考文化的工具。不止一次听余秋雨先生的妻子、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老师说,近年来,余秋雨先生可以称得上是痴迷书写,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写,墨迹盈室,四下堆叠,于是有诗“满地墨书妻笑点,空筐宣纸夜来添”。对书法,他是真爱。其实,早在《笔墨祭》中,他就说过,“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此处,他看重还仅是书法的审美功能。后来,在一件墨迹跋语中,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今余老矣,终可坦言,此笔墨之秘,并非巧计偶得,实乃余浮生之依。余命何在?辨浓淡墨色、纵横笔迹可也。”
所谓“浮生之所依”,言下之意,乃是视书法为生命。因此,余秋雨先生的书法,与时下诸多跨界书写者不可同日而语,一为名利,一为性命,高下立判。就字论字,余秋雨先生的书法当属二王帖学一脉,于米芾处得笔尤多,点画沉实、结字简约,写来潇洒从容、行云流水,诚如张海先生所说,“光看书法,也是一个大书法家”,此言不虚。
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
“中国文化是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江,而不是江边的枯藤、老树、昏鸦。”这是余秋雨先生在喜马拉雅网络电台主讲“秋雨书院-中国文化必修课”时的导语。每次讲课前,作为开场白,他都会把这句话吟诵一遍。课程结束后,根据授课内容整理出版了《中国文化课》,据不完全统计,收听人次多达六千万。
我们知道,余秋雨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走上荧屏,不仅参与、主持了凤凰卫视电视台的“千禧之旅”,后来还担纲凤凰卫视总策划,每天短短几分钟的“秋雨时分”,成为很多观众最美好的文化回忆。可以说,在借助现代传媒进行学术传播、文化普及方面,余秋雨先生是先行者,他因此被称之为“电视教授”。那么,现在“音频时代”到来了,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化课”应时而生。需要说明的是,此次云端开讲,并不是为了赶潮流,而有着更深的因缘。他说:“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主持的博士生专业,特别难考。眼看那些年轻的优秀人文学者怅然离去,我比他们更加怅然,于是接受喜马拉雅网站的邀请,把博士课程向全社会公开讲授……”
幸运如我,经过再三努力,终于考取余秋雨先生在“秋雨书院”招收的 “中国文化史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如余秋雨先生所言,这门课,是我的专业课,因此我听得特别用心。授课的过程中,余秋雨先生多次提到,希望他的博士生能写下听讲心得给他看一看。很惭愧,迟至今日我也还没能补交这份作业。
“中国文化”相关课程,相信很多高校、研究机构都为他们的研究生开设了,或者必修,或者选修,但是,事实证明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这门课并不太受欢迎更谈不上有魅力。为什么会这样?是这门课程不必要吗?当然不是。应该说,这门课当为全民必修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合理的推断是,学生们不喜欢这门课,原因在于课程内容、授课方式有问题,而不应该责怪学生。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是也”,“传道”是首位的,如果用枯燥而无用的史料、干瘪而虚伪的数据来填充这门课,只能说明“师者”之伪。对此,余秋雨先生深谋远虑,他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以“传道”,“除了讲述自己和古人的著作之外,世上最好的博士课程,一定是‘导师漫谈’。任何一个明智的导师都明白,那些从书上、网上都查得到的通行知识,千万不能多讲,学生们一定讲得比我们更好。如果有足够的自信,一个合格的博士专业导师应该把话题集中到独一无二的亲身感受中……当我把这些人生经历自然融入,课程也就有了体温……”
正因为课程有了“体温”,才会有那么多的听众积极参与,与现实中寥落、昏沉的课堂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也就意味着,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化课”,是有典范性的。这门课,应该这样讲授才合乎要求。平缓的语调、精辟的见解、机敏地感发,这堂课,我听得很是惬意。当然更重要的,我意识到,“中国文化课”不仅应该带着“体温”去讲,也应该带着“体温”去研究,因此我决定摒弃细碎的考辨、抽象的论证而转向体悟、生发。自此,我隐约窥到了学术研究的门径。
余秋雨先生的這堂“中国文化课”,课时很长,足有一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有哪些内容?或者说,他主要讲了哪些对于中国文化独到的见解?
我要说的是,通过这堂课,余秋雨先生讲出了中国文化的美丽。
论及中国文化,没有谁会否认它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就决定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有着数不尽的角度和话题。既然如此,为什么余秋雨先生不论其他,只看重中国文化的美丽?我想,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只有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才更加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生长。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比照下,最早觉醒的那批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了中国文化的腐朽落后,并进而予以批判。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中国文化沉睡的心灵、激活其生命活力。在此过程中,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最英勇的斗士。遗憾的是,刻骨的批判,并没有换来中国文化的新生。相反,却让中国文化越来越趋于西化、迷失自我。若此,谈何复兴?并不是要一味否定文化批判,只是说,仅凭批判并不能迎来中国文化的新生。比批判更适用的方式,是转而发掘、赞颂、承续中国文化的美丽。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懂得中国文化的美丽,都能自觉呵护中国文化的美丽,中国文化才值得期待。这是余秋雨先生最殷切的希望,也是他讲授中国文化美丽的主要原因。
其二,只有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才能破解中国文化的诸多不解之谜。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常常为诸多误解的谜团所困扰,比如为什么四大古文明唯有中国文化能绵延至今,为什么中国文化能够历经劫难而不亡,中国文化到底能为世界文明贡献什么等等。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余秋雨先生没有沿着既有思路去破解,他猜想,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美丽,给予了它恒久的魅力和生命力,美和美学才是破解中国文化奥秘的钥匙。我想,他是对的,尽管证明这一猜想,还需要有大量的工作要展开。
可以说,讲出中国文化的美丽、还原中国文化的美丽,是余秋雨先生文化研究的终极旨归。而美和美学,也就成为了理解余秋雨先生文化思想的核心所在。为此,余秋雨先生早年的一位学生江学恭先生,辑录他所有关于美和美学的文字,出版了一部《大美可追——余秋雨的文化美学》。在这部著作的封底,有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重心归向,有的归向于宗教,有的归向于战争,有的归向于科学,有的归向于政治,有的归向于自然,而中国文化,则归结于艺术。”在这里,艺术,无疑可以理解为美和美学。
对于中国文化的美丽,余秋雨先生是有偏爱的。他偏爱的,是唐代文化的美,准确地说,是唐代文化的“青春气息”和“整体诗性”。关于“青春气息”,他说,“……这种青春气息,我们在诸子百家中没有见过,他们总是显得过于老成。在秦汉王朝也没有见过,在那里,即使是年轻人也被巨大的社会职能掩盖了年龄。在魏晋名士中倒是见过,但他们过于凄美而短暂,总是昙花一现。唯有在唐代,青春勃发成了主要的人格特征”。关于“整体诗性”,他说,“所谓诗性,其实是一种不可重复的创造敏感,敏感于自然和人性之美”。
不难看出,余秋雨先生看重的中国文化之美,与“天真”相关、与“天性”相关。当看到有太多的研究者、青年学子,乃至年幼的孩子,苦苦跋涉于中国文化错综繁复的小径茫然而不知返时,他想告诉他们,有些典籍没有必要翻开,有些尘埃没有必要拂去,守护“天真”、守护“天性”,领略中华文化之美、创造中国文化之美,才是正途。学习中国文化当如是,研究中国文化亦当如是。
为现代汉语“招魂”
还记得在“余秋雨翰墨展”现场,有两件作品很是特殊。两件都是行草书长卷,体量也都很大,各自占据着展厅的一整面墙,一件写的是《逍遥游》,一件写的是《离骚》。
谓其特殊,是因为,在展示书法的同时,还展示了余秋雨先生用白话文翻译的《逍遥游》和《离骚》。准确地说,不是翻译,而是创作。文言的散文、诗篇,化身为白话的散文、诗篇,思想、意境没有变,却成为了另一件作品。两者之间,是相互映照、辉映的关系,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解说”“变身”。文辞典雅优美的散文和诗篇,加上诵读者的完美演绎,使得这两件作品成为展览的又一大亮点。欣赏书法的同时,更多的观众被文辞打动,并惊叹于作者的转化能力和创造能力。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就对余秋雨先生说,“你用现代诗意接通了古代诗意,让古代经典重新焕发了美学活力。这实在是当下社会迫切需要的文化工程”。
本来,用白话文译写《逍遥游》和《离骚》,不过是为筹备展而做的事情,属偶尔为之。不过,专家的肯定、读者的期待,让余秋雨先生开始用心做这件事情。经典译写,也真正成为余秋雨先生近年启动的一项“文化大工程”。果不其然,在“余秋雨翰墨展”之后的几年间,余秋雨先生接连推出了他的经典译写系列作品。
——2018年6月,出版《古典新译》。收录余秋雨先生译写的中国文化史上十篇名作,包括:《离骚》《逍遥游》《报任安书》《兰亭序》《归去来辞》《送李愿归盘谷序》《愚溪诗序》《秋声赋》《前赤壁赋》《后赤壁赋》。2022年,相继出版《文典一览》。
——2021年3月,出版《老子通释》,全文收录余氏白话文版《道德经》。
——2021年7月,出版《周易简释》,全文收录余氏白话文版《周易》。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散落各处的白话文版中国传统典籍、诗文。同样的事情,似乎还没有谁如此用心、如此下大力气做过。一件值得用心去做、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必定是有价值的。那么,余秋雨先生所做的经典译写这件工作,有什么重大价值呢?
约略来说,余秋雨先生近年所做的这项工作,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双向转化。
一方面,是传统思想的现代化。用现代白话文的形式译写传统文化经典,虽然没有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审美意趣,但是在“译”的过程中,自然融入了当下人的理解和感悟,无形中拆除了当代人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篱笆墙。传统,得以落实于当下,没有了障碍与隔阂;另一方面,是现代白话文的古典化。毋庸讳言,现代白话文的推行,接受了诸多西方现代语言的规范和法则,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距离中国文化本色远甚。不可否认,这一“西化”的过程和阶段是必要的,但是,仅限于此也就难以接续中国文化本有的气韵、风神。余秋雨先生的经典译写工作,使得现代白话汉语,自觉趋向古典汉语的优雅、简洁、含蓄、诗意。大概,这应该是汉语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再一次应有的转向。
不难想见,这一项工作的展开,是颇有难度的。用余秋雨先生自己的话说,难在“招魂”——
“招魂”之始,是回顾自己初读该文时的惊喜原因……
“招魂”之继,是献出自己,让自己与遥远的作者通过“移情”来“合魂”。他不再是古人,而成了自己的朋友,能够呼吸与共。他的一切思维方式、情感逻辑,已经与自己很近。因此,所谓今译,也就是用现代话语表述一个隔空而来的“自己”。
让文化回归于日常
余秋雨先生有过一个或许是“全世界最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简明扼要,浅显易懂,解读和演绎均无必要。简短、直白,不能等同于简单、浅薄,相反,寥寥数言却涵纳了文化之为文化的全部精要。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这些确实是文化的基本底线,同时也是文化的最高法则。
这里不打算从学理角度讨论余秋雨先生对文化所下的这个定义。与这个定义的提出相较,更重要的是,余秋雨先生用他的生命和生活,践行着他对文化理解、形象的诠释并演绎了他所定义的文化。一种学说,如果能与他的提出者,在生命形态相一致,那么这种学说往往是值得信赖的。
诗意的栖居,当下,几近滥用,以至人们连同诗意的生活本身也开始妄自菲薄。这是不应该的。诗意的栖居、诗意的生活,余秋雨先生做到了。那么,怎么才算上诗意的生活?简单地说,就是对世间的一切都看破、放下,转而对世间的一切一往情深地眷恋、眷顾。看不破、放不下,深陷泥沼,谈不上诗意;全看破、全放下,空寂悲切,也谈不上诗意。余秋雨先生的诗意生活,恰在悟空和用情之间。现实生活中,余秋雨先生确实有看破、放下的功夫,敢舍人所不能舍、敢弃人所不能弃,名利、恩怨,一一破之、放之。同时,他又钟情于这个世界,尽一切责任和义务、容一切情与事、爱一切人和物。空、不拒绝有,终极、连通日常,他的生活,因此诗意盎然。最终,余秋雨先生把他的诗意生活,烹成一盏茶,“觉悟者留心茶饮,是因为看穿了世人对种种高论伟业的盲目追赶,觉得必须从一座座空中楼阁落到实地,寻找日常生活的底线结构。底线结构,是衡量万象的质朴准绳。因此,他们端起了茶壶,点起了茶炉”。
余秋雨先生推重“君子人格”,为此,他还特意撰写了一部著作,《君子之道》。他认为,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无外乎“君子”二字。而“君子”,也是余秋雨先生对自己人格的期许。“君子”,给一般人的印象,通常是文雅、谦恭、秀逸,当然还不免有一点怯弱、伪饰。事实上,这是对“君子”的误解。在《君子之道》里,余秋雨先生没有给“君子”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列出“君子怀德”“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不器”等几项内容予以解说。反观余秋雨先生自身的“君子”人格,似乎,“士不可不弘毅”中的“弘毅”二字,是更恰当的注解。中国文化史上,余秋雨先生推崇的“君子”,是屈原、司马迁、颜真卿、苏东坡,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历经劫难而不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伟丈夫,何曾怯弱?何曾伪饰?余秋雨先生曾笑谈,他的精神和身体都皮实得很,经得起折腾、经得起颠簸。的确,如果不“皮实”,他如何能够敢于“苦旅”,又如何能完成“苦旅”,况且他所遭受的折腾和颠簸,何止于“苦旅”?无妨,余秋雨先生依然“弘毅”如故,“君子”如故。
……
接受中央电视台撒贝宁采访时,余秋雨先生曾说,“我是一个通透的山谷,一会儿,飘进来几朵乌云,一会儿,又飘进来几朵白云,都不必惊讶。来过的云,都会悄然离去”。
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泥步修行,云自舒卷,通透、自在。
(责任编辑:马倩)

韓少玄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工作站博士后。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刊编辑部主任、中华美学学会会员。出版有《水墨为上一中国书画艺术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