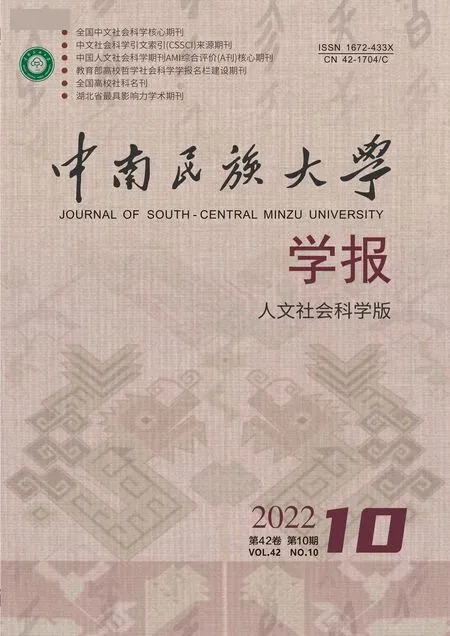汉赋的法律言说
彭安湘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法律与文学因对人性、人权有共同的关注而成为有一定知识增量和方法借鉴的交叉领域(1)法律与文学的关联有四种形式:法律中的文学、作为文学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及有关文学的法律。。中国法学在法律规范的对象、表达、理解与阐释上与文学领域从不失交叉性,然而文学领域参与、融入法学领域的程度却相对有限。研究者大多是将文学中的戏曲、小说、诗歌、辞赋当作蕴含法律元素、表达法律主题的“静态”史料、若干注脚或典型案例等。且目前学界对古代辞赋文本的法律性解读成果也比较少见(2)代表性论文有:余书涵、黄震云《法律语境下的汉代文学----以汉赋为例》,载《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楚永桥《<燕子赋>与唐代司法制度》,载《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鉴于此,笔者意欲用“法律言说”一词,来指称汉赋作品中所包含的与汉代律法相关的题材和内容,并运用目前较为流行的“新文化史学”的方法,探究在汉代知识与思想语境中两者融织的诸多镜相。
一、汉赋法律言说的角度与内涵
据统计,汉代与法律相关的赋篇有17篇之多,占现存完整的汉赋总量(75篇)的23%左右。这些作品不仅反映面较广,涉及了汉律中的立法、司法及法律结构要素等内容,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汉代律法的特点和精髓要义,故两者产生了较为紧密的融织与互渗。同时,赋因其从母体带来的政治伦理品性,不仅担负着“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文化使命,还发挥着“宣上德、抒下情”规制政治的功能和效力。因此,汉代赋家均自觉不自觉地将汉代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律法纳入了言说视野。
1.“取其宜于时者”:对立法切合时势的肯定。汉承秦制,从刘邦“约法三章”到萧何《九章律》的制定,其立法思想甚至基本律条都是源自秦律。不过,相较于严苛的秦律,汉律在立法原则和司法手段上又具有鲜明的儒家化特点。如《九章律》制作时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1]1096,却能以约法省禁为基本原则,对一些定罪、刑罚有所删减或减缓。《尔雅·释诂》曰:“律者,常法也。”可见,“律”在立法任阶上居于最高地位,为正司法法源。故《九章律》奠定了汉代法律的基本形式和内容,对后世也深有影响。这一重大立法举措及其影响,自然引起了赋家的关注。扬雄在《解嘲》中以历史的眼光对萧何造律予以了冷静的审视,称“《甫刑》靡敝,秦法酷烈,圣汉权制”,认为“靡敝”“酷烈”“相宜”分别对三种刑法定性,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扬雄还认为律法是随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人生存的需要而产生,任何时代都不能固守成法。故“萧何造律,宜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其律典是依人之所需而定的。其后,东汉崔寔的“圣人执权,遭时定制”、“世有所变,何独拘前”[2]469的观点与之桴鼓相应。
2.“明恤庶狱,详刑淑问”:对司法公正的歌颂。直接对汉代司法明恤详慎予以歌颂的是东汉崔寔的《大赦赋》。此赋是崔寔有感于新帝德政之美及大赦后之太平景象所作。据《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建和元年曾有四次赦宥(3)分别是:“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夏四月丙午,诏郡国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夏四月又诏曰: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十一月戊午,减天下死罪一等,戍边”。(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这一系列的举措,是新朝新气象的体现,应给予了崔寔非常大的震动。以至于崔寔在此后的《政论》中还提及:“顷间以来,岁且壹赦……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3]因此,他在赋中不吝称赞道“所以创太平之迹,旌颂声之期,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羡乎将来,此诚不可夺也”“虽皇羲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宁?”
除《大赦赋》这样直接地叙写具体某次赦宥且为其“明恤庶狱”揄扬歌颂的作品外,汉代还有一些间接颂扬律法诸层面的赋作:“芔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上林赋》),赞当代君王措刑不用之举;“徽以纠墨,制以质鈇,散以礼乐,风以诗书”(《解嘲》)、“制礼作乐,班叙等分,明恤庶狱,详刑淑问”(《七释》),赞古今德刑相辅之举。《汉书·刑法志》亦有相似的表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后寝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极功也。”[1]1091可见,这些赋文中不同时期的“法语”言说与汉王朝建立起来的德主刑辅的律法思想是基本一致的。
3.“用刑太深,方正倒植”:对酷法不公的批判。如果说自文帝废除肉刑后,西汉前期刑政得当,“从民之欲而不扰乱”,所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1]1099。那么,到了西汉中后期及以后,情形则发生了变化。刑狱繁重,以致于“断狱殊死,率岁千余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余”。所以,赋文之中亦出现了“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4]1077的否定与贬斥之声以及对司法严酷、立法不公正的指责之声。
如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对当政者的严刑峻法、专断横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控诉了他们善恶不分、公私不明及互相倾夺:“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又如贾谊《吊屈原赋》对屈原产生异代同悲之慨,更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对比与比喻,直揭汉初立法不完善与司法不公正的实质及由之带来的乱象丛生的社会面相。
4.“予畏禁,不敢班班显言”:对一己罹刑的陈情。不过,更有感染力的还有那些罹刑获罪后所书写的反映一己遭受不公正待遇和揭露整个社会司法不公和执法混乱的赋篇。其中典型者为赵壹之作。《后汉书·文苑列传》载:“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贻书谢恩……窃为《穷鸟赋》一篇……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4]2628-2630其《穷鸟赋》序中“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的陈述,显然是当时作者自己心态的真实写照。尤其是“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的经历,以及对穷鸟“罼网加上,机阱在下……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的险境铺写,更是对一己罹刑的客观性陈说及形象化比附。
5.“质剂、婚姻、死亡”:对部分民法的关注与展示。汉赋对民事律法如质剂、婚姻、田土、死亡诸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展示。如司马相如《长门赋》关乎婚姻制度;扬雄《逐贫赋》、张衡《骷髅赋》关乎田土等财产制度;无名氏《神乌赋》隐含着赋家对当时社会上偷盗、强占致死现象引起的法治败坏与道德沦丧的无奈和无所适从的悲哀[5];王褒《僮约》则对买卖奴仆的质剂(契约)实质作了揭示。在那种买卖关系下:“奴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洒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裁盂,凿井浚渠,缚落鉏园,研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卢……”这虽是一种文学艺术的夸张表现手法,但基本上还是能看出西汉时期奴仆艰难处境及卑微地位。而僮奴的贩卖和契约问题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即有印证(4)《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告臣,爰书:某里士五(伍)甲缚诣男子丙,告曰:丙,甲臣,桥(骄)悍,不田作,不听田令。谒买(卖)公,斩以 为城旦。受贾(价)钱。讯丙,辞曰:甲臣,诚悍,不听甲。甲未赏(尝)身免丙。丙毋(无)病医窬(也),毋(无)它坐罪。令令史某诊丙,不病。令少内某、佐某 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丙中人,贾(价)若干钱。”。可见,汉代律法在汉赋中的言说呈现出或明言或曲说,或作为正面素材或作为背景资料或作为具体故事情节的不同镜相。但是,这些言说传达出的法律精神却始终一致:那便是对清明与审慎、仁慈与厚德、正义与公正的呼吁与渴求。这是汉代赋家较为坚定的立场与基石。他们试图用儒家教义、思想,儒士品格、道德来实现他们匡正律法、肃清政治的愿望。因此,对法律本身或与刑法、民法相关的现象和事件,他们大都能由古及今、由己推人,从历史的迁变和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而扩展至对群体、对社会的整体观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主张的绝对正义与美感,对于社会矛盾及其不良情绪的描绘与消解……体现出文学特有的诗性正义”[6]。那么,汉赋“法语”言说何以成为可能?
二、汉赋法律言说的背景和方式
在汉初由黄老思想转向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叔孙通制定礼仪、文帝博士诸生奉命撰写《王制》、张苍确立律历、申公拟建明堂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活动至为关键。在拱卫皇权、形成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儒家学说起了重要的指引与支持作用。至武帝,则“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7]。汉赋即兴起于此文化政策变革与文化制度重建的宏大背景中。所以,汉赋家们所采用的法律言说方式,不仅是他们表达法律思考的文学策略,而且也是两汉思想、学术乃至神秘主义密切结合的政治文化产物的体现。
1.以儒入法和经义入赋。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所倡导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政治决策依经断事、司法活动以经义折狱、诏令奏议征引经义。这些既是庙堂之上政治言说的要求,也是政治施为尚‘文’的体现,由此建立儒术形式上的权威。经典之中构拟了治世的理想图景、运行模式与王政制作应当遵从的原则、规范,政治权威的稳固仰赖经典赋予的道义支撑,政治行为的运作则需要经典提供可用于操作的资源”[8]。显之于法律,则汉律呈现鲜明的儒家化特色。这既体现在修改或删除了秦律中一些过于严酷的律文,还体现在将儒家经典义理作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要而言之:
第一,确立德主刑辅思想。重德慎刑的思想根源始于西周。周公曾告诫康叔“克明德慎罚”[9]532,这一思想又为孔子所接受与弘扬。孔子憧憬“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蓝图,将执政者之德作为整个政治关系的支点,使政治关系归入一种德性的自我约束。而且,《为政》所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更是对周公“明德慎罚”的承继。至汉代,这一思想得到了陆贾、贾谊、路温舒、董仲舒、司马迁以及盐铁会议中的诸文学(儒生)进一步地申发。其中,董仲舒明确提出德主刑辅之说,称“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10]341、335。司马迁则反对严刑峻法,认为秦末汉初“天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上下相遁、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赞赏汉文帝废弃连坐法、“除诽谤妖言之罪”、“去除肉刑”之举是“德至盛”,是“仁”;对严刑峻法的法家、“挠法”“曲法”“滥施酷法”的“酷吏”,更不掩饰其反感乃至批判的态度。而刘向更是直接抬高了儒家“德治主张”的地位。至汉末,荀悦依然认为“德刑并用,常典也”[11],王充还特别强调“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12],等等。总之,董仲舒以后,德主刑辅的原则尽管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如王符的崇“德”重“法”理论和仲长统的法律“变”、“复”思想即是。但随着儒家思想逐步法典化以及汉代君王为仿效古者“明君”“仁主”“以创太平之迹,旌颂声之期”[13]的意愿较为明朗,故德主刑辅一直贯穿于整个汉朝占支配地位并在刑罚制度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如赎刑、输作、亲属代刑、募刑、赦宥等制度,均体现了执政者“以仁孝治天下”的德教思想。这恰如杨鸿烈概括的:“儒家传统的理想为‘仁政’,赦罪也是‘仁政’的一端。”[14]
第二,实行以师为吏。秦代曾试图建立一个“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专制文化国家。西汉自陆贾以降,凡是能卓然自立的儒生大都是反秦、反法的,尤其对“治狱之吏”深恶痛绝。当汉廷把以经典为依据的德与以法律为依据的刑相结合后,在主管刑罚的官制上,汉代也出现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将“以吏为师”转化成“以师为吏”。葛兆光认为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使得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运作方式兼容了礼乐与法律、情感与理智;一方面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被纳入王朝统治的范围之内,改变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命运。”[15]“以师为吏”中的“吏”,《汉书》将之称为“循吏”。班固为之作传,实际上是代表主流意识褒赞他们把儒家的道德人伦主义和仁恕思想注入实证法制中。当然,汉代亦有大批酷吏。有研究者认为他们是特定情况下,君主的“人治”之维对封建法制的一种突破[16]。
在浓厚的经学语境中,作为汉廷官僚机构中兼有一官半职的赋家也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和熏染。恰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鹜”,“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因赋与《诗》的近缘关系,“其时已成为儒家经典的《诗》深深地影响着赋之创作与评论。论赋者或以论《诗》标准比照于赋作,或将‘诗教’观点移植于赋作评价,形成了独特的从诗学角度来解读赋学的‘以《诗》论赋’现象。具体而言,就是以‘诗教’之讽谏、颂美两大功能比照并移用于赋论,使“美、刺”两端同样成为了汉代赋论中一以贯之的评判标准”[17]。基于此,赋家一方面在作品中对“先严断而后弘衍”“刑错而不用”“明恤庶狱,详刑淑问”“然犹痛刑之未措”等等慎刑的“仁政”之举予以美颂;另一方面又在作品中对立法缺位、司法不力、不公、滥刑等予以了讽刺。算是尽可能地发挥了赋因日月献纳而直达天听,以助天子“按之当今之务”“参之人事”,从而察盛衰、审权势的功效。所以,赋家对汉代法律所作文学化的言说,必然是其时法律思想、制度的真实映示,但探究其文学创作的精神内涵,则无疑在儒家的仁德理想。
2.法统依据与赋法思维。汉儒有意识地纠偏先秦儒家“罕言天道”的粗疏,开始搭建自然法则与人间秩序之间的关联。从现存资料看,汉儒是把“天”作为人间秩序合理性的背景。其论天,基本上在存在性、重要性及政治意义这样一个层面上。
就法统与天学的关系而言,汉人视天为法统之“极则”。首先,则天立法。此认知的历史渊源较早。在《尚书·皋陶谟》中,皋陶提出了最早的天道规则,认为“典、礼、德、刑”皆自天出,天次序人伦,使有常性[9]151。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汉代,如《汉书·刑法志》在解释《尚书》时就明晰地指出“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认为法的终极渊源在天,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则天道。其次,则天行刑。汉人认为天象与德刑相配,可根据四时变化规则依“天道”实施刑罚。如董仲舒论阴阳,有“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1]2502;论四时,有“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芷。……庆赏罚刑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10]68。再次,则天修德。汉人认为“仁之美者在于天”[10]329。在汉代天学的视域中,德与修德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因为德与不德对应着天象的祥瑞与灾异。若天灾见,则“日变修德,月变修刑,星变结合”[10]329。虽形式不一,“但总归都是修德,所谓‘太上修德’。可见,人君个人的德性修养于天象之变是何等重要”[18]。
这种以天为宪则的法统依据与由天道而君德的天人映射,在很大程度上与赋的思维传统颇为类似。从文化内涵上溯源,“赋法思维的生成在根本上是孕育于与原始宗教祭祀及上古政治密切相关的贡赋制度”[19];从语义特征上探析,赋之“敛”“班”“献”诸义所呈现出的王廷与方国、方国与王廷(5)方国只是王廷之外的指称,不同的时代,指称也不同,像边地、藩属、附属国等。双向度的地理与政治空间路径,则规定了赋以“讽谏”为旨归的思维指向。
因而,在汉代系统、严密的“天道”认知与汉人敬畏天命、隆崇“天地之本”[10]414的礼制文化语境中,汉赋同样呈现出从重“宗统”到明“君统”的变化。对此,许结认为“儒者倡礼,不忌繁文缛节,以取敬天受命、尊祖敬宗之意,而归旨王道政治;赋家亦倡礼,不忌铺采摛文,极尽闳衍博丽之能事,然‘曲终奏雅’,明礼言志,则其思想结穴”,这种归纳可谓点明了赋的思维传统之本相。
3.崇公抑私与重雅轻俗。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雷德菲尔德认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可以分为两大传统。大传统是社会精英及其所掌握的文字记载的文化传统,小传统是乡村社区俗民和乡民生活所代表的文化传统。”[20]察诸汉代的法律体系,亦有大传统所体现的公法(刑法)和小传统所体现的私法(民法)两类。不过“重公轻私”或“重刑轻民”为汉代法系的突出特征。汉代的法律形式为律、令、科、比,所谓“法者,刑也”[21]。之所以称为“公法”,是因其为君权的政治计议:“禁奸”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弼教”以推行儒学教化的社会作用。汉代的“私法”规范大多局限于交易、契约、婚姻、财产等法律行为中,“不仅量小且规定得较为简单,在地位上从属于公法规范”[22]。这种“崇公抑私”的法律观念,使时人认为群体利益、公共利益比私人利益更正当、更优先。如《淮南子·精神训》中汉人以为“延陵季子不受吴国,而讼闻田者惭矣;子罕不利宝玉,而争券契者愧矣”[23],均以为民事诉讼是惭愧之事,可见公权权力的影响之深。
汉赋亦有雅、俗之分,主要表现于:创作身份的学士大夫与市井民众之别;流播场所的宫廷与民间之别;审美趣味的典正化、贵族化与通俗化、世俗化之别;文化功能的正统化、中心化与疏离感、边缘化之别。导致雅、俗分野的原因在于:具有典丽雅正趣味的汉赋作品以典章制度、帝王功业、祭祀畋猎、都邑宫殿等题材内容,对大一统中央皇权的强大和声威的歌颂,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开阔视野,是符合当时人们“称颂国德”“光扬大汉”这一集体心理状态的。同时,汉赋作家亦以清醒的态度对当今君王进行过讽刺、规劝,对时政进行过讥刺、批评,也符合“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24]的诗教精神。与广传于市井、浅俗贴近民间生活、诙谐调侃的俗赋相比,典丽雅正的赋作才更具规制性的话语力量,更能体现赋文体的政治品位。因而,在对汉律的书写上,汉赋大多选择公权性强的法律事件、现象和观念,而对私法题材观照较少。然而,无可否认的是,正是知识精英和市井民众营造出不一样的辞赋趣味,才使得冰冷的律法弥漫着诗性的意味,主次分明又轻重相分,避免了单调与刻板,兼顾了群意与私情。
三、汉赋法律言说的功效和影响
汉赋与法律的融织、渗透,除了表现在汉赋法律言说的内涵和方式上,还体现在其传达出的“诗性正义”功效和对后世法律文学书写的影响中。下面仅以崔寔《大赦赋》中涉及到的汉代司法环节中常见的“赦宥”现象为例,对汉赋法律言说的功效和影响再作探讨。
《大赦赋》所写的大赦即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春正月戊午发生的事。崔寔对“治国二机”有着较深刻的认识,曾把治国与理身进行类比并提出:“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2]464因此,在新帝登祚之时,他继承了前人关于治国需要德、刑并用的理论,赞同“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对汉桓帝大赦天下的意义予以高度的肯定与由衷的称颂。
赋先对“法”的远古性、权威性及合理性进行追溯。它是远古帝王“承天据地”,依据“三时成功,一时刑杀”的天地之道(6)出自《黄老帛书·经法·论约》,“承天据地”在《全汉赋》中视之为并列结构,释为“承奉天道,依托地德”。笔者认为此词应为偏义复词,偏指“承天”,故下文只言“天道”。所立,开篇即蕴含着浓郁的“天宪”意味;次由天及人,写发布大赦的“君令”,展示了天、德、刑三方的关联。而文末的祥瑞描写,更是将赦宥后的政治大局与宇宙自然法则和秩序相对应,从而使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包含自周代以来的两个结构:一是从天开始的顺序结构,即天生德,德主刑。二是从刑开始的逆序结构,即刑维德,德维天。在崔寔看来,这是司法过程中量刑道德化的一个表现。这个道德化,既关乎君德,又关乎德教。
首先,《大赦赋》引用《易经·乾卦》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的爻辞,描述了汉桓帝颁布大赦令前“朝乾乾于万机,夕虔敬而厉惕”的勤谨表现。这是对其德性的自我约束的文学呈现。在桓帝砥砺德行的前提下,崔寔对其大赦举措是赞赏的。尽管这与他后来在《政论》中疾呼以严刑峻法肃清海宇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异。
其次,《大赦赋》传达出“慎刑”的观念,“慎刑”为前汉君王秉持的观念。如汉高祖、宣帝、元帝、成帝等多颁发了恤刑、慎刑、宽刑甚至赦囿的诏令。尽管原因多样、形式不一,但两汉从法律思想到立法实践对“慎刑”的遵循却是始终存在的。对此,班固曾给过一个合乎心理学的解释:“古人有言:‘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于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之凄怆于心。”[1]1108-1109比而论之,即想要行王道,惟悯物是先,要做明君,只有任德,而悯物、任德的表现就是多行赦宥,在此种背景下,赦宥的频繁施行,实际上是君主们要做明君、圣主潜意识的表现[25]。以此观之,《大赦赋》寄寓着以崔寔为代表的汉末士人对理想王政太多的企盼与美愿。此为该赋“诗性正义”功效的第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即是展示出赦宥所含存的人文情怀。赦或赦宥产生于上古三代。例如,《尚书·尧典》有“眚灾肆赦”;《易经·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尔雅·释诂》解“赦,舍也”;程颐注“赦,释之。宥,舍也”;等等。换言之,赦本意为免除、释放,后世之赦包含赦、宥两重含义,兼有免除、宽减之意[26]。汉代君王依据传统,本着“荡涤秽恶,与民更始”、“理阴阳,顺时气”以及“赦小过,举贤才”的赦宥理念和其他实际的目的(7)胡晓明认为大规模的赦免从思想方面来说是统治者“修德”的需要,但在实际中它又会服务于各种特定的目的。(参见《大赦渊源考》,载《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开创了多赦的政治传统。两汉四百余年,各类赦宥多达270余次,约平均一年半的时间就有一次宽刑的诏令,其中仅大赦天下一项,就颁布了151次(8)据《西汉会要》统计,汉高祖至汉景帝 66年中大赦22次,平均每年0.333次;汉武帝至汉宣帝93年中大赦35次,平均每年0.376次;汉元帝至汉平帝52年中大赦27次,平均每年0.519次。据《东汉会要》统计,汉光武帝至汉章帝64年中大赦天下14次,平均每年0.218次;汉和帝至汉质帝58年中大赦天下21次,平均每年0.362次;汉桓帝至汉灵帝43年中大赦天下32次,平均每年0.744次。,其密度之高,着实异乎寻常。
观两汉赦宥的时令,大多选择在春夏两季(正月至六月)。其中168次赦天下均是施行于这一时段,占总数178次(不包括更迭时期的还多)的94%还多,而秋冬季节赦天下仅为10次[27]。《周易·解卦》的《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解》卦上为震,下为坎,与《屯》卦上坎而下震之象正相反。依据傅道彬的解读,《屯》卦之“屯”,像草穿地而未申,为古“春”字[28]。而“解”则“象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所以,两卦均含《彖传》“天地解而雷雨作”之义,言成物当春,因雷雨而纷纷舒发生机,为“舒解”之象。正如《来氏易注》所云:“雷雨交作,天地以之解万物之屯。”《解》卦之《象》由自然天象而人事,说明“君子”效法《解》象,以“赦过宥罪”体现开释、舒缓的“仁政”。
选择在春天“君子以赦过宥罪”,还取“春”之文化意蕴。“春”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第一个意义是“劝生”,另一个意义是“禁杀”,处处体现出顺应生命的原则和精神。如《吕氏春秋》以“本生”解释“孟春”,以“贵生”解释“仲春”,以“便生”理解“季春”。而且,“东者,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动运”[1]971。四季中,同属阳气的是春、夏两季,具有动、轻、刚、热、明的属性,主养生。所谓“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10]324。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与流行,人们逐渐以四季的自然现象、属性与人事政令事物相属连。春夏赦宥之令多颁布于此,应是与天休戚、本生贵生这一文化理念的体现。
同时,赦令在春夏颁布还出于佑农的考虑。古代以农耕为本,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有充足的劳动力。若过多的劳动力拘禁于监狱之中,自然会妨碍春种夏耕等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故王夫之说:“省囚系以疏冤滞,赦宥过误以恤蠢愚。止讼狱以专农务,则君上应行之政。”[29]因此,实行赦免,也是统治者佑农的举措之一,是劝生这一人文情怀在司法实践层面的体现。
令人惊奇的是,以《大赦赋》为代表的赦宥题材,在后世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仅以唐、宋诗歌为例证之:一是从自身的流徙遭际出发,抒发一己遇赦之情怀。如“何年赦书来,重饮洛阳酒”(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杜鹃无血可续泪,何日金鸡赦九州”(黄庭坚《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是对赦宥的企盼;“去岁投荒客,今春肆眚归。……喜气迎冤气,青衣报白衣”(沈佺期《喜赦》),“陈焦心息尽,死意不期生。何幸光华旦,流人归上京”(张说《赦归在道中作》),是抒发遇赦的欣喜;“圣人宥天下……汪洋被远黎”(沈佺期《则天门观赦诗》),是对赦天下的颂扬;“坟垅无由谒,京华岂重跻?炎方谁谓广,地尽觉天低”(沈佺期《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是写有赦到不得归的绝望。二是从旁观者身份,表达对赦宥的看法。如“曈曨日出迎赦来,沸渭颂声何休哉。陛下万岁御九垓,王母献寿沧海杯,更看正仗单于陪”(晁说之《迎赦一首》),是对政治清明时的赦宥予以肯定;“去年经春频肆赦,拜赦人忙走如马。五月不雨麦苗死,赦频不能活穷寡。……使麦长熟人不饥,敢告吾君不须赦”(石介《麦熟有感》),是对天灾频仍时的多赦予以否定。
这些作品或倾心于内在的情感诉说,或是对大赦事件作平实的议论;或显得情绪浓烈、哀感伤怀,或显得冷静凝重、语势平和;或以五言形式,或以七言体制……各具风格和特点。无疑,它们是在汉赋言说赦宥的基础上,将归属刑法的赦宥纳入诗歌文学的视域,以文学的人文关怀、正义情感省视法律对人的社会生态、心灵生态的影响。“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是法对于人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30]诗赋作家之所以对赦囿题材情有独钟,是因这一量刑方式蕴涵了一种以人为终极关怀对象的精神气质以及以人为中心,并给予严肃认真的人文关怀的指向性意义。
四、余论
对于赋体起源,目前有源于原始宗教的赋牺牲古制和源于上古国家政治的礼乐制度两说。不管是由赋牺牲产生的宗教式的“物质+语言”言说形态[31]162,还是“登高而赋”式的政治言说形态[31]173,都“从原型意义上决定赋法思维在定型之后也始终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体现出它自身从母体中带来的政治伦理品性”[19]56。这种政治伦理品性一直伴随着赋文体的生成与演变。至汉代,赋多为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臣献纳而成。这是赋家采用的一种与天子及朝政发生关联的并以讽、颂为主要功能的交流活动。所以,在汉代的主流意识中,赋被纳入政治文化制度之中,在特定的语境中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威性与工具性。因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性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汉赋首先作为精英言说代表促成了群言议政的机制。而汉赋文本因其含容的法律因子,亦可作为其时政治言说形态的另一类----法律言说。同时,汉代法律对汉赋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汉赋提供了充足的题材内容以及富有思想深度和文化底蕴的表现领域。
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汉赋法律言说的诸种镜相就会发现,尽管法律是一种规范,具有强制性、适用性、约束性和理性化,但赋家将汉代法律世界中的合理与不合理现象较为具象地投射在文学的影幕之上,负载着有温度的情感陈述、有倾向的价值评判和有底蕴的文化涂饰,寄予着赋家对律法公平公正、社会清明有序的期盼和愿景。所以,这是富有力量的言说形态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发挥了其“诗性正义”的功效,在律法史和文学史上的贡献是不容轻忽的,应当引起我们充分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