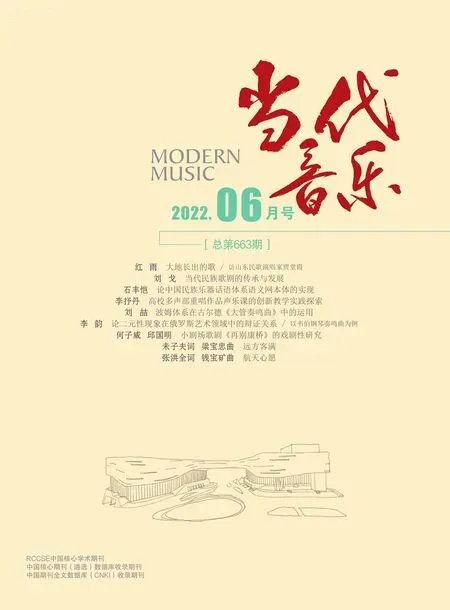舞台艺术新经典
——论歌剧《党的女儿》复排中的守正创新
肖 艳 王 湉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创排歌剧《党的女儿》,本剧由阎肃执笔,与王俭、贺东久、王受远等共同编剧,王祖皆、张卓娅、印青等作曲,于1991年由彭丽媛、杨洪基等艺术家参与首轮演出,成功塑造第一代《党的女儿》歌剧舞台人物形象,是一部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历史题材民族经典歌剧。
三十年间,《党的女儿》成功上演六百多场,其艺术水准经得住考验,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许多经典唱段深入人心。2021年恰逢建党百年之际,国家大剧院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重排《党的女儿》,带领观众重温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峥嵘岁月,使得经典民族歌剧复排再度燃情。
《党的女儿》是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它将观众的思绪带回革命战争年代,点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民能量。歌剧传递了革命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坚定国人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奋斗终身理想,这是经典作品的魅力,是《党的女儿》演出六百余场仍为观众所喜爱的根源,更是当下重新排演经典作品的动力。在当代各种流行文化的冲击下,热门影视、小说和短视频等娱乐方式充斥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艺术鉴赏需关注作品的美学呈现及其审美价值。“非意识形态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是不可取且极具迷惑性的。[1]以《党的女儿》为代表的我国经典优秀文艺作品,通过对善与恶角色的鲜明塑造与强烈反差,使人们对是非得以深刻辨析,进而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养成高尚的道德观念。同时,复排歌剧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通过新的制作展现出迎合时代变迁的现实意义,赋予经典作品新的灵魂。
在“当代呈现手段”“当代优秀人才”及“当代人民精神需求”三者推动下,重排了具有“历史自觉”“精神高度”及“生动的人物塑造”三者结合的《党的女儿》,致敬了百年前英雄的革命共产党人,致敬了三十年前倾注心血创作演出的中国歌剧人。国家大剧院王宁院长表示,“此次国家大剧院复排这部歌剧,不仅是向红色经典致敬,更是让英雄形象在舞台上延续强大生命力。希望将剧中‘田玉梅’的理想之光与信仰之力传递下去,铸就信仰之魂、挺立信念脊梁”[2]。
国家大剧院版《党的女儿》展现了其创作团队在新时代语境中守正继承地对红色题材歌剧的有益探索,展现了国家大剧院在科技赋能助力下对民族歌剧的舞台探索能力。歌剧中集中呈现了当代中国歌剧创作者们的风采,扩大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影响力;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信,以优秀的歌剧作品鼓舞国人、感染国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党的女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的复排,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的需要。
一、守正创新:新时代民族歌剧复排行稳致远
(一)守正与传承:礼赞时代群体力量
国家大剧院版《党的女儿》在剧本、人物形象塑造及音乐表演层面都遵循了原创作,在唱词、念白、旋律取材、音乐结构、声腔唱腔、形体表演等方面均体现了中国美学精神和中国民族风格。从音乐创作层面看,《党的女儿》中主题歌《杜鹃花》于戏剧事件中贯穿,其中凝结了整剧的核心精神内涵。将风雨不倒的杜鹃花这一具象客体抽象化,是以田玉梅为代表的坚定信念、献身革命的共产党员的化身,与此同时,创作者对于革命英雄的敬仰之情又通过比兴手法进行戏剧抒情,引起观众共鸣。与西方使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大胆洋溢的情感不同,中国审美风格的表达是内敛的、含蓄的,点到即止且意蕴丰富。
从音乐语言的创新层面,《党的女儿》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戏曲元素,“以中国戏曲结构为母体,以民间音乐为素材作曲,唱、念、做、舞并重的民族歌剧,深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3]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其包含了中国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表达习惯。歌剧与中国戏曲文化的结合便是中国民族歌剧实现发展创新的基石所在。《党的女儿》以江西地区的民间曲调和山西蒲剧音乐的调式、旋法特征为主要素材[4],将极具抒情性的江西民歌与带有戏剧性张力的蒲剧音乐结合,在鲜明的民族风格基础上注入了民间戏剧元素。
此剧运用我国传统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形象的所思所想。歌剧大量采用中国板腔体戏曲的音乐传统进行创作,运用板式和腔式的变化、发展,进一步刻画人物形象,推动剧情发展。从戏曲板式角度出发,《血里火里又还魂》唱段中通过慢板表现田玉梅在风雨交加中内心的悲痛和无助,增加装饰音,字少腔多的手法使音乐表现更为细腻;《万里春色满家园》中通过铿锵有力的快板段落表现田玉梅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刻画共产党员与敌人斗争的坚定决心。在慢板与快板运用的同时,《血里火里又还魂》与《万里春色满家园》均使用了自由散板,推动剧情发展,表现田玉梅悲愤之情。从戏曲唱腔角度出发,在民族歌剧中常常使用戏曲音乐中的拖腔手法和帮腔手法,如田玉梅劝说桂英重拾革命信心的唱段《生死与党心相连》以及桂英表达其愧疚之情的《一死抱党恩》中均使用了拖腔的手法;在《杜鹃花》《天边有颗闪亮的星星》《万里春色满家园》等众多唱段都运用了领唱、合唱、齐唱等多种方式运用帮腔,推动剧情发展,渲染戏剧气氛,表达坚定的革命信心。
《党的女儿》借鉴戏曲特色,进行多角度的学习和运用,给予歌剧更为丰富的音乐元素,更是利用传统戏曲中符合中国审美的元素推动民族歌剧发展,突出民族歌剧特色。《党的女儿》基于音乐戏剧结构及音乐语言运用的继承发展,在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时代气息融合下,适应了改革开放之后新时代歌剧受众的审美情趣,在传统和当代的接通中引起当代受众的情感共鸣,使其得以作为歌剧精品经久不衰。将数千年形成的中国美学思维运用于中国民族歌剧创作,是中国观众的审美趋向,亦是歌剧立足于中国的必然要求。坚持传承中国美学精神即国家大剧院版《党的女儿》所做到的“守正”。
(二)创新与发展:谱写民族歌剧新经典
1.科技为舞台视觉呈现赋能
歌剧评论家居其宏先生指出,对传统的回溯绝非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回归应以创新为宗旨。[5]作为曾参与1991年《党的女儿》首排导演的汪俊,三十年间曾先后执导歌剧《军营儿女》《屈原》等,2001年后转型成为电视剧导演,担纲《像雾像雨又像风》《四世同堂》《青年医生》《小别离》等电视剧,在荧幕内外取得累累硕果。本次汪俊回归经典歌剧舞台,与《党的女儿》重逢。对这部歌剧无比熟悉的汪俊导演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保留经典的艺术特色,基于当代观众审美习惯、观剧习惯,在表演、舞台、音乐等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在表演方面借鉴影视剧创作,在表演方式上将人物性格立体刻画。在舞台设计方面,合唱团走出乐池,走上舞台,扮乡民、革命战士、匪兵等角色,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基础上,增添了舞台的氛围感。在音乐方面,指挥家李心草带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及中央民族乐团充分展现了中国音乐家们对于民族民间音乐韵味及对中西配器平衡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将民族歌剧中民族民间音调及板腔体唱段从前辈手里稳稳地接过,再通过现代的方式演绎、传承下去。
在舞台设计方面,与三十年前首演《党的女儿》不同的是,国家大剧院利用了多媒体技术营创了观众身临其境的歌剧场景,正如雷佳在《中国文艺报道》访谈中所提及的,“现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比三十年前首演的舞台至少大了三分之一,三十年前因舞台限制无法绽放的艺术呈现,如今这个舞台给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演员很好的机会,在与精致的舞美效果配合中绽放自己”[6]。舞美设计刘科栋介绍,“从1991年到现在的三十年里,国家大剧院是国内剧场发展情况的一张名片。国家大剧院必须要把先进的技术调动起来”[7]。开幕时便呈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惊心动魄,乌云密布、电闪雷鸣,舞台声光电配合,营造出革命的紧张局势,观众仿佛置身于战争前线。舞台运用升降台顶层的金属网,影像和灯光不断变换,顶层的山坡开场时是令人感到危机四伏的刑场,终场的舞台布景更是呈现出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剧情、灯光、布景与冰屏的默契配合,为观众构建了想象空间:在田玉梅思念远方丈夫时,冰屏上出现了红军长征的画面,观众看到了场景的“实”和田玉梅脑海中“虚”的画面;当田玉梅和桂英回忆昔日点滴,冰屏上出现了两个少女正嬉笑打闹,同样是两人在场景中敞开心扉之“实”和回忆中美好画面之“虚”的交织。除了影像的灵活运用,《党的女儿》还利用了歌剧院的升降台技术,使换景更为自然流畅,提升了观众的审美体验。舞台场景的切换,呈现出以木板青瓦为特色的赣南建筑实景和处于深山竹林中的“七叔公的草屋”。刘科栋和主创团队表示《党的女儿》需要为建党百年“交上一份属于当代审美、富有当代意识的答卷”。在科技的赋予下,国家大剧院版《党的女儿》在舞台呈现上较1991年首演版本,具有了更强的视觉冲击力。
2.秉承初心谱写民族歌剧发展新篇章
《党的女儿》作为一部民族歌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1991年彭丽媛在首轮创演时专业、经典的演绎、创作是分不开的。作为全剧的主人公,田玉梅这一人物的演绎对歌剧演员的歌唱能力和表演能力都有极高的要求。2021年田玉梅的扮演者雷佳作为彭丽媛的首位声乐演唱博士,得到了其亲授,通过承袭其演出中的“神”,融入自身的“形”,刻画了田玉梅的新时代形象。雷佳曾指出传承和吸收是塑造经典角色的重要基础,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是在掌握了五百部传统剧目之后,才开始尝试塑造新的角色。雷佳在复排中坚持守正传承,结合其自身思考和经历为观众展现当代田玉梅。
《党的女儿》以民族唱法为主,提炼和传承了中国传统演唱精华,符合我国民族审美习惯,讲究情、声、腔、韵、字的融合。艺术家们在创作演出过程中表现的创新融合意识,是当代歌剧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雷佳在2021年“深圳声乐季·中国声乐高峰论坛”中提到,现代青年人才的演唱不应被方法禁锢,应以作品为本,以艺术表达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哪种唱法——民族、美声抑或是通俗,作品需要哪种唱法的表现形式我们就用哪种,可能是单一的,但更多时候应该是融合的。当今的声乐艺术整体呈现多元化趋势,雷佳正是把握了这一趋势,在传承和发扬传统的、传神的民族风格的同时,突出鲜明的个性和地方特色,而非声乐演唱技巧。让技巧辅助民族风格呈现,在中西声乐文化交流融合中逐步构建全新的声乐艺术形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使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满足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饰演“七叔公”这一角色的廖昌永作为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常年演出西洋歌剧,《党的女儿》是其主演的第一部板腔体民族歌剧,对其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在音乐上,廖昌永老师在戏曲和歌剧演唱之间找到平衡点,参考戏曲特色并将之融入歌剧演唱中。在舞台演绎上,七叔公老年人的体态,阅历丰富的语言语气,声音的年龄感,嫉恶如仇的真性情,都让人看到他在艺术上的细腻和严谨。对角色演绎和音乐诠释的亲近感、对中国民族歌剧发展的责任感,使七叔公这一角色更丰富、更真实。薛皓垠饰演叛徒马家辉,将背弃信仰的扭曲与对妻子的愧疚两种矛盾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小演员余梓溪饰演的娟妹子则用其真诚纯净的音色征服了全场观众,娟妹子与田玉梅的联结更是让田玉梅这一形象同时拥有了崇高的党性和伟大的母性,刚柔并济。
3.民族歌剧中传统美学精神的舞台呈现
从艺术作品的审美层面看,《党的女儿》的成功离不开其“言”(创作)、“象”(人物塑造)、“意”(意蕴)三个中国美学精神。中国美学精神即秉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中国的精神追求和美学风格,是主客二元区分后的天人合一的美学。[8]中国美学精神理论与中国艺术实践是互为表里的,融合了儒释道思想,包含了一系列美学词语,如“形神”“风骨”“气韵”“虚惊”“意境”“趣味”等。[9]中国民族歌剧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立于中国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学精神思考的产物。当代的中国民族歌剧更加需要坚守中国传统,并非只是坚守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或中国传统音乐结构,而是从自身根本上体现中国美学精神,指向更高的中国审美追求。复排版《党的女儿》集中了国家大剧院歌剧制作团队的精英力量、国内顶尖歌剧表演艺术家的力量,在现代化的舞台上展现艺术家的才华,用经典歌剧作品的传承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歌剧的美学品格与精神追求。
二、民族歌剧发展的路径探析
(一)对外传播的思考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民族歌剧在创作探索中,也逐渐具备代表中国文化进行全球化传播的可能性。
一方面,民族歌剧作为中西结合的艺术形式,在西方歌剧的艺术形式下融合中国传统音乐、戏曲、表演元素,形成了中方特有的艺术气韵;融入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并且在现当代的探索中,融汇进了中国时代精神与独特的意识形态。从而能够实现西方化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气韵与新中国时代精神的完美契合。
另一方面,民族歌剧的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当代歌剧的创制经验,形成属于当代中国歌剧独特的创制范式。在歌剧艺术的对外传播和交流方面,民族歌剧与西方传统歌剧院的制作方式上,有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可能性。中国在世界歌剧艺术的发展上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能够积极发挥促进作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中国民族歌剧的有益探索,而《党的女儿》就是这条探索之路上的里程碑似的作品,具有非凡的价值。
(二)经典重塑的探索
民族歌剧的经典作品是老一辈艺术家以其所居时代的丰富生活积累创作而成的。由于时代、创作者的生活经验和语境的不同,当代艺术家对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理解和情感与三十年前创作《党的女儿》的一批老艺术家是不同的。即使创作者无法回到原来的语境,但其精神的传承和延续是一代代中国歌剧人进行创作的不竭源泉。艺术的呈现、艺术家的表达以及不同年代观众对同一歌剧作品的情感共鸣点也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分割、断裂。如何划分经典作品的创新边界呢?《党的女儿》重排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党的女儿》基于扎实的一度创作,呈现“坐北朝南”的音乐新风格,经过精湛的二度创作,呈现了教科书式的歌剧表演,成为复排版《党的女儿》不易超越的高标准。面对高标准的经典歌剧,复排时如何平衡经典传承和当代艺术家的创新?《党的女儿》作为时代的经典之作重回舞台,其艺术品格和思想深度至今仍能为观众带来震撼和享受。以《党的女儿》为例的经典复排,为现代人展现了非现代性的、一种更为永恒的精神,这类民族歌剧是对革命精神的展现,是对老一辈艺术家艺术精神的学习。诸如此类经典,全方位地传承便是复排经典的艺术魅力所在,是对历史和经典的忠诚。在实现全方位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意愿体现,即通过舞美、设计和表演等新科技、新场景、新观念实现锦上添花的当代呈现。全方位复排并非民族歌剧发展的唯一路径,用对待新作品的眼光审视过去的民族歌剧,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是将过去的声音于当代复活的一种尝试。然而这一途径并非为了千方百计迎合观众,也非为了原版的消失,而是通过反复打磨,呈现一个鲜活的、属于当代的作品。
《党的女儿》在内容上以革命战争年代为起点,唤醒中国时代精神的艺术呈现,其内容与中国时代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就形式而言,西方歌剧艺术这一具体艺术形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契合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新时代的中国受众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多元文化的冲击,更加期待舞台艺术中传统文化元素呈现的创新,更加需要时代感强烈的舞台艺术作品。建党百年之际《党的女儿》复排的守正创新,为民族歌剧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与方向。
注释:
[1]董学文,李志宏.“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与当前文艺实践[J].求是,2007(02):51—53.
[2]刘 臻,郑新洽.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歌剧《党的女儿》上演,雷佳咏叹调唱哭观众[N].新京报,2021-07-13.
[3]安 琪.欧式歌剧中国化的成功探索——歌剧《司马迁》的审美特征[J].歌剧艺术研究,2001(01):19—20,18.
[4]居其宏.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321.
[5]居其宏.歌剧综合美的当代呈现[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323.
[6]http://tv.cctv.com/2021/07/22/VIDEIztlS6EartBrvqsJXmAH210-722.shtml.
[7]高 倩.《党的女儿》30年后再回舞台反响空前,“守正创新”赓续经典[N].北京日报,2021-07-19.
[8]寇鹏程.文艺美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247.
[9]潘知常.中国美学精神(修订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