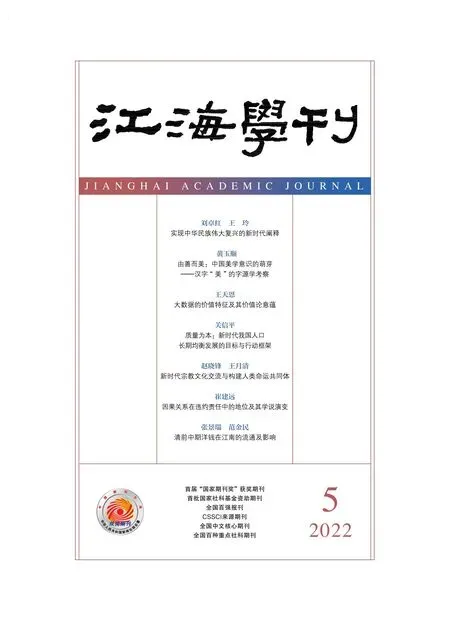技术人类形成与自然需要瓦解*
于天宇
在人类通过技术改变自然的同时,人类自身也在被技术所改变。伴随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的身、心正不断被技术化,强大的数据、算法,使人们趋之若鹜,又困陷其中。人类所能接收到的一切视讯都逐渐被技术重新包裹,强大的搜索与存储能力使人们习惯于“拿来主义”,这种现象也在不同程度上令人的思想力与记忆力退化。技术如同人的义肢,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也使人类对其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依赖性,技术悄无声息地渗入人类生活的全部场域,人类已逐渐不能适应技术退场后的生活状态。技术内嵌于人类的生命之中,人类对技术的绝对依赖,使技术从其工具性的意义中发展出一种统治性的趋势。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将技术形式新定义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在这个意义上,隐藏在技术背后的权力目的,即满足资本增殖需要抑或满足人类真实需要,则决定着技术的存在属性、发展趋势与人类未来。同时,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自然人类文明也将不可避免地过渡到技术人类文明。
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过渡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言到:“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所谓“人的科学”也正是关于人本身的科学,伴随技术工业和资本商业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人类文明已出现了断裂性的转变,这种断裂或者说转变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与资本已然渗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场域。资本权力对技术的宰制一方面使社会不断加速发展,另一方面使人类必须不断放弃旧的经验,并积累新的、不断变化的经验。这种由“过去”到“未来”的快速转向过程,同样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身体与内心,质言之,“人的科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积极因素,然而,人类仍需警惕并反思这种“人的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身、心两方面所造成的变化。
首先,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看到了身体被完全技术化的可能,事实上在一些方面人类的身体已经被技术化了。比如基因技术使人类具有从对身体的后天改良走向先天编辑与制造的可能。“作为当今世界发展最迅猛的学科,生物技术完全可能对外来生命本身和未来人类文明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3)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3页。在这个意义上,“人”这一自然的产物,将发展成为一种可能通过技术干预的后天产品。当然,这种假设有待时间的验证,并存在诸多风险,一方面由于这项技术本身发展过程中存在变数,另一方面则源于这项技术发展的具体指向,即人的本质改变。但是,我们仍需警惕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的预言,即伴随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的彻底发展,后人类主义将实现对人文主义的根本性颠覆。(4)参见[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51页。无独有偶,霍金也在其遗作《大问小答》中断言:一群超级人类将通过基因工程,甩开其他人类,最终接管地球。(5)参见Hawking, S., 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18, p.185.这意味着,在人类不断被技术化的过程中,技术由人类改变自然的工具,将发展成为彻底改变人类身体的工具。这说明,谁拥有控制技术的权力,谁就将拥有彻底控制未来人类存在样态的权力。
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已将算法、大数据以及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对人类内心世界的引导与改变。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义是在广泛信息采集基础上的超强算力,“因此,人类精神的技术化实际上就是计算化、算法化和数据化”。(6)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第86页。一方面,强大的数据存储使人工智能拥有比个体人类更为强大的知识背景;另一方面,精准的计算能力使人工智能比人类更为“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有可能完全替代人类的思维与思想,或者说,人工智能比人类更加了解自身。该领域权威学者博登在《人工智能:本质和未来》一书中写道:“不久的将来,通用人工智能将变为超人人工智能。届时系统的智能将足以自我复制,从而在数量上超过人类,并且还可以改善自己,从而在思想上超越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和决定将交由计算机负责。”(7)Boden, M.A., AI: Its Nature and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47.因此,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人类如何确保未来将产生的超级人工智能仍旧完全听从人的指令。当然,对于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可能推测,学界仍存在不同见解,认为人工智能奇点论的存在前提“反映了一种关于生命和心智的狭隘观念,而以这种狭隘观念为基础的人工智能体不可能具有自治性”。(8)李恒威、王昊晟:《心智的生命观及其对人工智能奇点论的批判》,《哲学研究》2019年第6期。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依赖于技术,并被技术化。人在获得某种程度解放的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方面的退化,技术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并进而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思想力、记忆力与理解力,人类所能接收到的一切视讯都逐渐被技术所包裹。这意味着,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类的思想引导,并改变着人类的行为方式与生活方式,这同样是对技术权力背后的“掌权人”的巨大考验。
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应用方式某种程度上是文明程度的测量器。在现时代,由生物技术与智能技术对人类造成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改变区别于工业社会早期那种由机器、工厂所带来的劳动者手工艺的总体性丧失,而是一种对人类生命结构、认知能力、思维能力、记忆能力的剥夺与重塑。当然,技术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抵抗技术进步同样是徒劳的,但是,现代技术的威胁在于,这种技术的本质是“非自然化”的,这种“非自然化”的特征,使现代技术似乎正在走向一种摆脱自然的道路,通过强大的技术控制,摆脱自然控制,使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不再依赖先在的自然规律。质言之,一切事物都已经或即将被现代技术所“置弄”,包括人类自身。现代技术似乎正走向自然的反面,使人类的身、心都将要或正在被技术所改变,这意味着自然人类将逐渐发展成技术人类。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然性”,但当技术使人类与自然分离,它就造成了人类某种程度上的缺失,这种缺失将改变人的本质属性,当人类完全丧失“自然性”,技术也就实现了对人类的本质改变,人类也将彻底从属于技术。孙周兴教授在《人类世的哲学》中重解了尼采所言的“上帝之死”:“上帝之死”即“人之死”,“即自然人类的颓败和没落”。(9)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第74页。这样的理解,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合乎时宜的,因为纯粹自然而形成的人类文明,正在被人类亲手创造出来的大他者所瓦解并取而代之,这种由人类衍生出的技术人类,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在此意义上,自然人类文明逐渐向技术人类文明过渡,而我们正处于过渡的转折点上。走出人类世,迎接我们的是一个“数字囚笼”,(10)蓝江:《走出人类世:人文主义的终结和后人类的降临》,《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抑或一种“数字解放”,这是当今亟待思考的问题。“在今天,因为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技术文明已经失控,也即失去了自然人类的控制,成为一种高风险文明,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技术的综观和掌控成为不可能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对未来文明的思虑和预期已成当务之急。”(11)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第287页。然而,在对技术本身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反思与预测的同时,更加需要对自人类社会形成以降,技术的发展目的与驱动力量进行重新思考。
资本权力下的技术统治
作为人与自然间的“中介”,技术在不断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不断进步,但在资本权力的宰制下,技术却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因为技术的发展依赖于资本的支持,而获得资本支持的唯一理由是实现更大的资本增殖。资本增殖依赖于人类为满足需要的消费过程,这种消费依赖于生产,而生产依赖于技术。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通过消费来满足的,正是被资本制造出来的不断膨胀的欲望。质言之,资本权力控制技术发展,技术促进资本增殖;资本权力制造人类欲望,欲望满足促进资本增殖。在此意义上,技术发展与人类需要都沦为了满足资本最大化增殖的工具,而现代技术对人的本质改变,使人类又将完全依赖于技术,资本与技术的联姻共同控制人类,这既造成了技术的异化发展,更消解了人的主体性。
首先,在资本权力的宰制下,现代技术改变了其服务对象。海德格尔在《演讲与论文集》中言道:“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技术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集置(Gestell)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带着一种可能性,即:人类或许已经不得逗留于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之中,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12)[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页。技术伴随人的理性发展,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通过技术改变了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动物只不过可以改变事物的外在结构。但是,现代技术已经触动了自然人类文明的最本质处,通过生物技术与智能技术造成的人类身、心的改变,使技术逐渐呈现出一种统治的趋势。因为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对技术的绝对依赖,然而,这似乎违背了技术与人之间“最初的协定”。在马克思看来,当人类通过劳动来满足自身的第一个需要时,就已经孕育着工具与技术形成的土壤。“人之为人,是能使用工具,使用工具即有技术。”(13)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第103页。技术作为人类发展的“帮手”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并不断发展。人是技术的最初所有者,然而自机器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已经不同于古代技术,“古代技术有一个古代存在学/本体论(ontology)的观念基础,而现代技术则有一个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观念基础”。(14)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第108页。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古代技术更多地注重对自然的迎合,偏重于在实践中的探索,而现代技术则试图在形式科学与实验的结合中,以主客二分的视角,改变自然与人的关系及存在状态。不仅如此,机器化流水线的功效强度,也大大超越了古代技术的手工技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显然,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和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效率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因此,资本不断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入于机器与技术的革新。马克思在论述资本构成与劳动力需求的关系时指出:“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7页。对资本技术构成投入比例的提高,可大大降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投入,并可实现更高的个别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个别资本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占据了优势。然而,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现有的机器、技术将再次无法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更高强度的生产需要更高新的机器与技术来实现,这要求资本技术构成的投入比例继续增加,技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资本为了实现更快速地增殖,必然发展更强的技术作为保障,在此意义上,资本是技术真正的主人。
其次,技术发展不再满足人的需求,而是满足资本增殖的需求。资本实现不断增殖的两个必要环节是:一方面,消费者派生出更多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通过技术进步来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谈道:“技术总是进行这样的循环,为解决老问题去采用新技术,新技术又引起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要诉诸更新的技术。”(17)[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曹东溟、王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对于资本来说,无论是“老问题”还是“新问题”,归结起来,都是如何实现资本最大化增殖的问题。技术为资本增殖释放了更大的生产潜能,而当现有的技术可能实现的生产效率不能再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时,新技术又再次出现了。在这样的循环过程中,技术帮助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并使无产阶级的力量愈发贫弱。当然,这并非否认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增殖的来源,只是在技术的帮衬下,工人的劳动获得了更高的效能,同时,创造出了更多异己的力量。罗萨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加速循环逻辑,他认为科技进步加速了作为引发社会变迁加速与生活步调加速的逻辑开端。(18)[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然而,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加速进步的直接目的在于使生产加速成为可能,而生产加速的目的即在于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求,从而使资本在消费者实际消费的过程中获取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增殖这个唯一目的。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节奏的加速,需求的连续进攻,使得巨大的生产力和更为狂热的消费性(丰盛可以理解为匀称方程无限的减少)之间的差距拉大。”(19)[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事实上,资本逻辑利用欲望逻辑,通过对主体欲望的控制,使更多的消费场景合理化,技术的进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因素,为资本增殖搭建了一个可能实现的重要基础。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技术的“中立性”已然完全倾斜。如马尔库塞所言:“不仅先验的决定着装备的产品,而且决定着为产品服务和扩大产品的实施过程……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2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6页。
最后,在资本与技术的联姻之下,人成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发展,同样期望着尽可能地取消人的劳动,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求得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马克思对此例举道:“现在一个八岁的儿童在机器的帮助下,比以前20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多。”(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当资本有机构成比例不断提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商品的投入比例必将不断减少,此时,原本属于工人的劳动机会不断被机器与技术所替代。“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32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具有了别样的意图,技术的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人的劳动,但同时造成了更多人失去劳动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技术已然失去了其原初的即主体改变自然的工具性意义,转而发展成为资本统治生命、调节生命的帮凶。在资本通过技术打开世界市场大门的过程中,“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19页。然而,现存的机器也同时存在着被更强大的技术所革新的可能。技术成为帮助资本快速增殖的手段,对技术强度的追逐,似乎发展成一种对于统治权力的追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作为连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在资本的作用下转移了其所服务的对象主体。正如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所揭示的那样,“统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越来越变为技术的、生产的甚至有益的统治”。(2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技术,并未兑现其拯救人受物质奴役的承诺,反之在资本权力的操纵下,幻化成为统治人的新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竞争”实则造成了人的不自由,全体人早已失去其主体性地位,技术发展的目的,不再立足于为人的解放而服务,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作为资本权力下宰制人的手段与工具,完全服务于资本,任何技术的发展,皆需要依靠资本的力量推动,任何需要技术发展来解决的问题,本质上都是阻碍资本增殖最大化或是在资本增殖过程中而产生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技术并非拓展了人类的本性,而是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奴役着人类的本性,作为资本宰制的工具,一切技术的进步,本质上都会加深资本对人的控制。现代技术在资本权力的控制下,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的发展模式,改变了需要与满足的价值尺度,更改变了技术发展本身的目的与意义。在现代技术为人类社会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逐渐瓦解了人的存在意义,技术使人类与自然相分离,“它就带给了我们某种形态的死亡”。(25)[美]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第241页。更为重要的是,由资本权力所控制的现代技术,期望将一切都变成技术生产的对象,以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换句话说,当人类的身、心两方面都完全地“非自然化”后,技术人类将完全取代自然人类,而这种彻底的技术人类也将彻底消解掉人的“自然性”,完全由技术生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对人类身、心的改变则尤为可怕,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自然人类文明完全过渡到技术人类文明之时,人类自身将成为技术生产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将完全成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因为资本权力宰制下的技术已然改变了人类的最本质处,资本权力将通过技术对人的统治,从而彻底统治人类。
技术需要对自然需要的瓦解
恩格斯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通过对流体静力学与电的发展的考察,揭示了技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8页。由此可见,社会需要极大地影响着技术发展的速度与方向。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与社会的一切需要都是以资本增殖的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当人们不断习惯并依赖于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改变之时,人们也愈发习惯于资本的剥削与宰制,并逐渐忽视其存在。同时,当人们不断对新技术产生强烈的需求与渴望之时,一切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资本权力与技术统治的相互裹挟之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已经成为一种“欲望动物”,人们“要”得太多,为“要”而要,这正是自然人类被技术化的后果之一,也是人类被资本化的后果之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人的交往关系时提出:需要是人的本质,“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继续讨论了不同层级的人类需要,即人类“自然的需要”与人类“历史形成的需要”之间的逻辑关系。所谓“自然的需要”,表达的正是人作为高等动物所产生的本能层面的需要。换句话说,“自然的需要”是人为了作为存在于世界上的生物体所必须的需要,“只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需要就是必须的”。(28)王庆丰:《欲望形而上学批判——〈资本论〉的形上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5期。因此,作为人类本能需要的“自然的需要”,其满足程度将直接决定着人是否能够生存,以及人的生存状态。与“自然的需要”相对,“历史形成的需要”则表现为一种超越人类本能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超越人类“自然的需要”的欲望。“如果说‘自然的需要’是维持人类本身再生产的必要的需求,而‘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是超越本能需要的欲望。”(29)王庆丰:《欲望形而上学批判——〈资本论〉的形上意义》,《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5期。总结来说,人类“自然的需要”自人类诞生伊始便内嵌于人类的生命之中,“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形成而出现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为实现其不断增殖的欲望,必然要求人类不断派生出更多的超越本能需要的欲求,使人们主观认同并渴望于资本逻辑的宰制与剥削。“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就是永不停歇、贪得无厌地榨取财富的强烈需要。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无穷欲望,是因为财富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指挥他人和让他人服从的力量,这就是权力。”(30)[美]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在这个意义上,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权力的意义,资本正是通过这样的权力,使人们不断追逐于权力,即不断渴望于财富的增加,并为此辛勤劳动。“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象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资本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劳动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7页。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展现出的是一种同一性的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被降格为物的本质,资本通过对物的控制,进而控制着人,人与人的关系也逐渐被物化,即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获得承认,实现交往与满足,则必须将自己的全部,投入到对物的无尽追求之中。而在对物的绝对追求中,资本逻辑迫使主体“自然的需要”逐渐被“历史形成的需要”所替代。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揭露的那样,“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为了使这种“物的要素”发展得更为丰富,资本权力通过技术的发展,使主体获得了更大的生产效能,以满足被资本刺激起来的更强的致富欲望。主体对物的依赖性,即对资本的依赖性,在实际过程中则展现为对技术的依赖性,在这个意义上,技术作为一种必要的条件,展现出了对人的控制力量。
当现代技术在生物与智能领域的发展,使自然人类文明完全过渡到技术人类文明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则可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完全改变,使人完全技术化。由此带来的问题是,首先,人类将完全依赖于现代技术,进而完全依赖于资本,人类的身、心将完全被现代技术所统治,进而完全被资本权力所统治。其次,伴随人类的劳动不断被现代技术所替代,同时,生物技术不断预设、修复着人类的肌体,人类的寿命将获得进一步的延长,这似乎实现了一种对人类未来的技术性解放。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的技术实现后,人的解放对于资本的收益何在?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发展的第一要义在于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因此,对于技术本身的发展与进步来说,真正将它们无偿地广泛应用于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似乎存在着更大的阻碍。更需关注的是,伴随技术人类文明对自然人类文明的彻底取代,在资本逻辑下,当技术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完全控制人类之时,技术也将彻底操控人类的需要。技术性的需要,这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成的需要,将完全替代人类的需要。当生物技术发展到极致,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要完全依赖于技术以实现,此时,在技术人类文明中,人类对于技术的需要将替代一切自然人类文明中人类“自然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通过对人身、心的影响,进而激发出调配人类需要的功能,人类对现代技术的需要,使资本权力完全控制着人。人的意义将完全依赖于物的意义,必须赚取更多的金钱,以支付技术对自身需要满足的服务。在这个意义上,即便现代技术的发展在未来可能使人类实现一种技术性的解放,但人类为了获得这种解放,将不得不被资本继续囚禁。现代技术使人类可实现的寿命越是延长,这种囚禁的时间也将愈发延长;解放越是看似触手可及,实现越是遥遥无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对人的解放成为一种幻象,一种虚伪的承诺,无论现代技术发展到怎样的高度,也从未摆脱资本权力对其的利用与控制,技术从始至终服务于资本。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自然的需要”与“历史形成的需要”并非对立而存在,二者皆发展成一种人类的真实需要,即非异化的需要,“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5页。然而,这一切的美好憧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被资本权力下的技术统治所颠倒了,技术化的需要将彻底瓦解“自然的需要”,发展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人,人的本质被资本彻底物化了。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社会福利如何提高,人类将永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存在历史现象,即具有一种命运性。(35)[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28页。当然,对于这样的观点仍然需要我们更深入的理解,但至少在目前来说存在两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第一,现代技术使人类社会的一切发生了最为彻底的改变;第二,这种改变以及改变的彻底性仍将持续下去。因此,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是应当对技术人类文明的到来发出最为强烈的抵抗,还是积极谋划并适应技术人类文明到来后人类的生活及交往方式,这显然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技术命运论”并非劝诫人类认命于技术,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在资本权力宰制下的技术统治中,将伴随技术对人类社会改变的彻底性,迎来一种彻底的异化。在资本权力的宰制下,现代技术所生产出的技术化需要也将彻底瓦解人类“自然的需要”。
规制资本挣脱“技术牢笼”
无论是尼采所言的“上帝死了”,还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抑或海德格尔所形容的历史的“另一个开端”,无一不在为人类揭示一个新的现实,即自然人类文明即将退出,技术人类文明即将登场。然而,人类是否已经准备好去迎接这样的文明时代?人类仍需思考的问题是:技术人类文明的降临,是否可以使全体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现代技术对人类的身、心两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当现代技术已经具备使人类寿命延长,并在绝大程度上替代人类劳动的条件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仍然无法真正实现自由,即便这种自由是一种技术上的自由。因为资本权力将通过技术继续控制人类的需要与选择,人类渴望的自由将被资本挂在橱窗中被包装成商品进行展示,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想获得技术的支持以实现自由的前提是,仍旧需要高额的等价物去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自由近在咫尺,人类将更加为之奋不顾身,投入于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异化劳动之中。人类“自然的需要”也将彻底被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成”的技术化需要所取代。所谓的“技术解放”在资本权力的宰制下,实则一个“技术囚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受资本“囚禁”的时间,将伴随他们寿命的延长而不断延长,直至生命的耗尽。因此,在对技术发展与人类未来的诸多思考中,如何使技术回归其原初的发展目的,将是一个重要且深远的理论课题。资本权力消解了技术的“中立性”,同时异化了技术“工具性”的服务主体,在资本权力的宰制之下,技术越发展,人类距离实现自身真正的需要与实现真正的自由将越遥远。无论在“后人类”时代现代技术将发展到何种高度,我们仍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与其盲目抵抗技术的发展,如“末世论”者们试图构建一种对技术发展的政治限制;或是渴望逃离技术的笼罩,如“游牧论”者们试图在数字和智能技术的控制之外实现一种游牧式的发展;再或者陷入一种乐观的遐想,如“赛博格”式的捍卫人类最后的尊严,皆非现实性的抵御手段,人类更应该抵抗的是资本权利与资本权力下的技术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技术化需要完全替代“自然的需要”之时,所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存在方式,更危险的是,资本权力将通过技术完全控制人,并剥夺人的存在意义,同时使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一种无法破解的“技术悖论”之中。
因此,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调和资本所带来的社会发展与主体异化间的矛盾。也就是说,不能一味地追求一种消除资本的策略,将资本完全否定,连同资本所带来的积极因素一并否定,而是应在保留积极因素的同时,削弱或瓦解资本对人与技术的统治权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必然需要对资本发展的边界进行重塑,使资本力量与统治力量相分离,实现政治逻辑、资本逻辑与人的发展逻辑的协调统一。在此意义上,一切由资本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因素,都将通过政治层面的强大保障,最终完全服务于主体自身的自由发展。使技术复归其原初的职能属性,真正破解由资本逻辑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发展与主体意义丧失间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