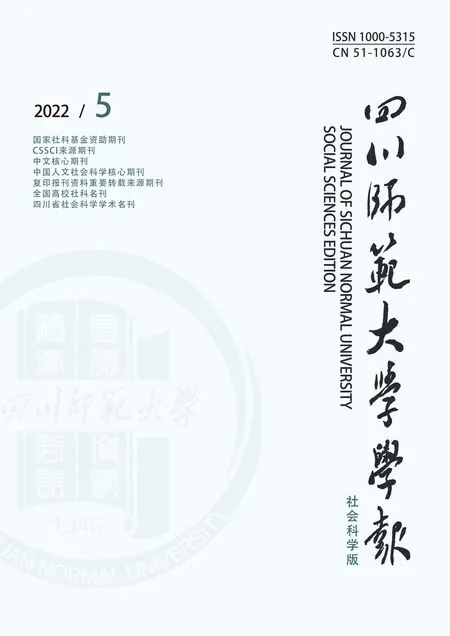《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本研究
丁小丽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本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共产国际文件的汇编文献,由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地下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于1922年4月全文出版(1)第三国际《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人民出版社1922年版。有研究指出,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6号,刊登了署名“朗生”翻译的共产国际二大的宣言。这个宣言与后来出版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的宣言文字一模一样,由此断定《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在1921年7月已经有部分译文。参见: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第99页。。目前学界以《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为整体进行的研究较少,即使有所涉及,也主要是考察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研究(2)钟海《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1920-1927)》,《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第113页;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第99页;张文琳、吕建云《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3页。。《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经典中译本——〈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是笔者检索到的唯一一篇在题目中出现“《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字眼的文章。但该文落脚点在于以《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为例,探讨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可见其仍然是对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研究(3)曾银慧、严雄飞《列宁东方革命理论的经典中译本——〈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决策与信息》2016年第10期,第164-167页。按:该文虽然是以《共产国际议案与宣言》为例,但通篇主要是阐述了《共产国际议案及宣言》一书中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中的思想,书中其他内容几乎未涉及。此外,文末列出的唯一一个“参考文献”著录将出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人民出版社”的社址误写为“北京”。因为1922年版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封面上印有“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同时,封底中的“发行者”为“人民出版社/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此时人民出版社的社址设在李达的寓所,即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对此,后文亦还会有所阐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译本的研读,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认识,有助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理解,有助于拓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掌握。基于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本进行探讨。
一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基本情况概览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汇编文件(5)作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包括三部分内容,是以汇编文件形式传入中国,不是由国人后来汇编而成。。1921年9月1日,《新青年》9卷5号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预告《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即将出版(6)《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5号。。1922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康民尼斯特丛书第四种”正式出版。封面署有“康民尼斯特丛书第四种”字样,封底署“著者”为“第三国际”,“译者”为“成则人”,“发行者”和“印刷者”都是“人民出版社”,出版地址为“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
(一)关于译者成则人
成则人,沈泽民(1900-1933)的笔名,著名作家沈雁冰(即茅盾)的胞弟,字德济。“关于沈泽民用笔名‘成则人’,据谢旦如回忆,‘成则人’和沈泽民谐音相近,据应修人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则为人,不是封建时代农民革命‘成则为王’,笔名‘成则人’大概是这个意思”(7)钟桂松《沈泽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除了用成则人作笔名外,沈泽民还曾用明心、希真、冯虚、直民、罗美等笔名(8)钟桂松《沈泽民传》,第1页。。由于接受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比较早,沈泽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沈泽民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读期间,就开始翻译英文小说,一生翻译诸多国外文学评论和著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田汉等人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认识到中国革命需效仿苏俄,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1年7月初,他翻译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沈泽民1926年随团到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后考取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1930年10月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9)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一个忠诚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回国。“同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成员、宣传教育秘书、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成员、党报委员会总干事会成员、《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负责人”,“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至1933年5月)”,1932年1月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员会书记,1933年11月逝世于湖北,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二)关于“康民尼斯特丛书”
“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康民尼斯特’是英语‘communist’即‘共产主义者’的音译。康民尼斯特丛书,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而出版发行的系列丛书之一”(11)仝华《关于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一至第四种文本说明》,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编《〈马藏〉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98页。。此丛书除了第四种《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其他三种分别为《共产党计划》(布哈林著,张空明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张西望译),《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李墨耕译)。而“康民尼斯特丛书”除了这4本外,还有另外7本,分别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布哈林著,彭成译),《世界革命计划》(胡友仁译),《共产主义入门》(布哈林著,罗雄译),《共产主义》(鲍尔著,张松严译),《创造的革命》(鲍尔著,李又新译),《到权力之路》(柯祖基著,孔剑明译),《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托洛茨基著,罗慕敢译)(12)《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5号。。
关于“康民尼斯特丛书”翻译和出版的消息,最初登载在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5号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中。《通告》主要内容有“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13)《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5号。。从《通告》的这些内容看,它不仅表明了“康民尼斯特丛书”的由来,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引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文献。此外,《通告》除了列出了“康民尼斯特丛书”外,还列出了已陆续出版或正在印刷中或准备出版的其他三大类书籍,分别为“马克思全书”,共15本,有《马克思传》(王仁编),《工钱劳动与资本》(已出版,袁湘译),《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定译)等(14)其中《工钱劳动与资本》今译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今译作《工资、价格和利润》,参见:仝华《关于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一至第四种文本说明》,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编《〈马藏〉研究》(第一辑),第198页。;“列宁全书”,共14本,有《列宁传》(印刷中,张亮译),《国家与革命》(印刷中,康明烈译),《劳农会之建设》(已出版,李立译)等;“其他”,共9本,有《马克斯(思)学说理论的体系》(布丹著,李立译),《空想的与学科的社会主义》(恩格斯著,陈佛突译),《伦理与唯物史观》(柯祖基著,张世福译)等。(15)《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5号。
(三)关于“人民出版社”
当时作为出版和发行“康民尼斯特丛书”的人民出版社,是中共一大闭幕后,根据中共中央局的决定,于1921年9月1日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地下出版机构,社址设在李达的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这里也是党的宣传主任的办公处所。据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并担任撰稿、译稿、组稿、校对和发行工作的李达回忆,“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16)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而封底署名地址的“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是新青年社迁到广州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新青年社的前身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1921年4月,新青年社从上海迁到广州(17)《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第2卷1号开始改称《新青年》),从1915年9月创刊到1926年7月终刊,前后共历经5次迁址,分别为:1917年从上海迁往北京,1920年2月从北京迁往上海,1921年4月从上海迁往广州,1921年7月从广州返迁上海,1922年7月从上海重迁广州。,落户于广州昌兴马路26号。1923年,人民出版社并入广州新青年社。蔡和森1926年曾评价:“人民出版社,设在广东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18)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6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于1950年12月重建。
(四)关于《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内容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三国际议案》,具体包括《国际共产党底法典》,《国际共产党底根本事业》,《加入国际共产党的诸条件》,《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任务》,《共产党与议会主义》,《劳动组合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形下,方应组织劳工代表的劳农会》,《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农民问题的议案》等9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为《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宣言》,具体包括《凡尔赛和会后的国际关系》,《经济的地位》,《战后的有产阶级政体》,《劳农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党》等5方面内容。第三部分,附录《第三国际第一次宣言》。该译本第一次印刷3000册,1927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江书店重印。
二 关于《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语言版本和传入时间的考证
(一)《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译本从何种语言的版本翻译而来
目前学界没有搜集到传入中国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原版本,但《共产国际议案及宣言》存在英文、日文等不同语言的版本,目前学界就传入的版本问题研究较少,因此对《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译本从何种语言版本翻译而来的问题有思考和探讨的空间。本文根据现有的相关资料分析认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译本,可能从英文版翻译而来。具体原因如下所述。
1.从译者沈泽民学习语言和工作经历看
首先,沈泽民于1916年夏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努力攻读专业课程,刻苦学习英文。“虽然学习理工科,同时也喜欢文学,英语基础也很好。他一边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一边在其兄沈雁冰的引导下,从事外国科学小说的翻译工作”。1918年1月,他与哥哥沈雁冰合译美国作家洛赛尔·彭特(Russeii Bond)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筑谭》,并“载于《学生杂志》第5卷第1、2、3、4、6、8、9、12号”。后来,他又翻译《理工学生在校记》,1920年发表在“《学生杂志》第7卷(连载)上”。(19)钟桂松《沈泽民传》,第297页。1920年7月,沈泽民赴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学习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同时翻译英文版的进步小说,撰写通俗科学短文,寄上海《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刊用,以补助学习生活费用。以上表明沈泽民在校期间就有多次翻译英文著作的经历,从其学习经历以及翻译著作情况看,当时沈泽民的英文水平非同一般,这也表明在《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之前(20)至于《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有不同观点。大多数学者赞成是1922年初传入,也有观点认为是1920年下半年传入,根据《新青年》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刊登的《人民出版社通告》预告即将出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看,本文赞同1920年下半年传入的观点。后文有具体阐述。,他已具有翻译英文著作的语言基础和重要经验。此外,沈泽民1921年底回上海参与筹建平民女校,并任英文教员。“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参与《热血日报》编辑工作,负责翻译外文(英、日)报刊资料和撰写评论”(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第169页。。这些从事英文教员以及翻译英文报刊的工作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奠定了沈泽民翻译英文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基础。
其次,沈泽民作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在从事如火如荼的革命工作之余,除了有任英文教员和翻译英文报刊资料和撰写评论的经历外,还在一些重要会议承担翻译工作。如1926年春,刘少奇率中国职工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代表大会,沈泽民作为英文翻译随团前往。会后留莫斯科并进入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师。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翻译工作”(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第169页。。沈泽民学习英文及翻译英文著作的经历为其翻译英文版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提供了重要基础。
2.从《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版本语言看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有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等版本(2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英文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存在,为沈泽民翻译英文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说法提供了文本载体。沈泽民虽然有学习和翻译日文报刊资料的经历,但除了没有资料显示有日文版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存在外,也没有资料显示有日文版的《共产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国内:至于德文,沈泽民在1921年准备“进同济大学德文预科或北京大学德文系旁听,但因同济是专业不对口而北大缺少文凭而作罢”(24)钟桂松《沈泽民传》,第51页。,表明沈泽民没有学习德文的经历。同样,他也没有学习法文或翻译法文相关著作的情况。
就俄文版而言,作为共产国际方面的文件,我们自然联想到俄文版,但可能性不大。
第一,成则人于1921年7月初翻译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通过查阅资料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以及《沈泽民传》等都没有指出在1921年7月之前,成则人有相关学习俄文和翻译俄文著作的经历,倒是有相当的篇幅论述了他学习英文和翻译英文著作的情况,对此上文已有阐述。
第二,成则人1926年到中山大学学习,不但没有资料表明此前他有学习俄文的经历,而且也没有资料表明他有一定的俄文基础。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定俄文基础,但仅有一点俄文基础,很难较规范和准确地翻译出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如此重要的国际性文件。并且从《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成则人译本来看,译文语言比较流畅,对文件中的主要思想表述比较准确,可见,没有比较深厚的语言功底很难达到这样的翻译效果。同时,通过查阅资料也没有发现沈泽民有接触过俄文版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记录。
此外,对于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两位中国代表(25)两名中国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二大的情况后亦有谈及。是否有可能带回俄文版的问题,从目前搜集的资料看,没有看到俄文版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也就是说没有俄文版作为佐证和支撑材料,并且参会的两位代表也未提及版本语言问题。以上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本是从英文版翻译而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
(二)《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时间分析
1.传入时间上的不同观点
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对《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讨论,有较大争议的是《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我国的时间问题。与之相关的是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即是说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传入是伴随着《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我国的,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等同于《第三国际议案和宣言》的传入时间,反之亦然。
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1922年1-2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渠道接受到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这次大会对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认清中国国情和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8页。。类似观点也认为:“通过远东民族会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27)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当然这类观点的重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到1922年初的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时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而不是刚刚接触。但有学者指出,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到我国的时间应在1920年下半年,并认为中共到1922年的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上才接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的观点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原因是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组织严密且效率较高的组织,它制定的战略、政策、策略,一般会比较迅速地传达给各国共产党组织,并很快得到贯彻执行;而在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特别强调对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政策必须严厉实行;所以认为中共在诞生后两年才接受1920年夏共产国际通过的东方革命战略是不可思议的。(28)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第98-99页。
此外,就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中共一大前是否传入中国出现了针锋相对的观点,即一些论著普遍认为中共一大以前该理论没有传到中国。如黄修荣在分析中共一大为什么没有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以及实现革命纲领的政策和策略时,认为是“由于当时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思想还没有传达到中国共产党内”(29)黄修荣《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而针对此类观点,有文章则明确指出:“可以肯定,到中共一大时,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提出的殖民地革命思想已传达到中国共产党内。”因为马林来华筹建中共时,已经将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带到了中国;同时根据1921年《新青年》9卷5号(1921年9月)刊登的即将出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通告》推测,一大前《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已经翻译完成(30)张文琳、吕建云《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3页。。可见,无论是认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时间是1920年下半年,抑或说是中共一大前,还是大多观点认为的1922年初,尽管传入时间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于《共产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上还不够肯定,也就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其实,根据现有资料就这个问题还可以做进一步分析。
2.《第二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时间论证
本文赞成《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为中共一大之前的观点,除了作者在其文章中给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有文献指出1921年7月初,沈泽民翻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第169页。。再对比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可见,认为中共一大之前《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已经传入中国的说法,有一定的可信度,但还稍显笼统。根据现有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论证,本文进一步认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时间大概为1920年8月。
第一,共产国际二大结束后,俄共(布)远东局外交科派往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已经获悉共产国际二大的相关信息,他在1920年8月17日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要求从俄共(布)中央和西伯利亚寄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书籍,并希望建立定期转寄报刊和文件的制度(32)《维经斯基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还有研究指出,同年8月,维经斯基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社”,在学社内部设置“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和消息(33)张文琳、吕建云《中共“一大”为何没有采纳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82页。。
第二,1920年8月13日,当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道:“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34)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蔡和森给毛泽东信中这段文字虽然无法体现《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具体细节,但也不能否认存在中国代表在共产国际二大后,将大会资料带回中国的可能性。毕竟共产国际为支持并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其存续期间曾通过多种形式将一些纲领性文件传入中国。如召开有中国代表参加的会议,成立专门机构,派遣代表以及培养革命骨干等形式。
第三,前文已经谈到译者成则人曾在1920年8月与田汉等人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特别是学习和讨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共产国际的文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仿效苏俄,以俄为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1920年8月时,译者沈泽民已经接触到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这也最能体现和印证《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在1920年8月传入的观点,而这更为成则人后来的翻译工作做了文本准备。
以上是根据目前档案资料就《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时间作出的概要分析,当然就此问题,还可以进行一定的延伸,即根据《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的时间,来考证它是如何传入,即通过什么途径传入中国的。现有研究中分歧最大的是谁将《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的:主张《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是1920年下半年传入中国的认为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传播到中国的,但是具体是哪位代表没有说清楚;主张《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是中共一大之前传入中国的,则认为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其传播到中国。
三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重要作用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其第一部分中《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35)有文章认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最有价值的就是专门翻译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核心文件《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参见:田子渝、杨荣《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传入我国的时间与最初影响》,《江汉论坛》2010年第8期,第99页。,首次给中国人带来了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是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在国内得以广泛传播的经典著作之一。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辑录的《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包括两部分:“A议案”,共12条;“B附加议案”,共8条。将《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中《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与《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对照发现:“A议案”部分是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之一,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36)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1920年6月5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列宁起草的提纲是作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决议草稿提交共产国际二大;“B附加议案”,是罗易向大会提交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共20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于7月25日对两个提纲进行了审议。26日,列宁代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指出,“我们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提纲初稿和补充提纲”,并对提纲的基本思想作了说明:“我们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37)《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没有收入列宁1920年7月26日代表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如列宁所说,“是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说明”,即“说明了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277页。28日,大会正式通过了两个提纲。
语言带有一定的时代印记,《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关于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议案》的译文虽然并不精准,但主要思想已经表达清楚,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和任务,是共产国际在此问题上制定的第一个完整的革命纲领。它指出了必须把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笼统说的民族利益即统治阶级利益区分开来,把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区分开来;认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现象;同时强调要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封建主义的农民运动,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要同东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紧密联盟。
鉴于对民族殖民地理论的探讨较多,本文主要分析《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是将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文件介绍到中国的重要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在国内的早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伴随着《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中国后,国内报刊对其主要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译介和宣传。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38)《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李达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了共产党的鲜艳旗帜,喊出了‘共产党万岁’的响亮口号,号召‘举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的国家’”。参见:《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李达文集》编辑组编《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页。译介了大量的关于共产国际方面的文章。如在其创刊号上刊登了《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一文;1921年的第3号和第6号分别刊发了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第三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宣言》,并直接翻译了共产国际二大的部分内容。同时《共产党》月刊还大量刊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方面的文章,如刊登在第1号的《共产党同他的组织》、第2号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第3号的《共产党的出发点》、第4号的《我们为什么主张共产主义》和第5号的《劳农制度研究》等。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上海出的《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39)毛泽东《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此外,1922年1月15日,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的《先驱》半月刊在其创刊号发表了《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以及《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第1部分到第5部分的内容。《新青年》于1923年6月第1号发表了《东方问题之题要: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通过》,于1924年12月第4号译载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以及《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等。1927年4月,长江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辑录了列宁的《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通过这些可以看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传入国内后,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文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影响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世界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认识与看法。这可从这一时期李大钊写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1921年1月)、《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年3月),陈独秀写的《讨论社会实际问题底引言》(1921年2月)、《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1921年9月),李达写的《马克思还原》(1920年12月)、《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921年4月)等文章看出。共产国际二大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三大、青年共产国际二大等国际性会议,逐渐认识到:世界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范畴,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等等。此外,我们从《共产党》月刊这一时期刊登的一些文章中也能体会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强调组织政党的必要性,呼吁进行直接革命,以实现社会革命。如1920年12月7日第2号刊发《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1921年4月7日第3号刊发《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1921年6月7日第5号刊发《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等。1922年1月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刊发《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和《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等文。这些文章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相关问题的新理解。
第三,《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和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40)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24年7月1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认识到:“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41)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24年7月1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5卷,第1页。“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无产阶级组成工会作经济争斗,并且要组织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商人而领导他们革命。”(4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第804页。这些认识相较中共一大前后关于中国革命对象、革命同盟者等问题的理解有巨大进步。此外,通过对比中共一大和中共二大政治纲领,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以及革命战略等问题的分析都日趋成熟。如关于革命性质,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强调“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义革命格外迅速成功”(43)《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6-77页。。这从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展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面相,拉开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综上,学界对于成则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中译本鲜有研究。本文主要对其传入的语言版本问题进行了分析,加强了对其传入时间的论证,阐述了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作用等。深化对《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的考证和探讨,对于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以及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