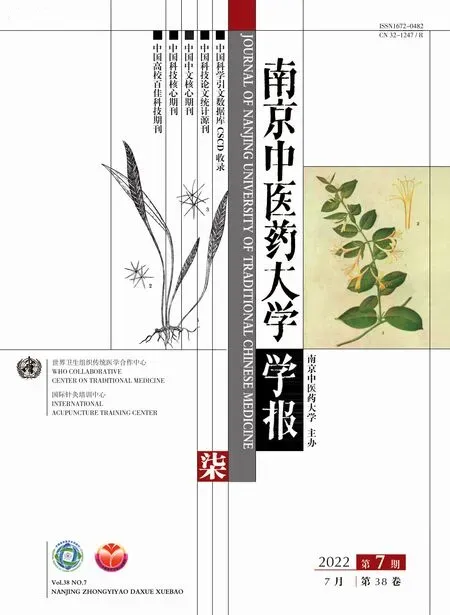国医大师夏桂成从“心-肾-肝-脾-子宫轴”论治复发性流产
唐培培,殷燕云,顾旻,陈颖君
(1.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2.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复发性流产指患者发生2次或者2次以上妊娠28周内流产,发生率约1%~5%[1]。临床上,复发性流产病因较为复杂,主要包括基因异常、解剖异常、内分泌紊乱、感染因素、免疫因素、精神因素及环境因素等。本病归属于中医学“滑胎”范畴,《诸病源候论》最早提出“数堕胎”之名[2],清代《医宗金鉴》将本病定名为“滑胎”[3]。
中医学认为本病发病机制为冲任虚损,胎元不固。中医药在复发性流产治疗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在本病治疗方面有独到的经验,夏老立足“心-肾-肝-脾-子宫轴”,以中医治未病思想,结合调周法,注重孕前及孕后管理,从而提高妊娠率及抱婴率。现总结夏老治疗复发性流产的临床经验,报道如下。
1 “心-肾-肝-脾-子宫轴”理论依据
心肾观是中医藏象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肾藏精,主生长发育和生殖,为五脏阴阳之本,人体生命之源。《素问·上古天真论》言:“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故形坏而无子也。”[4]2《医学衷中参西录》曰:“男生女育,皆赖肾脏作强。”[5]心乃君主之官,神明之脏,于诸脏腑中有着首要地位,可调控其他脏腑。《灵枢·邪客篇》记载:“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6],《素问·灵兰秘典论》亦言:“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4]17。而心肾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中藏经》曰:“火来坎户,水到离扃;阴阳相应,乃为和平”[7],初步提出了心肾相交的理论。《千金要方》云:“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8],首次明确提出心肾“水火相济”的理论。《傅青主女科》亦非常重视心肾理论,言:“盖胞胎居于心肾之间,且上属于心而下系于肾”[9]28。可见,通过胞脉、胞络相通,子宫与心、肾两脏密切关联。
基于前人学术思想理论及长期临床实践,结合中医传统理论,夏老于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了“心-肾-子宫轴”理论[10],认为心肾对诸脏功能活动具有统领作用,为生殖轴的核心,子宫为育子之脏,通过胞脉胞络与心肾相连,子宫的作用有赖于心肾两脏的主持。“心肾相交,全凭升降”[11],心肾两脏之火降水升有赖于气机的升降和物质的供养。“女子以肝为先天”[12],肝藏血,主疏泄,体阴而用阳,疏乃升,泄乃降。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气机升降之枢纽。唐容川《血证论》曰:“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主于肺;其间运上下者,脾也。”[13]肝脾升降有序、气血充足是保持心肾交济的重要因素。因此,夏老指出肝脾对心肾相交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并在原有“心-肾-子宫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心-肾-肝-脾-子宫轴”。
2 “心-肾-肝-脾-子宫轴”失衡是复发性流产的主要病机
2.1 肾虚为根本,心为主导,心肾不交是中心环节
肾对生殖有重要作用。肾藏精,为先天之本,主生殖和生长发育。《傅青主女科》中云:“大凡妇人之怀妊也,赖肾水以荫胎,水源不足,则火易沸腾,……水火两病,胎不能固而堕矣。”[9]46《女科经纶》中记载:“女子肾脏系于胎,……若肾气亏损,便不能固摄胎元。”[14]夏老强调,肾虚是导致复发性流产的主要因素,亦为首要因素,胎孕得肾阳温煦,肾精滋养,肾气固摄,方可进一步发育生长,反之,则易发生流产。若肾阳虚衰,胞宫虚寒则胎萎不长;若肾阴亏损,肾气虚弱,则胎不成实;若冲任受损,则系胎无力,而致滑胎。
心藏神而主血脉,居上焦,属阳属火;肾主水,位下焦,属阴属水。《素问·评热病论》曰:“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4]67,“水欲升而沃心,火欲降而温肾”[15],一升一降,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心肾交于胞宫,胞宫藏泄有度,胚胎方可正常生长发育直至分娩。《辨证奇闻》曰:“胞胎系于肾连于心,肾未损,肾气交心,心气通胞胎,故胞胎欲堕而未堕”[16]501,由此可见,胎元稳健的前提是肾气未损且心肾交合。一旦心肾不交,则肾虚进一步加重,胞宫失于封藏固摄,导致屡孕屡堕。因此,夏老指出,肾主生殖的更高调控部位在心,心为主导,心肾不交是复发性流产发病的中心环节。
2.2 肝脾气血升降失调是重要影响因素
陈士铎言:“心欲交于肾,而肝通其气;肾欲交于心,而肝导其津,自然魂定而神安”[16]719,肝为心之母、肾之子,在心肾相交中有重要的媒介作用。肝主疏泄,维持情志舒畅,而心藏神,主宰情志活动,倘若肝气郁结,疏泄异常,则心神不安;肝藏血,心主行血,若肝血亏耗,母病及子,血不荣心,易致心神失养。肝肾同源,肝藏血,而肾藏精,若肝血不足,则肾精亏损;肝主疏泄,而肾主封藏,若肝气疏泄正常则肾气开合有度,若肝气疏泄异常则肾气藏泄失调。
《杂病广要》云:“人之一身,以脾胃为主,……水火既济,而合天地交泰之令矣。”[17]可见,脾胃在心肾交合中亦有重要的作用。脾主运化,乃气血生化之源,水谷精微通过脾之升清作用上输于心,若脾运失健,则化源不足,导致心失所养。肾藏先天之精,乃先天之本,而脾主运化水谷精微,乃后天之本,且先天后天相互资生,相互影响,肾精及其所化生的元气依赖于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及其所化生的谷气充养,脾精不充则肾精失养,脾气虚弱则肾气虚亏。
《傅青主女科》早就提出肝脾对妊娠有重要的影响:“然则胞胎之系,通于心与肾,……补肾可也,何故补脾?然脾为后天,肾为先天,……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也”[9]38,又言:“妇人有怀妊之后,……其胎必堕,人皆曰气血衰微,不能固胎也,谁知是性急怒多,肝火大动而不静乎”[9]45。夏老强调,肝脾气血物质的供养及肝脾的升降疏泄对心肾二脏的交合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妊娠结局。肝脾升降有序、气血生化有源,则心肾交合正常,反之则导致心肾不交,最终引起流产。
3 调节“心-肾-肝-脾-子宫轴”防治复发性流产
3.1 防治结合,分期调理
夏老认为对于复发性流产类患者,应当防治结合,且防重于治。既往有流产史的患者不应盲目再次妊娠,而应寻找病因,“预培其损”[18]。《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4]6夏老强调,阴阳平和,方不易为邪气所伤,对于复发性流产的患者,孕前应当结合调周法,辨体调质,调理阴阳,从而真正做到未病先防。
夏老首次提出“经间期学说”,创立了“调整月经周期节律法”(简称调周法),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月经周期划分为行经期、经后期、经间期和经前期,从而完善了妇科周期理论。夏老指出,临床上应当依据月经周期各个阶段的阴阳转化及气血盈亏之变化规律,分期调理。行经期阳转阴,应活血调经,方用五味调经散加减;经后期重阴,应重在滋阴养血,补肾填精,方用归芍地黄汤加减;经间期重阴转阳,应补肾活血,方用补肾促排卵汤加减;经前期重阳,则重在补肾助阳理气,方用毓麟珠加减。夏老指出,孕前调周的同时应注重脏腑辨证,以“心-肾-肝-脾-子宫轴”理论为指导,疏肝健脾,宁心安神,将调周序贯法运用其中。
3.2 心肾合治,肝脾同调
夏老强调,“心-肾-肝-脾-子宫轴”理论应贯穿治疗始终。夏老认为补肾为固摄胎元的关键[10],且应兼顾涵养冲任。肾阳虚者应补肾助阳,肾气虚者当补肾益气,肾阴虚者需滋阴补肾,临证常用熟地、酒山萸肉、怀山药、续断、盐杜仲、仙灵脾、槲寄生、菟丝子等补肾填精之品,亦常用紫河车、鹿角霜、阿胶等血肉有情之品。
临床上,保胎尤其是滑胎患者心理压力大,易精神紧张,烦躁不安,夜寐多梦,持续处于紧张、焦虑、压抑的状态。夏老指出,对于复发性流产患者,临床上须重视心理疏导,治疗宜宁心安神,善用钩藤、莲子心、青龙齿、茯神、炒枣仁、丹皮、灵芝、琥珀粉等,心火偏亢者可予黄连清心降逆安神,使心肾相济,则胎元稳固。同时要注重肝脾的调节,临证尤应注重疏肝健脾,疏肝之品如广郁金、合欢皮、白芍、柴胡、荆芥等;健脾之品多选用党参、白术、木香、陈皮、炒扁豆、茯苓等,以旺后天之源,且有助于心肾相交。心肾合治,肝脾同调,阴阳平衡,胎元稳固,最终改善妊娠结局,提高抱婴率。
4 验案举例
患者豆某某,女,38岁,2019年9月30日初诊,主诉:不良妊娠史3次。患者2015年、2017年、2018年均在孕50 d左右因胚停行药流+清宫术,其中第2、3次妊娠均予黄体酮保胎未果,第3次妊娠行绒毛染色体检查未见明显异常。2018年女方行性激素检查、生殖免疫全套及凝血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男方精液常规、精子形态学分析、精子DNA完整性检测未见明显异常。因患者恐惧再次流产,后避孕至今。患者平素月经后期,40~50 d一行,量偏少,色红,有少量血块,轻度痛经,经期8~9 d。末次月经:2019年9月21日。刻下:月经周期第10天,带下量少,无明显锦丝带下,大便溏,受凉后腹痛,自觉易乏力,寐欠佳,易醒,多梦,基础体温(BBT)示低温相,舌质淡红,边有齿痕,苔薄白,脉细濡。中医诊断:滑胎(脾肾两虚,心肾不交),西医:复发性流产。从经后期论治,方用归芍地黄汤合清心健脾汤加减,处方:钩藤(后下)10 g,炒枣仁15 g,莲子心5 g,党参15 g,丹参10 g,生黄芪10 g,茯苓10 g,茯神10 g,炒白术12 g,炒山药12 g,炒白芍10 g,菟丝子10 g,续断12 g,巴戟天5 g,山萸肉10 g,灵芝粉(吞服)6 g,琥珀粉(吞服)3 g。共10剂,水煎,每日1剂,早晚分服。
2019年10月10日二诊,月经周期第20天,患者自觉乏力较前好转,便溏、多梦较前改善,见锦丝状带下,易烦躁,BBT示低温相,从经间期论治,方用补肾促排卵汤加减,处方:赤芍10 g,白芍10 g,红花3 g,制香附10 g,川芎10 g,淮山药10 g,山萸肉10 g,续断10 g,茯苓10 g,合欢皮10 g,荆芥10 g,巴戟天8 g。共7剂,水煎,每日1剂,早晚分服。
2019年10月17日三诊,月经周期第27天,乳胀,烦躁不安,BBT示高温相偏低,从经前期治之,拟毓麟珠合钩藤汤合越鞠丸加减,处方:党参12 g,炒白术12 g,炒白芍10 g,茯苓10 g,茯神10 g,巴戟天10 g,炒枣仁15 g,钩藤(后下)10 g,莲子心5 g,陈皮10 g,制苍术12 g,广木香10 g,荆芥10 g,广郁金10 g,紫石英15 g,鹿角霜(先煎)10 g,杜仲10 g,制香附10 g,生黄芪10 g,合欢皮10 g。共14剂,水煎,每日1剂,早晚分服。
2019年10月31日四诊,月经来潮第1天,轻度痛经,BBT示低相,从行经期论治,方用五味调经散合越鞠丸合异功散加减,处方:制苍术10 g,炒白术12 g,制香附10 g,陈皮6 g,姜半夏6 g,炒五灵脂10 g,红花6 g,丹参10 g,益母草12 g,泽兰10 g,赤芍10 g,续断10 g,肉桂(后下)6 g。共7剂,水煎,每日1剂,早晚分服。
此后继续调治,诸症好转,患者月经周期调整至35 d左右,经治半年余患者怀孕,2020年6月4日复诊,患者停经43 d,腰酸时作,胃脘时不适,恶心不显,易疲乏无力,乳房微胀,大便溏,受凉后腹痛,寐欠佳,易醒,多梦,舌偏红,苔腻,脉滑带细濡。实验室检查:雌二醇(E2)285 ng·L-1,孕酮(P)31.65 ng·mL-1,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3 519 mU·mL-1。治予清心健脾疏肝,补肾安胎,方用温胞饮合清心健脾汤加减,处方:钩藤(后下)10 g,莲子心3 g,党参15 g,生白术15 g,炒白术15 g,白芍10 g,广木香6 g,广陈皮6 g,砂仁(后下)5 g,杜仲10 g,菟丝子10 g,槲寄生10 g,炒续断10 g,鹿角霜(先煎)10 g,巴戟天10 g,炙黄芪15 g,蚕茧壳7枚。共7剂,水煎,每日1剂,早晚分服。
后患者定期复诊,调整用药,诸症好转。继予保胎治疗,足月产一子。
按:本病属于祖国医学滑胎之范畴。患者既往西药保胎未果,双方流产因素筛查未见明显异常。患者月经后期,BBT示黄体功能不全,易疲乏无力,大便溏,受凉后腹痛,寐欠佳,易醒,多梦,结合全身症状,辨证为脾肾两虚,心肾不交。肾阳虚衰,则胞宫虚寒而胎萎不长,肾气虚弱,则胎不成实,脾虚则气血生化不足,气机升降不利,故心肾不交,屡孕屡堕。夏老嘱孕前先调治月经,纠正体质偏颇,孕后继予保胎。“心-肾-肝-脾-子宫轴”贯穿本病治疗的始终。孕前从调周着手,初诊时正值经后期,乏力、便溏、寐欠佳,从滋阴养血、清心健脾论治,方选归芍地黄汤合清心健脾汤加减,方中钩藤、莲子心、炒枣仁、茯神、琥珀粉、灵芝粉宁心安神;炒山药、炒白芍、山萸肉、丹参滋阴养血,补肾调经;菟丝子、续断、巴戟天补肾助阳,党参、生黄芪、茯苓、炒白术健脾益气。药后患者乏力、便溏、多梦均较前改善,二诊时患者正值经间期,易烦躁,本期重阴转阳,从补肾活血、调和气血论治,方用补肾促排卵汤加减,并加荆芥疏肝解郁。三诊时患者正值经前期,烦躁不安、乳胀,从补肾助阳、疏肝解郁论治,方选毓麟珠合钩藤汤合越鞠丸加减,在助阳的基础上,加入疏肝理气之品。四诊时患者正值行经期,从活血调经论治,方选五味调经散合越鞠丸,行经期加入适量温药如肉桂有利于气血畅通。此后灵活运用调周法,预培其损,辨体调质,未病先防。孕后患者烦躁,心理压力大,从补肾安胎,清心健脾论治,注重调节情志,宁心安神,心肾相济,则可稳固胎元,终获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