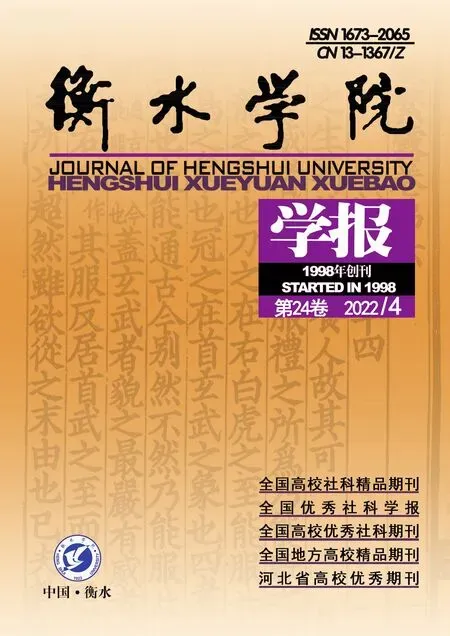董仲舒人性教化思想视域下思政课有效性探索
谢狂飞
董仲舒人性教化思想视域下思政课有效性探索
谢狂飞
(枣庄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枣庄 277100)
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传承和发展了孔孟之道意义上的人性论思想,从一个集大成的宽广视野拓展了对人性论的综合理解。董仲舒既重视人性的内在超越性,也强调不能忽视自然属性意义上的人性之自然维度。正是因为人性中有善的成分,也有恶的可能,所以董仲舒特别重视社会教化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作用。作为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注重社会道德教化并提出了“教化成性”的主张,同时,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进行了一种批判的传承,强调“性待教而为善”,善性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成就的,而是通过后天的教化才能将其转化成善性的实然状态,这对今天更有效地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教育功能并切实提升思政课的有效性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和意义。
董仲舒;人性论;教化思想;思政课;有效性
人性本善抑或是人性本恶?这是非常类似于莎士比亚经典戏剧《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句子“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中所彰显的带有终极道德探索意义的大问题。探讨思政课德育维度上的有效性问题,是绕不开对于人性善恶学说的讨论的。长期以来,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仅仅被限制于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狭隘的理论范围之内,并没有将其探讨扩展到其可能的对于思政课的具体教学实践的德性建构运用范畴中去。
1 董仲舒人性论概述及其现代德育意蕴
从思政课德育维度的源头去追溯,那么,关于人性探讨最早的开创者无疑是孔子。孔子在一种认可人性发展无限的可能性的前提下指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因为人性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的角度来说是相近的。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境界上之所以会出现天壤之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字——“习”。针对这个“习”字,后来孟子进一步发挥,“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外在的环境或者说外物本身,会遮蔽人的赤子之心,正如老子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告子则认为人性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因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下》)孟子针对告子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他的理由就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的性善论是建立在德性之端先验存在于德性主体的内在的价值事实的前提之上的。
相比于孟子充满浩然之气的性善论,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375荀子的观点沿袭了告子“生之谓性”(《孟子·告子上》)的观点,荀子说“不事而自然谓之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1]357,这就意味着荀子只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的意义谈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荀子没有看到人之为人在道德价值追求意义上的向上的超越性。
针对人性的问题,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提出“性三品”的理论。董仲舒指出:“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还认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春秋繁露》)从思政课有效性提升的角度来看,董仲舒在这里所提出的“质朴”一词对于我们在网络化时代切实改进思政课的教学实践方法并进而让思政课做到真正地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长期以来,孟子性善论对思政课来说是一种主要的人性论资源,但对董仲舒的质朴人性观研究得太少,而在今天,董仲舒的质朴人性观对于现代思政课的有效性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事实上,董仲舒的质朴人性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孔子说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这里孔子所强调的“野”就是一种带有浓厚乡野气息的人性之质朴。孔子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只有将后天的道德教化与先天的人性之质朴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就儒家的君子人格。
荀子也指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但是,相较而言,董仲舒的人性论从一个更加直接的角度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正如孟子所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与孟子相比,董仲舒更是强调:“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思政课的德育维度同样在实践使人成为人的重要的德育功能。董仲舒的人性质朴论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成为一个人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自然属性意义上的生长过程,而是一个“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的人文化成的教化之后的成长过程。
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的《实性》中特别指出:“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缲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这段话明确区分出三种境界的人性,即“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2]。董仲舒的这种将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品的做法后来就被公认为是董仲舒的“性三品”人性理论。事实上,董仲舒的这种对人性进行层次划分的思想是符合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的,并不是其对于人性有一种天然的偏见。德性的后天建构本身就需要我们在认可人性之善的前提下尊重德性主体的个体差异性。孔子也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德性主体的道德悟性和德性践履路径是有所差异的,有的学生适合以儒家心性之学的方式导入,如对弟子颜回,孔子就采取一种德性智慧启发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而对于子路,更多的是在道德行动的直接指引上下功夫。“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论语·先进》)
董仲舒认为“性者,天质之朴也”“性者宜知名矣,无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3]389。他甚至还指出“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3]376。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仁气”与“贪气”显然与孟子所说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章句上》)有很大的不同,也更有基于现实人性的教育说服力和基于常识观察的伦理合理性。尊重一种基于理性的真实人性观察,这正是切实让德性主体真诚信任德性教育的前提之一。
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人性,其实类似于英文中的“function”,意思就是一种功能或可能性。人性本身不是善的,是未完成的,人性最终成就的“善良意志”或“善之德性”,是董仲舒所说的“仁气”在教化之后的成果。相比于孟子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孟子·公孙丑上》)的举例,董仲舒的经典比喻是“禾米”之喻,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3]386“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3]378因此,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可以被概括为“性未善”,相比于孟子性本善,董仲舒赋予了后天教育或教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的教化意义和内涵。
2 基于董仲舒人性论的教化思想探析及其现代价值
尽管董仲舒教化思想是关于董仲舒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遗憾的是,董仲舒教化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教育意义,特别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课的视野来看董仲舒教化思想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启示作用的问题,长期以来因为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思想的强势遮蔽而没有被充分地凸显和重视。相比于孔子基于其仁者爱人意蕴的仁学德育,董仲舒更加重视基于天道和人性的后天教化的作用。孔子仁学思想更加重视个体道德建构意义上的德性涵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而董仲舒则更加重视整体意义上的社会教化的作用。
董仲舒关于人性论的观点类似于《中庸》中所说的“天命之谓性”,人性通于天性,人性包含着重要的“天性”之维度。“天生民性”“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性,止之外谓之人事”,善是“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3]378。《汉书·董仲舒传》曰:“天令之谓命。”朱熹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中庸章句》)董仲舒在这里明确区分了“听天命”和“尽人事”的两个德育维度。天性和人事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如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的。相比于孟子过犹不及的性善论来说,董仲舒更加强调教化意义上的“尽人事”的重要性。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与其“天人合德”的观点紧密相连的,而这种“天人合德”思想背后的理论则是天人感应。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性论的讨论有一个特点,“即以善恶论性”[4],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成了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中和论者”或“综合论者”。“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现代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性和思政课视野下德性建构环境的复杂性都需要我们多去借鉴董仲舒的人性智慧进而更好地提升思政课的有效性。
思政课有效性的提高,需要有直面现实的人性智慧作为指引。《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汉赵岐注:“充实善信,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孟子的这种德性理想拔高确实会使人感到一种道德情感的振奋,但是“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孟子·尽心上》)从现实的德育培养或德育建构角度来说,孟子的性善论显而易见有其问题,无法切实地让所有的受教育者信服。
针对人性的洞察,是需要基于生命成长的发展观点的。既需要有直面现实道德挑战的勇气去看到人性之恶的可能性,也要有相信未来的道德信念去逐渐扩充人之为人的善端。董仲舒在这一点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人性之善恶不是既定的、静态的、被研究的客观对象,而是基于“生生之德”的充满无限生命可能性的动态过程。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在我的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这种形而上学本来就是讲‘宇宙之生’的,所以说‘生生之谓易’。”[5]
从董仲舒的观点来看,这种生生的意味是有其双向性的。如果将一个人的善端不断地培养并使其很好地生长,是可以成就一个人高尚的德性的;但相反,如果没有很好的社会教化环境和实践,那么,很可能一个人的恶端也会生长。因此,从教化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做到抑恶和扬善的结合。董仲舒的人性论恢复了人性之本初的质朴状态,从董仲舒的人性论的观点来看,人性中蕴含着人向善行善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应然状态,要将这种应然层面的善的可能性或潜能转化为实然层面的真实德性践履条目,是需要有系统的道德践履意义上的社会道德教化的。
董仲舒指出:“以麻为布,以茧为丝,以米为饭,以性为善,此皆圣人所继天而进也,非情性质朴之能至也,故不可谓性。”(《春秋繁露·实性》)人性的天性维度只是赋予了人之为善行仁的可能性,而要将这种德性生成之可能性凝聚成德性主体真实具有的德性,是离不开基于实践智慧的道德实践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人性之善恶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需要经过后天教化的实践问题。作为人何以成为人?这不是一个思辨理性意义上的玄之又玄的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应当如何实践才能成为人”的道德实践的问题。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6]。毋庸置疑,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贯穿儒家始终的教化思想和传统,既注重“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也重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种深厚的儒家教化传统为当前的思政课有效性的切实提高提供了重要的镜鉴启示。
道德教化是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和路径。孟子说:“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德性主体要做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的德性境界,就必须历经社会人伦交往意义上的道德教化实践。
关于道德教化的重要性,《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有了庶和富的社会物质基础之后,就必须做到真正的“教之”,这样才能做到社会的整体进步。
董仲舒的人性论思想传承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董仲舒也指出:“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3]374“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3]386《说文》:“名,自命也。”《春秋繁露》:“名者,所以别物也。”
从思政课有效性提升的角度来看这种人性论意义上的名实相符问题,我们就能看出,思政课的教育首先就要针对学生内在的德性建构进行相应的“正名”的德性智慧熏陶。作为人,何为正确?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如何才能实现人生的道德价值?如何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生的幸福?在这种基于人性之善的正名的过程中,本身就能切实树立学生道德意识上的更高的人生期待,而这种道德意识上对自我的更高的期许正是最终激发学生德性自觉践履的内生动力。
3 董仲舒人性论思想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借鉴
董仲舒强调:“今世暗于性,言之者不同。故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洁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针对人性的问题,董仲舒有了更多的理性审视和思考。要真正地把握人性本身,就必须通过追根溯源的方法去把握人性之源头。按照董仲舒的观点,“性者质也”,探讨人性本身就是要探讨人性的全幅性的本质,而不能“举一废百”,即只是偏重于人性的某个方面,而忽视了整体意义上的人性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进而造成对于人性看法的片面性。正如孟子所说“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同时,董仲舒强调,要说明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必须直面人的自然属性,换言之,不仅要从人性之善的维度相信人性光辉的无限可能性,也要尊重人性的弱点。不能脱离形而下意义上的人的自然属性去悬空地谈论形而上意义上的人的内在道德超越之性。
因此,董仲舒强调:“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从思政课有效性提升的视角来看,只有当我们正视人性全幅意义上的整体性,才能做到既坚持思政课的高远的立德树人的目标,同时又坚持其脚踏实地的在实践上的务实性。立德树人是思政课的根本任务,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通过全面把握对人性的理解进而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学实践成效。
董仲舒说:“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故心之为名栣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栣”:“弱儿,从木,任声。”从思政课有效性的角度来说,它的意思就是“限制、控制、制约、禁制、禁锢等”[7]。孔子也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人之所以需要约束自己和做到克己复礼,就是因为人性具有可能趋向于善和恶的复杂的可能性。教育需要有高远的目标,但教育者不能天真地认为人性是全然善的。敢于正视人性善恶问题的复杂性的现实,才能真正实现深入人心的有效的思政课育人之课堂。
董仲舒的人性思想内嵌着儒家克己的德性实践工夫。儒家克己精神的本身就意蕴着可资思政课开发的德性实践质料和精神营养。孟子也强调:“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孟子·滕文公上》如果没有很好的社会教化和与此相对应的经由有效德育所形成的内在和外在的约束力量,那么,就会出现人性向坏的方向无节制的地发展,进而会导致孟子所说的“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的情况。即使是德性伦理所推崇的内在德性的建构,其路径的实现往往也是从外在规范开始的,不仅要“博学于文”还要做到“约之以礼”(《论语·雍也》),经由“礼”的约束和节制,循序渐进,最后才能逐渐沉淀和浸润成德性主体内在于心的“仁”和“善”。
当然,董仲舒同样强调“爱”对于人性之善得以建构的重要意义。《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同样也传承了孔子仁爱的思想。《孟子·离娄下》说:“仁者爱人。”《孟子·尽心上》也记载:“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尽心上》还说:“亲亲,仁也。”董仲舒不仅传承了儒家以“爱”释“仁”的注重真诚道德情感的精神,而且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董仲舒说:“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还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春秋繁露·仁义法》)如果说孔子和孟子更多的是从整体视域的高度来阐述何谓仁的问题的话,那么董仲舒则在德性践履的维度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究竟什么是仁。董仲舒说:“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董仲舒所说的这种仁德境界显然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想象,而是道德实践之后才能达成的德性状态。
朱熹也说过:“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8]他甚至强调“人只有天理、人欲两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9]。这都说明,要培养人的仁德,需要持之以恒进行这种针对人性弱点的克己和节制的工夫。直面德育的艰难,才能成就德育的目标。董仲舒的人性思想提醒我们,德性的培养或者说实现一种生命的“归仁”之境界,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一种久久为功的持续的德性践履努力。
要更好地了解董仲舒的人性思想,还必须综合地了解其“天人感应”的思想。董仲舒说过:“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道与人道是紧密相关的,道德伦理世界的道德动力有其在天道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伦理本体基础。如果人性追求善的动力仅仅是因为现实的需求,那这种动力是无法做到一种超越一切外在束缚的持续性的。董仲舒这里所强调的天道对于人文伦理的指令性不是一种所谓的神学意义上的命令性,而是基于德性主体内在超越性的向度。正如孔子所说:“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下学学人文和伦理,上达达于天命天德,下学和上达是生命学问之整体。天道最终要下贯到人伦之伦理实践才能得以体现。《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这种诚就是人之诚。《中庸》还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只有尽到人性善之诚,才能化生和养育无限生机,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尽到人心之伦理实践责任,方能做到如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
董仲舒也强调:“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不暖不生,不凊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凊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春秋繁露·基义》)人的行为要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需要一种基于内在超越性的天道人伦作为基础。人的道德价值有其令人敬畏的价值和尊严,这种道德价值不能仅仅是建立在充满变化的外在幸福追求上,也不能仅仅依托一种基于具体道德情境的个体理性选择,而且还应该建立在一个无条件的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崇高的道德律令的基础之上,这种从德性主体心中发出的道德律令直通一种“天命之谓性”(《中庸》)的天之道德命令,具有一种道德律令意义上的神圣性。
董仲舒的人性观点也直接影响到了其在儒家伦理义利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他强调“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春秋繁露·玉英》),这就呼应了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义利观点。孔子还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都在告诉我们,重义本身就是德性涵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学生如果长期接受的影响都是关于“利”的方面,那么,就会逐渐导致其内心的浮躁,而这种浮躁和喧嚣本身就会导致人本心的迷失。因此,孟子才强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总之,董仲舒的人性论在相当程度上传承和发展了孔孟之道意义上的人性思想,可谓是关于人性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强调人性之质朴,重视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现实属性和超越属性的结合的角度来综合全面地看待人性问题,这给思政课有效性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营养。同时,董仲舒重视“中民之性”,强调要加强总体意义上的道德教化,使德性主体从善质到成善的可能性转化为稳定持久的内在德性,这同样是思政课有效性提高可以借鉴的重要精神营养。
[1] 荀况.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3.
[3] 董仲舒.春秋繁露[M]. 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二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79.
[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1.
[6]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333.
[7] 王永祥.董仲舒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9.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1.
[9] 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7.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ng Zhongshu’s Humanistic Enlightenment Thought
XIE Kuangfei
(The Institute of Marxism,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Shandong 277100, China)
Dong Zhongshu’s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human nature is the combination of Confucius’s and Mencius’s ideas on human nature, expanding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from a comprehensive broad vision. Not only does he emphasize the transcending dimension of human nature, but also he stresses the natural dimension of human nature. It’s just because of the mixture of goodness and evilness of human nature that he pays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cultivation of one’s morality. As an essential internal part of the thought system of Dong Zhongshu, th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of Dong Zhongshu emphasize the role of social morality and he proposed that people’s nature are formed by cultivating. Meanwhile, Dong Zhongshu carried on a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Mencius' theory of original goodness of nature,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the human nature good by cultivating”, because the good side of human nature can not be realized naturally, but must be constantly cultivated and educated so that it can become the reality of human nature. This has important modern enlightenment and sig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more effectively.
Dong Zhongshu; theory of human nature; humanistic enlightenment thought;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4.010
谢狂飞(1977-),男,江西萍乡人,讲师,法学博士。
G642
A
1673-2065(2022)04-0052-06
2021-06-11
(责任编校:李建明 英文校对:李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