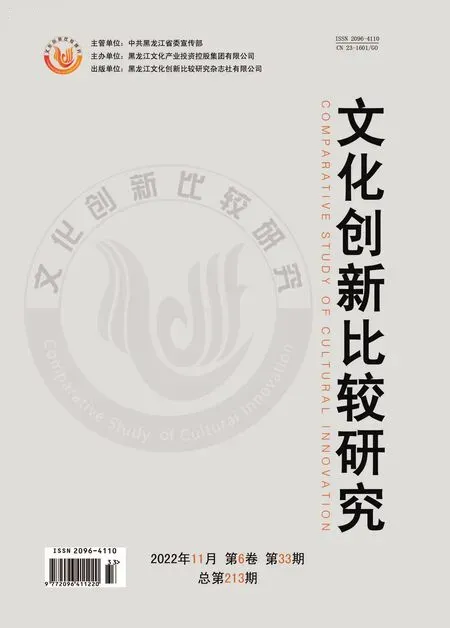古雷州府海上丝绸之路对雷州文化生成的影响
谢小羽,张楷昕,钟景媚,刘莹莹,刘刚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湛江 524003)
近年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受到重视,学界对粤西地区雷州半岛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雷州半岛涵盖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徐闻古港和南海航线的起点雷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重要地理位置,因此雷州半岛的文化生成也势必受其影响。然而学界的研究多着眼于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推广对雷州半岛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少提及海上丝绸之路与雷州文化生成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宗教文化、瓷器贸易、农业生产结构三个角度探讨古雷州府海上丝绸之路对雷州文化生成的影响。
1 古雷州府海上丝绸之路
古雷州府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唐贞观八年(634年)置雷州,下辖海康、徐闻、遂溪三县,历经南汉、宋、元、明、清而不变。清后几经改制,今为湛江市位处雷州半岛的行政辖区,在地域上涵盖雷州文化核心区,也是湛江海上丝绸之路物质文化遗存的主要分布区。
在唐中期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于陆上丝绸之路。后因战乱、经济重心迁移等原因,海上贸易道路得到开辟。“丝绸之路”的命名最早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的,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则稍晚,直到1913年才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年) 提出[1]。在此之前,这条海上贸易之路叫作“广州通海夷道”。隋唐时,海上贸易道路以运输丝绸为主,到了宋元时期则以运输陶瓷为主,因此也称 “海上陶瓷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古代从中国出发的中西交通海上航线,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东海航线,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直至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南海航线,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海上通道[2]。其中,南海航线是中外海上交流的主要通道,到达国家众多,开辟了古代最远的航线,影响深远,学界称之为“南海丝绸之路”。
古雷州府海上丝绸之路就属于南海航线。西汉时期,南越国与印度半岛之间海路已经开通。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上贸易的规模,“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兴起。有学者根据《汉书·地理志》梳理了海上丝绸之路: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3]。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古雷州府与海上丝绸之路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书·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4]由此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应在徐闻。据考证,徐闻港遗址在今湛江市徐闻县二桥村、南湾村、仕尾村前旧称三墩港的海湾,即今人所称“大汉三墩”。
南海航线全长1.4万km,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海上贸易线路,在宋元时期其贸易覆盖范围之广,成为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海上丝绸之路将我国儒家文化与传统手工艺品带向国外,在世界掀起一阵“中国热”。与此同时,海外的工农业商品、宗教文化等也通过这条线路传向国内。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古雷州地区文化的形成深受其影响。
2 雷州文化的生成过程
对于雷州文化的概念,多位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司徒尚纪将雷州文化定义为“泛指形成、发育于雷州半岛,并辐射周边地区的一种区域文化”,认为雷州文化的概念应包括雷州半岛的地理环境、雷州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雷州文化的空间拓展过程,以及雷州文化的特质和风格[5]。赵国政将雷州文化定义为 “历史上雷州半岛居民外化于各种物质形式中的主观意识”,并从时空范围、文化主体、文化本体、文化载体四个部分对雷州文化进行分点阐述[6]。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研究雷州文化的生成过程时,重点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创造文化的人类主体;另一方面是影响人类创造文化的区域地理环境。雷州半岛上的居民作为文化主体,其生产和生活活动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构成了雷州文化的现今状态。区域文化的生成与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得天独厚的环海地理位置决定了雷州人“以海为商”,也决定了其文化势必受到海上贸易的影响;打通广阔的海路,也给外来文化进入雷州半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雷州文化中,除了海洋文化占据重要地位之外,多民族文化融合也是其文化特性之一。
雷州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从史前社会到现代社会几千年的演进,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
2.1 萌芽时期:史前—先秦
雷州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存在明显的4次断层,其中史前至先秦时期雷州文化经历了两次文化断层。
第一次断层在旧石器时代。雷州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6 000年前的遂溪鲤鱼墩人生活时期。遂溪鲤鱼墩人是由北向南迁入的移民,以海生资源为主要食物,陶器上绘有独具海洋特色的水波纹,可见雷州海洋文化的源头在此。同时,遂溪鲤鱼墩人的曲肢墓葬蕴含着史前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地区也存在同样的葬式,说明了新石器时代的雷州文化就存在着与其他地区文化融合的因素。
夏商时期是第二次历史断层,据学者推测这一时期的文化仍旧保留原始社会的部分习俗。先秦时期雷州半岛尚未有统一的行政规划管辖,属于驼越、南越、西瓯交汇之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现象初见端倪。后来楚国南平百越,也为雷州半岛带来了荆楚的建筑文化和青铜文化。
2.2 多种文化融合时期:秦汉—宋元
雷州文化以百越文化为原始基础,不断融合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汉文化、闽潮文化及海外文化,形成了多种文化融合的雷州文化核心。
秦朝统治时期,雷州文化开始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秦朝前期雷州半岛归属象郡,雷州文化与中原文化开始融合。秦朝末年南方战乱,雷州半岛属于南越国,却因远离番禺政治中心,而未真正进入中原文明状态。到了汉朝,雷州半岛正式进入中原文明化的进程,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这一时期雷州文化飞速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汉武帝在雷州半岛上设置了徐闻县,并以徐闻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始发港。同时,徐闻县占据军事要地北部湾和琼州海峡,徐闻成为雷州半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为徐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徐闻县案本汉县名……故谚云:‘欲拔贫,诣徐闻’。”[7]海上丝绸之路还为雷州半岛带来了国内其他沿海地区,甚至海外的文化,印度佛教便是通过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进入雷州半岛的。因此雷州文化中的异域色彩,可以在此时期找到源头。
隋唐时期大量中原汉人迁往雷州半岛,为雷州文化注入了中原文化。隋唐时期人口的大量南迁,有着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被动迁移是战乱影响,主动迁移是开发南疆的需要。在两位对雷州文化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冼夫人和陈文玉的推动下,汉文化和本土的俚僚文化不断相互融合。陈文玉任职期间,为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百姓尊陈文玉为“雷祖”,每年举办3次敬雷活动,祭拜雷祖活动是半岛共同信仰和风俗形成的起点。当然,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冲突,隋唐时期存在着上文提到的雷州半岛的第三次文化断层,表现为崇狗信仰和食狗行为的文化冲突,实际上这是俚僚文化与汉族主体文化之间文化冲突的外露
宋代文人苏轼、苏辙等人曾被贬至雷州半岛,或被贬时途径雷州半岛,他们带来了中原的精英文化,对中原文化的传播、雷州半岛地区的民风开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雷州百姓为纪念这些为雷州半岛做出巨大贡献的官员修建了“十贤祠”,供奉着寇准、苏轼、苏辙、秦观、李纲、赵鼎、李邕、王岩叟、胡铨、任伯雨10人。北宋灭亡后,宋王室南迁,大量闽人迁入雷州半岛;其中莆田人由海上路线迁入,并成为雷州半岛的主要人口成分。他们带来的妈祖崇拜与依海而生的雷民生活需要相契合,使得民间祭拜妈祖活动盛行,闽潮文化在此时占据重要地位。北方汉人南迁来也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半岛手工业的发展,宋元时期制瓷业极为繁盛,使得雷州窑名震四方,满载着大宋风韵的瓷器从雷州港出发远销世界各地,主要依靠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2.3 成熟时期:明清—近现代
明清时期雷州文化逐渐走向鼎盛,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文化成熟的特点。
多形态文化的定型是雷州文化成熟的标志。在语言方面,雷城话成为最标准的雷州方言,清代雷州方言正式定型;在戏曲艺术方面,从汉末雷谣演变而来的雷剧,从宗教祭祀发展为民间艺术活动的飘色,都代表着雷州歌剧的成熟;在史书编撰方面,史志编纂活动空前繁盛;在文化人物方面,以“三陈”——陈瑸、陈昌齐、陈乔森为代表的杰出人才的涌现是雷州人文成熟的重要标志。
清中叶至近代,雷州半岛经济活动迎来汉代以后的第二次高潮。随着海禁政策逐渐松动,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赤坎商埠走向繁荣,赤坎展现出近代港口都市的繁华景象,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商业文化出现。近代中国国门被迫打开,雷州半岛的广州湾成为法租界。法国殖民者的侵略一方面带来了西方现代技术和商贸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如瘟疫般蔓延的低劣文化,毒品贸易泛滥,赌博风气横行,妓馆随处可见。
新中国成立后的雷州半岛又重新迎来了发展机遇,形成了传统色彩浓厚、时代特征鲜明的现代雷州文化。
3 海上丝绸之路对雷州文化生成的影响
通过梳理雷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情况,可见雷州半岛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博采众长,最终形成了多元的雷州文化。在文化传入的各类途径中,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8],自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至清代海禁中断,到现代重提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地位,这条交通要道一直扮演着文化交流枢纽的角色,从中足见其对雷州文化的生成有重要影响。
3.1 宗教文化的输入与融合
雷州文化的多元性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为本土民间崇拜与外来宗教相互融合。雷州半岛原著居民长期以来信奉原始图腾,将狗视为守护神,形成了以石狗像为图腾崇拜的形式;除了石狗崇拜之外本土居民还崇尚雷神,形成了独特的雷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外来的佛教、妈祖崇拜也开始融入本土居民的宗教信仰中。
3.1.1 佛教的传入与影响
多位学者提出佛教是从古印度分海陆两种方式传入中国的,并且南海海上传播途径远早于西域陆上传播途径。吴廷璆、郑彭年通过分析《汉书·地理志》的有关记载,提出:佛教由中印航线传入交州,而中印航线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通,始发地正是雷州半岛,由此可以推断出,雷州半岛是中国受到佛教影响最早的地域之一。
佛教文化不断影响着雷州人的生活,典型表现为殡葬文化的变化发展,将当地殡葬方式逐渐由土葬改化为火葬。艺术方面,形成了雷州佛乐中心、雷州佛像雕塑艺术中心,且在岭南地区占据较高地位。同时,雷州窑瓷器中也含有佛教元素,制瓷艺术审美受到佛教的影响。在有型文化遗产方面,雷州半岛留下了大量佛教圣地,如雷州市天宁样寺、高山寺、万寿應、宝林梯寺、天竺庵,徐闻县华捍寺、三元堂,遂溪县护国寺、龙华庵,昊川县古兴龙寺,湛江市城区楞严寺、福寿山玉佛寺、清凉寺、白良寺等。唐代时佛教被尊为国教,雷州半岛也因此成为岭南最大的佛教文化中心。
3.1.2 妈祖崇拜的传入与影响
妈祖崇拜产生于宋代。妈祖姓林名默,原生于福建,相传是能够呼风唤雨、预知福祸的神女,闽人在其死后尊其为海神,修建寺庙祈福,以求海上活动能得到庇佑。随着闽人海上航行经商及宋代之后大量闽潮人迁入雷州半岛,妈祖崇拜传播至此,成为雷州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妈祖崇拜能够在雷州半岛扎下根基,有以下4个原因:第一,唐末五代便开始有大量移民由北往南迁,宋朝时闽潮移民数量庞大,信仰妈祖人数占比高;第二,雷州半岛三面环海,海洋地理因素对民众生活影响大,渔业是重要的经济来源,航海活动不可避免,妈祖崇拜寄托了人们对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第三,由于雷州半岛地区常年受到台风侵袭,雷州半岛居民临海生活危险因素较多,因此妈祖作为海上守护神形象能够成为人们应对自然灾害的精神支撑;第四,粤西地区长期盛行巫术,为妈祖俗信融入雷州文化奠定了社会基础。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其他原因,如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妈祖信仰灵应、少数民族外迁[9]等。
妈祖崇拜的根源在于雷州人认同妈祖文化中保守的、敬畏海洋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妈祖作为沿海地区的守护神,她是救民于危难的神女,而非是搏击大海的英雄形象。因此,在妈祖的庇佑下,雷州人对于海洋探索的态度并非勇于开拓,而是趋于保守甚至回避,这种态度外化为雷州半岛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保守型文化。
雷州人对妈祖的祭祀活动遍布雷州半岛,到了明清时期雷州半岛妈祖庙多达30座,其中雷州11座、徐闻7座、遂溪12座[10],可见妈祖崇拜对雷州半岛民俗文化的影响之大。
3.2 雷州窑的繁荣与海上丝绸之路
雷州窑同样是雷州文化中灿烂的一部分,它和广州窑、潮州窑并称为广东三大窑系,是国内多地造窑技术结合而成的产物。其艺术形态显示出文化融合的特征,既饱含雷州风情,又具备异地特色。
雷州窑产生于唐代,上文提到汉人的迁移为雷州注入了中原文化,与此同时中原的制瓷技术也被带到了雷州半岛,褐彩瓷技术被广泛运用到雷州瓷器的制作中。宋元时期的雷州窑“窑口密布,规模较大,主要生产青釉下赭褐彩绘罐、枕、棺等”。其繁荣主要表现为:第一,窑口数量多、分布密集,形成了多处集中的窑址群。宋元时期雷州半岛窑址,集中分布在雷州半岛中部,南渡河中上游的两岸及东西两侧滨海地区,截至2002年仍存有窑址群150余处。第二,制作技术精湛。雷州窑主要生产青釉瓷,汲取了褐彩瓷制作技术,线条流畅,花纹繁缛,有着鲜明的南方制瓷特色。
雷州窑的兴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极为密切。海上丝绸之路也称为“陶瓷之路”,海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刺激了雷州窑的发展。雷州窑生产的瓷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要货品,远销海外,“在广东沿海丝绸之路航线、海南岛沿海、西沙群岛、东南亚诸国,甚至埃及均有出土”。雷州瓷的出口,对航海线路沿线地区的制瓷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考古发现越南与泰国部分窑址生产的瓷器与雷州瓷有着相似的外观特征,应是沿用了雷州窑的制瓷工艺。
雷州窑凭借着融合多地制瓷技术工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经贸地位和便利的通商环境,在宋元25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繁荣的景象。直到明清时期因为“海禁”政策及其他窑址的兴起,雷州窑才走向衰落。
总而言之,海上丝绸之路对雷州窑的繁荣起到了直接促发的作用,雷州窑的繁荣也推动了海上贸易的深入发展。在雷州窑文化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是其生成的重要因素。
3.3 农业文化的更新
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不局限于陶瓷、丝绸和香料的商贸往来,还引入了大量的农业作物,改变了雷州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深远地影响着雷州以至于全国的饮食文化。其中最为典型的外来作物就是番薯和花生。
3.3.1 番薯
番薯的传入与雷州半岛有着不解之缘,最早是吴川人林怀兰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入雷州半岛的。据清道光《电白县志》卷二十记载:
“霞洞乡有番薯林公庙,副榜崔腾云率乡人建立。相传,番薯出交趾,国人严禁,以种入中国者罪死。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关将有效,因荐医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食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关将曰:今日之事,我食君禄,纵之不忠,然感先生德,背之不义。遂赴水死。林乃归,种遍于粤。今庙祀之,旁以关将配。其真伪固不可辨。”[11]
吴川人林怀兰在明代万历年间,为安南国国王之女医治疾病,安南国将原本禁止出口的番薯赏赐给了他。林怀兰从海路将番薯带回吴川,此后番薯进入了雷州半岛的农业文化,慢慢遍布全粤。对于最初番薯传入的记录,吴建新在其《明清时期主要外来作物的再探》中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他指出在康熙年间的县志府志中多有番薯的记载:雷州府的电白县、石城县、徐闻县,琼州府的乐会县、琼山县、文昌县的县志上都对番薯有所提及[12]。可见雷州半岛和琼州岛区域在清代已有大规模番薯种植的情况存在。
番薯的传入不仅对农业文化产生了影响,还对饮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变了雷州人长期以稻米谷物为主粮的饮食习惯,扩大了人们对主粮的选择范围。因其高产且对环境适应性强,能够在全国大规模种植,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问题。
3.3.2 花生
如果说关于番薯的传入带有部分传奇色彩,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相对来说是间接的,那么花生的传入与海上丝绸之路就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花生的栽植和食用习惯被广泛记载于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及之后的各类方志和笔记中。
花生的传入方式和传入地在清乾隆年间檀萃的《滇海虞衡志》中已有记载,“粤估从海上诸国得其种归种之”“大牛车运之海上船,而货于中国”[13],证实了花生最早经粤西传入中国。对于花生的种植和加工,人们也已经有了深入的认识。例如《广东新语》卷二十七“落花生”条有关于小粒花生种的生态、性状的记载:“落花生草本蔓生种者,以沙压横枝,则蔓上开花,花吐成丝……以清微有参气亦名落花参。”且清代花生的种植在雷州半岛已十分普遍,雷州半岛也成为花生的主要产区,在清乾隆年间张渠的《粤东闻见录》文中记载了雷州、高州盛产花生。花生喜湿热,雷州半岛的气候正适合大面积种植。且花生能够改善土壤质量,通过与其他作物轮流种植,可提高复种指数。
花生富含蛋白质且食用方法多样,或生吃,或入菜,或制糕点,或制酱料。《滇海虞衡志》记载:“市上也朝夜有供应,或用纸包加上红笺送礼,或配搭果菜登上宴席,寻常下酒也用花生。”[14]雷州地区的传统小吃中,叶搭饼便是使用花生碾碎入馅,猪肠饼在上桌前要撒上一把花生粉才算地道的雷州风味。
除此之外,人们还学会用其来榨油、做肥料,逐渐成为我国日常主要的油料作物。范端昂 《粤中见闻》卷二十五提道“黄白豆、落花生皆可榨油充用”[15];张渠《粤东闻见录》中还提到花生油已作为食用,但“落花生油亦多,而力殊不及”[16],意指花生油产量虽多,但仍不及猪油。花生榨油之后所剩的渣滓还被人们用于作肥料,不仅肥效高,而且易获取。
由此可见,花生从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传入后,丰富了雷州人民的饮食结构,改变了经济作物占比情况,人们对花生的种植与研究也从未间断。除了农业文化之外,花生更是被赋予了吉祥、长寿、默默奉献的精神意义。从古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花生的谚语与谜语,都体现其已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花生土内长,秧苗节上生”“小胖子,穿麻衣,红衫白肚躲壳里”[17]。
4 结语
综上所述,雷州文化的生成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开辟以来到清末海禁为止,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雷州半岛作为粤西地区乃至于整个岭南地区对外交流的窗口,华夏文明通过这里向外传播,海外文化通过这里引进大陆,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这里交融。这条航线不断通过商品贸易等物质形式,改变雷州人的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生产生活和风俗人情,使这里原本的俚獠风气不断文明化,如此才诞生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展现出多样性、海洋性的雷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