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扎染图像的叙事解读
展嘉禧,杨 蕾
(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1 白族扎染图像的叙事情境
扎染又称“绞缬”,是我国传统的染缬方法之一。早在秦汉时期,扎染技艺就已经被国人掌握,并被广泛运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扎染工艺逐渐走向精致,人们会根据自然界动植物的形象制成花纹图案,如鱼子缬、鹿胎缬等技法。隋唐时期是经济文化发展繁荣时期,同时是染织手工业的全盛时期,扎染制品也随着植物染料的丰富和染色技术的提高而发展。根据《新唐书·舆服记》记载,当时民间最流行的服饰便是“穿青碧缬”,引得妇女争相模仿[1]。至宋元时期,统治者限制扎染在民间流通。因此,这时期的扎染缺乏民间的创造力,在技法上的创新与发展不明显。明清时期的扎染工艺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理的洱海卫红布、喜洲布和大理布都源自当地的特色扎染工艺,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近现代,随着西方化学染料的输入、现代印染技术的发明,传统扎染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逼仄。
云南大理是我国传统扎染工艺保存较好的地区之一,被誉为“民族扎染之乡”。白族女孩自幼跟随母亲学习扎染技艺,代代相传,技艺纯熟,展现了白族姑娘的聪慧与勤劳。白族扎染艺术渗透到白族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白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折射出文化与思想的变迁,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白族扎染属于民间传统工艺,是源于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白族扎染图像题材大多来自大自然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按照题材特征大致可分为动物类、植物类、自然景观类和综合类等。画面常以动物图像与植物图像和几何图像组合的方式呈现,以对称式和填充式构图为主,造型多变,整体画面充实[2]。白族扎染图像的表现手法不追求逼真的写实效果,而是根据真实形象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或以吉祥的手法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白族扎染强调缝扎结合的制作方法,使用传统的靛泥染料,塑造蓝底白花的民俗图像。白族扎染图像形色变化自然,透出一种朦胧与柔和之美,带有浓郁的民族风味。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研究者大多是从白族扎染手工艺的领域出发,研究白族扎染传承与发展的途径和思路。如邱春林[3]强调,白族扎染作为传统手工技艺,形成生产力并守住“核心技艺”,是保护它们的人文价值的最好方式;董秀团[4]倡议将大理周城建设成白族扎染工艺村,从传统扎染工艺出发,以此带动餐饮、旅游、销售等行业的发展,向外界展示扎染工艺的文化内涵;李尚书等[5]认为,白族扎染技艺作为传统的手工技艺,在图案、工艺、色彩上的推陈出新,是推动白族扎染技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刘守华[6]在与云南省大理市白族扎染传承人张仕绅的访谈中,提及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是白族扎染技艺传承的重要出路;金少萍[7]指出,白族扎染作为重要的旅游产品,其技艺的保护与开发必须实行精品化战略。
综上发现,前期的研究缺少从图像的角度分析白族扎染的叙事体系。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白族扎染图像的叙事情境出发,整理白族扎染图像的符号类型,解读白族扎染的隐喻传达,探究白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与叙事创新,以期对白族扎染艺术图像分析提供新思路。
2 白族扎染图像的符号及隐喻
白族扎染图像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承载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白族人民也通过图像隐喻的手法,展现中国传统扎染手工艺的博大精深和文化内涵。
2.1 白族扎染图像的符号类型与呈现
赵毅衡在《符号学》中提出,“每一件‘物-符号’在具体场合的功能变换,是使用性与各种符号意义的比例分配变化造成的。物(自然事物、人造使用物)可能带上意义而变成符号,而一旦变成符号,使用性与意义性共存于一事物之中……在人化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意义可变的‘物-符号’”[8]。白族经过数次迁徙,物质文化难以保存,图像符号成为白族最直接的文化载体,记录了人们生活,也记载了当地历史。根据当地民风民俗,白族扎染图像符号大致可分为花草植物类、鱼虫鸟禽类、自然景物类和图形字体类。
花草植物类是白族扎染中使用最多的图像符号,如莲花、山茶花、菊花、桃花等[9]。白族人民以打猎为生。鱼虫鸟禽类成为最常见的符号,其中包括金鱼、蝴蝶、蜜蜂、螺、喜鹊、燕子、凤凰、虎、蛇、蝙蝠、金鸡等图像符号。白族信奉大自然的本主崇拜,每个村庄都有各自的本主庙,如太阳神、苍山神等。日月、星辰、山水、大理三塔等自然景观类符号是白族扎染图像中必不可少的元素。除此之外,白族扎染图像也会选择一些图形字体类的符号,加深对本主文化的崇拜,如正方形、三角形、椭圆形、铜钱形、汉字等。动植物类符号常与花草植物类、自然景观类和图形字体类符号结合使用,可以丰富画面的整体效果,更具视觉冲击力。
白族人民独具匠心,使白族扎染图像更具辨识度与民族特色。白族扎染图像符号的布局结构一般分为单独图像式、中心对称式、中轴对称式、多方连续式。单独图像式见图1(图片来自白族扎染非遗传承人段银开作品《翱翔图》,145 cm×110 cm),是将图像符号以不完全规律的排列方式呈现。多方连续式见图2(图片来自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官网),是由一个至多个图像符号整合为单独图像,然后对其进行规律的扩展排列,视觉上较为单一[10]。中心对称式见图3(图片来自金少萍《白族扎染——从传统到现代》),图像符号按照某一点在进行180°旋转后还能与原图像重合,这种形式相比单独图像式更具有均衡感,手法简单快捷,运用也最为广泛。中轴对称式见图4(图片来自金少萍《白族扎染——从传统到现代》),图像沿着中轴两旁的符号部分进行规律地重合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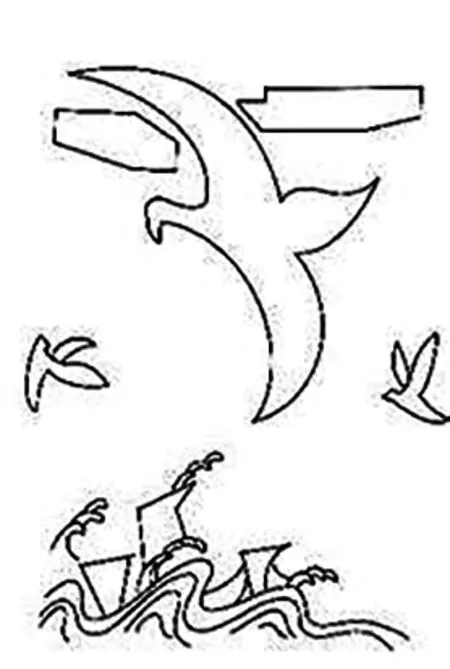
图1 单独图像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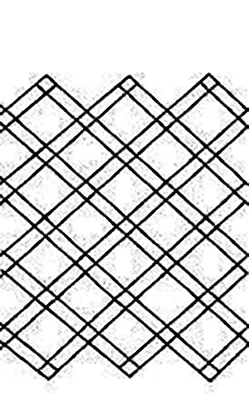
图2 多方连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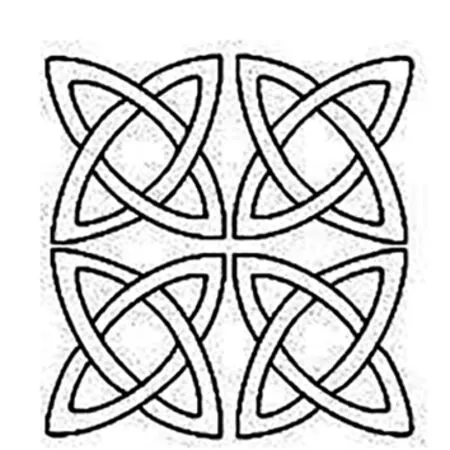
图3 中心对称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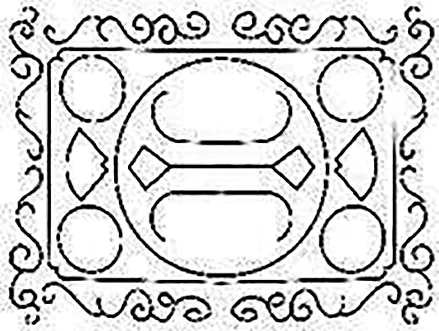
图4 中轴对称式
2.2 白族扎染图像的隐喻传达
2.2.1 祈盼美好生活的映照
数次的大规模迁徙使白族人民生活颠沛流离。因此,白族人民十分崇拜大自然,秉承着万物有灵的思想,渴望通过对万物神圣恭敬的态度换取大自然的庇佑。例如,白族扎染图像中的日月、水火、山川等符号,代表白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白族人民会举办“太阳诞”的祭祀活动,由当地老人制作表和诰,以诚心祈求太阳神能够庇护村庄;白族人民认为水中有神仙存在,每逢除夕和大年初一,他们都要到井水周围烧香磕头;白族人民敬畏苍山,多数村庄都盖有山神庙,当地人民会在农历三月十六这天,带着各种贡品去庙中祭祀山神,请求山神保佑人们出行顺利、捕获更多猎物。
“在白族地区关于龙的传说,对龙的崇拜观念极为广泛强烈,其共同点是凡有水必有龙。”[11]白族人民对龙的崇拜也十分普遍,会在龙王庙前献祭求雨,祈求龙王庇佑,并进行“绕三灵”的祭祀活动,其中舞耍的布龙就是由扎染制作而成[9]。梅、兰、竹、菊图像代表高洁的品性;石榴、豌豆、葫芦等图像通常蕴含着人丁兴旺的寓意(图5,图片来自刘丽娟《大理白族扎染图像研究》);鲤鱼与“余”谐音,代表生活富足有余(图6,图片来自白族扎染非遗传承人段银开作品)。这些扎染图像是白族人民渴望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也是其崇拜自然和富有生活情趣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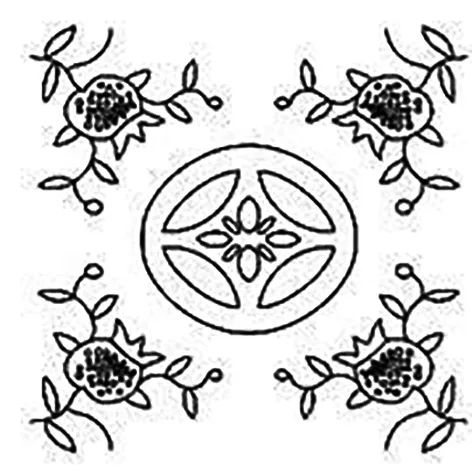
图5 石榴扎染图


图6 年年有余图
2.2.2 民俗信仰的图像转化
扎染作为白族当地的传统工艺,深深扎根于民间,与白族的民风民俗密不可分。本主崇拜是白族独有的民俗信仰,也是白族扎染图像的创作源泉。在本主崇拜中,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平民英雄等都可作为本主崇拜的来源,信仰体系较为丰富。当白族先民无法理解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时,便认为万物有灵,自然拥有神灵般的力量,可以呼风唤雨。因此,他们用祭祀来祈求本主这座保护神消灾降福,保佑人们顺风顺水[11]。
本主崇拜中的蝴蝶图腾是白族人民最常用的图腾之一。当地关于蝴蝶的传说众多,相传白族周城村附近有条巨蟒把一位姑娘掠走,猎人杜朝选将其救出并大胆求爱,但姑娘含羞跑开,不慎落入泉水之中,猎人急忙跳入水中抢救,最终他们一起化蝶飞走[12]。当地人们为纪念他们,特意修建庙宇,并将泉水命名为“蝴蝶泉”,每年4月定为蝴蝶会,届时周城村附近的青年男女都会聚集到蝴蝶泉,进行烧香、念经以及对歌等民俗活动。当青年男女恋爱后,也会把带有蝴蝶、双燕等图像的扎染方巾作为礼物赠予对方。
白族先民把公鸡作为民族图腾的历史十分悠久,如白族三月街的民族节就将一只昂首的公鸡作为节徽。公鸡图像在白族的传统民俗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地的求亲习俗中,男方带着媒人和烟酒在月圆之夜登女方家门,女方则需要以公鸡作为夜宵款待对方;求亲成功后,在订亲仪式当天,男方还要送来一只挂彩的公鸡和一坛烈酒,白族称之为“订鸡酒”;结婚时,男方再次送来一只挂彩的公鸡,以示夫妻恩爱白头、永结同心[13]。白族姑娘出嫁时也会把扎染公鸡、蝴蝶、喜鹊等图像的床单、被单、枕巾作为陪嫁用品(图7,图片来自金少萍《白族扎染——从传统到现代》),寓意永结姻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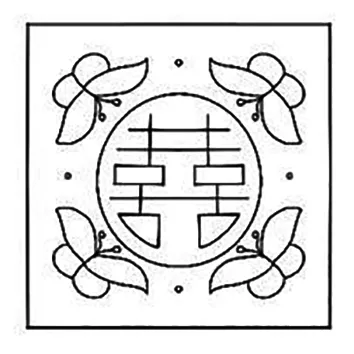
图7 蝴蝶扎染图像
在白族的传统习俗里,蝴蝶图像不仅是美丽的化身,也被视为爱情与自由的象征;公鸡图像则寄予着夫妻和睦的希望与憧憬,呼应了白族本主崇拜的文化特色。
在云南白族周城村的生育习俗里,当孩子出生十天后,孩子的爷爷会大办宴席,外婆则会准备一些婴儿用品以及鸡蛋、米等礼物,俗称“送祝米”,其中一个重要礼品是孩子用的顶头布。顶头布一般为八卦太极图像的扎染方巾,寄托着长辈对孩子身体健康、万事顺遂的祝福[9](图8,图片来自金少萍《白族扎染——从传统到现代》)。由此可见,扎染图像承载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无限遐想,逐渐演变、转化成白族民俗信仰的一部分。


图8 八卦太极扎染图像
2.2.3 对生命力的执着追求
除了对民俗信仰的崇拜,白族人民对生命力的崇拜在扎染图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白族人民居住在洱海附近,捕鱼是白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日常饮食以及祭祀场合中常有鱼的出现。学者李霖灿对南诏大理国的资料整理显示,鱼被白族人民视为“河神”,是神圣之物。白族人民对鱼的形象充满遐想,一是因为双鱼的外形与女性生殖器官的轮廓相似[14](图9,图片来自刘丽娟《大理白族扎染图像研究》);二是鱼具有强大的繁殖能力,这满足了白族人民对延续生命力的向往。因此,在白族扎染文化中,鱼图像常与莲花或双鱼形式组合,通常意味着多子多福、连年有余,代表着白族人民崇尚生命的延续,是生命力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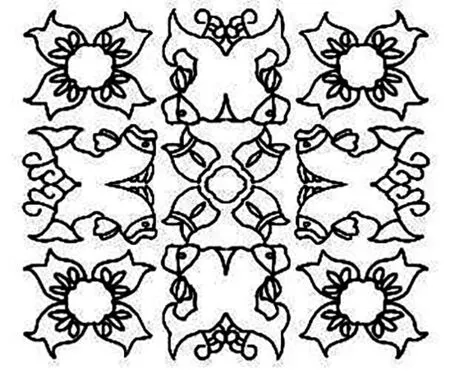
图9 双鱼扎染图像
其次,白族扎染图像中的葫芦图像也具有浓厚的生殖文化意蕴,体现着强大的生命力(图10,图片来自蒋才坤《扎染艺术》)。葫芦的形体上下饱满,与母亲十月怀胎的体型相似。葫芦中的籽,意味着腹中的胎儿,被视为生育繁衍的象征。在白族的民族节日“绕三灵”中,队伍的开头有两名中年男女手持柳枝引路,在柳枝上会悬挂葫芦,并把扎染布系在葫芦上,柳枝象征着本主崇拜和村社,葫芦则寓意着繁衍和丰收[9]。葫芦扎染图像寄寓着家族人丁兴旺的美好祝愿,是白族人民对生命力的执着追求的形象化体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图像延续着白族人民对生命力的情感表达和精神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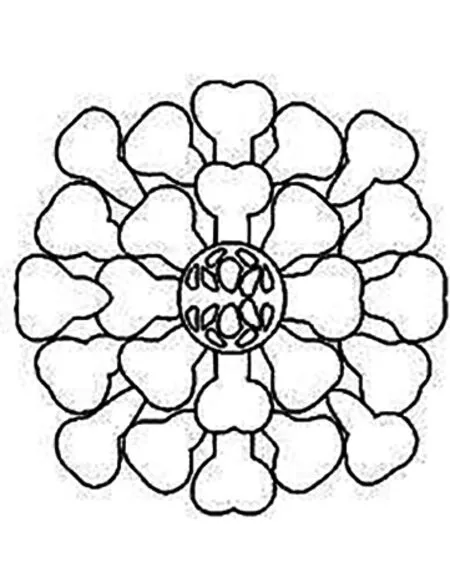
图10 葫芦扎染图像
3 白族扎染图像的叙事创新
3.1 白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转化
白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根据元初郭松年[15]在《大理行记》中的记载:“故大理之民,数百年间……使传往来,通于中国(中原)。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云(言)为(行),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唐、宋)之遗风焉。”此外,大理历代的统治阶层都十分推崇并主动吸收汉族文化,如马曜曾在《大理文化论》中提出,大理派遣数千人到成都学习汉文化,购买中原经典书籍;大理国第十八代国王段智兴曾要求白族画工张胜温绘制《张胜温画卷》[16],画卷中的线描画法、中原图像和小楷愿词等均可反映出汉族文化在白族文化中的体现。总之,白族文化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
在白族扎染创作中,其图像融入了具有特定象征寓意的汉族传统图像。白族扎染中的龙、凤图像明显受到了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汉族文化中,龙代表至高无上的存在,寓意着权威、吉祥;凤则是美丽和平的象征[17]。在白族的“绕三灵”节庆日中,当地人民常用蓝、白两色在扎染布上绘制龙的图像,而凤通常与蝴蝶、喜鹊等图像相结合,出现在白族女子的陪嫁品上。同时,龙和凤的结合图像在白族文化中蕴藏着“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的主题寓意,代表着白族人民追求吉祥的美好愿望。
莲作为汉族文化中的常用图像,蕴藏着高洁、祥瑞与美好之意。白族扎染中莲的运用也较为广泛,它常与鱼、鹭鸶等民俗形象结合,被赋予丰富多彩的吉祥涵义[18-19]。莲与鱼形结合,被喻为“连年有余”。《鱼戏莲图》由四条鱼围绕着中心的莲花组合而成,栩栩如生(图11,图片来自张义妮《云南白族扎染艺术研究》)。莲与鹭鸶组合,象征“一路连登”[20](图12,图片来自刘丽娟《大理白族扎染图案研究》)。综上可见,白族扎染创作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的艺术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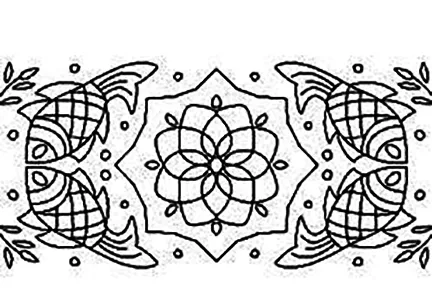
图11 鱼戏莲扎染图像


图12 莲与鹭鸶扎染图像
鹤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常与神仙联系在一起,又称为“仙鹤”,是长寿的象征。鹤图像也被白族人民应用在扎染创作中,通常用于家中最为年长、威望最高的男性老人[21]。鹤扎染图像见图13(图片来自宋博文《大理白族扎染纹样的研究与应用》),鹤以水平对称的结构分布,姿态优美,中心为旋转对称的祥云图像,四周点缀着花卉以及松针等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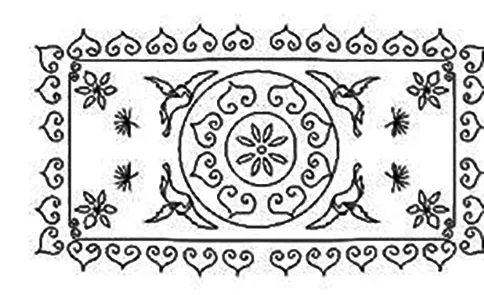
图13 鹤扎染图像
综上所述,白族扎染艺术与汉族吉祥长寿的文化追求相联结,融入白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白族扎染图像种类繁多,寓意丰富,寄托着白族人民对亲人的祝福、对婚姻美满的祈愿、对子孙代代繁衍的渴望。同时,这也是白族在继承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文化精华的成果。
3.2 白族扎染图像的时代更新
在白族扎染的传承中,不但出现了传承人老龄化的状况,而且面临着图像与当下社会环境和大众审美以及当前的时代潮流难以结合的局面,导致发展速度较为缓慢[22]。因此,白族扎染图像需在传承民间工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适应市场变化,进一步为白族扎染的传承保护提供更多的可能。目前,白族扎染图像的时代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图像内容的创新。白族人民基于本民族特色,结合大众审美情趣,进行图像内容的创新。白族扎染通过外贸渠道开拓了海外市场,将扎染制品远销到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白族扎染图像开始融入日本京都塔、富士山等海外符号。
第二,染制材料的突破。白族扎染创作材料除了保留板蓝根、栀子、姜黄、桑葚、藏红花、苏木等传统染料外[23],还进行了多种样式的延伸。比如白族地区“蓝续”扎染文化发展中心的创始者张翰敏,带领团队开发出艾草染、咖啡渣染、茶叶染等30多种染色技术[24]。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探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这项古老技艺注入新鲜血液。
第三,应用媒介的拓展。白族扎染图像一般运用在服饰、家纺等生活用品中(图14,图片来自汪鑫《大理白族扎染纹饰在现代家居配饰品中的应用研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开始更注重精神文化需求,追求个性化发展。设计师结合现代消费者的消费喜好,将扎染图像应用在鼠标垫、手机壳、艺术画等新媒介中。如图15所示的扎染艺术画(图片来自白永芳《大理白族扎染技艺拓展应用研究》),白族地区“青白扎染坊”手艺人陈意辉将绘画与白族扎染设计相融合[25],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

图14 扎染家纺产品

图15 扎染艺术画
4 结语
作为民族文化的非物质载体,白族扎染图像是白族人民生活劳作成果的记录,反映了白族地区的民风民俗,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其中,花草植物、鱼虫鸟禽、自然景观以及图形字体等经典图像符号,是对当地人们日常生活和信仰崇拜的真实反照。此外,白族扎染图像的变迁和白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转化有着直接的关联,映射出当地白族人民群众的审美意识。因此,白族扎染图像叙事是白族文化经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具有自生性和开放性的符号体系,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