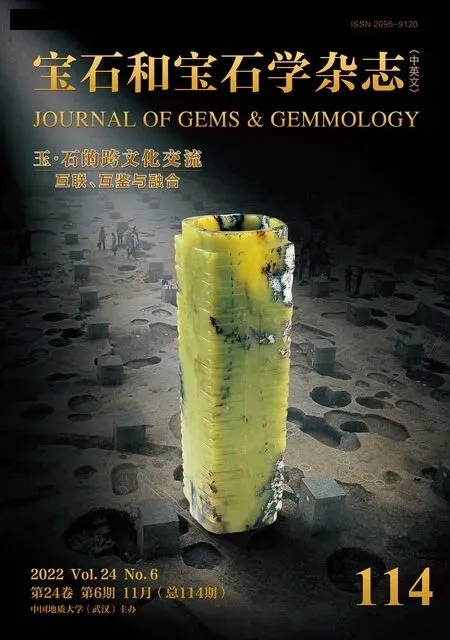史前至汉代广西宝玉石器物的考古发现及其对区域文化互动的指示
何 静,孙 媛,丘志力,3,李 珍
(1.桂林理工大学广西隐伏金属矿产勘查重点实验室,广西 桂林 541006;2.桂林理工大学珠宝学院/珠宝检测中心,广西 桂林 541004;3.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 珠海 519080;4.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1)
宝玉石文物是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物质创造,承载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特别是对研究文明演化与文化互动方面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广西史前至汉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宝玉石文物占据很大份额。前人[1-8]对于广西史前至汉时期的文明演化及文化互动多从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等的角度出发,而从宝玉石文物的角度去探讨广西地区文明演化与文化互动则较薄弱,因此从宝玉石文物出发是一个较新的切入点。且在前人的研究中,对器物本身研究较多,着重对墓葬形制,对出土文物的器型、组合方式、纹饰、制作方法等进行研究和对比,取得了大量成果。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对珠饰进行研究[9-16],重点是对于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部分宝玉石文物的科学分析,确定其材质,研究其工艺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溯源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进而为文化互动交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对于单独的宝玉石文物的研究分析则局限于某个区域、某个时代或某个品种,缺乏全区域、全时代、多品种的综合研究,从宝玉石方向去探讨文化互动的论述集中于汉代,着重强调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与器物,旨在论证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其它历史时期几乎没有。因此,本文将梳理史前至汉代广西出土的宝玉石文物,对其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探讨广西文明演化的历程及广西与周边其它地区交流互动的情况。
1 史前文明的曙光
石器时代,包括旧、新石器时代,始于距今约250万年,止于距今约4000年,广西暂未有统一的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根据《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17]中的分期,结合广西考古发掘简报和报告进行归纳,广西新石器时代末期约距今3000-2000年,由此可知广西石器时代结束时间稍晚。据考古发现,今广西地区早在80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百色旧石器遗址是广西已发现距今年代最早的遗址[18],出土的百色手斧距今80.3万年。约在5万年前,今广西境内古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0000-6000年前,境内古人类逐步走出岩洞与河谷,向平原和滨海地区发展,出现原始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该时期产生的宝玉石饰品,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发现的自然界中易于得到和加工的材料,如动物的骨、角、牙、蚌、贝等,木、石、陶、玉等,且使用材料有“就地取材”原则,但这种原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逐渐淡化;其造型早期以环、筒、球、线形等简单的几何图形为主,后出现较为复杂的组合图案、动物等造型。
广西地区旧石器时期考古发现集中于桂西、桂北-桂东北地区,多为洞穴遗址和露天遗址,主要的遗址有百色[18-25]、百寨、桂林宝积岩、柳州白莲洞、思多岩、来宾盖头洞、南宁小崩山、虎头岭、崇左矮洞、柳江陈家岩等[26](图1)。

图1 广西史前-汉主要遗址分布(据文献[1-8]综合整理)Fig.1 Distribution of main prehistoric-Han sites in Guangxi (Ac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s [1-8] comprehensive collation)
广西旧石器时期文明重点区域集中于桂西、桂北-桂东北地区;新石器时期在桂西、桂中、桂北-桂东北地区均有分布;到三代时期集中于桂西南、桂中及桂东北地区;秦汉时期主要沿桂东-桂东北、桂东南地区分布。秦汉以前,广西文明区域的变化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生产生活方式从采集狩猎到采集渔猎再到农耕,从洞穴到贝丘再到房屋住宅,发现的文化遗存也从洞穴遗址到贝丘遗址再到城址等。秦汉及之后,随着农耕技术的发展,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广西东南-东-东北部沿江沿海地区文化遗址遗存丰富,说明陆上文明的迁徙演变受到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影响。
通过对出土器物的墓葬形制、器型、纹饰、器物组合、制作工艺方法等进行比较,可以研究该地区与同一时期其它地区出土器物之间的联系。基于地区间旧石器文化遗存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广西与南亚、东南亚旧石器时期文化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共同性:(1)石器原料多为砾石,属砾石石器文化;(2)石器的器型基本上为大型石器,如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3)石器的制作简单且粗糙;(4)主要的器型组合是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有的学者根据这些共性,认为旧石器时代广西与越南地区存在文化交流与互动;也有学者认为是广西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文化上的趋同[27-29]。本文笔者认同前者,广西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河海相通,交通便捷,为相互间的交流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广西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旧石器时期石器文化存在的共性确实不是偶然,而是地理区域便利导致的文化交流的结果。
广西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较多,可谓是“遍地开花”,桂北地区的庙岩、甑皮岩、大岩、晓锦等;桂中地区的鲤鱼嘴;桂南地区的冲塘、何村、江边、敢造、鲤鱼坡、顶蛳山[30]、秋江、西津、灰窑田、凌屋、牛栏石、长塘、歌寿岩岩洞葬、岜旺岩洞葬[31]、弄山岩洞葬[31]等;桂西地区的百达、坎屯、革新桥、北大岭、弄石坡、北景岩洞葬1号洞等(图1)。
新石器时代早期与旧石器时期石器文化还存在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石器原料多数为砾石,属于砾石石器,多为单面打制石器,制作简单,保留粗糙的砾石面,以砍砸器为主,刮削器和尖状器次之,器型较大,与旧石器时期的石器文化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到新石器中晚期,磨制石器占主要地位,石斧、石锛等磨制石器大量出土,且制作较精,器型也较小,出现陶器,陶器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石器的数量逐渐减少甚至不见,陶器的种类、颜色、器表的装饰花纹等特征也成为研究广西与其它地区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物证。例如新石器晚期,桂东南地区的平南石脚山遗址[32]中出土白陶,器表装饰曲折纹、多线刻划纹、水波纹、压印纹等特征与广东中山龙穴[33]、深圳大黄沙等遗址出土白陶相似。白陶和彩陶是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1]。但是广西发现的白陶和彩陶数量较少,不典型,只在武鸣蜡烛山、平南石脚山、甑皮岩第五期文化中见白陶,彩陶也只在平南石脚山遗址、武鸣岜旺、弄山岩洞葬中见,由此推测白陶和彩陶是大溪文化向南传播的结果[3]。石钺是新石器时期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广西平南石脚山遗址出土1件深灰色板岩制成的石钺,器形斜肩,长方柄,刃宽,呈半月形。与长江下游地区及良渚文化出土的石钺相似,广西石钺被认为是来自于良渚文化地区的舶来品[8]。由此可见,广西地区在新石器晚期存在的对于其它地区的文化接纳、吸收与转化现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
经过对广西旧石器时期至新石器时期的考古发掘的整理发现,出现具有装饰性的宝玉石文物最早在新石器时期,这也就意味着广西先民在较早的时候就已有宝玉石装饰的意识和追求。这一时期装饰品的材质以玉石材料为主,有少量玛瑙、绿松石,出土的玉器主要分为两类,一为生产生活用具,包括锛、斧、凿等,二为装饰品,有玦、环、坠子、镯等。生产生活用具的器型较大,应是利用大件玉料切割加工而成。目前所知,广西玉矿主要在陆川、融水、博白、都安等[34],鉴于史前时期交通不便,大型玉料的搬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此推测玉质生产生活用具是就地取材,是广西本地自制的产品。
从表1可以看出史前时期广西地区玦饰出土数量较多,分布较广。而最早的玦出土于东北地区黑龙江小南山遗址,距今已有9000年[35-36]。新石器时代早期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地区、三江平原地区、第二松花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华北北部地区均有发现玦,主要材质为玉,石次之;新时期时代中期东北地区的辽西、辽东及中部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两广及海南地区出土玦,大多以玉玦为主,伴有石玦、蚌玦、水晶玦等,材质较之前更加多样,造型也更加丰富。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北地区的玦出土量减少,仍以玉玦为主;华北地区西部及南部出现少量玦,材质主要有玉、石;长江中、下游地区玦出土量减少,但仍以玦为主,出现玛瑙材质的玦,制作玦的技术水平有所提高;闽台地区该时期玦出土数量较多且造型多样,玉玦为主,石玦次之,成为玦的重点发展区域;两广及海南地区也大量出土玦,材质有石、玉、水晶、陶等,种类极其丰富[37]。邓聪等认为,玦饰的传播以中国东北为轴心向四周辐射,国内玦经历由北向南随东面沿海地域推进的一个传播过程;而华南地区,长江及珠江流域玦显示由东向西的传播情况[38]。由此推测,广西地区出土玉玦很可能是岭南以北地区的玦饰向南传播扩散的结果。

表1 广西史前出土玉器统计Table 1 Statistics of unearthed prehistoric jade artifacts in Guangxi

表1(续)
2 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指以青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兵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但岭南地区是否存在青铜时代仍有争议。广西出现最早的青铜器为铜卣,年代大致为商代,商代以后广西陆续出土青铜器,到战国中后期广西青铜器发展达到一个较为繁荣的状态[39],而学术界认为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进入青铜时代,广西地区青铜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广西发现夏、商、西周时期的遗存较少,发现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的遗存较多且分布范围较大,主要分布于桂东北的漓江、贺江流域,桂西南的左、右江流域,桂中的柳江、红水河流域,与出土玉石器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
左江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有大新歌寿岩岩洞葬、大新交岭战国墓[40]、龙州县更洒岩洞葬[41]等。右江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有田东锅盖岭土坑墓[42]、武鸣岜马山岩洞葬[43]、武鸣敢猪岩岩洞葬[44]、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群[45]、武鸣独山岩洞葬[46]、武鸣马头安等秧山战国墓葬群[47]、宾阳县战国墓葬[48]等。红水河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包括来宾白面山岩洞葬[49]、来宾古旺山岩洞葬[49]、忻城矮山岩洞葬[50]、忻城翠屏山岩洞葬、大化北景岩洞葬、宜州六桥岩洞葬、宜州鹞鹰山岩洞葬[49]等。柳江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包括象州下那曹村战国墓[51]、柳江县战国青铜器窖藏[52]等。漓江-桂江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包括贺州龙中岩洞葬[53]、灵川富足村岩洞葬、灵川水头村岩洞葬、灵川马山古墓群[54]、贺州高屋背岭古墓群[55]、贺州马东村周代墓葬[56]、广西恭城秧家墓[57]、平乐银岭山墓葬群[58]、贺县青铜器窖藏等。浔江流域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则有岑溪花果山墓葬群[59]等(图1)。
这一时期广西出土的宝玉石文物数量明显增多,主要以玉石为主,生产生活用具减少,更多为装饰品,除玦、环、坠子、镯之外,还出现了玉璜、镂空雕饰等,品类增加,工艺技术更精细,但玉器的具体原料仍不明确,如表2所示。结合上文分析得出,广西青铜时期流行玉玦随葬极有可能是受到北方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广西地区的玦造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花边形玉玦,杨建芳[60]将这种花边形玉玦称之为“越式玉玦”,并将其分为三大类,环形玉玦、方形玉玦、具凸饰之玉玦,又将具凸饰之玉玦细分为“C”字形、“山”字形、点状三小类(图2)。此类玉玦在广东、江苏、福建、越南、云南等地区也有出土[4],是古时百越地区特殊的一种玦饰品。杨建芳[60]从云南出土玉玦的造型、数量及时代多个方面与广西出土的玉玦进行比较分析,认为越南、云南地区出现此类产品应是从广西传入,进而也证实了该时期广西与云南及越南地区存在交往。

表2 夏商周时期广西出土器玉器物统计Table 2 Statistics of unearthed jade artifacts in Guangxi during the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表2(续)

图2 玉玦分类图[60]:(a)环形玉玦;(b)方形玉玦;(c)凸饰-“山”字形玉玦;(d)凸饰-“C”字形玉玦;(e)凸饰-点状玉玦Fig.2 Jade ring classification diagram:(a)penannular jade Jue;(b)squareness jade Jue;(c)hump-W shape jade Jue;(d)hump-C shape jade Jue;(e)hump-pitting shape jade Jue
广西地区也出土了玉璧,如表2所示,我国较多地区都有出土璧,璧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内蒙古西部及河套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均有发现,其中东北、华中、长江下游地区最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大部分地区有璧的出土,长江下游地区盛行璧,成为璧的重点发展区域,其种类和数量多,佩戴多样。湖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区也有类似的玉璧出土。李艳红[61]通过整理各地出土璧的文献资料,从时间、造型、器形体积等多个方面比较分析,认为东北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两个地区的璧为独立发展的;而长江下游地区与周边很多地区的璧有较多相似性,根据其所属时间及特征对比分析认为玉璧由长江下游地区地区向南传播,经福建、广东地区再向西传播影响到广西、云南甚至越南地区,进而说明广西与岭南其它地区之间存在交流与互动。
3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公元221年魏国建国结束的这一段时期。包括秦、西汉、东汉三个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广西历经多次统一与割据,广西境内族群增多,百越族、华夏族、东夷族等多个民族交错相居,不同族群的文化也相互影响。《汉书·地理志》[62]中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四月,有邑卢没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返还矣”。该段史料较为详细的记载了汉时,船只从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出发,历经都元国、邑卢没国、已程不国等多个国家(图3),进行贸易的情形,被学术界认定是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标志[63]。这显示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广西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往来更加密切。

图3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示意图(据文献[62-65]绘制)Fig.3 Maritime Silk Road route diagram during Han Dynasty(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s [62-65] drawing)
由于广西至今鲜有秦代墓葬的发掘,单独的秦代出土的珠宝玉石器物几乎空白。但广西汉墓葬发掘的数量已超过2 000座,主要集中分布于桂东北至桂东南一线,尤以合浦、贵港、梧州、贺州、桂林等郡县治所及重要水陆交通要道沿线最为密集,以墓葬群的形式呈现,另外在桂西地区的西林、崇左、都安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图1),但鉴于部分材料的年代测定并无精确的数据,无法完全确认是否有可能存在更早时段的器物,本文泛归为秦汉时期遗物进行讨论。
对秦汉时期考古发掘简报进行整理(表3),广西地区宝玉石文物除玉石外,还有大量的玻璃、水晶、石榴石、绿柱石等器物出土。与其他宝石材料相比,秦汉时期广西出土玉器相对较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初年墓中发现的一件高足玉杯,玉杯呈圆筒形,器壁厚薄均匀,平口、直腹、圜底、下连豆把形空心座足,腹部镂刻每两个乳钉为一组的谷纹,上下左右穿插排列,口沿和下腹各刻一周卷云纹,足柄素。玉杯是一种饮酒器,这种器形大约始于西汉时期。此件玉杯造型与杜陵陵区出土的玉杯相同,且纹饰与秦代云纹高足玉杯极为类似,推测其墓主人是身份较高的诸侯[66]。由此,该件玉器极有可能来自中原地区。黄启善等[9]、史美光[10]、李青会[11-15]等对合浦出土的宝玉石文物进行无损测试,并取得显著成果。根据测试结果对合浦出土的部分宝玉石文物进行了成分、制作工艺、溯源等分析,并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认为这些珠饰或来源于南亚、东南亚地区、或为借鉴技术本地制造、或直接为本土制造。

表3 广西出土秦汉时期宝玉石统计Table 3 Statistics of unearthed gems and jade in Guangxi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如图4所示,此类管形珠饰特征为两头尖缩,中间鼓起,加工工艺复杂而精细,据文献资料表明在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人们已经可以制作这样的管形珠饰[73-76],该珠饰在泰国中部华富里地区铁器时代遗址出土较多[77]。此类管形珠饰主要在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汉墓出土,但数量较少,可以认为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广西合浦地区,再向北传入湖南地区,由此印证汉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及文化交流(1)喻燕姣,段晓明,王卉,等.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宝石珠饰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2022.。

图4 缠丝玛瑙管饰:(a)合浦红岭头出土,合浦汉代博物馆藏品;(b)长沙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品;(c)泰国华富里府出土(图片引自B.Pongpanich)Fig.4 Wrapped agate tube:(a)agate unearthed from Honglingtou,Hepu.Collections of Hepu Han Dynasty Museum;(b)agate unearthed from Changsha.Collections of Hunan Museum;(c)agate unearthed from Lop Buri,Thailand
金花球(图5)在秦汉时期出土分布范围较广,且在体现区域间文化交流互动方面具有强代表性,因此本文中也将金花球划归于宝玉石珠饰一类加以讨论。金花球是用圆形小金条焊接12个小圈,以供连缀。12个小圈上下各一个,中分两层,每层5个;然后在这些小圈交汇的三角地带用高温吹凝的堆珠加以固定。堆珠有的只有一颗;有的是下面三颗上面叠垒一颗,似叠垒式的四联罐。堆珠之间以及堆珠与小圆圈之间都用焊接工艺加以连缀,整体稳定牢固[16]。在越南古海港奥埃奥、印度东海岸、印度河流域的旦叉始罗遗址,都发现这种“多面金球”装饰品。关于多面金珠或者说金花球等金珠饰品的来源和工艺等问题,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用粟粒金珠堆垒装饰的形制、工艺都不是中国所固有,这种金珠或者其制作方法极可能是由海路传入中国本土的。此外出土的玻璃[9-13,71]、肉红石髓[72,78]、水晶等珠饰在湖南、广东地区也有发现,说明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珠饰沿广西地区北上到达了湖南,甚至更北方的中原地区。

图 5 镂空金花球串:(a)湖南郴州出土;(b)广东广州出土;(c)广西合浦出土;(d)印度帕特南出土Fig.5 Hollowlike gold flower beads:(a)unearthed from Chenzhou,Hunan;(b)unearthed from Guangzhou,Guangdong;(c)unearthed from Hepu,Guangxi;(d)unearthed from Pattanam,India
如图6所示,耳珰是佩戴在耳部的装饰物,东汉刘熙《释名·释首饰》中记载:“穿耳施珠曰珰”[79]。考古发掘资料显示,目前发现最早的耳珰为新石器时代产物,辽宁沈阳新乐遗址出土“伞”形耳珰,距今约6000年历史,此外,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水晶耳珰,距今5300年,因此耳珰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风格器物。耳珰材质多样,有贵金属、玻璃、玉石、玛瑙、琥珀、水晶 、象牙等。玻璃质、琥珀质及红玉髓质耳珰在广西合浦[70]、贵港,湖南,广东的汉墓及越南北部,泰国南部[77],柬埔寨南部,印度南部[80]等的铁器时代遗址中广泛出土。从图6可以看出,东南亚及印度地区出土耳珰形制较华南地区出土的短粗,束腰较粗,而与湖南出土的部分耳珰相似,这可能是东南亚及印度地区利用当地原材料对中国传统耳珰器型进行仿制,而后又销往国内,形成双向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图6 各种材质的耳饰:(a-b)琥珀耳珰,广西合浦出土;(c)钾玻璃耳珰,广西合浦出土;(d)红玉髓耳珰,广西合浦出土;(e)红玉髓耳珰,泰国三乔山出土;(f)红玉髓耳珰,泰国孔通出土;(g)红玉髓耳珰,湖南长沙出土Fig.6 Earrings made of various materials:(a-b)amber earrings unearthed from Hepu,Guangxi;(c)potash glass earring unearthed from Hepu,Guangxi;(d)carnelian earring unearthed from Hepu,Guangxi;(e)carnelian earring unearthed from Khao Sam Kaeo,Thailand;(f)carnelian earring unearthed from southern Thailand;(g)carnelian earrings unearthed from Changsha,Hunan注:图a-f引自文后文献,图g摄于湖南博物院
综上所述,考古发现的宝玉石文物于当时而言既是贸易商品,也是交往媒介和不同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沉淀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
4 认识及结论
通过对史前至汉代广西出土宝玉石文物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及其与周边地区同时代出土宝玉石文物资料的比较研究,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广西史前至汉代出土的宝玉石文物种类丰富,其中,秦汉以前以玉石为主;秦汉伊始,出现了大量玻璃、水晶、玛瑙、绿柱石、石榴子石、贵金属等宝石类材料,品类丰富,其材料来源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属的,显示秦汉时期广西宝玉石文化空前繁荣,表明秦汉时期是广西文明进化和对外交流的重要转折时期。
(2)先秦时期广西出土宝玉石文物主要为玉石,包括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两大类,但具体玉石材料还有待进一步进行科学分析。青铜文化时期装饰品以玉玦为主,有环形玉玦、多边形玉玦、具凸饰玉玦(“C”字形、“山”字形、乳头形)。广西青铜时期文化与周边湖南地区文化、云贵高原地区、越南北部地区文化以及北方地区文化的联系便体现在玉玦之上。
(3)合浦地区是广西目前出土秦汉时期宝玉石文物最多的一个区域。本区域的宝玉石文物品类丰富、形制多样且制作工艺技术复杂精细。根据宝玉石文物在形制、工艺技术、造型纹饰及其组合特点,可以看出这些宝玉石文物既有华夏本土特色,也融合吸收了当时其它区域器物的特点,部分的宝石文物有可能直接来自异域,秦汉时期合浦地区考古发现的宝玉石文物有力指示了秦汉广西与其它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4)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加快了广西文明发展的进程,广西宝玉石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下显示出多元风格,且其对当地的发展与繁荣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厘清广西宝玉石考古发现对了解广西宝玉石文化的源流、发展等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对认识广西文明演化与文化互动具有重要意义。综上分析认为,广西地区从新石器中晚期开始就有渐进的文明发展进程,但其文明历程与周边地区有较强的内在联系,也有自身鲜明的区域特色,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重要的组成部分。
致谢:感谢湖南省博物馆喻燕姣研究馆员热情安排了我们对湖南省博物馆藏汉代宝玉石文物的上手观察,并对有关的研究进行了指导;感谢广东省博物馆吴沫副研究馆员和上海博物馆谷娴子副研究馆员对我们资料收集及成文过程给予的帮助,同时感谢评审专家的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