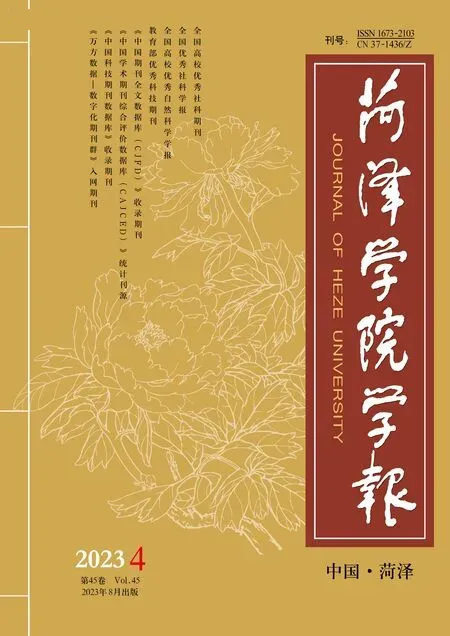《水浒传》非“隐居”苏北兴化人撰写
——就《大宋宣和遗事》中一些被《水浒传》写到的内容谈点感想
马成生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清代咸丰初年,兴化人施埁等把《故处士施公墓铭》中的“先公彦端”篡改为“先公耐庵”并假造这个施彦端为“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这“隐居”之处,当是其故乡苏北兴化①。
继承兴化施埁等说法的还有多人。下面,且举其最有代表性的三家。
2012年,苏北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作出《关于规范施耐庵宣传的学术研讨会议纪要》:“施耐庵,名彦端”“元末兵起,参与了张士诚起义”“后归白驹,以《大宋宣和遗事》为素材,闭门著述,写成皇皇巨著《水浒传》”②。
2014年,浦玉生先生认为:“施耐庵,本名彦端”“元贞三年(1296)生于泰州海陵县白驹场街市”“曾官钱塘二载。由于与当事权贵不合,愤然悬印辞官而去,隐居著《水浒》”③。
大丰市施耐庵公园《施耐庵塑像碑座文》:“公讳彦端字耐庵”“曾官钱塘”“辗转迁兴化定居白驹场”“中年即追溯旧闻《大宋宣和遗事》史迹,暮年以草堰张士诚起义成败为鉴,潜心著作”“撰成《志余》《水浒传》等巨著”④。
以上三种看法,都认为这位施耐庵(实指施彦端)是隐居在他的家乡兴化“著《水浒》”,且“以《大宋宣和遗事》为素材”。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辩的问题。
一
在《大宋宣和遗事》中,确是有多处提到梁山泊:
晁盖八个……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大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
宋江写着书,送这四人去梁山泊,寻着晁盖去也。
宋江……带领得朱仝雷横…等九人,直奔梁山泺上。
而在《水浒传》中也写了梁山泊: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週迴港·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第78回))。
所谓“素材”,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只仅仅是“梁山泊”(泺)三个字,仅仅是一个地名。上述描写,究竟是一种艺术虚构,还是在现实世界中,真有如此诸般的类似境界与物像?
莫其康先生在《兴化芦荡即是拟想的梁山泊》中说:
史称金时“渐淤”,元时“遂涸”。可见元末明初梁山泊已不复存在……他凭何体验而著笔,以何地理背景写出《水浒传》?
古代兴化境内,河流纵横,湖荡众多,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区区以为,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地理背景,主要是得胜湖和施家桥芦荡⑤。
还有姚恩荣、王同书先生在《张士诚——张荣——宋江》中说:
白驹施耐庵……以得胜湖、千人湖为原型,创造了水泊梁山。
上述这些话,分明是肯定兴化施彦端“隐居”其故居兴化而描写《水浒传》的。对否?我们且用实际情况来检验一下。
首先,所谓“金时‘渐淤’”,元时‘遂涸’”云云,看来颇重视史实,其实却并未较全面地看重史实。就在“金时”之前,据《新五代史》卷九所载:
石晋开运元年(944)六月,丙辰,河决滑州,环梁山入于汶、济。
在《宋史·宦者传》中又有这样的记载:
梁山泺,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渔之利。
这些史实,历历在目,为何视而不见,弃而不取?《水浒传》这部作品,历史背景是北宋末年宋徽宗时代,既有上述这些“水域”的记载就足足可以“著笔”“梁山泊”了。且看高文秀就这样写着: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园八百里。(《黑旋风双献功》)
高文秀所描写的“纵横”“四下”两句,把山东梁山泊的非凡气势表现出来了,可谓是描写梁山泊的经典性语言。本文上面所引用的描写《水浒传》中梁山泊的语言,其“週迴”与“四方”明显是“移”用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的语言。不仅如此,《水浒传》中还有多次“移”用呢。如第十一回,柴进向林冲介绍:“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园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又如第三十五回,宋江向花荣、秦明等介绍:“自这南方有个去处,地名唤作梁山泊,方园八百余里,中间宛子城,蓼儿地。”(上述所引用《水浒传》中描写梁山泊的文字,均见《明容与堂刻〈水浒传〉》),《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梁山泊,实际也就是以上这些,并未有其它描写了。可以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就是高文秀首先写出,《水浒传》的作者继承、使用罢了。这个高文秀是山东省东平人,“府学,早卒”。元人钟嗣成的棟亭藏书《录鬼簿》卷上已把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录鬼簿》成书于元天历庚午(1330),可见,高文秀“著笔”梁山泊之时,苏北兴化施彦端尚未必出世呢!而目,还须注意,高文秀所在的东平县就与梁山泊近邻,至今还有一个东平湖是当年梁山泊逐渐缩小后的遗留部分。高文秀自当是把他自己近邻的现实世界中的梁山泊艺术化为上述这样的描写文字。他难道会跑到苏北兴化去,观察“千人湖”或“得胜湖和施家桥芦荡”之类,因而“体验而著笔”梁山泊?简明说一句:我们现在所见的《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与苏北兴化的“水乡泽国”之类,并无什么“原型”关系。至于梁山泊中的“芦苇野港”之类,东南沿海,大江南北的湿地中,何处无之,自可根据需要而融汇进去的,要描写梁山水泊中这些细小部分,何必拘泥兴化的“施家桥芦荡”。
事实是,山东梁山一带,原有“河决滑州,环梁山”的水域,高文秀据此而艺术地运用“纵横”“四下”两句经典式语言,描写出梁山泊非凡的气势。这两句经典式语言,被 “移”用于《水浒传》中的梁山泊,直到如今,人们一提起《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这两句经典式语言,往往便也随口而出。究竟为的什么,莫其康先生等要抓住梁山一带一时的“渐淤”“遂涸”,要责问:《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凭何体验而著笔”?也许认为“石晋”时代的“环梁山”水域已经相隔远了些,那么,《明史·河渠志》不是有明确记载:“至正(1341—1368)中……济、宁、曹、郓间漂沒千里。”这与明代《水浒传》的“著笔”不是很近吗,为何视而不见弃而不取呢?看来,在对待史实方面,莫先生等可能是采用了一般学者所不用的断章取义手法,其原因也就是要认定兴化一带的水域是“创作《水浒传》的地理背景”。然而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史实,只能这样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著笔”与苏北兴化的水域无关,与苏北兴化的施彦端无关。
二
《大宋宣和遗事》中,描写了一个颇为引人的“智取生辰纲”故事: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匹缎,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至五花营堤上田地里,见路旁垂杨掩映,修竹萧森,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庾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时,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知人事。笼内金珠、宝贝、缎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
《水浒传》中,也描写了一个同样性质的故事,可以说是以上述故事为“素材”通过艺术化而成。且看:梁中书……即唤老谢都管并两个虞侯出来,当厅分付道:“杨志提辖情愿委了一纸领状,监押生辰纲十一担金珠宝贝赴京,太师府交割……次日早起五更……离了梁符,出得北京城门,取大路投东京进发……五七日后,人家渐少,行客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那十一个厢禁军,担子又重,无有一个稍轻。天气热了行不得,见着林子便要去歇息。杨志赶着催促要晏行,如若停住,轻则痛骂,重则藤条便打,逼赶要行……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多个人,没一个不怨怅杨志……当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岖小径,南山北岭,却监着那十一个军汉,却行了二十余里路程。那军人们思量要去柳荫树下歇凉,被杨志拿着藤条打将来……看看日色当午,那石头上热了,脚疼走不得。众军汉道:“这般天气热,兀的不晒煞人。”杨志喝着军汉道:“快走,赶过前面冈子去,却再理会。”……当时,一行十五人奔上冈子来,歇下担杖,那十多人都去松树下睡倒了。杨志说道:“苦也……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地名叫做黄泥冈。”只见对面松林里影着一个人,在那里舒头探脑家望……撇了藤条,拿了朴刀,赶入松林里来……原来是几个贩枣子的客人……没半碗饭时,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付担桶,唱上冈子来。
这“一付担桶”,挑来的是两桶酒。“贩枣子的客人”先吃了一桶,而后,巧妙地在另一桶中放入蒙汗药,让杨志等十五人吃了。于是,很快麻倒,“贩枣子的客人”吴用等便倒掉车子里的枣子,把十一担原是给宰相蔡京的“生辰纲”“取”走了。
在《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的黄泥冈地点,根据其情节的需要,安排在郓城境内一个叫双堆集的地方。此处,笔者于某次水浒研讨会之便,曾与一些学者去参观考察过,其实是一片平地,并无什么山冈峻岭。那么,这座黄泥冈是艺术虚构还是另有原型?
在钱塘(杭州)对江河上镇宋家古村,倒是确有一条山冈,长约两华里,高约六十米,冈上有各种树木、野草、乱石之类,名字就叫“黄泥冈”。冈下有“黄泥堰”“黄泥硬”“黄泥荡”等好几处小土名。这条“黄泥冈”,古代是杭州——义桥——诸暨——义乌的通道。历代相传,宋代名相楼钥就曾来走过,元明之交的刘国师(基)还曾在这条冈上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这条冈,是颇有名气的。久居钱塘的施耐庵,自当知道这条黄泥冈,是很可能把它移到山东郓城境内去的。附提一下,在《水浒传》中描写黄泥冈上吴用等七位“贩枣子的客人”在黄泥冈“松林里”歇凉之时,有这么一句:“松林里一字儿摆着七辆江州车儿”。只一句话,就用了两个杭州的方言土语“儿尾词”,这也可作为佐证。
在此,我们可以体会:《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的作者到底在何处“著笔”?
三
《大宋宣和遗事》中,还写有一事:
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岔气……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郓城县官得知,帖巡检王成领大兵弓手,前去宋江庄上捉宋江,争奈宋江已走,在屋后九天玄女庙里躲了。宋江见官兵已退,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
在《水浒传》中,因宋江“杀惜”辗转上了梁山。随之,回“家中搬取老父上山”,被迫捕,躲入玄女庙,得天书,描写了大段文字:
宋江只顾拣僻静小路去处走……只听得叫道:“宋江休走!早来纳降!”宋江一头走……远远望见一个去处……叫声苦,不知高低,看了那个去处,有名唤做还道村。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遭涧水,中间单单只一条路。入来这村,左来右去走,只是这条路,更没第二条路。宋江认得这个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早看见一座古庙……便钻入神厨里……
据《水浒传》描写,这“一座古庙”,就是玄女庙。宋江在玄女庙“神厨里”,做了一个梦,玄女娘娘“教取那三卷天书,赠与星主(宋江)”。《水浒传》中这些描写,究竟也全是艺术虚构?还是在现实世界中有某些素材?
萧山一位热心《水浒传》研究的柴海生在《萧山与水浒》第六章《萧山楼塔雪环村与〈水浒〉还道村》中说:
还道村就是今萧山区这楼塔镇的雪湾村……所谓还道村,就是村中只有一条道路。走完这条道路,必须原路返还,才能走出村去。
这个“还道村”,就在杭州对江的萧山县境。如今已是相当有知名度的黄泥冈、独龙冈这些被认为“移”入《水浒传》的山冈,与雪湾村相距不过二、三十华里。数年前,我们一帮对《水浒传》有兴趣的人,就请柴海生同志领队,去实地参观考察了一次。果然雪湾村的形势,正与柴海生同志所描述的一样,一从山口进入,三面“都是高山峻岭”,略如葫芦谷,入去出来,“单单只一条路”。相距这雪湾村村口不远,还有一座玄女庙,据说是楼塔镇一带大大小小的十八个自然村共有的祖庙,属道教管辖,始建于南宋。此庙座落处,名叫小春坞,因此也有称它为小春坞庙的。这些,我们几个人都觉得:与《水浒传》中的描写大致“对得上口”。
还不止于此。《水浒传》中还描写了玄女前有“一条龟背大街”。柴海生同志解析:“龟背大街”就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大路”。这样的路,在这一带以至浙江乡下处处都有。另外《水浒传》中还描写了还道村中的“茂林修竹”,“合抱不交的大松树”以及“潺瀑的涧水”“青石桥”之类。这些景物,我们在雪湾村一带也时时可见。
参观考察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感觉,这楼塔镇雪湾村一带的形势、四周的道路、景物,是有可能被钱塘(杭州)施耐庵描写《水浒传》中还道村的一种素材。我们也很希望,其他对《水浒传》有兴趣的同志也去参观考察一番,谈谈认识,相互切磋切磋。
四
《大宋宣和遗事》中还这么大书一笔:
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这“平方腊”一事,《水浒传》中整整描写了十回。对此,笔者于他处已多有涉及。这里,仅就《水浒传》作者的“居处”角度,粗线条式提一提。
宋江“平方腊”,从开封陈桥驿出发,“前军已到淮安县屯扎”,“本州官员”请进城中管待,诉说:“前面便是扬子大江”(长江)。这话对吗?前面已提及,有的学者认定:《水浒传》是兴化施耐庵(实指施彦端)“以《大宋宣和遗事》为素材”,“隐居”在他的“居处”兴化而“著《水浒》”的。而据出土文物“廷佐铭”这个“隐居”兴化者,于1353年张士诚“兵起”时,是避兵“播流苏”,“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的。他南下北上,已两次渡江,自当熟知,光从兴化到扬子大江就有两百余里,而淮安更在兴化的西北,相距兴化也有两百余里,可能还更远些。试问:怎么可能说淮安“前面便是扬子大江!”光凭这一例,就相当有力地表明:《水浒传》不可能是这个“隐居”于兴化故居者所写。
现举一位久居钱塘者,就其所描写的钱塘一带有关地理态势之类的实例,予以对照一下。
先看有关城镇的描写:宋江部队自秀州(嘉兴)西南向经临平镇入杭州,而后经富阳县、桐庐县,入睦州(梅城),自此沿新安江而上,与自临安、经歙州东南而下的卢俊义部队,会攻清溪。其城镇的次序、行进的方向,完全真实,一点不乱。
再看,部队战斗所涉及的关山,如临平山、皋亭山、独松关、桃源岭、五云山、半墦山、白峰岭、乌龙岭,乌龙山、昱岭关等,也描写得非常准确,未有差错。
还须特别提一下。《大宋宣和遗事》中,还描写了钱塘(杭州)周边一处方腊起义地点——方腊“啸聚睦州青溪帮源洞”,同时,又描写了方腊最后失败地点——“擒方腊于帮源山”。
这睦州,即今梅城,与杭州的桐庐近邻。青溪,即今淳安,在睦州境内。帮源洞,并非指一个山洞,而是一处地片之名,位于青溪西北面。有三条山溪,汇合于今天的威坪镇附近,即帮源洞口。且看《水浒传》中有关描写。在九十回中,就写着:“方腊就青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在九十八回中,就写着:宋江兵马“打破了清溪城郭,方腊……投帮源洞中去……坚守洞口……宋江卢俊义把军马周回围住了帮源洞,却无计可入。”这三条山溪两旁,都有高山峻岭,个人攀爬,也不容易,至于大队人马,因方腊“坚守洞口”,确实很难进入。只是柴进事先潜入方腊内部,里应外合,终于攻入帮源洞,在这一片地区之内捉了方腊。《水浒传》中这些地理态势的描写是相当真实的,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方腊“啸聚”“帮源洞”中与被“擒”于“帮源山”中的描写是一致的。所以如此,自当与《水浒传》作者久居钱塘有关。
此外,附带提一下有关建筑物。如杭州的桥梁,城东的东新桥,城北的北新桥,西湖北沿的西冷桥,短(断)桥,西湖南沿的长桥、定香桥,还有西湖湖中的苏堤六桥,等等。又如杭州的城门,“今方腊占据时,东有菜市门、荐桥门;南有候潮门、嘉会门;西有钱湖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北有北关门、艮山门”。东西南北,次序井然。
从《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宋江平方腊”这一“素材”,这位久居钱塘者予以大量充实、拓展,写成了十回书,八九万字,在地理态势、气候物像,人文史实以至节庆物产等等,都描写得相当准确、真实。以上所举,只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但是,仅仅这些,与那位被认定为“隐居”于“故居”兴化者所描写的苏北的一些内容对照起来,真实与虚伪,准确与谬误,已是十分明显。其实,上已提及,苏北那样地理态势的描写,不可能是那位所谓“隐居”于苏北兴化故居者所描写,而实际很可能是那位久居钱塘者所描写,因为,他不熟悉苏北啊!
不须言辨,仅就上述《大宋宣和遗事》中的“素材”而在《水浒传》中被大量充实扩展的几个例子看来,《水浒传》作者并非是那位被认为“隐居”于苏北兴化故居的施彦端,而更可能是久居于钱塘的施耐庵。
注释:
①施埁等的说法,见于清咸丰9年《施氏族谱》的“施让铭”中。这些全是他们篡改、假造出來的。笔者于《钱塘西溪——〈水浒传〉的孕育之地》中,已有具体论述,见于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237页、135页。
②这篇《会议纪要》,见于《耐庵学刊》22期,大丰市施耐庵研究会编,2012年9月印行。
③见浦玉生《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④见《施耐庵塑像碑座文》,转引自张袁祥《施耐庵是“子虚乌有”还是实有其人》,《水浒争鸣》第十期,崇文书局,2008年10月出版。
⑤参见莫其康《兴化芦荡即是拟想的梁山泊》,《水浒争鸣》第18辑146页,中洲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
⑥见姚恩荣、王同书《张士城——张荣——宋江》,《施耐庵研究(续编)》219页,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大丰《耐庵学刊》编辑部编1990年5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