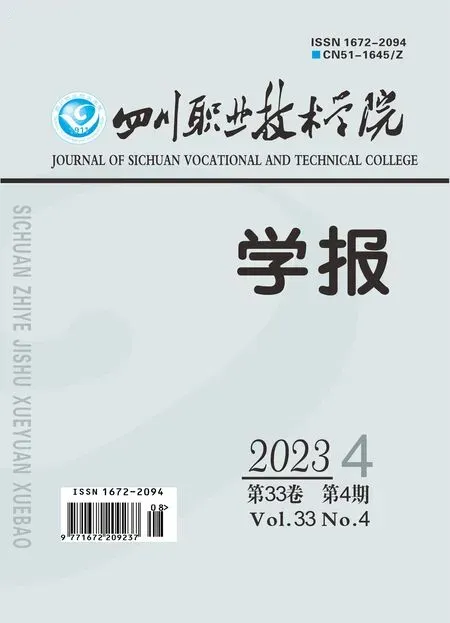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窥视”艺术
冯麒如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新小说”自20世纪50年代从法国应运而生,到60年代崛起风靡欧美文坛,因其彻底反传统的美学思想与展现出的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前所未有性与先锋性,可谓是20世纪最受争议的文学流派之一。新小说亦被称为“反小说”,即反对传统小说艺术中重人物刻画、重情节描绘、重读者阅读体验等特征。新小说作者们旗帜鲜明反对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旧小说理念,流派中的“心理写实主义大师”娜塔莉·萨洛特有言“小说被贬为次要的艺术只因它固守过时的技巧”。新小说创作强调有关于“物”的描写,通过客观事物自在的凸显尽可能还原世界细碎朦胧的真实性,因而也通过尝试通过语言形式的更新改变推动小说艺术发展。罗伯-格里耶在《未来小说的道路》一文中提到“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1]537,“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1]538,表明了他对小说创作所针对之客观世界的认知态度,也明显受到存在主义现象学思想影响。如何描绘格里耶理念中的客观世界,他找到了“窥视”这一角度。所谓“窥视”即为暗中观察或偷看,强调旁观性、隐蔽性和视角的集中局限性,是破除传统小说全知全能上帝视角的有效途径。格里耶在其创作中对“窥视”的运用灵活广泛,自成一派,甚至直接将一部作品命名为《窥视者》,足见“窥视”在其创作艺术中的重要地位。
一、“窥视”描绘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对人的描绘说道:“人性非善也非恶,人生出来只有本能和能力……因为社会上伤风败俗的行为在什么环境中滋长就具有那个环境的色彩。”[2]即强调通过环境对人的影响构造典型,再以典型性人物表达文学认识的准确普遍性,人物既具有唯一特性也上升到类型高度。这种看似客观的人物描绘是从上帝视角全方位展现人物衣着打扮、外貌体态与性格特质,呈现给读者一个完整充实的人的形象。如《欧也妮·葛朗台》中对老葛朗台的描述“下巴方方的,嘴唇没有任何曲线,牙齿很白,眼睛表情冷峻,似要择人而噬,俗称蛇眼……脸上的表情说明他精明狡猾、故诚实而又自私自利……厚实的鞋子系着皮鞋带,一年四季都穿着羊毛袜,粗呢栗色短裤系着银质的扣子”[3],人物的一切特征都由作者事先说明展示,读者面对的是宽阔明晰,敞开确实的作者视域。传统小说中故事由人物境遇展开,人既是故事主要元素,也是故事开展基础。格里耶在《关于某些过时的定义》一文中对此传统评价道:“写人物的小说彻底地属于过去,它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标志着个体达到顶峰的时代。”[4]33启蒙价值承续人文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在20世纪遭遇现代性爆发的剧烈冲击,典型后果就是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危机。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诸多人文学科也纷纷逐渐转向重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的修罗场。从马克思·韦伯阐释“世界的去魅”到胡塞尔提出“回到事物本身”,人之理性的价值发生经历了一场向内化的转变。人与世界的关系也从征服利用的二元对立转化为更为复杂的交织共存,亦如格里耶所说:“我们的世界已经不那么自信了,或许还更自谦了,因为它拒绝了个人的万能强力,但同时也更有野心了,因为它眺望着彼界。对‘人类’的专一崇拜让位于一种更宽泛的、更非人类中心论的意识。”[4]34形式的探索并不意味着人物的消失,更不像肤浅的批评者指责新小说“把人赶出世界”那般武断,人物的描绘只是通过一种全新的叙事视角开展,就是“窥视”。
兹维坦·托多罗夫把叙事视角分为三种形态,叙事者大于人物为“全知视角”,叙事者等于人物为“内视角”,叙事者小于人物为“外视角”。格里耶在小说中明确抛弃巴尔扎克式“全知视角”,叙述者机动而灵活,基本采用“内视角”与“外视角”及其变体手法,主要包括《窥视者》与《橡皮》中的第三视线内视角和《嫉妒》中的第一人称隐藏外视角。选用“窥视”是发现选中其旁观性、隐蔽性和视角的集中局限性等特点,故而从“窥视”角度描绘人物更符合其倡导客观视角“朦胧的真实”之文学理念。“窥视”描绘的人物既包括“被窥视的对象”也包括“窥视行为的发出者”,也会同时描绘双方。
《嫉妒》通篇没有“嫉妒”情感的展现,也没有关于处在嫉妒境况下对客观事态的考虑、分析、意图与打算,而是通过录像式“窥视”的眼光记述许许多多图像片段,嫉妒正是隐藏在这些蒙太奇式表现的联系中。阿X作为“被窥视的对象”,始终被一个无名叙事者窥视(即一直不现身的丈夫)观察。窥视者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于阿X与弗兰克间真实性有待考量的“互动”上,时刻感觉“阿X倒好像在有意等他”“阿X尽量地凑到弗兰克的座椅旁”“弗兰克看着阿X,阿X也盯着弗兰克。阿X朝着弗兰克微微一笑,在黑暗中,这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眼波”[5]21阿X对弗兰克的挽留、两人斟酒时的眼神交流、阿X为弗兰克准备餐具等等细碎微小的行为举动。格里耶通过无数繁复细致的场景画面堆积详细的故事生发空间,同时将场景元素的描述融入窥视,典型代表就是多次出现的窗子。窗子有时强制分割窥视者的视线,有时作为窥视路径得以通达对象的基质,凸显了“窥视”视角的非全面性与集中性,正如阿X透过百叶窗缝隙看向露台的视线局限性同时也隐喻了窥视者对阿X观察的局限性,由此造成窥视叙述的空白,叙述空白进而催生想象空白。这个嫉妒者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唯有那双摄像机似的眼睛暗中把所监视到的一切从各个角度精确地、不厌其烦地一一拍摄下来。窥视者是如此专注集中,把注意力放在与妻子有关的一切细枝末节上,这些景象与细节在他脑海不断重复、不断萦绕,在想象空白中无限繁衍膨胀,客观上就充分显示出他精神状态紧张的程度,显示出一个事实:他在怀疑自己妻子,他在嫉妒。窥视者描绘阿X的秀发、身着的紧身服装、写信时灵动的姿态,展现出一位优雅知性、平和有礼的女性形象,但这也是经过窥视者过滤引导的展现,阿X与弗兰克靠近时摇动的发丝、与炎热天气不相称的紧身裙、因害怕蜈蚣抓紧餐布的手指都被其倾注强烈性暗示,成为怀疑妻子与人有染的迹象。格里耶通过角度新颖、形式巧妙的“窥视”描绘的这一位精神状态敏感多疑的嫉妒者丈夫形象,成为新小说“以物写人”典范。
《窥视者》中马弟雅斯作为窥视行为的发出者,其窥视性首先是其职业赋予的,作为一名推销员,必须通过看目标对象迅速评估其是否可能买货品,而采取灵活的交谈话术促成生意,其次也是他本人性格诡谲敏感使然。他对女人的窥视往往充满了迷蒙的性意味,在咖啡店看招待姑娘“在她的黑袍上围着一条围裙,背后圆形的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了细嫩的皮肤,她的发式使她的颈背整个都显露出来”[6]42,回想观察雅克莲“在右腰肢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她有一粒凸出来的痣,颜色是红中透黑,蚂蚁一般大小,形状像一只三角星,非常像个V字或Y字”[5]107,描述雅克莲的照片姿势“背靠着一棵笔直的松树站着,头靠在树皮上,两腿挺直,稍微分开,两臂放在背后”[5]66。有针对性的窥视目光集中于女性肉体,暗含了隐秘的性指向,雅克莲腰部黑痣视线与VY形态暗示其性器官与子宫,照片的姿势则被意淫为被捆绑强奸。马弟雅斯的窥视描绘了其隐藏于平静外表下的性欲望,对恋童癖与性虐待的激情使其奸杀雅克莲,格里耶以窥视视觉的集中性、暗示性描述,塑造了一个道貌岸然的性变态。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对性的研究影响,罗伯-格里耶不仅认同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还强调所谓性变态实质上是人类性不能的原始而普遍的趋向[7]。性变态属本能,潜藏在每个人心灵深处,人没有必要为之感到羞耻有罪,他理直气壮写道:“我比大部分所谓反常者更了解那附在我身上的血腥魔鬼,我并不因此感到有罪,也不后悔。”[8]作者通过“窥视”尝试性地将性变态意识外化,描绘了马弟雅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隐喻的矛盾个体,融合了表面的平实有礼与内在的欲望攻击。而后其安然无恙离开小岛逍遥法外的结局或许也隐喻了作者对这样一种性心理的“正名”。
二、“窥视”建构空间
传统文学中的空间展现,大多体现为作者以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构建“人物活动背景”,同时倾注“主观精神投射”的形式。有擅长对社会物象进行细致描摹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风格,也有习惯于情感化空间环境的浪漫主义风格。进入20世纪以来,空间理论以福柯的权力空间、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索亚的第三空间、卡斯特的流动空间等为代表继续繁荣发展。从18世纪末边沁提出“全景监狱”设想到20世纪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考察监狱的权力机制,再到布鲁诺·拉图尔提出“独景窥视”以反对当代空间分析中源自边沁盛于福柯的“全景敞视”霸权性地位,“视觉”始终在对空间的考察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说福柯试图借由全景化凝视展现出权力如何借助空间的生产来实现自身的话,那么拉图尔恰恰是要颠倒这样的分析模型,将“全景”转变为“独景”,将立体化的“敞视”理解为纯粹平面化的“窥视”[9]。视觉作为人类最初用以体会空间的感官,其比触觉作用范围更广同时有益于激发想象对空间的认知拓展。视觉对空间的建构作为一个长久话题,诸多文学流派都对其有所探索,新小说亦然。“窥视”这一凸显旁观性、隐蔽性和集中局限性的视角,在格里耶小说中对空间的建构作用巨大。
窥视离不开空间,空间提供介质使窥视行为成为可能,同时窥视也在着力建构空间,二者间关系的矛盾复杂在格里耶小说中有丰富展现。以《窥视者》《嫉妒》和《橡皮》三部作品为例,空间的展现可以分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窥视对公共空间建构首先通过咖啡馆、小酒店代表的小型封闭公共空间打造了人物相互间的窥视场所,其次通过窥视视角描绘客观事物建筑形态建构人物行为活动附着的街道、社区等大型公共空间。咖啡馆等场所狭小,聚集在独立桌子旁的三两人群组成交流团体。这些小团体间的对话对内共知对外私密,外人可以通过偷听窥视间接参与对话内容,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的接触形成互相间私密空间碰撞的共存交织。窥视关注视角的持续定位转移使对象不断进出,构建动态的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交流模式。开放的街道城市等场所敞开,个体在物质上置身其整体中,但却可以通过窥视关注不同要素构建有意义的上层精神空间,由天然客观的能指物导向主观意图的所指物。同时透过外部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查探,如在街道上窥视民宅,也构建了空间视角的流动。窥视对私人空间的建构以家庭、室内为代表,封闭局部的空间为详细窥视供给条件,使有限的陈设物通过窥视的集中产生针对性力量,隐匿的空白则可以填充更多解读与想象。
《窥视者》中马弟雅斯的行动轨迹,就是由不断进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中交替绘制。来到小岛后,咖啡馆小酒店作为其临时落脚点,但因为需要推销手表他又不断进出居民家中,路途上又置身于街道外景的开阔空间。咖啡店小酒馆中出现多次马弟雅斯身处其中偷听窥视的桥段,招待姑娘从身处柜台绕出、店主靠着门框训斥其动作迟缓、水手们围着桌子讲神秘的闲话,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被窥视捕捉为动态物相,定为空间存在的基础。马弟雅斯虽然出生在岛上,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认识的人了,属于切实“入侵”的外来者,他编造自己认识某些不在场岛民的谎言企图拉近与居民的关系好有助于自己推销手表。从身份立场上看,外来者为了达成目的而编造不实的谎言的整套流程,在前视域心理赋予其视觉态度隐匿性,即为窥视姿态的隐藏性旁观性奠定基础。在他萌生杀害雅克莲想法与作案后,这种隐匿旁观心理又加上了躲藏隐瞒本能,使其感知时间空间的窥视性进一步增强。作者借着人物这种从一而终的窥视统摄心理展现了马弟雅思对小岛整体空间的建构,着重体现于他在脑海中对各种路线的规划回忆。岛上人口不多,马弟雅斯在推销路上对地理物象的观察与道路规划的注意都属于是通过窥视进行的空间素材积累行为。因为要实施作案,又要不被看到地抽身而出,因此就需要一套合理隐蔽行为流程,好让自己在时间和空间的追问中消失。格里耶运用大量笔墨细致描绘岛上风物建筑结构与马弟雅思的规划推理,如他在小酒店中与女店主谈话得知雅克莲的姐姐玛莉亚去找妹妹,发现人不见了,于是马弟雅思因害怕自己行踪暴露开始推理可能的路程,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作预演。想到自己作案时留下烟头,他准备回去清理现场经过纵横交错的路与环境场景,在此过程中他又重新根据实际空间距离规划分配了自己在岛上的时间,好让作案时间消失。这一系列的推理与观察,本质就是一种通过拼接组合从“窥视”获取的琐碎素材达成的空间建构,实际的空间被窥视的眼睛从各个不同的剖面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窥见,经过人物主观性重组,描述出来的正是有目的意图的崭新空间。真正的客观空间在此过程中被拆解隐身,凸显了“窥视”对格里耶新小说犹疑虚无与不确定性风格的重要塑造作用。
《橡皮》中对杀手格利纳蒂刺杀行为的描写,也是窥视对空间建构的实践。作为一个胆战心惊、疑神疑鬼的杀手,他在行动之前已经对杜邦的宅邸构造详记于心。但格利纳蒂进入房屋后又详细窥视了一遍自己行动空间的布置,从灯光、楼梯、油画、书籍等构建了与计划中描述的冰冷局部,充满绝对指向性不同的、现实的温馨拥挤的空间。刺杀计划是:格利纳蒂关掉门口的室内灯,黑暗中躲在椅子后,等待杜邦一开门,在过道灯光的照射下,其显现在门洞中间清晰的身影就是身处黑暗中杀手的直接射击目标。从杀手隐藏的位置到门口,两点间只有一条路线。这场谋杀行动的设计天然充满绝佳的“窥视感”建构,视觉路线的直接唯一、关注显现对象的局限范围、杀手潜藏黑暗的隐匿意图,建构起一个完美典范的窥视空间。犹如电影的空间特写,刺杀的紧张蛰伏气氛被固化附着于窥视空间,窥视建构的谋杀空间又反向催化气氛的意外不可控。格利纳蒂对宅邸空间的窥视评估导致时间没有按照计划严格落实,最终来不及关灯致使刺杀失败。可以说这两阶段行为也是窥视建构空间的两种指向:一方面窥视作用于具体物象,通过组合元素构建外延真实的空间;另一方面窥视作用于抽象路径,通过筛除余存构建内涵虚拟的空间。
无论是《窥视者》中马弟雅斯的窥视事象元素重组式的空间建构,还是《橡皮》中格利纳蒂的窥视路径参考集中式的空间建构,都展现了格里耶小说中“窥视”对空间建构的突出意义。
三、“窥视”交织结构
“结构”是故事的结构,也是语言的结构。在普鲁斯特的作品中,故事与结构被回忆式地分解;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故事与结构被流散式地打乱;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故事与结构被寓言式地赋能;在贝克特的作品中,故事与结构之间不断进行争辩质疑甚至毁灭。罗伯-格里耶在其小说创作中同样通过“窥视”交织文本结构,在纷繁物象、跳跃时间与多点叙述中进行故事与结构的交叉实验。罗伯-格里耶反对线性叙事模式,他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时空的跳接和时间的无序粘合,模糊的人物形象、断续的情节和缺乏必然性的结局,使读者很难统观事件的全貌。但是人物的心理反应和精神活动却能将种种用“现在时”描述的场景串联一体,构成内心事件的时间和空间[10]147。《窥视者》《嫉妒》和《橡皮》三部作品内容题材与叙事形式各异,却共同展现出了总体的迷宫式结构,读者需要通过介入参与到不完全的故事叙述中尽力发掘“真实”,感受思维阅读超越阻隔的愉悦。
格里耶的写作风格,常被冠以“零度写作”评价,即“比较来说,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就是一种新闻式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一般来说未发出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即感伤的形式)的话。……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11]是注重作者的旁观与隐身,也是凸显背后隐蔽的总体把控,这种姿态视角从创作者实践角度就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窥视”。针对人与物的刻画比重,他并没有刻意在作品里创造一个无人的世界,而是通过简化人物形象来表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新型的深层关系,表现处于物体重重包围之中的人类主体的被动性,以此深刻反映全面物化时代“主体危机”的特征[10]169。人被物的实存包围,物也被人的“窥视”视线包围,作品中的元素与故事整体在外部同样被读者的“窥视”查探包围。
分析“窥视”对《窥视者》的结构交织,从题名可直接入手,即“谁是窥视者”。作品译者郑永慧在序言中提出于连作为马弟雅斯杀人行为的“窥视者”。法国文学评论家让·里加杜(Jean Ricardou)在《新小说问题研究》中曾提到“《窥视者》(《Voyeur》)的第一个书名本是《Voyageur》,即旅者,或游荡的人,而在书中 Voyageur 和 Mathias 交替出现并都指代这个外来的手表推销员”。这一观点在午夜出版社对《窥视者》的评论中也得到了印证: “小说是由马弟雅思带领前行的,这位旅者—窥视者(voyageur—voyeur)不断推敲细节,计算来回行程的时间……是为了掩盖一段时间上的空白。”[12]马弟雅斯在故事中作为小岛外来者也始终处在他人的窥视中,马弟雅斯对女人的性欲窥视,叙述者不完全叙事对主人公行为的窥视,读者对故事发展与风物人为的窥视……可以说《窥视者》就是将结构建立在多重窥视交叉的浮空平台之上,随着马弟雅斯的足迹,在他不同的活动阶段、不同的活动地点编织这些不同的窥视关系网络。马弟雅思的犯罪和于连对他的窥视只是众多窥视被窥视关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只是引发新的窥视关系的契机,而不是作品叙述的最终落脚点[13]。读者可以从纵向横向不同的角度与路径进入文本,参与到真假虚实的场景建构中与遮蔽复现的解密过程。“窥视”交织的叙事结构打破传统小说整体稳定的结构,以“窥视”支撑人物行为动机过程、以“窥视”营造迷蒙幽闭气氛、以“窥视”交织游戏物象结构。
《橡皮》是格里耶作品中形式创新最为成功、同时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作品,全方位解构了传统侦探小说的解密模式。在作品开头第一章有一段关于人物的肖像动作描写,从表层看这段文字通过对主人公瓦拉斯行走的描写来赞颂其性格并预示其命运的发展,实质上却是对瓦拉斯的反讽。这段文字中的“他”与瓦拉斯的行为处处相左,与其说“他”是瓦拉斯不如说“他”是传统侦探小说的主人公。内容概括了传统侦探小说的三个特征:一是“像纬线一般井井有条地按先后排列起来”的事件;二是主人公“自己在行动”自己把握着大局;三是“必然的、光明美满的”结局。《橡皮》正是从这几个方面颠覆了侦探小说的传统结构[14]。“窥视”对结构的交织紧密作用于这三方面,发挥颠覆作用。首先,“窥视”视角的有限性使得叙述者的表述和读者的阅读难以把握事件逻辑意义的完整性,即呈现为起因、推理、解密等一系列过程的破碎感与不确定性。瓦拉斯的寻访与警察长罗伦的推测是作品中最突出明显的结构途径,两者秉持着不同的推理,难以互相说服,却在与其他角色的行为语言的交织中互相暗示影响。罗伦一开始不断确证杜邦是自杀,后来又觉得他是被他杀;瓦拉斯开始按照他杀去调查,后来又怀疑其或许是自杀。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结构统摄人物发展故事的路径,也没有设计任务的分工安排,作者冷静的记录描写撤出主观性,叙述者“看见”表述于文字的只有大量散碎的情节,人物的登场、内容的虚实与因果的顺序都交织成一团。同时,这些情节也没有如同传统侦探小说中角色的复盘梳理,难以呈现完整有序的故事结构,既强化新小说意欲展现的迷蒙幽乱风格,也增大读者理解难度,引导介入。
其次,“窥视”式写作剥离了主人公超越文本内世界的能动性,丧失把握大局能力。瓦拉斯作为侦探与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以及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赫尔克里·波洛机智聪慧、运筹帷幄的形象不同,他不仅在侦探技术上是个初出茅庐的菜鸟新手,在智慧魅力层面更像是个没有“主角光环”的跑腿人物。以福尔摩斯和波洛为代表的传统通俗小说中的侦探来说,他们的破案之所以有趣精彩,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越文本其他人物的认知的能力,即与接收到作者暗示的读者处于等同甚至更高的视线地位,擅长利用未被发觉的细节安排引导他人入局,最后找出凶手解开谜题,到达真相大白的结局。这种传统模式既从满足读者期待层面施予快感,也从应和文本结构方面展现优越。但这种模式的推进,根本上离不开主人公超越文本内世界的能动性与把握大局能力,格里耶降低主人公视线地位,以“窥视”式的新小说创作方法剥离自己可以赋予瓦拉斯的主观性,就使得他与故事中其他人在认知上无异,只能通过琐碎的走访、不成体系的探问和混乱的推理进行破案。人物完全内在于文本世界,难以对情节进行预知把控,读者与人物都只能窥视到部分真相内容。
最后,“窥视”打破结局在逻辑结构上的必然完满,呈现如玩笑一般的错位预言。这是基于“窥视”叙事角度对人物把握大局能力的剥离引发的连带结果。《橡皮》的结构看似混乱无序,却行文至尾照应相接,探案人瓦拉斯最后阴差阳错成了杀人犯、酒鬼的胡言乱语正好预言到正确的凶手、邮局女职员与巴克斯太太的证词指向瓦拉斯与杀手的相似性等等细节最后都得到了神秘的印证。这种设计将读者带入结构的迷宫,如同瓦拉斯迷失于街道上一般,是“窥视”式书写的有限性展现延伸出的结构创新。时间被打乱、逻辑被隐藏、物象在“窥视”中交织出新小说的独特结构。
纵观罗伯-格里耶小说创作中的“窥视”艺术,无论是作为写作风格还是叙事技巧都对其文学实践发挥巨大作用,具体将其倡导的“客观化”写作落到实处。格里耶曾言:“在作品之前,什么都没有,没有确定性,没有论断,没有信息。”作品是唯一客观冷静的舞台,展现世界原初的存在。面对二十世纪的浮动与不可捉摸,外部世界与人内心的迷宫状态,格里耶不理解,于是选择通过“窥视”尝试觅得细碎但真实的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