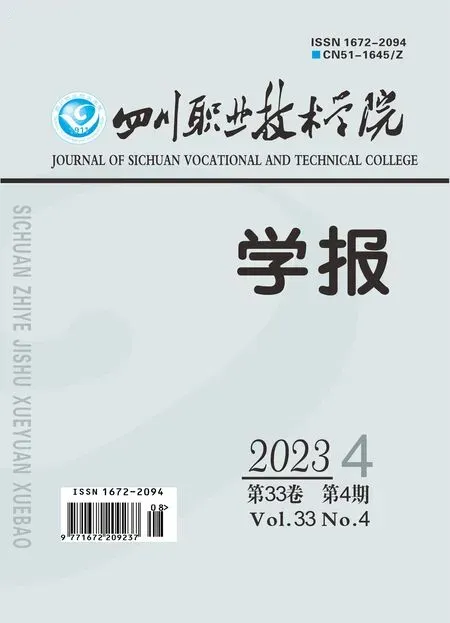论袁宏道尺牍中对自适的追求
宁玲玲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袁宏道是公安派与晚明文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强调“独抒性灵”,注重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价值。在尺牍中,袁宏道以简练直率的表达传达了自身的性情、思想与人格。通过袁宏道的尺牍作品,我们将更加了解袁宏道在仕进与隐退的曲折历程中,对自适生活的执着追求。
关于袁宏道尺牍创作中文人心态的研究,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展开,一是着眼于社会现实,分析袁宏道三仕三隐中的矛盾心理,并分析这种矛盾心理产生的原因。比如《“情腻”与“骨刚”的悖反——袁宏道尺牍中仕与隐的矛盾心态》认为袁宏道骨刚而逃世,情腻又不得不有求于世,始终与现实周旋,始终生活在矛盾之中。①二是从儒释道思想出发,认为袁宏道受佛禅思想影响而产生的复杂的心态变化。比如《论袁宏道复杂心态的形成与表现》认为袁宏道的佛禅思想经历了一个由鼓吹纵情适欲的狂禅,到提倡念佛往生的净土禅,再到主张安心任运的随缘禅的演化过程,而袁宏道的心态也经历了由纵情适欲到淡然处世的过程②。
无论是着眼于社会现实,还是从儒释道思想出发,众多学者都看到了袁宏道在晚明个性解放潮流中,追求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一面。但这种研究未将袁宏道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与其真实的生活状态结合起来,导致在肯定袁宏道追求个性解放的意义的同时,又认为他存在消解生活意义、逃避现实的思想。笔者认为,袁宏道在晚明复杂的社会环境里有着对个性解放的自觉追求,复杂的社会环境是影响袁宏道追求自适的外在因素,然而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袁宏道始终坚定的对个性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追求、对自适的向往。通过袁宏道给好友写的信我们得知,他所追求的自适生活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无关社会理想,而是将现实考虑在内后仍向往并追求的状态。袁宏道的这种对自适的追求,不是出于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在个性可以多元化的晚明社会对自己人生的主动把握。因此,本文主要着眼于袁宏道的尺牍创作,阐述袁宏道在尺牍文学中呈现的自适者面貌。
一、关于尺牍
“牍”的本义为书写所用的木板,长度有限,汉制木牍长度大约一尺,所以称为“尺牍”,因多用于书写文书、簿籍、书信等,所以“尺牍”一词也经常代指这些内容。“尺牍”一词发展到明代,基本上等同于书信。尺牍长约一尺,书写范围有限,所以文辞一般比较简练直接,常常显示出作者本人的性情情感,因此,“尺牍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较之于其他文学形式,更能以简洁自然的语言鲜明真切地表现作者的个性,是传达作者情趣、人格、思想的重要载体。”“明万历以后,尺牍创作盛极一时,晚明文人将尺牍作为抒写内心、展露性情的重要工具”,[1]并有意将其收入文集。晚明文人的尺牍作品既表达了自身的情绪情感与思想主张,又具有艺术审美价值,也正因此,尺牍成为研究晚明文人情感与思想的重要材料。
袁宏道的尺牍创作较为丰富,内容涉及性情书写、旅游观光、思想主张、亲朋问候等等,材料的丰富、内容的广泛使得通过尺牍了解袁宏道各个阶段的生活状况及思想心态的变化成为可能。另外,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说:“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2]这清楚地说明袁宏道受李贽的影响,形成了反对模拟、独抒性灵的文学观,[3]袁宏道自己也反对“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烂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申其才,无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4]710的行为,认为“文章新奇,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4]786的文章才是好文章。袁宏道创作的尺牍酣畅淋漓、洋洋洒洒,呈铺天盖地之势,不加掩饰,真诚地吐露自身的矛盾与纠结,为研究其人性情与思想提供了前提。
二、晚明社会背景下的自适成因
“自适”一词出现于袁宏道给友人徐汉明写的信中,信中他说:“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之人。”袁宏道接着说“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4]217由此可见,袁宏道十分向往适世之人的状态,认为适世者虽不被贤人君子认可,但他们自身却感到无比满足。晚明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变化促使文人回归自身,心向世外,袁宏道在此社会背景下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选择也体现了对自适的追求,展现了自适者的状态。
(一)官场环境的复杂与对个体生命的珍视
政治上,明代废除了宰相制度,以进一步强化了君主独裁的统治机制,而从嘉靖至万历等皇帝大都无心朝政,贪图享乐,国家政事由一些奸臣和权阉把持,群臣互相拉拢、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政局一派混乱。袁宏道在《摘发巨奸疏》中说:“夫都吏、当该,其本分制役也。平日瞒天作弊,招权纳贿,无所不至。”[4]1503此种贪污纳贿、只手遮天的行为,显然是明代后期统治者无能的结果。在这种环境下,朝廷法纪失去了应有的权威,官场环境一片混沌。袁宏道及其他文人大都清高廉正,不愿摧眉折腰,显然不适合在如此污浊的官场环境下生存,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正直之士大多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官场生活也变得十分严酷。
袁宏道在这种环境下备受煎熬,他在写给罗隐南的信中说:“人未有不佝偻其腰,足恭其面,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百苦备尝,而至三台八座者也。必百苦备尝,而后台座可望,是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狱也。人亦何为而乐地狱也哉?”[4]227将官场比作地狱,由此可见做官对袁宏道的折磨,以及袁宏道对官场的厌恶和恐惧。也正因此,袁宏道坚定地选择辞官,他写给管东溟的信中说:“病来五月,鸡骨支牀,面貌如烟,肘指如戟,宦心灰冷,归肠迫切,不肖虽愚,岂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4]257如此严酷的官场环境严重影响了袁宏道的身心健康,促使他远离官场、回归山林。当朝廷被权臣阉党占据,官场环境使人身心煎熬,袁宏道选择辞官不是退缩,是应对严酷的政治环境作出的合理选择,体现了袁宏道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坚守。
(二)经济发展的冲击与对享乐生活的追求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风气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消费主义蔚然成风,商人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升,传统的官贵商贱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动摇。消费盛行的社会风气加上腐败的官场环境,使得士人逐渐处于社会的边缘化地位,士人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传统道德观念,在现实中也越来越找不到支撑。另外,崇尚金钱与享乐的社会风气形成以后,很多文人见到了生活的更多面,他们在游玩、品茗、饮酒、收藏、参禅悟道中重新构建起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精神世界的满足使得他们大多不愿在晚明严酷的官场环境中挣扎。因此,晚明文人大多重个人趣味而轻功名富贵,重当下而轻传统,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坚定信念逐渐开始消解。
袁宏道也受到此种风气的影响,在吴地作县令时,袁宏道说:“奔走尘土,无复生人半刻之乐,名虽做官,实当官耳。”[4]205从这可以看出,此时袁宏道做官考虑的不是文人的社会责任,他更多把做官当成一件差事。另外,袁宏道受享乐风气的影响,也开始注重精神快适与物质享受。袁宏道指出人生“真乐有五,不可不知”,即:“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相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4]205这五种快活之事,大都与感官快适与精神享受有关,可见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深刻影响了袁宏道的生活追求与审美趣味。
(三)理学束缚的减弱与个性发展的强化
明代前中期,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力推行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控制了士人的思想。王阳明在陆九渊、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心学的思想体系,消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强制色彩,使得人们丰富的情感与欲望开始得到承认与重视,使人开始关注自身。李贽在此期间也以“狂禅”思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叛逆的思想解放潮流。
袁宏道受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在参禅悟道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个性与思想。袁宏道在给好友王百穀写的信中说:“往岁会诸名士,都无一字及禅。以故吴令时,每以吴侬不解语为恨,不知百穀之有意乎禅也。”[4]49袁宏道辞去吴县令,给聂化南写的信中说:“败却铁網,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4]311可知袁宏道深受佛家思想的影响,追求超脱快适的境界。而在《答乐之律》的信中,袁宏道也说:“弟懒僻若是,只合坐尊经阁读书。其实读书亦不耐,唯当枯守山林,作一绝学无为道人而已。”[4]749可见道家无为的思想也加强了袁宏道的自适个性。
三、仕、隐状态不断转换的自适者
袁宏道受晚明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多次为追求自适而辞官,然而袁宏道辞官后也不断做官,通过尺牍我们可以了解他在仕、隐状态间不断转换的原因,并以此看到在生活状态的不断转换中,袁宏道所坚持的对自适的追求。
首先,袁宏道清楚地知道仕进与隐退各有利弊,他在答王则之的信中说:“京中有苦有乐,家中亦有苦有乐。京中之苦在拜客,家中之苦在无客可拜;京中之苦在闭口不得,家中之苦在开口不得;京中之苦以眼目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为佛事。两苦相较,未知孰优孰劣,唯兄自评定。”[4]741做官需要拜客,在家见不到人又不免生闷,能解决这种矛盾的做法就是做个闲官,袁宏道再次回京做教官便是看中了教官的清闲。袁宏道在答梅客生的信中说:“饥急于名,饱急于乐,口腹急于身体,欲不教学何可得?且教学则永无大官之望,亦长在仕途之望,不唯官闲,而心亦闲,可以一意读书也。”[4]737可知做教官不仅可以满足口腹之需,更重要的是身心不会受到严酷的折磨,正如他所说“教官职甚易称,与弟拙懒最宜”。[4]741而此阶段袁宏道在尺牍中也叙述了许多读书论学、交友游玩之事,可见袁宏道做教官是较为清闲舒适的。
然而两年后袁宏道又乞假回乡,著书游览,参禅悟道。他在答王百榖的信中说:“仆来岁亦将乞假而南,……仆宦意甚阑,又如作吴令时矣。自思口腹无幾,身世受用无幾,安能劳碌事此生乎?青氊虽闲,要亦有拜客及不情应答之苦,终不若山居之稳贴也。”[4]787这便如《围城》中那句经典的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5]③在一个环境中呆久了便觉得无趣、感到束缚,这是人之常情,袁宏道想要再次辞官便表明他不愿受官场的束缚,表明了他对自适的向往。袁宏道对自适的追求是自觉且坚定的,他不仅意识到官场的束缚,更敢于打破这种束缚。另外,万历二十七年以后朝廷多生变故,袁宏道在《冯琢菴师》的信中说:“近日国事纷纭,东山之望,朝野共之。但时不可为,豪杰无从着手,真不若在山之乐也。”[4]782而他在回乡后所作的《答黄无净祠部》中也说:“弟往在邸,尝与伯修曰:‘今时作官,遭横口横事者甚多,安知独不到我等也?今日吊同乡,明日吊同年,又明日吊某大老,鬼多於人,哭倍於贺,又安知不到我等也?’以是无会不极口劝伯修归,及警策身心事,盖深虑朝露之无常,石火之不待。不幸而不待者果不相待,痛哉!”[4]793可知在朝廷做官不仅身心煎熬,还会因“横口横事”惨遭陷害。因此袁宏道此次辞官不仅为追求自由清闲的生活,也基于一种对朝廷的恐惧情绪。
万历三十四年,袁宏道又做吏部侍郎,虽不久辞官,但后又入京做官,直至万历三十八年请假归乡定居。袁宏道这样来回折腾多半是为了维持家计。在晚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金钱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袁宏道家中连最基本的糊口都越来越难维持,袁宏道作为文人,“在所谓的抗争与消极、进攻与颓废、清高与世俗之间,还有好多的实际考虑”。[6]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也就是说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从事生产实践的现实的人,个体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个体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袁宏道极其向往自由,但他从不标榜自己为名士,做一些疏狂自私的行为,在需要承担家庭责任时他也不逃避。他在《刘行素仪部》中说:“弟拙懒之性,最宜山林,而饥寒所迫,亦时有元亮叩门之恥。”[4]1263在《于刘云峤祭酒》中说:“弟山居全无长进,今秋尚当强颜一出,然酸迂成性,虽出何补?孟夫子所谓‘为贫而仕’者也。”[4]1595更直接点明了他为贫而仕的事实。袁宏道的这种做法看似与他追求的自适境界相违背,但其实正如袁宏道自己所说:“此事只求安心,便做官也好,作农夫也好,作侩儿市贾也好。”[4]1259真正的自适并不是无所顾忌,只贪图自己舒适,真正的自适是合理应对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求心安二字而已。
袁宏道在官场上进进出出,多次表明辞官的决心又多次做官,不怕为人所诟病,这既是因为他为人真诚,敢于表达,也是因为他自我意识的觉醒,对自己的生活有自觉且执着的追求。袁宏道对自我心性有明确的认知,对个人生活有自觉的追求,对自适的向往与追求是贯穿他生命始终的。他折腾一番最终仍回乡定居,在辞官回乡后袁宏道便说:“弟归来便杜门,如脱笼鹦鹉,见绿條翠蓧,尚以为笼也,入山唯恐不深矣。”[4]1627他“蔽长林而啸水石”“甘于鹿豕为伍”,[4]1256最终使自己回归到自适自然的状态。
然而袁宏道并非毫无社会责任感,他虽然多次辞官,但心未离世,仍时时关心世事,正如他在《与黄平倩》的信中所说:“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扰扰,山中人岂得高枕?此亦静退者之忧也。”[4]1611即使身在山林,也时时关注国家世事,这便体现了袁宏道的社会责任感。他所写的《摘发巨奸疏》据实直陈,对朝廷官吏的各种丑恶现象一一进行批判。万历二十七年湖北税监陈奉鞭笞官吏、恣行威虐,导致民不聊生,他对好友改善民生的举措大加赞赏:“今兄灼见弊源,大破旧习,不耗国,不厉民,此正荆民更生之时,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穷奇之腹,复何所厌?荆人岂有命哉!”[4]768可见他对民生还是十分关心的,只不过他志不在此罢了,正如他说自己“懒于世事,性僻而疏,大非经世料材”,[4]1238他在给陶石篑写的信中也说:“大官谁不愿作,然大官累人,远不如闲散可以适志也。”[4]264可见袁宏道追求自适是出于对自己心性的认识,他辞官追求自适,做官也是为了追求自适。
四、结语
综上所述,晚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使得社会风气发生转变,文人开始关注自身,袁宏道在此背景下开始追求自适的生活状态。无论是为追求自适辞官,还是“退”而做官,都是袁宏道为自适做的努力,都体现了袁宏道对自适的坚定追求。自适是袁宏道一生的处世态度,“他的真诚、坦率,生于乱世而不苟同的高尚品质,他有自己的见解,决不依附于今人和古人”[8]可以说是袁宏道从对自适的不懈追求中得来的。袁宏道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主动追求自适的状态,这是袁宏道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思索,彰显了个体的生命意识与力量,推动了晚明个性解放潮流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士个体意识的觉醒,对当今内卷环境下人们的精神构建也具有一种启发作用。
注释:
①花宏艳.“情腻”与“骨刚”的悖反:袁宏道尺牍中仕与隐的矛盾心态[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88-90.
②李艳丽.论袁宏道复杂心态的形成及表现[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6):67-70.
③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90.原句为:“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