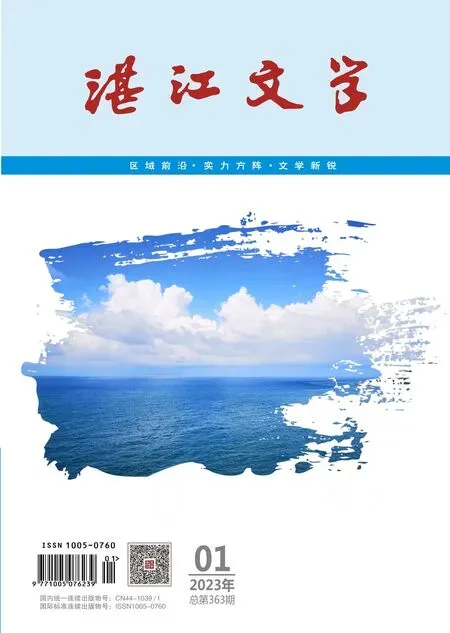时间的锯末或铁屑
◎ 董喜阳
东北的冬季带有预约的姿态提前到来,匆忙的人们纷纷袭上笨重的皮袄,像是给久别的时间举办一场华丽却低调的告别演出。清晨小路上鸟鸣的响声已成旧梦,轰隆隆启动的马达并没有黄鹂美妙的歌喉。落叶黏住我的眉梢,突然就有种想向生命诉求的冲动。
做一次精神的诉求与情感的梳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显然物质的世界给了我们更多遮掩的云障,沉淀淤积的流水漫过我的裤管,冰凉的文字爬上我的心灵。我想做一次呼喊,从我体内把冰川拔出,从黑土地里把诗歌的性灵抓起,从十月抓狂的风里聆听残忍的四月,看一看荒凉的土地上是否匍匐着T·S艾略特的《荒原》。眼前浮现出一幕精彩却又灰暗的画面: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沉默寡言的杀手,那个杀手丧生在对于这场看似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爱情里,他用生命和灵魂捍卫了情感的尊严,用一点余温庇护着精神的园地。对,你猜对了,我说的这个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
清晨的薄雾明如丝网,淡如云烟,镶嵌在上面的是我对这个时代诗歌的诸多疑问。这个清晨的冥想与思考已经给了我未知的答案。也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提起诗歌似乎有点奢侈,或是有点矫情。但我们不能否认诗歌作为一种艺术的客观存在性,我们更不能忽略诗人作为一个有名分的标签正在越来越多的进入生活的课本。诗歌应该是我们通往心灵的通道,是引导我们走向心灵皈依的小径,是在一朵璀璨的花里藏匿着的芳香。诗歌应该是诗人个体心灵的舞蹈,诗人是一个超级舞者,他的生命源泉与动力来自舞蹈的韵致与独立的精神内涵。是对人性内心深处隐私的深刻探究,是对焦躁不安生命的终极叩问。
在苍茫、寂寥的宇宙空间,诗人作为一个存在的生命个体,物质世界赋予了它更多的附属意义,更多包罗万象的哲学深意。诗人的存在与思索,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和谐统一,一首诗歌文本的创作与生成都似一条隐秘的河流,直接流淌在我们的心灵之上。我们对于诗歌﹑诗人和时代的怀疑都具有辩证的意义,它如一条无形的鞭子时刻鞭笞着我们的精神思考。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抒情诗大师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里面曾经高声疾呼哀歌:“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这句话如一计铁锤沉重的砸在我们“诗意”的心灵之上,能不能给丧失诗意主动性的时代与诗人砸出个痛彻心扉,砸出个痛改前非,还是值得我们探索的话题。但这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什么才是诗歌或是诗人终极的宿命成为了时代的强音。
诗歌终究不是低俗劣质的商品,不是可以让人任意剥削的产品的剩余价值。诗歌不是对现实的遮蔽,不是对生活真谛的悬置,更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夸张与隐喻。不是美妇脸上千篇一律的粉饰,也不是觥筹交错中附庸风雅的话题,诗歌应该是上帝留在宇宙中最后的一点空白,需要我们用精血与灵魂的雨滴浇铸的空白,这段空白使得诗人的生命具有了真实的意义。
天津大学教授马知遥发在《星星》(理论版)的文章《中国当下诗坛病症解读》,里面曾提道:“当众多这样可以模仿的‘情绪’和‘才华’出现时,就成为当代新诗发展的灾难。那些千篇一律的自抱自怨,那些自叹身世的凄婉,那些融入乡村中的陶渊明式的假抒情,都让诗歌离开质疑和追问的精神很远。诗歌成为主流审美的同谋者,成为文化消费的策划人。”这段话是发人深省的,这是作为一个有道德良知的诗歌理论家对中国新诗发展诟病的一种解答,这是来自上面的声音,同时也使得新诗的创作有了更为明确的文本方向。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劳作,它的进步和催生离不开诗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双重结合,文本的架构是在诗人不断与生活发生对接﹑碰撞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诗人在深切的关注现实生活后激发的,灵魂的火焰,它的燎原之势是对当下生存现实的延伸认识。诗歌就是诗人与生存环境发生一点具有神性色彩的关系后的符号,这种符号是诗人生命个体存在过的真实反映。诗歌来源于现实生活,必将回归生活,它是生活的关照与呈现,是醒着人的声音。
纵观西方的诗歌文本多数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宗教是某种特定意义上的哲学,诗歌的神性写作和达到神性境界的诗人多数把对于基督的信仰与诗歌的信仰归结,在基督这个更广袤的思想沃野里寻找文本与现实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必然会在日积月久的跋涉里得到印证。“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这是一个具有虔诚与忠贞信仰的基督教徒对于上帝的呼喊,因此我想诗人也需要这种对于诗歌艺术的呼喊与拉近,我们需要这种诗歌的心灵。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伟大的主宰,从而诗歌也应该带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能唤醒熟睡的人们,能打破沉默的世界,给冷淡的世俗一点精神的慰藉。想到伟大的基督教的布道者与殉难者,如穆迪﹑司布真﹑宋尚杰等。他们都是有信仰与灵魂追求的伟大之人,那么诗人是不是也是某种诗歌道路上的守望者,我们是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布道家,而这个“道”是具有灵魂意义层面的诗歌之路,我们的诗歌创作是不是可以比喻成“灵魂朝圣的旅程”?当然,在这个伟大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带有血泪的诗歌创作的文字都是我们可以擎起的照耀灵魂的精神火炬。那些带有光亮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语)地,是一个可以为我们的生命画上一个圆满句号的所在。
这样说的目的显而易见,并不是在夸夸其谈诗人的伟大或是诗歌艺术的伟大,这种伟大与渺小毋庸置疑在现实里都有自己的合理位置。而关键是我们作为诗歌的创作者背负着这些所谓的荣誉的光环到底为诗歌做了什么?仅仅是语言上的赋予或是脚本上的说辞?那样作为诗歌语言存在的缔造者,诗人的意义几乎等同于零。众所周知,零惟有和实数结合在一起才有它独特的命题意义,而如果诗歌可以比作零的话,那么所有的实数都是一个伟大且朴素的词:灵魂。在诗歌艺术上的坚守和站立并不是以你创作了多少数量的文本为依据的,也不是以你创作了多少年的诗歌而定义的,它是看你在真正意义上的诗歌道路上行走了多远的距离,这不单单是时间的概念,更是空间的位移。诗歌的半径辐射了多少距离我们生活的现实才是我们创作的终极意义。
对于普遍存在的事物,我们常常意识不到。包括我们的经验性写作和带有旨归性的阅读,没有什么比写作的经验更加普遍,更加不为人知,比如说诗歌创作。在诗学交谈中,我们很少谈论自我的诗歌文本的构建性,以及作为一个独立社会单元的差异化问题。
尽管今天,我们不再把诗歌创作和艺术视为一种模仿,却很难摆脱根植于我们语言日常行为习惯中的一种看法:认为诗歌是某种现实,它应该先于诗歌的搬移和再现。有人说诗歌是诗人的一种最简单的情绪宣泄和表达,是心中字词对于自然之景的描摹和反应。有人说,诗人是世界中最高贵的精神贵族,它只是活在自我的诗意世界里。但在我看来诗歌和诗人都是宇宙中一个分子,是朴素的事物和生灵。不同的是,诗歌文本作为诗人的脑力劳动和精神劳作就具有了生命,它是诗人精神世界对于现实生活的关照。单从这一点去思考,诗歌折射出的是诗人的精神世界,文本是它对外交流的窗口和身份证。
诗歌创作是诗人的思维、情感与秉性综合素质的体现,是其思想、意趣、学养等方面的彰显。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劳作,必须要具有点化历史、引渡众生、呼唤神圣的全部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诗歌是诗人才思和语言逻辑的产物,是情绪思维与自然建立的一种微妙关系。华兹华斯说;诗是起于沉静中回味得到的情趣。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纳兰性德时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诗人们以人的独立的精神站出来歌唱,诗无疑是语言上的艺术,是生活、是直觉、是情感,更是诗人“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格体现。“诗可以唤回某种失去了的永恒的东西”,通常我们能在一个文本中找到语言的各种语调,说明阅读和创作思维的多元化。
《一首诗的诞生》是我近期创作的一首五十行的略微长一点的诗歌,一首诗歌的诞生,让“受述者”和阅读者缩短了我们与想象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那些文字展现了世界之间的一切差异,诗人把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片段加工制作后,又归还于生活,并以诗歌的形式让人们看到了心灵世界盛开之花,扩大了我们的精神视角。
一首诗歌的诞生不像地震、海啸和泥石流,更不像世纪末的悲凉那么简单,来得肆无忌惮。首先诗人是常人,并不是长满羽翼的神,他具备与众人一样的、甚至更为敏感的道德和良知。他努力寻找写诗的灵感,对生活中美好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和关心,有一颗敏感而纤细的心。一个诗人无非想通过一首诗歌来反射出内心的精神与理想秩序,告诉人们整个意识形态的准则和方向。他涉及当下的事物,并永远转向不为常人所知的陌生领域。
一部韩国的电影《诗》里面说宗教对于主人公李沧东是很重要的宏观背景,其实我的这首诗歌里面无不浸透着宗教哲学,它是诗人从人性世界向神性世界进发的波纹。与宗教审美心性相通的语言,对传统诗质的再造和叙述性话语之诗性资源的有效挖掘,让诗歌的现代性在文本里体现的更加圆润和丰满,找寻诗歌深处的悸动,并把它作为自我精神世界的艺术关照,是我创作这首诗歌的初衷和归属点。艺术的眼睛不是被动的眼睛,不只是单纯的接受,记录外在事物的印象,艺术的眼睛是建设性的眼睛。
把宗教语言和伦理哲学引进诗歌是一种探索,因为诗歌不是欧美的,她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一双属于自己的鞋,能不能找到是一个问题,找到了合不合自己的脚则又是一个问题,索性我们在做有意义的探索和找寻。我的诗歌文本从外在形式到内部语言,从表层肌理到五脏六腑,没有莽汉主义和口语化的影子,也不具备超现实主义或是先锋文本的味道。它只是诗人对于自然世界的一次涂抹,是诗人自我精神的一次焕发和扬弃。每一种语言都是在某个概念系统里的具体表现,这一概念系统包含着知识世界的某一特定分析和解构。我希望我的诗歌语言带有透彻的批评、带有向下的挖掘,而并不成为形而上学的想象的世界。“为了一首诗的诞生,我向朴素的事物跪求/把我的双脚安歇在宽阔之地/即使咒骂、轻蔑和无厘头的讥讽,我的诗心/不会如森林般降落低谷,成为卑微的落日”,诗人可以在对于语言的使用中获得新生。所以阿恩海姆说,诗歌的创造,其实就是从一种极其普通和自发的经验世界方式中发展和衍生出来的。是的,我们知道诗歌语言王国是一个充满着强烈而丰富表现性的世界,也正是因为表现性,才可以把诗歌语言和普通语言做出比较明确而严格意义和形式的划分。
为了接受更多阳光闯进身体,我把办公室对准窗口的位置,我希望自己每一天都像阳光下的向日葵,金黄灿烂、籽粒饱满。向着有生存意识与精神结构的方向,不会向任何季节的风迫降。不让无辜的时光遮蔽写作,或是扼杀在写作的水中生出的芽。我时常需要自我淬炼、洗涤、淘刷,我想扩大心胸,让阳光在水里生长。即使冬日袭来,心中的稻谷也会在禾场上倚马可待。在安静中你能看清自我的脸,是否上帝亲手为你建造的。
通常惯性的阅读与抒写,我们是在内省自己,也是在甄别他人。我们的文化认同与诗学归属将达到一次井喷,一次寒夜里的高潮。我们通过阅读与写作来放慢生活,来减少世界缓慢的孤寂之感。安静的劳作具有效果,我们在缝制时间、织补家园。时光插图时而明亮、时而暗淡,被时间的追逐令人沮丧和痛苦,在时光的背后,赶制时装的针抖落一次安静。诗人是潮湿的。他自己寂寞的湿润着,也试图让所有人都进入雨季。拧干生活的汗水,在阅读与书本里,我们遇见未知的自己。在水边,站成淑女恬静的模样,散发出早上面包的气味,如木头在工厂里的火化一样刺鼻。在对岸,咀嚼的嘴就在唇前,为诗歌的路打上时尚的标签。不管文本是什么牌子,失去安静的过程,必须经历打折出售的惨淡。
被香烟点燃的夜晚,连夜晚都抽出滋味来。它向生活致敬,梦在河里游着,没有睡醒的岸停靠,我们只有一直寻找破口。突围需要勇气与力量,何里而来的坚强?当肉体无能为力,只有寄托于精神利器。在土地干裂的表层,蟋蟀伸着懒腰,每一个动作都那么鲜活。
我要写一首诗,不被外界认同和打扰的诗。要注册商标、冠名出售,在单薄的货架上鼓掌,用孤独的油漆涂抹。并在词语之间拽出迷乱、冷漠、堕落与泥泞。没写一首诗,我都一手打字,另一只手时不时的触摸良知。在心脏的位置,温热的心跳和纵横的鲜血交织。它们像潜伏在心底耸立的电线杆,一条隐秘的河流经过,沉淀起岁月圆润的羞涩。
为什么偏要写诗?为什么偏是诗歌?安静中的世界其实能迫使人思考,像雨。雨令人烦躁,但雨也让人清醒。写诗更直接、通透,或是更酣畅淋漓、情绪外漏,请把最好的时光都镶嵌在诗歌里,这像一种祈祷或是哀求。“A prayer for the wild at heart,kept in cages”,这是安吉丽娜·朱丽左臂文身,大意为心脏野生祈祷,不停地在笼子里。或是我们在樊笼里,用野生的心脏祈祷。肉体的不自由和心灵广阔的天地无关,内在的尊严和诗歌文本一样,带有光辉的气质、光荣的信念。在安静中写诗,其实需要这样的理由。
和诗歌有关的事物都值得期待,它能让你的灵魂暂时躲避灾难,心口上的刀光剑影。我们或许经常在诗歌的地域里投放星雨腥风的原子弹,在诗歌里快乐常有,悲伤常在。但悲伤带有喜剧的色彩,悲伤是为快乐镀上的一层情感外衣。因为安静中的悲伤是练达与机智,放任自由和洞察生命,我喜欢这样的悲伤。这样的安静与悲伤使得双脚穿越洼地,不沾染肮脏的泥土,油菜花开出星辰,像天空被雷声撕裂的印痕。写诗是为了寻找安静,可以这样理解。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名句说:“我心中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棒极了,这就是安静的气质与唯美的陈述,在心灵之外有一个广袤的世界。
生与死都需要安静。哭着来,笑着去。轮回的树上结什么果实,在于我们内心的动机。爱与眷恋也需要安静,如果为生存忙碌焦急,不如暂时安静下来。吮吸一口月光也是好的,何必着急。无论或快或慢,我们都每天走在赴死的路上。到头了,你想写诗、想安静,那得看上帝的心情与怜悯之心了。
杜拉斯在《情人》的开场白里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美在安静中,拥有优雅的光芒,在安静中写作,我们彼此怀念,不是虚拟之云的相互遥望,是真实之手的对撞、碰击,最终完成一次生命的激越……心灵的震颤在瞬间完成布道,一种诗意的河水决堤。愉悦和博大的自由经过我的庄园,来自源头的奔涌无法遏制。
一个少女就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一厢情愿的让她成为诗意的元素。就像普希金在诗歌《致恰达耶夫》中辽阔的诗行:“再见吧,自由的元素”。一首诗的诞生是如此的简单、婉约、美好、空灵,富于韵致,孤独的感觉器官和五脏六腑翻滚的想象力。一首诗和一首歌一样,应该电击心灵,像一把匕首从喉咙直接抵达心房,在平淡如水的光阴中产生奇绝的力量。
在喧嚣中的坚守,是著名作家蒋夷牧说的话。用来形容和隐喻我们生存的环境和创作的时代背景似乎恰如其分。其实,喧嚣不是这个时代特有的词,有声音的地方就会有喧嚣,就会吵闹。“制造声音,抑制喧嚣”,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诗人和诗歌作品。当然,是一种能够力透纸背的声响,一种穿越玻璃窗遥远的锐利,让听到的人如蜂蜇人一样的疼。
不夸张的说,诗人有着敏感的神经系统、强大有力的听觉意识、高难度分辨率的视觉感官。当他们敏感的耳朵和眼睛在现实的“场”内饱受折磨,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抗议。诗歌创作是他们强而有力的武器,他们试图通过感性认知和理性剖析,来深刻的接近这个尚未被全部接受的世界。很多时候,他们把渺远的想象力、视觉、听觉、理性思考从敏感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开始随意的精神游走和有机的秩序打理。
诗意原生态和在喧嚣中的坚守,显然不是占领山头的标语,拉帮结派的盟约,更不是诗歌创作中“醒目的广告词”,它是一种态度、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种敢于和流行风潮对抗的坚韧品质,一种“身居闹市,自辟宁静”的顽强进取精神。原生态就是要剔除诗歌之中的尴尬、荒诞、意外,甚至是多余的炫耀和技巧,以直接敏感的情感、有效节制的抒情、从容厚重的叙事为中心支点,让一首诗歌要拥有时代节奏感、立体画面感、多元有机感、高古脱俗的格调感,疏朗宽博的胸怀和跳出孤独自我的单调抒情,这才是诗意的目的地。
在喧嚣中的坚守需要寡淡、甘苦自知、冷暖自知的灵魂的独行。其实,“诗意原生态”和“喧嚣中的坚守”都少不了“淡”,寡淡、平淡、冲淡的品格与气象。周国平将“以平淡为散文的极致”作为自己散文创作的最高准则,苏东坡也曾说“寄至味于淡泊”,宋人梅尧臣有诗句:“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如今,面对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一笑而过的滚滚红尘,网络通途时代的亿万读者,“气象峥嵘,五彩绚烂”的流俗现实,我们将如何管理自我内心,修剪诗歌的枝丫?惟真性情,真学识,真精神与真生命体验方可见真世界。
回想自我的诗歌创作,有没有一首诗歌“惊动了读者的智性”,叫醒了读者沉闷苦涩的耳朵,吸引他们一目十行的阅读陋习。诗歌应该是没有对立面,没有任何一种事物会成为另一种事物的对照,诗歌的参照系就是自我内心,遵从自我内心的写作。不刻意求独特,不刻意求苍凉悲愤,诗歌里没有绝对的意气风发,没有绝对的豪逸翘楚和雄杰。诗歌创作需要对生命不失去热情,多生活充满热爱,更需要无时无刻不惊醒的灵魂的敲打。
周国平说,每个人只有自己寻找,才能找到它的上帝。太阳底下的河流皆都甘甜解渴,惟诸君自品方可知晓,勇敢的面对自己吧,那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因此,我在诗歌中这样写:“为了一首诗的诞生,我的年岁矮窄如手掌/窗口伸进来的月光引发霍乱/一通走失的光景是铡刀撕裂稻草,它咀嚼着/如羊群切慕溪水。有一天,恳求神抵不会让/诗歌随着我的名字灭亡”,诗歌创作中过分的修饰,可能有损自然,显得做作;过分的雕琢,可能有损个性,显得俗气;过分的夸张,可能有损和谐,显得不伦不类。不可浓艳,不可枯寂,应该是一首诗歌诞生的必要条件和有力补充。
“一首诗的诞生不是吹出来的,不是/风摆动水面坚固的波纹。它应该比牛犊的/跳跃更为艰难。如难产的妇人一样心酸/那些暂时安静的词语,穿越死荫的幽谷/孤独、嫉妒和冷漠的群体爬上纸页/它们绽放,像生命和花朵,是恩典和膏油”希望诗歌的时代没有尴尬的结局,更希望自我的探索和挖掘具有警觉的力量。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中国传统节日:九九重阳节。公交车如狭窄的暗道在空气里穿梭,我仅是里面一个可以呼吸的生灵,这种生灵本身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也想在未来的未来含有一点地域的魅力。吉林省是我的故乡,因此我想说点吉林的诗歌。
水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故乡情结,诗人尤甚。我们的创作或多或少都葆有故乡的灵气,带有故乡挥之不去的温度。大家耳熟能详的艾青的“为什么你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每当细细品味吉林诗人的诗作时,我的内心总会不由自主泛起一份感动,也不由自主会想到艾青的这首感人肺腑的诗。在我的潜意识深处,它们之所以能够引起我的相似经验的共鸣,就来源于一点,那就是他们诗歌当中共同涌现出来的那种对于土地(或者土地的隐喻)的发自肺腑的感情。我从大学毕业一直流落异乡,在异乡的街头无数次的眺望故乡的大山,想念着故乡的诗人,关注着吉林诗人的创作态势,我想我是个有着诗歌根的人,这种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情结。
记得早年看过的一本书叫《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他的作者是云南丽江少数民族诗人鲁若迪基。那个时候我就深切的感受到只有故乡的一草一木才能不断激发我们创作的灵感,产生生命底层的共鸣。鲁若迪基是那种深得故乡“土地根性”滋养的诗人。他的诗关注的是故乡小凉山的土地、土地上以“少数”命名的人群;所表现的也是那些基本的事物和基本的情感。他是一个因为要去“守望”所以对守望的对象忠贞得近乎痴情的诗人。吉林诗人老中青三代人的名字如一抹惊鸿,掠过我生命的天空,进而点亮了吉林的苍穹。他们的创作与坚守满足了我对故乡情感的表达,那么多我想说还来不及说或是根本说不出来的感情,他们的文字充满另类的诗意,在这片雄浑的土地上长出一双双翅膀,带我翱翔在深邃湛蓝的夜空。我只是想说句,有你们真好!
地域诗歌或是诗歌的地域性并不是乡土诗歌的全部或是简单概括,它只是以诗人的生存环境与地理创作位置定义的。他们的诗歌浸透着东北地域性的雄浑,博大﹑辽源﹑粗粝,并带有深邃的血性,那是东北特有的土壤赋予的诗意的气场。清新自然淳朴却又不乏灵气与情趣,甚至思想。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情不自禁的想到了广西诗人的诗句:“故乡是一纸生死契约在人生之处就签上了/我的姓名/故乡是一杯浓酽的茶在舌间在心头/轻轻润着。”故乡的诗歌与诗人会一直陪伴着我,还有我那身上一生都圆不了的乡情。
诗人鲁若迪基说:“我的终极目的不是要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有名的诗人,而是要成为——‘民族文化的守望者’,就像美国作家塞林格笔下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在诗歌题材和情感日渐私人化和鄙俗化的当下诗坛,鲁若迪基的这份追求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可是,但丁说过,诗人是那种善于走自己路的人。现在,鲁若迪基用他的诗集《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向我们证实,他是一个善于遵守诺言又勇于直面自己道路的诗人。而吉林诗人也在身体力行的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诗歌的热忱与追求,诠释作为真诗人的生活与性情,这是用灵魂爱着诗歌的人。流逝的岁月向我们证明什么样的诗人与诗歌文本才是这个时代的需要,才具有灵魂的精神向度。也许真的如我惯常梦里的景象一样吻合:吉林的诗歌春天并不远。
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是需要诗歌的,都是有土壤供给诗人的,只是太多的流云雾霭遮蔽了诗人的本性,阻挡了人们或是诗人自己对于本我的深刻认识。但是看到这么多坚守诗歌阵营第一线的诗人们,未来定会昭示着希望,东北诗歌的奔跑已经在路上。电影《这个杀手并不冷》已经进入热播后的冷静思考,而我们时代的诗歌,东北诗歌的局面是不是也应该升温,也许只有到达一定高度之后,诗人才会知道什么样的空气适合他自己。
而我在这个意犹未尽的清晨只想说一句:这个时代,诗歌并不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