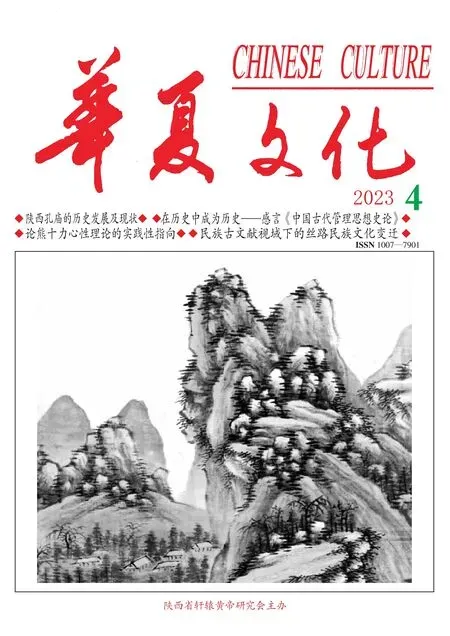史观:“外科”与“语言学史”如何沟通
□薄守生
中国语言学史研究主要涉及语言学学科,还涉及一系列的“外科”。这些“外科”中,关联最密切的就是中国历史学科,其他的还包括中国文学(语言与文学的互动)、政治学(对语言本体的重塑)、经济学(语言政策的选择)、哲学(如何处理“语言关系”)等等。
在学科的沟通、互动方面,这些“外科”与“语言学史”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这些障碍、误解,常常与“史观”有关。
一、“语言进化”的表述方式不恰当
在语言学专业著作之外,“语言进化”“文字进化”等表述方式多见,例如说“汉语处在人类语言进化的初级阶段”。按照语言学的现代观念,那是错误的表述方式。
在语言学史上,“语言进化论”曾大行其道,这大概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的发展有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曾深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语言进化论”近乎是一种比附,这种史观又被称之为“自然主义语言观”。现在,我们一般称之为“语言变化”(在侧重于历史进程时也被称之为“语言演化”),以区别于“进化”和“退化”。这个问题可能与“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变化的评价”有关(薄守生、赖慧玲:《区域视角:中国语言规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在把“语言”与“操语言的人”关联起来时“,进化”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词,这正如除了生物学家以外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与猴子放在一起比“进退”一样。
“文字进化”常常被用于比较世界上不同文明(民族)的文字体系,例如,把“形意文字→ 意音文字 → 表音文字”看成“文字进化”或者“文字改革”的方向。但是,现如今已经跨越了“文字改革”的时代。“汉字演变”是我们习惯使用的表述方式,“汉字进化”这种表达自古至今都不常用。
二、概念与词语:官话、国语、普通话
概念与词语不同,即使不是在哲学(逻辑学)领域,我们也不应该轻易混同。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它们简单地放在一个“共时”层面来理解,词语可以跨越历史(纵然有古义、今义之别),概念却包含很强的历史维度。在“语言学”之外,概念与词语的区分可能没那么困难、模糊,因为它们在“语言之外”,因“内外有别”而显得比较简单。然而,官话、国语、普通话、方言等本身就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它们同时存在于“语言之内”和“语言之外”,所以很容易被误解。
在学术上,我们需要使用各种概念。官话、国语、普通话、方言都有明确的时空定位。“官话”一般只指明清官话。至于“北方官话”“西南官话”等,它们只表示某一种方言,而不是作为“共同语”概念理解的“官话”。“国语”在中国大陆主要用于晚清、民国时期,与古书《国语》无关(“古书《国语》”或者适宜于改为“古书‘国语’”,不特指专书,只是泛指某本书)。在古代,“方言”可以指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外国的语言。方言在历时变化之后“方言这个词语”可以不变,但“方言这个概念”却早已不同。作为概念或者词语,“方言”都非常复杂,并且它还涉及政治学的内容(比如说,“民族”“国家”对方言划分的影响)。有人把“方言”词义范围的扩大、缩小归结为“中国古代本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林翔:《论“方言”概念在近代中国之演变》,载《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民族国家”这一个词未必好用,这主要是因为“方言涉及政治学的内容”。
在“国语运动”时期,“国语”只是一个虚概念,实际上还不存在(有名无实),所以胡适等人要求人们赶紧去“造”国语。与此相似,“古代‘存雅求正’的‘官话’只是一种‘意念上的存在’,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实在不好说古人在‘意念上’究竟有几种官话”(薄守生、赖慧玲:《中国语言学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第21页)。定义(内涵)不统一的概念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所使用的词语却可以是同一个词语。
三、文言(文)、白话、口语、书面语
口语与书面语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它们的区别理解得太过绝对、水火不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读书人看重的是书面语,普遍轻视口语。近年来,语言学进一步重视口语研究,有人误认为“口语和书面语最终会完全同一(传统意义上的书面语会最终消失)”。这种“同一(消失)说”抹杀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对立统一,其实“口语的书面化”和“书面语的口语化”相互依存,是能够相互转换的。甚至可以说,只要人类仍旧使用文字书写,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永远都会存在,只是它们的差异可能会减小、“相互转换”可能会越来越快捷。通常,书面语包含了反复思考、斟酌、修改的过程,而口语交流的即时性、线性常常容不得人们反复修改、不停地纠正。当然,古代的书面语(文言文)因其具有仿古、复古的倾向,直接模仿先秦书面语的程度更深一些,而“口语的书面化”程度可能更浅一些,这涉及文言和白话的区别问题。
但是,文言和白话没有绝对的界限。特别是,“白话”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区分标准,以至于胡适“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文言主要是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以及后来仿古的书面语。大概,古白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古代的口语,五四新白话的一部分成分接近于五四时期的口语。
近代以来,人们在提及“言、文分离(文、言分离)”时,强调“书面语”与“口语”的背离,强调的是“文”和“言”的冲突。如果按照这样来理解,“文言”一词在构词上的两个词素“文”和“言”就前后矛盾,即使是在后面再加上一个词素“文”组成“文言文”也无法避免这种自相矛盾。所以,我们或者可以考虑复以旧称“古文”一词,来代替“文言”和“文言文”这两个词。近百年来,著名学者周作人、魏建功等人都常用“古文”一词,他们似乎不大愿意使用“文言”一词。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国语文学史》基本上属于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这导致人们产生了“白话”等同于“国语”的误解。事实上,“《国语文学史》由黎锦熙等人组织出版,出版时并未征求作者胡适的意见,未经作者胡适同意就出版了”(薄守生、赖慧玲:《“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逻辑辩证》,载《南宁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这么重要的史实常常被“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者所忽略。
在诸“外科”中,文言(文)、白话、口语、书面语等常被用作“普通名词”(而非专业名词)。特别是,很多历史学研究者对它们作通俗的理解,称述比较随意。
四、先后与轻重:史观、史论、史料
可能是受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影响,长期以来,某些语言学史研究者把“学史”与“学理”分开——那是片面的做法。其实,“学理(史论)”只是“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的语言学史研究,应该是史观、史论、史料三者融合统一,缺一不可。
在中国语言学史的相关研究中,“史论结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观念,值得再三地强调。但是,在中国语言学史研究领域内(在此仅限于在此领域内进行讨论),“史论结合”、“学史”、“学理”、“史论”、“史料”几个名词容易引起误解,我们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学史’与‘学理’并不是对等的概念,‘学史’包含着‘学理’,但‘学理’并非仅仅归属于‘学史’,任何一项研究都应该包含‘学理’的内容。我们指出‘学史’与‘学理’不对等,同时强调不能把这两个词对立起来,不能把‘学史’与‘学理’看成是两条各自分布的平行线。‘学史’包括‘史料’和‘史论’。‘史论结合’中的‘论’是指‘史论’。但是,〔‘论’是指‘史论’〕之中的‘史论’这两个字是一个词,而‘史论结合’四个字中的‘史论’这两个字是两个词,也许,‘史论结合’如果写成‘史、论结合’可能会减少这种误解。‘史、论结合’中的‘史’,主要是指‘史料’。在专业领域,‘史论结合’习用,一般不存在误解,一般不必写成‘史、论结合’”(薄守生:《〈中国语言学史理论研究〉后记》,载《西吴史学》2023年第1期)。对此,那些侧重于研究“语言本体”的语言学家总觉得拗口,总是不能理解上面的这一段话,这让人十分遗憾。对于“史、论结合”的不同理解,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史观”问题。
史观的选择,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史料的判断。在细微层面,我们应该把“正确的语言学观念”作为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史料”之一,这不应被诸“外科”忽略(由于“语言学”冷僻、艰深、枯燥,各个“外科”学者避而远之)。在语言学之内,许多学者对于“史观”二字很无知,这也对语言学史研究不利。
比如说,关于共同语史的正确的观念就应该受到重视。人类起源是单一起源还是多源的问题,会影响人们对语言发展演变规律的判断。当然,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同语”多侧重于探讨《切韵》以降(隋唐以来)的共同语,这与人类起源类型的关系不大。
无论是“外科”,还是“语言学”,史料都是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基础,这从无争议。在当下,我们尤其要重视“史论结合”,因为这是在此之前研究者的弱项、短板。作为各个“外科”,特别是“历史学”学科,所秉持的史观中应该包括“语言学观念作为史料之一”这一“史观”。在语言学“之内”,人们不能不明辨“史观”,但“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为宜。这样一来,诸“外科”与“语言学史”就能够得到较好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