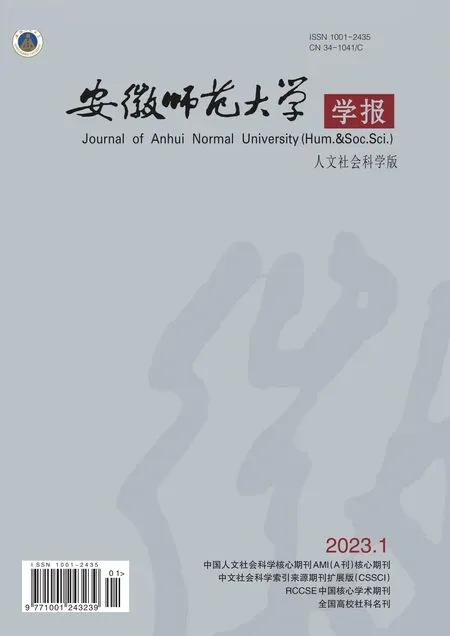身体哲学视域下身体形式完整权研究*
申长慧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275)
自古以来,身体就是哲学和法学研究的中心问题。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二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中规定了身体权的独立地位和丰富内容。身体完整系身体权的重要内容,然而,身体完整概念具有不确定性:完整话语所保护的身体本质处于含蓄和变动状态。确定身体完整的实质内容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体权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以来,意识现象学逐渐被身体现象学所取代,身体哲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代表,物性的肉体和灵性的主体在身体中结合。身体成为主体,而不仅仅是客观的对象物。身体权以身体为核心展开,对身体权的研究似乎也在有意无意地回应着哲学的身体转向。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二章第1010条规定了三种性骚扰侵权方式,包括以肢体行为实施的性骚扰;①当然,以言语、文字、图像方式实施的性骚扰侵害的不只是身体权中的身体免受触碰权,还使他人的精神安宁、平和、宁静利益受到侵扰,同时侵犯了身体权中的精神完整权。第1011规定了非法搜查身体侵权。这对身体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肢体行为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和非法搜查身体的行为,直接侵害的是在场的身体。基于身体哲学转向,身体作为感知主体,未经同意的冒犯性触碰行为侵犯了身体的形式完整性,即免受触碰的权利。《民法典》以反面禁止的方式对身体权进行了保护,一方面使对性骚扰的研究脱离了原来职场性骚扰和性别平等的探究路径,开拓了性骚扰构成身体侵权的探讨路径,使身体权中的形式完整权权能呼之欲出;另一方面,非法搜查身体侵权使身体的边界由物理有形边界拓展到与包括人体有密切联系的物的范围,扩大了对身体权的保护范围。但是,身体免受触碰权的内容丰富,性骚扰侵权和非法搜查身体并不能完全界定身体免受触碰权的具体内容。
一、主体哲学的身体转向旨趋下具身完整理论的嬗变
主体性问题是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对该问题的回答就是对身心问题的回答,这些回答可以分为主体为意识的意识哲学和主体为身体的身体哲学两类。意识哲学视域下的身体是客观对象,而身体哲学视域下的身体是灵肉合一的身体。不同哲学视域下的身体构建了不同的身体权。
(一)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下灵肉合一的身体
传统西方哲学中,早期现代哲学集中关注纯粹心灵,身体被纳入纯粹物的秩序中,没有能够在意识哲学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后期现代哲学突破传统意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身体对心灵的造反,肉身化主体成为哲学家关注的核心,物性的身体上升到了主导性的地位。②杨大春:《从身体现象学到泛身体哲学》,《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中身体和精神的分离与对立,无限拔高了智慧的价值,否定了人的意志、欲望、本能直觉等在认识世界和驾驭人类行为过程中的重要价值,把身体排斥在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观和审美观之外,加强了精神对身体的统治,日益导致身体的异化和沉沦,因此应当回归身体、解放身体,甚至用身体取代理性,进而认为人就是身体,身体就是强力,就是“物质性和生命性的肉体所固有的感受性、自发性、表现他者的能动性、超越肉体自身的思维性和自我性”。③张之沧:《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身体观》,《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2期。
梅洛-庞蒂用活的身体取代了纯粹意识,用身体意向性取代了自笛卡尔以来一直强调的意识意向性,用身体主体取代意识主体,确立了本己身体的优先地位:“我们已经在关于身体的客观而疏远的知识下面重新找到了我们关于身体的另一种知识,因为身体始终伴随我们,而且我们就是身体。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唤起向我们呈现的世界的经验,因为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身体知觉世界。但是,当我们在以这种方式重新与身体和世界建立联系时,我们将重新发现的也会是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身体知觉,那么身体就是一个自然的我和知觉主体。”④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Garlimard,1945,p.239.转引自杨大春:《从法国哲学看身体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浙江学刊》2004年第5期。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认为,触摸运动“不在于和意识一起发生的关系,而在于直接反应”。⑤[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4页。简言之,触觉是无需以意识为媒介而直接由身体感知的“最为直接的觉”,是我们人存活于世的本能活动,是感受生命之所在的根本。对此,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其他感觉“全都是依赖别的物,即通过中介而产生感觉,而触觉是在与对象直接接触时发生的,触觉名称的形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载苗力田主编,秦典华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有学者基于身体哲学转向的兴起,认为在人类感觉领域,开始出现了从“视觉中心”向“触觉为本”的转移,其在触觉是“最为直觉的觉”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认为触觉是“在场感的觉”“行动性的觉”“交互式的觉”“灵化的觉”。②张再林:《论触觉》,《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所谓“在场感的觉”是指不是我在触摸,而是我的身体在触摸,消解了身体的对象化属性,意即触觉是涉身的触觉,是具身的触觉;所谓触觉是“行动性的觉”,是指触觉是身体的感觉,身体是行动性之身,身体在感觉的同时即在行动之中,因此触觉不仅有最直观的“感觉义”,还有“运动义”;所谓“交互式的觉”是指,触同时即被触,被触同时即触,“我们有在触觉上构成的外部客体”——物,“以及一种同样在触觉上构成的第二客体——躯体”,正因为这种主体与客体在身体之中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西方哲学从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的彻底变革,同时使西方哲学从能受二分走向能受一体;所谓“灵化的觉”是指对身体的触碰和身体的触觉不仅是外在身体的直觉,更是内在心灵的触动,即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的触觉是灵魂化的感觉,身体是“可见的肉身与不可见的心灵的交织”,是灵肉一体的存在。
(二)身体权:边界完整到具身完整的理论嬗变
主体性问题的身体转向对身体权内容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身体不再是意识哲学中对象化的存在,活的身体通过最直接的触觉使身体成为主体的存在;其次,身体作为主体的存在决定了身体是有精神属性的,是具象化存在的,而非仅仅是以物理有形的空间存在;再次,身体作为一种运动性的存在,其在空间场域和时间场域趋向一个更为圆满的完整性时,不可避免地对外在的他者具有依赖性,需要得到国家和法律体系的承认和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身体权,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应当从仅保护身体实质完整的物理边界完整权,向将身体作为主体的具身完整理论转变。③申长慧:《身体完整权:边界完整到具身完整的理论嬗变》,《学术论坛》2020年第6期。
以意识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边界完整理论将身体视为一个有物理空间和边缘的特殊客体或对象,边界完整理论指导下的身体权以身体的物理空间和边缘的完整为内容,是一种静态的、消极防御性的权利,难以应对现实生活中复杂多变的身体。边界的概念更像是一个静态的面具,而不是生动多变的镜头,未能界定身体具身呈现的变动性。并且,边界完整理论认为所有的权利主体都以非常简单的方式拥有自己的身体,无法应对现实生活中社会性身体的复杂性。更为严重的是,边界完整理论指导下的身体存在潜在危险和暴力性特征,即将身体还原为与意识主体相对的物、客体,使身体降格为一种附属装置或躯壳,消解了人的自我同一性。简言之,边界完整理论用消极的排他权铺陈了身体的边界,未能抓取到身体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以身体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具身完整理论将身体视为主体,用统一性、完整性和现实性来理解身体,从而使身体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消解了身体内部物质和灵魂的自我撕扯,从完整的身体出发来理解身体的完整性。基于此,身体作为感知主体,这个感觉不仅是肉体的或动物般的感觉,而是完整身体的全面感觉,包括人的意识和思维、情绪。恰如马克思所言:“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④[德]马克思著,中央编译局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具身完整理论所保护的身体完整性包括静态的实质完整性和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连续发展的充分性、安全性的完整性。这使得身体权中的身体完整性不仅包括身体的实质完整权能,还包括以触觉为中心的身体免受触碰权这一形式完整权。
二、免受性骚扰侵权对身体形式完整权的肯认
《民法典》颁布之前,学者对身体完整权中是否包含形式完整权或身体免受触碰权这一权能尚未形成定论。杨立新认为身体的完全或完整性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实质性完整,是指身体的实质组成部分不得残缺;二是形式性完整,是指身体的组成部分不得非法触摸,并基于此认为非法搜查身体和性骚扰侵权均属于对身体权的侵权行为。①杨立新:《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96页。但有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实施某种侵权行为,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或抚摸他人身体等,这些虽然构成了对其他人格利益的损害,因为未侵害身体完整性,并不构成对身体权的侵害。②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6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同样主张该观点的还有柳春光:《身体权概念的再界定》,《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那么,《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的性骚扰侵权,其意欲保护的法益是什么?
此外,当行为人未经他人同意,以冒犯性的方式触碰他人的身体,若该种行为并不构成性骚扰侵权,则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若构成侵权,则侵犯了他人享有的何种权利?譬如,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一:行为人以侮辱性的方式触碰他人的身体,当该种行为并不构成性骚扰侵权时,则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如构成侵权,则侵犯了他人什么权利?③真实的例子:2019年7月3日,在百度AI开发者大会上,正在演讲的百度董事长李彦宏突然被人从头浇了一身冷水。
案例二:行为人以恐吓性的方式触碰他人的身体,当该种行为并不构成性骚扰侵权时,则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如构成侵权,则侵犯了他人什么权利?
(一)以性之名的失焦:传统性骚扰界定中窄化或泛化的二律背反
性骚扰是英美法系的舶来品。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之前,美国主要是通过道德谴责的方式对待性骚扰行为,并未将其上升为需要法律解决的问题。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后,职场性骚扰开始进入法律规制,美国学者开始从性别歧视角度对待性骚扰,认为性骚扰属于性别歧视范畴。④美国《民权法案》第703条明确禁止在就业中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出生国歧视他人。该条被界定为禁止职场性骚扰的法律渊源。换而言之,在美国的法律制度框架下,职场性骚扰属于该条所禁止的性别歧视行为。但这也并非是《民权法案》颁布后的当然结果,而是经历长达十年多的不断抗争的结果。起初的司法案例中,法院并不认为职场性骚扰属于《民权法案》第703条规定的性别歧视。直到1978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针对Barnes v.Costle案作出判决,认为性骚扰属于性别歧视;1980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颁布指导原则,认定性骚扰属于性别歧视,并将性骚扰区分为交换型性骚扰和敌意工作环境性骚扰两种类型。⑤郭晓飞:《性骚扰是性别歧视吗:一个法理的追问》,《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1期。此后,美国对性骚扰行为的规制从职场领域延伸到教育领域,各国也开始了对性骚扰问题的研究和法律规制。
我国对性骚扰的立法规制起始于2005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此之前,只有个别学者对性骚扰进行了学术研究,性骚扰行为处于无法可依阶段。《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第58条规定了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行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时的行政处罚和民事诉讼救济,但该法并未界定何为性骚扰。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1条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上述法律都没有规定何为性骚扰,而且将性骚扰的受害人局限于女性,未能考虑男性和儿童可能遭受的性骚扰。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全文并无性骚扰的字样,2006年和2012年修订时依然如此,2019年发布的修订草案中依然未见性骚扰的字眼;2020年修订时在第四章“社会保护”部分增加了第40条,该条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建立预防性侵害、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第54条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性骚扰,该修订稿于2021年6月1日生效。
此外,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在第九部分的“侵权责任纠纷”的“348、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之后增加了一个三级案由“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该种界定方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将性骚扰界定为一种损害责任,而非侵权行为,不伦不类;第二,将性骚扰侵权规定在“教育机构责任纠纷”之内,限缩了性骚扰侵权的适用范围。性骚扰侵权应当是一种侵权行为,而非损害责任,其应当囊括在身体权侵权之中。《民法典》第1010条以不完全法条的形式界定了性骚扰侵权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扰侵权行为的义务,开启了我国在主观权利层面和私法方面对性骚扰侵权进行界定和规制的模式,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何为性骚扰呢?美国以反性别歧视模式定义性骚扰。除此之外,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日本也采用此种方式界定性骚扰。有些学者认为性骚扰聚焦的是“性别平等”这一世界性的难题。①单纯:《论美国反性骚扰的法治化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通过“性别平等”这一世界人权的难题作为切入点来关注性骚扰行为,有助于对性骚扰行为进行法律规制提供一个大而宽泛的进入路径。同时,女权主义法学和女权主义运动确实为将性骚扰纳入法律规制作出了有目共睹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不仅存在于男性对女性实施的性骚扰,同样包括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还包括对儿童实施的性骚扰行为,甚至是同性之间的性骚扰。以“性别平等”或“性别歧视”之名对性骚扰进行界定,只是从外在的经验层面出发,以权力压迫为后盾,过于窄化,限缩了性骚扰的外延和受保护的主体范围,使性骚扰成为一个“男女问题”,甚至窄化到认为,只有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性才会受到性骚扰。这种界定方式脱离了性骚扰问题的实质,使之成为一个敏感话题,而无法得到真正的重视。
还有一种以维护人格尊严的模式对性骚扰的界定,如1991年欧盟《反性骚扰议案施行法》正式对性骚扰进行界定:“性骚扰是指对受害人实施的,违背对方意愿的带有性意味的行为,或者在工作场所中对其他工作人员所做的不受欢迎的性举动。”这种界定方式同样有失偏颇,因“性意味”“性举动”只是行为所指向的对象的主观感受,这并未对行为人实施性骚扰的行为本身进行界定。同时,这种界定方式似乎把一切与性或性别有关的问题都归为性骚扰,如近期英国劳动法庭裁定称男性秃头也构成性骚扰行为,②Mr A Finn v.The British Bung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and Mr J King,case number:1803764/2021.甚至有学者将性侵害或性暴力等犯罪行为都归为性骚扰,导致了性骚扰的泛化,使之成为一个大而不当的概念。这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性骚扰所归属的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身体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之间的界限模糊化。过于关注“性”,似乎指称的是“情欲本身就是骚扰”,使性成为不可言说、应当远离的特殊领域。对性骚扰的口诛笔伐不仅未能阻止性骚扰的发生,反而阻碍了性骚扰的解决,媒体大众带着异色眼光,竭力寻找控诉者行为中的不足,悬置正义,使受到侵害的人畏惧控诉、无力诉说,强化了性歧视。同时,这也不利于性教育和性话题的正常开展和讨论,被喊停的身体教育或性教育屡见不鲜。
在性骚扰成功纳入权利侵害的法律规制之后,仍然以“性”之名关注性骚扰,一方面过于强调性别平等或性别正义,不利于对性骚扰行为进行一个普遍的、全面的界定,容易忽视同性之间的性骚扰行为,无法解释儿童遭受的性骚扰行为。另一方面,将与性相关的一切话题都扩展到性骚扰的界定中,模糊了性骚扰问题的实质,使之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无法得到真正的重视。以性之名关注性骚扰导致其认定上窄化与泛化的同时存在,使之陷入二律背反的失焦困境。只有回答以肢体方式实施的性骚扰侵权背后所要保护的法益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才能对性骚扰的部分界定给出准确的回答。
应该将性骚扰从男女问题中解放出来,与其以“性别”之名关注性骚扰,不如以“身体完整”为媒介关注性骚扰。身体,人皆有之;性骚扰,人人皆可能会面临,实施性骚扰者也可能会成为遭受性骚扰者,两者之间并不以性别为界限。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对性骚扰实施方式的界定是较为全面的,性骚扰应该是以客观理性人的标准来评判,即行为人以肢体行为对他人的身体进行触碰、抚摸,以言语、文字、图像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实施的使处于当时情景的客观理性人可以感受到行为人的性暗示、性挑逗的行为。
(二)聚焦于身体:免遭性骚扰侵权与身体形式完整权的良性互动
首先,免遭性骚扰侵权使身体形式完整权成为一项独立的身体权权能。
在身体免受性骚扰侵权被规定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二章“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之前,免受性骚扰侵权所保护的权益有三种论述:身体权说、性自主权说、一般人格权说。①王毅纯:《民法典人格权编对性骚扰的规制路径与规则设计》,《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薛宁兰:《防治性骚扰的中国之路:学说、立法与裁判》,《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3期。支持性自主权说的学者将免受性骚扰的权利界定为性自主权的具体权能,而非身体权的具体内容,②杨立新、张国宏:《论构建以私权利保护为中心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2011年杨立新在其《人格权法》一书中,认为性骚扰侵权侵害的是身体权中的形式完整权,但在该篇文章以及此后《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逻辑结构的特点与问题》等文中,认为性骚扰侵权所保护的法益是“性自主权”。认为本应专门规定性自主权,并将性骚扰侵害规定在内,将之放在身体权部分是“颇为遗憾”的问题。③杨立新:《从生命健康权到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民法典〉对物质性人格权规定的规范创新》,《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杨立新:《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逻辑结构的特点与问题》,《东方法学》2019年第2期;齐云:《〈人格权编〉应增设性自主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支持一般人格权说的学者不加推理地直接认为“对于性骚扰行为侵害的是自然人的何种人格权益,学界尚无定论,但其不属于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物质性人格权’范畴则显而易见、毋庸置疑”,建议将之规定在司法解释中。④温世扬:《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评议》,《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3期。而支持身体权的学者认为大多数性骚扰行为都侵害了他人的身体权,因此将其放置在身体权章节中在体系上是合理的。⑤王利明:《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亮点及完善》,《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王利明在2012年的《人格权法研究》一书中,认为性骚扰侵权侵害的是一般人格权,而非身体权;而在该文中,他认为性骚扰侵权侵害的是他人的身体权。参见孙笑侠:《身体权的法理——从〈民法典〉“身体权”到新技术进逼下的人权》,《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
《民法典》人格权编在“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这一章中规定“免受性骚扰的权利”,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免受性骚扰侵权属于身体权的内容。这种规定不仅具有体系合理性,在内容上也是自足的。免受性骚扰侵权和性自主权看似都与性有关,但其保护的法益却不尽然相同:性自主权保护的是权利人对自身性行为的控制权和自主决定权,即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引诱、胁迫或暴力等手段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免受性骚扰侵权所保护的法益并非是性自主权,受到性骚扰侵权的主体,其性自主权并非当然受到侵犯。免受性骚扰侵权背后所保护的法益是身体权,其中以肢体方式实施的性骚扰侵犯的是他人身体权中的身体免受触碰权这一形式完整权。
《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的“以肢体行为”实施的性骚扰,是指未经他人同意,行为人触摸他人的身体,或者强行要求他人触摸自己的身体。即便发生触碰的身体部位并非是性别特征部位,比如手、脸、颈、肩、腰等部位,都会让他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受到了冒犯,这已然构成性骚扰,即便被触摸一方未遭受任何有形的身体伤害。基于传统的边界完整理论,身体是脱离灵性的客观对象,依附于精神,则以肢体行为实施的性骚扰并没有给他人的身体造成有形的伤害,似乎不构成侵权。但若基于身体哲学指导下的具身完整理论,身体是灵肉结合的主体,是感知主体,是能“体现”“体会”“体验”和“体知”的具有意向性的身体。⑥李金辉:《身体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以肢体行为实施的性骚扰侵犯了主体对其身体享有的免受触碰侵扰的感知自由,构成侵权。基于此,身体权中的身体完整性内容包括了身体免受触碰的权利,即便行为人实施的触碰行为并未给他人的身体造成有形的伤害,但未经同意的触摸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伤害的后果。
4.1 主界面 在登录进入系统之后系统界面展示运行效果见图4,在图中可以通过工作提醒界面看到每位工程师在指定日期内应完成的工作任务,系统分别设置了巡检提醒、计量提醒、维修提醒等。工程师如果未完成工作任务时,提醒条会一直延续至完成工作任务才会消除。
其次,身体形式完整权扩大了免受性骚扰侵权的保护范围。
在性骚扰侵权案件中,证据收集和证明难的问题是能否妥当解决该问题的最大障碍。过于强调对他人身体实施冒犯性触摸是否具备性意味或性暗示,无疑是要受害人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增大了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同时,如果要求受害人举证证明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其自身不欢迎的行为,同样是对受害人的责难。在性骚扰案件中,要求被害人负担其本身不欢迎此类行为的举证责任之做法已经被很多国家弃用,目的在于改变责难被害人的论调。①骆东平、谭彬:《性骚扰案件证据认定之实证分析——以海峡两岸的两起案件为例》,《三峡论坛》2011年第6期。基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法则,身体触碰一般分为两类:一般禁止型和一般允许型。所谓一般禁止型是指,在两人之间没有建立某种特殊关系时,通常情况下,不能发生过密的肢体接触行为,除非双方之间作出了明确的承诺。将身体免受冒犯性触碰权这一形式完整权纳入身体权的权能,保护权利人免受性骚扰侵权有助于降低受害人的举证难度。只要受害人证明双方并不存在特殊的关系,且在行为人对其实施冒犯性的身体接触行为时,权利人并未作出同意或接受的意思表示,即构成侵权,如未经同意的拥抱可以构成性骚扰。②刘猛、徐伶、成都市一天公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案号:(2020)民申4679号。
免受性骚扰侵权使身体免受触碰权上升为身体权的一项独立权能的同时,身体免受触碰权扩大了身体免受性骚扰侵权的行为边界,降低了性骚扰侵权的举证难度,使得免受性骚扰侵权的保护范围在扩大,或者说行为人行为的边界愈加清晰。因为自然人享有身体免受触碰权,行为人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身体触碰行为,如触摸他人的腰部、手部、脸部、背部等行为,都可以根据当时的处境和周边环境被认定为性骚扰侵权,从而扩大了性骚扰侵权的行为禁止边界。
三、身体免受非法搜查权对身体形式完整权物理边界的延展
(一)免受非法搜查是身体形式完整权的必然要求
《民法典》未在身体权中规定自然人享有身体免受非法搜查之前,《宪法》(1988修正)第37条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将其纳入人身自由权的范围内;《刑法》(1979年修订)第144条规定了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非法搜查罪;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4条规定了“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将其纳入妇女享有的人身自由权的内容;1994年《劳动法》规定了非法搜查劳动者时,用人单位需要承担的行政处罚;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了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行政处罚。上述规定是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都未能从主观权利的角度界定自然人享有的身体免受非法搜查所保护的法益属于自然人享有的何种具体人格权。而在司法实践中,涉及非法搜查他人身体而未造成有形身体伤害的侵权案件基本以“名誉权”受损进行审理,有时法官在说理时将身体免受非法搜查纳入到人身自由权的范围内。有学者认为搜查身体应为隐私权的侵权类型。③张红:《民法典之隐私权立法论》,《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1期。笔者认为,这一权利应属于身体权中的内容,系身体权中的身体免受触碰权这一具体权能的应有之义。
毋庸置疑,在公开场合非法搜查他人身体可能同时致使他人名誉权受损;同时,若非法搜查他人身体导致他人行动受限,也可能涉及人身自由权受侵害问题。但若非公开场合实施的非法搜查行为呢?或者行为人怀疑他人偷盗,未经他人同意,强行对他人身体实施搜查,发现他人身上存在丢失的物品时,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涉及到侵权呢?或者在非行为人造成的封闭场所内,他人无法自由出入时,行为人对他人身体进行搜查,是否会涉及到人身自由侵权呢?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损的情形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解决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直接受侵害的权益是什么。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直接被侵害的是他人享有的身体完整权中的身体免受触碰权。基于此,无论是公开场合实施的非法搜查还是非公开场合实施的非法搜查,都侵犯了他人享有的身体免受触碰权。当然,同一侵权行为可能同时侵害多种权益,当行为人在公开场合对他人的身体进行非法搜查,在侵害他人身体权的同时,也可能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或其他权益。只有厘清最基础的权利内容和范围,才能对权利人的主观权利提供更为全面的保护。
(二)免受非法搜查扩充了身体完整权的物理边界
在身体权的传统界定中,身体完整权包括两个主要的权能:身体边界完整权和身体支配权。①申长慧:《身体完整权:边界完整到具身完整的理论嬗变》,《学术论坛》2020年第6期。身体边界完整权以身体的物理实体为界划定了身体完整的空间边界。这一空间边界的界限随着身体的物质存在的改变而相应改变,但仅限于此。而身体免受非法搜查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扩充了身体空间边界的外延。因为此时被搜查的并非仅指身体本身,也包括与身体相连的衣物、权利人持有的或与其紧密相连的任何物体,如安装的假肢、指甲上做的美甲、穿着的衣物,该物体与他人身体相连的方式使它通常被认为是该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其不可侵犯的一部分。当然,并非所有权利人持有的或与其身体相连的任何物体都可被视为身体一部分的物体,对此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因为它依靠的是一种情感的反应。
行为人实施的非法搜查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他人身体实施的直接触碰行为,如对他人身体的直接触碰;一种是间接对他人身体实施的触碰行为,主要是对与他人身体具有紧密联系的物的搜查,如口袋、夹缝等。身体免受非法搜查这一具体内容延伸了身体权受保护的边界,将与身体具有紧密联系的物也纳入到了身体权的保护外延中,增加了身体权边界的延展性。
四、触碰作为损害:身体形式完整权的独立属性
(一)身体形式完整权中免受触碰的多样态表现
身体形式完整权的内容丰富,仅从禁止侵权的方式不足以覆盖其受保护的范围。身体免受冒犯性触碰权中的冒犯性包括四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羞辱性的冒犯性触碰;第二,伤害恐吓性的冒犯性触碰;第三,性骚扰式的冒犯性触碰;第四,令人反感的其他冒犯性触碰。其中羞辱性的冒犯性触碰是以某种方式触碰他人身体为一种信息传达方式,意欲传达羞辱他人的情感,如对他们面部、身体或衣物上吐口水,或者涂抹污秽物。所谓伤害恐吓性的冒犯性触碰是一种非以伤害有形身体的触碰方式,但结合行为人的语言或其他行为,使他人对行为人触碰其身体的行为感到恐怖,担心行为人会进一步实施伤害其身体的行为。如行为人触摸他人的面部或脖子,要求他人乖乖就范。所谓性骚扰式的冒犯性触碰是指行为人触碰他人的身体部位,或者是以肢体方式触碰,或者是以眼神触碰,如尾随他人到厕所,偷窥他人的身体等都属于对他人身体的冒犯性触碰行为。
触碰并不要求行为人的身体与他人的身体直接触碰,身体触碰实际指的是因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他人的身体与某种该人不愿意去接触的物发生触碰,他人不愿意被接触的物可以是行为人的身体、地面、棍棒、药物、酒精、污秽之物等。此时,他人的身体也不仅仅是指他人的肉体,而包括他人穿的衣物或其持有或与其相连的任何物体。②[美]爱伦·M.芭波里克选编,许传玺等译:《侵权法重述纲要》,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基于此,触碰行为可以四种方式发生:有形方式、无形方式、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触碰和间接触碰是以触碰的对象是受害人的身体还是与受害人身体紧密联系的物为区分标准的。直接触碰是指行为人以冒犯性的方式直接触碰受害人的身体,身体是直接被触碰的对象,如向受害人的身体上吐口水;间接触碰是指行为人触碰的并非受害人的身体,而是与受害人身体有着密切联系的物,如行为人将秽物涂抹在受害人穿着的衣服上或涂抹在他人将用于擦脸的毛巾上,但并未直接接触受害人的身体。有形触碰和无形触碰是以触碰的媒介是有形物实施的还是以无形的方式实施的。有形触碰是指行为人直接以其身体或有形物品直接或间接地触碰受害人的身体;无形方式是指行为人并没有用其身体或有形物品直接或间接触碰受害人的身体,如拉走受害人将要坐下的椅子,使受害人摔倒在地。①Ellen M.Bublick,A Concise Restatement of Torts,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2013,pp.21-22.
基于上述情形,身体免受触碰权具体包括四种情形:第一,身体免于遭受有形触碰的权利;第二,身体免于遭受直接触碰的权利;第三,身体免于遭受无形触碰的权利;第四,身体免于遭受间接触碰的权利。②Joseph W.Glannon,The Law of Torts (Fifth Edition),Wolters Kluwer,2015,pp.6-8.区分上述四种方式的触碰,将间接触碰和无形触碰包括在内,延展了个人的身体空间,扩大了个人身体完整权的领域,对自然人的身体免受触碰权提供了充分全面的保护。
免受性骚扰侵权只能对身体免受性骚扰式的冒犯性触碰进行保护,而无法对免于遭受羞辱性或伤害恐吓性的冒犯性触碰提供保护。免受非法搜查身体侵权只是从形式上扩大身体权保护的边界,并未涵盖身体形式完整权的内容。身体形式完整权的内容丰富,免受触碰中的触碰具有多样态的表现方式。
(二)身体形式完整权的神圣宣示性
身体免受触碰权的重要性不在于其保护人们的身体免受有形伤害,也不在于保护人类精神的安宁,而在于身体本身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令人敬畏的。任何权利都是神圣的,但身体权的神圣性与其他权利的神圣性并不完全相同,身体权的神圣性在于身体的神圣性,身体作为人之为人的基础,作为人立于世的载体,与人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可以说身体本身即是人的标志。与其他权利通过某种方式彰显对人的权利的重视不同,身体作为人本身,直接体现着、承载着人的重要性。
身体形式完整权的神圣性主要体现为身体的受尊重性,即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尊重其身体,未经他人同意,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方式触碰他人的身体或与他人身体密切相关的一切物品。身体作为权利主体,有免受他人触碰的权利,有感知尊严的能力。当我们将某物视为财产权的客体时,对该物实施的触摸行为并不构成侵权,因为触摸行为并没有使之毁损或灭失,其使用价值也没有降低。但身体作为权利主体,行为人实施某种冒犯性触摸行为时,主体作为感知者,感知到了这种被冒犯的感觉,感知到了这种令人反感的触摸,感知到人格尊严的受损,行为人的行为即构成侵权。
法律无法在不同程度的暴力之间划定清晰的界限,因此有必要完全禁止哪怕是最初阶段最轻微的暴力行为;每个人的人身都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都无权以任何方式,哪怕是最轻微的方式侵扰他人的人身。任何对他人身体的触碰行为,哪怕多么轻微,都可能构成殴击侵权。③Collins v Wilcock[1984] 1WLR 1172.承认身体免受触碰权是身体完整权的一项独立权能,将为那些以有形损害结果为必要构成要件的侵权损害赔偿所保护的法益之外的利益提供了一条新的保护和救济路径。
身体实质完整权以身体边界受到有形损害为前提,比如被抓伤的伤口和被打的黑眼圈,或者是以切、割、剪等方式使身体组成部分与身体整体脱离,或者是身体外在形态的变化,或者是以入侵的方式提取身体组成部分或破坏身体完整性。④郭京霞:《未婚女体检时处女膜破裂,体检中心被判赔偿1万元》,《北京晚报》,2007年12月5日。这些行为都是给身体边界完整权带来了某种损害后果,虽然相比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损害后果,这些损害后果相对轻微,但仍属于直接有形的身体损害结果。对于身体实质完整权而言,直到损害结果出现,侵权才最终完成。对于身体免受触碰权,当行为人实施了让他人感到冒犯的行为时,这种行为本身是可诉的,并不以造成实际的、有形的损害后果为前提。因此,当行为人以冒犯性的方式对他人的身体实施了某种接触行为,这种冒犯行为就是损害结果,他人可以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寻求救济。
(三)身体形式完整权中身体的直接在场性
以“冒犯性触碰”之名对身体权的保护,乍看起来,似乎保护的是自然人享有的免于陷入羞耻、尴尬、被侮辱等精神方面的利益,可以纳入到纯粹精神安宁利益中。身体免受触碰权保护的利益当然包括精神平静、安宁的利益,如同其他具体人格权中也当然包括精神平静和安宁的利益。但身体免受触碰权不同于身体权中的精神完整权,不能被囊括于身体精神完整权的内容之中,其体现了身体的直接在场性。
第一,身体形式完整权与纯粹精神安宁利益保护的直接利益并不相同。身体免受触碰权是以身体触碰为侵权媒介,其直接侵犯的仍然是身体这个有形实体,而非纯粹精神安宁利益。第二,所要求的损害后果不同。身体免受触碰权的侵权行为是一种行为本身可诉的侵权,其不要求原告在诉讼中证明其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或其他有形的身体损害后果;而精神完整权的侵权行为是以严重精神损害的后果为侵权赔偿的构成要件,原告在诉讼中需要举证其因被告的行为而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因此,若将身体免受冒犯性触碰权囊入精神完整权的内容中,因侵权人冒犯行为的轻微性,如冒犯性的拥抱和触摸行为,法院很难判决支持权利人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从而导致权利人诉求保护的利益不能得到侵权法的认可。而若承认身体免受触碰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身体完整权的权能,则只要行为人对他人的身体实施了冒犯性的身体接触行为,他人便可基于此行为本身要求行为人承担禁止侵权以及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
五、结 语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二章规定自然人免受性骚扰侵权和免受非法搜查身体侵权,以反面禁止的方式界定了身体权的身体免受触碰权这一形式完整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利保障的彰显,是我国立法技术先进性的体现;回应了现代哲学关于主体性的身体转向,具有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同时,身体免受触碰权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在未经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以羞辱性、恐吓性、性骚扰式等其他冒犯性方式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触碰他人的身体或与他人身体具有紧密联系的附着物,确保他人身体的形式完整性。保护权利人免受性骚扰侵权或非法搜查身体侵权不足以明确界定身体权中形式完整权的丰富内容,且该种反面界定的方式与《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正面界定方式不符。此后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司法解释应从主观权利角度正面界定身体权中的形式完整权,以实现对身体权的充分保护,构建身体权界定和保护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