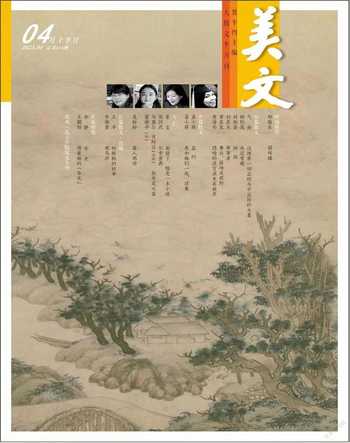借着她的“余光”
张爱玲的看人看事叫“张看”,余静的读人读书不妨叫“余光”。
人可以貌相。第一次见到余静,觉得“扶柳弱质”这个词终于有着落了。他们夫妻都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余静话不多,温凉,人好像刚从早春里出来,一段草色春气一节一节地传过来。她的夫君如同刚点燃的篝火,又是冒烟又是着火,热气腾腾。有一年,我们共同出游,一路游山玩水,吃饭喝酒,余静说什么我全没记住,但是她先生指点江山的手势我始终忘不了。还有一次,我们一起搭伴去看拍卖会,她先生只是坐在旁边,余静倒像是美术教师,在给我们普及书画作品:你看这色彩,你看这用墨,你看这线条,现在的人都画不来了。她先生坐在旁边,过一会儿只是问一下,举不举?余静说,没意思。又过了一会儿,余静说,举,接着举。她先生便高高举起。两个人举了一幅画,满意得欢天喜地。他们两个都在报社工作,余静搞文化,夫君搞体育,两人走到一块儿让人难免想,人家这两口子搭配得好。
余静在报社做记者、编辑,总让人觉得浪费。新闻是速朽的伟大事业,从事它的人常常不满足,特别是搞文化的人,如果有立言的雄心,难免有在报社体验生活的感觉。我们见了面通常都会说,最近写啥?如果没写,彼此都觉得可惜。如果写了,立马肯定,对着呢,就是得写,抓紧写。果然,余静后来就开始写小说了。我看完小说,说,这超过了陕西百分之九十多的作家。余静认为是熟人的客气,我说不是,这得归功于报社的工作,眼界宽,有烟火气。余静的小说虽然写感情、写日常生活,但是不枝不蔓,结构的稳定显示了作者内在的定力。这显然是做报纸编辑留下的影响。报纸的编辑要有刀斧手的狠辣,敢砍敢削。后来她又为秦腔立传,我说,这是向章怡和先生迈进。余静认为我评价太高,我说,气质是难于模仿的。余静是文化记者,又是学艺术出身,如果艺术的挚爱不渗进生命,文学的表达是没有气韵的。
我马齿徒增之后,买书越来越不敢下手,知道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多能力读书,但是看见人推荐的书还是禁不住想买。人是需要陪伴的动物。读书貌似一个人的活动,可是没有别人的“烛照”,我们还是会像长夜行路,觉得茫然不知所措。我一直觉得帕慕克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作家。土耳其处在欧亚的交汇处,被自己的信仰、历史和雄心拖拽得气喘吁吁。中国也有自己独立的文明,也面临现代的冲击和回应,两个国家相似之处颇多,帕慕克的写作自然会给中国作家和读者许多启发。我买了帕慕克不止一本书,《我的名字叫红》每次读后都会心不少。可是我读到余静的解读,赶紧点赞。余静从艺术和信仰两条线切入,把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信仰、历史对创新的禁限讲得清晰、通透,我读后感觉一下子就从隧道里出来了。余静梳理得简单,但是我知道这背后是有深厚的专业基礎做背景的。余静也画画,她也面临一个画家在传统和创新之间的两难,再宕开了说,也是她面对世界、人生变化的选择和坚守。所以帕慕克的故事她深有体会。
书话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周氏兄弟、叶灵凤、唐弢、黄裳等前辈都是书话大家。写书话的人大多出身作家或者编辑,作家能读懂作家,编辑和作家交往多。但是传统的书话写作,多的是见识和趣味,带有鉴赏的意味。余静的读书不是鉴赏,也不同于文学批评,而是与作家交换的生命体验,是个人思想的跋涉。她不满足于读懂作家,她要把自己也放进去。《记忆与梦境》实际上是余静和作品的互动、和自身记忆与梦境的互动,也是与一个小说母题的互动。这种阅读已经超出对一本书的欣赏,也是一个人的成长记忆。余静读《小团圆》,是作家在读作家,也是女人在读女人,更是心灵在探索心灵。我读《小团圆》也读不进去,连带影响我读张爱玲的所有作品,觉得都幼稚、做作。借着她的“余光”,看她对《小团圆》的欣赏,我又回到一个女人的角度,重新看待张爱玲,觉得依然尖锐、深刻、让人受伤。
写作是伤人的:伤身体、伤心。一个没有浓度和烈度的作家,一个灵魂平静安详的作家,作品注定是平淡的。余静写散文,是对她小说雄心的补充,也是她人生的休整。如果说她写小说像养虎,写散文就像养猫。她写小说,是照猫画虎。
(责任编辑:孙婷)

王朝阳 媒体人,在《收获》《人民文学》《美文》《散文》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多篇。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人民文学》新世纪散文家奖、《美文》报人散文奖、年度中国最佳散文等奖项。出版有《集体记忆》《丧乱》《我跪在故乡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