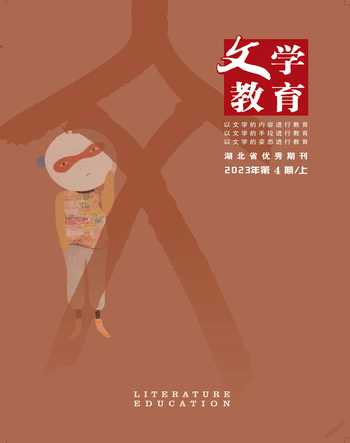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暴力叙事
徐涵
内容摘要: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一经问世,就因其“胜过千年”的“一句”而为读者带来了深刻的情感共鸣与心灵震荡。而从叙事层面来看,不论是《一句顶一万句》,还是刘震云其他的文学作品,其中的暴力叙事则往往为学界所忽略或搁置,叙事背后所蕴藏的写作姿态与思想意识仍尚待挖掘。本文尝试以《一句顶一万句》为研究中心,结合刘震云八十年代以来的部分文学创作对其作品中的暴力叙事表现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挖掘暴力表现背后的思想成因,探究其暴力书写为中国当代文学所注入的新质,力图展现作家对于社会历史困境的思考以及尝试缓和危机的努力与温情。
关键词:《一句顶一万句》 刘震云 暴力叙事
世界卫生组织曾对“暴力”一词作定義:“蓄意地运用躯体的力量或权力,对自身、他人、群体或社会进行威胁或伤害,造成或有较高的可能造成损伤、死亡、精神伤害、发育障碍或权益的剥夺。”[1]针对该定义进行解读,我们可以认为施加暴力的手段包括身体、权力等物质与精神力量,而暴力的承受者可以是个体化的自我与他人,也可以是集团化的群体或社会,暴力造成的后果亦有物质与精神之分。约翰·加尔顿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是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并尝试进一步将暴力分为三种类型:“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2]。其他更有如卡尔·施密特、瓦尔特·本雅明等思想家提出了有关“合法暴力”“语言暴力”“符号暴力”等种种分类,展现出了多样的精神面向。
为了本文叙述的推进,笔者倾向于将加尔顿的定义确定为对暴力概念的阐释,并暂时将暴力划分为直接暴力、语言暴力与精神暴力三种类型。总结来说,所谓暴力叙事,就是指作家以暴力作为手段或者叙述核心的一系列文学创作现象,其中的暴力可以包括肉体层面,也可以包括思想精神层面。
一.刘震云作品中暴力叙事的呈现类型
(一)直接暴力
《一句顶一万句》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想要“杀人”的行为动势,如渴望脱离“绕”而杀人的老裴,面对妻子出轨而想杀人的牛爱国,还有在心里斩杀老杨老马的杨百顺……这些“杀”多是存在于口头的无疾而终的暴力,没有落实实际意义上的杀人行为。而在整部小说中,真正在现实中完成“杀”,即直接暴力的,是山东人对姜虎的那一捅刀子。山东人将腰间的那把刀捅进姜虎胸膛又拔出,“血‘忽的一声,喷了一墙”,“姜虎在地上喘了一阵气,头一勾死了,地上又淌出一大摊血”[3]。在这里,刘震云对于姜虎死亡的描写冷静而迅速,读者往往尚未反应及时,就已被眼前的血腥震慑。而其中最让人感到无力的,则是这样一件持凶杀人的案件最后竟被十分默契地瞒了下来,杀者逍遥,被杀者闭嘴,而元凶沉默。类似的,在小说《头人》中,宋家掌柜的被杀同样荒诞而讽刺,吃枪子后他弓身在地上倒气,听了三姥爷的话后心想自己应该活不过来,才撅着屁股“决定”死去。这样的杀人行为原本野蛮而暴戾,结果最后也因三姥爷的身份而得以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二)语言暴力
暴力在现实中的推行受阻,就会努力探寻其他形式寄生并释放,语言暴力的狂欢也由此而来。“所谓语言暴力,就是用语不合逻辑和法律规范,欲通过不讲逻辑、不守法度的语言风暴,从而以语言霸权的形式,孤立和剥夺他人的某种权利,对他人造成伤害。”[4]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不少人物都在嘴上践行着暴力:吴摩西去杀姜龙姜狗时,硬着头皮拎刀直上,嘴里叫嚣着要杀人,最后却杀了只狗了事;牛爱国看到妻子的出轨对象小蒋一家依旧和睦,不平衡的心理刺激他说出“我想杀人”的话;吴摩西的养女曹青娥也说道,“我光想杀人,刀子都准备好了”“除了杀人,我还想放火”[5],情感宣泄毫无克制。言语的暴力弥漫在刘震云笔下各式人物的塑造之中,即使没有真正杀人,他们也早在唾沫星子横飞之中将别人杀了千百万遍。
而刘震云在书写时,也总保持着冷静而边缘化的叙事状态,习惯用白描式的灰色笔触呈现现实,记录痛苦。老李他娘会毫不犹豫地用铁勺在丈夫头上砸出血窟窿;老汪面对灯盏的死亡,只平静地说一声“死了正好”;杨百顺杀人的梦境里,“花花绿绿的肠子流了一地”;吴香香结亲时则感慨,“世上最难吃的是屎,世上最难寻的是人”[6]。这种流淌在作家笔尖的原生态暴力也在其他作品中得到呈现。《头人》中,“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7],三个“了”字连用,将一个人的死说得冷漠而平静。《一地鸡毛》里,老师的去世只给小林带来了短暂的伤心,被拽回现实的他最后说的是,“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8]。细碎而平庸的生活背后,是压抑而沉闷的人心。
(三)精神暴力
暴力形态进一步演化,就上升到了精神暴力的层面。张晓琴说道:“延津民众心中皆有一把刀,虽然没有形成事实暴力,却在内心中杀了无数次的人。”[9]《一句顶一万句》的暴力叙事中,内心杀人无疑是制造感官刺激最强烈的呈现方式。杨百顺还没杀到老马,在心里想就已经满腔痛快;杀人未遂之后,他不仅在心里将老马杀过一遍,还连同老马的同谋老杨和杨百利一并杀死。在扭曲而残暴的心里杀人中,他也逐渐明白:“原来杀老马并不是为了杀老马,而是为了杀给人看。他跟这些人,原来都有仇。”[10]假找妻子的路上,牛爱国夜里做梦梦见了庞丽娜。梦境里的牛爱国似乎忘记了妻子的背叛,急切地想要靠近她,因此第三者小蒋的出现使他毫不犹豫地掏出刮刀插进了对方的心口,完成了梦里的击杀。而到了后来,牛爱国遇到了真正能说得上话的章楚红,体谅了小蒋与妻子的背叛。再一次的梦境里,他弥补了自己与妻子多年以来婚姻的遗憾,小蒋刺进他肚子的那一刀,实则帮助他在心里正式放下了对庞丽娜的感情。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每个人都在苦苦追寻一种精神上的寄寓,然而不论是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还是一处能让自己“心安”的家园,都以触不到的虚空形式而存在,寻找和孤独,自始至终并行在一起。在曹青娥的梦里,爹的面目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模糊,梦做得多了,爹就成了无头的爹。因为这个梦境,她决定回到老家追寻过去的记忆,却发现地方还是同一个地方,人和事却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开封的火车站里,曹青娥再一次梦到了老曹,这时的爹有了头,心里却又苦得很。实际上,爹心里的苦即映照着曹青娥心里的苦,她执着地想要追寻那个“根”,追寻自己的精神原乡,却徒生悲凉,沦落孤独。通过荒诞的叙事,刘震云将中国人民痛苦挣扎的精神世界毫无保留地暴露在读者面前,带给我们惊颤的同时,揭示了人民生存的苦难与困境。
二.暴力叙事背后的思想因子
(一)童年经验的延续
宋雯认为,“在这些‘60年代出生作家笔下大规模出现的“暴力”与他们的共时性童年经验,也就是他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狂热、喧嚣、荒诞、忠良遭害、奸侯横行的时代密切相关”[11]。刘震云出生于1958年,童年经验与60年代出生的作家可以基本重合,虽然他的童年未曾有如同余华所经历的血腥与暴露,但也不能排除其童年经验对于后来创作的影响。在刘震云的回忆中,就曾提到自己贫穷饥饿的童年。因为吃不上饭,直到十几岁他的梦想仍是到镇上做一个厨子。这种切身的饥饿体验也使其在《温故一九四二》的书写中有了更加极致而真实的韵味。啃食树皮,转卖儿女,生命的交叠逝去让人触目惊心,而在這种暴力与悲剧的冲击之中,刘震云始终坚持探寻着死亡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
(二)《水浒传》与英雄崇拜
在刘震云的写作中,不时流露出一股在人群中穿梭而残留下的“人气”,这种“流民”视角的由来,则与《水浒传》有着密切联系。刘震云曾公开赞赏过《水浒传》这部作品的价值,并表达了对于林冲这一人物形象的喜爱。“我要想活,必须有人死,我要想活,必须杀人,当他产生了这种之前永远不敢产生的想法的时候,马上尸横遍野,鲜血像梅花一样在雪地里开放。”[12]刘震云所欣赏的,是作家敢于用杀人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人物情感,有着难以企及的气度与胸怀。在这种“林冲情结”与“梦回宋朝”的追求下,刘震云和底层民众站在了一起,展开了以“义”为中心的乡土复仇,以暴制暴,宣泄内心的快感与豪情。而当《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暴力施行只能存于言语和幻想之时,《水浒》则成为了凭吊喊丧的对象,乡土也陷入了迷茫和失语的困境。
(三)《出埃及记》与精神信仰
《一句顶一万句》常被视为是对《圣经》的模仿与对话,而通过对《出埃及记》中的叙事描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同样隐含着行动暴力和话语暴力实施:摩西作为上帝的代表,帮助上帝“行神迹奇事”而完成借刀杀人;上帝在“十天灾”和“晓谕”等描述中加注对于死亡的威胁,用以统摄众民。由此,笔者推测,刘震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圣经》将暴力叙事“弱化”存身于文本的创作方式影响,使其成为“恶魔的私语”,进而在写作中灌注更多信仰与精神意志的色彩。曹青娥追寻“无头的父亲”,既是对民间信仰中“天”的投奔,也是对整个民族信仰与身份的追认。
(四)鲁迅与悲剧与救赎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鲁迅对刘震云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90年代初期,刘震云就曾发表过一篇名为《读鲁迅小说有感:学习和贴近鲁迅》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辩证地评价了鲁迅小说的创作成就,肯定鲁迅在思想内容上对于社会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同时提出其在艺术方面单一化的缺陷,最后发出应该学习和贴近鲁迅的倡议。通过阅读刘震云的文学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始终笃实坚定地践行着这一理念,并尝试在实践探索中突破鲁迅的局限,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天地。
刘震云对于鲁迅最大的学习与承继,就是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揭露社会现实,展现人民的悲剧与困境。鲁迅曾用“砍头”这一意象批判道德文化的崩裂和生命意识的残缺,到了刘震云的创作中,《官人》《头人》等小说极力书写对于权力的批判,《单位》《一地鸡毛》的冷漠叙事暴露平庸生活的压抑,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更在心与心中间竖起高墙,演绎人性与伦理的危机。由此,出现在刘震云创作中的“杀人”,实际上是无助者诉诸非理性的暴力来掩饰恐惧的手段,是渴望通过原始性力量来获得自身存在感与价值认同的表现。刘震云借助这种蕴藏在叙述语言中的暴力,立足于底层民众视角,展现了国民集体层面的苦难与悲剧,发出了对于现实生活的批判以及人生意义的追问。
同时,在学习和贴近鲁迅的过程中,刘震云还尝试加入自己的理解与思考,探寻出了别样的创作生态,在他冷漠和暴力的叙事创作之间,我们往往能感受到隐藏在其中的温情与诗意。在《一地鸡毛》中,最后被生活折磨至麻木不仁的小林仍会因为老师的去世而感到难受与伤心,不经意间的人性流露,成为了整篇灰调之中的一声温暖变奏。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每个人欲动手杀人时,往往会因更“绕”的事情而中断杀人的念头,并产生了拯救他人的善念和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作者有意对杀人者施加的救赎,杀人的重复,成为了一种救赎的重复。此外,文中何玉芬的那句“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牛爱国的那句“找,一定得找下去”[13],也给整篇文章赋予了诗意的色彩,即使是难以走出的灰暗循环,也有着皈依精神家园的可能与希望。
三.刘震云作品暴力叙事的新质特点与意义
在浩荡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历来有针对暴力现象的书写:《史记·酷吏列传》记述了前朝十余名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的残暴官吏的史实;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不仅对人物话语的设计粗俗暴力,更在叙事中充斥杀人流血的血腥画面。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家尝试将暴力作为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联系的媒介,转向对文化和国民性的冷静批判,“人血馒头”“砍头”等暴力意象的出现,有着革命与唤醒的意味。而到了当代文学的视域,暴力则成为了余华、莫言、苏童等先锋派作家创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被中国与西方文学经典夹击的他们,紧紧抓住暴力这一写作特色,“解构主流与传统,动摇公认的真理,揭开人性的面具,披露生命的真相”[14]。可以说,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下,暴力叙事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创作指向。
而面对底蕴厚重的文学史流变,刘震云始终保持着不懈探索和辩证批判的创作姿态,在暴力现象的叙写中,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许多独特的新质。
首先,依托民间浑然原始的文化状态,刘震云构筑起了一套自我独有的价值视角——民间立场。从叙述对象上看,刘震云笔下的人物多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平民,他们身上无不带有小人物自私、贪婪、肮脏等劣习,更有不少人物立足平民身份,将脏话连篇的语言暴力狂欢作为自己宣泄情绪和展露个性的手段。然而在此视角之下,除却“民间本能的弱肉强食的血腥”,也“包含着那种民间藏污纳垢中的生命原始正义”[15],借助充满反讽和悖论的话语体系,刘震云得以倾注强烈的反思与解构力量。同时,刘震云选择将视角集中于这些底层平民,以平视的目光去理解和关注他们,不仅真实地揭开了小人物生存的苦难现实,也开辟出了乡土叙事更具体验性和暴露性的新路。借助“小”人物的身份反差感,表现“大”社会的典型问题,通过叙写个体在物质生活及精神世界中的残酷沉浮与挣扎,集体性的痛苦与困境进而无处遁形。
其次,诗意化也是刘震云暴力叙事的突出特点。从暴力形态上看,刘震云作品中针对直接暴力(即产生肉体接触)的叙述笔墨较少,而较多地倾向于语言暴力、精神暴力等更具梦幻、虚浮形态特征的描写。在这种“不落实”的手段之下,暴力得以更加自由和恣意地游走实施,作品的审美价值得到充实和发展。同时,在学习鲁迅的传统中开拓出别样生态的刘震云,以其含蓄而深远的温暖诗意为作品赋予了可盼的希望。不论是生动的人性流露,还是循环的暴力救赎,刘震云都试图让读者在有迹可循的温情之中感受到自己坚定而诗意的内心世界。
此外,文化性在刘震云暴力叙事中的表现也不容忽视。在这里,“文化”的内涵是丰富而蕴藉的。在摩西的寻找和“恶魔的私语”中,刘震云通过宗教文化建构起中西价值信仰的互动桥梁;在无头父亲和身份追认的断裂创伤中,民族文化又成为了刘震云描绘中原精神图腾的意志根基。或吸收或积淀的多元文化,通过暴力这种强烈的生命律动形式得以在广阔玄思中不断激荡,渲染出刘震云真实丰厚而又充满哲思的文学世界。
余华曾说道:“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16]针对暴力叙事开展研究,不仅能窥探时代之下人民的生存困境,更能感受到来自人心的那股难以遏制的精神力量。本文以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为中心,结合刘震云八十年代以来的部分文学创作,分析归纳了其作品中暴力叙事的诸种表现,并从刘震云个人经验和文学资源的角度出发探寻了暴力叙事的思想动因,进而思考其暴力叙事所呈现出的新质特征以及对于当代文坛的创新意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由于文本阅读数量的匮乏以及理解的浅表化,笔者尚未形成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索,值得在今后的学习中进一步提升。延伸拓展文学经典的价值,探寻叙事研究的更多可能,这也是我们执笔写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2]刘震云.一地鸡毛:典藏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2.
[3]左高山.政治暴力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4.
[4]Johan Galtung,“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1969):167-191.
[5]曾莹.影响的焦虑与先锋作家的暴力叙事[D].湖南师范大学,2019.
[6]童明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暴力描写现象透析[D].四川大学,2006.
[7]李妍.论语言暴力[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9:1.
[8]张晓琴.千年孤独 中国经验——论《一句顶一万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2):45-52.
[9]宋雯.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暴力”书写[J].社会科学论坛,2017(01):175-183.
[10]刘震云.读鲁迅小说有感:学习和贴近鲁迅[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03):112-114.DOI:10.16287/j.cnki.cn11-2589/i.1991.03.015.
[11]陈雪,刘泰然.现代性、仪式与奇观——从鲁迅、沈从文到黄光耀的“砍头”叙事[J].理论与创作,2011(02):51-53.
[12]张明.论刘震云小说中底层民众的语言暴力书写[J].阴山学刊,2020,33(04):38-42.DOI:10.13388/j.cnki.ysaj.2020
.04.007.
[13]胡琰.苦难悲情到荒诞孤独[D].河北师范大学,2021.DOI:10.27110/d.cnki.ghsfu.2021.001209.
[14]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等.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J].名作欣赏,2011(13):92-100.
[15]李一扬.史诗《出埃及记》中的暴力叙事[J].文学教育(下),2013(07):17-19.
[16]李丹梦.乡土与市场,“关系”与“说话”——刘震云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10):1-85.
[17]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注 释
[1]左高山.政治暴力批判[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4.
[2]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1969):167-191.
[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4]李妍.论语言暴力[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9:1.
[5]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6]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7]刘震云.一地鸡毛:典藏版[M].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2.
[8]刘震云.一地鸡毛:典藏版[M].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2.
[9]张晓琴.千年孤独 中国经验——论《一句顶一万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2):45-52.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3.02.007.
[10]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11]宋雯.童年经验与“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小说中的“暴力”书写[J].社会科学论坛,2017(01):175-183.DOI:10.14185/j.cnki.issn1008-2026.2017.01.015.
[12]刘震云,陈平原,孟繁华,等.从《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J].名作欣赏,2011(13):92-100.
[1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典藏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8.
[14]曾莹.影响的焦虑与先锋作家的暴力叙事[D].湖南師范大学,2019.
[15]姚晓雷.刘震云论[J].文艺争鸣,2007(12):122-132.
[1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