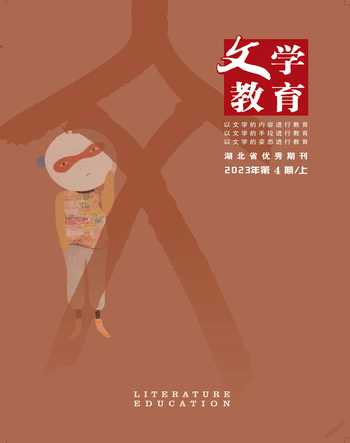骆以军《匡超人》中的后人类想象
郑若琰
内容摘要:当代作家骆以军的长篇小说《匡超人》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社会两个域界,仿佛一部当代台湾社会的《儒林外史》。这一文本超越了骆以军惯常书写的历史记忆与国族身份想象,而进入到对“后现代”与“后人类”的探讨之中。小说以“洞”为关键意象,贯穿人物身体与心灵以及故事时空,呈现出新的人类面貌与衡量世界的尺度。本文提供了一种解读《匡超人》的可能性:从无数的“洞”中看去,最终读者将接触到骆以军对现代人类这一对象的身份确认。
关键词:骆以军 《匡超人》 台湾文学 后人类
骆以军是台湾外省第二代作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员,陈思和称其“作为今天先锋文学的范例,创造了一个抽象的、实验性的文学,……不只对台湾文学有影响,他对整个中国文学都发生影响”[1]。其新作《匡超人》便鲜明地体现了“抽象”与“实验”两种特质。《匡超人》2018年在台湾出版,2020年在大陆出版,作品从“我”身体上的破洞出发,讲述了无数“我”和在他以往作品中曾出现过的“我”的亲友们的当代故事。相较于骆以军以往代表作品中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的追逐,《匡超人》选择融合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社会两个域界,仿佛一部当代台湾社会的《儒林外史》,在历史元素与当代社会文化元素的交错之中,在古典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其他作品中虚拟的形象与私人历史中或存在或不存在的形象交互的过程中,写出新时空的焦虑与思考。在小说构建的现代时空中,駱以军也不吝啬地指出现代人类空虚的痛处,对现代人类之后的“后人类”进行了思考与构拟。
一.躯体与心灵之洞
《匡超人》一书以“洞”意象串联始终,与“人”这一形象密切相关,破洞不仅仅存在于人的肉体之上,同时也存在于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之中。无论是生理或是心理上受伤、破洞,小说中的人物都在一条“变质”的路上行走,而这种“变质”似乎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后人类主义”的核心是对盲目尊崇人类理性和主体的反拨,本书中人在失能的过程中边缘化,从而消解了人类的中心地位,也引发了对“何以为人”这一问题的思考。这是当代社会人类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一个解决困境的方向。
1.破洞的人体
疾病叙事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匡超人》故事的起源就在“我”胯下的破洞里。对性与生殖的书写在骆以军的小说中并不少见:在《月球姓氏》中,看似破碎的伦理背后是家族历史的晦暗不明与经验匮乏;在《西夏旅馆》中,对性与生殖的惶恐延伸则成为对灭种和身份缺失的焦虑;但《匡超人》中的疾病并不仅仅在于对去势的恐惧。书中《吃猴脑》一章中写到:“那种‘身体轴心空了一个很深的洞的残障感,和手部或脚部截肢的不完整感、幻肢感,身体重心偏移的感受不同;也和古代阉人整个男性荷尔蒙分泌中心被切除的尖锐阴郁不同……洞,很像一个活物,每天都往你不知道那是什么境地的,反物质或黯黑宇宙,那另一个次元,灵活蹦跳地再长大,深入。”[2]在小说中,破洞不仅仅是“我”和其他“病人”的伤口,也存在于古往今来各色虚构人物身上,如二郎神的第三只眼,钢铁侠装甲的胸口,蜘蛛精的肚脐,阿基里斯的脚踝和雷震子的背脊。“洞”的普遍存在暗示了现代人类问题的普遍性,且提供了新的审视文艺作品中人物的视角。骆以军此前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提到去势的焦虑,以此影射对身份和历史的焦虑。“洞”可以表达对男性主体、社会权威乃至价值体系的指涉,但在本书中更多地带来关乎历史、时代与人类整体的困惑与痛苦。
小说中的“我”收到一个女孩的网上私讯,认为“洞”可能是种种重病的前兆,“我”开玩笑说这或许是一种业障,却得到女孩对“业障说”的批评。破洞是何种疾病的表征并不得而知,相较于致死,破洞的意义更使我焦虑,“我”或许不会因女孩提到的任何一种疾病而死,但“我”会因确信一种“业障”的存在并顺从、接受破洞而死。伤口的存在本身被赋予了滑稽感,因此无论重视或无视破洞,似乎都与严肃无关,但放弃思考破洞的意义,是否真的会导致“死亡”?纵观《匡超人》整部小说,破洞已成为一种伤痛体验的具现化,正是这份伤痛成为本书的重点,而并非骆以军以往作品中常见的焦虑隐喻。骆以军在小说中对“洞”的嘲讽与无奈自嘲,指向的是将历史与社会赋予的伤痛体验视作玩笑或业障的观点,以消解严肃的方式对抗现代社会的过度娱乐化。
2.空洞的内心
除了可视化的伤口之外,小说中出现的众多人物都有一颗空洞的内心。小说中一大部分人物是在骆以军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朋友”。 书中出场次数最多的友人老派是“我”之前的一代大陆移民,在书中象征着父辈,以流连于过去时光的“异乡者”的形象出场。《在酒楼上》一章中写到:“他们(父辈)的故事,一开口就是骗术。他们特爱讲《聊斋志异》(鬼故事)、《三国》(钩心斗角的故事)、《西游》(不存在的一趟大冒险)、《儒林外史》(所有人讲话全颠倒虚空的故事),因为他们自身的历史,就是死去的鬼魂的历史,而死去的历史的儿子们说的故事,不就是骗术吗?”[3]骆以军的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骗术”,这种骗术是关于身份历史的构拟。在漫长的历史之中,个人所能经历的只有其中的一小个片段,历史是由此前无数人的经验拼接而成的;作为认知主体的个人只是不断背负他人的经验,活在他人的经验之中,自己所拥有的的经验是无比匮乏的。如果说老派这一代人以及父辈们的生活是系在截止过去某个点为止的个人经验上,那么骆以军及他的同代人被给予的是系在与自身距离遥远的他人经验之上的生活。作为外省二代的骆以军一直以“经验匮乏者”自居,他广泛获得的是来自父辈讲述的经验,受到父辈经验的影响,并要面对如何处理父辈经验的问题。在关于经验的讨论中,空心感即在于上一代人停留在过去的经验之中,下一代人承接上一代的经验叙述却无法拥有真实的感知,没有人能够准确占领自己当下的记忆坐标,因而产生内心的空洞。
3.人与“他者”
在骆以军笔下的现代社会,无论是肢体上的破洞还是精神上的破洞,这些残障感出现得越来越普遍。当个体不再完整,怎样算作失能、失能的人是否还能算作人便成为了新的思考,关于人的界线问题又重新浮出了水面。在许多失能研究中,研究者反省残障人士和完整的健全人的区别,在“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之下,失能者只能不断边缘化,而在骆以军笔下,这种残障感扩散到每一个现代人身上。当每个人都成为边缘人物时,也就不存在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人是否为世界的中心?“人”的核心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再度思考。
本书中,骆以军写到了人与两个对照组的关系,一是其他动物,二是神。在所谓“万物之灵”的标榜下,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即使生命普遍地存在于所有生物体之中,其概念的使用却往往局限于人类这一物种内,或者说人类的生命与非人类的生命并不被放在一个层面上进行讨论。人类对非人类的生命形式经常施与支配性的暴力,甚至包括地球本身在内,都属于这样一个“他者”。可人與非人类的界限究竟在何处?人类如何确证自己的命运与非人类注定不同?在生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中,人类反而面临着非人性的时刻,此时人性的概念又从何解释?这无疑成为一个悖论漩涡。在《美猴王》一章中“动物”一节,骆以军写到,人类文明“建立在每日每日的屠杀,对不属于他们的成员的痛苦制造上”[4]。而此时情节突然跳跃到到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在小说中被圈养着的是克隆人,被用来给人类提供器官。克隆人与人类的区别仅在于克隆人并非自然产生,而是人造的“人”。《别让我走》中的克隆人们在物质上得到照料,在精神上同样也获得培养,但归根结底他们仍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不需要存在文明,或者说他们的“文明”是不会延续的。这是现代屠宰场的伦理,也是现代社会的“非人性”。在骆以军此处对“他者”的观照中,可以看到骆以军试图从“物”的视角反观人类自身:人类与其他所有普遍生命实则都是一致的。而骆以军笔下的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化”,如《阿默》一章中描写的黑狗阿默,就有许多人类化的特质,更引起读者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反思。
同样在“动物”这一节,骆以军笔下的人类通过将“神”创造的美丽动物、山川海洋降成只有功能性价值的物体来完成弑神的过程。“人类”对自我的定义与超越的企图都逐渐扭曲,似乎像一座不断吞噬“他者”的机器,这个过程也一并将意义吞噬。在《美猴王》一章的“消失”一节中,骆以军借美猴王之口写下“后来的人类”:人性膨胀促使人扭曲物理限制,从而摘除人性闸门,人类这一物种不断扩张,形成“不知哀矜、不恐惧灾祸的文明”[5]。将人抹去才是最强大的神力,而这一力量在现代社会已经由人从“神”的手中篡权而来。如果现在的人类不对“人性”重新加以节制的定义,“后来的人类”将会变成一场灾难。无论是书写“洞”的意象还是将人类与他者进行对照,《匡超人》都在试图消解过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打破对“人”的定义的固有概念,“后人类”并不是对人类本身的一种超越,而是希望超越人类孤立于其他所有物种与物体之外的自我想象。在破除了旧有的秩序之后,小说发出新的质问:何为现代人,现代人究竟要往何处去?
二.时空逻辑之洞
在通过对人类主体进行变异而消解中心性之外,小说另一方面也构造了超越现有人类中心的时空观。在对骆以军小说的研究中,“空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匡超人》中对空间的特殊处理在于将空间复杂化与将时间空间化,由此塑造了仿若巨大黑洞一般的超现实叙事背景。
1.空间复杂化
小说中许多场景设置在现实生活中实存的场所,但又跳出了日常生活的眼光,以人类之外、人类之上的眼光来看待日常空间。骆以军承认现代都市的空间是狭小的、局限的,因此他也更渴望追回类似神话般巨大空间尺度,在他的笔下,人物与空间存在对话交流,在庞大的空间面前,人类渺小反而自由,在这种尺度面前,作为书写对象的人的“他者”不再是持其他属性的人,也不是其他物,更像是空间本身。
骆以军在《匡超人》中可以轻而易举地使用生活中不常接触的空间尺度,大如星系、银河,小至电子、微子。在《美猴王》一章的“小雷音寺”一节中,宇宙尺度与微物尺度更是同时存在:二十八星宿原本在天空中标志着天宇的维度,在书中却挤在一个黑暗狭小的房间里;亢金龙解救大圣的过程则是小到原子层面进行书写,还使用了数学的大矩阵运算。这些文字剥离了日常感,使读者跳出了惯常的阅读思维框架进行审视,在超大宇宙观与微物宇宙观之间进行切换,对我们已存的衡量生活空间的尺度发起了挑战。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使用非日常的空间感与熟悉的空间对照之外,书中还有大量对网络空间的书写。网络是新时代的对传统人类生活空间概念的挑战。现代人类高度依赖网络这一虚拟空间——无实体,不能用二维、三维进行解释,由无穷无尽的资讯、信息、数据垒叠而成。在《美猴王》一章的“电脑时代”一节中,骆以军写到,网络世界是一个巨大而恐怖的新世界,“我不知道有一天,包括我,所有的人类都要被裹挟进那个网路海洋之中。确实它可能是比卡夫卡,比尼采,还要疯狂,吞噬所有迷宫、所有永劫回归之时间的发明”[6]。本书中,资讯在世界构成中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个信息世界中人类的身体由他的有机身体与资讯密码在网路资讯世界中交织与衍生的身体构成,“我”已不只是单纯的我一人物,而是由数量庞大的各种经验与资讯搭建成的虚拟体。网络在本书中是整个世界的缩影,骆以军使用了大量与网络相关的比喻进行书写:人类像一台信息设备,甚至也可以是一条虚拟指令、一串运算数列中的一个常数;死亡像是屏幕关机……
在网络时代,信息远比实体更为重要,重资讯而轻肉身或可导致一种信赖危机,带来对现实真实性的挑战。虚拟的空间在传统观念中并不能完全被体验,从虚拟感生发出来,何种程度的经验使我们能确证空间和生活的真实性?在《超人们》一章中,“超人们”在聊天中列举了许多关于人类灭绝的经典幻想,但同时也提出,这些恐惧可能只是一些电路脉冲,而世界末日已经发生过了,人类只是一种全息投影,一些游荡在虚空中的信息。这样的结论似乎不能证实,但也无法证伪。而当人类被用编码归纳后,个体性便被抹杀,“真实”的自己便难以呈现,从而失去单一人类个体性的动态,将世界化为电路一般的存在实际上同质化了具体的真实。
小说中有许多类似“表网”与“深网”的空间对立。世界呈现在外的是“表网”,在大部分人生活着的“表网”之下还有“深网”,“深网”中有人类的黑暗与痛苦。“表网”与“深网”都存在也都具有真实性,但只生活在任意一个层面都会导致失真。骆以军通过小说的书写提示每一个阅读者,我们必须时刻反思我们所经历、接受的一切。在《美猴王》一章的“另一颗地球”一节中,骆以军写到了克卜勒452b星球——类似于一个较年长、较巨大的地球。一种想象是:那颗星球上都是我们死去的亲人,像一个地球在生命上的倒影。然而本节结尾笔锋一转,提出了质疑:“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一颗,收藏了全部死亡的另一颗地球呢?你如何知道此刻的我们,是在那个‘活着的地球呢?如果其实我们是在克卜勒452b呢?”[7]真假是否能够分辨,其界限又在何处?骆以军在《粉彩》一章中以古董为例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赝品的历史是假的,但物品本身是美的。当“假”无比逼近“真”或者假得无比美好时,“我”一方面为创作者创造“假”而悲哀,另一方面为“假”之上寄托的时间、智力与感情而悲哀。前一章中提到“骗术”的话题亦是如此,有选择的记忆是一种“骗术”,骆以军甚至大胆地提到,历史也是一种骗术,如今的文明也是一个赝品,制作者花了大量精力只为“复刻”,如果不以概念中的所谓真假二元对立作为唯一尺度,每一件“赝品”,都在记录当下而非古代,在时间轴上真与假只是一个悖论。
在《匡超人》中,骆以军在虚实空间、真假空间中来回跳跃,同时打破了概念与概念之间固有的联系,在断裂中引发对社会中潜藏的空洞的思考。是否存在真实,我们用何种尺度衡量真实?人类又能否努力接近真实?如果说人类存在一个接近真实的能力极限,那么现代人是在争取这种极限吗?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像一个巨大漩涡,这种哲学般的挑战本身就如同一个思维黑洞,在黑洞边缘试探的书写一不小心就会落入虚无的窠臼。
2.时间空间化
书中时常提到一部漫画作品——《JOJO冒险野郎》[8],其中的主角拥有“替身”——一种具象化的超能力,能够暂停时间、删除时间。孙悟空在大闹天宫时施展的“定字诀”也是类似的法术。让时间凝固就是时间空间化最极致的表现,当时间定格,事件的发生就不受传统经验的约束。骆以军在小说中设置了“时间之屋”,时间在其中凝止不动,这一空间内任何一个物件上都有时间的隐喻:在《美猴王》一章的“定字诀”一节中,这个“时间之屋”是拾荒阿伯的房间,时间已从废品上死去,而废品的堆积却又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死去”的时空;在“游乐园”一节中,这个“时间之屋”是废弃的游乐园,因其废弃而得以将旧时光凝固在游乐场的器具中;甚至于,骆以军书写“破鸡鸡超人”胯下的破洞,也将它称之为“时间停止的破洞”。学者杨凯麟认为,骆以军的书写中,各式记忆物件拼装成庞大的记忆之城,“并非这些物件的历时排列,甚至不是它们的共时布置,而是‘像是紧急刹车”,层叠挤塞而成[9]。骆以军在小说中也写到“在时间之外另有一个空间”[10],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福柯对“异托邦”中“异托时”的叙述:如果一个场所聚集了所有的时间,那这个场所本身就在时间之外,当人们发现自己与传统时间观念相割裂时,“异托邦”就开始发生作用。
乌托邦是没有真实位置的虚构场所,而“异托邦”是我们文化和文明中真实存在的身体生活空间,但也借此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骆以军的笔下非常自觉地体现了这一观点,他构建的“时间之屋”将某种时间经验抛掷在另外一个时间层中,这些“时间之屋”都实际地占有一定的真实空间,但其涵义却指向一种抽象的、虚拟的空间。“异托邦”的存在像一种“他者”空间,折射出我们社会所谓“正常性”的存在。福柯的理论针对的是韦伯意义上科层化的现代性牢笼,骆以军在《匡超人》中的意图与此是相吻合的。《冰封》一章里,“我”的导演朋友沉迷于造船,吸引他的甚至不仅仅是航海这一冒险的行为,而是造船本身,他不断地造船却又不断地觉得他用3D打印技术制造出来的东西永远成为不了船,而只是船的某种过渡形态。骆以军直接在小说里点出:这是船?还是导演朋友的影片?还是我们的人生?無论是废品角落还是游乐场,甚至是电影、是小说,都是骆以军笔下的“异托邦”,在巨大的时代机器的高速运转之下收集被遗弃的记忆碎片,以对抗被规训的大批量的记忆消失。
《匡超人》一书仿佛是针对现代人的启示录,思考了何以为人、何以为现代中国人、何以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启蒙时期留下来的对“人”的定义需要已重新考量,二元对立亟需打破。通过身体上与心灵上的“洞”,骆以军重新思考了“人”的定义,深入伤痛体验,挖掘人性的边界。此外,本书也对故事时空进行了特殊的处理方式,将时间空间化,将空间复杂化,通过时空的“魔术”探索真理问题,剖开社会的漏洞,留下一个个困境、一个个难题。“后人类”之思仍然是一个正在探索中的议题,《匡超人》一书中,骆以军抛出了这个概念,并展现出有意识地顺从这个概念的书写模式,最终提出的解决方式是以写作尝试修复无数的“洞”。修复本身是一种对知识分子的挑战,骆以军在书中同时表现出了担忧与信心;而这部作品同时也是一种对小说本身的挑战。本书中时常提到中国古典小说,也使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写作笔法,但整部作品设立在非常后现代的环境中,尤其强调科技与网络的存在,即使是使用古典小说中的素材时,也放在了现代的、甚至科幻的视角进行解读。小说本身如同一个“洞”,在写作手法的不断翻转之中险些坠入叙事的黑洞,但最终骆以军仍旧成功地掌控了这一部小说,进行了完美的收尾,无论是这部小说还是小说这一事物本身都展现了失能与超能的一体两面,无疑是一场有趣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2]陈思和著,颜敏选编.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论稿[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3]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4]福柯.另类空间[J].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6):52-57.
[5]孙绍谊.当代西方后人类主义思潮与电影[J].文艺研究,2011(9):84-92.
[6]杨凯麟.骆以军的第四人称单数书写(2/2):时间制图学[J].清华学报,2005(民国九十四年),35(2):299-326.
注 释
[1]陈思和.有行有思,境界乃大——陈思和与“世界华文文学”之访谈录[A].陈思和著,颜敏选编.行思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论稿[C].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344.
[2]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409-410.
[3]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264-265.
[4]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45.
[5]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41.
[6]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157.
[7]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75.
[8]大陆通译《JOJO的奇妙冒险》。
[9]杨凯麟.骆以军的第四人称单数书写(2/2):时间制图学[J].清华学报,2005(民国九十四年),35(2):382.
[10]骆以军.匡超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35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