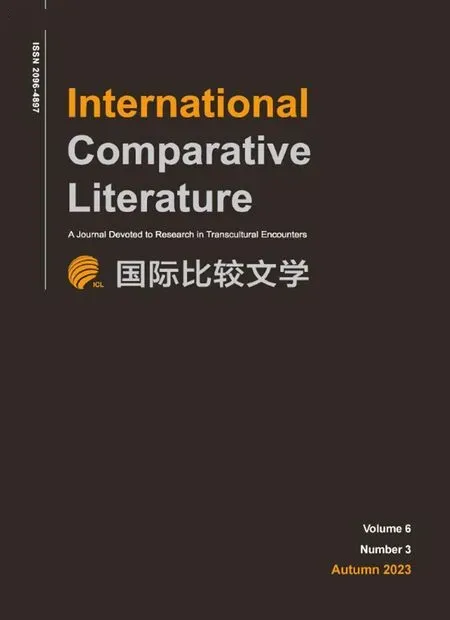《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欧洲的流变、改编与阐释*
远思 南开大学
《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主要讲述了26岁的“小霸王”孙策在占领江东后遭仇家行刺身负重伤,养伤期间力排众议斩杀了江东地区颇具名望的道士于吉,后被其魂魄纠缠,不堪其扰以致伤口复发而死。在卷帙浩繁的《三国演义》叙事以及三国故事相关研究中,这则故事在中国本土很少获得关注1参见:徐永斌:《从〈三国演义〉中孙策处斩于吉事看中国早期道教在江东的发展》,《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1期,第77~88页。[XU Yongbin, “Cong sanguoyanyi zhong Sun Ce chuzhan Yu Ji shi kan zhongguo zaoqi daojiao zai jiangdong de fazhan”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Jiangdong in Early China Based on the Execution of Yu Ji by Sun Ce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1(2012):77-88.],但它却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相继引起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汉学家及作家的兴趣,被多次译介、改写和阐释。《三国演义》第29回孙策斩于吉的故事在欧洲的流变是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中被吸纳和改塑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研究世界文学作品中的“中国故事”在西方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呈现出怎样的文化价值的变异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一、英语世界的传承性译介
《三国演义》的“孙策斩于吉”故事在19世纪英语世界的流传具有较强的传承性。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邓罗(C.H.Brewitt Taylor,1857-1938)、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等人相继对该故事选段进行了选译和评论。其中最早对《三国演义》中“小霸王”孙策的故事表现出关注的是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艾约瑟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从小受牧师父亲的影响在敬虔的环境中成长。1847年被按立为牧师后,艾约瑟于1848年被伦敦布道会派遣至中国上海,协助主持墨海书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1852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一部名为《汉语会话》(ChineseConversations,1852)的汉语教材中,艾约瑟选译了《三国演义》(San-kwo-che,HistoryoftheThreeKingdoms)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的内容作为中国小说的范例,并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刊载了故事内容2Anonymous,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Extract from Chap 29,” in Chinese Conversations: Translated from Native Authors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52), 158-83.。经考证,艾约瑟所用底本为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本3参见:王燕:《艾约瑟〈汉语会话〉与〈三国演义〉的英译》,《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6~169页。[WANG Yan, “Aiyuese Hanyu Huihua yu Sanguoyanyi de yingyi” (Joseph Edkins Chinese Conversat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2(2017):156-69.]。而英文部分则将摘译内容命名为《方士于吉之死》(TheDeathofYuKeihtheMagician),并标注了“摘自第29章”。艾约瑟只围绕“孙策斩于吉”的故事情节节译了中间部分,始于“正话间,忽报袁绍遣使陈震至”止于“言讫,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岁”4Katherine F.Bruner; John K.Fairbank; Richard J.Smith,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1854-1863,(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86), 43.。
除了艾约瑟之外,美国汉学家邓罗和卜舫济也分别单独选译过《三国演义》中孙策斩于吉的故事片段。邓罗于1889年在《中国评论》(ChinaReview)杂志上将其刊载的故事选段命名为《孙策之死》(The Death of Sun Tse)5C.H.Brewitt Taylor, “The Death of the Sun Tse,” China Review XVIII 3 (1889): 147-51.。卜舫济在其1902年的《〈三国演义〉选译》(Selections fromTheThreeKingdoms)中再次选译《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题名为《国王孙策斩杀道士》(King Sun Ts’é Has the Taoist Monk Beheaded)。该译文载于1902年上海版《亚东杂志》(TheEastofAsiaMagazine)第1卷,由上海北华捷报社出版发行6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 “Selection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The East of Asia Magazine 1 (1902): 122-28.。英语世界对孙策和于吉故事的讲述主要以翻译的形式进行,对其内容改动不大。卜舫济在对该篇故事的评论中称其讲述的是年轻的统治者对迷信的恐惧7Ibid., 122-28.,而艾约瑟则更多表现出对孙策的认同。艾约瑟在选取《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选段时保留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论共二十余条,收录在《方士于吉之死》英译部分的附录注释里。毛氏父子对待孙策的态度不同于罗贯中的批判,二人在评论中认为孙策斩于吉表现了他的英明见识,不信鬼神更体现其英雄本色8(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毛宗岗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26~227页。[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Bookstore, 2015, 226-27.]。而艾约瑟在《汉语会话》“序言”中也明确地提出对“中国人批评的精神和方式”9王燕:《艾约瑟〈汉语会话〉与〈三国演义〉的英译》,《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2期,第156~169页。[WANG Yan, “Aiyuese Hanyu Huihua yu Sanguoyanyi de yingyi” (Joseph Edkins Chinese Conversation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2 (2017): 156-69.]表示认可。整体来说,英语世界对《三国演义》中“小霸王怒斩于吉”这则故事的三次译介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在英语世界的跨文本旅行过程中所获得的多元化解读。“中国故事”在英语世界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的流布具有较为稳定的传承性。
二、法语世界的开放性增衍
除了上述三位英语世界的汉学家之外,法国汉学家西奥多·巴维(Theodore Pavie,1811-1896)也在同一时期对孙策和于吉的故事表现出了格外的关注,不仅在《三国演义》法译本中进行了译介和评论,还单独将该故事以《巫师于吉》(Yu-KileMagicien)为题收录在中篇小说集《海外故事与场景》(Scènesetrécitsdespaysd’outre-mer,1853)中。巴维在1845—1851年间陆续翻译并出版了《三国演义》法译本(Histoiredestroisroyaumes,1845)。他所采用的底本并不是艾约瑟所用的清代毛氏父子批评本《三国演义》,而是藏于皇家图书馆的满汉双语的明朝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这一点在他的《三国演义》法译本前言中有所体现:“在皇家图书馆有若干个《三国演义》版本,但最主要的版本有两个,一个是带图版的,……另一个在执行细节上不那么仔细,没有加标点,但行文中注有鞑靼人的满语,……鞑靼语的译文为我们帮了大忙。我们所选用的版本有8卷,共24册书,每本书10章。”10Theodore Pavie, Histoire des trois royaumes vol 1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vol.1) (Paris: Duprat, 1845), 51.他对《三国演义》章节和整体结构的描述与嘉靖壬午本24卷《三国演义》十分契合。与清代毛氏父子批评本《三国演义》不同的是,在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中,“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是单独成章讲述的。这也使巴维有更大可能单独关注到该故事。此外在《三国演义》法译本前言中,巴维还对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以及道教在三国时期崭露头角的情况表现出了关注:
在《三国演义》这样一本对孔子的哲学、对仪式的遵守如此充满敬意的书中,“道”的学说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各个教派的饱学之士从最初的几章就开始煽动民众;他们不断地使用他们的超自然力量,呼风唤雨。各种元素在任何场合都会受到他们力量的支配。死者的灵魂,无论是受祝福的还是受苦的,都会出现在他们保护的朋友面前,出现在他们恫吓的敌人面前11Ibid., 41.。
这段对道教和道士的评论与《三国演义》第29回孙策斩于吉的故事内容遥相呼应,也可以看出巴维早在翻译《三国演义》时对此故事表现出特殊关切的深层动因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儒释道三教地位的关注。1853年,巴维又在其编纂的中篇小说集《海外故事与场景》中再次叙述了“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题名为《巫师于吉》。《海外故事与场景》是一本收录世界各国中短篇小说的合集,巴维在前言中借助旅行回忆录的叙事方式以充满不舍、感伤和对东方世界无比眷恋的基调搭建了一个世界文学的乌托邦,叙述了包括印度、智利、秘鲁、新西兰、中国等地在内的海外见闻12Theodore Pavie, Scènes et récits des pays d’outre-mer (Scenarios and Stories from Overseas Countries) (Paris: Michel Levy Freres, Libraires-Editeurs, 1853), 5.。在进入故事主要内容之前,巴维为故事搭建了一个叙事框架:一位在中国传教15年的法国牧师在环游世界的游船上行为怪异而引起同船游客的好奇。这位沉默寡言、很少与其他乘客交流的牧师因平时喜欢翻阅中文的大部头作品而被游客们要求讲述一则中国童话故事。在众人强烈要求下,牧师“去船舱翻开一本大部头的中国书籍,拿着一卷印在绢纸上的书,”13Ibid., 258.并讲述了《三国演义》中“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故事开篇,巴维将中国的三国鼎立历史背景描述为每个民族历史都不得不经历的危机时期、革命时期和无政府主义时期,并将孙策及其领地同查理大帝与勃艮第公国相提并论14Ibid.。在故事讲述过程中,巴维对中国古代生活的物质富裕程度进行了超出原文本范围的想象,比如孙策及其臣仆皆穿丝绸服饰,孙策居住在城堡中,出行乘坐轿子,狩猎时的坐骑是来自鞑靼的骏马等。与英译本相比,法国汉学家巴维对故事的叙事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动,对故事中的生活细节进行了一定的增衍,把中国故事纳入到法国世界文学地图之中,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的故事放在一起讲述,为中国故事营造出异域风情,使中国故事呈现出可与欧洲和世界相互融通、相互了解的开放性。这样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异域文化发生兴趣,但尚未使中国故事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获得更多超越原文本的新内涵15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ed.Rainer Schulte and John Biguenet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1992), 73.。
三、德语世界的拓展性改编与阐释
(1) 作家保尔·海泽(Paul Johann Ludwig Heyse,1830-1914)的诗学重构
1856年,德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尔·海泽在青年时代以中篇诗体小说的形式对《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的故事进行了改编,题名为《国王与方士》(Königund Magier)。德国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在与海泽的通信中对小说予以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的选材与众不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16Roland Berbig, Theodore Fontane Chronik (The Theodor Fontane Chronicle) (Göttingen: Verlag De Gruyter, 2010), 682.。与英法两国对《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的改编相比,保尔·海泽首次在真正意义上将德语诗学和文化语境嵌入这则中国故事,为之赋予了独特的美学形式重构和文化内涵重塑。
从作品整体的文学形式角度来说,保尔·海泽对中国故事的改编采用了塞尔维亚五步抑扬格的诗行形式叙事,并且在改编故事中融入了作家自身的美学理论。在《三国演义》故事所改编的《国王与方士》中,一位云游道士(Tao-Sse)凭借自己的布道和法术获得了百姓和官员的青睐,年轻的君王孙策(Sün-Tse)以基督徒身份质疑道士,威胁要将他杀死。孙策的母亲怕儿子因此失去民心,劝说他给道士一个机会:道士为证明自己的法力,必须当众祈雨,若祈雨失败则要被处以火刑。道士祈雨成功,然而孙策仍然下令将他杀死,杀人的行径和道士的阴魂始终令孙策心神不宁17Nicole Nelhiebel, Epik im Realismus.Studien zu den Versnovellen von Paul Heyse (Epic Realism.Studies on the Verse Novels by Paul Heyse) (Oldenburg: Igel Verlag Wissenschaft, 2000), 72.。孙策的母亲劝他到寺庙忏悔自己的罪过,以此安慰百姓和官员们不满的情绪。孙策表面听从母亲的话,亲自前往寺庙,但因为悔过不诚,最终依然难逃道士的诅咒。他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杀死了近臣张昭,并因此精神崩溃,又因为腿伤复发,最终英年早逝。这样的故事情节设置与海泽在1871年至1876年间编纂的《德语中篇小说宝藏》(DeutscherNovellenschatz,1876)前言中所提到的中篇小说结构的美学范式“猎鹰理论”18Vgl.Paul Heyse;Hermann Kurz, Deutscher NovellenschatzBd.1 (German Novella Treasure: Volume 1) (München:Oldenburg, 2007), 20.十分相符。猎鹰理论的名字典故源于薄伽丘《十日谈》中第五天的第九个故事。在故事中,猎鹰是贯穿始终的一件物事,它把冲突推向高潮,起到决定故事发展和结局的作用。海泽认为,一部中篇小说只能讲述一个事件、一个冲突,并且应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每篇中篇小说都应借助一个“猎鹰”——一个关键事物来凸显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19Ibid., 20.。《国王与方士》选取《三国演义》第29回“小霸王怒斩于吉”的故事,以孙策的伤口为“猎鹰”(即线索),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在故事的开头,海泽就不断暗示孙策的腿伤,“他的大腿是否复发了旧伤,他的心中是否萌生了新爱。”20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1864), 86.当看到于吉受到百姓追捧时,孙策“额头青紫,怒从王座上跳起来,艰难地拖着受伤的腿,蹒跚着走上阳台”21Ibid., 88.。大臣张昭力劝孙策放过于吉,并劝他不要动怒:“你的伤口需要静养,箭头的毒已被药膏封住,一旦怒气搅动你的血液,伤口就会复发。”22Ibid.但孙策执意杀死于吉,并在其死后多次见到他的鬼魂纠缠自己。孙策因此心神不宁,“腿上伤口鲜血沸腾”23Ibid., 96.。母亲劝他为于吉修庙祝祷,孙策不情愿地参加这场政治做秀之后,于吉鬼魂仍旧纠缠不止,甚至使孙策一时精神错乱,失手误杀了张昭。这时孙策的伤口再次崩裂,医官宣判了孙策的死期:“箭头的毒再次复发,您的生命已快到尽头。”24Ibid., 99.而此时有大臣私下议论,“如果道士还活着,只有他能抚平这翻涌的血”25Ibid.。在《三国演义》原著第29回中也可清晰看出,孙策“伤口复发”是把整个故事冲突推向高潮、最后导致孙策悲剧结局的一条重要的线索。海泽敏锐地抓住了《三国演义》中的这一线索,对其进行美学重构的结果与作家自身的“猎鹰理论”暗中契合。
从作品的文化内涵角度来说,保尔·海泽为《三国演义》人物形象赋予了更贴近德国本土经验的、同时也与原著相比更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海泽将《三国演义》中孙策和于吉关于民间信仰和迷信问题的论争都置于基督教神学语境之下。《三国演义》原文中,“太平青领道”始创于张角26徐永斌:《从〈三国演义〉中孙策处斩于吉事看中国早期道教在江东的发展》,载《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1期,第77~88页。[Xu Yongbin, “Cong sanguoyanyi zhong Sun Ce chuzhan Yu Ji shi kan zhongguo zaoqi daojiao zai jiangdong de fazhan”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Jiangdong in Early China Based on the Execution of Yu Ji by Sun Ce i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ing Qing Xiaoshuo Yanjiu (Novel Studi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1 (2012): 77-88.],后被于吉一系发扬光大,在江东地区广泛流布。于吉在民间所做的事情只局限于“普施符水,救人万病”27(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毛宗岗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25页。[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Bookstore, 2015, 225.],他的教义《太平青领道》也多是“治人疾病方术”28Ibid., 225.,与核心政治纷争并无直接关系。而在海泽的小说中,于吉的名字直接被改为“道士”(Tao-Sse),所做的事情主要是传播太平道的教义,其宗教性质更为浓厚。海泽甚至在1878年再版的诗体小说中把标题直接改为《国王与传教士》(“KönigundPriester”),以强调道士活动的宗教使命。这或许与当时德国学界对道家经典与基督教思想渊源的解读不无关系。1870年,普兰克勒(Reinhold von Plänckner,1820-?)与施特劳斯(Victor von Strauss,1808-1899)曾经先后把《老子》译成德文,后者甚至把老子的道家思想归为“原始基督教”范畴,认为老子是受到“上帝启示”的先知,因此拥有非凡的智慧29Victor von Strauss, Lao-Tse, Tao Te King (Leipzig: Breitkopf und Härtel, 1870), 129.。或许受此影响,在同时代的海泽笔下,于吉作为道教领袖,布道方式上带有天主教色彩,并且因此吸引了底层民众:“一位道士来到城中,被人唤作圣人。他用赐过福的水为人们治病,他在永恒青春之中不死。”30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87.于吉自述自己得到 “通向安宁之道”《太平青领道》。“一共有一百多卷,其中五十卷是上古的法术咒语,可使身体康复;而剩下的教义,是教人如何永葆青春。”31Ibid., 89.而《三国演义》中百姓对于吉“焚香伏道而拜”32(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毛宗岗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25页。[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5, 225.]的推崇则被海泽描写成了一场类似天主教地区纪念圣人的节日游行:“妇女们晃动着香炉,孩童们在街道上撒花;圣人就立在道路中央,苍白的胡须直至腰际,他的容貌灿烂流光,如同五月的桃花。”33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88.海泽并没有去过中国,也并非汉学家,他以西方的表述对中国道士的修仙和方术进行了瑰丽的想象,依赖德国人熟知的基督教语境下的传统和习俗,为使德国读者达到更好的理解效果而采用他们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以此构造并表述中国,使中国在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话语中“存在”。34爱德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Edward Said, Dong fang xue(Orientalism), trans.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29.]
其次,海泽为孙策赋予并加强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启蒙主义思想,使一个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德语文学的土壤中获得了新生命。《三国演义》中的孙策具有一种朴素的启蒙信念,认为人读书应明理,坚决反对迷信,同时又表现出略显骄纵狂妄的自信——“吾命在天,妖人决不能为祸”35(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毛宗岗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25页。[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Press, 2015, 225.]。从始至终,孙策对民间迷信十分不屑,态度坚定,毫无半点动摇。而在《国王与方士》中,孙策则以上帝信徒的身份宣示自己的政治身份合法性:“身为国王,身为上帝的儿子,我维护父亲的荣耀和基业,定要把伪善者打倒在地。”36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权力只属于一个人,它属于那个被人需要的英雄和救世主,而不属于一个在永恒上帝面前不自量力的伪善者”37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学者罗瑟在其著作中认为这是一种近似于自然神论的启蒙主义思想38Ernst Rose, Blick nach Osten.Studien zum Spätwerk Goethes und zum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Looking East: Studies on Goethe’s Late Work and the Image of China in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19th Century) (Bern:Herbert & Cie Lang AG, 1981), 155.,与当时德国思想界的启蒙话语暗中契合。18世纪以来,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等人开创的德国启蒙理性哲学思想并不否定基督教的精神内涵,而是力图使理性与信仰协调共存。启蒙主义作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曾经把追求真理的求知欲称为上帝恩赐给人类的最高贵的冲动,并且认为人为了获得真理而付出的不懈努力值得赞美,不过“纯粹的真理只属于上帝”39Gotthold Ephraim Lessing,“Eine Duplik (1778)” (A Duplicate), in Werke und Briefe in zwölf Bänden.Werke 1774-1778, Hrsg.v.Arno Schilson, Bd.8 (Works and Letters in 12 Volumes.Works from 1774 to 1778, ed.v.Arno Schilson, Vol.8) (Frankfurt am Main: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9), 510.。德国思想界对启蒙主义的讨论总是被约束在基督教神学的框架之内,而海泽在其文学文本中所刻画的基督徒孙策也体现了西方意识形态向文学文本的这样一种分配40爱德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6页。[Edward Said, Dong fang xue(Orientalism), trans.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16.]。当孙策指责道士时,他表现出的并非武断和盛气凌人,而是颇具思辨性地以理服人:“我认得你和你的同类,你们一切谦卑都是伪善,你们的魔法是人类的疯狂,你们的永葆青春是诡计,这在你们教派中从未绝迹。”41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也许你们知道通向太平的路;但每个走上这条路的人,内心那本想走向真理的清醒声音就被麻醉,然后把身体埋进自己的谎言中。”42Ibid..孙策躁动不安、追求荣誉和真理,并且永不停歇地追求建立新的功业,这种主动好战的、渴望胜利的存在体现的是一种浮士德式的现代性的生命目标,与道士所提倡的无为、不争的“太平道”正相抵牾。与原著相比,这也是海泽为孙策故事注入的源于德国本土经验的全新思想内涵。
最后,在对孙策悲剧的书写上,海泽既表达了对他的同情和惋惜,又为人物赋予了比原著更为丰富饱满的人文内涵。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孙策的评价是“骁勇,与项藉相似”43(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毛宗岗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24页。[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Shushe, 2015, 224.],故而被人称作“小霸王”。他虽然战功赫赫但暴躁易怒,由于树敌众多而遭到刺杀,又加之受到于吉鬼魂的纠缠,最后精神崩溃而死。在孙策斩于吉一事上,不难看出罗贯中对孙策持有批判态度,而对于吉则表现出了同情。但在《国王与方士》中,海泽则更多地表现出对孙策的同情。这一点体现在故事开头和结尾对孙策的赞美诗中:“像一只虎,整天/在洞中等候猎物,/像一只鹰,突然/从高处扑向食物,像一只雄狮,张开大口,/百兽发抖,不语屈服;/我们的国王伟大无比,/他的名声越海过洋,/如烟雾,让敌人窒息,/如芬芳,让朋友舒畅,/翻腾在古老的长江边,/如初升艳阳,长久放光。”44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90.从诗的意象和情感来看,海泽的诗句与《三国演义》中的赞诗是遥相呼应的:“独战东南地,人称‘小霸王’。运筹如虎踞,决策似鹰扬。威震三江靖,名闻四海香。”45(明)罗贯中:《三国演义(上)》(毛宗岗批评本),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228页。[LUO Guanzhong, Sanguo Yanyi shang Mao Zonggang pipingben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hangsha: Yuelu Shushe, 2015, 228.]但与《三国演义》不同的是,海泽在《国王与方士》最后又再次引用关于孙策的赞美诗,并评论说“他的崛起曾焕发光芒,他的覆灭令人忧伤”46Paul Heyse, Gesammelte Novellen in Versen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in Verse) (Berlin: Verlag von Wilhelm Hertz, 1864), 100.。由此可见作家对少年英雄年寿不永的惋惜。另外海泽还用心理分析等文学手法为孙策赋予了许多内心独白,既表现孙策少年得志、战功赫赫之时的焦虑,如“在高墙之内的庆功宴上/坐着年轻的雄狮,我们的君王,/酒壶已温,宾客满堂,/他却并不说话,杯中的酒/没有濡湿他的嘴唇,外面的歌谣/也没有浸润他的心灵”;“他倾身闭眼,/梦境夺走了他清醒的精神。/这梦就像所有权威者梦到的那样,/他内心的不满无法餍足”又表现年轻君主面对道士威胁自身统治时的困惑和彷徨,“为什么他要来?难道我不是遵从真理?/为什么一个说谎者的鬼魂要这样暗地里与我纠缠?”;“我为了逃离他,竟要在谎言的沼泽里弥足深陷。我遇到撒谎的骗子,竟要用谎言的忏悔来摆脱这一切。我多么不愿意这样”47Ibid., 98.。这些增衍的内容使孙策的人物形象在离开中国古典文学土壤的德语文学视域下获得了更具丰满血肉的新生命。
(2) 汉学家与学者对故事的征引与阐释
继保尔·海泽之后,德国学者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相继表现出对《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的关注。德国汉学家与学者对该故事的征引和阐释呈现出与原著内涵不同的拓展的视角。1892年,德国驻华外交官卡尔·阿恩特(Carl Arendt,1838-1902)在《民俗协会杂志》(ZeitschriftdesVereinsfürVolkskunde)上发表的文章中再次叙述了孙策和于吉的故事,并对《三国演义》故事叙述过程中引人入胜的文学表现形式表达了赞赏和肯定。关于阿恩特对《三国演义》“小霸王”故事的关注是否受到了保尔·海泽《国王与方士》之影响,目前尚无法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阿恩特与保尔·海泽对该故事有着相似的理解和阐释。阿恩特对此故事并未止步于仅做讲述,而是将其与《东周列国志》中另外五个故事放在一起,将它们共同作为论证中国民间思想的例子在文章中加以叙述,并认为这些故事所讲述的“几乎都是鬼魅的力量对以暴力和无理的方式侵犯其同胞生命的人进行报仇”48Carl Arendt, “Aber- und Geisterglauben der Chinesen” (Chinese Superstitions and Ghost Beliefs), in Zeitschrift des Vereins für Volkskund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Association) (Berlin:Verlag für A.Asher und Co, 1892), 259.的问题,可以因其背后相同的思想而建立起联系:
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公认的历史人物,那么这些嫁接在真实事件上的神迹则要表达的是,中国的民间思想如何形成了一个观念,一个他们凭直觉当作真理、更多是感觉到而不是认识到的观念,即世俗历史是末日审判。它(中国民间思想)明确地试图将这个观念直观地表现出来。49Ibid..
阿恩特自称这种自由式的解释并不是他所征引的个别作家的个人发明,而是“植根于大众的一般思维方式,代表了中国人的普遍观点”50Ibid..。
除了阿恩特之外,德国学者罗瑟(Ernst Rose,1932-2013)在《歌德晚期作品与19世纪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1981)一书中也提到了《三国演义》“小霸王”故事,并对保尔·海泽的《国王与方士》进行了阐释和解读。罗瑟认为海泽在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改写得很成功:在原著《三国演义》中,孙策是个暴躁易怒的篡权者,而在海泽的《国王与方士》中,孙策则被塑造成为一个“早熟的、思想现代的年轻人”51Ernst Rose, Blick nach Osten.Studien zum Spätwerk Goethes und zum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Looking East: Studies on Goethe’s Late Work and the Image of China in German Literature of the 19th Century)(Bern:Peter Lang AG,1981), 155.。罗瑟认为整体来说,海泽用现代化的思想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了改写,使其呈现出一种“心理上的现代化”52Ibid., 174.。此外,德国学者尼尔西贝尔(Nicole Nelhiebel)在专著《青年海泽小说中的中国母题》(EpikimRealismus.StudienzudenVersnovellenvonPaulHeyse,2000)中也对《国王与方士》中的故事情节进行了阐释。该学者认为,孙策作为一位专制主义的统治者,害怕自己失去民心,进而失去对官员和子民的控制,因而把道士视作自己的竞争者。尼尔西贝尔的解读主要围绕着海泽小说所改编的基督教语境进行,在她的分析中可看到这样一种在西方汉学界普遍存在的观念前提,即道士作为宗教人士并不觊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哪怕是曾经的黄巾起义首领们也并非想建立一个农民政权53Max Kaltenmark,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Ching,” in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eds.Holm Welch and Anna Seide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5.,而只是把自己的世俗政治角色看作一种过渡性的解决54Anna Seidel, “Taoist Messianism,” Numen 2 (1984): 161-74.,他们本身对于称霸一方的世俗权力并无野心。在她看来,孙策要“把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统一在自己身上”55Nicole Nelhiebel, Epik im Realismus.Studien zu den Versnovellen von Paul Heyse (Epic Realism.Studies on the Verse Novels by Paul Heyse) (Oldenburg: Igel Verlag Wissenschaft, 2000), 74.,因此不能容忍道士获得舆论上的青睐,也不能容许百姓对道士的信仰。然而她认为,“杀人的行为并不能让孙策真正铲除道士,却反倒让道士成为殉道的圣人”56Ibid., 74.。
从上述德国汉学家和学者对《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情节的征引和阐释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故事的阐释体现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东方的有意建构,而这种人为的建构从始至终表现出一种内在的一致性57(美)爱德华·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页。[Edward Said, Dong fang xue(Orientalism), trans.WANG Yugen,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1999, 2.]。他们力图从文学作品中找出符合西方话语语境的逻辑,佐证并解释现实世界中他们所认识的“中国”。在蕴含着西方政治话语的语境下,德国学者力图发掘小霸王孙策这则故事中的体现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旨在完成并强化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自我确认。
四、结 语
《三国演义》第二十九回“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相继引发了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汉学家及作家的兴趣,对其进行不同形式的翻译、解读、文学重构和文本阐释。《三国演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的文本经历了跨越时代和文化的流通,在英、法、德语世界的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小霸王怒斩于吉”故事在欧洲的流变体现了中国故事在世界文学系统流传过程中的传承性、开放性和拓展性。该故事在欧洲的流变、改编与阐释体现了中国故事融入西方文化语境需应对的矛盾:文学阐释的流变过程受到不同民族国别与源语言国家历史文化交往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不断的扩展与外延中丰富自己的内涵;然而在作品的思想内涵得到丰富和扩展的同时,对其阐释解读的过程也难免经历误读和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