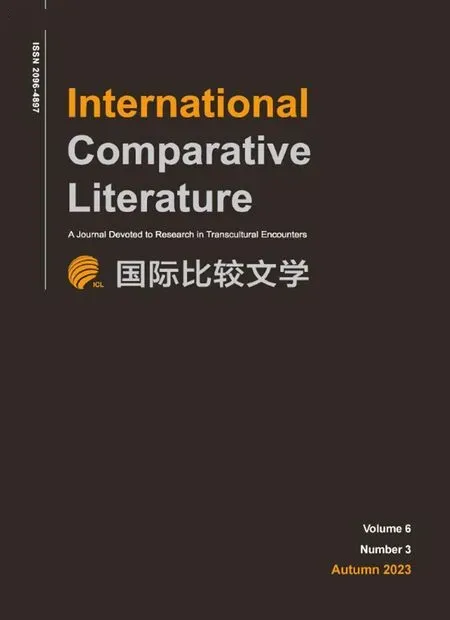现代欧洲的自我追寻之旅
——凯泽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的中国文化空间书写
郑家欣 岭南师范学院
德国哲学家赫尔曼·凯泽林(Hermann Graf Keyserling,1880-1946)的环球游记《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于1919年初版后再版6次,售出5万册1参看(德)何心鹏: 《论赫尔曼·凯泽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一书中的中国印象》,高琳琳译,见余明锋、张振华编:《卫礼贤与汉学:首届青岛德华论坛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84页。[Volker Heubel, “On his Impression of China in Hermann Keyserling’s A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trans.GAO Linlin, in Weilixian yu hanxue: shoujie Qingdao dehua luntan wenji (Richard Wilhelm and Sinology: Essays in the First Germany-China Forum in Qingdao), ed.YU Mingfeng, ZHANG Zhen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 184.],在德国畅销热度仅次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此书的热卖也使得凯泽林在一战后的欧洲文化界声名鹊起。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1911到1912年间到访印度、中国、日本、美国最后回到欧洲这段旅途中的所观所感,中国部分约占全书篇幅五分之一(他在中国的旅行路线为:广州—澳门—青岛—济南—北京—汉口—上海,历时约两个月2凯泽林在日记中并没有记录到达每个城市的日期,从他寄给母亲的信可大概推测他在中国的逗留时间大概为1912年3月到1912年5月(在中国写的两封信于1912年3月8日、14日从香港寄出,接下来一封信是1912年5月17日在日本京都写下,由此可推测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应该就是凯泽林在中国旅游的时间)。)。目前国内关于凯泽林的研究大多注意到中国哲学对其思想的影响,并以此管窥20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在对西方文明前途的忧虑下从中国文化中寻找良方的思潮3例如,顾彬、曹卫东、董琳璐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知识分子怀疑自己所处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解决西方文化危机的方案(参看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See Wolfgang Kubin: Studies on “Other,” trans.CAO Weid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又看曹卫东:《同异之辩:中德文化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2~263页。) [See also CAO Weidong, Tongyi zhi bian:zhongde wenhua guanxi yanjiu (Discussions about the Common and the Differences: Studies on the China-Germany Relationship),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6, 262-63.] 又看董琳璐:《凯泽林世纪纪行的上海印象与哲学反思:〈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见张帆等著:《德语文学中的上海形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65页。)[See also DONG Linlu, “Kaizelin shiji jixing de shanghai yinxiang yu zhexue fansi”(Keyseling’s Impression of Shanghai and Philosophical Refection during His Trip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in Deyu wenxue zhong de shanghai yinxiang (The Impression of Shanghai in German Literature), ed.ZHANG Fan,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20, 65.] 方厚升注意到,凯泽林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很复杂,日记中有不少前后矛盾的地方,但总体而言,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评价还是很高的。(参看方厚升:《君子之道:辜鸿铭与中德文化交流》,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3~155页。)[See FANG Housheng,Junzi zhi dao: GU Hongming yu zhong de wenhua jiaoliu (The Doctrine of Junzi: GU Hongming and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Xiamen: Xiamen Universtity Press, 2014, 153-55.],在这思潮下晚清西人眼中腐朽落后的中国形象发生了一些正面变化。然而,有学者对此变化产生质疑,认为“中国一些学者将该现象夸大为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中华文明救西论’的重大主题与时代思潮,虽然经历过思想的‘现代性焦虑’与‘一战’浩劫的英国似乎有改造自身文明的渴望,但如认定他们就是拜东方或中华文明为救世主,那显然缺乏足够的证据。”4参看叶向阳:《英国“中华文明救西论”辨正》,见《国际汉学》2018年第1期,第158页。[See YE Xiangyang,“Yingguo ‘zhonghua wenming jiuxi lun’ bianzheng” (Distinguishing the Viewpoint “Chinese Culture Saves the West”), Guoji hanxue (International Sinology) 1 (2018): 158.]凯泽林旅行日记中对中国文化的正面书写看似也是这种“中华文明救西论”的典型代表,到底能不能充分证明当时西方知识界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化解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最佳方案?本文通过结合历史语境和思想史背景,分析凯泽林《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的叙事模式和修辞策略,考察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状况及背后的主客观原因,进而探讨该文本的中国文化空间书写和中国形象构建在德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成和欧洲现代性展开中扮演何种角色。
一、自我追寻之旅
自16世纪起,欧洲贵族青年就有到异域旅行以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价值的文化传统。到了18世纪这种欧陆壮游(Grand Tour)甚至普及到市民阶层。而到了19世纪,铁路的建设和航路的开拓开启了一个更舒适更快捷的大众旅游时代,也使得环球旅行观光逐渐升温。凯泽林的旅行既继承了欧洲贵族青年的壮游传统,又带有现代大众旅游观光的性质,还具有文化朝圣的意味,更是一次自我追寻之旅。《一个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开篇(扉页右上角)即言:“通往自我的最短路程是环游世界。”5Hermann Keyserling, 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 (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München/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9), 1.环球旅程看似漫长,但在凯泽林那里,这是自我追寻的最短途径,在这路途上认识他者的最终目的还是指向认识自我。
我还要出门远游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的漫游期已经过去了。那些收集素材来丰富我的内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还没有耗尽、从未停滞的生命里,到了一定的年龄,自己必须要有一个维度转换。一个在年轻时就以扩张和丰富人生为目标的人,到了更成熟的阶段,依然还会有动力追求进深发展和潜力激发。6Ibid., 3.
印度智慧所教导的永远都是对的,一个灵魂在成熟并享受到知识的福分之前必须取得所有经验,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如果有人到达目的而没有经过绕弯(其实这个绕弯看起来是虚假的),那么他的到达目的也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目标并不是从外面能看出来的,而是在内在转变当中。每一个存在阶段都对应一个特别的真理,蝴蝶的生命程序不仅对毛虫有益,对最后的目标更有益——正是为了达到最后目标,它必须首先成为毛虫然后成蛹。人的灵魂也是这样[……]因此,越丰富的性情需要越丰富的经验。因此,对一个人来说,从各种意义上讲环游世界的绕圈是最理想的通往自我本质的途径。7Ibid., 645-46.
由此可见,凯泽林的旅行带有内在成长的自我要求,他的旅行书写也就同时隐含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叙事模式的烙印。8经典成长小说的叙事模式通常为:主人公在游历漫游中结识不同的人、体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而受引导和塑造,最终融入社会并对自我和世界有了新认识。主人公离乡漫游又回乡,在空间变换中获取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外部世界的印象为他自我反思提供质料(参看谷裕:《德语修养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页)。[See GU Yu,Deyu xiuyang xiaoshuo yanjiu (German Bildungsroma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3,43.]已到而立之年的凯泽林希望通过异域旅行重新激发成长潜能,原因就在于他意识到欧洲文化的单一性已成为他的成长阻碍:“我想让我的灵魂转变成新的状态,但欧洲不再推动我了,我对这个世界已经太熟悉了,这个世界的局限性很大,整个欧洲实际上是属于同一种精神的。”9Hermann Keyserling, 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 (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München/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9), 6.环球旅行中与他者的相遇为他提供一个“维度转换”的契机,异域文化的多元性能丰富他的精神世界。然而,游记研究学者岑科(Volker Zenk)认为,凯泽林并不像地理学、人类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的探险家那样观察外在客观事实世界,而是专注于内心世界的自我反思和体验,他的环绕世界之旅实质上是环绕自我之旅,他对他者文化的介绍其实只是为了寻找另一种表达自我的可能性,他的日记其实是他“精神综合治疗”(Psychosynthese)10一种把精神分析和冥想沉思、身体锻炼结合的心理治疗法。过程的记录。11See Volker Zenk, Innere Forschungsreisen: literarischer Exotismus in Deutschland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 (Inner Research Trips: Literary Exoticism in German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ldenburg: Igel Verlag, 2003), 172-174.岑科的观点注意到了凯泽林内在成长的需要同时反映了战后欧洲的主体性危机,那么,凯泽林日记文本建构中国文化的话语策略如何反映这种欧洲现代文化症候?其对中国文化空间的再现又表达了重构现代分裂主体的何种进路?
二、中国文化空间作为蜃楼幻景
不少晚清西人游记往往描摹出封闭腐朽、落后野蛮的中国形象,而凯泽林在日记中对中国儒家、道家、礼制、文学等思想文化以及中国风光、美食、劳动人民大加赞赏,文本呈现出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观看之道可从中国部分开篇描绘香港海岛景象的视觉修辞管窥。岛屿在旅行书写中通常承担着一种特殊的文化叙事功能,岛屿给漂泊者提供着陆地,也为那些试图逃离现代文明喧嚣的人们显示了“生活在别处”的可能性,一个新的文化世界。12参看张德明:《旅行文学十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63页。[See ZHANG Deming, Lüxing wenxue shijiang (Ten Lectures on Travel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tiy Press, 2021, 263.]
在这里,远东的大自然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感召力:一尘不染的纯净,令人沉醉的整洁;而这种整洁在我们的家乡只能创造虚拟的抽象价值!这样的大自然已然完美展现了上帝的风格,许多极其吸引眼球的中国画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艺术本体。当我最初远眺暮色下的大海时,海面上仿佛笼罩着一条长长的、乳白色的雾缎。在此之后不久,我穿过这层缭缭云雾,骤然看到数不清的海岛向我游弋过来,令我为之惊愕不已!没有任何一目了然的视野可以使我明白,这些岛屿并非来自天上;面对眼前的大自然,显然需要同样的想象力,方才能够抓住远景的关联,正如同欣赏东亚的绘画一般。
从这一刻起,我已然明白:在中国,我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视觉导向者;因为这里的所有表象都充满了思想。我突然预感到,我将要在这里接受,我此前从未经历的表象与本质的严峻考验。13(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殊、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4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3-4.]
在原文编排中,香港这一篇其实是放在整篇中国游记之前,暗示了他此趟旅程想看的中国是一个不参杂任何西方文化元素的空间,一个去政治化的纯净的文化统一体。中国文化在凯泽林面前就如雾中风景,他登高望远、雾里看花,看海上诸岛犹如天上仙境。这种游客凝视正是凯泽林观看异域文化的独特视角,文本构建的中国文化空间也因此仿如海市蜃楼幻景。凯泽林虽在“香港篇”中说要转化成为一个“视觉导向者”(Augenmensch),但实际上游记中他对外在事物的客观描述远少于探讨精神实质的个人感悟。他的形而上学训练使他习惯于登高远眺,从宏观的、超越的角度阐释具体的表象世界、深究表象背后的本质:“对我个人来说,沉浸在事物的意义当中让我感到很满足。这时大量事实涌来会对意义的把握毫无益处,反而会成为极大阻碍。谁要听清楚一个世界的根音,他就需要从几个和弦里仔细听出来,而太多乐声会混淆视听。”14Hermann Keyserling, 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 (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München/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9),19.他相信一个人要是沉浸到自我当中越深,就越能把握更深层的意义关联,他的精神涉足的境界就越宽广,最终达到如神一般的全知全能的程度。15See Hermann Keyserling, Schöpferische Erkenntnis (Creative Knowledge) (Darmstadt: Otto Reichl Verlag, 1922), 29-33.在这种观看模式下,中国文化被呈现为梦幻般的表面化的装饰物。即使他到了中国之旅首站广州,城市的脏乱依然无法给他的这种“精神审视”(geistige Betrachtung)造成干扰。
广州的街道无论外观抑或色彩,都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美丽,愈来愈令我沉醉着迷。各式各样的形体都代表了最高级的感官文化。几乎没有一种使用工具,没有一种阿拉伯花饰,不是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当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散尽之时,整个城市看上去仿佛是一个梦幻般的精灵,在黑色和金色相间的大地上演奏了一曲荡人心腑的交响乐。在黝黑的夜色当中,遍地冉冉升起了纤细的光体,处处闪烁着热情激昂的汉字。16(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14.]
然而,这种观察与其说是透过表象深入实质,不如说是感官经验和神秘直觉互融互动的过程,与客观真实始终还是有一定距离。同时代的宗教学家、文化哲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注意到凯泽林在书中极少提及当地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当下政治事件,可能因为这些跟他那精致的贵族精神相距太远;而他在写作中并不追求传统语文学和历史学要求的精确性、逻辑性和理性,文本中尽是“充满幻想”的综合和宗教式的冥想。17See Ernst Troeltsch, “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2 Bände by Graf Hermann Keyserling (Review)” (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2 Bands by Graf Hermann Keyserling),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Historical Jounal) 123, no.1(1921): 90.宗教学家琼斯(Rufus Jones,1863-1948)在书评中把凯泽林的写作过程与心理学家明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进行了一番比较:
雨果·明斯特伯格博士过去每当有很难的讲稿要准备的时候,常常会去剧院,坐在那儿,眼睛盯着舞台,绞尽脑汁想着即将到来的演讲题目。当帷幕降下时,演讲大纲就尽在手中了。类似的,凯泽林伯爵从一个国家旅行到另外一个国家,投入到各个国家和各色人种的诸种活动中,就为了他可以不受干扰地思考!他对自己脚踏之地的客观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兴趣。他是个知识贫乏的地理向导。他参观很多风景优美的奇观但不去描述它们。一些伟大惊人的事物出现时,他只是忙着思考这些事物的内在如何。我们一直读到的是一个灵魂的日记,而非外在世界的风景和环境。18Rufus M.Jones, “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 (Review)”,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35, no.3 (1926): 279.
从整本日记的修辞风格看,琼斯的类比不无道理。尽管凯泽林本人身临现场,但异域文化对他来说只是舞台上的景观。他只是远远坐在那里观看而不参与,他甚至无视舞台上发生着什么,脑子里陷入自己的沉思世界。受柏格森反理性、反逻辑思想的影响19凯泽林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与柏格森交往,1907—1936年间与柏格森通信往来一共24封,从这些来往信件可看出柏格森非理性倾向的生命哲学思想对凯泽林产生深刻影响。[See Hugo Dyserinck, “Die Briefe Henri Bergsons an Graf Hermann Keyserling” (The Letters of Henri Bergson to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German Quarterly Journal for Literary Studies and History of Thoughts) 34 (July 1960): 169-88.],他在日记中记录的个人思考具有碎片化倾向,整本日记成了他内在思想的意识流记录。游记中很少出现关于他在旅行途中遇到的真人真事的记述,而如果把这些仅有的少数段落全都删除,那么剩余大部分篇幅仅为个人即兴感想。这本书虽然题名为日记,全文却并没有出现任何日期。忽略凯泽林一直强调的地理学意义上的旅行路线,那么这本书其实可看作是一部各国哲学思想的简介手册,提供一种对全球各大文明体系的文化概览。不同文化空间被去时间化地平行并置在一个博物馆里,供欧洲游客按照各人喜好制定自己的参观路线。有研究者认为,凯泽林在游记中面对千差万别的各国文化时像古希腊海神普罗透斯那样经常变脸,改变自己的价值标准去适应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整本游记呈现为动态的意识流般的文化大杂烩。20See Volker Zenk, Innere Forschungsreisen: literarischer Exotismus in Deutschland zu Beginn des 20.Jahrhunderts (Inner research trips: literary exoticism in German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Oldenburg: Igel Verlag, 2003), 179.See also Sławomir Leśniak, “Graf Hermann Keyserling und Europa”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and Europe),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58, no.3 (2005): 293-305.有学者甚至形容凯泽林这部游记为“原创的、但并不十分可口的心理-哲学鸡尾酒”,只因刚好迎合世纪之交欧洲人对东方文化的倾慕而畅销。21See Suzanne Marchand, “Eastern Wisdom in an Era of Western Despair: Orientalism in 1920s Central Europe,” ed.Peter E.Gordon, John P.McCormick, Weimar Thought.A Contested Leg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7.
凯泽林尝试在旅行书写实践中把视觉表象(Schein)与精神实质(Sein)综合起来,然而,从篇章结构和逻辑严密性来看,整个日记文本其实只是意义连结十分松散的组合拼贴。他在短暂的两个月中国行程内途径七个城市,可推想他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而非逗留在城内景点细心欣赏,那么他对各种自然风光和历史名胜也只能匆匆一瞥。他在日记中极少交代世界时政现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重大历史变革所知甚少。他来华前在印度听到中国爆发辛亥革命的消息,加上身患严重肠胃炎,曾一度想过取消行程回国,但后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订了船票。22See Ute Gahlings, “Keyserlings Begegnung mit China und Japan”(Keyselring’s Encounter with China and Japan), in Hermann Graf Keyserling und Asien.Beiträge zur Bedeutung Asiens für Keyserling und seine Zeit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and Asia.Articles on the Importance of Asia for Keyserling and His Time), ed.Ute Gahlings, Klaus Jork (Biebelsheim: Edition Vidya, 2000), 157.他把辛亥革命评价为“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暴力革命”,对于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毫无意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也未曾把这场革命当回事”,“不久之后,孙中山将不再被作为英雄人物受到人们的敬重”。23(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6~8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8.]实际上凯泽林是革命的切身“受害者”,虽然他在日记中只字不提在广州中枪一事,但他在给母亲的信上写道:“我怀疑我在这里是否还能看到更多东西,最近我在广州刚被枪击中,必须乘坐舢板赶紧逃离这个城市的子弹,登上轮船。”24参看凯泽林于1912年3月14日寄给母亲Johanna Keyserling的信。此手稿现藏于达姆施塔特市图书馆,扫描件存于该图书馆电子数据库。http://tudigit.ulb.tu-darmstadt.de/show/Keys-161/0403/scroll,2022年6月21日检索。另外,他对辛亥革命的批评恐怕也跟好友卫礼贤和辜鸿铭有关。辛亥革命后,卫礼贤的家成为包括辜鸿铭在内的许多中国旧派士大夫的庇护所,而凯泽林跟二人都有密切交往。25参看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页。[See Wolfgang Kubin: Studies on “Other,” trans.CAO Weido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凯泽林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到革命后逃亡青岛的这些前朝遗老如何以雄厚资本带旺当地各行各业以及他们与殖民者的各种利益勾连,关于大批清朝遗老在革命后移民青岛的现象。参看陆安:《辛亥革命后清朝遗老移居青岛世态百象》,见《文史春秋》2011年第8期,第40~44页。[See LU An, “Xinhai geming hou qingchao yilao yiju Qingdao shitai baixiang” (The Life of Former Aristocrats of Qing Dynasty after their Immigration in Qingdao), Wenshi Chunqiu(Jounal of History) 8 (2011): 40-44.]在革命烽烟四起、新潮激荡的时代来到中国,凯泽林面对过去欧洲知识界想象的历史中国与他亲眼看到的当代中国正出现割裂,他选择了紧跟两位好友步伐,沿着文化保守主义路径竭力捍卫一个革命前的文化中国的想象。26这种知识趣味——对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和对现实中国的时政社会状况的无知——甚至延续到今天的海外中国研究,“汉学”和“中国学”的分化反映了海外中国学学界存在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割裂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参看张西平:《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统一性是汉学研究的出发点》,见《国际汉学》2022年第1期,第5~7页。[See ZHANG Xiping, “Lishi zhongguo he dangdai zhongguo de tongyixing shi hanxue yanjiu de chufadian” (The Starting Point of Sinology Should Be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Guoji hanxue (International Sinology) 1 (2022):5-7.]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与沈子培(沈曾植)的一次谈话,但是没有记录谈话内容,只有对沈本人印象主义式的描写。在这幅印象主义的肖像画面前,他又在沉思中对“中国性”作一个普遍的抽象化的定义,概括出纯粹的、伟大的、极致的、圆满的中国本体。由此想象未来理想人类的样式,“未来阶段最有教养的人与其说是同现代人类、不如说是传统的儒家学者更为相近”,“与可以想象的最高级的人类生存状态相比,传统的‘中国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27(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165.]然而,他在游记中描述中国人的一些特质,比如“实事求是”(sachlich)、“受良好教育”(gelehrt)、“有精神追求”(geistig),类似的语词在《欧洲光谱》中也被用来形容德国人的国民特性。28See Hermann Keyserling, Das Spektrum Europas (The Spectrum of Europe) (Stuttgart/Berlin: Deutsche Verlag-Anstalt,1931), 107-156.与其说这说明了凯泽林找到了中国人和德国人的民族共性,不如说他始终带着保守主义的眼镜去审视每个民族,所看到的并非每个民族的独特个性和现实处境,而只是他个人想象的理想样式。
凯泽林在日记中多使用现在时去描述中国文化,例如,在广州,当他描述士兵们毁坏寺庙神像这个行为和民众对此的反应使用了过去时,接下来使用现在时对中国人宗教信仰进行长篇大论。在澳门,记述中国人在赌场赌博的部分使用了过去时,而接下来转为现在时大段介绍印度文化中关于游戏的人生哲学。在人类学话语中,现在时的使用暗示着叙事者与他者文化处于一种看与被看的关系,揭示了异域文化的知识生产机制。29See Johannes Fabian, Time and the Other: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6), 86-87.凯泽林使用现在时书写中国文化现象,描绘出一幅本质主义化、无历史感的中国文化风景画,把中国文化封存在一个停滞不动、永恒不变的景框之内,仅供远距离审美消费,过滤了一切威胁性。始终保有这种浪漫怀旧情怀的凯泽林在旅途上遇到精神实质(Sein)与客观现象(Schein)出现矛盾时,往往给不能理解的文化现象蒙上一层理想主义的面纱30理想主义(Idealismus)在这里,既指一般意义上追求一些与现实情况有距离但应该实现的状态,又指哲学意义上思想观念决定事实,主观世界的理念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和依据。。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在北京至汉口途中火车被一群军阀士兵拦住的意外事件,后来军阀被火车上几位“和事佬”劝退。之后他没有交代当时中国内政局面,也没有描写他紧张和恐惧的心情,反而说中国人爱好和平:“即便他们使用了武器,看上去也是心不在焉”,“中国的文学很少将战场上的统帅描绘为英雄人物”,中国是一个“自有史以来便将和平标榜为最高理想、并为此不惜付出一切的民族所在的帝国”。31(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2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142.]然后他引用一则中国诗人的例证以说明中国人爱好和平32凯泽林虽然只介绍了人物和情节而没有点名诗人的名字,但根据他的描述可推测这个关于李白的故事应该来自冯梦龙的《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虽然他毫不讳言这则故事的传说(Legende)性质,但日记文本叙事以过去代表现在,以个人特例说明普遍民族特性,以虚构故事模糊历史真实,渲染出一种浪漫情调,而军阀混战的政治现实被理想主义的迷雾和谐屏蔽了。当凯泽林在旅途中遭遇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的差距时,他也尝试把体验到的文化冲击置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框架内去解释。在北京餐馆进餐时,他对中国人用海蜇作食材感到困惑不解,但他又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人使用了欧洲人不常用的食材,只是中国人一种沿袭传统的习惯而已。而当他还接触到用蛆虫做的菜肴时,他坦然首先感到很“惊恐”,但依然觉得这道菜肴“非常可口”。33(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5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105.]与其他一些西方旅行者相比,凯泽林并没有因为看到中国人吃海蜇、蛆虫而批评中国人的原始野蛮,反而大胆尝试,也极力把这种惊恐体验放到文化相对主义的框架内理解,以取得一定的安全感和心理慰藉。这样的修辞策略一方面呈现出一个敢于冒险、充满男子气概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东—西两极分化的认知倾向。方维规认为,凯泽林把西方—东方的文化关系置于“我—你”的二元结构内阐释,东西方文化差异就被相对化了。34See Fang Weigui, Das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Ein Beitrag zur komparatistischen Imagologie (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German Literature.A Studies on the Comparative Imagology)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2), 273-76.另外,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格的描述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如中国文化既务实理智又充斥各种鬼神崇拜,中国人既残暴无同情心又道德水平极高……这些矛盾都让他经历“表象与本质的严峻考验”。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天,他承认在中国受到的教育很多,中国给了他许多新体验,但他不满意自己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无能力更多了解中国,致使这些中国知识没有给他带来期望的改变:“我来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离开的时候几乎还是原来的模样”35(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殊、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7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167.]。凯泽林游记文本中的现实与理论的张力,正体现了欧洲现代形而上学危机的文化症候。从哲学史角度看,他感受到的这种表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理念与现实的分裂,正是现代哲学危机在跨文化相遇中的一种表现:现代的特产——主体性原则使得古代世界观和生活的统一性失去了,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陷于二元分裂的状态,也使得哲学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和时代语境而成为头脑中的纯粹的理论活动。36参看张汝伦:《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见《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23~42页。[See ZHANG Rulun,“Xifang xiandaixing yu zhexue de weiji ”(Western Modernity and the Crises of Philosophy),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5 (2018): 23-42.]
日记的断片式记录就像西洋景(Kaiserpanorama)37Panorama又译为“拉洋片”、“全景图”,是一个大箱子,里面是一个带有放大镜的鼓,鼓的内壁贴有异域风光图片的纸,还可以旋转。箱子上有数个往里观看的孔,人坐在椅子上,通过镜孔可以看到里面放大的画面。参看曾军:《本雅明视觉思想辨正》,见《学术界》2013年第2期,第60~69页。[See ZENG Jun, “Benyaming shijue sixiang bianzheng”(Distinguishing Right from Wrong of Benjamin’s Visual Thought), Xueshujie (Academics) 2 (2013): 60-69.]那样不停切换异域景观图画,正如本雅明回忆童年时观看西洋景的经验而感悟到的:“旅行让人觉得非同寻常的地方在于,旅行时邂遇的遥远世界并不一定是陌生的,并且它在我身上引发的渴望并不一定是诱人的要进入陌生之地的欲望,有时更是那种默默地要回家的愿望。”38(德)本雅明:《柏林童年》,王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Walter Benjamin, Bolin Tongnian(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 trans.WANG Yo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2008, 12.]在此,本雅明敏锐地发现,观众在欣赏西洋景当中的视觉经验所唤起的并非他乡愁(Fernweh)而是乡愁(Heimweh),这也正是凯泽林在异域旅行时的乡愁经验。正是因为无乡(heimatlos),所以思乡(Heimweh)、寻乡。出走,是为了回家,正是为了寻找自我的国族身份认同。由此看来,凯泽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特性的介绍,问题意识还是自我与民族国家以及与欧洲文化共同体的关系。他在此书最后一章作出对自我身份的陈述:
是的,当我分析我自己的自我意识——我怎么看自己呢?首先,作为我自己;第二,作为贵族;第三,作为凯泽林;第四,作为西方人;第五,作为欧洲人;第六,作为波罗的海人;第七,作为德国人;第八,作为俄国人;第九,作为法国人——是的,作为法国人,因为我在法国的学徒经历给我带来深远的影响。39Hermann Keyserling, Das Spektrum Europas (The Spectrum of Europe) (Stuttgart/Berlin: Deutsche Verlag-Anstalt,1931), 377.
有当代研究者留意到,凯泽林在游记中显示出一种“世界公民-自由主义的(cosmopolititan-liberal)”态度,而《欧洲光谱》却显示出“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就具体的政治认同而言,凯泽林还是倾向使主体的个性“屈伸融入意识形态的构建”。40参看(美)贝尔托诺:《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大陆快照——凯泽林的〈欧洲〉与斯宾格勒的〈决定时刻〉》,张培均译,见娄林主编:《斯宾格勒与西方的没落——纪念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年,第2-20页,此处第4~5页。[Thomas F.Bertonneau, “Snapshots Of The Continent Entre Deux Guerres: Keyserling’s Europe(1928) And Spengler’s Hour Of Decision (1934),” trans.ZHANG Peijun, in Sibingele yu xifang de moluo: jinian sibingele Xifang de Moluo chuban yibai zhounian (Spengl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Memorials to the 100 Years Celebration of Spengler’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18, 2-20, here 4-5.]凯泽林出身波罗的海的俄国贵族,后来又经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帝国的崛起,各种身份认同危机和张力在他面对异域文化时凸显。这一旅行书写文本中中国形象的构建在其对国族身份认同的追寻以及对现代国家的文化共同体想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口号把中国民族和国家分裂的问题尖锐化。但在凯泽林笔下,中国仿佛有史以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统一体,“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41(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50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105.]。在凯泽林对中国民族构成的叙述中,满汉民族矛盾被遮蔽,阶级共同体构成了国民主体。“只要中国不存在阶级差别,只要农民依然还是中国人,并且不会改变他们的性格特征,儒家思想的独特性便不会消亡”。42同上,第151页。他担心革命之后农民会被改变,美好的儒家传统及其道德基础将会受到冲击,对此感到“深深的悲伤”:“当我有足够多的理由开始担心中国的旧秩序将要打破时,对革命的反感之情尤甚。”43同上,第50页。凯泽林害怕旧中国的更新变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家园,这种怀旧心理实则也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德国旧市民阶层的普遍心理,反映了此时因工业化而兴起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市民阶层” (Wirtschaftsbürgertum)和“占有财产的市民阶层” (Besitzbürgertum)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固守古典教育价值的旧富阶层担忧社会地位和价值准则受新富阶层动摇,鄙视为他们带来财富的新技术和工业文明,于是以精英主义姿态维护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呼吁重建(旧)精神价值。44参看曹卫东等:《德意志的乡愁: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57页。[See CAO Weidong &co, Deyizhi de xiangchou: ershi shiji deguo baoshou zhuyi sixiangshi (German Nostalgia: History of Thoughts about German Conservati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2015, 56-57.]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与20世纪初德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共享着深层的文化无意识。此时英法已经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德意志民族还没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只作为“文化民族”而存在,“文化”(Kultur)这个词是唯一强大的认同机制。45同上,第53页。而代表艺术和科学等精神方面高级成就的“文化”(Kultur)与外在的、表面的、物质性的“文明”(Zivilisation)二元对立的思维,导致了德国知识分子倾向以文化宗教(Kulturreligion)作为民主政治替代品的治国方案。46同上,第566~568页。凯泽林与当时的保守主义革命者都怀有复兴文化传统的理想,两者思想也分享着深层的哲学连续性和意识型态相似性:在哲学基础上,反对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主义,认为认识的基础不是理智或意识,而是感性和直觉;在国家学说上,认为解决德国现代化出路的有效途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包括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组织上的精英原则以及领导上的领袖思想;在现代性话语谱系上,从文化路径寻求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体现了一种“激进的审美主义式精神冲动和乌托邦设计”。47关于保守主义革命的思想机制参看曹卫东等:《德意志的乡愁: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2~375页。[See CAO Weidong &co, Deyizhi de xiangchou: ershi shiji deguo baoshou zhuyi sixiangshi(German Nostalgia: History of Thoughts about German Conservatis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2015, 332-57.]但是此著作中并没有提到凯泽林,而在曹卫东《同异之辨》关于凯泽林日记的研究中也没有提到凯泽林与保守主义的关系。迄今为止的国内外研究中对凯泽林政治思想的关注甚少,但笔者认为若将其放在时代精神谱系内看待其思想史位置,将更能体现中国文化在西方现代性话语形成中扮演的角色。
而关于理想的国家政治统治形式和作为精英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中国文化风景为他提供了一个想象空间。在北京最后的日子,凯泽林到郊区旅行,再次用俯视的眼光观看中国的土地,开始假想自己是中国天子,不仅统治全中国,而且统治全世界。他想象在“我”这位神圣的伟人面前整个世界呈现出一派和谐的景象,如同浮士德站在自己所创造的伟业面前自我陶醉,这位“天子”也眺望着宽广的大自然而情不自禁地赞叹“我真伟大!”48(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36~138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136-38.]他把舜帝看作贤君榜样,而三代贤君的统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推崇的理想政治秩序。舜的贤君形象其实是儒家传统构建出来的,凯泽林所说的这位舜帝,也正好符合了德国帝制时期对理想皇帝的想象。而“天下”在多数古代典籍中指的只是中国,但凯泽林显然把中国的“天下”概念理解为全世界(Welt)、全球(Erdball),那么他自我想象的这位“天子”的统治范围就比中国皇帝要大得多。后来他亲自成立的智慧学院就提供了一个展现“贤君”、“智者”自我形象的平台,让他作为精神领袖为学徒设计“玻璃球游戏”而尝试实践“哲人王”治理天下的理想。凯泽林接下来说到在自感伟大的同时,也感到个体的渺小而谦卑。这种复杂的情感其实是一种追求崇高景观的浪漫主义情怀,高山之上乃是神灵居所,攀山登顶乃是一场朝圣之旅,也体现了渺小的个人对崇高伟大的审美追求。49参看(美)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求崇高景观》,陆小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年,第41~44页。[See DUAN Yifu, Romantic Geography: In Search of the Sublime Landscape, trans.LU Xiaoxu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21, 41-44.]对高山的征服彰显了登山者的超人素质,从侧面暗示了知识精英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统治力,这种精英治国的理念也呼应着当时保守主义思潮的政治诉求。他认为,构成中国国民主体的是农民阶层,但是创造中国文化的主体始终都是士大夫阶层。凯泽林后来在《政治、经济、智慧》提出一个理想化的国家政治形式应该是教养程度和道德水平较高的精英阶层创造民族文化,作为国家的引领者主导国家建设的未来方向。50See Hermann Keyserling, Politik, Wirtschaft, Weisheit (Politics, Economics, Wisdom) (Darmstadt: Otto Reichl Verlag,1922), 103-4.他在文中还探讨一战后的德国如何进行精神重建,好让德国重新回到世界列当中,认为精神重建首先从个人的自我实现开始,个体的自我完善关系到整个德国的未来,但德国并不愿意也不想推行靠政治强权推行帝国扩张,在这一点上德国人跟中国人很相似:“他们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文化爱国主义和家乡感,他们内心并不关心政治领土大小。”51See Hermann Keyserling, Deutschlands wahre politische Mission (The Real Political Mission for Germany) (Darmstadt:Otto Reichl Verlag, 1921), 12.经历了殖民侵略和辛亥革命的中国人逐渐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这当中实际上不只是“文化爱国主义”了,中国人也当然关心国家政治领土的大小。凯泽林的这种误读缘于他欲为一战后的德国重新辩护的爱国心,也缘于作为俾斯麦孙女婿对威廉皇帝帝国扩张政策的不满,同时也跟他追求的德国精神引领欧洲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密切相关。他在文中声称,德国的使命在于“从瓦解一切历史遗留的灵魂形式的混乱中塑造一个新的灵魂宇宙”,由此产生一个“新的欧洲灵魂”。52Hermann Keyserling, Politik, Wirtschaft, Weisheit (Politics, Economics, Wisdom) (Darmstadt: Otto Reichl Verlag,1922), 104.
三、欧洲作为起点与终点
那么,凯泽林在日记中表达的对东方文化的认同和推崇,能不能也算作“中华文明救西论”?
和地理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类似,凯泽林在游记中也采取了景观(Landschaft)地理学对区域性分析的修辞策略,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聚落的特征上,探讨聚落的历史和功能,绘制出一幅全球文化地图。这种强调景观和区域理念的德国地理学派的兴起其实正呼应着一战后的保守主义革命,既然保守主义者需要了解现代世界权力的基础与领土问题,那么景域主题的地理学研究就尤显重要。53参看(法)克拉瓦尔:《地理学思想史》,郑胜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1~116页。[See Paul Claval,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s, trans.ZHENG Shenghua, Beijing: Peking Universtity Press, 2015, 111-16.]特洛尔奇批评凯泽林日记中对非欧洲思想的一些哲学表述跟他自己关于“绝对”(das Absolute)的阐释相差无几,只不过凯泽林用到了“印度的”形而上学作为佐证而已。54See Ernst Troeltsch, “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2 Bände by Graf Hermann Keyserling (Review)” (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2 Bands by Graf Hermann Keyserling),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Historical Jounal) 123, no.1(1921): 90-96, here 92.这一批评确实留意到凯泽林异域文化书写的欧洲底色,而从凯泽林的环球之旅路线来看,这一路线是一个封闭圆环,何谓西方何谓东方,其实取决于地理分界线。而何谓东方文明何谓西方文明,与其根据两种文化的本质内涵来作界定,还不如明晰外延、划分两者的界线来得容易。当作者到达印度德里,站在远东立场再看伊斯兰文化、犹太文化,这两种文化就与希腊文化一起归到西方文化大类,成为以印度、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远东文化的对立面,而包含着原著民神秘的精神性和宗教性的美洲又成了东西文明的过渡区域。由此,东西文明的地理分界线得以明晰,全球文明秩序得以确立。那么可以说,凯泽林对异域文化的书写虽不乏对非欧洲文化的溢美之词,但这些话语背后仍可窥见欧洲中心的世界文明秩序框架。他这一趟文化旅程最后还是返回家乡,其实还是回到“欧洲命运”。
欧洲未来命运如何是一战后整个欧洲思想界在世纪末的精神危机下热切关注的问题,“欧洲”观念是当时一股有着相当社会舆论基础的政治思潮。齐美尔(Georg Simmel)对欧洲未来命运十分悲观:“那个精神统一实体,那个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已经被摧毁了,我们也不可能再期望它的重建。”55Georg Simmel, Der Krieg und die geistigen Entscheidungen.Reden und Aufsätze (The War and the Spiritual Choices.Speeches and Essays) (München/Leipzig: 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 1917), 68.卡勒季(Richard von Coudenhove-Kalergi,1894-1972)则力推欧洲统一运动,后来自己亲自建立泛欧联盟(Paneuropean Union),他借鉴德意志帝国统一为联邦国家的历史,从中概括出欧洲联盟的发展理论。56参看李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泛欧”联合思想的产生》,见《北大德国研究》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4~132页。[See LI wei, “Diyici shijie dazhan yu ‘fanou’ lianhe sixiang de chansheng”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Emerge of “Pan Europe”), Beida deguo yanjiu (Germany Studies in Peking University), vol.5,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4-32.]他在《欧洲合众国》(Pan-Europa)中提出,欧洲必须建立一个政治的、经济的国家联合体进行自助,以维持欧洲在世界中心的秩序。57See Richard Nikolaus vo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Pan-Europe) (Wien: Pan-Europa-Verlag, 1923).中文译本参看(奥地利)卡勒季:《欧洲合众国》,夏奇峰、李实译,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他把欧洲文化定义为一种“以古代经典和基督教为根基的白种人的文化”,其对立面则为亚洲的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文化和儒家文化。58Ibid., 34.另外,德国语文学家库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法国作家杜哈默尔(Georges Duhamel,1884-1966)和罗米尔(Lucien Romier,1885-1944)都倡导构建一体化的欧洲精神以挽救欧洲文明衰落的危机。59See Jan Ifversen, “The Crisi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fter 1918,” ed.Menno Spiering, Michael Wintle, Ideas of Europe since 1914.The Legac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4-31.凯泽林也认为欧洲是一个由一些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元素组合而成的整一的共同体(Einheit)60See Hermann Keyserling, Das Spektrum Europas (The Spectrum of Europe) (Stuttgart/Berlin: Deutsche Verlag-Anstalt,1931), 16.,而他本人也在其他场合阐述过他对欧洲文化一体化的“捍卫”。1933年10月,瓦雷里(Paul Valery)在法国主持组织了一场讨论“欧洲精神之未来”的会议,托马斯·曼寄去一封短信作为发言稿但并没有出席,受邀的斯宾格勒、茨威格、威尔佛(Franz Werfel)也没有出席,凯泽林作为唯一的德国代表奔赴巴黎参会作了两场演讲。他在会上对基本的欧洲精神作了他的阐释,认为欧洲的心理—精神根基受到来自非欧洲地区的多重影响动摇和破坏,已经无法恢复旧日的精神活力;这些非欧洲地区的精神包括美国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独裁、东方宗教和哲学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黑暗的地下精神,会从底部掀翻欧洲精神的根基。61See Sławomir Leśniak, “Graf Hermann Keyserling und Europa”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and Europe), German Life and Letters 58, no.3 (2005): 293-94.凯泽林的欧洲精神共同体构想实则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其中一面,就如同时代的作家兼外交官凯斯勒(Harry Graf Kessler,1868-1937)所言,凯泽林的内在精神立人计划只有在一个推行普世主义的世界中才可行,而这种普世主义的政治形式在当时的欧洲就只能是一种多个国家的联合组织。如果沿着凯泽林的思路去构想德国的对外政策,那么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追求尽可能正义的、推行社会福利的、持久的国家联合体。62See Harry Graf Kessler, Aufsätze und Reden 1899-1933: Künstler und Nationen (Essays and Speeches 1899-1933:Artists and Nations) (Hamburg: Tredition GmbH, 2012), 182.
由此看来,凯泽林热衷探索和书写非欧洲文化的潜在动机还是重建欧洲精神的抱负,这种对欧洲文化的自豪感甚至也体现在他中国之行的公开演讲中。1912年5月2日凯泽林在上海尚贤堂举行了英语演讲,演讲辞于次年被孔教会创办人陈焕章用文言文节译,分两篇发表于机关刊物《孔教会杂志》和《宗圣汇志》创刊号,题名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该文也可视为陈焕章作为袁世凯总统顾问与严复、梁启超等向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的理论准备。凯泽林演讲中的保守复古倾向以及文化救国的情怀显然正对陈焕章胃口,他因此也只选择了凯泽林的这方面言论而进行创造性意译。例如,陈焕章把凯泽林的“Ideal”译作“道”,掩盖了凯泽林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内对绝对真理(柏拉图的理式“ideas”)、内在真实(innere Wirklichkeit)的一贯追求,而添加了儒家的道统意味,而凯泽林的“Konfuzianismus”就被译为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孔教”。从摘选的译文看,凯泽林把“孔教”视为“各种文明之模范”、“中国之中心”、“国家新命之所托”63参看盖沙令:《孔教乃中国之基础》以及《中国之新命必系于孔教》,陈焕章译,见《孔教会杂志》1913年第1卷第1期,第7~13页。[See Keyserling, “Kongjiao nai zhongguo zhi jichu” (Confucianism is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 “Zhongguo zhi xinming bi ji yu kongjiao” (The new destiny of China muss be determined by Confucianism), trans.CHEN Huanzhang,Kongjiaohui Zazhi (Journal of Confucianism Society) 1 (1913): 7-13.],读者会很容易因此认为这位“西儒”把“孔教”推崇备至64也正是这篇译文,加上凯泽林与辜鸿铭、沈曾植、卫礼贤的交往,凯泽林被当时知识界乃至后来研究者认为是孔教运动的推动者。参看邱巍:《民初的西儒与孔教会》,见《安徽史学》2002年第2期,第54~55页。[See QIU Wei,“Minchu de xiru yu kongjiaohui” (Western Confucianists and Confucianism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ation of Republic China), Anhui Shixue (Anhui Historical Science) 2 (2002): 54-55.] 又见张艳国:《五四时期西方“中国通”的尊孔观述评》,见《江汉论坛》2003年第6期,第72~77页。[See also ZHANG Yanguo, “Wusi shiqi xifang ‘zhongguotong’ de zunkong guan shuping” (A Commentary on the Idolization of Confucius of Western China Experts during the May Forth),Jianghan Luntan (Jianghan Forum) 6 (2003): 72-77.]。然而,在凯泽林旅行结束次年出版的德语版讲稿《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问题的内在关系:致东方民族的一则消息》中,在这段文字之前,凯泽林明确否认西方人将会全盘接受东方文明然后与东方走向同一个方向,因为两者目标本不相同。65See Hermann Keyserling, Schöpferische Erkenntnis (Creative Knowledge) (Darmstadt: Otto Reichl Verlag, 1922), 238-239.而在《创造性认知》中,尽管凯泽林援引孔子和老子,高举深入意义内在的中国思想进路,但也直言路径虽是东方的,而最终指向“自由人格”这一目标还是西方的,在个体这一层次东方思想还是不如西方智慧。66See Hermann Keyserling, Über die innere Beziehung zwischen den Kulturproblemen des Orients und des Okzidents.Eine Botschaft an die Völker des Ostens (On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Problems of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A Message to the Peoples in the East)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13), 21.凯泽林看到儒道两家都已经失去了原初的本真意义:“在中国,道家思想沦为法术迷信,儒家思想沦为僵死的礼仪习俗”67Ibid., 23.。而西方人天生就不盲目崇拜权威:“我们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自由活跃。”68Ibid., 23.他认为,西方很快就会赶上东方,而且一旦找到启蒙之光就不会再失去。
东方过去曾经活在太阳底下,只要它还留在那儿,它必定还是在亮光当中的[……]它一旦朝某个方向动了一下,它就离开了光,太阳照在它背后,到最后就再也照不到它了。——我们西方人过去从来没有活在太阳底下这样的幸福,但我们小心地慢慢接近太阳。[……] 但我们也避免了东方遭遇的灾难:我们一旦认识到这种状况,也会去掌控它;一度赢得的光明,我们再也不会失去。69Ibid., 24.
另外,在《大陆报》刊出的英语演讲词中,也可看出凯泽林虽然首先批评了西方文明发展到今天太物质化,但他又相信西方文明很快又会回到正轨。
在进化的现今阶段,我们在科学、技术、机械等方面的成功都把我们的注意力朝向外在,以至于在各种仪器设备的复杂性中丢失了真正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很多人完全意识到这种危险,正在尽全力排查,而那些一直都在各自为政的机构早晚会重新恢复生命力。70Hermann Keyserling, “East and West Are Compared in Lecture.Count Keyserling on Their Search for Common Truth”,见:《大陆报》,上海,1912年5月3日,第3页。结束环球旅行的第二年,凯泽林补充深化了内容在德国出版了德语版单行本的讲稿Über die innere Beziehung zwischen den Kulturproblemen des Orients und des Okzidents.Eine Botschaft an die Völker des Ostens (On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Problems of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A Message to the Peoples in the East)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13).
虽然凯泽林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性深表认同,但他在演讲中又大谈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对内在灵魂的强调,依然呈现出欧洲文化精英的优越姿态。通过“我们西方人/你们中国人”的他者化话语策略,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在进化论话语中被置于先进/落后的时间等级秩序中,这样的时间修辞不仅挖出一道隔开欧洲与非欧洲地区的鸿沟,并且把过去与现在的划分转变为东方与西方的空间区隔。凯泽林认为,西方有古希腊和基督教追求内心真实的优良传统,本来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然而当下物质发展超过精神发展而失落了这样的西方文明精神遗产。71See Hermann Keyserling, Über die innere Beziehung zwischen den Kulturproblemen des Orients und des Okzidents.Eine Botschaft an die Völker des Ostens (On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al Problems of the Orient and the Occident.A Message to the Peoples in the East)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13), 11.然而看到中国正在走着西方的老路子,也面临着跟西方一样的问题,凯泽林追溯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以“过来人”的姿态倡导追求内在真实才是解决物质文明弊端的出路,并且呼吁中国人保持其传统文化根基,正好呼应报刊大标题下的副标题“中国人应坚持的和放弃的”(what Chinese should hold and give up)。凯泽林对内在真实的理解具有先验论的倾向,并肯定道德和宗教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这两方面都印证了其思想受新康德主义影响。那么,当凯泽林高度赞扬“中国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儒家思想在精神教育上的胜利”时72(德)凯泽林:《另眼看共和:一个德国哲学家的中国日志》,刘姝、秦俊峰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6~48页。[Hermann Keyserling, Lingyan kan gonghe: yige deguo zhexuejia de zhongguo rizhi (My Observation on China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Dairy about China of a German Philosopher), trans.LIU Shu, QIN Junfeng,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5, 46-48.],其实不过是戴着新康德主义的眼镜看到异域文化之镜中的理想化自我。虽然凯泽林强调中国的改革需要从自身文化根基出发,然而,从凯泽林的保守主义倾向和全文的论证逻辑来看,这样的观点本身仍属于西方思想的理论进路。73保守主义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坚持传统、捍卫现状而反对现代化变革,保守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参看曹卫东:《保守主义:一种现代性话语》,见《学海》2006年第4期,第84~96页。[See CAO Weidong,“ Baoshouzhuyi: yizhong xiandaixing huayu” (Conservatism: a Modernity Discourse),Xuehai(Xuehai) 4 (2006): 84-96.]另外,从演讲者的启蒙立场可见,医治西方文明病根的良方依然源于西方,中国文明的未来也依然需要西方启蒙者的明灯点亮。
凯泽林抓住1919年日记畅销的契机,于次年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创办了一个“智慧学院”(Schule der Weisheit),尝试在继承欧洲东方学的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柏拉图和佛教思想、日耳曼精神与东方思想,以思想革命的形式重塑西方文化。74See Suzanne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45, no.4 (2001): 471.智慧学院每年出版学术集刊《烛台》(Der Leuchter),开设一些冥想和瑜伽课程,邀请东方学学者作演讲(如卫礼贤为学院常客),还盛情邀请泰戈尔来访德国并为他安排了满满一周的行程。同时,凯泽林也欢迎语文学者、弗洛伊德的圈子、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家等通晓西方文化的各色知识精英。75但因凯泽林常有专横傲慢的态度,与各人的友谊大多不能持久,年刊印刷量只有不到三千册,学院只维持了十年。See Suzanne Marchand, “Eastern Wisdom in an Era of Western Despair: Orientalism in 1920s Central Europe,” ed.Peter E.Gordon, John P.McCormick, Weimar Thought.A Contested Leg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350-53.有学者认为,凯泽林的智慧学院其实也并非东方智慧的传播热点,并没有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哲学,相反,学院的设立是为西方人激活西方哲学的智慧而深化对西方哲学的认识,从而达到自我完善。76See Ute Gahlings, “Die Kulturphilosophie von Hermann Keyserling” (The Cultural Philosophy of Hermann Keyserling),eds.Ute Gahlings, Klaus Jork, Hermann Graf Keyserling und Asien.Beiträge zur Bedeutung Asiens für Keyserling und seine Zeit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and Asia.Contributions to the Importance of Asia for Keyserling and His Time) (Biebelsheim:Edition Vidya, 2000), 46-68, here 58.智慧学院其实没有任何理论性纲领,也没有实质性的教授内容,教学目的声称是让每个人自我追寻一条通往整全人的道路,追求“精神化的灵魂”。但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因意义一直在动态变化而失去稳固的哲学根基,而且这种贵族式的精神追求也不是一般普通大众能达到的(会员年费高达一百多马克、年刊精致但昂贵),其实很难衡量这种理想主义式的精神运动对整个欧洲思想界的影响力。77See Gunther Stephenson,“Das Lebenswerk Graf Keyserlings aus heutiger Sicht” (Count Keyserling's Works from Today's Perspective),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Journal for Religions and History of Thoughts) 33, no.1(1981): 32-41, here 39.See also Walter Struve, Elites Against Democracy.Leadership Ideals in Bourgeois Political Thought in Germany, 1890—193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02-3.有学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智慧学校只不过提供一些逃避现实困境的方法,在政治稍微稳定的二三十年代,只被看作“无害的安慰补养调制品”78See Walter Struve, Elites Against Democracy.Leadership Ideals in Bourgeois Political Thought in Germany, 1890—1933(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310.。凯泽林沉浸在“自我中心、自给自足的幻想”中构筑保守的精英主义政治理念,但其思想因远离当下社会政治形势而最终无法真正改变德国政治现实。79Ibid., 315-16.
四、结 语
凯泽林的旅行书写文本暗含的成长小说叙事模式,即出走他乡为了返回自身完成主体性建构的路线,反映了德国人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国族身份认同追寻和重建欧洲精神的抱负。该文本再现的中国文化既陌生又充满异国情调,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必须保留其“中国性”,才能让西方文化在他者镜像中得以自我确认。吊诡的是,文本构建出一个静态的、失去历史纵深感的、本质主义化、去政治化的中国文化空间,这种他者化话语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放置在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框架之内,一方面致使西方对阐释现代性的话语权在世界文化版图的新秩序上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前景也因此得以自我确认。表面上看来,凯泽林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推崇是藉此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以寻找西方文明的出路,实际上通过这样的自我追寻,让西方文明一体化想象得到自我确认,现代化工程规划愿景通过否定之否定又返回自身。由此看来,凯泽林本来在世纪之交的欧洲精神文化危机中远走他乡,带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寻找欧洲出路,此时环绕地球一周又回到原点,欧洲的出路还是在现代化进程,而且中国的出路也是。其对中国文化介绍背后的精英主义立场和欧洲立场,恐怕也是智慧学院影响广度、深度和时间受限的重要原因。
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汉学家在介绍中国文化时,也与凯泽林分享着相似的思维框架和叙事模式。例如有研究者批评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国社会制度有普遍化倾向,他构建的理念型(ideal type)只是一种研究假设,他选取的历史材料来自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段,忽略事件的时间顺序,固化了“不变的中国”的古老神话,这样一来,历史的动态性就专属西方。80See Otto B.Van Der Sprenkel, “Max Weber on China,” History and Theory 3, no.3 (1964): 348-70.斯宾格勒虽然重视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世界文明的多元化,但是他的“文化周期论”同样也有把中国看作停滞不动的文明的倾向。相比之下,他认为以浮士德精神为内核的欧洲文化有着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81参看詹向红、张成权:《中国文化在德国:从莱布尼茨时代到布莱希特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91页。[See ZHAN Xianghong, ZHANG Chengquan, Zhongguo wenhua zai deguo: cong laibunici shidai dao bulaixite shidai (Chinese Culture in Germany: from the Time of Leibniz to the Time of Brech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6: 291.]也有学者批评斯宾格勒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压缩到一个决定论的系统里面,否定了人类未来的开放性,而不同文化各自独立发展的理念也夸大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82See John Farrenkopf, “Spengler’s historical pessimism and the tragedy of our age,” Theory and Society 22, 1993: 391-412.由此看来,从欧洲思想史背景看,二十世纪初以凯泽林、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出发点依然是德国国族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德国精神在欧洲精神重建中扮演的角色,最终落脚点依然是德国及至欧洲的现代化。正如刘东在《我们共通的理性》所言:
无论出现了“中国热”还是“中国冷”,都主要出自这个“阐释主体”的自身需求,从而也都必须面对那个“阐释还是过度阐释”的质疑。换言之,那个遥远的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其本身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堕落”至此的。由此说穿了,无论它是被投以了“热”还是“冷”,那温度都很难说是来自雾里看花的“远东”,而只是缘自西方当时的自身发展需要,取决于它在建构“民族国家”的那个节骨眼上,更愿意去强调中国多棱体的哪一个侧面。83刘东:《我们共通的理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页。[LIU Dong, Women gongtong de lixing (Our Common Reas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2021, 23.]
那么,若要把20世纪初少数几个精英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看作整个欧洲知识界一致认为中国文化就是欧洲现代文明的救赎之路,那显然也是缺乏充分的理据。而且“中华文明救西论”的逻辑起点依然是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依然是站在西方立场远观中国这个“异”,从这种自我-他者关系出发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实际上也不自觉陷入西方中心的理解框架中。不过西方知识分子在构建中国文化时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自始至终处于落后、从属的、被动的位置,恰恰相反,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正好说明中国文化在参与欧洲现代性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而关键的角色,现代性的生成并非先进的欧洲再带动全球“落后文明”,而是一个中西文化同步互动共同参与的动态过程。也正如哈若图宁所言,地理大发现以及其后殖民主义的兴起让人们认识了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存,而殖民话语把欧洲文化与非欧洲文化置于历时性秩序中划分等级,“文明的”(civilized)欧洲就显得走在“未开化”(uncivilized)的亚洲和非洲之前,这样的“进步”“发展”话语生产了文化差异性,但同时也唤醒我们重新思考全球文化的共时性和非共时性,因为这种差异性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尝试修复过去遗产以弥补当下文化缺失时会遇到的问题。84See Harry Harootunian, “Some Thoughts on Comparability and the Space-Time Problem,” Boundary 32 (2005):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