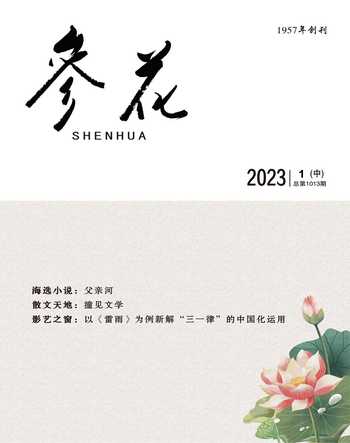解析《嘉莉妹妹》中的艺术手法
一、引言
德莱塞创作《嘉莉妹妹》时,美国正处于社会高速发展、工业文明不断占据人们日常生活的时代。小说通过描写女主人公的个人发展和对社会地位的不断追求,揭露出当时的整体现状。除了巧妙独到的情节构思,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德莱塞对各种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也极具特色。不论是摇椅这一贯穿始终的意象,又或者是小说前后辛辣的对比和反讽,都值得人们深入探讨和品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中的艺术手法,考察它在刻画人物性格特征、成长经历,以及主角之间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从而加强对小说主题的理解。
二、象征手法
纵观全文,德莱塞描写摇椅的频率非常高。摇椅不只是环境描写的一部分,它也是一个意象,坐在上面的不同角色赋予了它不一样的意义,其中,德莱塞对嘉莉和赫斯渥坐在摇椅上的描述最为丰富。作为使用摇椅次数最多的人,嘉莉在屋子里的描写总是会伴随着摇椅的出现。小说最开始,坐在摇椅上的嘉莉是贫穷的,她要写信给杜洛埃,让他不要来找她,因为她的自尊心不容许让别人看见她住在这么寒酸的地方。这时,摇摇晃晃的摇椅正像嘉莉忐忑的心境一样,一方面,她对这个城市抱有极大的幻想,希冀着过上富太太们珠光宝气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为贫寒的现实生活而沮丧。很长一段时间,摇摆的摇椅象征着嘉莉时而充满美好期望,时而又苦恼沮丧的纠结状态。
而当嘉莉投靠杜洛埃后,嘉莉时常坐在摇椅上思考她的情感需求以及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比之前富裕的生活并没有换来她的满足,相反,她感觉到失落空虚,因而当比杜洛埃更显体贴富有的赫斯渥出现时,嘉莉情感的天平逐渐偏向了赫斯渥。这时,不断摇晃的摇椅象征着她和杜洛埃之间岌岌可危的关系,嘉莉即将抛下这些旧的生活与人物,转而迎接生命中新的转折。
在跟随赫斯渥到纽约做家庭主妇的日子里,摇椅是嘉莉唯一的情感寄托,无人诉说时,她坐在上面回忆艾弗里会堂成功的表演,借此安慰自己不甘的心。同時,她又在摇椅上不断构想着如何实现自己挤进上流社会的美梦,摇椅为她提供无尽的力量,供她一次次在残酷的现实里顽强地生存下来,让她一直保持着向上奋斗的野心与欲望。故事最后,看似已经实现所有美好梦想的嘉莉,依旧坐回了她的摇椅,这一次,她脑海里出现的不再是由各种奢侈品组成的美好生活,她开始幻想一种好像永远都得不到的幸福。摇摇晃晃的摇椅意味着她的梦想永远没有尽头,她终将不能实现梦中的幸福。
随着故事展开,坐在摇椅上的常客又多了一个赫斯渥。与嘉莉逐渐向上的命运相反,赫斯渥的命运在纽约急转直下,摇椅一直伴随着他从上流社会沦落到中产阶层,进而破产,走向自我堕落的道路。不同于嘉莉日渐丰富忙碌的工作生活,赫斯渥的生活轨迹越发狭窄,最后停留在了小小的摇椅上,他的心理活动全都表现在摇椅晃荡的弧度里。德莱塞对赫斯渥破产后的描写,常集中于他坐在摇椅上的时候,他喜欢坐在摇晃的摇椅上,摊开一张报纸,能从早看到晚。这样无聊的日子,他却觉得满意舒适,究其缘由,是因为这时的摇椅不再只是一件家具,它成为赫斯渥用来缅怀美好过去、甩开残酷现实的工具。起初,赫斯渥坐在摇椅上,只是为了短暂地逃避现实生活中的失败,可就像没有坚实底盘的摇椅一样,赫斯渥的精神也不坚定,最后,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摇晃中消失殆尽。之后他放任自己,渐渐沉迷于坐在摇椅中回忆在芝加哥的那种生活。这时的摇椅象征着他所追求的一切——体面的工作、优渥的生活、和睦的家庭,以及奋斗的欲望和野心都在摇晃中一点点消失,每当他认为可以追求到什么的时候,这一切就像摇椅摇晃一样,又被晃走了。
从体面的经理到终日沉溺于躺在摇椅上看报纸的失败者,赫斯渥可以说是那时人们的代表,他们习惯于由各种奢侈品、名誉、地位堆砌成的空虚生活,乐于在尔虞我诈、推杯换盏中寻找虚荣感,对自己的家庭却缺少责任感,甚至为了一时的激情与欲望背叛家庭。摇椅的出现象征着嘉莉与赫斯渥“对于过好一点的日子的欲望毫不隐瞒——漂亮衣服、财富和社会地位”。[1]无论是贯穿始终的摇椅,又或者是诸如报纸、窗户和镜子等其他意象,都帮助德莱塞丰满了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出两个被欲望推着走的可怜人。
三、对比手法
作为艺术创作中常见的艺术手法,对比无声无息地吸引着读者的注意,让事物在两相对比中显得更加鲜明起来。运用这种手法,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染力。[2]文章的情节发展和嘉莉的成长随着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对比展开。作者正是通过嘉莉和赫斯渥完全颠倒的命运和地位,表现出命运无常的戏剧性。小说主要讲述了嘉莉和赫斯渥的成长变化,同时,又不局限于这两个人的对比中,嘉莉在遇见杜洛埃后的两次交谈,也是相当具有讽刺性的对比。
嘉莉和杜洛埃的第一次交谈是在开向芝加哥的火车上。彼时,18岁的嘉莉还只是一个除了幻想,什么都不懂的乡村姑娘,她只携带了一点行李,乘坐火车去投奔姐姐,前途未知。而与之相对的,无论是从搭话的技巧、体面的穿着,又或是绅士的举止,都可以看出推销员杜洛埃是一个有着一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热情浪漫的中产阶层男人。很快,嘉莉便被这个和家乡男性完全不一样的人深深吸引。这是两个背景相当悬殊的人物,可以对比两人对话时的语言选择,据此分析两人此时的性格和所处的地位。在两人的对话中,善于交际的杜洛埃一直把握着对话的节奏,他说话的次数远高于嘉莉,并且不断抛出话题。腼腆害羞的嘉莉则处于守势,言谈举止都极为局促,在杜洛埃热情而积极的攻势中,才渐渐放下了防御和克制,开始和他交谈并约定下次见面。如此可见,杜洛埃在两人的谈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除了语句数量的对比,还可以对比两人使用的句子种类。杜洛埃在对话中多采用问句,例如“你对这一带地方不熟悉吧?”[3]这一问题可以很好地帮助一个人获取对方的信息,提问的人通常在对话关系中扮演着更主动、更强势的一方。相比之下,用简短的陈述句回答问题的嘉莉,便一直处于被动的位置。在一问一答的情况下,意味着回答者嘉莉一直跟随着杜洛埃的思路,处于被他牵制的状态。当然,嘉莉在对话中也抛出了几个诸如“啊,你真认识吗”[4]这样的疑问句,但这种疑问语气通常意味着把话语权又重新交还给了对方,让自己置于被动的聆听者的位置。另外,在这场对话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杜洛埃多次使用了祈使语气,“你一定要逛逛林肯公园”。[5]这是一种比较强势的语气,而嘉莉全程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语气。
告别杜洛埃的嘉莉,开始独自在芝加哥找工作,屡屡碰壁后,在残酷的现实和她日益膨胀的欲望中,她最终选择投入杜洛埃的怀抱。可当她遇见赫斯渥后,她的眼界随之开阔,心思也活络起来,不再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她把赫斯渥当作进入上流社会的橄榄枝,因此,当杜洛埃把赫斯渥有家庭的事告诉嘉莉后,嘉莉一时无法接受美梦落空,而与杜洛埃爆发了争吵。这时对比两人争吵中选择的语句,可以发现两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首先,嘉莉代替了杜洛埃,成为对话中一直掌控方向的那个人。她不断地质问杜洛埃,给他施加压力。从她密集的话语和咄咄逼人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嘉莉开始学会反抗。其次,与之前的对话相比,嘉莉两人都倾向于选择各种具有情感色彩的词语来表达自己,例如“现在,你却鬼鬼祟祟地回来”,[6]激烈的语气和强势的表现,都反映出两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而德莱塞描写嘉莉时也常使用“咬牙切齿,跺着脚,叫了起来”等非常具有情绪化的动作描写,这和之前腼腆害羞的乡村姑娘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时期的嘉莉的心理已经逐渐成熟,敢于为自己发声。可以看到,嘉莉的语言风格是符合她的成长变化的。同时,嘉莉常使用感叹句,或者“呵,唉”等词语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这也符合她作为女性角色的特点。最后,虽然杜洛埃也使用了一些问句和表示情感的词汇,但他并不专注于在谈话中压过对方,他只是企图保持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和地位,实际上并不想破坏两人的关系,这符合杜洛埃畏手畏脚的个性特征。
总体而言,这是嘉莉在文中第一次用严厉的语气来表达她的情绪并反抗加诸她身上的不公,相反,一直是花花公子形象的杜洛埃在对话中败下阵来,试图安抚嘉莉的情绪,稳固好两人的关系。对比前后两次交谈,双方语言选择的变化反映出两人身份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女主人公嘉莉的成长,在经受过经济威胁以及心灵自由上的胁迫后,她逐渐成长为一个思想进步的新女性。
四、反讽手法
H·R·耀斯曾指出,“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7]小说中反讽的运用不仅体现出嘉莉和赫斯渥命运变化的戏剧性,也明确地表达了德莱塞对物质、消费等的批判态度。该小说的反讽主要集中在情境反讽上。情景反讽一般用于表现小说人物的期望与实际情形的反差,作者用强大的命运操纵着角色离她的目标越来越远,以达到一种徒劳无功的滑稽感,实现对人物的嘲讽。当嘉莉来到芝加哥之前,作者描述她为,“她正十八岁,伶俐,腼腆,满怀着无知的年轻人的种种幻想”,[8]这时的嘉莉对大城市抱有许多期盼。在找工作之前,她以为这里遍地是机会。但当她真正去找工作时,才发现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早已把人划分,像她这种既没经验,又比较挑剔的乡村姑娘,最后的结果正如文中所写,“这么严重的失败,使她的精神颓丧不振”。[9]但即使嘉莉看清了这里虚伪的本质,她仍然没有放弃她想要变得富贵的愿望,这种在姐姐看来不切实际的想法,以及看戏等奢侈的做派,都和古板守旧、生活拮据的姐姐一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嘉莉对上流社会的积极追求和她的出身十分不符,她不具备任何吃苦耐劳的性格,却惯于模仿富家小姐的身姿做派。最后走投无路的嘉莉在杜洛埃那里找到了喘息的机会,她一度待在杜洛埃为她购置的套房里做他的金丝雀,甚至于当她结识到更加富有的赫斯渥以后,她又把她的心交給了体贴的赫斯渥,甚至和他相伴去了纽约生活,她就这么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富有。
而就当读者们以为这样爱慕虚名的嘉莉必然会落得一个不好的结果时,因为她所具有的特质与传统道德观念是如此相悖。德莱塞为情节的戏剧化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转折,嘉莉“既没有被饿死,也没有失去美丽的容颜或者怀孕,她不像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或克兰恩的《麦琪》中堕落的女主角那样不得不死去”。[10]相反,在纽约这个具有魔力的城市里,嘉莉和赫斯渥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实在让读者倍感意外。嘉莉从一个乡村姑娘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一员。而曾经上流社会的代表——赫斯渥却一跌再跌,直至落魄死去。曾经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竟没有一个还能想起他,都只专注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情节的发展俨然与读者的预期背道而驰。这样颠倒的命运完全出人意料,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赫斯渥畏手畏脚,和当时大胆追求享乐的潮流不一致,因此,他在这个充满野心的地方里无法向前,必然会被抛弃。而当极度渴望物质财富的嘉莉熟悉了这里的本质后,她的价值取向逐渐被它同化,因此,她的蜕变是自然的结果。作者在小说中运用反讽手法,刻画出两位立体的人物以及他们被这个欲望环境推动着随波逐流的命运。德莱塞正是借用对嘉莉和赫斯渥的对比与讽刺,将所有情节以及情感推至全文高潮,表现他对当时流行的消费风气的批判。这样辛辣又无处不在的讽刺,着实为主题的表达增色不少。
五、结语
《嘉莉妹妹》的成功,很大部分原因源于德莱塞运用了精湛的艺术手法,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现状。小说围绕嘉莉的成长展开,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嘉莉逐渐成熟的心态,都揭示出在繁华社会下纠结的人性,也展示出19世纪开始苏醒的女性心理变化。嘉莉也不再只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是广大普通群众的代表,她的变化映射出普通人在那时所受的影响。作者对芝加哥和纽约这些大城市的描述,不再局限于珠光宝气与生机勃勃的面貌,转而揭露了它的本质。在德莱塞的笔下,嘉莉的成名和赫斯渥的落魄,印证了重视物质的风气带来的种种危机。
参考文献:
[1]High,Peter B.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Longman Inc,1986:113.
[2]肖建云.麦克白悲剧之探究——浅析《麦克白》中对比手法的运用[J].语文建设,2014(32):55.
[3][4][5][6][8][9][美]德莱塞.嘉莉妹妹[M].裘柱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0;22;22;310;18;37.
[7][德]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82.
[10]Cunliffe,Marcus.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M].Virginia:R.R.Donnelley&Sons Company, Harrisonbury, 1986:244.
(作者简介:黄彬冰,女,硕士研究生在读,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