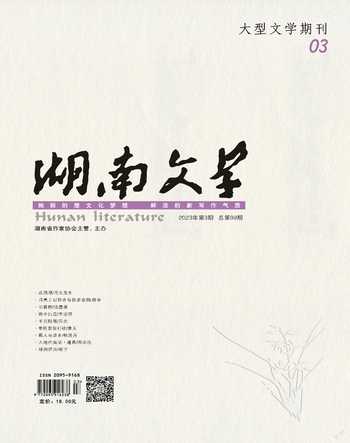大过山
黎粟
粤西山系连绵,常年染绿。俯瞰,像黄槲树大叶的经络,将连片的山岭笼罩其中。脉络间高低起伏,如瘫软一堆的云衫水袖,把地势挤出褶皱。逼仄处形成低谷,平宽处多是村圩。
冲龙塘就藏在高要林岭的山塅里。
沿塘下土坡爬过山腰,翻出围坪,有几条旧时栈道。泛着光的湿滑青石板边角,渗满藻色青苔。古路隐在郁林里,连通五岭八脉。往西,步行可到阳春;往南走,过了天露山就是开平;往北最远抵广宁返身。若向东,在高明被西江阻断,渡过江,能到番禺。
秋官常年跟大先生出门。每年,南、北、西各三次。东边路崎岖些,单程只走十天。临近春祈时起身,到高明掉转,只走一遭。
去高明路上,前两日不用放戏。跃过罗带岭、大蛇乸,才可喘息。后面八天,白昼赶山路,晚上在村圩扮大戏。
秋官和大先生不讲排场,放戏时只在小村圩停。想多揾戏银,也帮偶遇的氹仔班、八仙班、过山班打锣。
秋官跟大先生快五年,精攻武生,兼修花面,身段扎得标致。平日里大先生管教得严,探海、柴翻、三及第(三个长跟头翻种的合称)、风吹元宝的招式,他早已干净利落。兄弟班里客串五军虎或者拉扯(类似京剧中的龙套,扮书童、家人等角色),从不怯场。
秋官南功科威水,夹音也亮嗓。对山林低谷叫唱,能引得回声远荡,惊飞阵阵鹞雁。他还有单传绝活,那是别的班牌里见不到的。
秋官和大先生,班牌也没有,是这里最小的戏班了。熟悉的村圩只叫他们草鞋班或者响锣班。一面响锣,一口清唱,戏银自然不多。除了没班牌,盔头也是没有的——天官盔、白须、高靴,自不必说;帅盔、雉尾、箭靴也全无一件。大多时,就在村塘坪尾划地为台。
秋官唱戏常不开面。唱到首本折(拿手戏)时,他耐不住,央求半开。大先生才放下响锣,掏出巴掌大小的纳彩盒子,只把粉彩从秋官眉心向上一勾一抹。红的,是降龙罗汉面;白的,是蒋干面;黑的,是铁拐李和张飞面;绛紫色的,是雷公面;黄色的,就当作黄巢面。豆绿色的,印在拇指下面的厚肉上,往额头和太阳穴侧手一蹭,就当是杨志面了。
别说开面,他们戏服也没几件,无非就是一件绣了花的猎装,半套洗得发灰的武松装(灯笼裤也没有),拎起都是分不清年月地旧。
这所有家什,用一尊竹箩就能背起。跟大班名角的私伙衣箱比,不知隔了几层云天。
竹箩就是冲龙围自编的。饱肚,平底。戏服在最下,然后是杂衣,两三件常服叠好摞起,上面压八音锣——大先生的八音十番勾锣,是远近一绝。
竹箩盖子编成蛤蟆头,唇口吐出两条绑在一处的蓼蓝印染土布带,活结挂在箩沿下面的吊龙勾上,平日走村过寨由秋官背起。
往年向东,大先生要算日。想去年应承了哪村哪寨,要多放一晚。今年不知怎地,定要选顺日吉时,俩人晚走了两天。前几天的村圩尽量避开,赶路不停。
秋官想是大先生要回程再演,当然不问——他还巴不得。他心里暗算,论脚程,明日过午,便到高明。
高明何家每年开春祠酬神,都请省城红船班咏丰华做大戏。咏丰华的《六国大封相》倒是响亮,可何家是大户,也曾在省城包过戏场,那几位老听倌总觉得锣点儿不对经谱,点名要大先生做全戏响锣。
大先生自知过界,会搅散同行的饭钵,只应承在尾戏里收锣。
何氏是高明望族,出过不少大功名的先人。这样的人家指名收锣,戏银自然肥盈。隔着十天的山路请大先生,也不是何家矫情,大先生的勾锣实在醒神。
薄饼铜锣黄澄澄,长探头的榆木小槌直愣愣,摆在那儿毫不起眼。大先生提到手里,仓——仓——仓仓——咣,稳稳敲在锣心上,响音向四面八方荡出去,震得耳朵眼儿发颤。悠远、沉郁、清脆、跳活……大先生的敲法除了端、举、托、提这些单槌、抛槌,还造出很多听头儿。什么彩云追、海底捞、胸口闷……他一槌在手,衬着戏文的锣点滚着花似的往外翻,轻快得像阵急雨坠在芭蕉葉上,噼噼啪啪地密响,可声音却能从锣面上逸出去,戏棚也嗡嗡颤栗。
这几年放戏,秋官越来越讨厌翻山。讲古人说,望山跑死马。秋官觉得,跑死倒未必,只是这山岭起伏,又连起来,一座接一座,大的山头埋在云雾里,像是顶过了天,怎么也走不到边际似的。他一想起这,身上便如同隔夜音吊嗓——绵柔无力了。秋官还觉得今年脚程特别慢。大先生在前面走得也慢。刚跟大先生那阵,脚下这段山路可半日不歇,一气到岭下村寨。现在,靠水烟撑起,半日里要停两停。
“秋官,等阵先。”大先生把辫子捉到背后,又再叫。
“大先生,仲不服老乜,锣槌拎唔拎得动先。”
“规矩,冇大冇细。”
“啰,规矩再大,大过山乜!”
话才出声,秋官知道讲错,心虚地把竹箩搬到胸前遮面。
大过山,大过山,你都识得大过山。大先生嘴巴挪开烟口,呲起黄牙,似笑非笑。
秋官忍住口舌,不敢争辩。大先生也不理他,又咕嘟两口,收了水烟继续往前。
秋官是冲龙围孤小,乡老做保,跟大先生签的六年师约,自此,他便拜华光揾食。大先生虽是哑嗓,可懂戏懂教,四年头上传给他三门武生花技。二郎点睛、飘须碎扇,他都早早习得。只有大过山这一式……
过山是武生的表演排场,说的是戏台上夫妻两人被仇家追杀,仓皇逃走,途中被高山挡道,夫妻涉险攀过高山,逃出虎口。武生把遮挡叠砌的桌子和椅子比成山,表演乌鸦晒翼、起虎尾,然后登上椅背翻跟斗而下。大先生觉得人人都会的把子定要出新,他教秋官的难多了。收尾是要横翻两座桌椅山。
秋官练这式把子用的是功凳,没少摔打,前胸后背又青又紫,像半开的花面。每到这时,大先生就会在旁啰唆。
大先生说,等秋官练好了这三式把子,就可真正过山,到能开全面、有排场戏台、能演对手戏的大班去。
大先生说,练成了三式把子,切莫叫人偷学了去,要等到挂了武生正印,才一个一个放出来,保准式式旺台,场场爆棚。
大先生还说,练成了,他“仲沽个好价添”。
秋官可早想出师了。冲龙围那山坳坳有什么好。红船班才够姜么,来往行水路,有天地艇,舟船飘飘摇摇,不需脚上奔波。不过红船班都要童子科,自然进不去,可大班却不难。先做手下(通传、备马、摆酒、磨墨等角色)、拉扯、五军虎,等挂了小武,衣盔登台,戏迷彩声一浪一浪,比山还高。最不济,转八仙班也好,能全开面。他可不想现在这样,小村圩放戏时叫好声都是星星廖廖。戏银也没有几毫。就讲今晚要留宿的岭下寨,别说戏棚,戏灯都没一盏。听戏的手里都擎住一柄黄面灯笼。不过走惯的戏路都在山里,一人高的戏台他想想又觉得脚下发空。况且,他还舍不得。
秋官越往前想,心和口里越是苦燥,像是有条蓟草叶子在拉扯,索性就亮起嗓子。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我好比潜水龙被困在沙滩……
唉,又唱行货(照本宣科)交差,无悲无喜。
吊嗓呀。秋官没有好气。
开嗓需使精,开面定有神。
嗨,又没听客。秋官还不服气。
山中树草花鸟、飞禽走兽都是听客。山林里吊出来的嗓,还不如回音壁出的童子科么。大先生摇头叹气。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秋官撇了撇嘴角。
大先生还要唉声,秋官已拨开茅草,岭下寨里稀稀落落的炊烟就在眼前。
响锣班,响锣班。
俩人刚入村路,寨田里耕种的农人已在叫嚷。
岭下寨实在穷困,戏牙和会主自不会来。要听戏,需要去外面请,可这里还少人,那便是请不起的。每年大多只一回。晚饭过后,寨里各户开始向祠堂汇聚,人却还是零零落落。
大先生支好锣架,难得捧出纳彩盒子。白粉铺底,红粉吊睛,竟涂了全开面。秋官早盼着这出,把脸凑向大先生的八音锣。左面,右面,瞧了又瞧。想摸摸,又怕抹花了脸。锣面倒映的才子武将模糊不清,可煞是好看。秋官眉毛佯挑,摆了个亮相,突然觉得好似杨四郎这尊神明上了身,眉心聚在一起,眼里也闪出神采来。
仓——仓仓——仓——咣。勾锣先开了腔。
一朝登台亮相,他朝侧帆远——呐——航。
大先生压起声,摇头断喝,手中锣槌滚起花来。
仓唥——仓唥——唥——唥——咣。
抛槌轻擦锣身,滑音滚过。一会儿似虫鸣啭,一会儿变成猎猎风声,突地又化为轰隆雷音。真真的是一台锣鼓半台戏。
锣声打作一团,听客的耳神仿佛都被请了出来,秋官倒是静下来了。他不再翻山,不再背箩,兴奋得心口如江潮涌动,脑子里全都是厮杀马鸣。他抬眼望见祠堂檐角的朝天吼,竟觉得周遭听客都幻化成了山林草木,嗓子眼儿阵阵湿痒。排场也好,唱腔也罢,他不能给杂乱留下丝毫空隙。大先生说,一切就像风起云至,鱼在水游,自然而然。榆木锣槌在他眼前敲开了一扇花棂旧窗,时辰也因他的叹唱被拉长。秋官自如又小心地控制,抛出去的声线像在走悬索,不敢有丝毫失音。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只杀得众儿郎滚下了马鞍,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我被擒改名姓身脱此难,将杨字拆木易匹配良缘……
听客们放下手中摇摇欲坠的光亮,鼓起掌叫好。
秋官还在甩收尾的龙虎音。
今夜,秋官就是岭下寨的大佬倌。
许是晚间的戏给大先生挣足了脸面,他特意从戏银中取出几毫,买了秋官提过几次的艾叶糍粑。煮熟的艾叶搅碎,和糯米粉一起舂,打成胶泥,颜色像淋过雨的早春山岭般翠绿时,再包上花生碎、熟芝麻、蔗糖,用芭叶裹起蒸熟,出屉后好似上了一层墨绿的芝麻釉。这是赶路人绝好的口粮。
晚上,秋官和大先生摸到寨边谭公祠。谭公祠门前有水塘,门内一进一出,正殿盘藤贯茎,壁残瓦乱,泥胎涂彩也早已斑驳,面目模糊。这里早就没了庙祝。倒是侧殿,留有木板,还能容身。往年,秋官和大先生就住在这里。
秋官趁著大先生把脚伸进水塘洗,也凑过去。舍不得擦去的彩面旁,是一汪圆得像黄面灯笼似的浑月。那塘里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秋官瞧了半天,只能掬捧清水冲洗,又撩动水花搓手,等塘水中晃动出本来面目,彩面已经留在心头了。
这一夜,秋官躺在大先生旁,忍着不动,各样的脸谱却在脑子放花片儿一样,怎么也止不住。他的心,可从没这般辗转反侧。
第二天,天光未亮,大先生就把秋官轰起,粗食些茶饼要上路。今日午时,他们定要赶到何家公祠。秋官早起,却不露倦态,难得摇摆起蛤蟆箩走在前面。他恨不得一个大翻越过山岭去。他知道,前面就是青石路的尽头,低首钻过两头斜枝探路的老榕,转弯便是坦途。
那两头歪脖老榕,一前一后,旁枝侧斜,高过人肩,前后隔着小半个戏台。路人需要矮身或是俯首才可穿过。
秋官急匆匆往前。大先生却又卸下水烟袋叫。
歇阵先。大先生吸了水烟,又在唠叨。
师傅知道你想打个大翻。
啰唆,乱说。
你心急去高明,我还看得出!大先生重重吸了一口。
你什么都知啦——我同戏钉强一年没见了。
我没说他。
秋官心里一紧,嘴上竟输了。
我说你想过界,转投大班牌。大先生吞吐云雾,身上拢起一团烟气。
秋官长长暗嘘。他抹了一把汗,准备卸下蛤蟆箩。才蹲下身,前面树林窸窸窣窣,紧接着灌木丛里“嗖”地一声响动,窜出来只黄色小兽。
是黄麂。
今次一路上山林寂静,难得见到林中鸟兽,秋官兴起,双臂出力一撑,顺势跳起,顾不得蛤蟆箩还背在身上,三步并作两步,一阵旋风追过去。黄麂胆小,窜入路中左右跳跃。秋官继续往前,眨眼就到歪头榕,他也不停,竟加快速度,还有一人距离时,双腿同时跳起,身子向前扑,跃到第一株斜出树干时,双掌一按,身形好似兔子蹬鹰,猛地甩起后腿,霎时人已跃到第二株上方,可他仍不减速,双掌在树干轻点,腰身继续发力,凌空前翻,双臂马上收回抱膝,稳稳落下。
黄麂已经跳进密林,不知去处。
秋官一下清醒了,不敢转身。
咳咳咳。
秋官聽到大先生在抓嗓子,知道是叫自己,不得已低头从老榕下钻回。走近了,也不敢抬眼。着草鞋的脚正搓灭半明半暗的烟火。
刚刚——,大先生放下水烟。
秋官不敢搭话,从蛤蟆箩里掏出艾叶糍粑,塞到大先生手里,然后自顾自揭起手上的芭叶。吃过糍粑,大先生再也不说话了,俩人一前一后,只剩下脚步唰唰作响,四下野鸟啁啾。
山路已是下坡。秋官只觉脚掌悬着,身子不自主向前倾,要屈膝软步才行。好在背上有蛤蟆箩往后坠,斜岔里还有枯木老藤。他费力放慢速度,让大先生能跟上自己。他不敢回头,只觉得大先生的脚步越来越轻,心里也越来越没底。山中腐叶败枝味道难闻,熏得秋官头晕。恍惚间他生出幻觉,大先生已经不在身后了。他更不敢回头看,既怕看到大先生的眼,也怕看不到大先生了。
隐约间,秋官好像看到了咏丰华的红船。大佬倌鱼贯下舟,衣箱伯父、杂箱叔父紧随卸货,衫手、饭质在打下手。还有在船板上古灵精怪的妹仔巧蓉……像是戏开了头,却收不得尾,秋官越想越乱,最后竟发起狠。
哼,大先生自己的锣点,不是也要零沽!
剩下的路,秋官走得不在板眼,话也没有丝毫腔调。直到入了高明何湾,快到公祠时,远远看到戏钉强还是老样子,蹲在子棚趟栊(听客席位外的闸口)听白戏,他才缓过劲儿来。
戏钉强跟秋官同年,是前两次来高明何家打收锣时黏熟的戏友。据说家世风光过,后来破落了,被家人带回老家祖屋。戏钉强跟秋官吹水,说省城四大天王的戏他都听过,怕秋官不信,还开嗓唱了几句暖场。
大先生一到公祠,早有何家和咏丰华的人候着,引他进了后棚。戏钉强见到秋官,也兴奋起来,拉住不放。秋官心里还在难过,竟怎么也提不起劲头,推说还要收拾宿位,晚上再来找他。戏钉强嬉笑,挤眉弄眼,用肩膀侧身顶了一下秋官心窝,说,晚上你不见巧蓉吗。这话说得,比那只黄麂更让秋官心慌。他还想辩白,戏钉强撇撇嘴,说,巧蓉可早就来了,喏,我才还见她在扮梅香(宫女等角色)。
秋官不敢再说什么,背起蛤蟆箩飞也似的逃开。往东放戏,只有这一天能睡得舒坦——主人家必定选好宿处,哪里还要他收拾。秋官只是知道时间还早,要见她,须得等到月上树梢。这可真是煎熬。倒比十天的山路还远,还累。天黑得又慢,晕月不知费了多少力气,才爬上山尖。
秋官换了杂衣,往李林匆匆去。脚步轻快能连打百十个大翻。走近了,打着双髻的黄褂人影,正在费力拉长身子。是巧蓉了。
巧蓉踮起脚,蛮腰盈握,费力摘李花。秋官悄然身后,轻呼两声乳名。
蓉姐儿,蓉姐儿。
巧蓉心喜,转回头觅,正看到秋官蹑手蹑脚凑过来。
蓉姐儿莫动,我来替你摘李子。
巧蓉手一滞,见秋官又近了,蓦地反应过来。李花方开未败,哪里来的果儿。她只道中了秋官的心计,柔枝轻甩,佯做负气。
秋官厚起面,又往前一步,蹭到树下,从怀里掏出偷留下的艾叶糍粑。
是去年在这株李树下给巧蓉应的诺。她最爱吃的。
巧蓉眉目松了,嗤地笑出声。缩回手,粉腮半掩。秋官大胆起来,捞起香手,半推半塞。缓了一缓,醒悟过来,又从巧蓉手里拿回。小心翼翼地摊在掌心,轻轻地撕开裹着的芭叶,才又递过去。
巧蓉不作声了,伸手接过,坐在白色树下小口吃。
嗳——莫动,你唇角粘了芝麻。
巧蓉又被唬住,嘴也停了。伸头向前凑,等着秋官帮他擦。
不对,她挥拳捶过去。
哪有哪有,那是天生痣,好衰。
打完,脸却收不住,红像潮水从面颊涨起,漫上耳朵去。巧蓉暗叫冤家,定心不去想他,可抬头正看到秋官调笑的眼,更难自止,红又深一层,久久不肯褪下。
秋官再也忍不住,捂起肚子,眼泪也挤出来。
“啊,初惊艳,初惊艳,骤然望见一位小婢似天仙……”
不远处,公祠前,“唐寅”在戏台上摇扇数白榄。
春月冻黄,两人静默,声气相闻。秋官不说话了,手指沿着青石纹路胡乱扣着心事。
糍粑软糯丝凉。巧蓉肚鼓了,心却暖了。料峭的月光里,脸上是晃晃荡荡的红。这红色像是开脸时涂抹的粉彩,化成媚意在秋官心头流动。他满目春光,一时竟看得呆了。
要走了,要走了。巧蓉轻声嘟囔。
今日戏约到了,晚上天光戏收官。明日红船起锭,翁家班该返程了。她撩起鬓角别在耳后,又补充。
秋官不愿再想,只觉得生出燥意,大起胆揽过去。
“……哈,佢系菩萨面前对我一笑,系官船又对住我一笑,依家又对我一笑,分明系对我有意思个啫……”
“唐寅”念白恰在好时。
巧蓉慌忙向后倚,鬓和髻被花枝扎乱了。心里鼓点也敲乱了。
过山秋,过山秋。
有人在暗处蹑声。秋官不看也知,只有戏钉强这样叫他。他老大不情愿,顺着声音转过身,把巧蓉挡在身后。戏钉强正东张西望,他还没有看到他。秋官不愿答应,却被身后巧蓉推了他一把。他没奈何直起身,闪身挪位,让巧蓉先走。
你不在子棚听戏,来这里做什么?
哎呀呀,大件事,大件事啦,你还有心思在这里。
怎么了?
大先生卖了师约啦。
什么?
哎呀,哎呀呀!你都知道,我没银纸买戏票,躲在棚外做戏钉。《跳加官》那阵,一锭金锣点才止,听到翁班主拉住大先生话买你的师约呀。我看到,大先生收了一封银元啦。
秋官头脑一阵晕眩,险些跌倒。大先生把他卖了。把他卖了。
戏钉强把秋官送回坪塘时,大先生还没回来。他躺在木板床上,悲伤从心里往喉头滚。他怎么会卖他,他怎么能卖他。他快出徒了,可以养他。大过山这式把子,去年就会了,就是那句“仲沽个好价添”,他一直压起。怪都怪自己,手脚不稳,心也不稳,偏要追黄麂。可是,可是……大先生回来一定会解释,一定会。
咳,咳咳。
大先生推门进来,见秋官躺在床上,灶膛没有燃起,从壁角拎出些干枝,又自怀里掏出张黄纸。嚓,点燃,等火旺,塞进灶膛。水烟凑过去,呼噜噜,呼噜噜,烟泡从竹筒里吸上来。
嘘——好长的一声叹息。
秋官见大先生竟不叫他,心里更难受了,一口气憋在胸口,撑着不让它吐出来。胸口的气到顶得住,可眼泪却要止不住了。他不愿意被大先生看到,闭紧眼翻身,把脸躲进暗处。才背过去,眼泪一颗接一颗,滚出来。上面眼角里的泪划过鼻根,和下面眼里的泪汇到一起,在鱼尾处晃荡,等滴落了,洇湿成一摊更暗的影子。
你要卖就卖吧。嗨,谁想守住你这老头子。
你要卖就卖吧。呵,出门放戏再也没人给你背蛤蟆箩。
你要卖就卖吧。哼,我还能天天见蓉姐。
“山高水低,各安天命”吧。这可不是我秋官自讲自话,是师约上黄纸黑字写的。
秋官侧卧在木板床上胡思乱想。大先生抽完水烟,也凑过来。他知道大先生在看他,可忍住不睁眼,等大先生解释。大先生竟不再说什么,屋里只有木枝噼啪作响,不过一时,映在墙上的火苗也越来越暗了。
秋官再被摇醒时天已放亮。巧蓉正坐在木板旁看他。
喂——秋官以为还在梦里。
大先生把你过给翁家班啦,巧蓉眼角都在弯起。再不跟我上船耽误了起锭。
我知呀,卖了我师约嘛。秋官有气无力。
傻子,哪里卖了师约啦。大先生同班主谈妥了,认你已出了师,要你过山至咏丰华做五军虎。
啊!
翁班主本不答应,可大先生说你不入班,他明年不再起锣。
大先生不是收了班主一封银元?
都说你傻子啦,打锣不收银纸么!
秋官突然想起,昨晚大先生点水烟的黄纸,可不正是那张师约。
你别想了,我来时见大先生已走返程,快到山梁啦。
秋官再也忍不住,起身冲出围塘。
远远望,还能见到大先生背着蛤蟆箩,已翻到山尖。秋官眼睛追过去,翠绿林路里,那一点的身形,正大过山。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