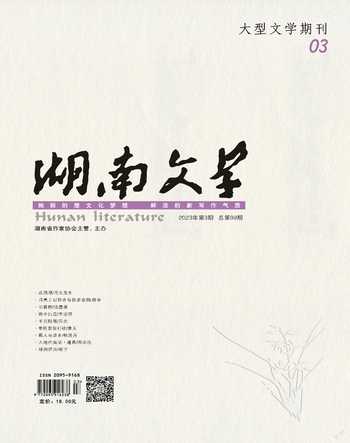绿洲辞典
南子
英吉沙刀
他将全部身心专注在一把刀上——磨刃、瞄视、吹气,再磨刃、再瞄视、再吹气……铁锤敲击、砂轮嗡嗡,铁腥气随着炉火中溅起的火星四处弥漫,直至如线的刀刃泛着银光,他才向我露出一丝微笑。
此刻,我坐在他对面,手持一把小巧的英吉沙刀,尝试将半只圆馕削成一片一片。在手工作坊尘土飞扬的光照中,我看见刀柄上刻着葡萄藤蔓,以及他的名字:热合曼·塔石。
他是一位制作英吉沙刀的艺人。
从这行文字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埋头做刀的手工艺人,背影模糊,从未起身,他在小刀刚与柔、水和火的锻造过程中,仿佛在锻造另一种语言。
英吉沙在维吾爾语中是“新城”之意。以它之名命名的英吉沙刀一般长十一二厘米,最长的达半米以上,最小的仅两寸左右,它们的造型有月牙儿、鱼腹、凤尾、雄鹰、红嘴山鸦及百灵鸟头……还有的则难以名状。
无论何种式样,它的做工都非常精细。且不说它锐利无比,那是许多刀具所共有的特点。我曾见过卖刀人的现场表演:切毛发一触即断,削铁片屑落纷纷。
喀什英吉沙县芒辛乡栏干村,是当地有名的“小刀村”。据说,全村三百多户人家竟有一半以上从事这个行当。小刀的整个生产过程都是手工操作,一副小泥炉,一把小铁锤,一支小铁钻,这就是刀匠们最主要的工具。
锻打、沾火、定型、磨刃、制柄……英吉沙刀既是切割水果、肉食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无与伦比的小刀是靠这些原始落后的工具,用粗糙的双手锻打出来的。
“其实,每一把英吉沙刀都是独一无二的。”在热合曼眼中,刀是有生命的东西,“你看,生硬的钢板经过打磨,变成了锋利的刀身,就像帮助老人吃东西的牙齿,那些破损的牦牛角、黄羊角及鹿角,经过剪拆、修磨后,再加以装饰,就变成了刀柄,成为有用的东西,有如一件废物获得了重生。”
四十年前,十八岁的热合曼在喀什市的巴扎漫游,街道狭窄,土坯民居和旧木头门的店铺高低错落,镶牙的彩色招牌旁的窗户下面,挂着啼鸣不止的鹦鹉,人们遵循古老的训戒,恪守清贫的生活,白杨树干覆盖着用树枝或草搭成的顶棚,光线半明半暗,时光好像停滞了下来——
商贩们的脸被炽热的阳光晒得绯红,空气中有茴香、肉桂、葡萄干、植物染料、灰尘、汗液,以及烈日的灼热气息……
热闹的集市上,铺在脚下的都是同样颜色的花毡,头上撑着的,都是同样的苇草棚,而招来买家的,也都是同样一种声音——这些商品在路途中穿梭不已,从一些人手里到另一些人手里,或者到土里,或者到火里,或者在人的身体里消失。喧闹中,不时传来商贩们吆喝时的奇特声调。
巴扎角落,一间英吉沙刀手工作坊里尘土飞扬,一位老人正在铺子里做刀,铁锤叮叮当当,刀具在粗粝砂轮上的摩擦声,像维吾尔族传统的木卡姆舞曲,尤其悦耳。
刀铺的院子打理得果木葳蕤,夹竹桃粉色桃花开得正盛,但是店铺里的铁腥气,与植物敏感的性情不相应,不过,屋子里飞扬的尘土与土坯房的泥土本色,倒与刀匠这个职业有着本质上的贴切。
热合曼在这家刀铺前站了好几天,飞溅的火星像星光,照亮了他的心。
刀铺的主人是一位毕生锻造英吉沙刀的匠人,叫买买提,多年前,由他的爷爷制作的一种雕刻有红、绿、黑等颜色的木柄小刀,锋利美观,人们纷纷盘炉仿制,从而世代相传。后来,工匠们各出心裁,制作出各种造型的小刀,并在刀柄上用黄铜、白银、牛角及贝壳等镶嵌,并雕刻富有民族特色的图案,英吉沙小刀手艺从此兴盛开来。
在这里,年轻的热合曼开始了拜访名师的生活。他在这里淬火、锻打锉磨,开始了一位民间手工艺人的艰辛生活。一种对技艺的追求和向往,使他忘记时间、饥饿,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数年过后,热合曼已是一个身怀绝技的制刀艺人。刀,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他用优良钢材锻打刀具,制成粗坯后,再用各种锉刀锉平磨光,最后进行淬火。经过淬火处理的小刀刀刃锋利,削刮铁器,只见铁屑迎刃而起,刀锋却未见卷刃或崩口,不缺不卷,如同月光般洁净柔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一生锋利,那是缘自热爱才有的奇迹。
英吉沙小刀之所以传世,还有一项独门秘技——以舌开刀,相当于以吻封缄,更是近乎于爱情的狂热。
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穆萨莱思
葡萄,是做穆萨莱思最重要的原料。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波斯(即今日伊朗)是最早酿造葡萄酒的国家。张骞凿空西域,葡萄先传至西域,又由他从西域传至中原。
话说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与胡奴甘父风尘仆仆地来到大宛,发现这里俨然是中亚葡萄的种植中心。田野及村路两侧的葡萄藤架上结满了葡萄,它们呈球形、卵形、椭圆形等,有的圆若珍珠,有的艳似玛瑙,有的绿如翡翠,入口一尝,皮薄、肉嫩、多汁和味美。仰头的时候,环顾的时候,串串葡萄充满了整个视野,而低下头,地上也印满了葡萄的影子。
一日,张骞在隐隐的奇香中,来到一处酒肆门前,只见几位豆蔻少女将新鲜葡萄洗净后,装入布袋里绑紧袋口,然后光脚踩踏出葡萄的汁液。随后,一位长须老者将其倒入一口铁锅,兑入水,用文火慢煮至水蒸发出渣,再倒入绸布口袋,慢慢挤压出如琥珀色的汁液,同原有的葡萄汁混合在一起,再用文火慢煮,随后,锅中汁液表面会有一层白色杂质泡沫,滤去,再煮,一层红褐色的泡沫浮了上来……
酿制库兹娜(葡萄酒)的动作,在这位老者手中几乎一气呵成,张骞看得入迷极了。
这时,一位少女走到张骞身边,微笑着对他说,这锅液体静置几个小时就得停火,在锅中存放一整天后,将其倒入土陶坛中自然发酵,然后再加入上好鹿茸等几十种食材,经四十天晒发酵后窖藏而成,这时候的葡萄酒最有酒性,可储藏十多年不坏。
说完,她像变魔术似的,从身后拿出一杯酿好的葡萄酒,示意他喝下去。
张骞将这杯酒喝下去后,顿时感觉腹部涌出一股热气,一种莫名的美妙感觉让他想哭,想笑——“库兹娜,这是西域琼浆啊。”
关于葡萄酒的制作技术,《史记·大宛列传》进行了相关描述:“宛左右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积数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萄肥饶地。”而《博物志》中,也有“西域有葡萄,积年不败,可十年饮之”的记载,并有“葡萄酒熟红珠滴”的赞美诗句。
不过,张骞仅从大宛带来葡萄种子,但没获得葡萄酒酿造技术。据后人考证,“库兹娜”就是当今被称为“穆萨莱思”的酒。它是西域最古老的葡萄酒。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西域民族嗜酒如命,收录在《突厥语大词典》中的民歌證实了这种豪饮:“让我们吆喝着各饮三十杯,让我们欢乐蹦跳,让我们如狮子一样吼叫,忧愁散去,让我们尽情欢笑。”他们喝的是西域最古老的葡萄酒——穆萨莱思。唐人诗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瑟琶马上催”中的“葡萄美酒”,以及当年高昌王向唐王朝进贡的“西域琼浆”,指的就是穆萨莱思。如今,它的盛产地主要在新疆的阿瓦提县。
“穆萨莱思”,当地人称它“朵拉”,就是药的意思。有人说,来阿瓦提如果不喝穆萨莱思葡萄酒,就像吃烤羊肉忘了放孜然一样,让人遗憾。
阿瓦提县乌鲁却勒镇海勒畔村被誉为穆萨莱思的发源地。
海勒畔村是阿瓦提县距离沙漠最近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刀郎人。刀郎人像风吹来的沙,一直生活在叶尔羌河流域,逐水草而居。如今,他们已从原先的渔猎和游牧转为农耕定居生活。
有一年初秋,我来阿瓦提县海勒畔村时,天色已近黄昏,斜射的光从正午的白炽,正变成柔和的暖色光晕,简直可以捧掬啜饮。
村路两旁高大笔直的白杨树随风飒飒,晚归的羊只,三三两两地从树下的瓜摊前走过,驴车在马路上缓行,车上的维吾尔族汉子头枕羊皮袄,陷入慵懒的昏睡中。
一路上,我看见那些农家小院木门紧闭或虚掩,一切按部就班又无所事事,毫无意义却又生机盎然。这时,我突然嗅到了空气中一股发酵般的酸甜、微涩的果香味道,闻久了,竟有一种微醺的感觉。
随即,我为路边一处农庄葡萄林所震惊——迷宫般的木架下是一大片葡萄的海,纠结的藤蔓泛起绿色波澜,成熟的葡萄带着蜜汁四溅的放肆,点亮翡翠之灯。我摘了一颗葡萄,皮上带有微微的白霜,果实的汁液甜而微涩。
如同葡萄到葡萄酒的演变,从夏天到秋天,是葡萄园从肉身向精神的一次缓慢过渡。当葡萄变成了琼浆,变成了纯粹的精神饮品,葡萄园的世俗意义也在发生变化。
几乎每一位阿瓦提人都是酿酒师。在乡间酒舍,要是谁敢说自己不会做穆萨莱思,那么,他肯定不是纯粹的阿瓦提人。
在这个葡萄庄园里,我就遇见了阿瓦提最有名的穆萨莱思酿酒师:毛拉艾买提。
酿造穆萨莱思,完全是纯手工,靠的是视觉、嗅觉、味觉及手感。由于人们在酿造过程中加入了不同材料,所以,每家穆萨莱思的口味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重复与模仿。
在同一个村庄,即使有上百户人家,也不会有滋味雷同的穆萨莱思。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做的葡萄酒的口味也会截然不同——这与酿酒人的性格、心情、境遇等等全都有关,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气质和个性风格完全融入了穆萨莱思。
毛拉艾买提认可了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年轻人酿的酒血气方刚,喝多了会让人热血沸腾;老年人酿的酒浑厚深沉,得花些时间细品;失意的人酿的酒,多有苦涩味,喝了会让人忍不住潸然泪下;恋爱的人酿的酒,则含有玫瑰的味道,喝了后令其心情愉悦……
这些个说法令我新奇。
他还说:“葡萄就像人一样,是有生命,有性格,有脾气的。你对它好,时常精心修剪、关爱、照顾它,它就会把好报给你,长出的葡萄甜蜜水灵,酿造出的穆萨莱思就是好的。”
起初,阿瓦提人用当地种出来的葡萄酿制穆塞莱思,后来发现,和田“和田红”的葡萄与阿瓦提的葡萄混合在一起,经过长时间熬制和发酵后,口感和味道非常独特。于是,这种酿制方式延用到了现在。如今,阿瓦提人每年都要到和田买回大量的“和田红”葡萄来制作穆萨莱思。
说起来,毛拉艾买提酿造穆萨莱思的方法,与别家没啥两样,经常有人过来观看过他做穆萨莱思的全过程,一样的葡萄,一样的烧煮,一样的封存,可口感和色泽就是相差很远。
穆萨莱思的酿制方法和自酿葡萄酒稍有不同,自酿葡萄酒,在整个酿制过程中不会加入一滴水,而穆萨莱思不但需要加水,还要蒸发锅中多余的水分。并且,酿酒师根据自己的喜好,会添加不同的东西。
毛拉艾买提告诉我,酿造穆萨莱斯时,根据季节不同,采用了一些维吾尔族常用的中药材如丁香、鹿茸、玉竹、小豆蔻、石鸡苦胆、藏红花,还有雪山红花、新鲜肉苁蓉、三年野生红枸杞、枝顶红葡萄、成年雄鸽血及小枝玫瑰花瓣等。
“我放的东西更加大胆,有时还会把整只烤全羊放入酒液中,待羊肉完全融化于酒中,捞起骨架,穆萨莱斯就酿成了。这种穆萨莱斯营养很好,我干脆把它叫作‘肉酒。”毛拉艾买提补充说:“我做的穆萨莱思,液体有韧劲有黏度,往指甲上一滴,来回晃动都不会掉下去,甚至能倒挂住!”
我忍不住端起酒碗喝了一口,果然别有风味,除了葡萄的酵香,还有一股淡淡的药香。
汉族人戏称穆萨莱思为“没事来事”。许多刚喝穆萨莱思的人感觉它没什么酒味,于是就漫不经心地多喝两碗,孰不知,穆萨莱思后劲极大。
据说,穆萨莱思在缸里发酵时,有的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开水煮沸似的声音,有的还会发出“砰砰砰”的爆炸声。酿酒师听一下响声,就知道穆萨莱思的成色和质量了。
和当地那些烧煮穆萨莱思的人家一样,毛拉艾买提与村民一直延续着多年前的风俗习惯,每到农闲时节,穆萨莱思发酵好了,大家煮好羊肉,一起畅饮穆萨莱思,还要比一比看谁家的慕萨莱思烧煮得好。刀郎人生性剽悍不羁,美酒与歌舞是伴他们得度茫茫尘世的最好方式,亦是传统。他们喝穆萨莱思,跳刀郎舞,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中度过整整一个冬天。
在阿瓦提的那些天,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天下已经有这么多葡萄酒了,可阿瓦提县的人们为何还要这么费力地酿造穆萨莱思酒呢?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葡萄的,又是在什么时候掌握穆萨莱思酿造的秘密的?在酿造的过程中,又耗费了多少热情和光阴……
祖传手艺就是安身立命之道,毛拉艾买提深知酿制穆萨莱思就是家族的印记和骄傲。经他酿制的穆萨莱思,除了留些自家享用之外,其余都销往县里的餐饮行业。可如今,村子里家庭作坊式的酿制工艺遇到了来自外部世界与现代化酒厂的冲击,这让他时常感到困惑。
不过,到了每年五月,毛拉艾买提与阿瓦提的村民又开始像往常一样,期待九月的一场秘密的酿造。村子周围能看见的地方,都是葡萄树,都是等待酿造的成熟的葡萄。
每一个装着穆萨莱思的大陶缸都相约守着秘密,在五月的阳光下沉默不语。
白杨树
去南疆的路,必定是一条戈壁沙漠之路,一条绿树锁住黄沙之路。
这树,就是白杨树。
它有如绿色屏障,把天山南北的绿洲分隔成一个个方块。
现在是八月,正午阳光下破旧集镇的路上没什么人走动。村庄的宁静,就像田野的宁静一样,把许多有声色的情节掩埋了——泥土是灰色的、僵硬的,夹杂着陈年的稻草。苇子扎起的如鸽舍般的土泥小屋,黄色火焰般的草垛,散落在叶脉般的道路两旁。被树木及葡萄架子环绕的土房周围有狗及牛的粪便。
这时,我看到了白杨树。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钻天大白杨。
它们密集地默立在公路两侧,带着热情的绿色和乐观的哗笑着,列队守在道路两边,如绿墙般,一棵棵地笔直高大,相连成行,每一棵树都像陪伴母亲的孝子,一棵树与另一棵与它相邻的树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深沉的渊源和默契——树顶的枝叶纠缠,形成遮挡强烈日光的阴凉通道,有如白杨隧道,一路走过去,我看见它们手挽着手,像在举行一场集体婚礼。
从一棵白杨树到另一棵白杨树。从一个枝柯叶簇到另一个枝柯叶簇,所有的叶子随风摆动,上肢在空中相挽,形成一个巨大的绿色拱道。树林间穿透着稀疏的阳光,一种别样的温馨流淌。
风从它们中间经过,一股微苦青涩的气息,延续到下一个村庄的更深处,时间的更深处。
有人称,白杨树是“绿洲之树”,是“迎宾之树”。它们身上几乎不长什么虫子,像英姿勃发的小伙子,从不生病,且精力充沛。
诗人庞培曾在新疆待了大半年时间,尤喜南疆风物。他说:“白杨树周围有一种可称为‘南疆空气的音质,你在其他地方不可能听见。”
作为南疆土著,我大致懂得他所说“南疆空气”的音质是什么意思。
维吾尔族人尤爱白杨。无论搬到哪里,只要有条件,他们就要在自家门前屋后栽种白杨树,然后在树下筑居,安身立命,渐渐有了家园感。
也有人称白杨树是农民树。
这是与老百姓的生活最近的树。还没哪一种树,像白楊树这样高且直。虽说栽种稠密,但生长很快,七八年就成材了,十几年就成大材,等自己的孩子长大该结婚了,白杨树也就长成了,人们用白杨树叶养羊喂牛,而它的树干是盖房子的上好材料,便伐掉用它盖新房,打家具。
在南疆乡村道路两侧,都是密集的白杨。
一个清晨,天晴得呀,像一个清脆的唿哨。灰鸽子像一个个泥塑的玩具,停留在村巴扎的旁的白杨树梢,赶巴扎的驴车过来了,嘚嘚嘚着地的声音,搅得马路尘土飞扬。
鸽子的美梦被惊醒,呼啦啦地飞到天空,仰头看,像是谁将一把碎纸屑随手撒向空中,阳光下刚烘烤出来的馕,与尘土味、果香味,以及孜然和烤肉味混合,组成浓烈的巴扎味,在吆喝声及白杨树搅起的风声中,让我感觉四周都是愉快而古老的人间景象。
到了中午,白杨树的浓荫密密地遮盖了炎夏的太阳,水池里,树叶上,羊背、草尖、屋顶、土路等等,阳光底下的一切都闪着又亮又硬的光泽,白色的太阳炙热得像是把一切东西晒得冒了烟,烟气从地面树梢屋顶冒上来,似乎看得很清楚,一眨眼却又看不见了,再一看,眼见的一切都浮在热气中,摇摇晃晃的,有些不稳似的。
赶巴扎的人三五成群地坐在浓荫里闲聊,睡觉,阳光被层叠的树叶过滤,漏到人身上,就变成了淡淡的圆圆的光斑。
在烈日与荒漠之间,几头卧在远处木桩子下的绵羊,好像死了。
白杨树属于落叶乔木,树干最高可以达三十米,是西北最普通的一种树,只要有人有草的地方,就有白杨树的身影。
自古以来,描写白杨的诗句比比皆是,如两汉佚名的《驱车上东门》中有:“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唐代王昌龄《长歌行》的“系马倚白杨,谁知我怀抱。”魏晋陶渊明的《拟挽歌辞·其三》中有“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唐代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李白的《劳劳亭歌》“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以及两汉佚名的《去者日以疏》,“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另有“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玉局他年无限笑,白杨今日几人悲”等等吧。
这类诗歌多以描写白杨萧萧来烘托诗人的愁思。诗句多与生活的艰辛及人类的悲秋意识联系起来,让我看到,落日映照下,秋风萧瑟,荒台破败,古墓荒凉,白杨树在秋风中萧萧的声响,使人愁煞——这都是生死离别的地方啊!可在我看来,一棵棵枝叶繁茂、挺拔健美的白杨树,怎可以有如此苍老无力的万般愁绪?
白杨树,它是一个意气风发、仪态俊朗的少年的青春啊,是树中的男子汉和伟丈夫,是扎根在心底不断生长的声音,是来自绿洲集体主义的赞美诗,更是随风起伏,繁音促节的合唱和重唱。
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在新疆住过一段时间,他发现,无论是在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两边,还是在乡村的街巷和院落,新疆人最喜欢种植的树是白杨树。水渠边、田埂旁、居民家院的房前房后都种有白杨树。这种枝叶繁茂,挺拔健美的树,不仅可以挡风、遮阳、纳凉,还可以美化城市街道及庭院。一棵白杨树站在那里,就能抵挡一些风沙,或产生一个地名及村庄。后来,茅盾回到内地,写了一篇赞美白杨树的散文《白杨礼赞》。他称它是团结向上的树。
有人还将白杨树比喻成少女之树——她挺拔、苗条、骄傲,喜欢站成一排挽臂而出,她们的树干如玉腰,收紧的枝条,像高举的玉臂,一片片整齐的叶子,如同一根根向上飘起的辫子。
因新疆多白杨树,好多地方的地名,都以它命名,比如,往乌鲁木齐县的天山里有一条沟,叫白杨沟,大概那里多白杨树吧。这条沟一直是徒步爱好者必去之地。而叫白杨河的地名,也有好几处。
按照维吾尔或者哈萨克语的读音,白杨树通常译写为铁列克、铁力克。去往阿勒泰哈巴河县,有个铁热克提乡。铁热克提之意是杨树林,因境内白杨树较多而得名。不过,这里除了白杨树,更多的是白桦,一到深秋季,景色绝美。
除了哈巴河县的铁热克提乡,新疆其他与杨树有关的地名也不少,比如喀拉铁热克黑杨树,萨尔铁热克黄杨树,科克铁热克青杨树,琼铁热克大杨树,霍斯铁热克两棵杨树,别斯铁热克五棵杨树,铁热克里克意为杨树多的地方。还有叫汗铁热克的,也就是杨树王。
另外,还有“杨树的集市”叫铁热克巴扎,甚至还有一个塔吉克语的地名:很祖铁热克,意思是姑娘的杨树,据说是姑娘们喜欢聚在这里的杨树下。更多的地方则直接叫铁热克(杨树)或者铁热克提、铁热克特,杨树林等。
不过,最有气势的应该是波斯坦铁列克,波斯坦是“绿洲”之意,因此,波斯坦铁列克的意思,就是绿洲白杨或者白杨的绿洲。
那蒙古语的地名中有没有杨树呢?有的。
新疆很多地方叫乌拉斯台或乌拉斯塔,大大小小少说也有十几个,其实就是蒙古语杨树林的意思。
如此看来,新疆的杨树还真不少呢。
那天,我们“新诗写新疆”采风团在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一天。
白天,克孜尔山谷树叶翠绿,木扎提河水欢畅,静坐于莲花座的鸠摩罗什雕像,正静静地俯身沉思,整个深黑色雕像笼罩在热风中,同身后盘旋的阶梯、红褐色山峦中层层叠叠的洞窟、湛蓝的天际线融为一体。
这里,成为方圆几十公里荒原内一处有山有水有丛林有佛像的神奇所在……
山谷中有一条长而直的白杨路。路两旁都是白杨树,一棵棵挨得很近,树比别处略粗、略矮一些,好像每一棵树都可以和人拥抱,都像清晨鸟儿的羽毛一样干净、松软。像被蓝天深邃的,令人眩晕的引力召唤,竭力在燃烧这怒放的绿色火焰。
到了晚上,喝得有些微醺的我们,沿着这条白杨路,慢慢地走,小声说话。走着走着,有人还唱起了歌。
山谷幽静,路两旁白杨树的气息,似乎在夜晚要更浓烈一些,好像它们在大口呼吸。
克孜尔的夏夜多美,在这里,我看见的是时间与人生的缓慢幽暗。夜宿克孜尔是一种奇妙而又奢侈的感觉,微风,流泻的星,夜意和白杨树的绿意无声漫流,克孜尔的夜晚充满了清凉、纯蓝、裂冰似的移动碎光。
几千年前僧人們的诵经磬音早已停歇,在酣睡中难以辨别,不知,它是石窟中菱形格里的壁画飞天的呼吸,还是我们的呼吸。白杨树下的歌声和微笑使这一夜区别于曾经的许多夜晚。
直到夜深,我们还没走回住所。
此时,我看不见明屋塔格山上蜂房如织的洞窟内,婉转曼妙的龟兹伎人,以及行云流水般的经文,还有那生生不息、潺潺流淌的木扎提河……风吹过,哗哗作响的白杨树叶仿佛在琅琅可诵读“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此句出自鸠摩罗什)”这简雅优美,包含无穷智慧的偈语。
我站在路中间,心似有所动,但却又不知为何而动,抬头仰视着一棵棵白杨树的阴影,一轮半月形的弧线隐藏,或者浮现。
一个溽热的夜,在等待黎明。
塔克拉玛干沙漠
一个燠热的夏日正午,热风吹拂塔克拉玛干沙漠,空气中弥漫着浓稠的、梦魇的气息,缓慢得像要凝固。
中途休息的时候,我下车,远离公路和人群,踏上沙丘漫无边际地走,此刻正是太阳热烈、熊熊燃烧的时候。万物困倦。
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细细的、无所不在的、神秘的“咝——咝——”声。我停下脚步,那不是虫鸣,不是风声,没有方向,也找不到出处,静声屛气去听那声音,它便消失了,一转脸,那声音又聚拢过来。
我被这若有若无的声音迷惑,以为是幻听。后来,我向同车一位搞民俗的老先生请教,才弄明白了这标志性的声音,他说,天地为鼎,烈日为焰(人间的大火来自天上,如同地狱之火来自阴冥),万物如同这铁锅中不变的炒货,而这声音,就是那最后一点水分蒸发时发出的天籁。
和湿润的大河流域三角洲繁荣的绿连绵地生,不断增多,不断地乘和加,不断地变和有,发酵、繁殖、孕育有所不同;沙漠是剔除和取消,是除和减,是无。二者如同水火,如同生死。
这片沙漠戈壁、极端干旱的地域,有着提炼和挑选的功能。对植物的挑选,对动物的挑选,对人的挑选,对文化和精神的挑选。它以少胜多,拒绝中庸,拒绝含混暧昧,是火焰的形象和向上升腾的气流,它倾向于纯粹、极致,倾向于唯一性和至上性。
这种现象,在此刻的戈壁沙漠中看得最清楚——在日光直射下的一处沙丘中,我看到一截白骨,它可能是马的,也可能是骆驼的。贴近看,这截骨头没有沾染沙土,像是肉身被火之沙漠舐噬后,难以消化而呕吐出来,又被时间之手剔得光滑、干净,它半掩在黄沙中,不含一丝水分。
让人想到,除了所谓“灵魂不死”的观念,肉体也可以不朽。而这,也只有沙漠能做到。
塔克拉玛干沙漠,维吾尔语意为“进去出不来的地方”。
千百年来,进入西域沙漠的探险队、商队、寻宝者及朝觐者络绎不绝,怀揣的目的也各有不同,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湮没的文明或者黄金宝藏。
《北史》中清晰地记载了穿越沙漠的旅人们所要经历的艰难险阻:“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啧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掩鼻口,其风迅速,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
这些倒毙在沙漠里的人、马、骆驼,最后变成了一堆堆狰狞的白骨,半掩在黄沙中,可仍未吓退人们勘踏此地的决心。
这,恰恰是沙漠恐惧的魅力吧。
而在唐代,库木塔格沙漠被称为“大患鬼魅碛”,至今还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我有幸在木姆塔格沙漠见到过海市蜃楼奇观。
在新疆,车子开出县城或村子几百米,就是戈壁或沙漠。但所有这些景象,都没有像鄯善县城与库木塔格沙漠那样触目。
“库木塔格”在维吾尔语里是“沙山”之意,指的是“有沙山的沙漠”。其沙漠地形非常丰富,有沙窝地、蜂窝状沙地、平沙地、波状沙丘地、鱼鳞纹沙坡地等。沙丘轮廓清晰、层次分明:丘脊线平滑流畅,迎风面沙坡似水,背风坡流沙如泻。
它作为世界上少有的与城市零距离接触的沙漠,距离吐鲁番市区也仅九十公里左右,与鄯善县城更是一线之隔——一边是浓绿,一边是黄沙。触手可及的滚滚黄沙,波涛汹涌的滚滚黄沙,如同一件丝质披风,流过绿翡翠般的绿洲之地。
那天正午,我们一行在库木塔格沙漠公路行走时,发现远处地面的水汽使地平线波动扭曲,阳光折射下的柏油路面好像出现一个个水洼,随着车轮飞驰,水洼不断消失又不断出现。
远处,空旷沙漠的地平线突然出现了一个水波荡漾的大湖,湖面有影影绰绰的波光闪动,岸边隐约有树木、房屋的轮廓。
“海市蜃楼——”。同行的人低声惊叫了起来。
一二二四年,马可·波罗经过新疆的罗布沙漠,确信沙漠幽灵的存在:“这片沙漠是许多罪恶的幽灵出没的场所。它们戏弄往来的旅客,使他们发生一种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
对于他们来说,沙漠中出现极具诱惑性的“海市蜃楼”是一种噩梦,尤其是发生在沙漠之中的海市蜃楼,如对地形不熟悉的人,很容易因为发现“绿洲”而狂喜,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奔向绿洲,如此几次之后,就会致人精疲力竭,脱水而亡。
沙漠地区发生海市蜃楼对古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但现如今的我们有汽车,有导航,还有北斗系统等,可以尽情欣赏海市蜃楼美景,而不会将其当作不祥之兆。
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将沙漠视为“一神教的风土”。这与埃及学者艾哈迈德·爱敏认为自然环境足以解释众多一神教为何产生于沙漠地区有着相似的观点:
“沙漠地带生物稀疏,无论植物、动物以及人类,都較城市稀少;大部分的地方,差不多没有人类的踪迹,没有壮丽的建筑,没有大的田庄,没有茂密的森林。
沙漠地方的人,面对大自然,目无所障;烈日当空,则脑髓如焚;明月悠悠,则心花怒放;星光灿烂,则心旷神怡;狂飙袭来,则所当立摧。人们在这样强烈的、美丽的、残酷的大自然下生活,心性未有不驰思于仁慈的造物、化育的主宰的。
这,或许可以解释世界上大多数人信仰的三大宗教产生于沙漠地区的秘密。犹太教产生于西奈沙漠,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沙漠,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沙漠。”
佛教,则越过昆仑,穿越干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留下繁星般的洞窟,而在敦煌,则隆起为一个壮丽屋顶,光芒一直到达潮湿的中国沿海和东亚、南亚。
诚如史学家希提所言:“对沙漠居民来说,沙漠不仅是一个可居住的地方,而且是他的神圣传统的守护者,是他的纯粹的语言和血统的保者。沙漠里的人民只要遇到机会就能够汲取别人的文化,这是他们的显著特征。潜伏了好几百年的才能,遇到适当刺激的时候,似乎突然觉醒,一鸣惊人。”(见《阿拉伯通史》)
责任编辑:易清华